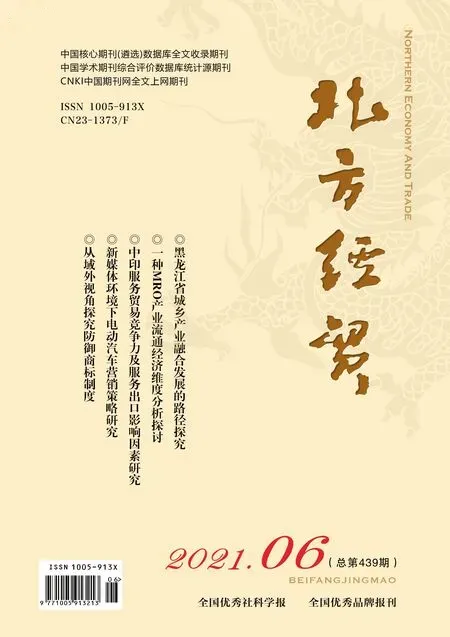主權財富基金的公私屬性與投資者地位
劉 禹,董 洋
(北京工商大學法學院,北京 100048)
隨著國際經濟交往日益頻繁以及全球資本普遍流動,資源輸出國和新興經濟體積累了大量外匯。從20 世紀50 年代開始,各國利用外匯儲備設立主權財富基金進行海內外投資,從而實現豐富外匯儲備和平滑代際等目的。直到2005 年,主權財富基金這一概念才由美國學者洛扎諾夫提出。此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下的“主權財富基金國際工作組”(后為常設國際論壇)對主權財富基金作出了精確定義:為一國政府所有的,出于特殊目的而設立的投資基金或安排;設立時主要考量因素為政府在宏觀經濟方面的目的,主要通過對資產的持有、管理和經營,特別是對境外資產進行投資的方式,來實現金融目標;主權財富基金的資金一般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官方授權的外匯業務、私有化收入、財政結余,以及/或商品出口收益。[1]因此,可以將主權財富基金界定為由國家外匯儲備作出資設立的投資工具。
盡管主權財富基金在海外投資日益增長,但目前大多數的國際投資協定關于主權財富基金等國有實體是否在“投資者”范圍的規定都是模糊不清的。[2]因此,其是否能夠享有國際投資協定中“投資者”的保護和待遇,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公私領域的劃分與主權財富基金的公私屬性
(一)公私領域的劃分
公私領域的劃分以特定行為體從事特定活動為界:國家(包括職能部門和地方政府)和國際組織等行為體發揮治理作用的領域是公領域,具有政治性與規制的屬性。私領域則由自然人、法人、利益團體組成,以合同和利益最大化為基礎。現在越來越多的國家等傳統公權壟斷主體,以商業為基礎參與到全球私人市場來發揮公共權力,完成了自身行為主體的重構,使私領域主體范圍得以擴大。
(二)主權財富基金的公私屬性
主權財富基金已成為本世紀全球治理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了國家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根據權力和治理模式的現實變化來行使主權。從法律和組織形式的角度來看,主權財富基金是國家的產物,由國家完全所有和控制,具有公共目的。但從功能的角度來看,主權財富基金似乎表現更像私人投資實體,參與市場而非規制。[3]因而,主權財富基金連接公私兩個領域,兼具政治和私人屬性,一方面強調商業目的純粹性,遵循市場規律進行投資、參與競爭,另一方面投資行為要符合國家的意志和戰略規劃,這可能會使其母國以威脅現行經濟秩序基礎的方式行使公權力。
二、投資者地位的認定
國際投資法具有促進、保護與管理外資的作用。各國國內的外資法以及各國際投資協定是國際投資法的重要淵源,為投資者提供了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等實體待遇以及國際投資仲裁等救濟途徑。因而,獲得投資者地位,是投資實體依據東道國外商法或國際投資條約獲得保護的前提。
(一)“投資者”條款的規定
“投資者”的概念尚不統一,暫由各國外商投資法或各國際投資協定來界定。以發展眼光來看,明確將國有實體納入“投資者”范圍的投資協定日益增加,逐漸形成趨勢。目前近16%的國際投資協定將國有實體納入“投資者”條款。越來越多的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將“國有企業”明確納入“投資者”的范圍。[4]
對于沒有明確規定“投資者”范圍的條約而言,依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對“投資者”進行解釋時,應當考察該國際投資協定的制定目的,通常會導致對“投資者”概念做擴大解釋。
(二)國際投資仲裁實踐中“投資者”的范圍
《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間投資爭端公約》(以下簡稱ICSID 公約)旨在填補國家間(國際法院等司法或準司法機構解決)或私人實體間(國內法院或商事仲裁等解決)爭議以外的程序空白。[5]雖然ICSID公約未給“投資者”具體下定義,但從其管轄范圍來看,它適用于“締約國和另一締約國國民”。這為“國有實體”在實踐中獲得“私人投資者”地位留下了規則空間。
目前,國際上尚無與主權財富基金直接相關的案例,但因其與國有企業在從事海外投資活動中都被視作“受政府控制的實體”,所以后者的案例在此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例如,在涉及國有企業仲裁申請資格問題的“捷克斯洛伐克銀行(CSOB)訴斯洛伐克案”中,ICSID 仲裁庭指出:“ICSID 公約的制定過程確實表明第25 條的‘法人’(投資者)并不限于私有企業,還包括政府所有、或政府部分所有的公司,這樣的解釋被廣為接受。”有學者甚至推測,即使對于擁有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并宣稱僅存“公共企業”而無營利性國企的美國,也難說它的主權財富基金不具有投資者的身份。
三、主權財富基金公屬性對投資者身份的阻礙
(一)主權財富基金的政治目的
一般認為,私領域行為體是以商業利益最大化為基礎來實施行為的,而主權財富基金的設立和運作只服務于出資人,即國家政府。作為私領域行為體,主權財富基金應只追求其商業目的,并獨立于央行或財政部以確保其不受過度政治影響。[5]
石油經濟的發展、新興經濟體的騰飛促使建立國家資產管理機構的需求不斷增長,而全球經濟危機更是讓國家干預的經濟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普遍適用,主權財富基金應運而生。在國際市場中,主權財富基金的這種行為導致私人企業的生產資料重新收歸國有,主權財富基金母國不僅完成投資行為,還對外推行其外交目標,[6]很可能會將地緣政治利益排在投資利潤最大化的要求之上。
除通過注入資本促進東道國經濟發展、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外,一些國家的主權財富基金采取策略性投資,在東道國重要行業中尋求更高的持股比例,從而獲得控制地位,使得主權財富基金或其母國能夠直接獲得該行業中的核心技術,從而對本國的產業發展進行反哺。但也有學者認為不應因主權財富基金的主權屬性就強化其政治背景,也不應對其自身的投資需求作扭曲解釋。
而主權財富基金的二重屬性,使其在財務管理和投資行為不透明,導致東道國大多難以平衡監管,觸發了發達國家的自我保護功能。部分西方國家甚至指控主權財富基金代表的外國資本可能會對東道國的利益和國家安全帶來極大的威脅。
目前,主權財富基金的母國,多數為長期接受發達國家主導經濟秩序的發展中國家,由于主權財富基金規模不斷擴大,提升了這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上與發達國家博弈的能力。因此,主權財富基金不單純是一種外匯管理方式,而且會成為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先鋒。
(二)對目標企業的“政治政策影響”
目標公司主要利益在于獲得外國資本,特別是來自長期被動投資者的資本以及進入新市場的機遇。相較于會尋求或分享公司控制權的主動投資者,目標公司更傾向于被動投資者,希望維持公司統一的控制結構。為消除自身投資的政治影響,主權財富基金往往會保持其被動投資者身份,在持有該公司大量股權的情況下,也不介入到公司具體運營管理中。
但是,主權財富基金即便是被動投資者,在一些情況下依然可能通過直接控制或施加影響的方式,使目標企業損害自身或東道國利益來實現其利益。[7]以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為例,由于其巨額資本帶來的市場優勢,即使享有的股權相對較少,依然可以影響目標企業的公司治理行為。而主權財富基金的信息優勢更是其他投資者或市場參與者難以獲取的。例如,其能夠通過政府渠道了解其投資項目的競爭者是否陷入訴訟,也能夠對其競爭者直接提起訴訟。主權財富基金運作的長期性使得它們有一定的自由來尋求行使治理和公司權力的方法。
(三)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2015 年《世界投資報告》顯示主權財富基金有100 多家,管理著7 萬多億美元,約占世界各類資產管理機構管理總資產的十分之一。有觀點認為,不管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行為產生什么作用,其成立的前提本身就是全球經濟失衡,如果任由它繼續發展和擴大,無疑會加劇當前不平衡的局面。主權投資是否應當得到支持仍存在爭議。雖然主權財富基金遵循自由市場中投資者的行為方式,但就反映投資者偏好而言,它們允許母國以威脅到現行經濟秩序基礎的方式行使公權力。[8]同時,主權財富基金擁有一般投資者無法比擬的雄厚資本,在進行投資時往往會一次性注入大筆資金,這種投資行為本身就會帶來市場波動,反過來影響金融市場的穩定。
但也有學者認為,東道國能夠通過對資本充足率的要求來承擔這種投資風險,也能通過立法規制杠桿的力量。但卻忽視了主權財富基金不同于一般投資者的主權屬性,一國國家機構不一定能夠直接加以監管,因而關于資本充足率以及風險承擔的要求也不一定能夠加以適用。況且現有的全球金融體系尚未形成針對主權財富基金的有效規范,主權財富基金的監管面臨國際層面上“無法可依”的情況,這將給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更多不確定的因素,也更有可能形成系統性的風險,而主權財富資金在透明度方面的缺陷還將進一步擴大該風險。[9]
四、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者地位
(一)認定投資者地位的“商業行為”標準
ICSID 裁決顯示,所有權和控制因素并不構成國有投資者成為“另一締約國國民”的障礙。在“CSOB 訴斯洛伐克案”中,斯洛伐克認為捷克政府通過持股等方式對CSOB 形成絕對控制,應被認定為國家機構而非商業實體。但仲裁庭認為,判斷企業是否為“另一締約國國民”的標準并非所有權歸屬,而在于企業是否像政府機構一樣進行活動或實質上履行了政府職能。
相比于依據投資實體所有權結構的所有權標準,仲裁庭所采用的“商業行為標準”更符合現代經濟發展。在現代全球市場下,私人經濟力量積聚,私人行為已蔓延至公共領域。盡管國際市場強調投資者的私人屬性,但私人并不完全是以盈利為目的進行投資的行為體,也有可能是基于政治目的或其他非商業目的。比起原有的跟自身利益直接相關的、低層面領域,私人實體參與的政治領域逐步上升到間接相關的、涉及更高層面國家內部調整的高層次政治領域中。[10]大型公司越來越多地監督它們所參與的市場,并對東道國產生政治影響。跨國公司更多通過兼并或收購的方式,對東道國國內的某些行業形成控制,以商業舉措向東道國政府施壓。
因此,“私人投資與公共投資的傳統區別即使未過時,也已毫無意義”,應從企業與政府間的實質關系來確定企業是否屬于國家投資者。如果企業充當的是履行政府職能的工具或者是政府代理人,那么就認定其為“國家投資者”。
至于主權財富基金的這種被動投資是否會產生政治影響,有學者圍繞一些樣本進行數據匯總分析后,得出一致結論:起碼從短期來看,主權財富基金的被動投資行為就算對目標企業產生了影響——不論是不是政治因素帶來的,也基本是短暫的積極影響。[11]從國際實踐來看,尚未出現主權財富基金援引主權豁免原則來逃避處罰的情形。對于東道國法院,主權財富基金是商業實體,不能援引主權豁免原則。[12]
(二)私領域的非商業目的
投資者作出一項投資通常出于商業、公共或是政治目的。采用“商業行為標準”認定主權財富基金投資者身份,面臨的問題是投資者怎樣的目的會阻礙商業行為的確定。目前廣泛認為若投資實體不是商業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則不能認定其投資是商業行為。但具有商業目的的投資者同樣可能會對東道國或國際市場造成政治影響,公共目的下的投資未必不符合商業行為。私領域行為體在參與私人市場的同時,正承擔越來越多的社會責任。跨國公司需要對東道國的可持續發展負責,主權財富基金等國有實體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主權財富基金投資行為是資產循環的體現,增加市場活躍性,帶來就業崗位增多、技術進步等有利作用。[13]主權財富基金不同于一般的投資者,長期存在于投資市場,周期較長,對沖本國對某些商品價格依賴的風險,其投資往往帶有逆周期的性質,這無疑會為金融市場帶來穩定,減少價格波動。隨著規模進一步增大,主權財富基金將成為全球股票和債券市場最大的參與者,也可能是影響力最大的購買者,這將有利于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性。[14]盡管主權財富基金在金融危機中受到較大影響,但不影響其仍將持續為全球金融市場帶來積極影響。
因此,主權財富基金無謂好壞,對其作用的評估應從其投資動機入手。如果主權財富基金是以營利或社會責任為投資目的,那么其投資特性和投資策略能夠帶來穩定金融市場的作用的。但如果是以政治動機作為投資目的,就會使得資產價格在有意的投資策略選擇中被扭曲,加劇市場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