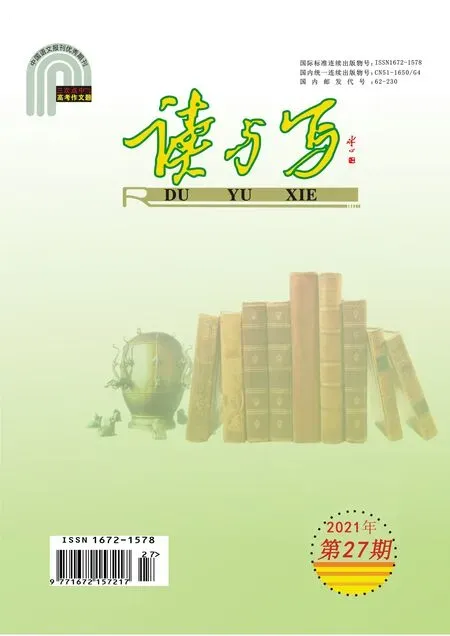高中冷戰史教學再思考
——冷戰史新研究與教學淺思
潘 偉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級中學 湖北 利川 445400)
高中歷史新課改的一個重要理念就在于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它要求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促進學生的個性發展,從而形成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同時符合時代對人才素質的要求。因此現在的高中歷史教科書在對新的課程標準進行解讀時,應當充分尊重史學前沿的觀點與熱點問題,從而推動高中歷史教學的發展。事實上,隨著新史學觀的不斷涌現,許多歷史問題已經出現一些新的解釋;隨著史料的不斷更新和挖掘,許多既往的結論已經受到新的史料的挑戰與質疑。倘若將這些新的史學研究的成果都拒之于教科書之外,必將嚴重束縛學生的思維跟上時代對歷史的解釋以及探究精神,這與新課標“理解和尊重世界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傳統,汲取人類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進一步形成開放的世界意識和國際視野”[1]的要求也是相抵牾的。然而令人擔憂的是,新課標教科書的這一變化,一方面是并沒有引起中學教師的強烈關注,在平常的歷史教學中沒有關注最新的史學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在教材研討和教材輔導資料等著作也鮮有提及,這使得教師忽視了最新學術爭鳴的問題所在。如果一線歷史教師能夠主動、積極地汲取學術爭鳴的新成果,將它們引入課堂,啟發學生對歷史問題的思考,從長遠來看,將學術爭鳴的問題與研究成果引入教科書這一行為,對高中歷史教學是大有裨益的,它不僅體現了教材編寫中多視角、多層次的特點,而且為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同時,中學教科書在編寫中將最新研究動態引入教材,可以規避教科書的保守與滯后,使教材的形式和內容更為生動活潑,符合課程改革的長遠趨勢與學生能力的養成。當然,“我們也應當注意到,對于史學研究中的學術爭鳴,不能簡單地做一個拿來主義者”[2]。因為高中歷史教科書畢竟不同于一般的學術專著,教科書的編排還涉及到學生的認知規律問題,故而合理、有序的知識結構體系也是至關重要的。
冷戰是存在于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出奇特的景象,美國著名的外交史學家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Jr)將其稱作“近代歷史上的荒謬插曲,漫長的、代價高昂的、黑暗陰郁的、危險的事件,是人類最接近于集體自殺的一次經歷”[3]。其發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持續近半個世紀的時間終于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宣告結束。冷戰史在中國的研究一直備受矚目,隨著冷戰的終結,現今的冷戰史研究“大力倡導開展‘冷戰史新研究’(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即在冷戰結束賦予研究者的全新時空框架內,利用多國多邊檔案,掙脫“美國中心”論的羈絆,重點關注“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并重新認識意識形態在冷戰中發揮的作用”[4]。雖然冷戰史研究出現了新的形勢,但歷史學家對冷戰史的進一步研究并未停止,有學者便“截取近十余年中國冷戰史研究的某些片斷,從新領域與新問題、新方法與新路徑、外國檔案文獻翻譯整理三方面展現中國冷戰史學界研究的新氣象”[5]。可見,現在的冷戰史學術研究已經在2007年最新版的人教版高中歷史教科書發布后,出現了很大的進步。反之,既是現在的高中冷戰史教師教學和學生學習如果完全按照現今歷史教科書的內容教學和學習,已經落后于現在的最前沿的冷戰史學術研究。要想在歷史教育教學中彌補這一差距,首先便是清楚它們內容上到底有怎樣的差異,然后在日后的教學設計中進行相應的彌補。
冷戰史研究的權威學者約翰·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于 1997 年在其代表作《我們現在知道了:冷戰史再思考》一書中提出了“冷戰史新研究”這一概念。冷戰史開始滋生出“新冷戰史”(the New Cold War History)的萌芽。 此后,隨著理查德·勒博(Richard Lebow)、梅爾文·萊夫勒(Melvyn Leffler)與加迪斯的論戰的開始,“冷戰史新研究”這一概念也逐漸進入研究者的視界,引起了各國冷戰史研究者的廣泛關注。“冷戰史新研究”成為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發展潮流和前進方向。[6]至于冷戰史新研究是什么含義,陳兼教授和余偉民老師說過“冷戰史新研究不是一個在國際關系史學科之中可以清晰地進行界定的學術流派,也不是一個新的學科,而是一種由來自不同國家、屬于不同領域的學者們通過一系列個案研究以及相互之間的學術交流、討論而產生的學術現象。”[7]對于冷戰史研究學者們所歸納的冷戰史新研究而言,我認為是一個非常廣泛的概念,冷戰史新研究所呈現出來的特點也是多種多樣的,例如研究冷戰的研究者視角,研究資料檔案的運用,歷史學科與其他學科的綜合運用等。我在對高中歷史教學研究過程中,主要涉及高中歷史教材的內容分析,重視文本和理論研究相結合,故而為了與我所確定的論文研究視角相切合,我主要查閱冷戰史新研究中就冷戰史研究內容、學術觀點方面的資料。現在,冷戰研究的視域不斷拓展與進步。目前“很多研究超越了傳統外交史,更越過對‘新冷戰史’最初較為狹窄的定義。把‘新冷戰史’界定為后冷戰時代的冷戰史研巧雖然寬泛,但似己舍此無他”[8]。新冷戰史的研究越來越呈現跨學科的態勢,從原有的將軍事、外交作為重點研究的國際關系領域逐步延伸到各國的思想文化、國家安全機制等為重點的更深層次的研究。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研究與冷戰結合衍生出經濟冷戰史、社會冷戰史等新的研究課題。此外,學者們開始對美蘇以外國家在冷戰中的角色給與更多關注,尤其是不發達國家。冷戰的概念從多個層面被極大地擴充了,它不再局限于國際關系與外交史的邊界,采取更加全面、多元的研究路徑,將傳統的冷戰研巧問題與經濟、文化、社會、科學等因素相結合形成全新的冷戰史課題。[9]“在這種潮流中,關于冷戰的問題意識和具體研究在向著舊的學科觀念所不能容納的更寬闊、更豐富、更深刻的多個方向推進,而不能包容多樣性、復雜性的精確性和確定性已不再是這個研究領域里的領袖人物和大多數成員的智識倫理和學術追求。”[8]這種全球史視角“拓展了冷戰史研究的問題領域與史料來源,通過更新研究視角與分析路徑,描摹了更為豐富復雜的冷戰歷史圖景。雖然其學術價值還有待后續研究檢驗,但確實代表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新方向”[10]。在此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當屬于2010年由萊夫勒、文安立主編,多國學者參與編撰的《劍橋冷戰史》三卷本,它被認為代表了目前冷戰國際史研究的前沿水平。[11]在今后對高中冷戰史教學和冷戰史學術前沿研究進行對比探討時,就將以此為主要的參考文本。在此,可見新冷戰史研究在內容上相較于之前的冷戰史內容已經豐富很多。同時,隨著人們對冷戰史研究的深入,之前的部分史學觀點也已經出現了變化,畢竟一切歷史均是現代史,隨著社會壞境的變化,人們對歷史的解釋也會出現相應的變化,這也需要進一步的更正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