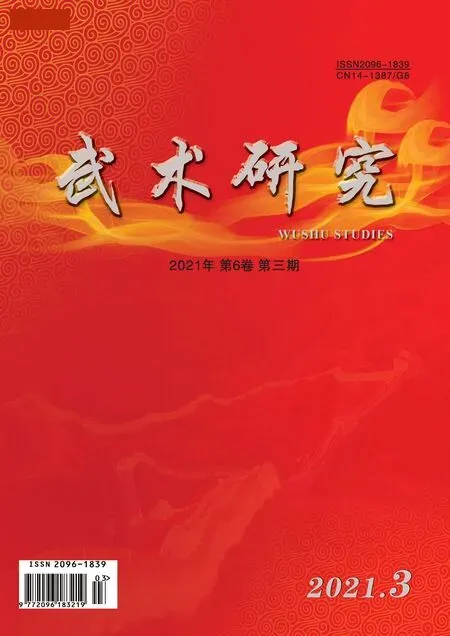武術的演藝傳承
陳 青 閆士芳 馬 威 馬振磊
河北體育學院 武術系
武術從冷兵器戰場下退役之后,轉戰于為鏢局、演藝、授徒等戰場。能否在這種新的戰場上立足,同樣需要具備高超武術技法水平。其中,武術演藝作為能夠滿足民眾娛樂之需的內容,在社會文化生活中備受世人關注,是武術退役后的主戰場。武術演藝者的專業演藝水平決定著他們的生存狀態和武術技法的傳承程度。
1 演藝的傳統
劍被刀取代,劍由軍用轉入民間普及發展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學劍、擊劍之風很是盛行。曹丕在《典論·自敘》中稱:“余又學擊劍,閱師多矣,四方之法各異,唯京師為善。桓、靈之間,有虎賁王越善斯術,稱于京師。河南史阿盲背與越游,具得其法。余從阿學之精熟。”曹丕自豪地講述了比劍經歷:“嘗與平虜將軍劉勛、奮威將軍鄧展等共飲,宿聞展善有手臂,曉五兵,又稱其能空手入白刃。余與論劍良久,謂言將軍法非也,余顧嘗好之,又得善術,因求與余對。時酒酣耳熱,方食芊蔗,便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展意不平,求更為之。余言吾法急屬,難相中面,故齊臂耳。展言愿復一交,余知其欲突以取交中也,因偽深進,展果尋前,余卻腳剿,正截其顙,坐中驚視。余還坐,笑曰:‘昔陽慶使淳于意去其故方,更授以秘術,今余亦愿鄧將軍捐棄故技,更受要道也。”這是“一對一”的擊劍記載,與軍事戰爭的劍法不同,可進行比賽,更可觀賞,與先秦擊劍相比,技術、戰術已有發展。轉入民間的武術依然保留著濃烈的格斗意向,秉持著技法的精湛較量的水平,同時開始顯露演藝的苗頭。曹魏時出現了“力士舞”類的演藝內容,《魏書·奚康生列傳》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生乃為力士舞,及于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殺縛之勢。”[1]這是武術在尋求新生存的空間的表現,沒有想到的是這種趨勢一發不可收拾。
無論是將軍還是舞者,武術演藝都是顯示武技水平的重要方式。據《獨異志》記載:裴旻將軍為吳道子表演時,只見他“走馬如飛,左旋右抽”“擲劍入云,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悚栗。”可見,其高超的武技演藝水平。公孫大娘作為開元盛世時唐宮的舞者,舞“劍器”聞名于世,贊美之聲流傳至今,大家耳熟能詳。
宋代中國的市民階層的出現,有了濃厚的市民娛樂生活需求,武術演藝當之無愧地占據了一定市場。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崇、觀以來,在京瓦肆伎藝:小兒相撲、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俎六姐。”“駕登寶津樓,諸多諸軍百戲呈于樓下。樂部復動《蠻牌令》,數內兩人,出陣對舞,如擊刺之狀,一人作奮擊之勢,一人作僵仆。出場凡五七對,或以槍對牌、劍對牌之類。”[2]能夠在大庭廣眾的眾目睽睽之下,尤其是在皇上面前表現武術,必須有好身手。沒兩下子,可是要掉腦袋的。
連闊如在《江湖叢談》中記載了近代掛子們走鏢、護院、賣藝的故事,其中走鏢時“無論來了多少綠林人,全瞧鏢師的‘尖掛子’(受過訓練的練把式賣藝的人)‘鞭上’(打的)如何了。若是鏢師憑‘尖掛子’把綠林人驚得扯活啦,然后,還得叫伙計各處‘把合(看)’到了,防備賊人藏起來。”護院是鏢局漸趨慘淡后的新產業,護院一點也不比走鏢安逸。“若是雇傭四五十歲的人,那全是上過道(他們管走過鏢說行話叫上過道)的,只要上過道,他的武藝錯不了,經驗閱歷一定豐富。如若遇見黑門坎的人,不用動手,幾句話就能把他說走了,永不來偷。”賣藝也不輕松,“掛子行的人將地打好了,到了游人最多的時候,師徒們扛著刀槍靶子到了地內,將刀槍架子支好嘍,不能凈說不練,得先大嚷大鬧的招來人看,調侃兒叫詐粘子。等人圍著瞧啦,才能連點小套子活兒,把人吸住了,四周圍得里三層外三層,才算粘子圓好了。圓好粘子,就得使拴馬樁兒(用話留你,讓你走不了),用話將圍著瞧的人們全都栓住了,沒有走的人啦,才能看可看的把式哪!”[3]在過去,習武人真的不容易,自己要練得好,還要掌握產業營銷的技能。
時至今日,習武人更加的不容易,社會文化活動日趨豐富,習武人欲在社會找到一片天地,專業技能自不多言,需要借助新媒介,新途徑尋找立錐之地。在習武人苦苦尋覓中,武打影視為習武人打開了一扇窗,李小龍、成龍、李連杰、吳京等充分地借助新媒介實現了武術新跨越。可是,這種途徑只能允許個別的知名運動員、演員入圍,廣大的習武人難以躋身演藝圈。面對這種情況,習武人自然不甘落伍,除了參與各級各類的競賽,他們通過諸如《風中少林》《武頌》《少林武魂》《盛世雄風》《武林時空》《競藝武術》等功夫舞臺劇和專業競賽等形式,以中國武術為重要元素而創作的藝術成果,是武術深入挖掘自身的文化潛質,豐富自身的表現形式,形成完善的創新體系的舉措。對此,馬文友、邱丕相甚至認為武術的藝術性很可能遮蔽武術的技擊性而成為其主要外顯特征。
從這些故事中,我們看到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就是武術自古至今,武術演藝是一種武術重要的存在形式,武術演藝具有悠久的傳統。
2 武術演藝的競技
武術技法應該包含兩部分組成:一是隨意活動,大多屬于原始的武術元素;二是成型技術,為傳統武術的主體。紛繁的原始武術元素有益于傳統武術素材的積淀,但是無益于武術演藝,更無益于直接推動傳統武術發展和傳承。成型的、嫻熟的、精湛的、自動的技術是武術演藝的重要依托,能夠直接促進傳統武術延伸和傳承。
武術演藝是有習武人有意識地運用專門的身體技術去完成特定任務的武術表現形式。[4]在武術演藝中,武術演藝者主要是以身體行為為主體。身體行為包含著各色的武術技術,當成熟技術出現了明顯的意向性,技術完善成體系后,技術又有機構成了武術演藝的專門身體行為。身體行為具有意識嵌入、內容廣泛、形態各異、完整系統、明確目標等基本屬性的人體活動。身體行為明顯別區于肢體活動,是構建在肢體活動基礎上的凸顯內在意識、專有方法、明確目的的人體活動。武術演藝中的身體行為包含著突出的專業性身體素質、技術規范、運動內容、特定目標等技術成分。專有技術是載體,專有技術完成著將意識與行為目的相銜接,使意識指向并落實于目的之上,實現目標相關任務。《呂氏春秋·劍伎》云:劍技乃“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表明了劍術是武術演藝者使用長度有限的劍,用“短兵長用”意識,借助“倏忽縱橫”短兵技術,實現長兵的技擊效果。此刻可以清晰地看到,短兵靈活的技術是“短兵”連接“持短入長”的載體,“倏忽縱橫劍走青”演練風格是區別于其他拳種特殊身體行為表現能力的技術中介。可見,始終保持拳種固有的“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陽”技術技巧,可防止身體行為因為缺失技巧的專業技術性維護,而出現“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唯有當技術技巧被根深蒂固地納入身體行為,身體行為便會保持長久的、特有的身體控制能力。試看,《說劍》:“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后之以發,先之以至。”之技巧,方得“劍使之家,斗戰必勝,得曲城越女之學。”(《論衡》)之行為表現。的確,技術與身體行為的高度關聯中也存在著不可相互替代的差異,技術是局部具體的,身體行為是整體系統的;技術是慣習性的,身體行為具備明顯的指向性的;技術是人的客體活動,身體行為是人的主客體合一的;技術是生物技能的,身體行為隱含著社會文化的人體活動。
如何使武術演藝的身體行為滿足民眾的娛樂需要,實現自身的生存發展,關鍵在于身體行為的狀態,這種狀態可以使用現代學術用語,即競技狀態。競技狀態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武術演藝身體行為的水平。如果從競技角度分析,競技是一種為了自我、相互抗衡,經過長期系統習練儲備起來的身體控制能力。在運動訓練學中重點強調競技是一種技術動作的自動化程度,當技術動作熟練到一定程度,技術表現出較高的自主、自如狀態。在武術演藝中除了這種基本屬性外,更有特殊的身體抗衡、協調、控制能力。抗衡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繁雜,遠不只為一種競賽活動,競賽僅僅是一種外顯的抗衡方式,但不是唯一。相互的抗衡可以比較明顯地表現出競爭的色彩,與競賽活動的表現形式相似。武術演藝的競技是一種被人們忽略的競爭,在這種競爭中,不僅需要自我的抗衡,也需要與演藝的同伴或對手進行抗衡,更有與觀眾的互動抗衡,這種抗衡對武術演藝者來說難度更大,在前述的例子中可以鮮明地看到圓粘子、拴馬樁兒過程的艱辛和技巧,當下武術演藝者如何搏得觀眾隔空式的票房認可,除了噱頭,更為關鍵的是演員的技術競技狀態,以及個人技術、人格魅力的影響,無人否認李連杰、吳京出色的武術專業功底才是幫助他們確立為武打影星地位的關鍵。由此看來,武術演藝同樣是一種競爭、競技,是一種與單純的體育競賽活動不同的,形式更為豐富的競技。
3 懸置是競技的核心能力
武術演藝者的身體控制能力,主要表現在在自我抗衡。武術技術體系異常的繁雜,加上眾多的拳種,以及拳種的各異風格,武術演藝者必須在掌握武術基本功的基礎上,通過悟性,精確地掌握某個拳種,出神入化地表明拳種的風格。在這種自我抗衡過程中,武術演藝者的技術向著日趨嫻熟、精湛、高超的方向邁進,逐步達到了游刃有余的身體控制狀態,此刻武術演藝者具備了應有的競技狀態。在這種競技狀態的背后是十分重要的武術演藝者的懸置能力,這種能力是身體控制能力的一種。只有武術演藝者能夠懸置技術,完全沉浸在演藝之中,方可說達到了“應有的”競技狀態。比如,裴旻擲劍入云,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這種狀態,已經完全將拋劍與持鞘承之技術熟練到無需丈量,無意專注如何承之,而將精力灌注于走馬如飛的迅疾利索表現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庖丁解牛,故事中說道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庖丁置牛、刀于不顧,而是“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這就是典型的技法懸置。時至今日,在武術影視演藝中,這種懸置得到了現代科技的幫助,武術演藝者完成不了的技法,可以通過科技手段實施,武術演藝者只需關注影片的情節表達,可以懸專業技術于不顧。這種情況導致了武術影視脫離于現實,誤導習武愛好者,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武術傳承的一種阻力。在現場的武術演藝中,這種情況可就沒有這么樂觀了,必須依托于武術演藝者可見的身體行為懸置能力,通過高超、嫻熟、精湛的武術身體行為在懸置技術中,實現了對技術的超越,展示了對人的本質力量的表現,實則是有效促進武術生存的關鍵所在。
身體行為的懸置能力是身體控制的重要構成,是達到競技狀態的核心環節。老子主張“道”要“絕圣”“絕學”“棄智”要“滌除玄覽”。老子認為“能無疵乎”的經驗和成見就像蒙在人們心靈上的灰塵一樣,妨礙了人們對于真知的認識,必須保持內心直觀鏡子的清潔。采借老子的理論,可以從中看到,武術演藝者的技術動作中必然保留著大量的,類似于經驗和成見的技術成分,比如技術慣性,對技術意向的認知等等,這些內容雖然有益于技術體系,但是同時也存在有塵埃效應,阻礙著武術演藝者對精細技術的掌握和表現。需要對此進行“滌除玄覽”的懸置,防止思維惰性、身體惰性、技術惰性等所衍生的遲滯和倒退。莊子進一步告誡人們在特定情境中將自身利益置之度外,將過分的欲望化諸無形,以“忘其身”“墮形體”等超脫身體桎梏,實現高遠目標。《淮南子》進而闡述順乎自然必須“不治而治”“達于道者,反于清凈,究于物者,終于無為。”[5]老莊等思想提供了充分發揮身體行為之競技僭越須至懸置狀態的邏輯基礎。
武術演藝者的身體行為更受制于除了技術之外的思維、意識和心理等內部因素影響,比如武術的尊祖,凡是祖上傳下來的技法是不容改變的,這種意識嚴重地制約著武術演藝的水平。前文中提及的各色掛子們的圓粘子的路數和套話如出一轍,難出新意,掛子們認為這是傳統。殊不知這種思維方式忽視了觀眾們的感受。到了當下,武打影視的故事情節也百變如一,一點一滴的小事兒便開打,而且打斗貫穿始終不可開交,似乎人的血肉之軀是金剛之體,這種情況并不符合人際互動的常理,即使在先前走鏢的鏢師們也多是靠智慧避免武力沖突。這種情況更不符合暴力沖突的實際,根據研究暴力的專家柯林斯的研究表明:“事實上,正是雙方互相關注之下所產生的緊張感,才導致這種內在的矛盾。面對面沖突會激發腎上腺素的分泌,并制造出緊張感;對此,我們能夠從人們的面部表情與身體姿態中看出端倪。隨著心跳上升到每分鐘140次以上,人們在舉槍瞄準等精細動作上的協調性會出現下降,當上升到每分鐘170次以上,人們的感知會變得一片模糊;當上升到每分鐘200次以上,人們就可能會動彈不得。”[6]通過這種理性分析,我們看到實際的打斗就是短短的幾招,之后人的生理限度將人困住,而且人是非常脆弱的,幾招之后便會結束打斗。另外,人們始終認為武術就是以技擊性為本質的,這種一成不變的意識和思維使習武人面臨著無窮的窘境,也使得武術演藝者無論是影視、舞臺劇、競藝競賽中清一色的武打場面。如此看來,這種塵埃式的內容需要滌除,需要主動地使用懸置之法。
關于本文涉及的懸置,采借于胡塞爾為了追求純粹,對前人的知識予以懸置后的自我辨明,從而在這樣的方法中獲得相應的“洞見”品質,[7]強化“洞見”能力,以此進行事物還原,用中立、存而不論的自然態度,對事物進行本真的純粹研究的“懸置”措詞。本文的技術動作、身體行為懸置與哲學中的“滌除”“忘身”“無為”和懸置在有意無意地忽略身體行為方面有一定關聯。然而,本研究中懸置概念舍哲學懸置之還原,求武術演藝的技術動作懸置之進取,重自如懸置專門技術之能力,以期演藝不為技術羈絆之本。認為身體行為懸置,就是武術演藝中的身體行為控制能力已經達到了駕輕就熟、無需特別關注的全自動運行狀態。懸置是身體行為的競技狀態的高級表現形式,不僅反映技術完備程度和技能成熟程度,更是身體所具備的高度自主、有效控制其行為的能力。當擁有這種控制能力的人,嫻熟地運用身體行為去完成各種有較高難度的任務時,他們根本無需考慮如何運用各種具體的技術動作,身體行為是實施各類目標的助力而非阻力。如同演講人不會關注舌頭如何運動一樣。只有達到這種狀態和擁有這種能力,武術演藝者的身體行為就處于競技狀態。但見,只有身體行為達到了懸置狀態,方可身械合一,演藝者方能如《劍俞》所云:“劍為短兵,其勢險危。疾喻飛電,回旋應規。武節齊聲,或合或離。”身法回旋、劍法飛電、起伏開合、節奏輕快怎能不“俞,美也。”拳種演藝達精至湛,懸置技法、競技自如便備受稱頌:“進退疾鷹鷂,龍戰而豹起。”“如亂不可亂,動作順其理,離合有統紀。”(傅玄《矛俞》)“手盤風,頭背分。電光戰扇,欲刺敲心留半線。纏肩繞脰,耈合眩旋。卓植赴列,奪避中節。前沖函禮穴,上指孛慧滅,與君一用來有截。”(陸龜蒙《矛俞》)[8]
在中西體育文化中,身體行為的懸置能力和類型不同,大體上可分為單獨的和復合的身體行為懸置兩種能力和類型。胡塞爾在提出了懸置的概念后,發現世間不存在絕對的懸置,人畢竟在“生活世界”中生存,所以在生活世界中的人在看待世界的時候必然附帶著相應的“視域”,[9]這種客觀存在影響著人的身體行為懸置狀態。在西方主客兩分的文化氛圍中,身體行為與主體難以作為有機體整體來懸置。身體行為作為人們進行競賽活動的手段,被人們高度重視,始終被作為改造的對象,身體行為日趨精細完善,并成為專業的獨立體系。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固存著合一的意識,天與人、人與物、內與外、知與行等合一決定了人的主客合一傾向,身體行為復合地運用在社會活動中,很少單獨地專門地用于體育競賽、演藝,身體行為更傾向于對人教化與娛樂,身體技能不是主體首先關注的對象,身體行為缺乏必要的空間和氛圍形成細化、特化的獨立技術體系。在“忘我”語境中,身體行為跟隨主體一同懸置則更加徹底。兩種文化追求的終極目標更是大相徑庭,西方競技體育是以挖潛為主,中華民族體育則以養育為主,不同目標對身體行為的利用明顯不同。為了實現挖潛、競爭,需要精湛的技術,必須練就高超的身體行為,并能夠在特定時間段內隨心所欲地保持高度的身體行為懸置,階段性的懸置能力十分強大。娛樂、養生是一個悠哉的終生過程,無緊迫的時間要求,娛樂、養生彌散于生活之中,然娛樂、塑生之重任,乃人生之浩大工程。為了有效地完成娛樂、養生,特別是養生更需要意向性控制、專門性技能,且需強化身體行為的緘默、滌除羈絆,以“忘身”“墮爾形體”[10]的懸技娛人、塑生形式自如踐行。悠閑的娛樂追求、悠緩的養生效應促使身體行為形成身心合一的終生性懸置能力,實施生命塑造的身體行為來不到的半點虛假和偏差。武術演藝者立足社會,其身體行為懸置能力,也須具備高度精細的競技狀態,“功夫”的武術演藝是常人在短時間內難以掌握的。不然,武術演藝便成為人人唾手可得的技能,而非寥若晨星的精英專利。
4 武術的演藝傳承
精英式的武術演藝專利,可以概括為嫻熟、精湛、高超的技術,化作容意識傾向、任務目的為一體的身體行為,自如、自在地懸置能力,表現出高層次的競技狀態,在實施自娛、他娛的目標時,表現出曲高和寡的地位,受世人仰慕,不經意間有效地傳承著武術文化。《夢梁錄》記載宋代市民們觀賞武技表演時,武術演藝者們首先是“先以女飐數對打套子,令人觀睹,然后以膂力者爭交。”由此看來,套路類型的演藝格外引人注目。武術演藝必須具有高超的水準,才能發揮引人注目的效果。觀眾雖然明白這是非技擊的表演,但是演藝者要有逼真的表現能力,《清稗類鈔》記載:“兩兩揮拳,雙雙舞劍,雖非技擊本法,然風云呼吸之頃,此來彼往,無隙可乘,至極迫時,但見劍光,人身若失,為技至此,自不能不使人顧而樂之。”逼真的演藝,可以將觀眾帶引特定的場景,產生共鳴,生發愛好,由此使得這類武術演藝得以代代相承。為了能夠達到這種狀態,成為武術演藝精英,站穩社會地位,演藝者必須勤學苦練。必須經歷“三膘三瘦”的形體變化,勁始入骨,又須經“三伏三九”的刻苦磨煉,勁始歸根。王宗岳概括為“招熟”“懂勁”后才能達到“神明”狀態。萇乃周則也強調:“煉形合氣,煉氣歸神,煉神還虛”是武術演藝者習武的三部曲。其中的“神明”“歸神”包含有懸置色彩,“還虛”更強調懸置能力。練到這種“功夫”,要經歷“三年一小成,十年一大成”的漫長過程,越是見功夫的文化,越能被世人所珍重。在這些精英武術演藝者們出色演藝,給觀眾以強烈的視覺沖擊,留下撼人心魄的印象,感召人人習武。這種途徑和氛圍使得這種個體,或者是集體記憶逐漸擴充至節慶、演藝等文化事項中,成為文化記憶的有機構成,被世人銘記在心,習練隨身。
武術個體、集體記憶尚不足以長久傳承,須將個體和集體記憶向文化記憶轉移。“有歷史研究者指出,交往記憶的傳承一般在三到四代人中延續,40年是一個重要門檻,80年是一個邊界值。從‘交往記憶’傳承來看,超過了80年的上限,就會進入到揚阿斯曼所說的‘文化記憶’的狀態。”[11]在梅洛-龐蒂看來,身體是具體的自我所能夠看見的表現,身體與文化記憶類似于自己的右手觸摸左手,都是主客合一的身體記憶,相互的轉化易如反掌。競技化的身體行為有效地將傳統武術的身體記憶、集體記憶向前推進,優雅地跨越了記憶時間門檻,成為文化記憶,代代相承,始終與國人相伴,成為中華民族歷史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正是“凡是曾經有記憶的地方,就該有歷史。”[12]在當下,武術演藝這種特殊傳承形式,更應充分地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實現優勢互補,保障武術文化傳承。
呵護武術演藝市場,是延續武術傳承場域的合理選擇。呵護武術演藝精英,是傳承武術文化的必然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