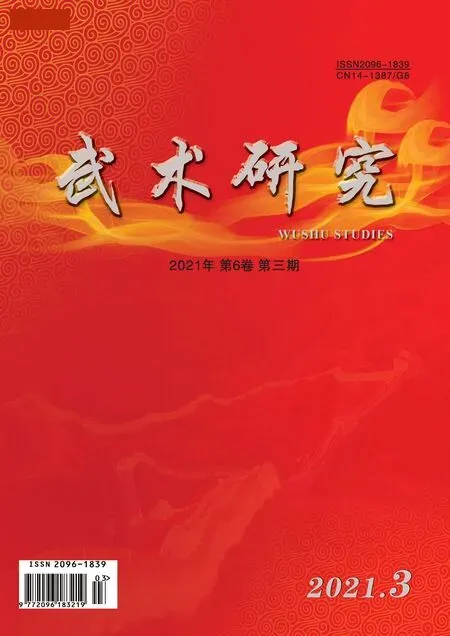試論馬氏通備武學育人思想的四個要素
姜存喜 陳海東
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1
1 前言
“武學”一詞的概念在古代和現代社會隨時代的要求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古代武學多指古代兵學和武備學校武學。而現代武學是由馬明達提出具體的概念并得到其他人的廣泛認可和效仿。馬明達將現代武學的概念定義為現代武術的學科體系。它不同于古代的兵學,又不同于古代武備學校的武學,而是一個既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又具有一定創新意義的學科概念。[1]他還強調是一門擁有龐雜的技術體系和理論體系的傳統學問,特別要注重武術文獻學系統的建立。武術學是多學科交叉的學科,需武術要不斷加強與相鄰學科的關系,已達到跨學科整合研究的狀態。[2]這就要求馬氏通備武學需要培養注重以武術文獻學為理論依據并重視技術體系實踐的通備人才。因此,通備學子需要不斷提升練、讀、打、寫的四個基本素養以實現通備武學文武兼備的思想。
2 馬氏通備武學育人思想的四個要素及其關系
通備武學吸收顏元、戚繼光、唐豪等人在武術學術和技術方面的成就和貢獻。其中潘文學, 倡言“通神達化, 備萬貫一;理象會通, 體用具備”之說, 以“通備”二字為拳派命名, 其精神或直接源自顏李, 或受到過顏李的影響。[3]通備武學踐行者馬明達認為:自古以來,歷史學與武術學之間就具有多學科交叉整合的特點,互為補益。不然不成為“學”。在練習技藝時,需要通過研讀武學書籍和史學等書籍來印證練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這就需要用打來進一步驗證。寫是通備武學在掌握現代學科與現代科學方法的學術性研究,是對練、讀、打的更深一個層次的提煉。因此,通備學子應該不斷提升練、讀、打、寫四項基本素養以實現通備武學所倡導的文武兼備的思想。
首先,“練”是最初始也是最基礎的體悟。通過不斷的練習可以體會技術動作是否具備可行性。如果一味的談理論而不去身體力行的感受,那就是紙上談兵。戚繼光的《拳經》中講到:“拳打不知。”“拳打不知”不是通過臆想就會憑空出現。它需要通過長期反復地練習后達到一種自動化的狀態。馬氏通備武藝中的劈掛拳的特點是猛劈硬掛、大開大合。這些技術的完成要求需要單劈手的練習來實現。單劈手是起點,是需要反反復復、貫穿始終的內容,是功力訓練的內容,也是技戰術訓練內容。[4]它既是劈掛拳基礎也是劈掛拳的核心。如果只講理論而脫離了練習,就會失去檢驗理論對依據。因此,理論的正確與否都需要親自實踐去檢驗其可行性。
其次,“讀”是對練的提煉和校正也是激發思考和判斷的基本途徑。“讀”可以使最初通過身體實踐感知的技術動作進一步鞏固和完善。比如短兵運動中最基礎、使用最多的直刺技術,這可以在書本中尋找其中的合理性。其一,自古以來中國就有單手使用短兵器的傳統。其二,西周到兩漢的創造了豐富的劍文化,這一千多年的鼎盛期中不光有著高超的擊劍技術也出現了關于劍的專門著作。“讀”的過程中不光是深化直刺技術的過程,更是觸類旁通、刨根問底的探尋與直刺技術相關的文化知識的過程。“讀”的過程就是不斷完善自身對武術認知和思考的過程。比如,了解宋代的棍棒武藝發展狀況以便更好的理清古典武藝基本史實。還有戚繼光的軍事著作《紀效新書》看到關于選兵、實戰演練這些武藝中必不可少的智慧元素。因此,要深入了解武術自身的文化和歷史,也要辨別武術著作真偽的同時去潛心探索歷史、哲學、文學中所蘊含的武術文化。
再次,“打”是武術本質屬性的體現。在現代社會中可以表現為散手、短兵或者射箭等對抗性項目,其目的在于保證武術對抗項目的完整性和系統性。在“打”的過程中要嚴格遵循競技運動公開、公正、公平的普世價值觀。民國時期的中央國術館已經初步建立了的國術體系,它們包括拳術、短兵、長兵和摔角等運動項目。國術體系的建立有利于推動武術技擊性的發展。通備武學正在努力使民族傳統體育對抗性項目短兵、射箭、散手等項目復興和發展。因此,通備學子應該通過對抗項目中的實戰、比賽等形式來培養“打”基本素養。
最后,“寫”是對身體與思想在不斷沖擊、內演后的延升。寫不只是自我思想表達重要依據也是后世認識和了解武術的重要途徑。胡適先生在《中國人思想中的不朽觀念》中提到了三不朽觀念,即立德、立功、立言。他指出:“這古老的三不朽論,它賦予了中國士大夫以一種安全感,縱然死了,但是他個人的德能、功業、思想和語言卻在他死后將永垂不朽。”[5]立言的作用在于將一個人的思想通過文字的形式進行表達而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應。
明代的戚繼光、俞大猷、程宗猷以及近代的唐豪那些文武兼備的武術家們留下的那些寶貴的武學資料成為認識和研究武術的依據和資料。戚繼光的《紀效新書》、俞大猷的《劍經》、程宗猷的《耕余剩技》以及近代唐豪的《少林武當考》和《中國武藝圖籍考》都為武學發展留下了可供參考的武術史料。唐豪先生面對大量怪力亂神的寫作風氣卻始終能從武術史實出發,苦心追尋和探索為開創武術史學科確實有著可貴的貢獻。寫的能力對通備學人是至關重要的。如何在低迷混亂武術發展現狀之中找到武學的發展方向和動力是至關重要的,寫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致力通備武學研究的馬明達在武術和歷史方面古典文獻的整理研究方面有著突出的貢獻。1984 年點校本明代戚繼光《紀效新書》20 萬字,1995 年校注《中國回回歷法輯叢》160 萬字,1996 年出版的《中國回回歷法輯叢》 獲甘肅省委和省政府頒予的三等獎,2000 年出版輯考本的《潮汕金石文徵》25 萬字,2006年出版《中山市明清檔案輯錄》140 萬字,2015 年出版了《中國古代武藝珍本叢編》,近年先后發表了《論武術古籍和民族體育文獻學的建構》《吳殳著述考》《中國古代射書考》等論文,這為“民族體育文獻學”提供了珍貴的參考史料。通備武學積極踐行者馬明達正以身體力行的方式為通備學子樹立榜樣。因此,通備學子需要順著前人的足跡不斷地吸收古典武學中的養分才能保住使現代武學的更加富有底蘊和內涵,同時要不斷吸收不同學科的知識才能使現代武學的豐富和絢爛。
因此,一個武術工作者必須具備的立言的基本能力才能更好推動“寫’在通備武學育人過程中的價值和意義。寫在最初表現為主觀的好惡,但是通備武學在育人過程中更注重明確的邏輯思維,掌握現代學科與現代科學所普遍倡導的科學研究方法的學術性研究,是對練、讀、打更深層次的提煉和凝結。
總之,作為一個通備學人必須兼顧練、讀、打、寫四個基本素養。這對于通備學子綜合能力提出了艱巨的挑戰。這對于通備學子來說要以通過身體的練并進行針對性的讀來踐行學術并重的育人理念,打是對技術和理論一致性的進一步驗證而寫是對練、讀、打的提煉和總結。兼顧四項基本素養確實不易。在繼承和發展通備武學的過程中要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要有所偏重的同時也要全面提升四個基本的素養。練、讀、打、寫四個基本素養相互融通、緊密結合才能減少走上學術分離的道路。通備學人應該根據自己的特點和優勢發展一項或兩項自己的專長再兼顧其他素養,既要有偏重也要兼顧。經過時間的積淀,才能養成通備武學所需要的基本素養。
3 對馬氏通備武學育人思想的價值分析
馬氏通備武學中蘊涵文武兼備的思想要求通備人在實踐過程中要求練、讀、打、寫四個基本素養的全面提升。這四個基本素養所反映出來的育人思想既符合古代士人育人的基本思路,更是與當代素質教育的基本思路一致,這就是通備武學中的育人思想合理性的體現。在未來發展中通備武學育人的價值需要不斷地在繼承中創新以適應時代發展需要。
3.1 與古代士人育人思想相符合
在中國古代,讀書人被統稱為“士”。“求道”是他們的第一追求。[6]曾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這說明古代對士的教育是很注重道德、品質的培養。士人的理想追求、價值觀念、生活情趣、社會品位,無不受到自身品格的支配。品格與“人品”“人格”相通,是指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由其行為所反映的精神面貌。在中國古代士人的品格建構中,最突出的特點是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憂患意識。[7]受“學在官府”體制的影響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較為完善的學校教育體制以及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主體的教育內容,極其重視道德教育,以“明人倫”為其核心,培養統治階級需要的治術人才。[8]“禮”以倫理教育為主,政治、道德、生活方式的教育,士人往往追求嚴于律己、尊君愛國等傳統精神品質。“樂”指的是倫理教育又是美學教育。“禮”和“樂”緊密相連、互為表里,貫穿整個社會生活活動。“射、御”基本上是軍事體育教育。“書”指的是文字,“數”指的是算法。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為主體的教育注重士人綜合性和全面性能力的培養。
綜上,“六藝”教育中包括多方面教育因素,它既重外在的禮儀規范,也追求內心的倫理道德的培養;即重視文化素養的培養,也重視實用技能的訓練;這是文武并重、諸育兼修的一種綜合性教育的表現。通備武學中的育人思想同樣也注重全面性、綜合性的提升,通過對打、練、讀、寫四項基本素養的培養來提升對武學的認知的能力。可以看出,它們是不同個體對受教者綜合性和全面性的素養的體現。
3.2 與現代素質教育中的育人思想符合
素質教育就是要使人各方面的才能、興趣和特長全面發展。素質教育強調全面發展人的德、智、體、美、勞等素質。1957年2月,毛澤東在其文章中就明確地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9]這對于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改革開發以來,人的全面發展理論不斷在實踐中完善和發展。鄧小平認為,精神文明建設就是為了讓全體人民“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10]在2018 年9月10日,全國教育大會在北京召開,習近平提出我們的教育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11]并在此次全國教育大會上指出要進一步將勞動教育納入了全面發展教育的素質規格的范疇。[12]勞動教育納入人全面發展的范疇說明了在不同時代和背景下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有了新的要求。
綜上,隨著時代的發展對人的全面發展的素質要求變得更加全面和細致。素質教育既要貫穿幼兒教育、中小學、高等學校的各個階段,也要貫穿于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各個領域。有學者提出,不同目標層級定位和不同表述方式的理念是教育目的的時代意蘊和行動演繹,素質教育是教育宗旨的中國式表達,“三維目標”和“核心素養”則是對全面發展教育和素質教育在不同層級目標體系的深化、繼承、演繹和超越。[13]在實施素質教育,必須根據不同的個體進行相應的德育、智育、體育、美育、勞育等在教育活動。通備武學根據武學體系的建立、理論與實踐性聯系強、學術分離等因素的基礎上,提出要培養練打讀寫四位一體的通備人,從而更好的推動通備武學的發展。
4 結語
練、打、讀、寫的基本素養實際是當代通備武學發展過程中學術并重的體現。鐘敬文先生曾經說過:“一般人只問治學之術,其實光有術不行,首先得有道,有道必有術,有術卻不一定有道。[14]馬明達先生非常贊同和支持鐘敬文先生的觀點。馬明達認為“學”是科學,是系統化的理念。他將當代武學分為六大部分,它們分別是由技藝、義理、文獻、器具、文藝、醫藥六部分組成。這六部分構成了立體結構,像金子塔的形狀。塔基是技藝、文獻,中層是器具、文藝、醫藥,頂端是義理,是武學的思想。在這六部分可以偏項也可以兼項。六項兼通即為不易。它的全面性要求全面掌握武學確實需要巨大的付出和心血。當代武學的發展就是將這六項緊密結合,堅守在本土體育的土壤里,理直氣壯走自己的路,獨立發展,自成體系,經過時間的檢驗,通備武學的價值將發揮它的作用。通備武學的發展要求通備學人具備練、讀、打、寫四位一體的綜合能力。這是對通備武學自身的完善和發展的必然要求。通備武學的發展對整個武學體系的構建將產生獨特的效果和作用。
總之,通備武學在育人過程中注重專注性、綜合性、全面性多元一體的人才培養。通備武學既吸收古代士人教育注重倫理道德的優良傳統也注重現代教育過程中素質教育的主體的適用性。在繼承的基礎上進行不斷地“揚棄”發展通備武學。通備武學在發展遵循中國古典武藝實踐和理論相結合的傳承模式。可以預見的是,通備武學會繼續成為最具活力的中國傳統武術流派,甚至成為相應的學派,通備的技術發展會繼續與時俱進,不斷吸收科學的訓練和思維,但同時,得益于對武術研究的固守,通備也具有更強的文化本位主義情懷,因此更容易表現為具有中國傳統武術文化特質的現代中國流派。通備學子應主動承擔責任,固守武術研究,心存強烈文化本位主義,從而構建出具有系統、科學通備武學體系,最終,通備武學也將成為當代武學體系的構建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