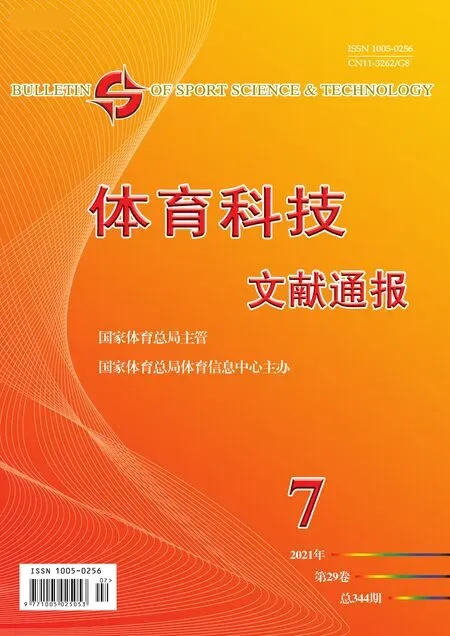“ 停課不停學 ” 背景下大學體育在線教學方案窺探
艾安麗
“ 停課不停學 ” 是教育部針對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保障青少年生命健康安全做出的緊急部署,教育部提出延期開學,印發了《關于在疫情防控期間做好普通高校在線教學組織與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各個高校積極應對,疫情期間大學體育究竟應該如何實施?筆者通過對網上公布大學體育在線方案的22所高校進行資料收集,對防疫期間大學體育在線課程存在的問題進行深入剖析,并針對相關問題提出了相應的策略,為后疫情時代改進大學體育教學提供參考。
1 大學體育在線課程教學方案存在的問題
大學體育在線課程教學方案是響應教育部《關于在疫情防控期間做好普通高等學校在線教學組織與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而臨時性制定的方案,[1]通過百度網頁以及進入相關高校體育部網頁查找,共查詢到北京大學、上海財經學院、韶關學院等22所高校大學體育在線教學方案,涉及教學指導思想、教學方式、教學內容、教學評價和教學管理等內容。
1.1 大學體育在線課程教學指導思想不明確
《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明確指出 “ 體育課程是大學生以身體練習為主要手段,促進身心和諧發展,德育、生活、體育技能和身體活動有機結合的教育過程 ” 。突如其來疫情導致 “ 停課不停學 ” 通知出臺,大學體育在線課程指導思想是應該照搬傳統線下課程?還是應該更加有針對性?北京大學提出了 “ 標準不降低、學習不停頓、研究不中斷 ” 的指導思想,上海財經大學最開始認為實踐課課程不適合線上開展,面對疫情來勢洶洶暫時無法恢復上課的現實,制訂了與北大方案相同的指導思想,目標為 “ 增強學生體質、平緩學生情緒、緩解焦慮以及提高免疫力 ” ;四川大學提出了 “ 緊急圍繞全程關愛、全面育人 ” 的目標,桂林旅游學院同之;其余18所學校制定方案中均未提出明確的指導思想。
1.2 在線學習平臺互動缺乏臨場感
“ 互聯網+ ” 時代的在線學習撬動了體育教師角色轉變,從傳統的體育知識傳授者、動作示范者、道德培養者、意志磨煉者轉變成為學習設計者和促進者。[2]盡管在線學習平臺形式多樣,比如國家級教學平臺,愛課程(MOOC)、智慧樹(知道APP)、超星泛雅(學習通APP)、對分易、雨課堂等,校級服務平臺如韶關學院綜合服務平臺、 “ 云大體院 ” 微信公眾號、川大創高體育APP、北財體育公眾號等,專門的運動APP,如步道樂跑、Keep等,互聯網社交平臺如微信、QQ等。無論哪種平臺,線上學習都存在空間屏幕相隔,時間上信息傳輸延緩,在線體育課程更是將三維立體局限于二維平面,學生很難從中體驗到身體臨場感。[3]
1.3 教學內容體能技能分化,輕健康知識
大學體育教學內容涉及體能、技能和健康知識。調研得知,疫情期間大學體育教學內容主要包括四種形式,一是以身體鍛煉為主,如華南理工大學采用步道樂跑,主張學生居家鍛煉,四川大學采用川大創高體育APP推送身體專項練習的圖片、動圖或者視頻,云南大學、浙江大學、大連理工學院等鼓勵居家鍛煉,每天鍛煉一小時;二是限定學習項目內容,如浙江大學限選《太極拳初級》《體育舞蹈之拉丁舞》,同時提供八套強身健體操,韶關學院要求全校學生不分年級、統一限選《瑜伽》《太極拳》《健美操》三個項目;三是理論+運動技能限選+身體素質,比如云南大學采用慕課《體育與健康》、對場地器材無要求簡便易行的太極拳、體育舞蹈或者健美操為主要內容,輔以自重力量、有氧耐力、柔韌練習等內容;四是按照常態大學體育課程內容安排,比如北京大學充分發揮體育育人作用,倡導 “ 完全人格,首在體育 ” ,由最初組織專家編制有北大特色課程方案,便于學生宅家抗疫,四周一個階段逐步持續改進,最終開設35個必修運動項目,著重于專項課程的基礎訓練。可見,教學方案設計教學內容出現體能、技能分化,缺乏 “ 健康 ” 內容的融入。
1.4 學習效果評價缺標準
調查得知,12所學校提及評價方式,但沒有提及評價依據,提及評價的類型主要集中于評價的百分比:(1)平時成績30%+期末考試70%比例,如內蒙古科技學院,平時成績分為理論學習階段,太極拳組合學習階段,每個階段學習按照10分計算,共30分,線下學習70分計算;(2)上網次數和時間(30%)+作業(5分鐘練習視頻)30%+到校后考核40%,韶關學院采用上網學習時間記錄、作業完成以及到校后考核40%進行計算,沒有明確線下課程與線上課程的百分比;(3)532結構,如四川大學課堂教學效果50分,疫情期間居家鍛煉效果考核30分,在線慕課學習20分進行評價;(4)在線學習與線下學習各占50%,如浙江大學春夏各占50%,身體素質練習簽到,對每次練習的基礎心率和即可心率要求進行測試,學會自我醫務監督,掌握自己的健身鍛煉效果;(5)提及考核標準有體育部統一制定,如西南石油大學提出返校后對教學效果進行考核,這樣的評價方式完全沒有針對性。1999年中共中央提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2002年教育部推出《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倡導評價方式、評價內容、評價主體多樣。而目前大學體育在線課程評價依據不明確,方案中評價標準模糊。
1.5 教學管理重形式
全國教指委發文要求監督在線課程教學質量,保證 “ 線上課程教學質量標準不降低 ” 。調查得知,只有1所大學提出了學校、學院和教研室三級督導管理的要求,其余21所學校均未對教學管理提出具體要求;具體操作層面,學校教務處注重學生的出勤率,要求各二級學院提供學生出勤率統計表,一周一匯報;學院層面,只要按照學校教學計劃開課即可,對教學監督較少;教師層面,一是通過教務系統導出學生作業查閱考勤;二是由任課教師根據學生打卡或者上交作業記錄到班群進行學習監督。
2 改進特殊時期大學體育在線課程方案的策略
2.1 加強研討,明確特殊時期在線教學指導思想
“ 健康第一 ” “ 學生中心 ” 是大學體育課程的指導思想,也是防控背景下的主導思想。《全國普通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教學指導綱要》明確指出:增強體質、增進健康和提高體育素養是大學體育的目的。健康教育是大學體育(《體育與健康》)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健康知識應對防疫特殊時期正當時,增進健康的適量運動可以提升免疫力。[3]防疫期間,健康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廣大民眾甚至扒出鐘南山院士八十多歲依然精神抖擻源自中學時代就愛好并堅持體育運動。 “ 學生中心 ” 是以學生發展為中心、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以學習效果為中心的 “ 新三中心 ”[4],即成果導出導向(簡稱OBE),在線大學體育課程建設應以此為導向,響應 “ 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 ” 中 “ 共建共享、全民健康 ” 的戰略,為全面健康奠定扎實基礎。[3]
2.2 加強體育教師信息化水平,豐富教學平臺資源,變革教學方式
防疫期間學習健康知識正當時。隨著MOOC時代到來,互聯網+教育的普及,建設在線課程,利用互聯網平臺,推動教學資源如視頻、動圖以及在線文本、圖書、PPT等都需要體育教師教學信息化水平的提升,選用、管理教學資源,提供豐富的教學平臺資源,滿足學生健身愛好的需要,彌補學生健康知識的不足。在線學習過程中教與學的行為時空產生異位,人機學習環境缺乏學習者與教師之間以及學習中之間的面對面交流與互動,導致在線交流情感缺失。[5]在線大學體育也應該針對遠程教學進行設計,課堂結構一樣應該存在課的開始部分,教學過程與課的結束部分。
采用對分課堂[6]教學模式。第一步,將整節課分為先建立學習群,然后將學習群分為若干學習小組,便于生生互動;第二步教師作為主播講解學習要求、學習主要內容,關于動作示范教師可以直播,也可以采用錄播,還可以推動視頻;第三步,學生自主學習,自主鍛煉,內化吸收;第四步,小組成員之間分享學習成果,探討學習重點和難點;第五步,教師抽查小組同學學習情況,也可以自由發言,展示動作,詢問難點,最后教師答疑解惑,布置課后作業。對分課堂教學模式既可以采用當堂對分,也可以采取隔堂對分模式。這種教學方法很好解決了線上課堂對分問題,將線上與線下混合學習相結合。
2.3 制訂科學合理的評價標準,加強教學監督
評價在線課程課程資源。課程資源是否符合國家標準?是否經過專家團隊進行審核?是不是適于大學生疫情期間 “ 適時適地 ” 開展?是否教給學生充分利用課程資源?是否保證了課程資源的多樣性和有效性?
評價教師的教學。對教師教學設計是否合理,教學計劃是否科學,教學準備是否充分,教學過程態度是否認真,教學效果學生是否滿意需要制訂出考核標準,并且定期安排學校、學院教學督導進行聽課和檢查。
評價學生的學習。評價大學體育在線課程學習應該從知、情、意、行等多個方面進行。首先,(1)從學生網上簽到打卡來考查學生的學習參與;(2)從學生的自主練習、課堂展示來檢驗運動技能;(3)從學生的課堂提問、小組討論來檢驗學生參與熱情和積極性;(4)從學生課后作業來檢驗學生的學校效果和鍛煉習慣。其次,要明確規定大學體育在線學習的總體分數,可以采用 “ 一個基準兩套方案 ” ,線上學習與線下學習的百分占比,以及每次考勤、自主練習、課堂互動以及課后鍛煉的百分比以及制訂依據需要明確,只有科學合理的教學評價標準,才能對學生學習起到檢查、監督和反饋的作用。
3 結語
疫情防控期間,政府、社會和高校共同實施并保障 “ 停課不停學 ” ,大學體育在實施過程中有些高校認為不適合開展在線教學,有些高校匆忙制訂方案,考慮不周全,對教師沒有進行充分培訓,漏洞百出,形式主義盛行。在疫情防控期間,大學體育在線教學應該分時段邊教學邊改進, “ 一個標準兩套方案 ” ,讓線上教學與線下教學混合搭配,逐步培訓教師信息化水平,為大學體育教學、促進大學生健康發展奠定較好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