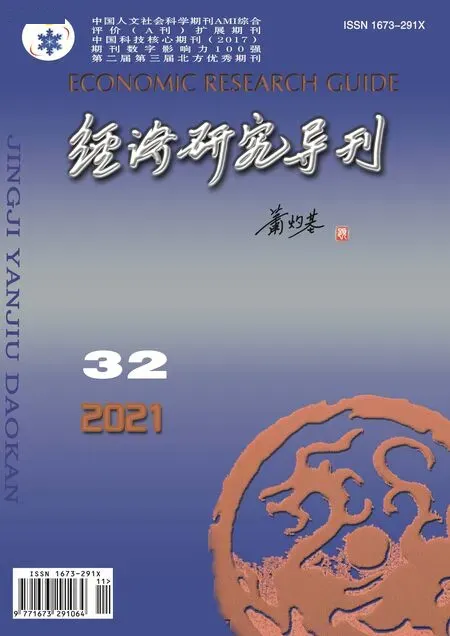新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思考
孟慶吉
(嶺南師范學院 法政學院,廣東湛江 524048)
隨著人口的增多,城市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發展重心,而關于市域治理日益成為現代國家治理以及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命題,衡量一個國家的法治水平時,市域治理情況是一個重要參照。就我國而言,從國家到地方,在習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論述以及黨和政府的各級會議推進下,有關市域治理,黨和政府對相關工作提出明確要求、作出戰略部署。“加快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第一次出現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議文件,“加強和創新市域社會治理,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再次得以明確。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緊緊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總目標,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以共建共治共享為導向,以防范化解影響安全穩定的突出風險為重點,以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平安創建活動為抓手,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這集中凸顯了市域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有效的市域社會治理將各種資源下沉到基層,不但為城市居民提供更好的精準化、精細化服務,還可以及時發現各種風險隱患,以便將矛盾在基層解決。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要發揮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作用。法治是新時代市域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價值所在,也是衡量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尺度。法治對城市現代化發展的貢獻比率日益成為現代城市發展進步的重要保障。很難想象,在失去法治依托的城市能夠實現治理現代化和文明發展。
一、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含義
從漢語構成來說,所謂“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也就是在“市域”范圍內實現治理的現代化。對于“市域”的理解和把握需要抓住以下三個要素。
(一)設區的城市為市域社會治理的主要載體
“市”作為中國行政區劃的概念源于1921年的《廣州市暫行條例》,其第三條規定:“廣州市為地方行政區域,直接隸屬于省政府,不入縣行政范圍。”“市”也是法律概念和政策概念。實踐中,主要是通過行政層級來定義來進行“市”的分類。中國社會結構脫胎于農業社會,縣域治理自秦漢以降就是國家治理的重心。但時至今日,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新的矛盾類型,縣域經濟及文化的包容性是遠遠不及城市的能量的。隨著中國城市人口的集中、經濟力量的高度集合使得風險的積聚和擴散帶來的重大考驗,時代和發展的現實也讓城市成為市域治理的必然選擇。
(二)市級層面應主導市域社會治理
如果從各級行政單位的分工來看,我們國家的三級行政體系可謂各有其責。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者當然是國家層面,下面的區縣則當仁不讓地成為政策和法律的執行者,這種定位符合我們國家的現行行政管理體系。那么出于中間環節的“市域具有承上啟下的樞紐作用。市域對上承擔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責任,對下指導基層一線工作,是推動基層治理的組織者、領導者。抓住了市域這個關鍵環節,就可以起到“一子落而滿盤活”的效果。”[1]從現代城市發展來說,市域治理的中心環節是不可替代的,通過整合行政資源,通過“市-區(縣)-鄉鎮(社區)”構建一個權責明確、上下協調、靈活運用的有效提高市域治理的核心價值將達到一個完善的治理體系。在各級黨委的領導下,社會和人民大眾形成一個多元主體融合共治的社會治理體系,從而推而廣之,在法律規則的指引下,形成市域范圍內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三)城區為市域社會治理的重點
隨著“以人口由鄉村向城鎮、由欠發達地區向發達地區遷徙為主的特征鮮明的人口流動大潮”,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帶動了中國的城市化已經不可逆轉。隨著人口規模的迅速膨脹,“鄉土中國”正日益發展為“城鎮中國”。[2]城市的發展也會帶來種種問題,各種矛盾不斷出現,對于市域管理帶來極大的挑戰。既然要建設“市域治理現代化”的城市體系,就要求工作中心和重心向城市空間轉移,充分調動市一級管理的協調統籌能力和資源及技術優勢,集中精力發展城市,從而帶動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從而最終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綜上,“市域治理現代化”并非單純是為了發展市域的治理,其戰略目標在于以市域治理理念的現代化、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帶動全部中國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法治化、專業化和智能化,即以點帶面,通過調動全社會的資源和力量,逐步推進實現既定的國家治理目標。
二、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化需求
截至2020年末,我國城鎮常住人口約90 199 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63.89%[3]。“五治”在市域社會治理中各有分工,其中法治的協調作用毋庸置疑,其獨有的治理功能無可替代。首先,法治為市域社會治理供給了基本的運行規則,法治原則通過明確市域治理的參與主體、各方參與主體的權力界限、治理方式等可以確保市域治理在法治軌道上有序進行,保障法治的正確道路。其次,社會問題紛繁復雜,涉及的利益群體更是相互交叉,多頭治理與交叉治理現象也是司空見慣,諸多問題內在聯系需要法治確定的秩序規則抽絲剝繭、細致梳理,以此保證公民和社會組織有序有效參與社會治理。
所以,市域社會治理脫離法治的軌道是不可想象的,唯有正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處理市域社會治理中的“痼疾”,才能保證社會安定有序且充滿活力。“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只有全面依法治國才能有效保障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規范性、協調性,才能最大限度凝聚社會共識。”[4]易言之,法治是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與重要內涵。
三、新時代下市域社會治理法治能力的短板
市域社會治理由空間范圍、行動主體、治理手段、治理目標四個要素構成,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化包括治理空間法定、治理主體適格、治權運行合規、治理手段合法、社會公共產品供給均衡、公共服務分配公平,以及解決社會矛盾糾紛的法治程度等方面的內容。但現實問題是,新時代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目標雖然納入了各級政府的規劃,可是作為治理現代化重要內涵的法治化水平卻亟待提高。
首先,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延續,社會多元主體間的利益紛爭逐漸加劇。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發揮群團組織、社會組織作用,發揮行業協會商會自律功能,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夯實基層社會治理基礎。”然而“社會組織參與基層社會治理既要依法進行,也需要法治保障。”[5]由于法律制度上的缺失,使市域社會治理僅局限于政府,行政化色彩濃重,難以形成治理主體多元化格局。
其次,政府權力界限不明致使政府依賴程度過高。在社會矛盾糾紛解決機制方面還存在過度泛化、過度濫用等問題。政府承擔著社會管理職責,作為唯一的社會治理主體,政府極易過度干預,其依靠所掌握控制的資源優勢及行政職權,對社會事務進行寬泛而細致的管理,發揮大家長作風,大包大攬,政府的手伸的越長,其他社會治理主體的雙手便被壓縮的越短而失去施展的空間,政府則因背負包袱太重,陷入疲于治理,越治越多的現實困境。在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過程中,因為理念轉變不到位,在處理社會事務、化解社會矛盾的過程中,手段簡單粗暴,不顧及對社會公眾的合法權益保護,行政權高于公民權的思想依然盛行。政府機關履行行政職權時,隨意改變既定規則,通過批復、批示等形式對具體的社會治理事務進行干預。此種做法在一定情形下有利于快速、高效解決問題,但卻脫離法治框架預設軌道,容易引發公眾對法治的不信任感。由此,又可能導致市域社會治理對政府依賴程度過高,以致拓寬了行政權力對社會治理的邊界。而追求行政效率的內在誘因又催生了不合規不合理的治理亂象,尤其體現在征地拆遷、公共秩序管理等領域。行政權力的強硬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社會組織、公民參與社會治理的空間,治權沖突主要體現在行政機關與社會組織的治理邊界或治理權限問題之上。行政機關對行業規則的過度調整勢必會影響行業自治權的發揮。因此,市域社會治理的治權邊界有待進一步明晰。
最后,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是優化社會治理的重要形式,是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現代化、變管理為治理的重要措施,對提高社會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促進作用。但我國目前的公共法律服務供給能力并未達到市域社會治理現代化的應有標準。例如,對公共法律服務體系的內涵和外延認識過窄,服務內容不清晰,服務質量和服務效果無標準,服務界限不明確,沒有提高到市域社會治理的站位上謀劃全局,對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支持力度不夠,公共法律服務缺位的現象隨處可見,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體制機制、財政保障及制度保障不甚健全等等。
四、新時代市域社會治理法治水平亟待提高
事實證明,脫離法治力量的市域治理無異于空中樓閣。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是城市現代化的不二之選。但是,我國對社會治理體系和法律體系正處于發展階段,尚有諸多領域需要探索和加強,諸如城市文明、城市應急體制、城市綜合協調發展等多個領域仍然需要不斷努力和平衡,市域治理非朝夕之功,其若沒有“定盤星”,則有失衡的可能。為化解城市社會矛盾,我們需要提供妥當的法治框架,為實現市域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建立健全地方立法制度
按照《立法法》第72 條的規定,我國設區的市擁有一定范圍的地方立法權。與國家立法權相得益彰的地方立法,其更接地氣,更能有的放矢地對每個城市給予恰如其分的法律表達,更為直接和有效地實現城市依法治理。圍繞城市管理、生態環境、社會民生等重點領域,應充分發揮市域立法的探索性功能,地方立法可以更為自主性和創制性,通過具有地方特色的立法破解社會治理難題,從而將市域治理納入法治進程。①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深化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紛機制建設推動矛盾糾紛源頭化解的實施意見》(法發[2021]25號)。
(二)確定公權治理的外在界限
現代法律表明,沒有萬能的政府,政府需要依靠看不見的手在調控社會資源,政府不能事無巨細,否則就會掛一漏萬。政府需要通過法律法規以及穩健的政策維護來為社會經濟發展搭建舞臺,為其他社會主體參與社會治理提供有效的空間。也就是說,“推進城市治理創新,需要打破政府唱‘獨角戲’的格局,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參與城市治理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6]
(三)建立完善系統治理制度開展訴源治理和矛盾糾紛多元化解工作
“要堅持把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挺在前面”。在各類解紛方式中,訴訟可以說是最費時費力、成本最昂貴的[7]。要改變“喜訴”和“好訴”的格局,高效利用司法資源,將社會力量用于化解社會矛盾。但這不是說要游離于法律之外去解決問題,相反,我們更需要法律思維,更需要依靠現代技術,依法采用多種方式方法調處社會矛盾,并且及時加以經驗總結,將零散的經驗進行整合,加以制度化和理論化,升華為社會治理制度。
(四)塑造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文化
觀念的轉變素來是從少部分人開始的,法治的觀念也是如此,有時候很多人達成共識,但還會有人冥頑不化。在一些機關,副職轉變了,但正職沒有轉變;有時候群眾轉變了,但是領導不同意;也有時高層轉變了,基層卻無法推動;有時候部分地區轉變了,但還有一些地區停留在非法治的思維,并把它當做主流和常態而閉目塞聽。這仿佛一條河流里總有干燥的石頭,河流的方法便是默默地沖刷,并且讓石頭之間進行摩擦,從而將大石頭打磨成小石子,小石子打磨成沙粒,把封閉的小循環割裂開來,最終讓每一顆冥頑不化的石頭都感知到法治的洪流力量。社會和法治的進步就是通過觀念競爭——代際更替——持續影響等幾重機制最終實現的[8]。
(五)堅持和完善落實市域社會治理法治責任工作機制
首先,黨的地方委員會在本地區法治建設中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黨的地方委員會在本地區要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按照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對本地區法治建設實現全面領導。地方各級黨委法治建設議事協調要加強對本地區法治建設的牽頭抓總、運籌謀劃、督促落實等工作。其次,黨政主要負責人要履行推進市域法治建設的第一責任人職責。市域各級黨政主要領導要認真履行職責,堅持在法治軌道上推進社會治理,督促各級領導干部在法治之下想問題、做決策、辦事情。市域管理者必須帶頭厲行法治;領導干部要習慣在法治軌道上、監督環境下用權做事,嚴格按照法定權限、程序履行職責行使權力。通過在法律的框架內行使權利,達到權為民所用。同時,要建立督查督導機制,實施市域社會治理法治建設的專項考核,定期對各級領導干部責任進行督查,確保市域社會治理的法治建設得到有效的符合標準的落實。應當依據黨內的法規,建立健全領導干部法治工作的效果檔案,將社會治理法治化作為黨政綜合考核的重要參照。黨政主要負責人應該起先鋒模范作用,在市域治理中率先垂范,對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推進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職責的,應當根據《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等有關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法規予以問責。
——評《中國現代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