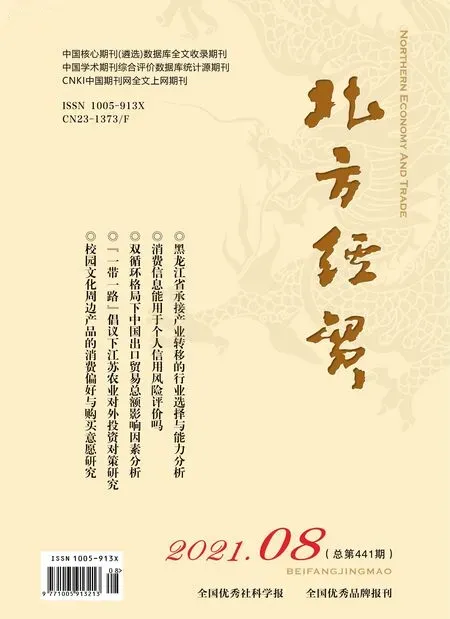“一帶一路”建設與金融服務創新
王春梅,李 畫,王春黎
(1.齊齊哈爾大學a.科研處;b.馬克思主義學院,黑龍江齊齊哈爾161006;2.南通大學化學化工學院,江蘇南通226019)
一、前言
“一帶一路”旨在將古代“絲綢之路”歷史印記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融合,“一帶一路”將陸路、海洋貫通起來,在陸路,以國際大區域為中心,以沿線核心城區為合作伙伴,打造多條經濟合作線路,在海上,建設安全便捷的海上運輸線路,相關政策逐步推進,與之配套建設逐漸深入,致力于構建歐亞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共享,建立與沿線各國伙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元化、綜合性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周圍各國自主、自由、健康、可持續的發展。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推出8 年以來,得到周圍沿線國家的認同、參與和構建,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打造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合作區域與領域不斷拓展,新的商業合作模式不斷嘗試,開發包容合作原則,這一切都與金融服務分不開。“一帶一路”倡議為推動全球經濟一體化快速發展,深化國家間金融合作,促進沿線地區間金融服務創新、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一帶一路”建設與金融服務創新密不可分,主要表現在:一是亞洲大部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仍由金融機構貸款驅動,如蒙內鐵路、卡拉奇—拉哈爾高速公路、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站等;二是沿線國家貿易融資需求不斷擴大,在能源、資源及產業結構等方面需金融機構融資,如中亞天然氣管線鋪設、孟加拉希拉甘杰用電項目等;三是由于外部投資環境風險大及基礎設施投資項目風險性使得對于保險服務業務的需求,跨國公司對于員工生命財產安全的保障需求,金融機構的保險產品受到關注,主要是能源、石油天然氣、運輸、醫療、發電等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公司;四是跨境金融業務日益增多,積極探索建立雙向金融監管合作模式,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主要對地區基礎設施投資資金需求進行測算。金融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支撐,為金融服務創新發展和國家金融機構間合作提供了機遇與挑戰。
二、“一帶一路”建設為金融服務帶來的風險與挑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金融服務行業由于其專業性、普惠性、自由化逐漸成為知識密集型、技術為核心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托條件。隨著金融服務類型不斷豐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來往越來越密切,金融服務規模不斷提升,但由于金融服務構成上存在不平衡現象、產品更新緩慢、出口逆差等情況,因此,要加大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溝通與合作,消除金融貿易壁壘,力求在更高層次上進行合作與交流。
(一)金融合作機制不健全
由于國家政策的扶持、金融機構積極參與和金融合作逐步推進,促進資金融通,由于金融合作缺乏監管機制,導致區域范圍內金融合作效果不夠理想。主要表現在:一是合作意向臨時性、程序不夠嚴謹、項目選擇隨意性、政策把握不夠精準等因素,出現金融融資配置效率低,承擔巨大債務風險的情況;二是金融服務體系整合不到位,由于傳統金融機構資金持有力度有限,面對金融產品和服務需求差異較大現狀無能為力,各國金融服務多以政策性服務和開放性指導為主,商業性金融、社會資本及服務型金融機構參與度不高,多層次金融資本仍處于觀望階段或待開發階段,金融市場運營程度有待開發;三是金融合作“走出去”顧慮比較多,[2]“一帶一路”旨在通過沿線國家合作,推進經濟發展,構建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經濟發展新格局,實現全球經濟快速健康發展,這一舉措勢必會觸動持貿易保護主義為核心觀點的某些經濟發達國家的利益,使得金融合作面臨來自經濟發達國家的某些金融限制政策;四是“一帶一路”沿線一些國家還處于徘徊猶豫階段,不同國家間經濟政策及市場波動等因素,商定協議由于一些因素在簽署前、項目進展中被暫停、中止、取消的情況時有發生。如,英國核電工程在簽署協議前一日由英方單方面叫停;緬甸水力發電與海港碼頭基建項目進展過程中由緬甸單方叫停;印度地緣戰略學者布拉馬·切拉尼利用個人影響力發表“中國將馬爾代夫帶入債務陷阱的言論”,嚴重影響中國與南亞國家“一帶一路”合作項目的正常進展。
(二)“一帶一路”沿線區域金融服務存在差距
共建“一帶一路”秉持開放區域合作共贏精神,促進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經濟要素有序流動來實現沿線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打造區域經濟合作體系。區域金融服務需要一整套復雜的服務模式,不僅僅需要融合區域范圍內各種資源和匯集數據資源信息,還與內外部資源共建共享、互通交流、采集存儲等環節息息相關,環境、資源、信息、人才、產業集群等均是區域金融服務能力提升的關鍵因素。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歷史沿革、經濟基礎、產業結構、政策等不同,國家間金融服務水平存在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國家金融服務存在差異和不健全,缺乏信用風險、統一監管、法律協調合作機制、政治風向標一致性等要求,金融服務僅停留在政策性協議、合作溝通、友好意向等層面。[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貫穿亞歐大陸的65 個國家和地區,占世界人口60%,這些國家和地區大多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有些國家金融服務水平相對較低,導致金融資源在“一帶一路”沿線存在分配不平衡現象。如,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摩爾多瓦等國家由于一些歷史原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金融服務水平也較低;中國與馬來西亞、泰國、印度等東南亞國家進行貿易合作,與其他沿線國家貿易相對較弱,出現雙邊貿易不平衡現象,成為構建區域貿易一體化格局的制約因素。
(三)金融監管有待加強
金融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持主要體現在金融制度、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資本等金融要素的作用。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社會中促進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核心要素,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些年,隨著服務于“一帶一路”的金融機構、金融產品及各種多邊金融合作先后推進,金融風險增加,與之相匹配的金融監管制度也要加強。現狀是,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發展水平差異大,地緣、政治等因素影響,金融監管存在監管障礙、不同步、不健全等現狀,金融監管處于意向協商和政策性綱領階段,實質性金融監管有待加強。[4]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監管體制存在不互相融合,均以自己現有監管制度為指引,無法構筑沿線國家金融監管合作機制,不能建立順暢的溝通交流平臺,關于保險、項目合作意向、匯率風險等方面不能更好地達成合作備忘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法律法規、金融管理制度、貿易政策等合作機制有待加強,由于國家間歷史制度、風俗文化、政治環境等的不同,導致對金融監管制度認識不同,有的國家禁止存貸款收取利息而有的國家支持鼓勵該行為;[5]“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缺乏金融合作廣度與深度,缺少信用風險、流動風險、項目資金監管等方面的信息交流與共享,沒有構建完善的金融監督管理平臺,不能更好地在沿線國家金融市場中拓展相關金融業務,與之相關的配套服務更是無法有效開展。
三、“一帶一路”倡議下金融服務發展對策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對于促進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深化合作國際經濟金融合作、推進沿線國家多邊金融合作與交流,構建一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體發揮了重要作用。優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服務環境,整合金融資源,形成資金合力,拓展金融多領域合作空間,共商共建多層次金融保障體系,激勵有能力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投資,運用大數據信息技術建立金融數據信息共享平臺,構建一個互聯互通能鏈接所有相關企業的金融服務系統,激發相關項目的金融需求,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良性可持續性發展。
(一)健全金融服務體系建設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資源整合是一項系統性工程,需要多方通力合作,形成共擔風雨、共商共建、合享利益的良好溝通局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府間需要整合資源優勢,發揮政府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市場主體地位,合理布局,加強溝通交流,充分利用金融合作平臺,拓展金融服務手段,鼓勵保險、擔保、信托、融資、租賃等金融機構發揮優勢,創新金融服務模式,提供低成本、低風險、高利潤的金融支持,構建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促進金融產品的多元化發展,結合一些國家的先進金融經驗與具體實際,對具有不同特征的基礎設施項目促進金融產品管理及風險管理產品的管理進行創新與發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經濟發展不協調情況,需要從國家高度構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政府對話、經貿合作,建立利于區域金融機構協調合作體系,定期、不定期舉辦金融活動,如,2017“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投資金融論壇、2018全球治理高層政策論壇暨2018“一帶一路”金融投資論壇、2020“一帶一路”金融合作論壇等會議活動,對當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中遇到的金融問題進行溝通交流。建立區域金融協調監管機制,為金融機構與跨國企業投資環境提供助力,出臺相關金融政策,如,《“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6]整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優勢資源,發揮市場配置力量,合理布局金融配比,提升金融服務水平,健全金融服務層次,加快其余市場的融合,充分挖掘金融服務平臺資源與手段,全力打造“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
(二)保障金融安全可持續發展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于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文化背景各異,政治環境差異較大,金融服務存在風險,應建立金融安全保障體系。創新金融安全方式,推進簽署項目盡快落實,推動與沿線國家簽訂金融投資保障協定,加強金融安全合作與交流,實施更高水平的金融一體化管理模式。一是國家間、區域間加強金融安全政策溝通交流,依托金融平臺資源優勢積極推進金融監管合作模式,在金融安全政策區域協調方面達成合作共識,加強區域間金融監管制度、金融市場運行狀況,金融安全漏洞等方面交流與溝通,增進彼此間了解與默契,打造合作監管的局面;[7]二是構建以信用評價體系為核心的區域間金融安全風險監測數據平臺,全力打造與國際標準相銜接金融安全評價數據體系和相關金融產品,擴大信用評價體系應用范圍,與金融監管機構數據信息共建共享,打造共同信用評價監管平臺,聯合打擊失信行為,力保金融安全;三是完善金融風險預警機制,搭建風險信息監測、信息披露、預警響應平臺,及時了解金融政策及市場變化,建立跨國度、區域金融監管機制,尤其是大規模金融資金流動的情況,設置風險預警機制,加強對大額資金項目、政治敏感項目、稀缺資源項目等方面評估、監管、監測,對項目資金流向動態進行實時跟蹤,確保金融風險可防可控可跟蹤,并制定相應措施,推動金融安全標準化運行。
(三)構建完善金融風險監督體系
“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沿線國家地緣政治、經濟活動、政治環境等因素差距較大,“一帶一路”合作項目由于匯率變動、恐怖主義、政治動蕩等因素影響面臨各種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貿易合作和經濟發展需要與之相配套金融監管體系支持,不斷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金融風險監管合作意向,構建適應于“一帶一路”金融監管機制與框架。一是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金融機構的作用調動起來,針對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創新金融融資方式,擴大金融機構服務的規模與領域,加強沿線國家之間金融機構平臺合作廣度與深度,在合作溝通中探索最佳的金融監管方式,如,俄羅斯聯邦中央銀行主要是對信貸機構、金融機構實施監管與調節,對金融機構之間合作與運行進行協調;二是構筑完善的沿線國家金融監管合作框架,與沿線國家就跨境危機管理、貨幣兌換匯率、合作協議簽訂合作備忘錄,便于對沿線國家之間金融風險進行提前預警及有效應對,如,中國11 家中資銀行與29 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80 家一級分支機構,做好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金融服務的同時,加強風險監測,通過金融機構合作深化跨境金融監管合作;三是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制度、人文歷史、風俗習慣均不同,要深入調研沿線國家的法律法規與投資環境,實施差異性銀行風險監管防控制度和金融機構安全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