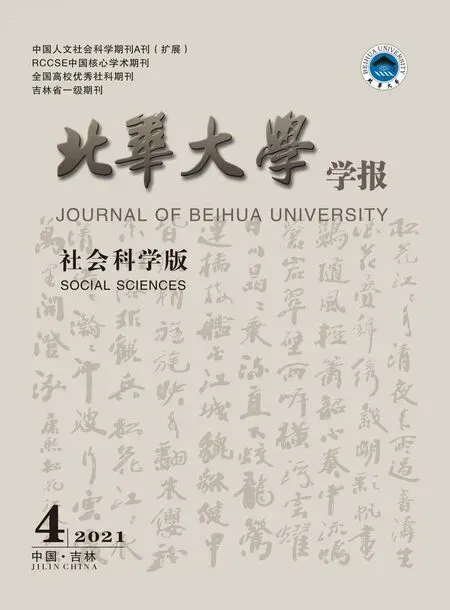價值、路徑、成效:居民參與和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邏輯理路
歐陽麗
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也是城市社會治理的落腳點和基石,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是實現國家社會繁榮穩定,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我國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經歷了單位管理、街道—居委會管理以及社區治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在這一發展進程中,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呈現出政府職能逐步縮小,社會力量參與不斷擴大的態勢。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多元主體中,城市居民以個人或群體的形式廣泛參與基層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對于“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1],“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2],“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3]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
一、居民參與和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價值契合
20世紀90年代以來,治理理念在全球范圍內廣泛興起并得以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的領導下,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的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等國家治理體系正在有序重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和基礎支撐,以城市社區治理為基本形式,一方面,在價值取向層面,社區居民在城市治理中占據著主體地位,以社區居民為中心是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根本價值取向;另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和共同發展,民主、人民權利的充分保障,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現,無一不與城市居民積極參與社會治理緊密相關。居民參與是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重要制度、途徑和方法,就價值層面而言,居民參與和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高度契合。
2015年12月,時隔37年重啟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指出:“我國城市發展已經進入新的發展時期”,“城市發展波瀾壯闊,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城市發展帶動了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城市建設成為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引擎”,“做好城市工作,要順應城市工作新形勢、改革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城市為人民。這是我們做好城市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4]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再一次明確了城市工作要服務于人民的核心指導思想和根本工作原則,也奠定了人民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解決了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為誰治理”和“朝什么方向治理”的價值問題。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就要以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滿足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的新需要,解決好城市居民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回應城市居民對美好生活的新向往和新要求。
在城市基層社會治理中,城市居民主體地位的有效實現,單純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是難以實現的,城市居民的意愿、主張和社會訴求在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社會公共事務處理中得到表達,需要在相關城市基層社會公共事務決策中擁有選擇的權力,能夠對城市公共事務的處理發揮其影響作用,而這一切的實現有賴于城市基層管理向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轉變。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政府系政治學教授格里·斯托克認為:“治理的本質在于,它所偏重的統治機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權威或許可。‘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創造的結構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強加,而是多種統治過程和互相影響的行為體的互動帶來的結果’。”可見在組織框架上,“治理出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5],還與“廣大范圍的眾多社會勢力”有關。由此公共部門、私人機構以及公民個人都是城市社會實現治理、推動城市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主體。城市居民作為城市基層公共事務管理主體參與城市基層公共事務管理,是實現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前提和基礎。
繼城市社會單位管理、街道—居委會管理體制后,城市基層管理體制改革開始強化社區功能,我國城市基層管理體制由此全面轉型到社區管理時期。在社區管理發展階段,城市社區不僅成為城市大多數居民生活和居住的主要形式,而且也為城市居民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提供了良好的空間和載體。而與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管理的日益擴大相伴隨的,是城市基層管理重心的進一步下移,城市居民在基層社會治理中的主體地位得以進一步確立和保障,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20世紀70年代以來,伴隨著“新公共行政”運動以及“新公共服務理論”的興起與發展,公共行政“經濟”“效率”傳統核心價值為“平等”“社會公平”“民主”所代替,平等、社會公平、民主成為公共行政管理活動追求的目標。作為國家治理重要組成部分的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由于其目標和利益的多元發展,對社會公平和民主的追求也必然是其核心價值取向。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對平等、民主、社會公平的追求必然離不開城市居民的參與,從本質上說民主就是多數人的統治,“民主決定于參與——即受政策影響的社會成員參與決策”,“民主的廣度是數量問題,決定于受政策影響的社會成員中實際或可能參與決策的比率”[6]12,“民主的廣度是由社會成員是否普遍參與來確定的,而民主的深度則是由參與者參與時是否充分,是由參與的性質來確定的。”[6]21由此可見,廣泛而充分的居民參與,與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存在著根本的價值契合,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實現具有顯著的正向功能。
二、居民參與是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路徑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城市社會和居民生產生活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國企、所有制結構、管理體制以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經濟體制改革舉措為城市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生命力,城市經濟面貌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不僅城市經濟增長迅速,經濟成分和居民就業方式也迅速實現了多樣化發展,城市社會市場繁榮,流通活躍,城市居民收入不斷提高。與經濟體制改革相伴隨,我國的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也在不斷發展和深化,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政治制度不斷完善,以轉變政府職能為核心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使政府微觀事務管理職能大大減少,宏觀調控能力不斷增強,有效地協調了政企關系和政社關系,為社會力量在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活動中發揮作用創造了條件。
在經濟文明和政治文明不斷發展的基礎上,城市社會層面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由于城市經濟成分以及就業方式的多樣化發展,傳統由單位承擔的對城市居民的管理職能轉歸于社會,由街道辦事處和居委會等城市基層管理機構進行管理。街道辦事處作為城市基層政府的派出機關,對轄區事務承擔行政管理職能,具有濃重的“行政色彩”,權責配置不清,職能范圍界定不明確,工作方式單一等問題,造成工作量大、疲于應付、服務不足的困難局面,使社區公共事務管理成本過高,效率低下。在街道辦事處領導下的群眾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也帶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自治的功能十分有限。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濟文明和政治文明大大改變和提高了城市居民生產、生活方式和水平的同時,也催生了城市居民對生產生活更高層次、更多樣化也更為復雜的現實需求。集權、等級等觀念逐漸式微,民主、法制等觀念日漸深入人心,對于和自身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公共事務管理,城市居民有了更多樣化和更高程度的訴求。
“行政色彩”濃重的城市街居制管理體制效能的有限性與城市居民對基層公共事務管理訴求不斷擴大和提升的現實矛盾,迫切呼喚城市基層管理向治理的轉變,即充分發揮社會力量,擴大城市居民對基層社會治理的參與度,使他們的意愿和訴求,諸如社區衛生、安全、消防、房屋改建、教育、環境污染等和居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實際矛盾和問題,能夠直接得以表達和有效解決,這不僅可以為政府行政政策的制定提供更多、更符合現實的可靠信息,提升行政政策的科學化水平,更能夠使城市居民享有更多、更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增進其對政府的理解和信任,提高其獲得感、歸屬感和幸福感,從而促進城市社會的穩定和發展。正如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所指出的,要“通過完善制度保證人民在國家治理中的主體地位”,要讓群眾參與社會治理,貢獻社會治理成果,基層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3],居民參與是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必然依賴的路徑選擇。
三、居民參與提升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有效性
有效性,可以簡單地將其理解為完成某項活動以及實現該活動預期結果,達成其目標的程度。對于城市基層社會治理而言,有效性指的是人們在進行城市基層治社會治理活動中,對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所預期的結果的顯現程度及預期目標的實現程度,居民參與是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有效性提升的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
從理論層面分析,善治,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參與’是善治的一個本質特征,并深刻地影響著善治其他要素的實現程度。沒有‘參與’就談不上‘善治’。”[7]廣泛而最大限度的居民參與,可以將城市居民從政府管理的被動對象轉化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責任主體和行動主體,在其積極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活動中,形成其對社會生活的歸屬感、認同感,以及對社會治理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也可以培養其在社會生活當中的公平意識、正義意識、參與意識、公德意識和法律意識等良好的公民意識,塑造其自覺遵守城市社會共同生活中的行為準則和規范的公共精神,由此建立起成熟完善的、有自治能力的公民社會,也才能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有效性的提升奠定強有力的支撐。
城市基層社會是由每一個公民個體共同組成的共同體,廣泛而充分的居民參與是“使社會治理成為億萬人民參與的生動實踐,真正讓人民群眾成為社會治理的最廣參與者、最大受益者、最終評判者,有效推進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保持社會穩定、維護國家安全”[8]的關鍵所在。實踐表明,在社區居民代表的積極組織和引領下,居民參與程度較高的社區治理活動中,公眾愿景和居民訴求可以更好地表達,就某一治理問題也可以迅速有效地形成一致意見,更可以獲得更多的資源支持和幫助,從而使社區治理生活更有效率和效果。反之,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活動則難以有效的實現。
居民參與與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的價值契合,使其成為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必然的路徑選擇,與此同時,居民參與也是城市基層社會治理成效性提升的重要影響因素。城市基層社會治理,離不開廣泛而有效的居民參與,城市基層社會治理經驗積淀的歷史邏輯,參與與善治的理論邏輯及當前我國城市基層社會治理問題導向的實踐邏輯構成了其形成和發展的內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