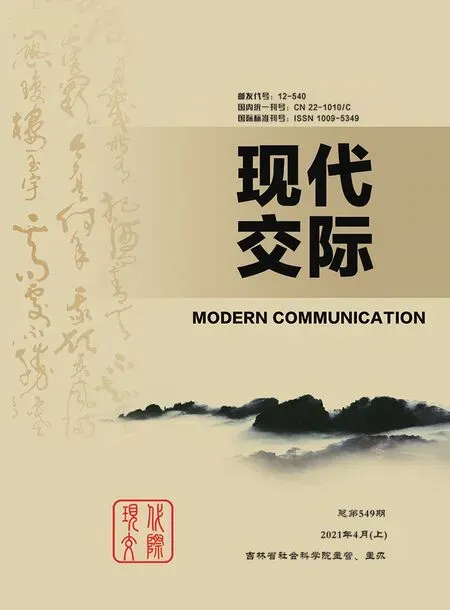偵探小說在近代中國的功能轉變
趙昱輝
(1.山東大學 山東 濟南 250100;2.山東布克圖書有限公司 山東 濟南 250100)
從19世紀末,中國興起了一股翻譯熱潮,西方的偵探文學被廣為譯入。由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經濟危機造成的壓力及20世紀初期“一戰”帶給西方各國的沖擊,偵探文學一直扮演著休閑娛樂的角色;然而進入中國后,其這一功能未能完全延續,反而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功能。本文介紹了西方偵探小說的功能及成因、在中國被“強加”的社會功能及中西方偵探小說功能定位差異的成因。
一、西方偵探小說功能
學術界普遍認為,愛倫·坡的發軔之作——《莫格街兇殺案》奠定了現代偵探小說的基石,在此之后,阿瑟·柯南道爾將偵探小說發展到頂峰,成為一時間最受歡迎的通俗讀物。
作為通俗讀物,偵探小說在西方社會最大的功能就是娛樂消遣。從作者的角度看,寫作偵探小說的動機之一便是暢銷,因此非常重視迎合讀者的閱讀心理,一切都在順應故事情節的新奇和懸疑,從而達到讓讀者廣為接受的目的。《教父》的作者——著名通俗小說家馬里奧·普佐曾表示,他寫這些小說就是為了“賺錢”。也正是由于娛樂性,偵探小說也遭受了很多批評。英國批評家朱利安·西蒙斯就說95%的偵探小說“基本上是消遣性的無聊之作”[1]56。就連被授予爵士勛章的柯南道爾也把偵探小說作為二流文學,并不在意自己在偵探小說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
偵探小說之所以在誕生之初就具有娛樂性,是因為19世紀20世紀之交西方社會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得到了充分發展。然而,隨著資本主義日益走向壟斷,加之“一戰”的沖擊,持續的經濟危機給人們造成的壓力,讀者亟須一種能起到消遣娛樂功能的精神讀物來緩解內心的重壓,而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強調公平正義及邪不壓正的偵探小說正能滿足這一需求。偵探小說中最常出現的秩序公平的觀念,為當時的人們勾畫出了另一個世界——與金錢至上和供需關系等的冷冰冰的資本主義不同的世界,起到了逃避和放松的作用。除此之外,同樣是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為了保護統治集團和資本家的利益,一套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體系也已經建立,這也為偵探小說的孕育提供了的土壤。
二、偵探小說在中國被賦予的社會功能
在西方社會,偵探小說為休閑娛樂的文學形式;而在中國,接觸偵探小說要從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算起。當時,上海《時務報》刊登了張坤德翻譯的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的4篇福爾摩斯探案故事[2]。然而,偵探小說在進入中國時就被“強加”了更多的社會功能,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啟民智
1898年,梁啟超在《譯印政治小說序》中說道:“政治之議論,一寄之于小說。于是彼中綴學之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巿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梁認為政治小說的作者不是一般的窮酸文人,而是學者和政治家,其內容也不是盜淫兩種,而是深厚的政治議論,這就為改良中國小說的格局面貌提供了可行的思路[3]。正是在梁啟超譯介小說,尤其是政治小說的大力倡導下,形成了小說翻譯的高潮,偵探小說也正是在這個時候被廣泛譯入。
啟民智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同梁啟超倡導小說翻譯一樣,偵探小說譯本也承擔了引入西方制度和思想的功能。人們可以在小說中了解到西方制度體系,從而加以學習和吸收。另一方面,偵探小說本身具有非常特殊的元素:百科性,其中蘊含了各個學科的知識。比如,福爾摩斯作為偵探深諳邏輯推理、物理、化學、醫學甚至格斗等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知識;小說中出現的火車、電報、電話、化學實驗等,自然而然展示了西方先進的科技發展成果,極大開拓了國人的視野。
2.科學精神
程小青就曾提出偵探小說是“化裝了的科學教科書”的說法。偵探小說必須回答的問題是,這件案子是“誰做的”(罪犯),“怎樣做的”(犯罪過程),“為什么要做”(犯罪動機),涉及對一起案件的破解過程,其實是一種編碼到解碼的過程。因此,這其中就涉及了對于案情的了解、現場的勘察、證據的采集及演繹、歸納判斷等,暗含了一種科學的探究方法。
民國時期,出版的單行本偵探小說有148種,涉及作家、翻譯家達54人。1900—1920年之間,僅在上海一地便有24家出版偵探小說譯本的民營出版機構[4]。如阿英所說:“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沒有。”[5]偵探小說的受歡迎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一些偵探小說的作家或譯者由此認為,要借助偵探小說來引起人們對于科學的興趣,使人們能夠以偵探小說中的科學的探究方法來研究問題。張亦庵就曾表示,對于理智的尊重,“偵探小說實在是有力的先鋒隊,因為偵探小說是以理智和科學為立場的,而小說之入人又最易,只有一般人對于偵探小說的興味能夠普遍,那末玄秘的頭腦不難打倒,理智的、科學的頭腦不難養成”[1]56。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問題的考量往往離不開感性層面,且這種考量常處于決定性的位置;并且由于封建觀念的影響,應付事理的方法往往依靠經驗、習慣或人情世故。而偵探小說中蘊含著的以科學知識為基礎、通過邏輯推理判斷并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便是偵探小說作家和譯者希望一般民眾所具有并增進的處世哲學。
3.探求欲望
1907年之后,世界各國流行的偵探小說家的作品幾乎都有翻譯,各種偵探小說鋪天蓋地而來,數量之大,品種之多,不勝記數。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中說:“如果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占五百種以上。”偵探小說的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6]。同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一樣,偵探小說在進入中國之后,又被賦予了另一種功能——激發民眾的“好奇心”,或者說探求的欲望。
近代中國的民眾,由于傳統的封建迷信、家庭倫理、所接受的教育及當時社會的影響,廣大民眾對于任何稀奇事、怪事都很難產生一探究竟的想法,甚至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正如臺灣作家柏楊在《丑陋的中國人》中所表述的那樣,人們的視野和好奇心無法逾越自身的生活范圍,人們也因此變得自私而猜忌,更何談對于周圍不尋常之事的探尋。對于事理的探求是近代中國所缺乏的,而在偵探小說作家和譯者看來,極受歡迎的偵探小說正是引發興趣的絕佳工具。
這種探求欲望的培養大致可以分為具體和宏觀兩個方面。具體來講,偵探小說中出現的各種西方社會的科學產物不僅有助于人們去主動了解科學的進步,并且逐步沉淀為漢語的常用詞匯,比如“雪茄”“咖啡”“摩登”“幽默”“邏輯”“阿司匹林”等[7]。宏觀來講,偵探小說的出現和傳播,其背后是法律體系的相對完善,完善的法律體系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感受到偵探行為的合理性。存續千年的羅馬帝國也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卻沒有偵探文學產生,一定程度上是關于證據的法律不夠完善,因為當時的訴訟程序是逮捕、拷問、招供和處刑[8]。偵探小說的接受一定程度上與中國古代公案小說有關,而公案小說中維護的是綱常倫理;偵探小說卻在表述法律高于一切,這也是近代中國迫切需要民眾形成的一種觀念。
三、中西方偵探小說功能定位差異原因
在西方作為娛樂消遣的偵探小說之所以在中國被賦予了新的社會功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
1.文以載道
文質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源于古人對生存世界及合理生存方式的深入思考,其實現的方式之一便是文以載道,即文學的社會功用,講求“真、善、美的統一”[9]。小說雖然在當時“并不入流”,但也不能忽視它的社會作用,尤其是偵探小說這種人們喜聞樂見的讀物。而作為“小說革命論”的代表,梁啟超更是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如是說道:“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因此,以“文以載道”觀念為基礎,從偵探小說之中發掘“啟智”素材也是必然之舉。
2.社會背景
中西方的社會現實差異也造成了偵探小說社會功能的不同。19世紀初期,歐洲多個國家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歐洲的法律體系和司法制度逐步走向完善,法學、犯罪學等相關學科也隨之產生。同時,工業革命的豐碩成果也給偵探的邏輯推理提供了較為有效的依據。由于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個人財富也有了很大程度的積累,因此產生了很多盜竊案、兇殺案;于是,保護私有財產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高。當時,巴黎警察局長找來曾經是罪犯的弗朗索瓦·維多克,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偵探組織“Brigade de la surete”;隨后,他在1834年1月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名為“包打聽(Le Bureau des Renseignments)”的私人偵探所[10],偵探這一文化現象也因此出現。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已經充分發展,隨后出現的偵探小說的商品屬性也日漸明顯,作者通過寫作來獲得生活來源,民眾在生活壓力之下需要以閱讀偵探小說為放松的方式,偵探小說也因此具有了娛樂消遣的功能。
而在近代中國,內有封建體制的荼毒,外有帝國主義帶來的深重災難和資本主義入侵,中國人艱難地邁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步伐,中華民族在這種災難下開始了痛苦的文化覺醒,大量向外國派遣留學生,翻譯西方的書籍。中國部分有識之士逐漸認識到了中國現有法律體系的不完善,又在偵探小說當中感受到了科學的方法和先進的制度,因此必然會通過這種通俗文學來介紹西方的進步思想,并將之作為介紹先進科學知識的載體。
3.發展階段
1841年5月,愛倫·坡的《莫格街兇殺案》于《格雷姆雜志》上刊登,從此開始到1896年上海《時務報》刊登張坤德翻譯的題為《歇洛克呵爾唔斯筆記》的4篇福爾摩斯探案故事,西方的偵探小說已經歷經了五十余年的發展歷程,無論是創作的數量還是質量都有了成熟的發展,也使得西方偵探小說作家及理論家、批評家越發清楚地認識到了偵探小說在西方社會的本質屬性——娛樂性。因此,讀者的需求對創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為了暢銷,作者會主動順應讀者對于新奇故事情節的追求,使其能為更廣大的市民群體所接受。倘若賦予其過多的社會功能,必然要犧牲其受歡迎程度,從而被相當部分讀者所拋棄,這是西方偵探小說作家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中國偵探小說的產生與西方國家不同,它并不是在自然條件下、在自身土壤中生發的,是外國的偵探小說作品和思潮的影響促成催生的。中國的偵探小說作家和譯者在外國作品中感受到了新的文學形式和思想的力量[11]。中國偵探小說處于起步階段,對這種新的文學品類還沒有充分認識,最初進入中國的偵探小說也只是譯本;加上中國傳統的封建觀念和當時特殊的社會背景,當這兩種文化相遇時,難免會在功能方面產生錯位現象。
四、結語
在西方具有娛樂消遣功能的偵探小說在近代中國被賦予了更多的社會功能,這種功能定位方面的差異,源于中國傳統的“文以載道”思想、不同的社會背景和發展階段,是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從社會現實和時代需求出發給予偵探小說的社會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