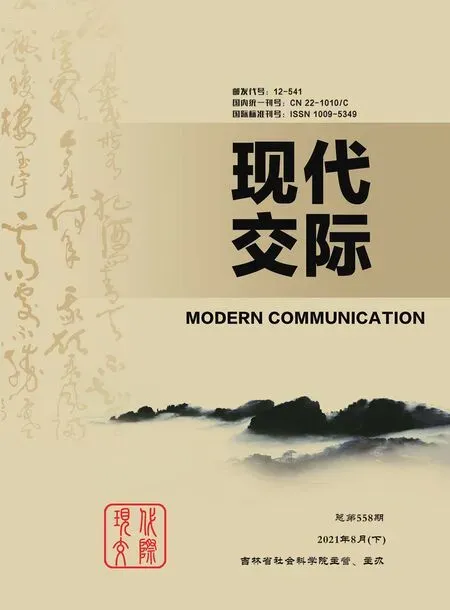淺談日本語言文學中的家園意識
孔枳蘄 林 松
(延邊大學外國語學院 吉林 延吉 133000)
日本雖是一個陸地面積小、山區面積大的島國,但在經濟及文化的發展上卻有著自己的獨到之處。隨著時代的發展,日本文化與他國文化的碰撞也越來越頻繁。其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階段,都出現了文化間相斥相融的局面。正是這種碰撞,促使日本形成了具有自己獨特主流意識的文化。[1]如今,越來越多的中國高校設置日本語言文學學科,而了解日本的語言文學及其民族文化的發展過程成為日語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項。受戰爭、自然災害及特殊的地理環境的影響,日本民族具有強烈的“家園意識”,“家園意識”在日本語言文學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日本語言文學的形成
日本語言文學是綜合、積累與融合各國文化的成果,其形成時間約是公元8世紀。日本文字的形成受到了來自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至今日本文字中仍保留著中國漢字草書的形態。同時,日本藝術的先期表現形式與中國藝術表現形式極為相似,有些甚至還能看出較濃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子。在積累與融合外來文化的過程中,日本民族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特有的文化風格和特色。
后期,日本開始以極具開放性的態度拓展語言文化,加強了與西方文化的交流,鼓勵本國學生前往歐美諸國學習他國的優秀文化。日本從英語、法語、德語等語言中吸收了眾多近代工業及自然科學詞匯,并將它們以日語外來語的形式融入日語詞匯體系,使日語詞匯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豐富,促進了日本語言文學的長足發展。
二、日本語言文學的特征
1.極為顯著的時代標記
隋唐前的三次戰亂使中國傳統文化傳播至周邊國家,而日本作為中國一衣帶水的鄰邦,自然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日本派遣遣唐使到中國學習,掌握了諸多先進文化知識和科學技術,從而改善了日本落后的政治、經濟局面。因此,兩個國家在文字、風俗等方面有共通之處。日本語言文學受中國文化影響深遠,在文字的書寫上也有中國漢字的印記,但兩者在發音上是有明顯差別的,其語言文學中的時代標記也極為鮮明。如公元8世紀誕生了舊文學形式下的抒情詩,這時的抒情詩是31音節的。經過九個世紀的時代更替和文化演變,新文學形式下的抒情詩縮減至17音節。雖然音節有了明顯的縮短,但是文字表現力卻比31音節的抒情詩更勝一籌,韻律也變得更加和諧。單從抒情詩的發展上來看,就可以看到日本文學在創作和發展進程中對新文學中精華的接納,以及對舊文學中糟粕的舍棄,于不斷的取舍中成長為更加成熟的文學形式。由此可以看出,日本語言文學的新舊形式于發展進程中不斷融合,因此日本語言文學有著極為明顯、獨特的時代標記。[2]
2.強烈的社會性特征和地域性特征
通過對其文學作品、藝術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日本語言文學具有極強的社會性特征。日本的文學家和藝術家運用文字和其他藝術表現形式來反射所在時代的社會狀態,抒發民眾心聲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憧憬。正因如此,日本語言文學具有獨特的社會性,文學作品中也蘊含著極濃的社會意識。如平安時代的日本,京都是經濟及政治的中心,文學及藝術作品大多以京都為背景創作。進入江戶時代后,武士、貴族成為文學作品的重點創作題材。其中《今昔物語》《古今著聞集》都是這一時期日本文學的代表作。后受十月革命影響,出現了諸如《沒有太陽的街》等有著極為鮮明的無產階級思想的文學作品,同時,與之相對的階級特色明顯的“新感覺派”也出現了。這些文學作品的形成,無一不蘊藏著強烈的時代感。[3]除此之外,日本語言文學的地域特性也極為明顯。當文化、經濟、政權等以京都為中心時,語言文學的發展也是以此為中心展開的,到了江戶時代,武士是日本的新貴族且參與日本文學的創作,文學重心便逐漸從京都轉移到江戶。以上種種,皆能體現出日本語言文學所蘊含的獨特的地域性及強烈的社會性特征。
3.日本語言文學與日本人生活習性密切關聯
優秀的文學作品是無法脫離真實生活的,二者相互依存,互促發展。如飲食方面,日本人的飲食習慣是極具特色的。因為日本是島國,四面環海,日本人極其喜愛海產品及其加工品,如生魚片、壽司、生魚粉等。但是正如諺語所說“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即便是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食物的吃法、種類和特點也是不盡相同。日本作家基于真實生活創作文學作品,自然會將各自的生活習慣帶入其中,使讀者身臨其境,體驗日本各地不同的特色文化。
三、日本語言文學蘊含著濃厚的家園意識
日本語言文學蘊含著濃厚的家園意識,且透露出對于家庭和諧的重視,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
1.家園概念的內涵
從大眾認知的角度,家園一是指具象意義上的土地領域,二是指抽象意義上的家庭概念。從美學的角度解釋“家園”,就是祖輩繁衍棲居的地方,往往最能夠帶動和影響一個人的情感和思想。隨著時代的發展,“家園”逐漸被賦予更多內涵,擴展至人類精神、國家意識等層面。因此,這個私人領地既包括實質意義上的土地領域,也包含抽象意義上的家庭概念。家園逐漸從具象意義上的土地上升為思想、精神和靈魂的皈依處。
2.家園意識形態的具體概述
日本語言文學所包含的家園意識在日本文學作品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家園意識有多種表現形式,如“思鄉情”就是家園意識的一種表現。常年漂泊在遠方的游子從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對家園故土進行審視時所流露出的復雜、獨特的情感就是家園意識的體現。但家園意識不僅限于此,還包含著對于家園的責任意識與擔當意識。面對社會發展及自然災害給家園帶來的變化和挑戰,無數作家用筆尖敘述對家園的愛與想象,從而創作出了飽含家園意識的文學作品。[4]
四、日本語言文學中家園意識的形成因素
1.戰爭因素促使日本語言文學中家園意識的形成
通過翻閱大量日本文學作品發現,社會背景對于文學創作影響極大,而在戰爭年代,這一點更為明顯。日本作家創作的文學作品大多飽含著因社會動蕩或者家園遭遇破壞而產生的強烈愁怨、不安及哀傷之情,將當時社會背景下民眾身心受到的重創,以及對理想生活的憧憬和渴望表達得淋漓盡致。在多種條件影響下,家園意識逐漸成為日本語言文學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也逐漸成為其代表性的特征。如日本戰后派作家安部公房,他出生于日本東京,后舉家搬遷至中國沈陽。在搬遷途中,他目睹了戰爭帶來的慘狀。在《白癡》中他對東京大空襲的描述:“只有高射炮還在繼續發出瘋狂般的聲響……只見工廠一帶已成了一片火海,令人驚訝的是從剛才頭頂上飛過去的飛機正相反的方向,也不斷來了很多飛機,它們向后方一帶給予了猛烈轟炸。”殘忍的戰爭經歷使他對家園有著比其他作家更加深刻的失落感,安部公房一生都在追逐自己的理想家園。這個家園不局限于地域和國家層面,還包含著精神和思想上的家園,即對自由的向往。他以自身戰后的真實體驗為素材撰寫了紀實性小說《野獸奔向故鄉》。在這部小說中,他訴說了對家園的渴望,因為戰爭,他成了一個“沒有故鄉的人”,這份渴求與希望也隨之破滅。他對家園一直處于追逐與放棄的矛盾當中,在這個過程中,他筆下的家園的意象也從早期局限于地域含義上的家園逐漸轉變為思想上的精神家園。安部公房以《櫻花號方舟》抒發了自己對核危機的見解和時代危機意識,體現出了他厭惡戰爭、向往和平的理念。正如在二次大戰戰敗后,日本民眾普遍感到失去肉體及精神皈依的“故鄉”那樣,在安部公房內心深處最渴求的就是和平、自由、能夠讓靈魂棲息的精神家園。[5]
2.自然災害促使日本語言文學中家園意識的形成
自然災害是促使家園意識形成的重要因素。按照存在與意識的辯證關系,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原始奴隸社會及古代封建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主要以落后的農耕文明為主,這也間接導致了當時以農民為主要組成部分的社會大眾對于土地的極大依賴性。而對于日本這樣一個山地占大部分國土面積的島國來說,可以用來種植農作物的土地極為稀少,再加上日本列島處于兩大板塊交界處,這種地理環境使日本自古以來就要承受比陸地國家更多的自然災害。不穩定的自然生存環境使日本民族對于“土地”“家園”的依賴和情感都更加明顯,并在各個時期的文學作品中得以體現。如日本科幻作家小松左京的作品《日本沉沒》,講述了劇烈的地質運動導致日本列島的大部分土地將于一年內沉入海底的故事,在基于此書改編的電影中,日本人在海水退去后依然回到了自古以來居住的日本列島,由此可體現出日本民族極其強烈的家園意識。
五、家園意識在日本語言文學中的發展
家園意識一直是日本語言文學中“安寧和平”的象征,這種意識貫穿了整個日本語言文學的發展進程,是日本語言文學的靈魂所在。無論是傳統還是現代的文學作品,都能從字里行間看到“安寧”的影子。這其中包含著人們對社會安寧、穩定的期望,更體現了人們內心深處對安定、和諧的生活的向往。日本文學作品受傳統思想及國家政策影響深刻,在漫長的演變及發展進程中屢次受到阻礙。明治天皇自上而下進行國家改革后,經濟形勢發生巨大改變,日本原有的傳統農耕文化也受到了沖擊。與此同時,日本不斷對外發動戰爭,為其他的國家帶去災難,這就使民眾對“安寧”的渴望更加強烈。而作家也通過文字抒發了民眾的心聲,將人們失去家園和親人的悲慟描寫得淋漓盡致。如日本小說家廣津柳浪創作的小說《今戶心中》,用社會環境的苦楚與動蕩,反襯出家園“安寧”的特征。小說出色地敘述、刻畫了底層人民的悲慘生活,在敘述人物經歷、刻畫人物形象的同時,也表達出“家園意識是與生俱來的意識,是不可缺少的”的觀點。小說中貧苦的底層人民長期遭受壓迫,現實社會的殘酷使他們迫切地找尋精神上的“避難所”,對他們而言,家園是最舒適且有安全感的地方。因此,對和平家園的期盼與渴求就成為他們最大的心聲。[6]
六、結語
日本語言文學中以家園意識為主的文學作品極為廣泛,其大多表現的是文學家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安定和諧生活的渴望。通過探索、研究和分析日本語言文學蘊含的家園意識,能夠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提高日本語言文學基礎和文學素養,為我國日本語言文學研究體系的建立及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