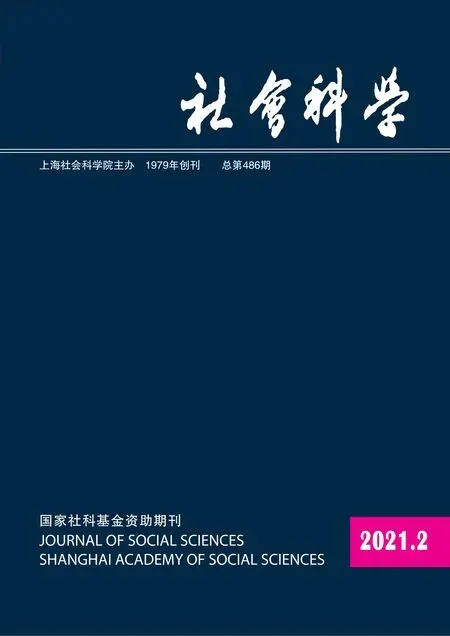相似、揀選與類比: 早期中國的類概念*
李 巍
如果說名為“中國哲學(xué)史”的研究,其作為“史”的實質(zhì)是要從中國古代文本中尋找并系統(tǒng)呈現(xiàn)能被稱為“哲學(xué)”的素材;那么這種訴求在被稱為“中國邏輯史”的研究中同樣存在,就是要從古代文本中尋找并系統(tǒng)呈現(xiàn)能被稱為“邏輯”的素材。顯然,因為以“哲學(xué)”或“邏輯”為名的東西最先來自西方,所以在中國文本中找到的素材是否具有冠名資格,就會引起質(zhì)疑,因此才會有中國哲學(xué)合法性或有無中國邏輯的漫長爭論。但實際上,即便這種以“找哲學(xué)”或“找邏輯”為訴求的“史”的研究沒有遭遇冠名權(quán)的質(zhì)疑,也很難說是一種談?wù)撝袊枷氲挠行Х绞健R驗樗枷氲墓趋朗歉拍睿绻袊枷胫心男└拍钍浅跏嫉模男┦谴渭壍模前础罢艺軐W(xué)”或“找邏輯”的需要編織譜系,就意味著對概念的理解不是依賴文本,而是由對哲學(xué)或邏輯的理解決定的。比如在“哲學(xué)史”的一般敘述中,道概念被視為重要的,正因為相比其他概念來說它更適合充當(dāng)中國古人進(jìn)行哲學(xué)思考的標(biāo)志;在“邏輯史”的一般敘述中,類概念被視為重要的,同樣因為相比其他概念來說它更適合充當(dāng)中國古人具有邏輯自覺的標(biāo)志。問題是,如果此類“哲學(xué)史”或“邏輯史”的概念研究取決于對哲學(xué)或邏輯本身的理解,那必定陷入惡性循環(huán)。因為中國古人對某一概念的談?wù)摚瑹o論道還是類,有待說明的正是其能否充當(dāng)哲學(xué)或邏輯的素材;可當(dāng)這些概念首先是作為中國古代有哲學(xué)或有邏輯的識別標(biāo)志被談及時,顯然已經(jīng)預(yù)設(shè)了答案。因此嚴(yán)格說來,這樣一種以“史”為名、以“找素材”為實的研究,至少在概念層面并不能為中國思想提供有意義的說明。因為無論道成為哲學(xué)史研究優(yōu)先對待的概念,還是類成為邏輯史研究優(yōu)先對待的概念,這至多表明中國古代可能有某種哲學(xué)或邏輯的概念,卻不能表明這些概念到底意謂什么。
這一點,我在關(guān)于道概念的專門研究中已有闡述,但主要是對“找哲學(xué)”的訴求來說;(1)參見李巍《道家之道:基于類比的概念研究》,《深圳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20年第5期。現(xiàn)在,為表明在中國文本中“找邏輯”的訴求面臨同樣的問題,有必要將注意力再轉(zhuǎn)到類的概念。如后所見,在中國邏輯史的研究中,人們把類看成中國古代邏輯意識的萌芽,主要是以西方傳統(tǒng)邏輯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種屬理論作為參照;而其動機(jī),就是想借此觀察中國思想中有無對應(yīng)于西方邏輯的成分。因此,比照邏輯上類概念(主要是種屬概念)來談?wù)撝袊湃说睦斫猓烧f是“找邏輯”的代表性實踐。但我認(rèn)為,這非但不能澄清,反而還會遮蔽類概念在中國思想中扮演的基本角色,那就是:類首先是一個指導(dǎo)行動的規(guī)范概念。
一、類的涵義:種屬與相似
在揭示類概念在中國思想中扮演的基本角色之前,我們先要考慮類概念在中國思想中的涵義。就研究者通常視為參照的傳統(tǒng)邏輯,尤其是亞里士多德的理論來說,類主要是種和屬(species / genus)。要理解這樣的類概念,至少要考慮兩個層面:一是本體論上,種屬是邏輯的抽象對象;另一是知識論中,種屬構(gòu)成了下定義的基礎(chǔ)。但無論怎么說,作為邏輯種屬的類并不是無需說明就能理解的。相比之下,中國古人對類的認(rèn)識卻簡單得令人詫異,因為它通常僅僅被看成事物特征的相似,如《孟子·告子上》說的“同類者,舉相似也”,代表的就是早期中國的普遍看法:
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左傳·襄公三年》)
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楚辭·謬諫》)
夫物多相類而非也,……此皆似之而非者也。(《戰(zhàn)國策·魏策》)
類:種類相似,唯犬為甚。(《說文·犬部》)
以上,類僅被說成“似”或“相似”,表明作為抽象事物的邏輯種屬在中國思想中并不顯著。不僅如此,中國古人對類的確認(rèn)也往往不受種屬包含關(guān)系的限定,這在許多中國古代文獻(xiàn)中都能找到證據(jù),比如:
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物各從其類也。(《荀子·勸學(xué)》)
水流濕,火就燥,云從龍,風(fēng)從虎,圣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易·乾·文言》)
火上蕁,水下流,……物類相動,本標(biāo)相應(yīng),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虎嘯而谷風(fēng)至,龍舉而景云屬。(《淮南子·天文》)
火上炎,水下流,圣人之道,以類相求。(《文子·上德》)
以上所見的類,如(1)火/干燥/向上/陽燧/日,(2)水/濕潤/向下/方諸/月,(3)云/龍/天,(4)風(fēng)/虎/地,僅是以某種特征相似建立的松散關(guān)聯(lián);若依嚴(yán)格的種屬關(guān)系,顯然不是同類。因此從比較的觀點看,中國式的類似乎既不夠抽象(缺乏種屬概念),也不夠確定(不受種屬限定)。
不過,人們認(rèn)為,從中國古代語言與邏輯的特殊性著眼,這種非抽象、非確定的理解未必就不合理。(2)從古漢語句法和語義的特殊性說明中國古人滿足于對類的非抽理解,典型如陳漢生及其追隨者基于物質(zhì)名詞假設(shè)(Mass Nouns Hypothesis)宣稱類的抽象概念之于中國古人并非必要。今天不再有人嚴(yán)肅對待這個觀點,曾經(jīng)卻轟動一時,參見C.D.Hansen,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pp.112-113; D.J.Moser, Abstract Thinking and Thought in Ancient Chinese and Early Greek,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PH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6,p.171。此外,Chmielewski指出中國古人通常不關(guān)心類的包含與屬于關(guān)系,大概最早涉及中國邏輯的特殊性,參見J.Chmielewski,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ogic, Warszawa: Komitet Nauk Orientalistycznych PAN,2009,pp.181-182;后來,Lucas以墨家為例,引入一階邏輯的擴(kuò)展系統(tǒng)將中國的類概念描述為數(shù)學(xué)上的笛卡爾積,這是對中國邏輯特殊性的進(jìn)一步刻畫,參見T.Lucas, “Later Mohist Logic, LEI, Classes and Sorts”,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9,2005,pp.349-365;此外,關(guān)于中國邏輯特殊性有影響力的觀點,也來自崔清田等人對“推類”問題的專門研究,參見崔清田《“推類”:中國邏輯的主導(dǎo)推理類型》,《中州學(xué)刊》2004年第3期。并且除了類的問題,不難發(fā)現(xiàn),只要對中國思想的言說涉及中西比較,就總有基于特殊性的辯護(hù)。然而,在我看來,此類辯護(hù)價值不大,僅是研究者受迫于比較的表現(xiàn)。但比較不可避免,并非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要求,而是語言貧乏使然,即由于談?wù)撝袊枷氲膶W(xué)術(shù)語言尚不完備,人們不得不對來自西方的特定詞匯有所借用。比如談?wù)撝袊糯挠?無概念時,就不得不引入“本體論”(ontology)這個術(shù)語,因為看起來,說明(1)有/無概念是什么?要能被當(dāng)成關(guān)于“哲學(xué)概念”的說明,似乎只能是去說明(2)有/無是怎樣的本體論概念?而這必定會引出中西比較的問題,因為“本體論”既是迻譯西方的術(shù)語,則它在問題(2)中的運(yùn)用就必須包含對原生用法與引進(jìn)用法的關(guān)系說明,如(3)有/無作為中國古代的本體論概念,與西方哲學(xué)的本體論概念有何異同?以及(4)為什么在西方哲學(xué)語境之外,將有/無概念視為“本體論的概念”是正當(dāng)?shù)模亢苊黠@,問題(3)(4)的出現(xiàn),僅僅因為問題(1)被表述為問題(2)——也就是說,中西比較成為問題,不在于比較本身不可或缺,而是因為研究者離開“本體論”之類的術(shù)語,無法為概念提供一種哲學(xué)上的說明。
所以,若說關(guān)于中國思想特殊性的辯護(hù)本質(zhì)上是由比較引發(fā)的,就能確認(rèn),其根源是談?wù)撝袊枷氲膶W(xué)術(shù)語言還很貧乏。相反,如果語言完備,即研究者不需要引入“本體論”之類的術(shù)語,又能對有/無概念提供一種“哲學(xué)味兒”的說明,討論可能就僅限于問題(1),而不涉及(2)-(4),至少不是邏輯地關(guān)聯(lián)于后一系列問題。可是,“語言問題”往往偽裝成“中西問題”來迷惑人,讓人把比較視為思想研究的題中之義。而當(dāng)描述中國事情的初始語匯中舶來詞的占比越來越大時,就不僅迫使人們?nèi)ケ容^語詞的原生用法與引入用法,還可能把前者視為標(biāo)準(zhǔn)。因之,為中國思想做辯護(hù),就成了為非標(biāo)準(zhǔn)的東西爭地位。比如,通常關(guān)于中國古代思維方式的辯護(hù),說的就是相對西方的分析思維,中國思維作為某種非分析思維的合理性;類的問題也一樣,為中國的情況做辯護(hù),是相比于西方邏輯中抽象、確定的類概念,說明中國古人對類抱有一種非抽象、非確定的理解的合理性。但無論如何辯護(hù),只要中國思想的特殊性被表述為非A,就已經(jīng)將之視為非標(biāo)準(zhǔn)的,因而默認(rèn)了西方的觀點就是標(biāo)準(zhǔn),即便人們的目的是要挑戰(zhàn)這個標(biāo)準(zhǔn)。故此種辯護(hù)的價值不大,就在于“中西問題”只是“語言問題”的表象,因此語言建設(shè)而非中西比較才是學(xué)術(shù)規(guī)范的要求。不過,這一要求還要得到更細(xì)致的闡述,這里只是強(qiáng)調(diào),既然比較并非學(xué)理的必然,則由之引出的對中國思想的特殊性辯護(hù)就不僅限于類,對理解其他概念也一樣,并不產(chǎn)生實質(zhì)幫助。
當(dāng)然,僅就類的概念來說,不可否認(rèn)中國式的理解有其特殊之處,問題是,如果把這種特殊性默認(rèn)為相對西方來說的非標(biāo)準(zhǔn)形態(tài),那由此出發(fā)的推論一定有問題。比如,前引文所見的特殊性,即中國思想中(1)種屬概念并不顯著和(2)對類的把握超出了種屬關(guān)系的限定,這的確是事實,但卻推不出(3)中國古人對類抱有“非抽象”和“非確定”的理解。因為不是只有邏輯種屬才是抽象的類概念,也非只有種屬關(guān)系才是確定的類關(guān)系(詳見后文)。所以,如果允許從(1)(2)推出(3),只能基于一點,就是種屬理論代表了什么是類的標(biāo)準(zhǔn)觀點。但若果真如此,則可斷言被視為特殊的(實際是非標(biāo)準(zhǔn)的)中國理解并無辯護(hù)空間。因為尤其回到亞里士多德來看,種屬理論不僅是劃分的理論(1037b29)(3)本文對亞里士多德文獻(xiàn)的引用參見The Work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Under the Editorship of W.D.Ross, M.A.,Hon.LL.D(Edin.), Vol I, III,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8.,更是定義的理論(1038a30),是把分類視為說明本質(zhì)(essence)或一事物精確地是什么(1030a3)的手段。基于此,從種屬的角度思考類的問題就是正當(dāng)?shù)摹R驗閷僮鳛轭悾鐏喞锸慷嗟滤f,是在本質(zhì)范疇謂述事物的東西(102b31);種則是一個屬之下不可再分的最小類(123a30),并且是唯一代表事物本質(zhì)的東西(1030a5-13)。因此分類用于定義就只能是從屬到種的縱向劃分,即給定作為大類的屬,通過指出其下事物能被區(qū)別開的差,并直到指出“最后的差”(1038b25-30),就得到了不可再分的種,也就指出了事物的本質(zhì)(精確地是什么)。現(xiàn)在,若以此為標(biāo)準(zhǔn),不難看出,中國古人對類的理解與其說是特殊的,不如說是沒用的,因為“相似”不能說明一事物精確地是什么(本質(zhì)),“舉相似”更不足以刻畫大類小類的邏輯包含關(guān)系(種屬關(guān)系)。
然而,一種關(guān)于類的理論是否能被視為標(biāo)準(zhǔn),取決于類概念的應(yīng)用場合(語境)。比如,在下定義尤其是給出本質(zhì)定義的場合,將種屬理論視為標(biāo)準(zhǔn)或許沒有問題。問題是,這并非類概念得到應(yīng)用的唯一場合,因為下定義不是人們談?wù)撌挛锏奈ㄒ环绞健K裕紤]到類的其他用途,對定義負(fù)責(zé)的種屬理論就很難視為標(biāo)準(zhǔn),甚至沒有參照價值。回到早期中國的文本看,情況就是這樣,因為類概念的主要用途不是定義事物,而是指導(dǎo)行動,尤其是為跨場合行動的一致性提供說明。比如:(1)魯班反對殺人,又為楚國制造戰(zhàn)爭器械,這被墨子評價為“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2)有人不遠(yuǎn)千里去醫(yī)治彎曲的手指,卻對“心”或道德稟賦的缺陷不以為然,這被孟子評價為“不知類”;(3)在商業(yè)活動中使用尺子和秤作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卻在治理實踐中舍棄法度,這被戰(zhàn)國的法術(shù)之士評價為“不知類”。(4)參見《墨子·公輸》《孟子·盡心上》《商君書·修權(quán)》。凡此,“類”所描述的都是行動,“不知類”則是指行動者沒能從類的角度理解跨場合行動的一致性。那么從這些案例看,既然中國式的類概念不是服務(wù)于定義或精確地言說事物,其不同于邏輯上的種屬概念就不值得詫異。至于說中國古人對類的把握超出了種屬限定,這同樣無須辯護(hù),因為對指導(dǎo)行動而非定義事物來說,首先要考慮的并不是一類行動與另一類的種屬關(guān)系,而是一類行動如何以相似關(guān)系為紐帶,從一個場合被應(yīng)用到其他場合。
回到上舉案例(1)-(3),質(zhì)言之,這一應(yīng)用的實質(zhì)就是行動基于相似性從初始場合到目標(biāo)場合的類比,如(1)′在某一場合拒絕殺戮(不殺少數(shù)人),也應(yīng)類比于此,在另一場合拒絕殺戮(不殺多數(shù)人);(2)′在某一場合完善自身(矯正生理缺陷),也應(yīng)類比于此,在另一場合完善自身(矯正道德缺陷);(3)′在某一場合遵循標(biāo)準(zhǔn)(商業(yè)交易中使用量具),也應(yīng)類比于此,在另一場合遵循標(biāo)準(zhǔn)(政治治理中使用法度)。因此,如果下定義并非類概念的唯一用途,中國式的“舉相似”也是一種,就應(yīng)指出其核心是做類比;而中國古人將類理解為“相似”,雖缺乏種屬概念的嚴(yán)格性,卻很適合類比的需要,因為相當(dāng)程度上,類比就能理解為相似性的跨場合擴(kuò)展。而這種為類比而非定義服務(wù)的類概念,應(yīng)當(dāng)說有更為廣泛的用途,因為不僅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嚴(yán)格的科學(xué)探索中,跨場合類比正是基本的行動機(jī)制。(5)科學(xué)實踐中的類比,參見Metaphor and Analogy in the Sciences, edited by Fernand Hallyn, Springer, 2000.本文旨在刻畫的,也正是類概念在早期中國用于建立行動類比的特征。為此,以下將逐步探討兩個問題:首先,早期中國與邏輯種屬不同的類概念經(jīng)由怎樣的方式得到?其次,這樣的類概念如何在跨場合類比中為行動者提供指導(dǎo)?
二、類的確認(rèn):劃分與揀選
質(zhì)言之,相比從屬到種的劃分,中國式的類概念主要來自相似特征的揀選,即仍是孟子說的“同類者,舉相似也”。但在解釋這種揀選之前,先要指出,相似的概念恐怕并不像表面看來那么簡單,尤其是之前提及的,類作為相似并不像邏輯種屬那樣抽象和確定,也只是一種表面的印象。實際上,兩種意義的類的差別并不在抽象性與確定性,而是類作為對象概念與作為關(guān)系概念之分。種屬顯然是邏輯上的對象,此外如sets、classes、sorts、natural kinds等意義的類則是數(shù)學(xué)或哲學(xué)上的抽象對象;至于相似,則應(yīng)理解為事物間的一種關(guān)系。當(dāng)然在中國古人看來,尤其是按《墨經(jīng)》的以下論述(A86, NO6),(6)本文引用《墨經(jīng)》文獻(xiàn)基于葛瑞漢對《道藏》本的校訂,參見 A.C.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3.相似代表的事物關(guān)系僅是被稱為“同”的關(guān)系中的一種,后者包括:(1)重合或等同(“重同”、“同名之同”),(2)部分構(gòu)成的整體相同(“體同”、“連同”、“鮒(附)同”),(3)對象所處的位置相同(“合同”、“具同”、“丘同”),(4)事物表現(xiàn)的特征相同(“有以同”),而只有(4)才是類所代表的相似關(guān)系,墨家也稱之為“若”(A78)。但要點是,沒理由因為中國古人把類視為關(guān)系概念,就認(rèn)為他們抱有一種非抽象、非確定的理解。因為本體論上,不是所有場合都需要給出類是對象的承諾,(7)按照現(xiàn)代觀點,人們更傾向于消除類的對象性,最多將之視為出于便利的準(zhǔn)對象(quasi objects)。參見R.Carnap, 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nd Pseudoproblems in Philosophy, translated by R.A.George, Open Court, 2003/2005,pp.57-58.而將類視為“……相似于……”的關(guān)系,因為并不限定是哪些事物在哪種特征上相似,而是對不同或可變的關(guān)系項存在這樣一種關(guān)系,那當(dāng)然既是抽象的,也是確定的。回到墨家的論述看,這種關(guān)系的抽象性與確定性又表現(xiàn)為事物的相似作為一種特征關(guān)系,是區(qū)別于等同關(guān)系、構(gòu)成關(guān)系、處所關(guān)系等事物關(guān)系的獨(dú)立范疇。
因此談?wù)撝袊降念惛拍顣r,我認(rèn)為,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由“舉相似”所得的類是一個關(guān)系概念而非對象概念。也正因此,人們以種屬理論作為參照,這個出發(fā)點就有問題。因為種屬關(guān)系正是充當(dāng)“關(guān)系項”的種和屬的“關(guān)系”,也就是說,在談?wù)撨@種關(guān)系時只有將類預(yù)設(shè)為對象,才能談?wù)摱叩年P(guān)系。但在中國古代,人們不大可能這樣談?wù)搯栴},因為類本身就是關(guān)系。(8)Chmielewski注意到中國古人并不重視類的包含關(guān)系,但因為他恰是從對象類的角度來解釋中國的類概念,所以不能解釋為何如此,只能視之為中國古代的邏輯尚不成熟的表現(xiàn)。參見J.Chmielewski, 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ogic, Warszawa: Komitet Nauk Orientalistycznych PAN,2009,pp.181-182。而這就決定了對類的把握很難從種屬劃分的角度得到解釋,因為從大類分出不可再分的小類,正是發(fā)現(xiàn)某一邏輯對象的過程;但在中國古代,對類的把握并非發(fā)現(xiàn)某個對象,而是確認(rèn)一種關(guān)系。又因為類作為關(guān)系主要是就事物的特征來說,所以確認(rèn)一個類的基本手段就是做揀選,即舉出某一特征來判斷事物是否同類(相似)。當(dāng)然,這似乎存在任意性的風(fēng)險,如《莊子·德充符》談及的,僅僅揀選不同點,能說肝膽之別如楚越之遠(yuǎn);僅僅揀選相同點,又能說萬物是一樣的。因此,如果分類取決于揀選,就可能因為不同的揀選得出萬物既同類又不同類的結(jié)論,如名家所說的“萬物畢同畢異”(《莊子·天下》)。實際上,將“萬物畢同畢異”視為任意的分類,就像認(rèn)為中國古人把火/干燥/向上或水/濕潤/向下歸為同類具有任意性的理由一樣,是以種屬關(guān)系的限定作為標(biāo)準(zhǔn)。但既然種屬理論并不適合作為參照,則中國古人對類的把握是否任意,就要依據(jù)其他標(biāo)準(zhǔn)來看,尤其是,有沒有克服任意性的揀選規(guī)則。我認(rèn)為,這是談?wù)撝袊降念惛拍顣r要知道的第二件事。早期文本尤其是與名辯思潮相關(guān)的部分,對此提供了相當(dāng)充分的論述。
從中可見,揀選規(guī)則的運(yùn)用涉及兩種情況:(1)析取揀選,指要么揀選不同點,要么揀選相同點。(2)合取揀選,指既要揀選不同點,也要揀選共同點。關(guān)于(1),《荀子·正名》談?wù)撁鳛閽x手段時說的“同則同之,異則異之,……不可亂也”,就是對析取式揀選的規(guī)則表述,即要么取其同、要么取其異,兩者“不可”混淆。由此再看《墨經(jīng)》中的牛馬比較(B66),同異有別作為規(guī)則,也是針對任意為之的“狂舉”。比如,墨家認(rèn)為,舉出牛有齒、馬有尾來區(qū)別牛馬就屬于“狂舉”,因為有尾、有齒是牛馬的共同點(“俱有”),而非一方有一方?jīng)]有(“偏有偏無有”)的不同點。因此“牛馬雖異”,也不能任意舉出某一特征來區(qū)分二者,因為這很可能是把相同點混淆于不同點,所以同異有別正是克服任意揀選的規(guī)則。再看(2),涉及克服“狂舉”的另一規(guī)則。回到牛馬比較,墨家接著指出,牛有角、馬無角雖然代表了二者的“類不同”(A),但若“以是為類之不同”(B),仍然是“狂舉”。理解這個說法,要注意(A)(B)的差別并不在“類不同”與“類之不同”,而在表斷定的“以是”,(9)“以是”表斷定,如“以是為不恭”(《孟子·萬章下》)、“以是為隆正”(《荀子·王霸》)、“以是為差”(《禮記·王制》)、“圣人以是為未足也”(《禮記·祭義》)。它意味著“狂舉”是僅以某個差別斷定牛馬不同類,未顧及其他情況,也即以局部揀選得出了絕對的結(jié)論。那么,關(guān)于牛馬乃至一般事物的比較,墨家期待的結(jié)論就是雙方既在某個方面同類(相似),又在某個方面不同類(不相似)——至于絕對不同類的情況,如木頭的“長”與夜晚的“長”、智慧的“多”與粟米的“多”、爵位的“貴”與商品的“貴”等,則被說成“異類不吡”(B6),即特征截然相異的東西沒有可比性。那么,可比者就總是有同有異。因之,能被視為揀選規(guī)則的除了同異有別,還應(yīng)有同異兼顧,前者是來自析取揀選的要求,后者則是來自合取揀選的要求;前者確保了揀選的一致性,后者則克服了揀選的局部性。
以上規(guī)則,名家代表公孫龍在其《通變論》中也有討論,只是方式有點怪,不是以特征揀選來確認(rèn)兩個事物是否同類,而是將兩方構(gòu)成的組合與第三方作比,并涉及兩種情況:(1)第三方也是組合成分之一,(2)第三方不在組合成分中。先看方式(1),其例子是牛羊組合與單獨(dú)的牛或羊作比較。公孫龍認(rèn)為,舉出牛與羊的不同點,不意味牛羊組合非牛或非羊,因為獨(dú)羊的某個特征不同于組合中的牛成分(“不俱有”),卻同于羊成分(“或類焉”),獨(dú)牛亦然,所以只能說牛羊組合與單獨(dú)的牛或羊在特征上既非全同、也非全異,而由此肯定的,不過就是牛羊組合有牛有羊。但緊接著,公孫龍主張,舉出牛與羊的共同點,也不意味牛羊組合是牛或是羊,因為牛羊除了存在共同點(“俱有”),也有不同點(“類之不同”),所以結(jié)論就是牛羊組合中的牛不是羊,即構(gòu)成組合的兩個成分并不相同。所以不難看出,以上論述正是遵循同異兼顧的規(guī)則,將組合關(guān)系界定為ab組合有a有b且a不是b。不過,這還只是關(guān)于一個組合中有什么的內(nèi)部界定,轉(zhuǎn)向比較方式(2),即組合相比于非其成分的第三方,又能給出組合中沒有什么的外部界定,可表示為ab組合沒有c,即《通變論》所謂“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具體來說,公孫龍認(rèn)為,只有揀選牛羊組合與馬不相交的特征,如犄角是牛羊都有但馬沒有的,長尾是馬有但牛羊都沒有的,才能從組合成分中排除馬。但方式上,仍然要遵循同異兼顧的規(guī)則,因為揀選不相交特征的實質(zhì)就是劃出組合成分區(qū)別于第三方的共同界線。因此被揀選的滿足劃界需要的特征,就既是馬與牛羊組合的不同點,也是組合成分的共同點。可見,同異兼顧的規(guī)則既能用于說明一個組合中有什么,也能用于說明一個組合中沒有什么。
《通變論》進(jìn)一步談及的情況,表明除了同異兼顧,忽視同異有別的規(guī)則,描述組合關(guān)系的特征揀選也會陷入“狂舉”,例子是從牛羊組合中排除雞。公孫龍的觀點是,如果舉出牛羊有毛雞無毛,或者雞有羽牛羊無羽,則可確認(rèn)牛羊組合與雞的特征沒有交集,所以是可行的排除方式。但若舉出“牛羊足五”和“雞足三”則不可行,因為“牛羊足五”實際是將牛羊四足與概念上的牛羊有足(“牛羊足一”)相加得到,“雞足三”則是將雞兩足與概念上的雞有足(“雞足一”)相加得到——這意味著,“牛羊足五”與“雞足三”并非不相交的特征,因為有足(“足一”)正是牛羊組合與雞的共同點。所以,這種揀選式分類不能從牛羊組合中排除雞,因為違背了同異有別的規(guī)則,把組合成分與第三方的相同點當(dāng)成了不同點。故公孫龍稱此為“狂舉”,并強(qiáng)調(diào)“材不材,其無以類”,就是指出混淆同異不可以把握類。
因此以荀子、墨家和公孫龍為例,可見對類的確認(rèn)訴諸揀選,絕非任意為之。但公孫龍為何采用組合與單獨(dú)事物作比較的怪異方式,仍是個問題。我想,這可能是出于做類比的意圖,如論“羊合牛非馬”時說的:
1.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
2.若左右猶是舉
以上就是兩個類比。其中的“猶”“若”,以及古漢語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譬”,還有兩者作為合成詞出現(xiàn)的“譬猶”“譬若”,正是表達(dá)類比的句法裝置,可直譯為“猶如”。不過,第二個類比服務(wù)于《通變論》自身的主題,這里僅來談?wù)撆c類相關(guān)的第一個類比,其說的是舉出牛羊組合與馬的不同點,猶如舉出牛和羊的“類之不同”,或者更一般地說,就是:
判斷ab組合與c不同類,〈猶如〉判斷a與b不同類。
因此,這一類比的實質(zhì)就是將確認(rèn)事物是否同類的方式從二元擴(kuò)展到多元范疇,即除了a, b是否同類的關(guān)系比較,也能類比于此,進(jìn)行a, b, c是否同類的關(guān)系比較,并能不斷擴(kuò)展下去。而這已經(jīng)暗示了類作為特征揀選的產(chǎn)物,其價值可能主要體現(xiàn)在做類比的領(lǐng)域。因此,讓我們把注意力從揀選再推進(jìn)到類比,并正面處理前文提出的第二個問題,即類的概念用于類比,這對于解決行動問題有怎樣的意義?
三、類的運(yùn)用:類比與行動
單就“舉相似”這個說法本身來看,回到《孟子·告子上》的著名闡述,就能肯定類作為特征揀選的產(chǎn)物,服務(wù)于做類比的目的,這包括:(1)通常情況下,同類事物能被“舉相似”;則類比于此,人之為類也能被“舉相似”(“何獨(dú)至于人而疑之?圣人與我同類者”)。并且,(2)除了能對人的生理本能“舉相似”(“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也能類比于此,對道德本能“舉相似”(“心之所同然”)。并且,(3)正如有人擅長駕馭生理本能(廚師易牙、美人子都),也能類比于此,肯定有人擅長駕馭道德本能(“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于是,基于類比(1)-(3),結(jié)論就是凡人皆有道德本能,并應(yīng)向駕馭這一本能的圣人學(xué)習(xí)。不難看出,這些類比正是“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的核心,但通常更受人關(guān)注的卻是他關(guān)于人性與樹木、水流、顏色等的類比,(10)這些類比參見Lucas的最新研究,但他仍然沒有認(rèn)真對待“舉相似”的類比,參見蒂埃里·盧卡斯《〈孟子〉中的類比與類比推理》,《邏輯學(xué)研究》2019年第6期。而忽視了類作為揀選的產(chǎn)物主要服務(wù)于類比的目的。
這個特征,回到文本來看,在“舉”和“推”這兩個術(shù)語關(guān)聯(lián)出現(xiàn)的地方已見端倪。比如,孟子設(shè)想的將道德本能在某一場合的呈現(xiàn)應(yīng)用到其他場合,這個過程在《梁惠王》篇既被稱為“舉斯心加諸彼”,也叫“推恩”。“推”即“舉……加諸……”的概括表達(dá),是把一事物從被舉出的場合推廣到其他場合,而其實質(zhì)就是類比——如孟子的名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梁惠王》),就是把愛人作為道德本能的實現(xiàn)分為兩個步驟:(1) 揀選此道德本能最易顯露的場合,即舉出面對自己親人的情況;(2)類比于此,將這種道德本能應(yīng)用到面對他人親人的情況,也即推及到尚未顯露的場合——這個從“舉”到“推”的過程,如說是孟子眼中道德行動如何可能的基本方案,核心就是從做揀選到做類比。
再看荀子,從“舉”到“推”的過程則用于說明語詞的運(yùn)用。按《正名》篇,“舉”是將命名描述為語詞揀選事物,包括:(1)沒有特征限定的“舉”,如語詞“物”能無差別地揀選一切對象(“大共名”);(2)有特征限定的“舉”,如語詞“鳥”“獸”只揀選有差別的對象(“大別名”)。但無論哪種揀選,荀子強(qiáng)調(diào)的是這些語詞不僅“舉”出了對象,且能在所有適合的場合“舉”出對象(“徧舉”),那么,這種揀選式的命名就只能訴諸于“推”,即以類比的方式將語詞從一個場合擴(kuò)展到其他場合。比如,(1)′語詞“物”不限定對象,則當(dāng)下場合的對象被共同命名為“物”時,也能類比于此,將這種共同命名的方式推及其他場合(“推而共之”),直到窮盡一切對象(“無共而后止”);(2)′因為“鳥”或“獸”限定了對象,則當(dāng)下場合的對象被分別命名為“鳥”“獸”時,也能類比于此,將這種分別命名的方式推及其他場合(“推而別之”),直至窮盡一切對象(“無別而后止”)。
此外,墨家也以“舉”和“推”說明語詞的運(yùn)用。如《墨經(jīng)》所見,命名被界定為“以名舉實”(NO11),并分為“達(dá)、類、私”三種形式的“舉”(A78),正是指語詞可用于(1)揀選一切對象、(2)揀選一類對象和(3)揀選一個對象。在墨家,這種揀選也是服務(wù)于命名方式的類推,但最受關(guān)注的是類名的“舉”如何應(yīng)用于“推”(B1-3)。當(dāng)然,墨家所謂“推”不僅是命名的方法,更是論辯的方法,即當(dāng)人們贊同p而反對q時,可類比于p被接受情況來推廣q(NO11)。比如,為鼓吹“殺盜非殺人”,墨家專門論述了這個觀點與人們通常接受的“愛盜非愛人”出于相似的構(gòu)造(“同類”);那么,就能類比于得到“愛盜非愛人”的方式,同樣得到“殺盜非殺人”的結(jié)論(NO15)。
由上,從“舉”到“推”幾乎能被視為一種說理策略,即為了說明某個主題,需要(1)揀選或舉出有待談?wù)摰闹黝}在某一場合的狀況,(2)類比于該主題在此初始場合的狀況,推及說明它在目標(biāo)場合的狀況。比如,舉出(a)張三愛親人是道德本能,再類比于(a),推及說明(a)′張三愛陌生人也是道德本能;舉出(b)這些東西都名為“物”,但名為“鳥”的不是“獸”;再類比于(b),推及說明(b)′那些東西也名為“物”,但名為“鳥”的仍不是“獸”;以及,舉出(c)以某種方式得出“愛盜非愛人”的主張,再類比于(c),推及說明(c)′也能以相同的方式得出“殺盜非殺人”的主張。因此,無論這種說理策略被用于談?wù)撌裁矗瑨x式的“舉”正都服務(wù)于類比式的“推”。也正因此,當(dāng)主題被設(shè)定為類時,就能說對類的“舉”同樣服務(wù)于“推”,即除了是在某一場合“舉相似”,還要類比于此,推及另一場合中“舉相似”。 例如,孟子說的“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獨(dú)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告子上》),就是類比于在一個場合舉出人有相似之處,推及在另一場合也舉出人有相似之處。因此,只要初始場合I中的a,b都有特征θ,目標(biāo)場合T中的c,d也有θ,就能建立一個類比是:
(1)T中舉出c相似于d,〈猶如〉I中舉出 a相似于b
鑒于相似關(guān)系正是中國式的類,以上類比也能表示為:
(2)T中舉出c與d同類, 〈猶如〉 I中舉出a與b同類
由此,就能看出類概念在中國思想中的基本用法是做類比。
但在這種以類或相似關(guān)系為核心的類比,并不是唯一形式的類比。因為類比雖然仰賴相似,卻不是類比項成員在特征上的低階相似,而是類比項的結(jié)構(gòu)(structure)和做類比的目的(purpose)決定的高階相似,(11)參見Keith J.Holyoak, Paul Thagard, Mental Leaps: Analogy in Creative Thoughts, MIT, 1996,p.137。尤其是場合間的關(guān)系對應(yīng)。(12)參見斯坦哈特《隱喻的邏輯:可能世界之可類比部分》,蘭忠平譯,商務(wù)印書館2019年版,第136頁。比如,T中的事物存在關(guān)系R,I中事物也存在關(guān)系R,就能以R為中心在兩個場合的事物之間建立類比:
(3)T中的c, d具有R, 〈猶如〉 I中的a, b具有R
其實,連接詞“猶如”表達(dá)的就是高階的相似,即T中存在關(guān)系R,這一狀況相似于I中存在關(guān)系R。但關(guān)系R不必定是相似關(guān)系,即低階的事物的相似。比如,孟子說的“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僅是將“理義”之于“心”的關(guān)系(T中的c取悅了d)類比于“芻豢”之于“口”的關(guān)系(I中的a取悅了b),卻并不意味“理義”與“心”或“芻豢”與“口”是相似的,因為二者的特征完全不同。再比如,漢儒董仲舒說的“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同樣不是說性與禾或善與米相似,而是說,善與性的關(guān)系(T中的c出自d)相似于米與禾的關(guān)系(I中的a出自b)。所以,類比項的相似或同類不是做類比的前提。
相反,若只有相似的東西才能類比,這將是非常嚴(yán)格的類比,即類比項始終要遵循相似關(guān)系或類的限定,否則就會導(dǎo)致墨家所說的“推類之難”(B2)。其例子是對某物“謂四足”(B3),這個主張要能被類推到不同場合,要明確它說的是(1)牛四足、(2)馬四足還是(3)獸四足。因為,如果初始場合的“謂四足”說的是(1),目標(biāo)場合說的卻是(2)或(3),就并非同類主張的類比推廣(“推類”),而是在不同場合提出了不同的主張。反之,如果允許初始場合的(1)被類推為目標(biāo)場合的(2)或(3),則意謂它們是相同的主張,談?wù)撝嗤臇|西。但這顯然是荒謬的,因為任何“謂四足”的主張沒差別,墨家認(rèn)為,就相當(dāng)于說所有四足的東西都是麋鹿(“俱為麋”)。因此超出類的限定,任何主張都難以推廣(“推類之難”)。于是,墨家又提出“止類以行,說在同”(B1)的原則,正是指:肯定事物如此,便始終做出斷言;否定事物如此,則始終表示質(zhì)疑,類推到各個場合的只是相同的主張(“說在同”),所以要以類為限(“止類”)。很明顯,這說的還是“類”的范圍決定了“推”的可行,因此“推類”區(qū)別于一般類比的首要特征就是它的嚴(yán)格性,即所“推”的僅只是“類”,即只是同類事物的跨場合類比。
問題是,中國古人為何設(shè)想這種特殊的,實質(zhì)是相當(dāng)嚴(yán)格的類比呢?我認(rèn)為,根源就在解釋行動問題。之前談?wù)撛缙谥袊摹爸悺敝鲝垥r,已經(jīng)指出,對類的洞見本質(zhì)上是對行動具有跨場合一致性的洞見。現(xiàn)在看來,這一洞見正關(guān)涉以類為中心的類比(“推類”)。因為沒有這種類比,類僅是描述事物特征的概念,即“知類”僅是知道事物是否相似,而與對行動規(guī)范的認(rèn)知關(guān)系不大;但當(dāng)類概念同時構(gòu)成跨場合類比的限定(類比項必須同類)時,就不僅意謂了相似性,更代表了一致性,如荀子說的“類不悖,雖久同理”(《荀子·非相》)或“推類而不悖”(《荀子·正名》),“不悖”就是對一致性的要求。而要點是,這種除了意謂相似性,也能表象一致性的類概念,正適合從描述事物的領(lǐng)域應(yīng)用到指導(dǎo)行動的領(lǐng)域。比如,參照荀子關(guān)于行動準(zhǔn)則的遞歸式論述(《非相》《天論》),可知他所謂“類不悖”主要就是對跨場合行動的要求,即:(1)“道”能貫通一切場合(“道貫”),是它所代表的行動準(zhǔn)則或“理”能貫通一切場合(“理貫”);(2)“理”能貫通一切行和,則是它所規(guī)定的行動在一切場合都“類不悖”。那么行動者遵循“道”或“理”的指導(dǎo),最終就是遵循“類”的指導(dǎo);而這種指導(dǎo)行動的類概念顯然不僅是事物相似的標(biāo)志,更在“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類度類”(《非相》)的跨場合類比中表達(dá)了對行動者必須一致行動的要求。
所以在早期中國,類概念本身被用于類比,就能歸結(jié)為對不同場合如何行動的關(guān)切,決定了人們需要一個能用來描述行動一致性的概念——而這個概念所以是類,就在于行動者試圖類比某些場合決定接下來該怎么做時,最易設(shè)想的保持一致行動的方式,就是讓類比項的成員(即初始場合與目標(biāo)場合中的行動)保持同類。是故對類的把握就構(gòu)成了以類比指導(dǎo)行動的關(guān)鍵,正如荀子指出的:
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tǒng)類而應(yīng)之。(《荀子·儒效》)
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荀子·王制》)
應(yīng)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與,以待無方。(《荀子·臣道》)
以上所見,就是同類行動的跨場合類比構(gòu)成了應(yīng)對陌生情況的行動機(jī)制。并且,因為應(yīng)變的訴求得到了突出的強(qiáng)調(diào),這種類比就呈現(xiàn)出顯著的技術(shù)意義,可說是每個追求正當(dāng)行動的人都應(yīng)掌握的行動方法,荀子則稱為“操術(shù)”:
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yuǎn)。是何邪?則操術(shù)然也。……推禮義之統(tǒng),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nèi)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nèi)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shù)然也。(《荀子·不茍》)
很清楚,“操術(shù)”正是以近知遠(yuǎn)、以小見大、以少治多的類比技術(shù)。但能被視為君子之道的核心,就在于“操術(shù)”的運(yùn)用,也即“推禮義之統(tǒng)”,始終基于對類的把握——因為在荀子看來,禮義正是統(tǒng)領(lǐng)每一類行動即“統(tǒng)類”的原則,“知通統(tǒng)類”則是成為大儒的標(biāo)志(《荀子·儒效》)。因此,禮義的價值就表現(xiàn)為它所統(tǒng)領(lǐng)的每一類行動皆能被進(jìn)行跨場合的“推類”,而類作為行動規(guī)范的意義也正是在“推禮義之統(tǒng)”的類比中呈現(xiàn)出來的。
結(jié) 語
論述至此,我的觀點可概括為:(1)中國古人眼中的類不是種屬劃分的產(chǎn)物,而是特征揀選(“舉相似”)的產(chǎn)物。(2)揀選不能任意為之(“狂舉”),要遵循同異有別和同異兼顧的規(guī)則。(3)這種揀選式分類主要服務(wù)于類比(“推類”),目的則是確保跨場合行動的一致性。因此最終,(4)類概念在中國思想中扮演的基本角色就是為正當(dāng)行動提供指導(dǎo)。現(xiàn)在,基于(1)-(4),有理由相信將類概念的確立解釋為中國古代邏輯萌芽的出現(xiàn),并不能為我們理解這個概念提供實質(zhì)幫助,也就無助于達(dá)成在中國思想中“找邏輯”的目的。不過,鑒于“邏輯”一詞的不同涵義,也可說中國古人對類的認(rèn)知代表了特定類型的邏輯(如行動邏輯)。但提出這個新主張的代價是,名為“中國邏輯史”的研究必須暫停其常規(guī)實踐,即不再是從中國文本中尋找邏輯的素材,而要退回去辨析“邏輯”的涵義。同樣,若名為“中國哲學(xué)史”的研究中也嘗試說明中國思想有特定類型的哲學(xué),也必須暫停其找素材的實踐,退回去辨析“哲學(xué)”的涵義。表面看來,這似乎是研究者校準(zhǔn)其出發(fā)點的積極嘗試。但此項工作恐怕永遠(yuǎn)無法完成,這不僅因為哲學(xué)或邏輯很難有一個通行的定義,更因為這本身就不是“中國哲學(xué)史”或“中國邏輯史”被設(shè)置為一個學(xué)科的任務(wù)。所以,上述“倒退”一旦發(fā)生(已然發(fā)生),與其說是一種研究再出發(fā)的積極嘗試,不如說是對既有研究范式的事實否定——因為在給出何為哲學(xué)、何為邏輯的新界定前,這種以“史”為名、以“找素材”為實的研究并不能有任何推進(jìn)。不過,舊范式的弱化也是學(xué)術(shù)進(jìn)步的契機(jī),讓我們有動力去探索談?wù)撝袊枷氲男路妒健1疚木劢褂陬惛拍畹挠懻摚沁@樣一種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