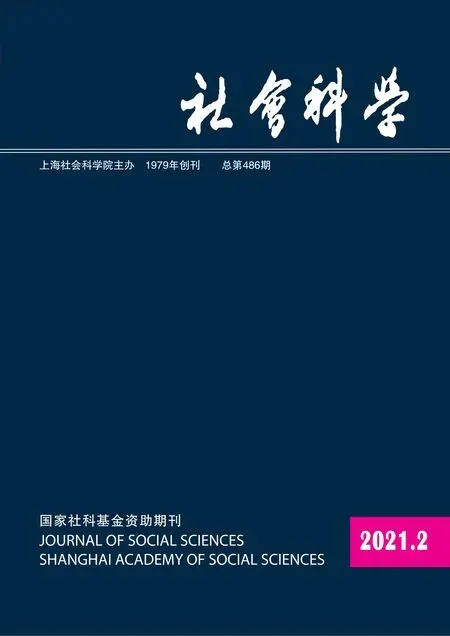個體存在:老子的價值取向*
楊國榮
一
如何理解個體存在?這是價值領域無法回避的問題。當然,對個體的考察,可以有不同的視域,老子注重自然原則,對個體的理解也以此為出發點。在談到“身”之時,老子指出:“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1)《老子·第七章》。自然作為價值領域的基本原則,并非抽象、空洞,其內涵展開于多重方面。這里的“天地”泛指自然界或一般意義上的世界,“天長地久”,表明世界是永恒的。天地為何能長久?或者說,世界何以具有永恒的品格?老子用“以其不自生”加以解釋。這里的“自”,著重的是有意而為之或追求某種自身的目的。依此,則天地之所以長久,主要在于它非有意生成,也非刻意預設永恒存在的目的,一切自然而然。在老子看來,“天地”的長久性也屬這種自然的形態。以上主要從自然的角度,揚棄自然(天地)的目的性。
以此為前提,老子進一步考察了個體的存在,所謂“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涉及的便是在社會領域的具體交往過程中,個體如何維持自身存在的問題。“后其身”即先退一步,“身先”則是居于領先之位;“外其身”是將個體自身置之度外,“身存”則是安然存在。從個體生存的角度看,這種關系表明,個體不刻意地謀求自身的生存,反而能使其更好地存在。就以上論辯而言,老子似乎又將前面揚棄的目的性重新引入進來。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對天地的規定不同于對人的理解:盡管在價值性質上,老子趨向于等觀天人,但在存在方式上,卻仍肯定了兩者的差異。天地作為自然的對象,是無目的、無意志的;但人卻無法完全擺脫目的性的追求,事實上,對于人及其活動,老子注重的是其合目的性與合法則性的統一,后者也使之有別于莊子。在以上分際中,同時包含著超驗的目的與人的目的之區分:天地不自生,表現為對超驗目的的拒斥,而個體存在(“身存”)則關乎人的現實目的。按老子的理解,在人的存在過程中,如果僅僅以主觀的目的為出發點,完全無視自然的法則,亦即以合目的性壓倒合法則性,則這種目的性的追求便需要否定。但另一方面,個體如何生存又是老子一直關注的問題。個體的生存難以離開目的性,事實上,以什么樣的方式使個體生存于世,構成了人所關切的內在問題。個體之所以需要堅持自然原則,避免以目的性消解自然的法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唯有尊重自然法則,才能使自身更好地生存。如果說,“后其身”和“外其身”表現為順乎自然的過程,那么,“身先”和“身存”則構成了個體追求的內在目的,在這一意義上,自然的原則(合法則性)并非疏離于目的性。
以上引文最后提到,“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方面,這里涉及某種處世方式并表現出向權術、謀術等方面演化的趨向:“以其無私”而“成其私”,與“將欲奪之,必固與之”(2)《老子·第三十六章》。等表述,顯然前后呼應,這種“在”世方式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容易取得權謀的形式;另一方面,與“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一致,其中又包含對個體存在,包括以“身”為表征的生命存在的注重。在老子那里,兩者相互糾纏,從一個方面展現了其思想的復雜性。
在如何對待寵辱等不同境遇的問題上,對個體存在的關注得到了另一重展現:“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3)《老子·第十三章》。這里再次肯定應當注重“身”,并將“身”提到重要的位置。“寵”和“辱”是人在世俗中的兩種境遇。“寵”意味著得志,“辱”則表現為失意。然而,在老子看來,不管是“寵”(得志),還是“辱”(失意),都不是人理想的在世方式。在當時的背景之下,“寵”或“辱”,往往有天壤之別,但個體即使受寵,也無法改變被支配的命運:“寵”的結果無非是成為統治者的依附者,由此,個體往往遠離本然形態,難以真正實現自身的價值。一旦受“辱”,則更意味著失去自身的內在尊嚴。所謂“寵辱若驚”“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便體現了以上狀況。
從表層看,老子對“身”的關注,前后似乎存在某種張力。“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蘊含著輕“身”或去“身”的觀念。人世種種災禍的出現都與“身”相關,如果沒有“身”,人在世間所遭遇的一切都不復存在。同樣,榮寵也與“身”相關。王弼在解釋“何謂貴大患若身”時,曾指出:“人迷之于榮寵,返之于身,故曰‘大患若身’也。”(4)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第十三章》,載《王弼集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9頁。在此,“身”構成了“榮寵”的承擔者。作為一切問題發生的根源,“身”若不存,則與“身”相伴隨的一切問題也就消解了。從邏輯上看,這種觀念將導向“輕身”或以超脫的眼光來看待“身”。然而,后面“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卻表現出“貴身”“愛身”的意向,這與前面對“身”的看法似乎不相一致。不過,如果做進一步的考察,便可注意到,老子在此所討論的,實質上是兩重意義上的“身”:其一是世俗視域中的“身”,這種“身”,也可以看作是“名利之身”,世間的“大患”,包括災禍、“榮寵”,都以這種“名利之身”為承擔者。以這種“身”去追求名利、追求“榮寵”,往往會招來“大患”,所謂“無身”,主要便趨向于消解這一意義上的“身”。其二是與自然或“道”為一的“身”,這一意義上的“身”不再是名利的載體,而是與整個自然合而為一,“貴以身為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之“身”,主要便指以上之“身”。消解名利之身,回復到與“道”為一之“身”,這就是“貴身”的真正意義。唯有達到“身”與自然、“身”與天下為一的境界,才能實現“身”的意義。這一看法在實質的層面上,展現了對個體存在的肯定,它所體現的是老子內在的價值取向。
在“身”與“名”、“身”與“貨”的比較中,以上取向得到了更明確的體現:“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5)《老子·第四十四章》。與前述之“身”相近,這里的“身”也可以理解為具體的個體或人的生命存在。對個體而言,其生命存在(身)與外在名利之間,哪一個更重要?“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的追問將這一問題直接地提了出來,后面“得與亡孰病”,則在更普遍的層面追問名利得失的問題。盡管此處主要是提出問題而沒有給出答案,但其內在結論已經隱含于其中:按老子的理解,相對于外在的“名”和“利”,個體的生命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后面“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便是從這一角度立說:過度關注于名利,反而會付出沉重的代價。這一推論的前提是對立的兩個方面可以相互轉化,所謂“反者,道之動”。從“身”與名利的關系看,離開“身”而追求名利,將導致消極的后果。
“身”與感性、具體的個體聯系在一起,與肯定“身”相應,老子也關乎“長生”、養生等問題,通過“知足”、“知止”、淡泊名利以獲得“長久”,便表明了這一點。從其整個哲學構架看,“道”盡管內在于萬物,但它本身主要表現為超感性的存在,無法以感性的方式加以把握。然而,在老子看來,超越感性的“道”與有生命的“身”之間,并不相互對峙,二者具有相關性,可以并重:一方面,生命的維護、“身”的持久存在,離不開循乎普遍之道;另一方面,在追求超驗之道的同時,也不能遺忘作為感性生命承擔者的“身”。在某種意義上,“身”構成了形而上之“道”與形而下的存在溝通的具體載體之一。與以上進路相應,在“身”的理解方面,老子與儒家存在內在差異。儒家主要把“身”視為德性的承擔者:儒家所說的“修身”,其實質的含義是涵養德性。相對于此,老子更多地將“身”理解為個體天性的載體。
二
對個體存在價值的肯定,以個體與社會或個體與群體的關系為背景。由此引向天人之辯,便涉及在更廣意義上對人的理解。以后者為指向,老子指出:“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6)《老子·第五章》。在老子那里,天人之辯首先關乎以“天”(自然)觀之。從自然的觀點來看,整個宇宙中一切對象都是平等的,其間沒有差異。天與人之間,也同樣如此:人首先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作為生物學意義上的對象,人與其他事物并無不同。“芻狗”即以草扎成的狗,用以祭祀。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肯定的便是萬物之間的無差別性。與“萬物”相對的是“百姓”,在這里,“百姓”主要泛指不同于“物”的“人”,由“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引出“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意味著將自然原則運用于社會,強調天人之間、人與人之間不存在根本不同。
這里的“不仁”,首先表現為對“仁”的否定。如所周知,“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在孔子那里,“仁”既意味著肯定人之為人價值,也引向以人觀之,即從人的角度看問題。與之相對,老子所突出的,是以天觀之或以自然觀之,后者較之孔子的“以人觀之”表現為考察世界的不同方式,由此形成的價值判斷,也展現了重要的差異。從“仁”或以人觀之的角度看,人是整個世界中最有價值的存在:天地之中,人最為貴。這也是儒家反復強調的觀點。然而,從以天觀之或自然的觀點來看,儒家的這種價值原則便失去了前提。所謂“不仁”,便趨向于消解儒家以人觀之的價值觀念,并由此凸顯自然的原則。以上引文著重從價值論的角度,將“道”引向社會領域,并把自然的原則提到突出地位。
從天地自然的角度看,萬物都是平等的,不同的事物之間沒有優劣之分,也沒有價值的高低之別。如果將這一原則運用到社會領域中,則同樣應肯定,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價值上的高下、貴賤等等區分,所謂“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便表明了這一點。在本體論上,萬物都是齊一的,后來莊子將其進一步引申為萬物一齊、道通為一,認為世界最原始的存在狀態是“未始有封”,即它一開始并沒有界限:“封”在這里有界限之意。在莊子看來,從“道”的角度看,不應該對事物作種種區分,這一意義上的超越分界更多地帶有本體論意味。就價值觀的角度而言,此處似乎還包含超越以人為中心的趨向。儒家的仁道的觀念傾向于以人觀之,其基本要求是以人的存在價值為中心來考察萬物,儒家一再強調天地萬物人為貴,便表明了此點。《老子》“天地不仁”的觀念則在一定意義上表現了試圖消解把人視為萬物中心的觀念,這也構成了后來道家前后相承的思路。
從理論上看,這里涉及對所謂“人類中心”的理解。“人類中心”是現在經常提到的話題,對它的討論以批評居多。然而,如果從歷史的觀點看,恐怕對此也要作一些具體分析。在某種意義上,完全地超越人類中心可能是很困難的,從人自身的存在出發看待事物、看待存在、看待世界,是人難以避免的存在境域。現代的生態倫理、環境哲學強調天人和諧,反對生態破壞,通常將此視為對人類中心的超越,但事實上,重建天人統一、恢復完美生態,等等,從終極的意義看,乃是為了給人提供一個更好的存在處境:天人失調、環境破壞之所以成了問題,是因為它危及了人本身的存在,就這一意義而言,完全超越人類中心,本身似乎缺乏合理的根據。此處可以將狹義的人類中心論與廣義的人類中心論作一區分。寬泛地看,人類當然無法完全避免“以人觀之”,所謂生態危機、環境問題等在實質上都具有價值的意味:如上所述,生態、環境的好壞,首先是相對于人的存在而言,無論維護抑或重建天人之間的和諧關系,其價值意義都與人自身的生存相關。從這方面看,廣義的人類中心確乎難以完全超越。然而,在狹義的形態下,人類中心論所關注的往往僅僅是當下或局部之利,而無視人類的整體(包括全球及未來世代的所有人類)生存境域,由此所導致的,常常是對人的危害和否定,這一意義的人類中心論,最終總是在邏輯上走向自己的反面,它也可視為狹隘的人類中心論。籠而統之地否定人類中心,往往會導致一種虛幻、詩意、浪漫的意向,這一點在時下的后現代主義觀念及對所謂現代性或近代哲學的批判中經常可以看到:在后現代主義那里,詩意的想象常常壓倒了對人類現實的社會歷史過程的關注。老子哲學以自然為理想的形態,這一視域往往與批評文明的演化相聯系,其中每每流露出對文明歷史進步的疑慮,后者既具有提醒人們避免天人沖突的意義,也隱含著某種消極的歷史意向。
在本體論上,老子強調以“道”觀之,物無差別。從價值觀看,老子則肯定以“天”觀之,天人如一。相對于通過確認“身”以突出個體的存在價值,這里更多地從類的角度,強調人的存在與自然(天)的相通性。盡管側重不同,但都基于自然的原則:如前所述,個體之身的價值意義在于與自然為一,天人之辯中人的存在品格,同樣以自然為根據,在本于自然原則這一點上,二者彼此一致。
從價值觀的層面看,天人之辯同時關乎“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區分。盡管老子從自然的角度趨向于等觀人與天,但以“道”為視域,他仍對“天之道”與“人之道”的不同涵義作了考察:“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7)《老子·第七十七章》。這里首先在肯定“天之道”的前提下,提出了如何達到均衡的問題。“天道”所體現的是某種均衡狀態:不足的加以增補,多余的加以消除,所謂“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然而,這種均衡是通過合乎自然的調節而達到的,其過程猶如射箭,“高者抑之,下者舉之”,由此達到適當的平衡。“人之道”則相反,剝奪貧者,補償富者,亦即“損不足以奉有余”,由此加劇貧富不均。對“人之道”的以上批評,表現為寬泛意義上的社會批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貧富不均屬廣義的社會不均衡,對老子而言,自然均衡既是本然的形態,也是理想的狀況,與肯定萬物平等、天地間所有事物無價值上的高下之別一致,在社會領域,老子要求從不均衡回歸自然均衡。
如何讓社會在擁有的資源、財富方面達到平衡,是社會運行和治理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現代社會通過社會資源的再分配,以避免人們在資源占有方面過于兩極化,也體現了這一現實要求。老子以“損有余而補不足”為達到社會均衡的“天之道”,無疑也提供了解決以上問題的思路。當然,對達到均衡的方式以及如何看待相關目標的實現等方面,老子又有自身的看法:“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初看,這句話與前面所述似乎沒有直接關系,但事實上并非如此。這里所說的“圣人”,可以視為上述“有道者”,亦即真正把握了“道”或對“道”有所體悟的人。在老子看來,只有這種“有道者”,才可能通過自身調節,回歸自然的均衡。這一意義上的“得道者”的特點,在于一方面堅持達到自然的均衡,另一方面又不因此而據以為功,而是將其理解為自然而然的過程。老子曾反復提到“為而不恃”,其要義在于強調人的所為是一個“為無為”的自然過程,這里所表達的是相近的含義。從存在形態來看,社會均衡既是理想的目標,也是自然原則的題中應有之義;就人之所為而言,達到或回歸社會的均衡也是一種自然的過程,兩者從不同的方面體現了“天之道”。
對“天之道”與“人之道”的區分,無疑有其值得注意之點。作為存在的普遍原則,“天之道”同時表現為自然原則;“人之道”則指與有意而為之的行為相關。在不同的語境中,“道”的含義可以有所不同。在寬泛的層面上,“天道”和“人道”分別表示普遍的宇宙法則和社會領域中的原則;就社會領域而言,“人道”本身則可以被賦予不同的意義:它既可以與“天道”相對而表示社會之域的存在法則,也可以指“有意而為之”的特定行為原則,所謂“損不足以奉有余”,即是后一意義上的“人之道”。對老子來說,在行為過程中,人應當選擇的,首先是合乎自然意義上的“天之道”。
三
由等觀天人,老子進而對偏離自然的價值觀念和價值規范提出了種種批評。在談到道與仁義等關系時,老子指出:“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8)《老子·第十八章》。這里所說的“仁義”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去理解:從廣義上看,“仁義”表現為約束社會成員的普遍規范或一般準則;在狹義上,“仁義”則與儒家所提倡的價值規范相聯系。老子對仁義的理解,同時包含以上兩重含義。就前一方面而言,問題涉及“道”與一般社會規范之間的關系:社會規范是如何出現的?“道”本來處于未分化的狀態,以混而為一的方式存在,在這種形態之下,既不存在對象之間的區分,也不存在社會領域中不同的行為以及約束多樣行為的規范。從這一角度看,作為一般規范的“仁義”并不是“道”的題中應有之義。“道”本身拒斥分化并以統一的形態存在,只有當這種統一形態被破壞之后,才由“道”分化出各種現象:從自然來說,經驗世界中的山川草木等等對象由此形成;從社會來看,不同階層和領域的區分以及引導處于相應階層與領域的行為的不同規范也隨之產生。規范以分化為前提,“道”則以統一為其特點,在這一意義上,兩者顯然不同。
后面提到的“慧智”和“大偽”,其間關系也與上述情形有相類之處。“慧智”近于“知識”或世俗之知,與今天所理解的“智慧”正好相對,所謂“慧智出”,也就是“世俗之知”的形成,這種“知”一般被用作獵取名利的手段,其形成往往導致“偽善之舉”:為了達到某種名利的目的而刻意地做出合乎規范的行為即與之相關。與上述現象相聯系的是“孝慈”和“忠臣”。在原初純樸的形態下,并不存在這一類現象和人物,也不需要對其加以提倡和表彰。只有當社會成員之間發生了問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緊張,包括家庭成員間出現“六親不和”這一類現象,“孝慈”才成為需要加以倡導的品格:如果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本身和諧和完美,“孝慈”等要求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同樣,在廣義的政治領域中,只有當出現了政治秩序失衡、“國家昏亂”等情況之后,才彰顯出“忠臣”的價值,如果政治秩序處于和諧狀態,則“忠臣”作為榜樣的感召力也就失去了意義。(9)“大道廢,有仁義”,帛書乙本作“故大道廢,安有仁義”,郭店竹簡《老子》殘簡也作“故大道廢,安有仁義”。這里的“安”可作“因而”解,也可釋為“怎么會”,前者意味著“大道”與“仁義”之間的不一致(“大道廢”導致“仁義”出),后者則肯定了“大道”與“仁義”之間的一致性(無“大道”,則也無“仁義”),二者側重雖然有所不同,但在以“大道”為主導這一點上,又具有相通性。
這里同時可以注意到儒道之間的差異。從一個方面看,儒家并不完全否定自然的觀念,在追溯“仁”、“孝”等概念時,早期儒學總是最后追溯到人的自然心理情感。如孔子講到“孝”和“三年之喪”時便認為,守三年之喪,是出于子女對父母的自然情感,這種情感構成了孝的原始根據。然而,在對既成社會規范的理解方面,儒家往往趨向于承認這種規范的價值。與儒家相對,老子則對社會規范本身持質疑的態度,這種質疑多少緣于社會規范容易導致作偽:一旦標榜或提倡某種原則和規范,就會出現刻意仿效、有意為之以博得外在贊譽的行為,此即老子所說的“大偽”。在老子看來,唯有保持“道”的原初形態、遠離各種社會規范,才能從根源上消除“偽善”,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等等,主要就此而言。
從歷史的層面看,由未分到分化是文明發展的必然趨向,因此,問題不在于拒斥這樣的分化,而是如何在分化之后重建統一。這種統一不同于回復到原始的未分化狀態,而是在既分之后使統一的形態在新的層面得到重建,社會的規范則是重建這種統一的必要手段,對于這一點,老子顯然缺乏充分的把握,比較而言,儒家在這方面更多地展現了歷史的意識。
社會中出現的各種負面現象既然主要根源于悖離自然之道而形成不同文明的規范和文明的產物,則消除這種現象的前提,便在于拒斥如上的文明規范和產物。以此為視域,老子進一步提出了如下主張:“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10)《老子·第十九章》。從字面的意義上看,“絕圣棄知”中的“圣知”、“絕仁棄義”中的“仁義”、“絕巧棄利”中的“巧利”,都與自然相對而表現為世俗的品格或世俗的價值規定。在老子看來,“圣知”是導致各種社會問題的緣由;“仁義”作為約束人行為的規范,其出現本身是因為社會發生了問題;“巧利”則是偷盜等社會現象產生的根源。唯有拋棄這些價值規定,回到自然的存在形態,才能避免各種負面的消極后果。為什么“絕圣棄智”就能引向“民利百倍”?“絕仁棄義”就可達到“民復孝慈”?其根本的原因在于,通過“絕圣棄智”“絕仁棄義”,各種文明的價值規定和規范便可被消解,人則將由此回復本然的天性,社會也可復歸沒有等級分化、沒有利害沖突的存在形態,以此為前提,人的存在價值可以得到充分實現(“民利百倍”),合乎本然之性的淳樸風尚也將回歸(“民復孝慈”)。同樣,財富的存在是人的欲望萌發的根源,如果不存在這些財富或者不把它們看作財富,就不會有千方百計地試圖占有、獲取的沖動,也不會發生以非正當(如偷盜)的方式去攫取的現象。在第三章中,老子已提及,偷盜等現象的出現,是因為有“難得之貨”,“不貴難得之貨”,便可以“使民不為盜”,所謂“絕巧棄利,盜賊無有”,主要從人的價值取向這一角度,表達了類似的觀念。
以上更多地從否定的視域,對“圣知”、“仁義”、“巧利”等文明規定作了抨擊。后面則側重于肯定之維。“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意味著揚棄外在的文飾,回復本然之性。“素”本來是指沒有染過的絲,在此隱喻本然的規定,“樸”是未經雕琢之木,也喻指事物的本然形態。可以看到,老子注意到了知識、規范、財富可能引發的消極意義。確實,在文明化的社會中,普遍的規范可能導致各種偽善之舉,財富會激發人的各種欲望,“圣知”、“仁義”、“巧利”則可能成為名利的工具,這些現象都表現為負面的存在形態。然而,歷史地看,知識、規范、財富對人的存在本身并不僅僅具有消極的意義,走向合乎人性的社會形態,事實上也無法完全拋卻以上方面。老子對以上規定完全持否定的態度,無疑僅僅見其一而未見其二,其思維進路也相應地呈現抽象的性質。
順便提及,“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在郭店竹簡的《老子》殘篇中表述為:“絕智棄辯,民利百倍;絕巧棄利,盜賊亡有;絕偽棄慮,民復孝慈”,后者與通行本的主要差異在于沒有提及“仁義”。然而,從哲學的層面看,兩種表述在實質上并沒有根本的區別。前面已提及,“仁義”可以作廣義或狹義的理解,從狹義上說,它們與儒家提倡的特定價值原則相一致,從廣義上看,則可以泛指一般的社會規范系統;與之相應,對仁義的批評,既針對儒家的倫理原則,也涉及一般的規范系統。對老子而言,世俗之智及社會規范系統(包括儒家的倫理原則)之所以應當疏離,主要在于它容易偏離本然之性而導致偽善之舉,前面提到,一旦本然之道被拋棄、世俗之智得到發展,便常常容易引發各種外在之“偽”,所謂“大道廢,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偽”。郭店竹簡的老子殘簡所說的“絕智棄辯”、“絕巧棄利”、“絕偽棄慮”,事實上也體現了類似的思路,盡管以上表述沒有提及“仁義”等規范,但其實質的指向,同樣涉及這類規范:“智”和“辯”、“巧”和“利”、“偽”和“慮”、“仁”和“義”在價值的層面處于同一序列,運用“智”和“辯”、“巧”和“利”、“偽”和“慮”往往將導致雖合乎仁義等外在規范但卻悖離自然之性的偽善之舉;“絕智”、“絕巧”、“棄慮”等等,便旨在消除以上行為的觀念根源。
從社會的層面看,普遍的文明規范往往以“禮”為其外在的形式,由此,老子對“禮”提出了更為尖銳的批評:“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11)《老子·第三十八章》。相對于仁義、圣智,“禮”作為規范更多地具有外在性甚至強制性,從而與老子所推崇的自然原則相距更遠,故老子稱其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這里同時提到“前識”的問題。“前識”通常被置于認識論的視域之下,但聯系前后文可知,這里的“前識”不僅限于認識論意義上的先天觀念或詮釋學上的“前見”。一方面,它意味著以先在的動機為整個行為的出發點:動機相對于后面的行為過程而言,乃是先在的“前識”;另一方面,普遍的規范較之個體意識而言,也帶有先天的性質,事實上,不管是普遍意義上的邏輯規則,還是道德意義上的社會行為規范,都先于特定個體而在,與之相聯系,這里的“前識”并非僅僅指“前人而識”(12)王弼:《老子道德經注·第三十八章》,《王弼集校釋》,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4頁。:所謂“前人而識”,主要指先于他人(其他個體)而對特定事物有所了解,從更為內在的層面看,與前述“仁”、“義”、“禮”相關的“前識”,具體指對這些先在規范(“仁”、“義”、“禮”)的了解,爾后按其要求有意而為之。在老子看來,以上二重意義的“前識”都與“自然”的原則相對,屬于“道之華而愚之始”。老子以拒斥“前識”為“在”世的基本方式,體現的是“道法自然”的價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