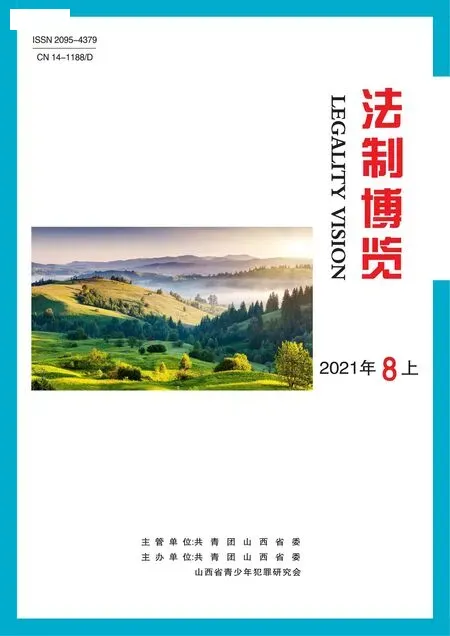我國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認定問題研究
欒思遠
(河北大學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一、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概述
(一)家庭暴力的特征
在討論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認定問題之前需要對該類犯罪的特點加以明確。
第一,家庭暴力對象是特定的。家庭暴力的特殊首先體現在它所針對的對象局限于一個較為封閉的家庭環境之中。但在現代社會中,封閉的家庭環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家庭中的角色也不斷擴展和更新,例如同居的夫婦等,再加之女性權利覺醒等因素的影響,家庭內部中對男性的暴力行為也很普遍,使得家庭暴力犯罪問題越加復雜,司法工作人員的工作壓力也隨之增加[1]。
第二,家庭暴力具有隱蔽性。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組織之一,是人類最基本最重要的一種生活形式,由于其多以住宅這種封閉性場所為表現形式,因此發生在家庭內部的家庭暴力具有相當的隱蔽性。此外,由于中國傳統的家庭文化影響,受到家庭暴力傷害的家庭成員一般也不愿意向社會公眾尋求幫助,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家丑不可外揚”。與此同時,我國公權力對家庭糾紛的介入力度不夠,很多家庭糾紛就是因為發現不及時,外界介入遲緩,最終演變為家庭暴力。以上因素綜合決定了家庭暴力犯罪與一般的暴力犯罪相比取證較難。
第三,家庭暴力具有反復性。較為封閉且穩定的家庭環境直接導致了暴力雙方會有較長的接觸時間。此外,此類案件往往不會因為一次暴力行為就導致犯罪案件的發生,被害人大多情況下會因為傳統家庭觀念和對施暴者的恐懼而進行妥協,導致家庭暴力開始循環往復、依次遞進地發生,最終轉化為暴力犯罪。
(二)家庭暴力犯罪中的防衛行為認定
上文已經對家庭暴力犯罪的隱蔽性、復雜性進行了相關介紹,由于家庭暴力犯罪的種種特性,被害人很難尋求來自社會力量的救濟,我國的司法機關在面對該類案件多以“家務事”為由主給事人自行處理。當面對家庭暴力的魔爪,并且無法得到來自其他力量的援助時,大多數家庭暴力犯罪的被害人會選擇拿起武器進行防衛,我們這里簡要介紹一下防衛行為的幾個必備要素:
首先,是不法侵害的客觀存在。根據學界通說,不是所有情況下家庭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都可以實施防衛行為,而要以其面對客觀存在的不法侵害作為前置條件。筆者所述的不法侵害并非僅包括犯罪行為,由于被害人并不能預見到其所遭受的暴力行為可能會發展成犯罪行為,因此應當放寬被害人實施防衛行為的前提條件,將一般違法行為納入其范疇中。
其次,防衛人在實施防衛行為時其必須具備主觀上防衛的意思表示。換言之,防衛人在實施防衛時必須認識到自己正在遭受不法侵害,防衛人在認識到自己面臨不法侵害的危險后,在這種主觀認識的指導下進行一系列的防衛措施。同時,防衛人的意思表示應當是故意,如果防衛人欠缺這種故意的防衛意思,那么該防衛行為就違背了刑法學中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該防衛行為缺乏客觀科學的理論支撐,在該理論體系下不應當構成正當防衛。
最后,被害人所進行的防衛必須是對不法侵害人本人的防衛。這是傳統意義上對“不法侵害人”的認定。中國的家庭構成不同于國外,不僅包括妻子、丈夫和子女,還有其他的家庭成員。例如,有的家庭是妻子同丈夫一家一起生活,當發生家庭暴力時,妻子不僅會受到來自丈夫個人的暴力行為,還可能受到來自丈夫一家人的欺辱,這個情況應該如何認定?筆者認為,家庭中的其他家庭成員對施暴者的幫助行為應當被認定為是幫助犯,如果這種幫助行為構成了對被害人現實緊迫的威脅,例如甲的哥哥給甲遞刀去砍殺自己的妻子乙,那么乙對甲的哥哥的防衛行為應當構成正當防衛;如果其他家庭成員對施暴者的施暴行為給予放任,并阻止被害人尋求界外幫助,例如,甲的弟弟阻止自己的妻子乙外逃,放任甲去追打乙,乙對甲進行的防衛同樣也應當構成正當防衛;但如果其他家庭成員僅僅是對施暴者的施暴行為進行放任,既沒有對施暴者予以幫助也沒有阻止被害人尋求幫助,那么該家庭成員僅構成一定程度下的不作為犯罪,被害人不能對其進行正當防衛。
(三)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的認定
1.防衛限度。正當防衛的認定要求被害人所采取的制止施暴者進行施暴的行為,是不能超過必要限度的。由于家庭暴力犯罪發生在家庭內部,而家庭又是一個與外界相對隔絕的封閉空間,因此很難對施暴者所實施的不法侵害的程度進行認定。司法實踐中,由于家庭暴力犯罪存在取證困難、認定困難的阻力,因此各級法院一般都不將防衛人造成重傷或死亡的行為認定為正當防衛。筆者認為這種判決方式存在漏洞。在一般情況下,殺人或傷人行為屬于犯罪行為,如果防衛人的生命權受到相當緊迫的威脅時,法律會賦予其傷人甚至是殺人的權利,就像法諺語所說:“自然理性允許人們在危險之中防衛自己。[2]”正當防衛中的特殊防衛就貫徹了這一原則。家庭暴力犯罪由于具有反復性和長期性,被害人在多次遭受家庭暴力侵害后,他們的身體和心理承受了巨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被害人很難再憑借自己的理性去分析其所面臨的暴行的程度,更無法準確進行與之相匹配的防衛行為[3]。筆者認為,在“以暴制暴”行為發生時,家庭暴力的被害人在遭受暴力侵害時,往往對自己處境預估不準確,因此在認定家庭暴力犯罪中防衛行為限度時應當將被害人此前所遭受的暴力虐待與被害人此時此刻的精神狀態考慮在內。
2.防衛時間。防衛時間是正當防衛成立的另一項客觀要件,它是指在哪一時間節點下防衛人防衛行為可以構成正當防衛。學界主流觀點認為,防衛時間應當與被害人的法益相關聯,當被害人的法益受到現實緊迫的危險時,被害人的防衛行為才會被放置在合法的框架內,而將這種法益狀態轉化為一種現實情況就應當是施暴者已將開始實施不法侵害,并且尚未停止。如果將這一理論運用于家庭暴力犯罪中,只有在施暴者已經開始施暴并且尚未結束的過程中被害人的防衛行為才能夠被認定為正當防衛。筆者認為這種規定未免過于苛刻,家庭暴力犯罪與其他暴力犯罪相比,其發生的頻率較高,犯罪周期較長,性質惡化的可能性較高,整體發展趨勢是一個螺旋上升的形態[4]。此外,家庭暴力犯罪中的施暴者往往會在身體素質和家庭地位等方面形成對被害人的一種不對等的優勢,在這種不平等的環境下,別害人一方的防衛能力和防衛條件被進一步的壓縮,學界主流的防衛時間理論難以在該種情況下得到較為理想的運用。在家庭暴力爆發時,要求被害人立刻戰勝自己的恐懼準確無誤地在犯罪過程中進行防衛是不現實的。筆者認為,在認定家庭暴力犯罪中不法侵害是否“正在進行”應當分情況討論:對于暴行頻率不高的家庭暴力犯罪,應當嚴格將施暴者實施暴力的這一過程認定為不法侵害“正在進行”;而對于暴行極其頻繁的家庭暴力犯罪,應當適當擴大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的范圍,可以將施暴者實施犯罪之前以及之后的一段時間都包括在內。
3.不法侵害必須具有緊迫性。對所謂不法侵害具有緊迫性這一概念的理解,學界的觀點并不統一。有學者認為不法侵害人進入侵害現場就已經構成緊迫性,這種觀點過于寬泛,不分情況地給予防衛人過多的防衛自由,容易適得其反,引起司法秩序的混亂[5];也有學者認為判斷施暴者所實施的不法侵害是否緊迫應當以被害人的法益是否直接面臨侵害或者施暴者制造的危險能否直接轉換為侵害為根據,但這種判斷標準依舊沒有對家庭暴力犯罪給予針對性變通,依舊沒有脫離不法侵害正在進行這一體系標準。筆者認為,家庭暴力犯罪的特殊性就決定了應當根據案件事實區分情況討論正當防衛認定中的緊迫性要件,不法侵害的緊迫性認定不僅要考慮到被害人的法益直接面臨不法侵害的情況,還應該考慮到家庭暴力下的被害人已經感知到侵害行為的緊迫這種情況。被害人由于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侵害,對施暴者的生活習慣以及性格脾氣十分熟悉,對于自己何時會遭受暴行具有一定的預知性,對已經預知自己將要遭受來自施暴者的暴行而進行的防衛應當被允許,當然,要對這種預知行為進行嚴格限制,明確規定可預知的依據和限度,否則容易構成假想防衛。
二、我國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司法認定分析
前文筆者從理論層面上分析了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認定的理論基礎和問題所在,放眼到司法實踐領域,我國目前針對該類案件的處理依舊存在司法認定不清,量刑不均的問題。對此,筆者援引典型案例對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司法認定問題加以分析。
(一)典型案例
張某與劉某是一對夫妻,平時因為性格原因感情一直不和。某日,張某在翻看丈夫劉某的手機時發現劉某與一名女子的曖昧聊天記錄,張某質問劉某此事,劉某矢口否認,并且惱羞成怒毆打張某,同時威脅張某不能跟自己離婚,否則打死張某。張某因懼怕劉某再次對自己施暴繼續和劉某生活,在這期間劉某經常因為生活瑣事侮辱張某并對其施暴。某日,劉某酒后回家,張某知道劉某有酒后毆打自己的習慣,在長期忍受劉某家庭暴力的情況下,張某的心中產生了反抗的想法。夜間,張某趁劉某睡著后,手持家中的錘子對劉某的頭部擊打數下,劉某經醫院搶救無效后死亡,案發后,張某主動向公安機關自首。法院經過審理認為,張某的行為已經構成故意殺人罪,考慮到案發前劉某長期虐待張某存在重大過錯,張某在案發后主動投案自首,對張某可以依法從輕處罰,最終法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張某有期徒刑4年。
(二)問題分析
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法院認定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實施的防衛行為構成正當防衛的情況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在大部分家庭暴力犯罪中,被害人與施暴者存在身體素質差距過大的情況;或者由于被害人身處于封閉的家庭環境中沒有進行防衛的條件;或者被害人存在對施暴者的恐懼心理,在遭受施暴人的暴力行為后被害人不會立刻實施防衛行為。而又因為家庭暴力具有反復性的特征,被害人在施暴者長期施暴的情況下,心理和身體上都達到了極限,而最終選擇使用暴力對施暴者實施反抗行為。在一些司法實踐中,法院對遭受暴力的婦女的防衛行為給予否認,多數情況下會認為其是在進行一次有預謀的故意殺人行為。筆者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在家庭暴力案件中,受害婦女長期遭受丈夫的身體與心理上的暴行,在密閉的家庭環境下,無力當面反抗在體能上強過自己的丈夫,只能選擇在丈夫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反抗。此外,我國司法實踐針對類似這種家庭暴力犯罪中“以暴制暴”的案件普遍存在量刑過重的問題。針對以上這些問題,筆者認為可以引入“受虐婦女綜合癥”理論,并且通過將正當防衛認定的“緊迫性要件”改為“必要性要件”進行處理。
三、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認定的完善路徑
(一)對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的“時間條件”的完善
對于“不法侵害已經開始尚未結束”這一時間要件的認定標準,上文已經介紹我國學界存在四種觀點。但是這幾種學說都難以解釋家庭暴力犯罪中的一個棘手問題,即被害人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無法尋求公力救濟,并且被害人已經預見到施暴者即將進行下一次暴行且無法避免這次暴行,受害者基于這一環境下所實施的傷害行為。在筆者看來,被害人在該情況下選擇在一個暴力行為停止后,或者下一暴力行為發生前釆取反抗行動應當被允許的,但是這種既符合社會大眾認知標準又符合法理依據的行為卻在司法實踐中無法構成正當防衛,而是被曲解為被害人出于報復心理所進行的有預謀的“犯罪”,這是難以理解和接受的。對此,筆者建議,在認定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的時間條件時應當著重考慮到被害人在遭受家庭暴力犯罪時的精神狀態以及內心真實意思表示,在合理的范圍內擴大時間條件的適用范圍,從而彌補我國司法實踐對于正當防衛這一違法阻卻事由在家庭暴力犯罪中的應用缺失,進而保障家庭暴力犯罪中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二)對家庭暴力犯罪中正當防衛的“緊迫性條件”的完善
家庭暴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正當防衛認定中的“緊迫性條件”往往不能對家暴被害人一方予以較為充分的保護[6]。筆者認為,家庭暴力犯罪中,即使不緊迫的不法侵害也會對被害人形成巨大的威脅,因此有必要對該不法侵害進行防衛。但是如果濫用必要性要件去認定正當防衛,容易出現假想防衛的問題,因此應該對其進行嚴格限制:第一,必要性判斷必須合乎情理,被害人的防衛行為必須存在充分的理由;第二,被害人進行防衛行為的情況必須也能得到社會公眾的接受,而不是僅僅出于被害人本身的主觀考慮;第三,被害人進行防衛必須要在無法尋求其他救濟渠道的前提下;第四,被害人的防衛行為必須是自己獨立的意思表示,警惕“防衛挑撥”情況的出現。
很多國家將正當防衛認定中的“即刻發生的攻擊”改為“無法避免的攻擊”,這種法律術語的轉換代表了這些國家已經認清在該類犯罪中采用緊迫性條件作為正當防衛認定標準的弊端。雖然我國司法實踐對于“以暴制暴”案件的處理往往會從被害人過錯以及公序良俗的角度出發進而從輕減輕防衛人的刑事責任,但是正當防衛理論在司法實踐中缺乏運用的情況依舊存在,不能從最大限度上保護家庭暴力犯罪中被害人的合法權益。
(三)在司法實踐中借鑒“受虐者婦女綜合癥”理論
“受虐婦女綜合癥”是在美國醫學界所形成的一種學說,是指長期受虐的婦女會有以下幾個特征:一是暴力的周期性,即妻子所遭受的家庭暴力是循環往復的,妻子在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情況下會產生極度的恐懼心理,因此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隨時會遭受下一次暴力。二是后天的無助感,即妻子在長期的家庭暴力的壓迫下會變得更加脆弱和被動,久而久之會放棄尋求來自社會的公立救濟,直到家庭暴力超過其所能忍受的上限[7]。筆者認為,我國可以在司法實踐中借鑒該理論,其必要性表現在:如果想要防止“以暴制暴”現象的發生,公力救濟就應當提前介入。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活動對于這類案件依舊按照普通的暴力案件進行審理,雖然會從被害人過錯以及公序良俗的角度出發從輕減或輕防衛人的刑事責任,但并沒有形成對受虐婦女進行保護的系統的理論體系。很多發達國家已經將該理論應用于司法實踐中,并且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不僅對受虐婦女提供了充分的救濟渠道,也極大地打擊了家庭暴力犯罪的囂張氣焰,對于維護社會穩定和節約司法資源上也頗具成效。
(四)公力救濟提前介入家庭暴力犯罪
由于家庭暴力犯罪中被害人在長期遭受家庭暴力的折磨下,多出現“受虐婦女綜合癥”現象,主要表現為受虐婦女會變得更加脆弱和被動,久而久之會放棄尋求來自社會的公立救濟。此外,在家庭暴力行為演變為犯罪之前,我國的司法機關并沒有介入的權力以及可能性,而當暴力行為演變為犯罪后,會對被害人本人、家庭、社會造成巨大的傷害,而此時司法機關的介入已經難以阻止這一結果的發生。所以僅僅憑借司法上的救濟并不充分。筆者認為,可以設立相關的社會組織與政府部門對家庭糾紛進行專門性的處理,從源頭上化解家庭矛盾,避免家庭暴力乃至家庭暴力犯罪的產生。如果能從這一層面減少家庭暴力犯罪的產生,那么家庭暴力犯罪中“以暴制暴”的現象也會隨之減少,家庭中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也會得到更為有力的保護。但是,必須嚴格規定該社會組織或政府部門的相關職能,以免權力被濫用,破壞社會的和諧穩定。
四、結語
家庭暴力目前依舊是我國社會存在的一項頑疾,對家庭成員身心健康和家庭環境穩定的危害是巨大的。此外,社會是由一個個家庭有機組合而成的,家庭暴力犯罪雖然發生在家庭內部,但也會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隨著社會持續進步,針對家庭暴力犯罪進行防治刻不容緩,而在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家庭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進行保護,對他們的正當防衛行為進行認定,只有讓家庭中的弱勢群體真正了解到他們面對家庭暴力可以采取行動保護自己,而不是坐以待斃;讓我國的立法與司法系統給予家庭暴力犯罪中被害人相應的保障;讓全社會樹立起反對家庭暴力的風氣,打擊施暴者的囂張氣焰,家庭暴力犯罪才能從根源得到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