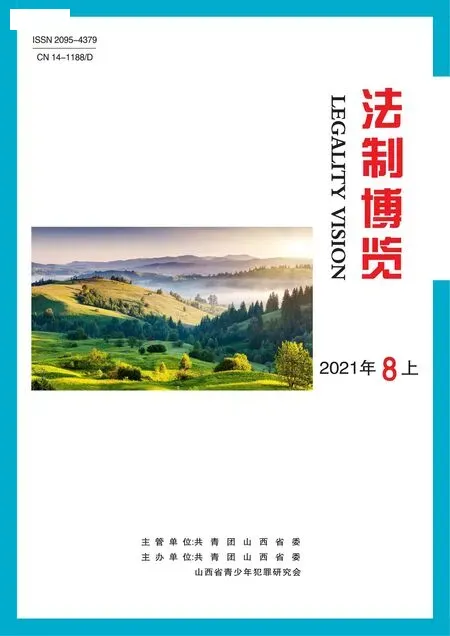《超級基金法》對我國土壤污染協同治理問題的啟示
——環境管理經濟視角
李婉秋
(榆林學院,陜西 榆林 719000)
20世紀70年代美國最引人關注的社會問題即環境保護問題,拉芙河事件使公眾第一次嚴肅地意識到危險廢物的任意填埋和處理給居民的生命、健康、財產及生態環境所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沖擊和危害,而公民環境保護的強烈意愿則成為啟動環境立法的巨大推動力。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綜合環境反應、賠償與責任法》,又稱《超級基金法》,這不僅大大推動了美國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同時也喚醒了國際社會對看不見的土壤污染的關注和重視。下面本文著重從環境管理經濟視角探索《超級基金法》對我國土壤污染協同治理問題的啟發和借鑒。
一、超級基金制度分析
超級基金最根本的原則即污染者付費,但潛在的污染者往往人數眾多,且責任的分擔也異常困難,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為此《超級基金法》首次創設了危險物質信托基金,即通過聯邦資金提供在責任主體無法確定或無力承擔情況下的資金支持,保障聯邦政府及時反應行動和土壤污染治理及修復。盡管《超級基金法》的實施對于危險廢棄物的清理和修復,人類健康發展,生態環境保護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促進全社會對危險物質以更加謹慎的態度去處置。但在其實施的過程中仍凸顯出眾多的問題,其中超級基金的經費缺乏問題爭議最大。
《超級基金法》確立基金來源的原則有二:污染者付費和受益者付費[1]。根據污染者負擔原則,超級基金的融資渠道主要來源于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原料稅,針對個別對環境影響較大的行業征收,如國內生產和進口石油產品稅,化學品原料稅。另一種大型企業環境稅則是面向年收入200萬美元以上的企業法人,是受益者付費原則的體現。最后則是聯邦政府的常規撥款。由于土壤污染所帶來的責任認定、技術處理、修復治理的復雜性和冗長性,資金支持就顯得尤為重要。從超級基金的融資方式看來仍是過于狹窄,導致后期出現了資金鏈嚴重供給不足的問題。有鑒于此,拓展多元的融資渠道則成為解決土壤治理問題中的關鍵。
(一)征收企業排污稅
基于污染者付費原則,防控環境污染,保護生態安全的目的,依法向環境污染責任人征收環境保護稅則順理成章。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從事含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產品生產、加工、消費的營利性企業均成為課稅的主要對象,并根據其排污的濃度,以及排污總量來確定排污稅的具體數額。另外廢棄物的不合理填埋處理也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應根據廢棄物的危險程度、處置體積,如果是多種不同程度的廢棄物混合掩埋的,則按費率高者計費,向相關企業征收排污稅。
(二)征收消費者環境保護稅
企業的排污行為不是獨立存在的,與其密切關聯的行為即消費者的物質需求。誠然污染的源頭在排污者,歷史實踐證明很多的污染行為均是基于工廠、企業的環境保護意識淡薄、利益驅動以及受制于技術水平的局限性所導致的。但如果將巨額的環境污染修復費用全部壓在企業的身上,尤其是基于我國國情,原本就脆弱的經濟環境,中小企業不堪重負,會嚴重影響國家的穩定及不利于社會的發展。所以,融資渠道的多元化、社會化就成為不二選擇。消費者的客觀需求一方面引導企業生產,另一方面也是產品消費的終端,因此基于受益者付費原則,由消費者承擔一定比例的環境保護稅也有其相應的法理依據和事實依據。當然消費者所承擔的環境保護稅顯然處于超級基金的補充地位,適度分擔責任,轉移風險。
(三)政府財政撥款
污染者付費原則是現代環境責任確定的主要原則,但污染物排放絕不僅僅是企業的孤立行為,與其他相關利益群體需求密不可分。土壤污染主要集中在重工業產業,如石油、化工行業,而這些企業往往又是帶動地方政府經濟發展的龍頭企業,納稅大戶。政府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也作為經濟發展的受益人,理應承擔一定比例的環保資金投入。具體而言,國家層面每年應有相當比例的財政預算,專款專用。地方政府則結合當地的稅收情況,污染情況,確定撥款比例,并根據其土壤治理及修復的情況及時調整預算金額。
二、環境責任保險制度分析
考慮到環境風險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土壤污染修復的高成本,排污企業迫切希望通過風險的分散和轉嫁來緩解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壓力。也為了更加及時高效地使土壤污染受害者獲得救助,穩定社會秩序。在此背景下,環境責任保險在美國應運而生,并被證明是一種有效的環境風險管理市場機制。我國自2007年開始也在國內陸續開展環境責任保險試點工作及相關立法,結合美國經驗,筆者認為對我國環境責任保險的立法啟示如下:
(一)關于保險范圍
綠色保險在我國剛剛起步,保險公司面對環境污染的巨額賠償責任,一方面鑒于其本身的承擔能力和自身利益的保障,另一方面考慮到環境風險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相關數據、技術的局限性也會加大風險評估、定損理賠的難度。所以關于保險范圍的確定可以參考美國《超級基金法》,將惡意的環境污染排除在承保范圍之外,保險范圍僅限于非故意的環境污染行為對公眾利益的損害[2]。
(二)關于投保方式
以美國為代表的《超級基金法》很早就確立了環境污染損害的強制性保險制度,在環境高風險的生產經營行業如石油、天然氣、化工、材料合成、藥品、危險廢棄物處置等,推行強制性的綠色保險是必要且必需的。
(三)關于責任限額
通過保險手段,運用市場風險轉移機制,解決環境風險責任的分擔問題,突破了傳統救濟方式,對污染者、受害人都能起到很好的補充作用。但給保險公司卻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從美國經驗看來被保險人環境污染賠償數額往往相對巨大,有些甚至無法估量。為了合理地規避風險,保險公司除了嚴格審查保險范圍,確定保費外,也有必要對環境保險的賠償限額根據被保險人投保額度,給予嚴格的限制,如最低風險險、有限責任險。政府也應通過保險補貼,稅收減免等方式降低保險難度,提高保險行業的經濟效益,促進綠色保險行業的發展,為分擔環境風險提供專業的可持續保障系統。
三、綠色信貸制度分析
《超級基金法》對綠色信貸的確立和興起也起到了積極的影響。由于《超級基金法》設立了嚴格的溯及既往的無限連帶環境責任制度,導致大量的潛在責任人面臨巨額的土壤污染賠償責任,有些企業無力償還甚至倒閉,最終也導致幕后的融資銀行無法收回貸款,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有鑒于此,綠色信貸悄然生長。綠色信貸注重對企業環境風險掌控能力的評估,加強對企業貸款項目和用途的審查,把土壤污染防控和修復能力作為發放貸款的重要參考指標,既可以從源頭處預防和控制對土壤的污染,又可以為銀行規避風險,避免對銀行利益和聲譽的損害。
綠色信貸在我國仍處于剛剛起步的階段,雖部分銀行有所落實,但總體而言,由于環境風險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相關技術數據的缺乏、風險評估系統尚不明確、銀行經驗不足等原因,加之專業的環境立法的不足,綠色信貸制度有待于進一步系統化、規范化、明確化。企業的發展離不開銀行的融資支持,因此在防控環境污染具體制度的落實中,不妨將銀行作為遏制企業環境污染的重要平臺之一。一方面銀行必須制定與環境污染防控指標相匹配的借貸政策和程序,在項目融資審批過程中注重對環境問題的謹慎審核調查義務,這樣高污染高耗能的企業則無法獲得銀行貸款,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污染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正是基于以上壓力,污染企業必須不斷提高環境風險的控制力,增加環保投入,減少環境污染,以期獲得銀行的融資支持,從而實現環境保護的目的,促進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兼容和平衡。[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