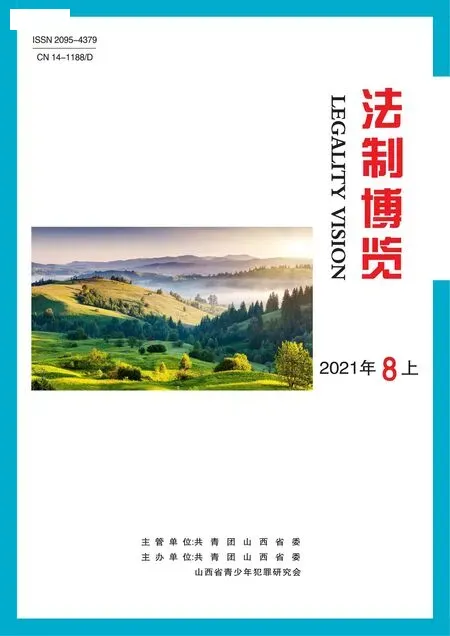自擔風險的法學原理
——基于《民法典》一千一百七十六條的分析
王樹海
(遼寧師范大學海華學院,遼寧 大連 116400)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隨著歐美國家的經濟復蘇,大眾體育和職業體育獲得了迅猛發展,同時催生了體育經濟學。體育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越發達,體育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的體育事業也獲得了飛速發展。為了提高中小學生的身體素質,加強體育鍛煉,減少參加體育活動的法律責任,是社會現實的迫切需求,因此在我國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規定了自擔風險條款:自愿參加具有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因其他參加者的行為受到損害的,受害人不得請求其他參加者承擔侵權責任;但是,其他參加者對損害的發生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除外。
一、自擔風險不是自甘風險
我國許多學者都認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條的法理基礎是自甘風險,本人實難贊同。
自甘風險的意思就是在意思表達真實、自由的情況下,在參加某個活動時已經預料到了風險的存在并且自愿承擔這種風險帶來一定程度的傷害[1]。從主觀上講,行為人按照社會通行規則和生活經驗能夠充分認識到存在一定的風險;從客觀上講,行為人經過理性思考之后自愿承擔參加活動所帶來的風險。
自擔風險并不注重考察行為人的認知情況,而是從客觀的角度出發,即只要行為人參加了某種可能存在一定風險的文體活動,無論其是否認識到風險的存在,該種風險都由其自行承擔。
按照大陸法系對于侵權責任的通說觀點,侵權責任的產生以行為人在不法侵害他人之際,具有認識能力,這也是過失侵權的基礎。[2]如果行為人無論如何都不會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他人的損害,那么就不應該承擔侵權責任。
關于認識能力,世界各國的學者眾說紛紜,有的認為認識能力就是“辨別自己行為在法律上某種責任的能力”,有的認為認識能力就是“對于其行為方法侵害他人權利之行為,有正常的認識能力”,有的認為認識能力就是“足以識別自己行為能夠發生法律上不當行為責任的認知能力”。雖然各個學者的意見無法統一,但是大體上的意思是一致的:能夠認識到自己的行為可能導致他人受到損害,至于損害程度則在所不問。
未成年人之間的嬉戲或體育活動等,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會認識到這種活動的危險性,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認為參與者不應該承擔法律責任。
日本法院在判決相關案例時認為,孩童之間做戰爭游戲而傷害了眼睛等重要部位,其損害程度超過了被害人所甘愿忍受的危險程度,因此行為人要承擔侵權責任,對于一般的傷害,行為人不承擔侵權責任;奧地利法院認為,打雪仗這種比較常見的嬉戲行為,在嬉戲過程中發生損害,行為人不應該承擔侵權責任;瑞士流行一種追擊游戲,在追擊過程中可以拿非常小的石子或者泥丸投擲對方,因此種行為發生損害,瑞士法院認為行為人不應承擔責任。
但是,這些國家認為不應該承擔侵權責任,卻不是因為自甘風險,而應該是自擔風險。
自擔風險和自甘風險相差僅一字,實際意思卻相距甚遠。
二、自擔風險不要求行為人對危險的認識性
按照自甘風險的理論,自甘風險構成要件有三:一是受害人參加文體活動且在風險出現之前就已經知道存在危險,這里的知道包括狹義的知道以及應當知道。這里的危險包括文體活動中固有的危險和意料之外的危險,這種危險由潛在到現實是無法提前預料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二是受害人沒有職業要求、道德要求和法律要求。所謂職業要求就是參加文體活動的主體不限于職業運動員、職業演員;所謂道德要求就是在某些文體活動中為了比賽的勝利,一方即使違反游戲規則也只能在游戲規則范圍內受到懲罰,不應該對其有道德上的額外要求,比如足球比賽或者籃球比賽中的主動犯規,主動犯規的目的可能是為了達到一定的戰術目的(籃球比賽中主動犯規讓對方球員上罰球線從而為己方爭取時間),也可能是為了今后的比賽做好準備(洗黃牌);三是受害人自愿承擔這種為活動所帶來的損害。
自甘風險的構成要件有時候并不需要完全具備,但是當侵權行為發生之際,按照民法理論衡諸情理,侵權人承擔侵權責任則不妥當。
在我國北方有這樣一種游戲:在秋天樹葉掉落之后,一個人雙手持葉柄的兩端,另一個人同樣如此,兩個人讓葉柄交叉拉拽,葉柄折了的一方為負方。兩個8周歲的小孩,模仿中學生玩耍此游戲,在游戲中摔倒受傷。鑒于這種游戲基本沒有受傷的可能性,因此這種情況下兩個孩子是認識不到玩耍該游戲的危險性的。
比如在中國足球超級聯賽的比賽中,某10歲小孩甲自己買了門票觀看足球比賽。在足球比賽中因為某隊員將球踢出場外,足球砸傷了小孩甲的臉部。足球砸傷人是低概率事件,因此這種情況下足球運動員和觀看比賽的小孩甲,都沒有認識到風險的發生,但是按照《民法典》的規定,卻不能要求足球運動員承擔侵權責任。
從邏輯學的角度,證明一個命題是假命題,舉一個反例即可。從上述兩個例子來看,自擔風險相對于自甘風險更為恰當和準確。
三、自愿參加不能做狹義解釋
某小學體育課上,體育教師組織同學們做熱身運動,熱身結束后組織足球比賽,在足球比賽中學生乙絆倒了學生丙,學生丙受傷住院花費醫療費若干。
在這個案例中,學生丙的家長提出:學生丙自幼不喜歡球類運動,學生丙參加足球比賽是基于教師的命令,而不是自愿行為,因此教師的雇傭者即學校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民法典》增設一千一百七十六條的自擔風險,其目的之一就是降低文體活動參與者、組織者的法律責任,通過文體活動促進學生美育和體育發展,如果上述案例在司法實踐中得到法院的支持,那么和立法初衷相悖,因此,自愿參加不能做狹義解釋。
自擔風險就是一種實際情況,不應過多苛求行為人的主觀心理狀態。禁止矛盾行為是民法領域的基本原則,比如民事訴訟法中的禁止反言的法學原理就是禁止矛盾行為。[3]在許多文體活動中,每一個參與者都是危險制造者,因此要求自己對自己的危險行為承擔責任是矛盾的,與基本法理相悖。
四、自擔風險的法學原理是默示承諾
承諾是合同法中的術語,系從國外翻譯而來,在英文中稱為“acceptance”,在一些國際法中也翻譯為“接受”。通常來講,承諾需要做出意思表示,比如我國《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九條就明確規定:承諾是受要約人同意要約的意思表示。鑒于社會生活的復雜性,后來人們又認為承諾可以通過行為作出,因此我國《民法典》第四百八十條規定:承諾應當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是,根據交易習慣或者要約表明可以通過行為作出承諾的除外。
默示承諾屬于承諾中的極為例外的情況,現在民法學家對默示承諾的意見就是相對人從特定的行為(包括不作為)推斷對方做出了意思表示。
行為人自愿參加某種文體活動,現行民法的通說觀點是他在參加這種文體活動時,默示了他人在不違反運動或游戲規則的情況下,愿意忍受此種運動或游戲所產生的損害。這種默示承諾是無需受領的默示承諾,作為承諾當然成了違法阻卻事由,因此即便有侵權行為的發生,被害人無損害賠償請求權。
當然,默示承諾的范圍在世界各國有所不同,比如日本認為默示承諾應當限定在一定的范圍,即便加害人不是故意或重大過失,僅僅是一般過失,如果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害程度極高,受害人得請求損害賠償。從我國的立法看,并沒有做出損害程度方面的規定,因此應當和法國、奧地利等國的立法取向相同。
值得推敲的另一個問題是作為未成年人自愿參加一些文體活動,因為欠缺民事行為能力,那么他們作出的默示承諾是否能夠處分自身的民事權利能力。[4]按照我國大多數民法學者的觀點,被害人承諾屬于法律行為的表示,法律行為規定僅能類推適用,并應當就不同案例作出不同的分析,對于大多數文體活動,未成年人能夠認識到這種文體活動的大部分規則和可能存在的風險,就可以做出默示承諾,承擔自擔風險的法律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