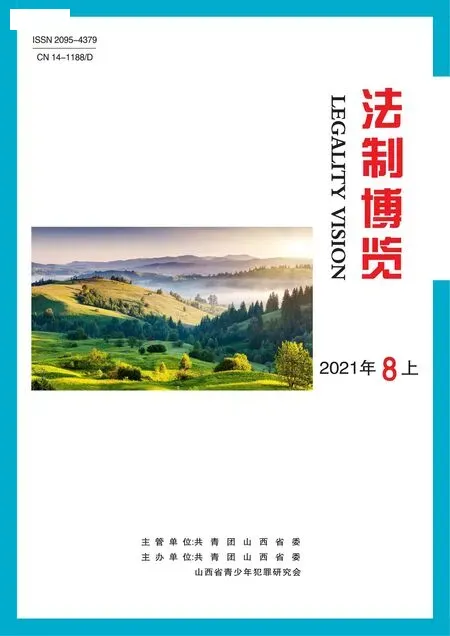違法建筑處理的法律問題相關探討
陳岳榮
(浙江萬申佳律師事務所,浙江 麗水 323000)
在城市管理中,違法建筑數量較多,城市管理難度增加,不利于城鎮化建設與發展。違法建筑的形成原因以及建設目標等存在差異性,但管理過程中,由于我國對違法建筑這一現象的立法不夠完善,缺乏良好的執法力度,對違法建筑管理效率低下。針對違法建筑,若采用強制性拆除這一單一管理方式,將會導致資源浪費。若不拆除違法建筑,則違法建筑數量不斷增加,影響市容,制約城鎮化進程。行政機關在開展違法建筑處理工作時,需要始終遵循我國法律規定,嚴格遵守流程,一旦出現違法處理違法建筑現象,則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將我國現有法律作為基礎,提出完善的違法建筑行政執法措施,明確提出違法拆除違法建筑的行政賠償,提高違法建筑治理質量,優化城市環境[1]。
一、違法建筑處理的現實困境
(一)對違法建筑認定較為混亂
現階段,行政主體對違法建筑以及違法建設行為的認定標準不明確,因而在實際執法過程中,將需要全部拆除的建筑以及需要部分拆除的建筑混為一談,在一定程度上將損害部分民眾的利益。違法行政行為產生的主要原因則是對違法建筑認知不明確,在開展違法建筑整治以及處理工作時,需要始終將我國法律法規作為基礎,正確認知違法建筑。當前我國針對違法建筑這一問題時,通常采用經驗式立法,因而出現認定混亂現象。在認定違法建筑時,無法充分分辨出違法建筑以及違章建筑,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缺乏統一標準,甚至將違章建筑作為拆除對象,同時也并未進行相應補償,因為這一問題所引發的爭議相對較多。我國并未針對違法建筑制定完善的法律條例,甚至對違法建筑的界定不明確,不利于行政執法機關開展違法建筑管理工作。
(二)違法建筑處罰方式存在單一性
當前我國關于違法建筑的處理,法律中共計規定了四種處理手段。第一種方式則為立即停止施工,這一處理方法主要是針對正在施工的違法建筑,要求當事人立即停止施工建設行為。第二種方式則為限期拆除,執法機關需要給出拆除期限,在這一期限內,違法行為人需要自行拆除違法建設。若拆除難度較大,可由其他組織協助拆除。第三種處理方法則是行政機關在執法過程中,當事人拒絕拆除,則行政部門可申請強制拆除。最后一種方法則是行政機關需要對違法建筑建造者進行行政處罰,有兩種處罰方式,一種是罰款,另一種則是沒收非法財務。但行政機關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面對違法建筑,通常采用限期拆除方式,若當事人未在規定期限內拆除違法建筑,行政機關則會強制拆除。行政機關在處理違法建筑時,處罰方式存在單一性,因而極易引發多種糾紛問題[2]。
二、違法建筑處理的執法機制完善
(一)明確違法建筑的認定要件
1.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的使用
行政執法機關在進行違法建筑管理中,在認定違法建筑時,認為不具備審批手續的建筑即為違法建筑,具備合法手續的建筑則認為是合法建筑。但需要明確的是,存在部分不具備合法手續的建筑,在一定情況下,也不能將其認定為違法建筑。在違法建筑認定過程中,往往需要結合多種因素,只有依據違建行為發生時,法律認定為違法建筑,才能將這一建筑認定為違法建筑。在違法建筑認定中,需要始終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并且在認定過程中,需要注意時間節點問題。首先針對我國村鎮建房用地管理條例實施前,針對農村以及鄉鎮地區建設并投入使用的房屋,由于我國建房審批制度不完善,因而不能夠將其認定為違法建筑。其次我國于1987年頒布了《土地管理法》,使得城鄉用地以及建房等制度更加完善。針對土地管理法實施前所建設并使用至今的房屋,缺乏審批手續以及產權證書,同樣不能認定為違法建筑。最后針對1987年之后建設的房屋,缺乏審批手續以及產權證書,也不能將其認定為違法建筑。由于我國土地法落實時間存在差異性,行政執法機關在工作中,需要結合房屋所在地土地管理法落實時間,判定房屋是否屬于違建。在對農村地區住宅建設進行管理中,需要結合房屋建設時的法律規定以及歷史情況等綜合考量并認定。
2.確認行為具有單獨可訴性
在管理違法建筑時,只有明確違法建筑的違法性,才能夠將其作為后續行政處罰制定的基礎。針對這一規劃認定行為是否對人的權利與義務造成實際影響,能否尋求一定司法救濟,關于這一問題,當前還存在一定爭議,共存在兩種不同觀念。第一種觀點認為,在對違法建筑認定中,這一行為并未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實際影響,屬于內部行政行為。并未這一行為屬于內部化,并未外部化,因而屬于不可訴行為。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在將建筑認定為違法建筑時,則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進行了處分,因而這一行為屬于可訴行為。
(二)規范違法建筑的處罰行為
大部分城市其行政機構在進行違法建筑管理工作時,所采用的處罰方式主要是以拆為主。但由于違法建筑間存在差異性,不同違法建筑所帶來的危害也不相同,若未對違法建筑進行深入分析,統一采取拆除的處罰行為,將會造成社會資源浪費等問題。在我國《城鄉規劃法》中,對違法建筑制定了三種不同處罰措施,針對正在建設的違法建筑,為降低其影響,則需要禁止繼續建設。其次針對不利于城市規劃但能夠消除影響的在建或者建設完成的建筑,可采用處罰以及限期改正兩種處罰方式。最后針對嚴重影響規劃并且無法改正消除影響的建筑,需要要求行為人在規定時間內拆除,針對無法拆除的建筑,需要沒收違法收入,并處于相應罰款。行政部門在管理違法建筑時,需要結合實際情況恰當判定,并采用不同處罰方式。針對城市規劃范圍內存在的部分違法建筑,牽扯了較多法律關系以及公共利益等問題,若行政部門僅簡單采用拆除這一處罰措施,明顯不適用,甚至會加大民眾經濟損失,不利于社會穩定發展。因此行政部分需要遵循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分析拆除成本以及違法建筑的再利用,選擇有效處罰措施,維護社會穩定[3]。
三、違法處理違建的行政賠償
(一)確定行政賠償主體
當違法建筑被行政機關強制拆除后,當事人對違法拆除行為的行政賠償主體確認存在一定爭議。部分學者則認為,應當將違法建筑拆除的實際實施部門作為賠償主體,雖然區縣人民政府作為組織部門,但在具體實施中,主要是由實施部門開展的拆除工作,因此將拆除實施部門作為被告更加恰當。但同時也存在反對意見,這一觀點則認為應當將區縣政府作為賠償主體,區縣人民政府則是違法建筑強制拆除的重要組織者,應當對這一行為負責,針對拆違實施單位超范圍的拆違行為,區縣人民政府需要承擔相應責任。從司法實踐角度出發,在違法超出違法將建筑的行政賠償中,即使區縣人民政府并未參與到強制執行中,但為全面保證當事人的權利,區縣政府也需要承擔一定賠償責任。
(二)合理確定賠償數額
當違法建筑被強制拆除后,若當事人無法提供完整的物品清單以及財產說明書,無法證明損失數額時,法官則需要結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充分運用當事人所提供的證據,結合生活常識,確保判斷的準確性以及客觀性,掌握證據材料與案件之間的關系,判斷出當事人的財產損失情況。當事人需要竭盡所能提供證據,證實自身合法權益受到的損失,但需要明確的是,需要保證證據的準確性,不得提供虛假證明。
四、結論
在我國城鎮化的發展過程中,面臨違法建筑處理難的問題,行政機關要始終將我國法律法規作為執行的前提,遵循以人為本原則,有效解決違法建筑處理中存在的問題。合法合理處理違法建筑,不僅能夠發揮民眾的監督職能,還能夠避免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沖突,優化執法成本,提高行政機關對違法建筑的處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