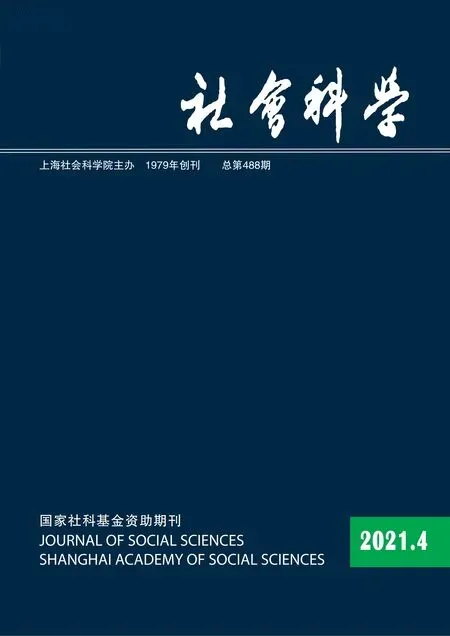重建時(shí)代與抗拒政治的再興
任劍濤
中國正處于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關(guān)鍵時(shí)刻:進(jìn)則成為現(xiàn)代國家,退則打回欠發(fā)展原形。當(dāng)此關(guān)鍵時(shí)刻,人們大都會(huì)覺得周遭世界混亂得出人意料:不僅日常秩序難以維持,而且法治規(guī)則不彰;不僅熟悉的生活模式不再,而且未來顯得高度地不確定。這正是人們面對(duì)一個(gè)重建時(shí)代的顯著社會(huì)心理表現(xiàn)。為此,需要率先摸清舊秩序失序或崩潰的門道,保證重建不致陷于茫無頭緒的窘態(tài)。在一個(gè)重建時(shí)代,急于為舊秩序打上補(bǔ)丁,以為如此便完成了重建任務(wù),這是一個(gè)很容易走偏的行為定勢(shì)。為矯正這種急功近利的心態(tài),需要尋找準(zhǔn)確的重建方向,以摸清舊秩序因何失序?yàn)榍疤幔M(jìn)而為新秩序的生長路徑提供指引。其間,因?yàn)榕f秩序失序而激發(fā)的抗拒政治,正是摸清舊秩序因何失序的一個(gè)切入口。
一、被逼入重建時(shí)代
中國當(dāng)下所處的重建時(shí)代(1)重建時(shí)代是一個(gè)挪移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早期使用者卡爾·曼海姆的說法,所謂重建時(shí)代就是一個(gè)自由放任秩序失效、計(jì)劃調(diào)節(jié)秩序勢(shì)不可免的時(shí)代。前者的解體危機(jī)與后者的浮現(xiàn)生機(jī)如影隨形。推而廣之,所謂重建時(shí)代就是一個(gè)舊秩序失效、新秩序萌生的時(shí)代。參見[德] 卡爾·曼海姆《重建時(shí)代的人與社會(huì):現(xiàn)代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研究》,張旅平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2年版,第2-3頁。,是一個(gè)舊秩序喪失、新秩序浮現(xiàn)的轉(zhuǎn)變時(shí)代。這個(gè)時(shí)代明顯呈現(xiàn)出兩個(gè)鮮明不同的畫面:一是人們對(duì)當(dāng)下社會(huì)各個(gè)方面所懷的失望心態(tài),二是對(duì)將要到來的時(shí)代心懷深切期待。失望與希望之間存在著明顯錯(cuò)位,因此,極易引發(fā)人們對(duì)現(xiàn)行秩序的憤懣,抗拒政治由此勃興。在社會(huì)行動(dòng)的形式上,社會(huì)公眾的政治抗拒(2)政治抗拒不同于政治抗?fàn)帯G罢呖赡苁切睦砩系模部赡苁切袆?dòng)上的;后者則是行動(dòng)導(dǎo)向的。抗?fàn)幷位蛘慰範(fàn)?Contentious Politics)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社會(huì)公眾以行動(dòng)展現(xiàn)政治圖謀的革命、內(nèi)戰(zhàn)、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等政治形式。參見[美] 查爾斯·蒂利等《抗?fàn)幷巍罚盍x中譯,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不單表現(xiàn)為傳統(tǒng)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也表現(xiàn)為社會(huì)騷動(dòng)、局部混亂乃至權(quán)力癱瘓。在抗拒政治的理論表達(dá)上,人們對(duì)現(xiàn)行秩序明確表達(dá)出不滿,并將希望投射到理想秩序的構(gòu)想上。由于這種想象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改善功用不彰,明顯加劇了社會(huì)的抗拒心理。取決于這兩方面的緣故,讓這個(gè)時(shí)代的重建任務(wù)變得沉重和艱巨。重建時(shí)代以“重建”來定位,當(dāng)然要落到建設(shè)的目的性上。但是,重建時(shí)代是一個(gè)難以輕而易舉實(shí)現(xiàn)新舊秩序交接的膠著時(shí)代。重建時(shí)代需要付出相當(dāng)?shù)臅r(shí)間代價(jià),才足以摸索出重建道路。換言之,重建時(shí)代的新舊秩序反復(fù)特質(zhì)最令人矚目。因此,認(rèn)清重建時(shí)代新舊秩序的膠著狀態(tài),便成為實(shí)現(xiàn)新舊秩序交替的首要任務(wù)。
中國進(jìn)入重建時(shí)代是在下述意義上得到確認(rèn)的:一是改革開放的前路不暢,因此需要重新審視改革開放的未來。人們熟絡(luò)于心的是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的改革開放就在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之間徘徊,迄今可以說經(jīng)歷了三次大的起伏:1986年至1980年代末出現(xiàn)了第一次起伏,這次起伏付出了政治沖突的代價(jià);1995年至1997年出現(xiàn)了第二次起伏,這次起伏付出了“姓資姓社”辯論的代價(jià);2004年至2005年出現(xiàn)了第三次起伏,這次起伏付出了爭論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錯(cuò)誤的代價(jià)。這里所說的代價(jià),其實(shí)都是由后續(xù)事件實(shí)際呈現(xiàn)出的代價(jià)。在起伏出現(xiàn)之際,因?yàn)轭I(lǐng)導(dǎo)層力挽狂瀾,大致矯正了其時(shí)引起的社會(huì)不安。但從后續(xù)發(fā)展來看,這幾次起伏集聚了讓改革開放難以為繼、讓中國社會(huì)回流的能量。這才是以時(shí)間差呈現(xiàn)出來的真正代價(jià)。客觀地看,改革開放凝心聚力效用的衰變是一個(gè)可能的事實(shí)。基于此,重新審視中國的前路,成為中國進(jìn)入重建時(shí)代的一個(gè)顯著標(biāo)志。
二是現(xiàn)代謀劃遭遇了難以克服的障礙,因此不得不重新謀求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進(jìn)路。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截至改革開放,已經(jīng)大致呈現(xiàn)了一條從器物現(xiàn)代化到制度現(xiàn)代化,再到人的現(xiàn)代化的進(jìn)路。但中國新一輪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似乎與晚清和民國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一樣,在走到制度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處時(shí),很難往前推進(jìn)。如果說器物的現(xiàn)代化主要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它確實(shí)對(duì)中國人具有強(qiáng)大的吸引力。這是現(xiàn)代化具有強(qiáng)勁動(dòng)力的實(shí)際緣由。這種低度的現(xiàn)代化,既不挑戰(zhàn)現(xiàn)行秩序,也不動(dòng)搖既定價(jià)值的堤防,因此不會(huì)遭遇什么抵抗,確實(shí)能夠比較順利地推進(jìn)。一旦器物現(xiàn)代化需要以制度變革來擔(dān)保的時(shí)候,社會(huì)變遷就會(huì)遭遇既得利益集團(tuán)的集體性抗拒,也會(huì)觸及人們習(xí)以為常的生活慣性,更可能會(huì)顛覆既定的價(jià)值秩序,因此較難獲得社會(huì)的認(rèn)同與權(quán)力的響應(yīng)。尤其是來自權(quán)力或明或暗的組織性抗拒,它構(gòu)成現(xiàn)代化一再謀劃、不斷重建的重要原因(3)參見任劍濤《現(xiàn)代中國何以轉(zhuǎn)型艱難:追尋古今中西的沖突根源》,《學(xué)術(shù)界》2020年第1期。。
三是四十年發(fā)展遭逢內(nèi)外條件的趨緊。中國的改革開放是近代以來現(xiàn)代化轉(zhuǎn)變的一個(gè)較長周期的一個(gè)階段。如果說晚清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起止于1861年到1894年,持續(xù)時(shí)間三十余年;1927年到1937年被稱為民國的黃金時(shí)代,時(shí)長僅為十年;1978年至今的改革開放,盡管有實(shí)質(zhì)推進(jìn)與文獻(xiàn)求存之別,但總長度已經(jīng)超過四十年。從過程的角度看,改革開放源于國家的貧弱,因此較易聚集民心民力;改革開放是融入世界,因此較易得到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的歡迎,從而贏得較好的國際發(fā)展環(huán)境。但經(jīng)過四十年的發(fā)展,中國的國內(nèi)生產(chǎn)總值已經(jīng)躋身世界第二位,不僅改變了國家貧弱的狀態(tài),而且以強(qiáng)勢(shì)姿態(tài)進(jìn)入國際社會(huì)。于是,國內(nèi)公眾的訴求已經(jīng)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西方發(fā)達(dá)國家面對(duì)中國崛起的態(tài)度也發(fā)生了大幅度的轉(zhuǎn)變。尤其是中美貿(mào)易摩擦引發(fā)的國際環(huán)境巨變,正面阻遏中國發(fā)展的上升勢(shì)頭。由于這兩種因素的交互作用,使中國的發(fā)展動(dòng)力較為缺乏。這就不能不重新聚集中國的發(fā)展動(dòng)力,重塑國內(nèi)外的發(fā)展環(huán)境。這將是一次艱難的轉(zhuǎn)身,對(duì)中國的政黨-國家而言,無異于一次極具挑戰(zhàn)性的“自我革命”(4)參見習(xí)近平《牢記初心使命,推進(jìn)自我革命》,載《習(xí)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34-535頁。。就此而言,一次全局的重新謀劃勢(shì)在必行。
由此可以說,中國是被逼入重建時(shí)代的,這就給掌握重建時(shí)代的主動(dòng)權(quán)與主導(dǎo)權(quán)帶來極大壓力。主動(dòng)掌握重建時(shí)代,意味著對(duì)重建時(shí)代的新舊秩序更替了然于心,可以做到新舊秩序的有序更迭;主導(dǎo)整個(gè)重建時(shí)代,預(yù)示著重建時(shí)代推進(jìn)手段與所需資源的有效儲(chǔ)備。顯然,面對(duì)一個(gè)前路不明、改革轉(zhuǎn)向和內(nèi)外環(huán)境緊張的局面,官民雙方都很難成竹在胸、循序推進(jìn)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三期疊加”的權(quán)威表述,即增長速度換檔期、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再明確不過地表明了中國被逼入重建時(shí)代的總體態(tài)勢(shì):中國經(jīng)濟(jì)的快速增長期已過,不可避免地進(jìn)入了一個(gè)緩慢增長階段;中國的功能性改革選項(xiàng)大致窮盡,必須面對(duì)結(jié)構(gòu)性改革的深度難題;中國借助國家權(quán)力手段不斷刺激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政策引發(fā)諸多問題,需要艱難消化。當(dāng)下時(shí)代“三期疊加”的特征,是一個(gè)讓習(xí)慣性享受改革紅利的官民雙方很難一下子適應(yīng)的艱難時(shí)世。
觀察世界現(xiàn)代化史可知,任何國家從傳統(tǒng)邁入現(xiàn)代都不是一帆風(fēng)順的。英國始自1215年《大憲章》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一直到1688年“光榮革命”才宣告完成,時(shí)長達(dá)470余年,其中的艱難困苦可想而知。法國經(jīng)歷的大革命陣痛,讓長期處于革命浪潮中的中國深有同感。德國歷經(jīng)三次殖民與準(zhǔn)殖民過程,才十分艱難地完成了現(xiàn)代蛻變。俄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幾起幾落,直到今天還難稱現(xiàn)代國家。相比而言,中國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在世界歷史上并不是最為艱難曲折的。但中國不斷進(jìn)入重建狀態(tài)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也讓人深思。因此,試圖理解當(dāng)下中國何以被逼入重建時(shí)代,需要拓寬視野,先期理解中國現(xiàn)行秩序的結(jié)構(gòu)狀態(tài),以此理解中國何以再次進(jìn)入重建時(shí)代。這樣的理解可以區(qū)分為兩個(gè)路徑:一是在秩序重構(gòu)中,既存秩序因何增添了人們心中的緊張與焦慮;二是在秩序喪失情況下,現(xiàn)行秩序怎樣發(fā)揮引人思考的作用。這里著重從前者來分析中國被逼入重建時(shí)代所具有的影響力,后者留待以后分析。
中國的現(xiàn)行秩序可以說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的秩序“修正”。這催生了一種具有特色的經(jīng)濟(jì)形態(tài),即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實(shí)質(zhì)的結(jié)構(gòu)則是高度集中的政治權(quán)力體制、微觀價(jià)格領(lǐng)域放開的局部市場(chǎng)機(jī)制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體制相混生。在改革開放初期,具有高度權(quán)威的政治領(lǐng)導(dǎo)人掌握國家權(quán)力,這樣的混生機(jī)制可以發(fā)揮引導(dǎo)中國發(fā)展的強(qiáng)有力作用。一旦建國領(lǐng)袖群體退出政治舞臺(tái),這種混生的秩序就很難再有權(quán)威護(hù)航。在這種情況下,要么掌權(quán)者對(duì)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不放心而可能回望計(jì)劃經(jīng)濟(jì),要么市場(chǎng)機(jī)制的縱深推進(jìn)會(huì)向既定的政治機(jī)制與文化體制發(fā)出挑戰(zhàn)。總之,三者的搭配關(guān)系需要重新處置。于是,社會(huì)重建就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shì)。恰當(dāng)此時(shí),長期被快速增長的經(jīng)濟(jì)總量慣養(yǎng)的公眾消費(fèi)習(xí)性,仍然在按照增長的邏輯自然延伸。因此,權(quán)力體系與社會(huì)期待之間就會(huì)出現(xiàn)縫隙,并因之生出各種錯(cuò)位、矛盾與對(duì)峙。在這種處境中,人們對(duì)權(quán)力的滿意度會(huì)下降,對(duì)生活的期待度會(huì)提高,對(duì)想象與現(xiàn)實(shí)之間明顯加大的距離會(huì)產(chǎn)生極大的抵觸情緒。“塔西佗陷阱”——即不管政府做好事還是做壞事,人們都傾向于不相信政府的定勢(shì)就會(huì)浮現(xiàn)出來。為了避免出現(xiàn)社會(huì)政治總體危機(jī),官方不得不籌劃總體改革計(jì)劃,并加大對(duì)社會(huì)公眾的承諾力度。社會(huì)公眾對(duì)改善處境的強(qiáng)烈要求,稍有不滿足的地方,便會(huì)催生出更多更強(qiáng)的要求。權(quán)力的承諾與公眾的期待之間,距離日漸加大,政策改進(jìn)與處境改善之間的磨合讓社會(huì)重建處在一個(gè)緊張的拉鋸狀態(tài)。
可見,中國重建時(shí)代的再次降臨,可以說是一種危中有機(jī)的緊張狀態(tài)。危險(xiǎn)即重建不是在一種從容的社會(huì)政治處境中,而是在緊迫的社會(huì)轉(zhuǎn)型需求中浮現(xiàn)的,它讓人難以駕馭;機(jī)會(huì)即盡管中國是被逼入重建時(shí)代的,新舊秩序確實(shí)膠著,但尋求新秩序的動(dòng)力與壓力同在。挺過這一關(guān),也許現(xiàn)代化的曙光就會(huì)普照中國大地。但很顯然,由前述三種機(jī)制混生的改革開放既定秩序,直接生長出新秩序并不容易。如何促成一種有利于中國朝向健康的現(xiàn)代機(jī)制發(fā)展的新秩序,這是當(dāng)下這個(gè)重建時(shí)代最大的挑戰(zhàn)。由于這一挑戰(zhàn)的全面性,在新秩序浮現(xiàn)出來之前,新舊秩序的雜陳狀態(tài),一定會(huì)讓分別或共同抗拒新舊秩序的各種社會(huì)理念與社會(huì)行動(dòng)浮上臺(tái)面,從而催生出一種頗具危險(xiǎn)性的抗拒政治。最近十年,人們對(duì)之有了一個(gè)更加直接的體認(rèn):對(duì)幾乎所有西方發(fā)達(dá)國家的仇視言論充斥坊間,尤其是流行于微信等自媒體言論空間;對(duì)中國具有的不同于西方現(xiàn)代特質(zhì)的辨識(shí)熱情極為高漲,似乎中國已經(jīng)闖出了一條全新的現(xiàn)代化道路。這固然是中國再次被逼入重建時(shí)代的觀念體現(xiàn),但也構(gòu)成將中國逼入前景不明的重建時(shí)代的驅(qū)動(dòng)力量。
二、攘外型抗拒政治
當(dāng)中國進(jìn)入一個(gè)新的重建時(shí)代之際,新的抗拒政治相伴而生、如影隨形。如前所述,當(dāng)今中國進(jìn)入的重建時(shí)代,在最直接的含義上是指改革開放的既定模式“無以為繼”,并且直接引發(fā)或間接誘發(fā)了種種社會(huì)問題。因此,必須促成一種更高級(jí)或更有效的社會(huì)秩序,以保證中國長期、持續(xù)、穩(wěn)定與協(xié)調(diào)的發(fā)展態(tài)勢(shì)。但放眼望去,中國重建時(shí)代是一個(gè)反反復(fù)復(fù)出現(xiàn)的時(shí)代。出現(xiàn)這種時(shí)代的重復(fù),一方面固然提示人們,中國的重建時(shí)代屢屢沒能完成重建的基本任務(wù),因此,同樣的時(shí)代才會(huì)三番五次地出現(xiàn)。另一方面也提醒人們,中國的重建時(shí)代乃是一個(gè)頗具韌性的時(shí)代。它的反復(fù)出現(xiàn)是對(duì)國人的友善表現(xiàn),是對(duì)中國必須完成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一再促進(jìn),是對(duì)現(xiàn)代化世界進(jìn)程的一個(gè)強(qiáng)力推動(dòng)。當(dāng)然,再一方面也讓人們醒悟,中國現(xiàn)代化進(jìn)程推進(jìn)的艱難,現(xiàn)代轉(zhuǎn)變對(duì)中國而言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即便中國人追求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目標(biāo)始終未變,但因?yàn)椤拔髁|漸”與“西學(xué)東漸”相伴隨的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變進(jìn)程自始至終充滿了內(nèi)外部的尖銳矛盾與沖突,因此,讓人發(fā)自內(nèi)心予以理解的抗拒政治之勃興也就在情理之中。
抗拒政治乃是既有的內(nèi)生社會(huì)力量對(duì)新生的外來社會(huì)力量的一種抵抗政治形式。內(nèi)生的社會(huì)力量,當(dāng)然不僅僅由一個(gè)群體的內(nèi)部力量構(gòu)成,也包含已經(jīng)內(nèi)化于該群體的外來力量。這樣的力量可能是觀念形態(tài)的,也可能是行動(dòng)形態(tài)的,更可能是兩者交疊在一起的復(fù)雜形態(tài)。外來的社會(huì)力量,不僅僅是由一個(gè)群體外部生成的力量構(gòu)成,也包含這個(gè)群體內(nèi)部被群體主流視為外來物而加以排斥形成的力量。外生力量的構(gòu)成形態(tài)與內(nèi)生力量相仿。因此,對(duì)中國這樣被卷入現(xiàn)代化進(jìn)程的國家來說,抗拒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力量構(gòu)成是相當(dāng)復(fù)雜的:一些舊秩序中的開明人物是認(rèn)同現(xiàn)代秩序的,因此也就可能被舊秩序的守成人物視為敵人。自晚清以來,在中國社會(huì)被廣泛貶斥的“漢奸”中間,便有這樣的人物(5)參見桑兵《歷史的原聲:清季民元的“共和”與“漢奸”》,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0年版,第215-350頁。。一些舊秩序中的守舊人物,也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的冥頑不化之人,其中一些只不過是吁求放慢轉(zhuǎn)變步伐或重視傳統(tǒng)政治智慧的人士(6)成為保皇分子的康有為、楊度等人,主張以君主立憲解決中國的立憲政體問題。參見姜義華《20世紀(jì)中國思想史上的政治保守主義》,載李世濤主編《知識(shí)分子立場(chǎng):激進(jìn)與保守之間的動(dòng)蕩》,時(shí)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7頁。。
總體來說,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變既是一個(gè)無法逆轉(zhuǎn)的歷史進(jìn)程,也是一個(gè)遭遇或強(qiáng)烈、或韌性抗拒的過程。這樣的抗拒即便是在認(rèn)同現(xiàn)代轉(zhuǎn)變目標(biāo)的人群中,在心理與行為上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體現(xiàn)。從心理上講,主張“全盤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胡適,便在批判傳統(tǒng)文化的同時(shí),花費(fèi)了巨大功夫進(jìn)行過一番“整理國故”的艱辛嘗試。這就勢(shì)必消耗他對(duì)現(xiàn)代認(rèn)同的強(qiáng)度,無形中增加了抗拒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心理力量。從行為上講,即便是主張徹底革命的孫中山,也對(duì)西方國家的侵略深懷痛恨,因此謀求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fā)展道路。這就必然讓他全力尋求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發(fā)展道路,追求富強(qiáng)發(fā)達(dá)與公平分配“畢其功于一役”的社會(huì)革命目標(biāo)。這同樣是一條抗拒現(xiàn)代主流方案的進(jìn)路。而且,后者在無形中成為現(xiàn)代轉(zhuǎn)變中的國人解除精神緊張與行為失措的最佳出路:保有認(rèn)同現(xiàn)代的立場(chǎng),走在自信是出自傳統(tǒng)的道路之上。殊不知,這樣的取向構(gòu)成一種最具韌性的抗拒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深層結(jié)構(gòu)。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可以說是化解國人抗拒現(xiàn)代轉(zhuǎn)變心結(jié)的一次成功嘗試,但不是說改革開放就不存在針對(duì)現(xiàn)代化、原生現(xiàn)代西方國家的抗拒政治。相反,這樣的抗拒力量在臺(tái)面與臺(tái)底一直頑強(qiáng)存在著。從簡單的辨認(rèn)角度看,贊同市場(chǎng)化改革還是稱頌單一的國有化舉措,認(rèn)同法治邏輯還是推崇集權(quán)政治,主張適應(yīng)多元社會(huì)還是重回意識(shí)形態(tài)一律,這是劃分融入現(xiàn)代與抗拒現(xiàn)代的政治分水嶺。這樣的簡單辨認(rèn),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思想史進(jìn)程中,一再得到呈現(xiàn),勿需贅述(7)馬立誠對(duì)之有過描述性的回觀,參見馬立誠等《交鋒——當(dāng)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shí)錄》,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馬立誠《當(dāng)代中國八種社會(huì)思潮》,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2年版。。透過簡單辨認(rèn),可以得出一個(gè)相對(duì)復(fù)雜的觀察,即改革開放正在走向一個(gè)必須自辯其正當(dāng)性與合理性的地步,確實(shí)顯示了抗拒政治對(duì)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變所發(fā)生的巨大影響。可是,今日抗拒政治儼然成為主流政治形式。這是何故?細(xì)究起來,下述幾個(gè)原因值得重視:
首先,對(duì)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權(quán)力與利益結(jié)構(gòu)的嚴(yán)重不滿,構(gòu)成了中國抗拒政治再興的主因。改革開放確實(shí)大大推進(jìn)了中國的現(xiàn)代發(fā)展進(jìn)程。但因?yàn)楦母锏牟慌涮祝泊呱藱?quán)力與金錢的聯(lián)姻機(jī)制,造成了貧富的嚴(yán)重不均,引發(fā)了種種社會(huì)矛盾。因此,在深度改革開放進(jìn)展不暢的情況下,社會(huì)公眾對(duì)現(xiàn)實(shí)政治幾乎是全方位的抗拒,這便成為意料之中的事情。加之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變需要向縱深推進(jìn),因此會(huì)改變之前粗放式的發(fā)展模式。這勢(shì)必要?jiǎng)由鐣?huì)公眾基本利益的奶酪,諸如拆遷、提高稅負(fù)、就業(yè)形勢(shì)變化等,更是會(huì)嚴(yán)重影響諸多人群的生計(jì)。這無疑加劇了抗拒政治的嚴(yán)峻局勢(shì)。
其次,對(duì)西方國家提供的現(xiàn)代主流方案的抗拒,已經(jīng)成為官民輿論的主調(diào)。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變每每走到制度現(xiàn)代化的關(guān)鍵時(shí)刻,官方不愿意償付交出權(quán)力的“代價(jià)”,民間不愿意為限權(quán)行動(dòng)付出心力與行動(dòng),結(jié)果在這兩種消極意愿的阻力下,無法將中國的現(xiàn)代轉(zhuǎn)變推向縱深。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變所經(jīng)歷的晚清、民國與當(dāng)代三次“淺嘗輒止”,即止于器物的現(xiàn)代化,而無法臨門一腳,完成制度轉(zhuǎn)變,正是這種定勢(shì)所造成的局面。但官民雙方又不愿意承認(rèn)自己對(duì)現(xiàn)代制度的抵抗,于是將現(xiàn)代制度建構(gòu)視為西方國家試圖控制中國的手段和陰謀,并不約而同地以抵抗西方國家控制中國的圖謀來抗拒制度的現(xiàn)代轉(zhuǎn)變。
再次,以“中國模式”抗衡西方方案,已經(jīng)成為強(qiáng)壓所有其他主張的一種強(qiáng)勢(shì)立場(chǎng)。中國的發(fā)展確實(shí)是一個(gè)奇跡,但奇跡的延續(xù)遠(yuǎn)遠(yuǎn)比奇跡的凸顯要困難得多。因此,如何為奇跡自辯便成為固化奇跡思維的一條便利途徑。“中國模式”就是這樣出臺(tái)的。如果人們對(duì)“中國模式”的論述與推崇僅僅是基于中國發(fā)展經(jīng)驗(yàn)的一種事實(shí)描述,那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對(duì)“中國模式”的描述與推崇是為了排斥西方現(xiàn)代方案對(duì)中國的引導(dǎo)力,那么這樣的嘗試便屬于情緒化的抗拒政治的產(chǎn)物——抗拒西方對(duì)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影響力,試圖以絕對(duì)屬于“中國”的現(xiàn)代化方案來消解這樣的影響力。其實(shí),這也不是當(dāng)下才表現(xiàn)出的中國抗拒政治的特點(diǎn),而是自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的一種共性。晚清推崇祖宗之法,民國試圖走出一條“非蘇”(社會(huì)主義)“非美”(資本主義)的禮義廉恥治國道路,而今這樣的念想不過是以“中國模式”再次登場(chǎng)。
最后,抗拒政治已經(jīng)從輿論空間進(jìn)入國際政治領(lǐng)域,成為當(dāng)下中國一種令人矚目的政治定勢(shì)。近年來中國的抗拒政治對(duì)象愈來愈超出國家范圍,進(jìn)入國際空間。而且,抗拒政治的主要對(duì)象已經(jīng)變?yōu)槲鞣絿摇T鴰缀螘r(shí),中國的改革開放以西方國家為取法對(duì)象,而今的西方國家則成為中國抗拒政治發(fā)泄抗拒情緒的目標(biāo)。這可以從幾個(gè)方面得到印證:一是在中國的國際處境方面,與西方的對(duì)抗已經(jīng)成為局勢(shì)明朗的事情。二是在學(xué)界主流那里,西方國家成為接受批判的對(duì)象(8)在坊間,這類批判文章的結(jié)集讓人屢見不鮮,大有對(duì)西方國家的一切進(jìn)行總清算之勢(shì)。相比于改革開放前期對(duì)西方國家的潛心學(xué)習(xí)取向,讓人覺得走到了另一個(gè)極端。至于人所熟知的網(wǎng)紅教授發(fā)表的相關(guān)言論以及所引起的廣泛喝彩,更是讓人覺察到時(shí)變世易。。三是在社會(huì)輿論的重要空間如自媒體中,與西方主要國家均不惜一戰(zhàn)的言論甚囂塵上、持續(xù)不衰。四是在國際交往方面的“戰(zhàn)狼”精神與舉動(dòng),讓人意識(shí)到中國所懷有的“獨(dú)孤求敗”心態(tài)。至于中美如今走到脫鉤的境地,既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出人意料是因?yàn)橹袊冀K把中美關(guān)系作為最重要的雙邊關(guān)系,意料之中是因?yàn)槿镣獾目咕苷伪厝粚?dǎo)致這樣的結(jié)果。
引人矚目的是中國近期的抗拒政治表現(xiàn)出一個(gè)醒目的特點(diǎn):對(duì)內(nèi)抗拒的軟化與對(duì)外抗拒的硬化,成為鮮明對(duì)照的兩個(gè)畫面。本來,國人的對(duì)內(nèi)抗拒是直接受改革開放形成的不公利益格局驅(qū)動(dòng)的。因此,源自切身利益的抗拒政治在此之前一直是中國抗拒政治的主調(diào),其政治形式便是當(dāng)時(shí)人所熟知的維權(quán)政治。維權(quán)事件的此起彼伏,令世人矚目。維權(quán)政治的研究成為學(xué)界的一時(shí)熱點(diǎn)。近年來,這種情勢(shì)出現(xiàn)極為顯著的轉(zhuǎn)變,對(duì)內(nèi)的抗拒政治不說是銷聲匿跡,至少在臺(tái)面上不再引人矚目。相反,對(duì)外的抗拒政治迅速成為中國抗拒政治的主流。這種攘外的抗拒政治,不僅表現(xiàn)為反抗西方的主流價(jià)值觀,而且抵制西方國家創(chuàng)制的現(xiàn)代制度,自然也對(duì)西方的現(xiàn)代生活方式嗤之以鼻。這是對(duì)西方國家全面抗拒的一種政治局面。非抗拒或反抗拒的聲音不是沒有,但相比于抗拒西方的巨大音量、行動(dòng)狂熱與權(quán)力加持,幾乎完全被遮蔽住了。這種幾乎純?nèi)蝗镣獾目咕苷危墙谥袊咕苷蔚耐怀鎏攸c(diǎn)。
一般而言,內(nèi)外兼具的抗拒政治屬性,是因應(yīng)人們對(duì)一個(gè)國家內(nèi)政外交兩個(gè)向度作出相關(guān)反應(yīng)的必然構(gòu)成面,但何以近期中國的抗拒政治會(huì)轉(zhuǎn)變?yōu)閹缀跻匀镣鉃槟繕?biāo)的抗拒形式呢?一方面,這與當(dāng)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矛盾尖銳凸顯具有密切關(guān)系。在將近四十年間,中外關(guān)系尤其是關(guān)系到中國現(xiàn)代轉(zhuǎn)變成敗的中國與西方的關(guān)系,基于“和平與發(fā)展”主題而促成的合作與共贏,成為雙方關(guān)系的主調(diào)。但久而久之,中國的發(fā)展出乎西方的意料,而發(fā)展的軌跡似乎越來越偏離西方的預(yù)期。復(fù)加西方國家認(rèn)為,自身在這一時(shí)期的國際經(jīng)濟(jì)貿(mào)易中沒有獲得期望的利益,且認(rèn)為中國在“不公平競(jìng)爭”中獲得了太多利益,不僅經(jīng)濟(jì)貿(mào)易摩擦的出現(xiàn)不可避免,還會(huì)進(jìn)一步延伸至社會(huì)政治層面,甚至是文化文明層面。全方位展現(xiàn)的中西交往張力,迅速轉(zhuǎn)變成為中西沖突,尤其是中美沖突的現(xiàn)實(shí)。中美雙方對(duì)之的管控如果說不是失效的,起碼是低效的。因此,在中美對(duì)抗加劇之際,信息來源受限的國人以高亢的熱情抗拒美國等西方國家,就是合乎邏輯的變化。
另一方面,這與中國國內(nèi)局勢(shì)的走向密切相關(guān)。毫無疑問,中國經(jīng)歷四十年的高速發(fā)展,且一直以經(jīng)濟(jì)建設(shè)為中心,關(guān)聯(lián)性發(fā)展相對(duì)遲滯,因此各種矛盾集中浮上臺(tái)面。假如任由這種矛盾轉(zhuǎn)換為社會(huì)認(rèn)知,進(jìn)而升級(jí)為社會(huì)行動(dòng),并且放任社會(huì)行動(dòng)激化為社會(huì)抗議,那么勢(shì)必催生社會(huì)動(dòng)蕩,甚至社會(huì)大亂。這是中國轉(zhuǎn)型社會(huì)難以承受之重。基于此,如何轉(zhuǎn)移中國社會(huì)對(duì)種種缺憾的不滿情緒,并重新集聚推進(jìn)中國發(fā)展的動(dòng)力,乃是當(dāng)今中國治國理政的一項(xiàng)極具考驗(yàn)性的重大事務(wù)。無疑,中美關(guān)系的緊張恰好提供了一個(gè)疏導(dǎo)國內(nèi)抗拒政治蘊(yùn)蓄的緊張情緒的渠道。這是自媒體上出現(xiàn)人人爭說中美關(guān)系、熱議中美摩擦的內(nèi)部導(dǎo)因。
放寬視野來看,中國致力于攘外的抗拒政治可謂由來已久。從歷史角度來看,七十年的抗拒政治呈現(xiàn)出明暗相連的三個(gè)階段:毛澤東時(shí)代對(duì)美蘇的全面化抗拒政治,鄧小平時(shí)代堅(jiān)守底線而不受西方影響的防守性抗拒政治,當(dāng)下堅(jiān)守中國道路并拒斥西方觀念與制度的排拒性抗拒政治。當(dāng)代中國的抗拒政治對(duì)象,從散漫不定的觀念與行動(dòng)針對(duì),到幾乎聚焦于西方國家,可以說是這種攘外型抗拒政治傳統(tǒng)的一個(gè)最新呈現(xiàn)。這種攘外型抗拒政治,確實(shí)也具有深厚的歷史理由,如西方國家近代以來對(duì)中國的侵略與掠奪,總是有著似乎永遠(yuǎn)也訴說不完的、激發(fā)針對(duì)西方抗拒政治的事實(shí)基礎(chǔ)。中國在國際經(jīng)濟(jì)體系中的交易與合作,也總是會(huì)浮現(xiàn)新的、讓國人自認(rèn)受到不公待遇的事件,這無疑會(huì)給攘外型抗拒政治提供新的理由。
三、失序之憂
當(dāng)下中國攘外型的抗拒政治,是一種對(duì)現(xiàn)行秩序進(jìn)行心理與行為抵抗的政治形式。循此可知,這種抗拒政治不過是不滿于現(xiàn)行秩序,要求啟動(dòng)秩序重建進(jìn)程的社會(huì)意愿的反映。因此,弄清現(xiàn)行秩序的結(jié)構(gòu)狀態(tài),明晰現(xiàn)行秩序何以失效的緣由,就成為理解今時(shí)今日抗拒政治的前提條件。在此基礎(chǔ)上,可以幫助人們厘清何種秩序最有助于化解抗拒政治之結(jié),疏導(dǎo)抗拒政治郁積的不滿,將政治秩序引導(dǎo)到理性、法治、妥協(xié)、安寧與有序的軌道上來。
抗拒政治所抗拒的現(xiàn)行秩序,并不是鐵板一塊的。它在結(jié)構(gòu)上具有復(fù)雜的構(gòu)成部分,在功能上不斷重新組合。不過,現(xiàn)行秩序的來龍去脈仍然是可以得到描述的,從而讓人們觀察到現(xiàn)行秩序的構(gòu)成情形與致效機(jī)制。分析起來,中國的現(xiàn)行秩序是由四種機(jī)制所組成的: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的運(yùn)行軌跡所展現(xiàn)的更替秩序,二是二戰(zhàn)結(jié)束后形成的所謂戰(zhàn)后發(fā)展秩序,三是17世紀(jì)以來確立的、中國致力于現(xiàn)代性轉(zhuǎn)變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秩序,四是更加久遠(yuǎn)的古典時(shí)代給現(xiàn)代社會(huì)奠立的基礎(chǔ)性秩序。
分別來看,首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前三十年與后四十年的替代秩序,呈現(xiàn)為兩種大不相同的秩序機(jī)制。前三十年是由集權(quán)政治、剛性計(jì)劃與給定生活樣式塑就的“硬”秩序。在這種秩序中生活的人群,卷入了昂揚(yáng)向上、紀(jì)律嚴(yán)明、貧寒清苦、遠(yuǎn)望將來的生活模式之中。后四十年則是由法理政治、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各尋出路塑就的“軟”秩序。在這樣的氛圍中,人們的生活特征可謂務(wù)于現(xiàn)實(shí)、目標(biāo)多樣、追求財(cái)富、重視當(dāng)下。但是,兩種秩序的作用不是截然分離的。前一階段的普遍貧窮與后一階段的部分富裕形成鮮明對(duì)照,從而給抗拒政治打上不同時(shí)代的烙印。在前一階段,盡管有政治壓力維系,但也有少數(shù)人表現(xiàn)出抗拒;在后一階段,已富和未富的社會(huì)群體表現(xiàn)出的政治抗拒,所抵抗的對(duì)象大不相同。已富群體主要抵抗的是讓他們感覺到財(cái)產(chǎn)、人身不安全的種種經(jīng)濟(jì)政治機(jī)制,未富群體所要抵抗的則是導(dǎo)致他們貧窮困頓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機(jī)制。前者在抵抗中寄望于民主法治,后者在抵抗中面向歷史而懷舊。兩者之間自然有交叉,但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前者的抵抗以捍衛(wèi)財(cái)產(chǎn)為中心,從底線的維權(quán)政治到上限的限權(quán)政治,構(gòu)成其基本面;后者的抵抗以結(jié)果平等為訴求,從底線的生存權(quán)到上限的發(fā)展請(qǐng)?jiān)福瑯?gòu)成其基本面。由于中國社會(huì)對(duì)這兩種秩序的供給能力較低,因此讓兩種抗拒政治都有了現(xiàn)實(shí)的動(dòng)力。
其次,二戰(zhàn)的戰(zhàn)后秩序構(gòu)成中國建構(gòu)現(xiàn)代國家的國際環(huán)境。但是,由于中國先后出現(xiàn)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gè)政治體,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又經(jīng)歷了兩個(gè)具有重要差異的歷史階段,因此,這一秩序催生了很不相同的中國秩序建制。就中華民國而言,承接的是西方發(fā)達(dá)國家護(hù)航的戰(zhàn)后秩序,并先后在大陸和臺(tái)灣地區(qū)落實(shí)這一秩序。就中華人民共和國來看,前三十年承接的是蘇聯(lián)護(hù)航的戰(zhàn)后秩序,集權(quán)體制、計(jì)劃經(jīng)濟(jì)與模式生活成為國家主導(dǎo)的秩序樣式;后四十年轉(zhuǎn)而承接由西方國家護(hù)航的戰(zhàn)后秩序,民主政治、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與多元文化成為國家權(quán)力面上推動(dòng)的秩序形式。在前一階段,中國是明確抗拒西式戰(zhàn)后秩序的;在后一階段,中國是努力疏離蘇式戰(zhàn)后秩序的。但是,對(duì)經(jīng)歷了兩個(gè)時(shí)代的人群,并經(jīng)由這一人群傳遞給中國社會(huì)的抗拒理念與行為,則成為站在維護(hù)兩種不同秩序立場(chǎng)上的人群采取不同抗拒姿態(tài)的載體。這正是戰(zhàn)后秩序在中國并不具有自明性,所以成為抗拒政治多樣來源的緣由。
再次,17世紀(jì)以來確立的、中國致力于向之轉(zhuǎn)變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秩序,因?yàn)槭峭鈦碇刃颍谥袊涞厣喈?dāng)困難。因?yàn)椋瑯?gòu)成這一秩序的價(jià)值理念如自由、平等、博愛等,制度架構(gòu)如立憲、法治、民主等,觀念基礎(chǔ)如宗教、哲學(xué)、科學(xué)等,文化機(jī)制如多元、寬容、妥協(xié)等,都是中國人相當(dāng)陌生的東西。加之這套觀念與行動(dòng)模式是由西方國家借助戰(zhàn)爭手段強(qiáng)行加予中國的,因此促成了中國人心中那種理智認(rèn)可、情感反對(duì)的悖謬性現(xiàn)代認(rèn)同機(jī)制:中國人尤其是那些“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9)《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頁。的人士,在理智上于中西接觸之始就明確而堅(jiān)定地確立了認(rèn)同這套秩序建制的立場(chǎng)。但是,這樣的確認(rèn)既無法與這類人群心中的傳統(tǒng)情感相抗衡(10)勒文森曾經(jīng)以梁啟超為例,說明那些“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的人,由于“看到其他國度的價(jià)值,在理智上疏遠(yuǎn)了本國的文化傳統(tǒng);由于受歷史制約,在感情上仍然與本國傳統(tǒng)相聯(lián)系”。參見[美] 勒文森《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思想》,劉偉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頁。對(duì)于這樣的斷言,人們有不同的看法,要么認(rèn)為梁啟超在理智與情感上都認(rèn)同現(xiàn)代化,要么認(rèn)為他在理智與情感上都認(rèn)同傳統(tǒng),但這都是為了彌合國人對(duì)現(xiàn)代化的分裂性認(rèn)同所作的修正性表述,本身并不構(gòu)成對(duì)勒文森斷言的否定。,也抵擋不住社會(huì)公眾在現(xiàn)實(shí)認(rèn)知上被塑就的抗拒西方的心理力量。因此,在理智與情感之戰(zhàn)中,理智常常處在弱勢(shì)甚至是失敗的位置上。從大處而言,中國人在情感上對(duì)源自于西方國家的現(xiàn)代秩序都懷有或強(qiáng)或弱的抗拒心理。當(dāng)抗拒西方與抗拒現(xiàn)代重合的時(shí)候,中國的抗拒政治似乎就成了抵抗現(xiàn)代轉(zhuǎn)變的政治行動(dòng)了。這連帶催生出一種抗拒政治的混亂性。
最后,古典時(shí)代給現(xiàn)代社會(huì)奠立的基礎(chǔ)性秩序也成為中國抗拒政治的源頭之一。古典時(shí)代或者說軸心時(shí)代的文明,是發(fā)源于西方、中國與印度等地區(qū)的文明體系。在各有淵源的流變中,古典時(shí)代生成了具有不同價(jià)值理念、制度安排與生活方式的文明系統(tǒng)。由于中國人發(fā)達(dá)的歷史思維,勢(shì)必高度關(guān)注當(dāng)下秩序的古典源頭。因此,古今秩序的實(shí)踐對(duì)接雖然沒有成功,但古今秩序的觀念對(duì)接從來就很順暢。尤其是在中國經(jīng)濟(jì)迅速增長的當(dāng)下,人們覺察到需要為之提供價(jià)值論證的時(shí)候,“訴諸傳統(tǒng)”(11)翟振明對(duì)“重視傳統(tǒng)”與“訴諸傳統(tǒng)”的根本差異以及“訴諸傳統(tǒng)”本身的推理謬誤進(jìn)行過很有見地的分析。參見翟振明《“訴諸傳統(tǒng)”何以毀壞學(xué)術(shù)傳統(tǒng)——兼評(píng)劉小楓、秋風(fēng)等的學(xué)術(shù)倫理》,《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評(píng)價(jià)》2015年第2期。這里對(duì)“訴諸傳統(tǒng)”的弊端不作進(jìn)一步的討論。的心理習(xí)性就更是驅(qū)動(dòng)人們?cè)跊Q斷價(jià)值與采取行動(dòng)的時(shí)候仰賴傳統(tǒng)支持。于是,堅(jiān)定支持中國古典傳統(tǒng)便以堅(jiān)決否定西方古代歷史為寫照,由此強(qiáng)化自身抗拒現(xiàn)代秩序的傳統(tǒng)理由。這雖然毫無疑問地強(qiáng)化了人們的抗拒心理,卻很難促使人們擇善而從。
就上述四重秩序而言,分別引發(fā)了四個(gè)意義上的社會(huì)重建。一是改革開放秩序的重建,即重尋改革開放的歷史定位、制度機(jī)制與真正目的。這讓改革生成的新舊秩序混生,促使人們新舊相抗,進(jìn)入一個(gè)前景不明的艱難摸索狀態(tài)。二是二戰(zhàn)后秩序的重建。盡管中國力圖維持戰(zhàn)后秩序,但人們心知肚明的是戰(zhàn)后秩序已經(jīng)無法維持。因此,新的國際秩序究竟如何建構(gòu)并發(fā)揮作用,成為又一個(gè)前途未卜的事情。三是17世紀(jì)以來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主流秩序的重建。這是東西方社會(huì)在經(jīng)歷幾輪競(jìng)爭性發(fā)展之后的必然結(jié)果。受技術(shù)革命的驅(qū)動(dòng)、地緣政治的變動(dòng)等因素的影響,人類已經(jīng)無法安享四個(gè)世紀(jì)以前創(chuàng)制的現(xiàn)代秩序,必須嘗試構(gòu)造新的秩序。不過,新的秩序是否是一種非支配的公正秩序,抑或是一種按照政體因素區(qū)隔的秩序,這是一個(gè)未敢斷定的事情。四是行之久遠(yuǎn)的古典社會(huì)秩序的重建。這是一個(gè)后發(fā)外生現(xiàn)代國家遭遇的獨(dú)特問題。對(duì)像英國那樣的原發(fā)內(nèi)生現(xiàn)代國家而言,現(xiàn)代秩序是從其傳統(tǒng)秩序中生長出來的,盡管也會(huì)發(fā)生內(nèi)生文化斷裂的情況,但總體上波瀾不驚,不會(huì)讓人處在高度緊張的疏離傳統(tǒng)、轉(zhuǎn)向現(xiàn)代的境況之中。對(duì)中國這樣的國家來講,不僅現(xiàn)代轉(zhuǎn)變是被迫而困窘的,而且必須作別傳統(tǒng)秩序,才能為現(xiàn)代秩序的進(jìn)入騰出空間。如前所述的理智與情感的矛盾,讓人們無法對(duì)現(xiàn)代全心認(rèn)同,也讓人對(duì)傳統(tǒng)終結(jié)難以釋懷。于是,在建構(gòu)現(xiàn)代秩序的同時(shí),人們不得不付出極大精力去重建傳統(tǒng)。這就讓現(xiàn)代秩序與傳統(tǒng)秩序處在相互抗拒的狀態(tài),明顯增加了以傳統(tǒng)抗拒現(xiàn)代或以現(xiàn)代抗拒傳統(tǒng)的雙向?qū)χ诺膹V度與強(qiáng)度。這在近年來傳統(tǒng)文化的“復(fù)興”中讓人體會(huì)尤深:大陸新儒家全盤反對(duì)西方現(xiàn)代方案,力主從傳統(tǒng)儒家開出——其實(shí)就是仿照西方——專屬于中國的現(xiàn)代方案,這是中國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相互抗拒的一個(gè)象征性事件(12)參見任劍濤《現(xiàn)代變局與何以為儒》,《深圳社會(huì)科學(xué)》2018年第1期。。至于長期處于撕裂狀態(tài)的左右互搏,已是人們無可奈何、不知如何處置的陳年老問題了。
由上可見,中國當(dāng)下的抗拒政治具有一種全方位、多層次、總體上的相互抵抗性質(zhì):抵抗的對(duì)象、目的、方式、舉措與行為多有不同,相互交錯(cuò)、相互消解、相互促成,呈現(xiàn)出抗拒政治的復(fù)雜畫面。如此突兀顯現(xiàn)的抗拒政治,讓中國社會(huì)很難呈現(xiàn)出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主流趨向。由此不能不直面中國的遠(yuǎn)慮近憂:從近處看,中國因其存在的普遍抗拒,讓人心生世俗秩序的失序之憂;從遠(yuǎn)處看,中國因其存在的不知何求的抗拒,讓人擔(dān)憂總體秩序的失序之患。
以前者而言,中國作為一個(gè)早期文明發(fā)展階段就出現(xiàn)“絕地天通”事件的標(biāo)準(zhǔn)世俗化國家,世俗秩序是維系社會(huì)的根本條件。從傳統(tǒng)邁入現(xiàn)代,中國也就從儒家倫常秩序轉(zhuǎn)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huì)形態(tài)演進(jìn)秩序。整個(gè)國家的總體秩序面相一直是世俗化的。這就與人心秩序依賴宗教維持、政治秩序依靠法治維持的現(xiàn)代社會(huì)大為不同。一旦純粹的世俗社會(huì)處在一個(gè)相互抵抗的狀態(tài),那么,抗拒政治最后一定會(huì)走到共同體內(nèi)部矛盾的極端。
以后者而言,倘若中國社會(huì)長期處于一種世俗社會(huì)秩序難以維持的狀態(tài),而且共同體成員彼此敵視的情形一直無法得到有效改善,久而久之,人心便無法收拾,社會(huì)便衰敗頹喪。整個(gè)社會(huì)的總體秩序因此很難維護(hù),失序之患便會(huì)催生一種近乎前社會(huì)的自然狀態(tài)。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個(gè)失治社會(huì)的必然走勢(shì)。從社會(huì)理論角度來看,這是社會(huì)在自然狀態(tài)與社會(huì)立約之間循環(huán)的可能性。從現(xiàn)代國家發(fā)展的實(shí)際進(jìn)程來看,不少曾經(jīng)邁進(jìn)現(xiàn)代門檻的國家,由于沒能解決成員、群體之間以及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相互抗拒,因此被打回欠發(fā)展國家的原形。
由于中國社會(huì)長期存在著相互沖突的秩序結(jié)構(gòu),因此,社會(huì)的復(fù)雜重建較難在現(xiàn)代化的平臺(tái)上奏效。如果現(xiàn)代化進(jìn)程自身處在一個(gè)進(jìn)退不得的尷尬處境中,更會(huì)將社會(huì)成員與群體之間的相互抗拒激化為嚴(yán)重的對(duì)立,終致權(quán)力的無效與社會(huì)的解體。今日中國社會(huì)個(gè)體間的敵視,缺乏起碼的公民友愛精神,已經(jīng)顯現(xiàn)出抗拒政治的憂人后果;群體之間,尤其是干群之間、貧富之間、城鄉(xiāng)之間、區(qū)域之間的對(duì)立局面,特別是仇官、仇富社會(huì)心理的泛濫,官方對(duì)此的改善舉措明顯乏力,明顯讓彼此之間的對(duì)立情緒有增無減。攘外型抗拒政治的形成,將國內(nèi)政治亟需解決的問題遮蔽起來,更是讓失序之憂迫在眉睫。因此,如果試圖化解中國社會(huì)的抗拒型政治風(fēng)險(xiǎn)與危機(jī),就需要系統(tǒng)了解和分析構(gòu)成中國社會(huì)秩序的諸要素,同時(shí)在價(jià)值觀念、制度供給與生活方式等維度展開系統(tǒng)性的現(xiàn)代建構(gòu),以此降低公民個(gè)體、群體之間以及他們與社會(huì)和國家之間的抗拒強(qiáng)度,提升理性合作意愿,強(qiáng)化友善相待意識(shí),避免社會(huì)脆性崩潰,增進(jìn)社會(huì)妥協(xié)彈性,從而讓社會(huì)與國家具備全局與長遠(yuǎn)的自我修復(fù)機(jī)制。
四、抗拒的“歸去來”
近期中國社會(huì)抗拒政治的走勢(shì)對(duì)國家發(fā)展具有的威脅性蓄能,似乎已經(jīng)為社會(huì)有識(shí)之士和國家權(quán)力方面所明確意識(shí)到。就國家權(quán)力方面來看,緊鑼密鼓的改革修補(bǔ)與全方位的改革重張相伴出場(chǎng)。對(duì)改革的緊急修補(bǔ),以對(duì)“人民中心”(13)參見習(xí)近平《習(xí)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3-144頁。的鮮明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分配改革問題的抓緊處置、對(duì)“六穩(wěn)”“六保”事務(wù)的一再前置等為標(biāo)志。這些修補(bǔ)是因?yàn)閲覚?quán)力方面充分意識(shí)到抗拒政治所可能引發(fā)的嚴(yán)重后果,因此,才要加大力度緩解社會(huì)成員與群體對(duì)現(xiàn)狀的明顯不滿,以及化解由各種不滿驅(qū)動(dòng)的社會(huì)緊張與彼此抵抗。目標(biāo)有高低兩個(gè):低階目標(biāo)是避免中國陷入“塔西佗陷阱”;高階目標(biāo)是重聚中國社會(huì)的向心力,以開拓新一輪的長時(shí)段發(fā)展周期。至于布局全方位改革,它是近年來中國國家權(quán)力方面的一個(gè)主攻事務(wù)。對(duì)改革的重張,即對(duì)改革的全盤重新謀劃,既源于改革在推進(jìn)過程中的不配套,也是由全方位推進(jìn)改革所可能具有的社會(huì)效應(yīng)與政經(jīng)收益決定的。
在這方面,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及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huì)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堅(jiān)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huì)主義制度 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最具標(biāo)志性。前一個(gè)《決定》推出了改革開放以來最全面的改革清單,圍繞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社會(huì)、生態(tài)文明、黨建等六大改革主線,提出涵蓋十五個(gè)領(lǐng)域,多達(dá)六十余個(gè)大項(xiàng)、二百二十多項(xiàng)具體改革任務(wù)的一攬子改革方案。前一個(gè)《決定》所謀求的改革廣度與力度可以說是空前的。時(shí)隔五年,后一個(gè)《決定》不僅將前一個(gè)《決定》所確定的“推進(jìn)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總目標(biāo)作為決定的論述宗旨,而且對(duì)之作出了全方位的布局。之所以國家權(quán)力高層會(huì)連續(xù)推出兩個(gè)主題相同的文件,正是要以更具廣度與深度的改革開放來解決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問題。在本論題中,自然就是為了化解抗拒政治走向極化政治的風(fēng)險(xiǎn)而作出的政治布局。
作出這樣的布局,自然是受兩種動(dòng)力驅(qū)動(dòng)的:一是推進(jìn)改革開放,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mèng),這可以說是主動(dòng)而為的動(dòng)力;二是推進(jìn)改革開放,化解發(fā)展進(jìn)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風(fēng)險(xiǎn)與危機(jī)。對(duì)于前者,所論較多,無需重復(fù)。對(duì)于后者,可以從中共中央兩任總書記胡錦濤與習(xí)近平都著重論述過的“四大考驗(yàn)”(執(zhí)政考驗(yàn)、改革開放考驗(yà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考驗(yàn)、外部環(huán)境考驗(yàn))與“四大危險(xiǎn)”(精神懈怠危險(xiǎn)、能力不足危險(xiǎn)、脫離群眾危險(xiǎn)、消極腐敗危險(xiǎn))中得到印證。這些考驗(yàn)與危險(xiǎn),無疑都與抗拒政治緊密關(guān)聯(lián)。由于改革開放已推動(dòng)中國進(jìn)入一個(gè)深度現(xiàn)代化的境地,因此,階層、集團(tuán)甚至階級(jí)之間的分化日益明顯,個(gè)人與社會(huì)、國家的疏離也顯著加大,而執(zhí)掌國家權(quán)力的集群缺乏應(yīng)對(duì)這種局面的經(jīng)驗(yàn)積累,也比較缺乏積極應(yīng)對(duì)新局面的意愿和動(dòng)力,一種被社會(huì)和權(quán)力等級(jí)驅(qū)動(dòng)的被動(dòng)管治模式已經(jīng)形成。因此,執(zhí)政者很難有效管控一個(gè)長期由抗拒意識(shí)引導(dǎo)的復(fù)雜社會(huì)——這個(gè)社會(huì)曾經(jīng)是被抗拒意識(shí)引導(dǎo)的簡單社會(huì)。簡單之處在于,它由國家權(quán)力游刃有余地控制著抗拒政治,在極度貧窮的狀態(tài)中抗拒那些威脅中國的外部因素。如今,這個(gè)由抗拒意識(shí)引導(dǎo)的社會(huì)已經(jīng)變得高度復(fù)雜化了,因?yàn)槭袌?chǎng)經(jīng)濟(jì)激活了個(gè)人的權(quán)利意識(shí)。這種權(quán)利意識(shí)既不被國家權(quán)力按其權(quán)力意志所引導(dǎo),也不被現(xiàn)代政治理念所塑造,唯有切身辨認(rèn)的個(gè)人利益在抗拒中發(fā)酵。這是一種既很難控制、又很難滿足的利益訴求。因此,其對(duì)現(xiàn)存秩序所具有的威脅性是顯而易見的(14)長期研究維權(quán)政治的肖唐鏢最近指出了維權(quán)群體政治觀念的特點(diǎn),“因維權(quán)實(shí)踐,行動(dòng)者已在淺層政治意識(shí)上出現(xiàn)了獨(dú)特的政治亞觀念,如有了更強(qiáng)的政治認(rèn)知,較低的政治情感、政治信任和政治認(rèn)同,較為包容的宗教觀,但是,維權(quán)實(shí)踐并未影響其政治效能感,更未影響其權(quán)利觀、法治觀、政府觀以及傳統(tǒng)權(quán)威觀等深層的政治價(jià)值觀。在民主、權(quán)利、法治、政府、政黨和社會(huì)組織等核心政治價(jià)值層面,維權(quán)人士群體仍然與其他民眾保持著無異的觀念……總之,維權(quán)行動(dòng)并未對(duì)行動(dòng)者的核心政治價(jià)值觀念產(chǎn)生實(shí)質(zhì)性影響,有所影響的只是淺層政治意識(shí)方面。對(duì)于我國的維權(quán)人士群體而言,他們的政治觀念依然是以傳統(tǒng)為底色,與其他民眾并無顯著差異”。參見肖唐鏢等《維權(quán)人士群體的政治觀念分析》,《社會(huì)科學(xué)戰(zhàn)線》2020年第8期。。
在國家權(quán)力集群面臨中國社會(huì)急遽的現(xiàn)代轉(zhuǎn)變之際,不僅要面對(duì)上述重大考驗(yàn),而且因?yàn)檫@一集群的積極性與主動(dòng)性的匱乏,已經(jīng)或顯在、或潛在地表現(xiàn)出種種高度的危險(xiǎn)性:這個(gè)群體對(duì)公民個(gè)體利益訴求的結(jié)構(gòu)性變化大多不以為然,并未意識(shí)到這是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化的重要征兆,因此似乎并不打算為之作出相應(yīng)的準(zhǔn)備。相反,權(quán)力集群習(xí)慣以陳舊老套的高壓手段來應(yīng)對(duì)日新月異的嶄新自主局面,讓權(quán)力管控處于疲于奔命而不自覺的被動(dòng)狀態(tài)。正是因?yàn)楣芸匾庾R(shí)的陳舊,權(quán)力集群相應(yīng)缺乏積極主動(dòng)增長才干的意愿,因此也就缺乏有效應(yīng)對(duì)復(fù)雜社會(huì)管治要求的基本能力。這對(duì)一個(gè)習(xí)慣于控制溫順對(duì)象的權(quán)力集群來講,一旦面對(duì)群情洶涌的維權(quán)民眾,就會(huì)變得縮手縮腳、不知所措。于是,高壓控制就成為不二之選。這種簡單粗暴的控制手段,在簡單社會(huì)中長期有效,因此,權(quán)力集群用起來得心應(yīng)手、樂此不疲。但以此應(yīng)對(duì)復(fù)雜社會(huì)的治理需要,必然南轅北轍、績效低下。隨著中國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迅速向縱深地帶推進(jìn),一個(gè)需要專業(yè)化、精準(zhǔn)化、高績效的國家治理模式的社會(huì),卻不得不面對(duì)一個(gè)計(jì)劃經(jīng)濟(jì)時(shí)代形成的粗暴、粗糙、低效的權(quán)力控制集群。因此,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治理令人不滿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權(quán)力與市場(chǎng)聯(lián)合推進(jìn)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權(quán)力謀求利益、權(quán)錢勾結(jié)成為“政治之癌”,很難根治。運(yùn)動(dòng)式反腐恰恰構(gòu)成運(yùn)動(dòng)式治理的反面,并不能有針對(duì)性地懲治腐敗。可以說,當(dāng)今中國的國家治理模式與社會(huì)的運(yùn)行實(shí)際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錯(cuò)位。這在有意無意之間、有形無形之中,強(qiáng)化了社會(huì)的抗拒政治態(tài)勢(shì)。這也正是國家權(quán)力高層緊鑼密鼓地布局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原因所在。
當(dāng)代中國的抗拒政治有一個(gè)從國家層面下沉到社會(huì)層面的重大轉(zhuǎn)變。如前所述,在改革開放以前,國家權(quán)力剛性主導(dǎo)著反對(duì)“帝、修、反”的抗拒政治。在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權(quán)力主導(dǎo)的是“和平與發(fā)展”的政治形式。但在致力于合作的政治嘗試中,因?yàn)榘l(fā)展中出現(xiàn)的不均衡性,引發(fā)了種種社會(huì)矛盾。在國家權(quán)力地位穩(wěn)固的情況下,社會(huì)不同集群、階層與階級(jí)向國家權(quán)力方面表達(dá)自己的訴求,以抗拒社會(huì)、權(quán)力對(duì)自己的不公正對(duì)待。這種新興的抗拒政治,在形式上是比較和平和理性的,并沒有挑戰(zhàn)現(xiàn)存政治秩序的動(dòng)機(jī);在表達(dá)抗拒的方式上,主要是向執(zhí)政黨和政府機(jī)構(gòu)請(qǐng)?jiān)福虼耸且环N以承認(rèn)執(zhí)政黨和國家權(quán)力的權(quán)威性為前提的做法。這正是抗拒政治最溫和的行動(dòng)形式,也是抗拒者到各級(jí)信訪部門信訪的原因。但這種抗拒政治滿足抗拒者訴求的通道是不暢通的,績效明顯是低下的。因此,在國家與社會(huì)的疏離加大的當(dāng)下,抗拒政治表現(xiàn)出趨于激進(jìn)的走勢(shì)。由于中國幾乎從來不存在理性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的政治空間與社會(huì)經(jīng)驗(yàn),這種極化的抗拒政治便可能從和平請(qǐng)?jiān)钢苯犹缴鐣?huì)騷亂的極端。因此,引導(dǎo)社會(huì)公眾的抗拒情緒便成為國家權(quán)力部門聚焦思考的問題。在引導(dǎo)社會(huì)抗拒情緒向攘外方向成功轉(zhuǎn)移的情況下,抗拒政治對(duì)國內(nèi)政治的壓力似乎明顯減少。但是,這樣的做法反而遮蔽了從內(nèi)政方向疏導(dǎo)抗拒政治壓力的重要性。因此,這等于放任抗拒政治對(duì)內(nèi)政壓力的蓄積。這就讓抗拒政治進(jìn)入一個(gè)要么瓦解現(xiàn)行秩序、要么臣服現(xiàn)行秩序的怪圈。唯獨(dú)抗拒政治的理性模式——合理合法表達(dá)政治抗拒,經(jīng)由抗拒者之間、抗拒者與國家權(quán)力之間的理性妥協(xié),解決抗拒的糾紛與對(duì)立,實(shí)現(xiàn)社會(huì)和解與合作共進(jìn)——殊難形成。于是,在抗拒政治氛圍中,所謂“改革與革命賽跑”的說法便有了落地的理由。
對(duì)中國而言,抗拒政治是一個(gè)給人極強(qiáng)印象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從總體上看,自踏入近代門檻,中國就被抗拒政治所主宰。這是國家處境所注定的。從全局來看,中國對(duì)現(xiàn)代化采取的改革措施也好、排斥行動(dòng)也罷,都具有鮮明的抗拒政治特點(diǎn)。在晚清帝國向民族國家轉(zhuǎn)變的初始階段,少數(shù)族群對(duì)多數(shù)族群的強(qiáng)力統(tǒng)治、“西方列強(qiáng)”對(duì)中國的強(qiáng)力施壓是造成現(xiàn)代中國抗拒政治的早期緣由。自中華民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本來出現(xiàn)過兩次化解抗拒政治定勢(shì)、走向現(xiàn)代建設(shè)的契機(jī),即1927年至1937年的民國黃金十年和1956年確立的四個(gè)現(xiàn)代化建設(shè)的進(jìn)路,但前者因日本的入侵而被打斷,后者因?qū)鴥?nèi)外形勢(shì)的嚴(yán)重誤判而夭折。前者的建設(shè)中斷后,隨之而來的便是強(qiáng)化抗拒政治的國內(nèi)外對(duì)抗政治;后者的嘗試告終后,抗拒外來威脅的攘外型政治便走向勢(shì)不可擋的全面抗拒/對(duì)立政治。在改革開放時(shí)期,抗拒政治的權(quán)力土壤與社會(huì)機(jī)理發(fā)生了重大變化,本來應(yīng)循序進(jìn)入一個(gè)理性妥協(xié)的法治秩序,但因?yàn)閮?nèi)政外交上的不平衡發(fā)展,讓社會(huì)蓄積了抗拒政治的勢(shì)能。長期沒有得到很好疏導(dǎo)的維權(quán)政治,以及再次塑造的攘外型抗拒政治,成為抗拒政治重啟的輪替性模式。抗拒政治仍然顯現(xiàn)出不斷反復(fù)的特征。
是不是說中國的抗拒政治已經(jīng)成為解不開的死結(jié)呢?當(dāng)然不是。環(huán)顧世界現(xiàn)代化史可知,化解一個(gè)國家抗拒政治的癥結(jié),需要將國家安頓在理性、民主與法治的平臺(tái)上。一般而言,在這樣的國家平臺(tái)上,公民及社會(huì)群體之間的差異、糾紛、對(duì)峙自不可免,但卻有一個(gè)理性處置相互抗拒行動(dòng)的政治平臺(tái),人們不需要極化自己的抗拒理念與行動(dòng),而能夠借助合法的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與理性協(xié)商,解決對(duì)抗,理性妥協(xié),各得其所。即使出現(xiàn)非常情況,不同集群之間出現(xiàn)一時(shí)難以化解的對(duì)峙,甚至出現(xiàn)激烈的沖突,以至訴諸于戰(zhàn)爭,走到瓦解國家的邊緣,但最后也會(huì)因?yàn)榉€(wěn)固的憲治機(jī)制,將國家重新安頓在立國時(shí)所確立的理性政治平臺(tái)上。美國南北戰(zhàn)爭的歷史結(jié)局提示了人們一個(gè)國家解決非常狀態(tài)下內(nèi)部對(duì)抗的路徑。一旦國家落在立憲民主的平臺(tái)上,對(duì)內(nèi)提供保障,對(duì)外抵御侵略,它就有了一個(gè)讓自己的公民和平寧靜地尋求發(fā)展的強(qiáng)大制度保障,對(duì)內(nèi)的同胞友愛與對(duì)外的理智相待成為國家處理內(nèi)政外交的基本導(dǎo)向。因此,抗拒政治即便存在,也不可能絕對(duì)主導(dǎo)政治走向,因?yàn)榭咕軐?dǎo)致的政治極化只會(huì)是一時(shí)一地的偶然現(xiàn)象,不可能主宰國家的政治命運(yùn)(15)當(dāng)下美國處在政治極化的不正常狀態(tài),這是二戰(zhàn)以后美國與蘇聯(lián)主導(dǎo)的世界秩序瓦解,尤其是蘇東劇變以后單極主導(dǎo)全球政治,國際問題在美國的地位下降,而國內(nèi)問題升級(jí)為主要問題的必然結(jié)局。但是,美國的當(dāng)下危機(jī)即便被認(rèn)為已經(jīng)從社會(huì)危機(jī)升級(jí)為憲政危機(jī),那也只是美國社會(huì)自我修復(fù)的國家運(yùn)行周期的表現(xiàn),大概率不會(huì)像人們預(yù)測(cè)的那樣走向崩潰。。
中國正努力邁進(jìn)在民主法治的軌道上。從積極應(yīng)對(duì)的視角看,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huì)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努力實(shí)現(xiàn)的目標(biāo)是國家持續(xù)發(fā)展,以“更好維護(hù)和運(yùn)用我國發(fā)展的重要戰(zhàn)略機(jī)遇期,更好統(tǒng)籌社會(huì)力量、平衡社會(huì)利益、調(diào)節(jié)社會(huì)關(guān)系、規(guī)范社會(huì)行為,使我國社會(huì)在深刻變革中既生機(jī)勃勃又井然有序,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發(fā)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會(huì)公正、生態(tài)良好,實(shí)現(xiàn)我國和平發(fā)展的戰(zhàn)略目標(biāo)”。從解決消極問題的角度看,則是要化解抗拒政治極化的種種法律導(dǎo)因,下大力氣解決“有的法律法規(guī)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guī)律和人民意愿,針對(duì)性、可操作性不強(qiáng),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quán)諉責(zé)現(xiàn)象較為突出;有法不依、執(zhí)法不嚴(yán)、違法不究現(xiàn)象比較嚴(yán)重,執(zhí)法體制權(quán)責(zé)脫節(jié)、多頭執(zhí)法、選擇性執(zhí)法現(xiàn)象仍然存在,執(zhí)法司法不規(guī)范、不嚴(yán)格、不透明、不文明現(xiàn)象較為突出,群眾對(duì)執(zhí)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qiáng)烈;部分社會(huì)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quán)意識(shí)不強(qiáng),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lǐng)導(dǎo)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qiáng)、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quán)壓法、徇私枉法現(xiàn)象依然存在”。循此路徑,確實(shí)有望避免抗拒政治的再興,即解決抗拒政治僭越為中國主流政治的問題。
在一個(gè)重建時(shí)代,中國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化解抗拒政治風(fēng)險(xiǎn)的進(jìn)路。一旦真正建成了民主法治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政治體制,那么,反復(fù)出現(xiàn)的抗拒政治就失去了它的存在理由和作用根據(jù),中國也就可以從容地完成重建時(shí)代的任務(wù),成為秩序可保的現(xiàn)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