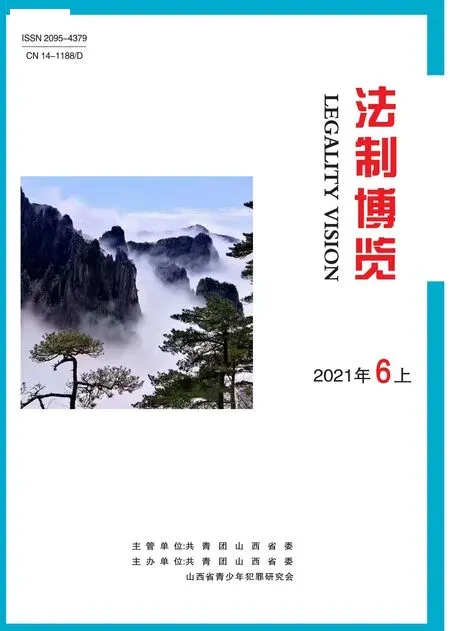宅基地使用權的法律規制建設思考
陳怡竹
(重慶三峽學院三峽庫區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重慶 404100)
自宅基地的三權分置相關理論提出以后,深入分析現行三權分置有關制度,不難看出,在部分試點地區制度改革還存在宅基地的確權困難、監管不到位、分配不均、立法不健全等問題。因此,需要從法律層面對于相關問題進行總結,并對政策展開合理性分析,擬訂完善的解決措施。
一、宅基地使用權的法律規制建設法律問題分析
(一)宅基地確權問題
農村地區民用房改革需要從產權制度方面展開創新,明確產權置換,房產擔保、農戶產權、土地的自由權承包、土地的入市轉讓、土地自愿承包和民主管理等多方面內容。產權明確能夠為農戶宅基地的所有權確認和農村地區土地資源的分配奠定重要的法律基礎。其中農戶產權內涵有兩方面:其一,對農村住房用地的使用權確權;其二,對于農村地區民住房用地使用進行確權,提高農民對于住房用地的產權認識。然而,在農村地區的住房用地所有權主體還存在地位空虛之問題,農民可能不了解產權屬性特點,將住房用地所有權和使用權概念混淆,導致部分集體成員認為集體擁有的住房用地歸私人所有,還可能產生買賣或者轉讓等想法。同時,農村地區宅基地的確權問題也十分嚴重,以村委會協調或者集體協商等形式難以高效解決,由于缺乏法律方面制約,就會影響住房用地確權工作開展[1]。
(二)宅基地的分配不均勻
我國宅基地數量、范圍在第一次分配的過程就已確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而未發生改變。在時代快速發展過程中,隨著農村人不斷流動,初次分配住宅基地特點和當前使用情況出現不適應問題。具體如下:第一,同一家庭存在多片宅基地,農村人口大面積向城市涌入,部分宅基地出現虛置現象,導致宅基地資源發生過度浪費問題。第二,計劃生育放開,農村人口增加,新增成員需要獲得全新宅基地才能滿足生活需求,但是宅基地在初次分配過程就已確立,因此新增成員沒有機會重新獲取宅基地,還會造成農村地區宅基地資源緊缺問題。由于宅基地的分配不均衡,可能影響三權分置順利推行。
(三)監管機制不完善
隨著三權分置試點區域的建設,宅基地第三方使用者擁有房屋用地收益權。為了規避個體工商戶借助社會資本,通過土地下鄉的方式招商圈地,不規范使用宅基地,應該對上述行為實施監管。實踐階段,村集體針對居民的住房用地監管措施應用可能存在問題,導致農民與第三方經濟體產生“多對一”關系,還有部分農民存在僥幸心理,尋找制度漏洞,導致監督權難以有效落實。
(四)相應法規完善性不足
自三權分置實施以后,農民與第三方經濟體在居住用地使用方面不可將其局限為農村住宅,還需要住房用地用途和集體所有權加以拓展。對此要求相關立法不斷完善,才能使宅基地的使用權和改革過程相適應。當前,我國還未針對宅基地的使用權放活方面制定專項法規,相關制度規定相對零散,急需實現農村地區住房用地的三權分置,將住房用地的使用權放活,明確宅基地使用權放活途徑,并制定相應法律。
二、宅基地使用權的法律規制建設法律問題解決對策
(一)制度層面的創新
對于上文中提到的三權分置有關法律問題,從制度方面分析展開創新,具體可從如下方面入手:第一,將宅基地的所有權主體加以明確,解決宅基地分配或者流轉階段執行,明確村集體的經濟組織所有權,可依法行使宅基地處置權,加強宅基地使用管理,探索提高農民住房收益的路徑。第二,優化改革農戶資格權獲取途徑,結合三權分置對于土地改革各項要求,以戶作為單位完成農戶資格權的確認,確權以后展開住房用地登記管理,保證土地交易安全性,為宅基地管理和土地使用提供便利[2]。第三,拓寬宅基地用途,可使用出租、抵押或者轉讓、置換多種形式加速住房用地流轉。第四,落實三權分置有關管理監督工作,嚴格按照政府要求,由行政部門對于農村住房用地經營、開發等工作實施監督,保證土地的經濟化利用,如果發生違法現象,應及時整頓,提高農民風險意識,能夠行使自身監督權,調動農民參與三權分置制度改革積極性。
(二)立法層面的完善
1.增設農戶資格權
資格權可以說是特殊的益物權,涉及的民事主體一方為物所有者,另一方為用益物權人。三權分置政策實施以后,讓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從原權利當中脫離,新設宅基地應該包括收益權、占有權和處置權。農村住房用地的資格權獲取,可引入集體組織成員權利,如果農戶想要擁有住房用地的資格權,應該以戶作為單位,及時備案,通過村集體大會完成住宅用地的資格權確認。針對宅基地資格權缺失問題,由于農村住房用地的資格權是村集體內農戶依法獲取物權性權利,此時,如果農戶由于特殊原因從村集體當中脫離,自愿向城市當中遷移,或者農戶已經死亡,無繼承人,農戶物權性權利應該回歸純集體,農戶失去原居住宅基地資格權。
2.完善使用權的流轉相關法規
一方面,要明確農村的宅基地獲取、退出等機制。雖然我國對于宅基地的有償或者自愿退出相關機制加以明確,但是仍然需要從立法層面對于其退出機制加以規范。如果農戶從村集體當中脫離,就代表其已經放棄對于原居住地宅基地所有權,同時也不具備宅基地的資格權和使用權。此時,村集體可成為農村地區居住用地所有權人,可對于閑置住宅用地合理配置,如:用于改造獲取經濟利益或者分配給其他需要的村民。針對退出宅基地資格權的農戶,應該變為永久居住式城鎮人口,這樣才能保證其合法權益,完成宅基地改革最終目標。
另一方面,還需將宅基地使用權流轉范圍加以明確,讓農村住房用地的使用權更加靈活。對此,可在民法典物權編的編制過程,將農村的住房用地使用權流轉范圍加以擴充,允許村集體之外其他成員獲取住房用地部分使用權,加速使用權的流轉,并將流轉主體加以明確。在兩權分離階段,農村住房使用權包括使用和占有等權利,不包含經濟效益權,這時住房用地使用權屬于不完整形式的用益物權。如果根據三權分置有關制度,對于住房用地權加以改造,改造以后住房用地權變為經濟效益權,又成為效率低的用益物權。所以,需要在《民法典· 物權編》當中將經濟效益這項權利明確規定,賦予農村住房的使用權經濟效益,使住房用地得到最大化開發。這時,住房用地使用權從法律上也更加完整,成為益物權,不可再將用地使用權歸入《土地管理法》之內,而是置于民法體系當中,以適應當前住房用地管理需求,從法律層面理清農村的住房用地權屬劃分問題,使我國法律體系更加完善[3]。
總之,從現有三權分置制度方面來看,還存在與我國現有經濟的發展狀態不符問題。在三權分置改革過程中也面臨著重重困境。對此,需要將農村居民的住房用地所有權人加以明確,保護農村住房用地三流轉階段經濟效益,并且對于農戶資格權展開物權創設,保證其財產權益。除此之外,還需賦予第三方使用人監督權,在宅基地使用權方面通過法律規制將其退出機制不斷健全,讓農村宅基地的使用權流轉范圍加以明確,提高農村宅基地的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