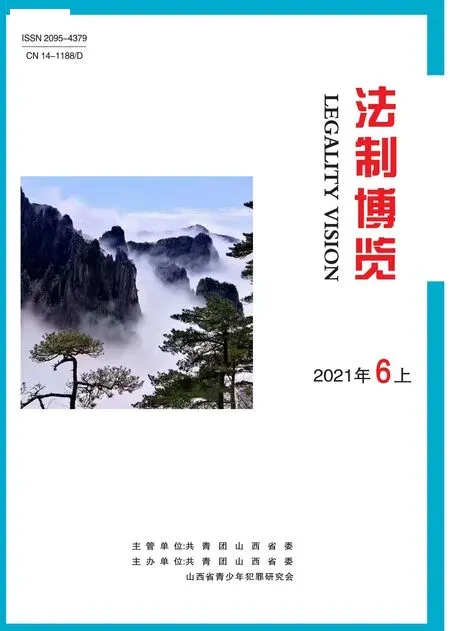對我國現(xiàn)行民事訴訟回避制度的探析
董婉鈺
(吉首大學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一、我國回避制度的內(nèi)容
根據(jù)現(xiàn)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下文稱《民事訴訟法》)(2017年)的規(guī)定,民事訴訟回避制度,是指在民事案件訴訟過程中,本案當事人、翻譯人員,書記員、鑒定人、勘驗人等因與案件或案件中的當事人,具有在某一種相關利害關系,或說其他一些特殊關系的,有可能對此次民事案件審判不能公平公正的處理的時候,從而暫停參與該案訴訟審判等活動中的一項訴訟制度。更通俗地來說,即為日常所言之“避嫌”。在該制度中,回避可以被分為自行回避和申請回避。有關情形在我國的《民事訴訟法》中第四十四條中作出了明述。
二、我國現(xiàn)行回避制度的問題及原因
我國之所以需要借鑒無因回避,究其原因在于:一是從社會層面上,仍存在著一種找熟人托關系的社會現(xiàn)象,即處理問題時依靠“熟人”這層關系,在“熟人”的情感面前,審判的結果難免對一方有所偏頗。同時對另一方帶來不公平的審判,導致審判在一些程序上抄近道、相互包庇、徇私舞弊,甚至可以說是會影響司法的公平正義。二是從國家層面上,現(xiàn)有施行的“有因”回避制度當中,主要存在操作困難,附條件冗雜、門檻高且實用性非常之差,所以說在某種實際操作中,是比較難于實現(xiàn)的。本文從以下幾點簡述:
第一,申請回避條件苛刻。我國雖然在《關于審判人員嚴格執(zhí)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規(guī)定》(2000年)中擴充了回避事由,比如對親屬關系的補充。[1]但在人際關系如果僅從規(guī)定中所列出的著手,就會造成一些不為人知的關系鉆空子。在國家現(xiàn)有當中的有因回避制度中,如果當事人有申請回避的需求,那么則需提供充分的證據(jù),來作為申請回避的理由。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如果回避者是法官等司法人員,取證難度將會大大增高。借鑒無因回避制度的情況,則無需提供過多證據(jù),只需對申請無因回避人數(shù)進行控制,對可能產(chǎn)生不公平現(xiàn)象的評判標準進行劃分,既可減輕司法人員整理核對大量證據(jù)的負擔,也可以在整個案件庭審過程中,適當?shù)臏p輕案件當事人,對整個審判結果認為不公平的懷疑和顧慮。
第二,立法語言不夠準確。最高法、司法部雖然在《關于規(guī)范法官和律師相互關系維護司法公正的若干規(guī)定》(2004年)中回應了有關“其他關系”的內(nèi)容,但仍然缺乏適用率。[2]《民事訴訟法》(2017年)中仍存在不明釋義的字眼,比如“其他不正當行為”,是否包括產(chǎn)生利害關系的程度、不正當行為的內(nèi)容等。畢竟人類是一個復雜的群體,存在各種各樣的關系,在明確關系范圍的同時,擴大回避對象的內(nèi)容。一旦規(guī)定中未提及的關系或情形出現(xiàn)在審判過程中,可借鑒無因回避制度進行解決。此外,民事訴訟中的“近親”,這一概念范圍有過于狹窄,只是僅僅包含當事人的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這些近親屬關系的概念,顯然和我們?nèi)粘K斫獾慕H屬關系,有較大范圍的理解偏向,也是回避制度的缺陷所在。
第三,當事人不知情而審判人員也未及時告知。我國僅在《民事訴訟法》中規(guī)定了兩種回避途徑:自行回避和申請回避。但從實際操作看來,如果當事人在即將審判時才了解到回避制度,在缺乏準備的情況下,無疑是對當事人新增負擔;即使將回避內(nèi)容附帶于應訴通知一并書面?zhèn)鬟_給當事人,許多當事人也難于真正理解,更不用說實際操作了,甚至審判人員也僅僅把其當作訴訟程序中一項“走過場”。也就是說在當事人未申請回避,而審判人員等相關人員又沒有自行回避時,不僅此前的審判結果會失去信服力,即使延期審理,也是對當事人不利的狀態(tài),必然會影響案件的公正審理。
三、世界主要國家的無因回避制度
目前,采用無因回避制度的基本是英美法系國家,而采用有因回避制度的國家是大陸法系國家。
(一)德國等大陸法系國家
德國、日本的民事訴訟法按照回避方式的不同規(guī)定了相對分離的回避原因。在德國,其回避方式分為自行回避、申請回避兩種,在《德國民事訴訟法》中,法官自行回避的原因為六項,較為明確,沒有兜底條款(第四十一條);當事人申請回避的,除了可以引用法定的自行回避理由外,還可以擔心法官偏頗(不公正)為理由(第四十二條)。雖然形式上并未明確“無因回避”這樣的字眼,但實質(zhì)上“法官偏頗”的理由也無異于無因回避的本質(zhì)。《日本新民事訴訟法》(第二十三條、二十四條)回避理由的規(guī)定與德國類似。可見,在德、日等其他大陸法系國家中,自行回避的原因側重于法官與當事人的身份、血緣等利害關系或者程序上的客觀因素,在方便法官引用退出審判、保障當事人程序權利的同時,也為防止法官拒絕裁判留下了制度空間;申請回避的理由則更側重于當事人主觀上的不公正感,對當事人提供更為有力的程序保障。
(二)美國等英美法系國家
美國的回避制度具有其司法體制和法律文化的特色。作為事實審理者的陪審團,其成員可通過有因回避請求與無因回避兩種方式被取消其陪審員資格。有因回避請求同樣需要提出具體的回避事由;后者無因回避則無需說明任何理由即可提出回避請求。美國法官的回避事由及回避程序則通過《美國法典》《司法行為準則》等的相關規(guī)定來調(diào)整。相對于大陸法系國家的回避原因,美國的法官回避事由更具有包容性,在對當事人憲法權利和程序性權利的保障的方面更為重視。
四、我國無因回避制度的構建
(一)我國參考無因回避制度的價值
建立無因回避制度,一方面維護了當事人的回避申請權,也從另一方面打消了訴訟雙方對于“暗箱操作”的顧慮,無疑給雙方打了一劑強心針。畢竟在實際生活中,還有很多沒有考慮周全的情況,或是取證遇到瓶頸的回避對象,而當事人又覺得很有必要進行回避。此時,申請無因回避也是另一種使審判更加公平、更具信服力的做法。同時,也為法官進行公正裁決清掃了障礙,有利于法官更加客觀公正的裁決。
回避制度的設立和完善,究極目的不只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使其受到盡可能公平公正的對待,也是為了使案件能夠得到公平的審判。尤其是我國現(xiàn)在正處于社會轉型階段,社會矛盾增多,再加上我國人口眾多,人際關系錯綜復雜。因此適當引入無因回避制度不僅能維護司法程序的公平,也能最大程度上減少社會公眾的疑慮,進而節(jié)約司法資源、提升司法效率。
(二)對于我國無因回避制度構建的建議
1.將模糊字眼做出明確釋義
建議將關系回避情形下需回避人員的個人的經(jīng)歷信息作出詳細的披露,建立“回避檔案”制度。[3]這樣的信息披露人員不僅需要包括家庭主要成員,還有對于有相對近親關系的,在工作、學習以及投資等方面的一些基本情況。由于信息過于龐雜,可以以網(wǎng)絡數(shù)據(jù)庫的形式來進行登記和公開,以便于申請者進行查詢。在這樣較為完善的信息當中,當事人再提出回避申請時,只需提供相應必要的證明(即客觀上能夠對被申請對象產(chǎn)生合理懷疑)即可。既能加快審理進行的速度,也能避免當事人未被提前告知回避制度的情況。
2.擴大回避對象及申請主體的范圍
在我們國家目前實行的回避制度中,所對應的回避對象只是包括案件審判人員以及庭審的書記員,案件翻譯人員、鑒定人和勘驗人員,而回避制度的決定主體在這些回避對象中,在我認為依然有待擴大對象潛力,比如案件審判委員會委員,案件庭審庭長,案件相關司法機關人員等。根據(jù)我國目前所實行的回避制度內(nèi)容中,現(xiàn)行回避制度的申請其實就是主體的當事人,和其法定代理的相關人員。而實際案件中,不免有當事人沒有意識主動行使回避申請權,本文建議將律師、檢察人員納入申請主體范圍,同時在申請回避制度中,也應考慮到案件執(zhí)行程序主體的執(zhí)行人員。
五、結論
隨著人們的綜合素質(zhì)顯著提高,對于權利的保護意識也逐漸增強,在權利受到侵害、利益發(fā)生損害時,更多的公民選擇拿起法律的武器。結合我國的基本國情,以實際情況作為出發(fā)點,將無因回避和有因回避相結合,有利于構建更加公平有序的法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