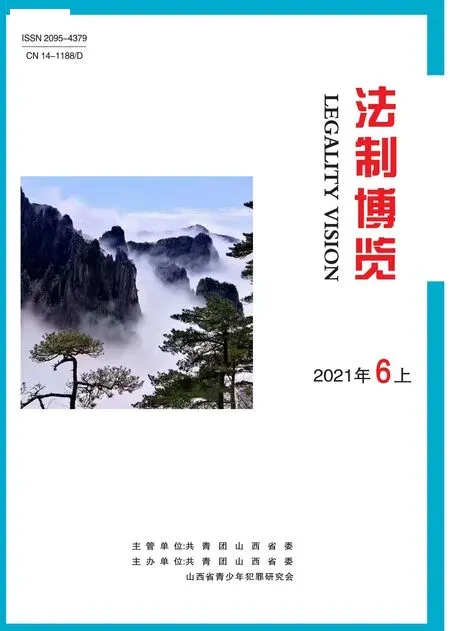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著作權間接侵權責任
劉舜堯
(青島科技大學,山東 青島 266061)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各樣的網絡服務平臺層出不窮。與此同時,網絡侵權行為也時常發生,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由于其“客體的非物質性決定了侵權易發生、難保護的基本特點”[1],知識產權的網絡保護值得法學界關注。與傳統的知識產權侵權不同,網絡知識產權侵權由于網絡服務商的中立幫助行為使得侵權者的侵權成本大大降低,又由于網絡匿名等原因,權利人的維權成本較高。此時,比起向直接侵權者求償,轉而要求網絡服務平臺為其間接侵權行為負責成為看似更加便利的選擇。
對于網絡領域的間接侵權責任,學界一直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爭議和探討,本文將嘗試證明追究網絡服務平臺之間接侵權的合理性,同時對我國網絡間接侵權責任制度的完善提供一些建議。
一、間接侵權責任綜述
間接侵權行為是相對直接侵權而言的概念,其一般表現為“直接侵權行為的幫助行為或預備行為”[2]。直接侵權指“未經著作權許可,直接實施侵害或者妨礙著作權專有權利行使的行為”[3],相對的,間接侵權行為不會直接侵害著作權專有權利的行使,往往幫助直接侵權的完成。直接侵權直接將侵權作品作為其最終產品,屬于內容傳播。而間接侵權則僅僅為侵權作品的傳播提供技術或設備,系技術支持。[4]
美國在《數字千年版權法》規定了協助侵權和替代侵權兩種間接侵權類型,最高法又在Grokster案后確定了引誘侵權責任這一類型,“實質性非侵權用途”原則、“避風港原則”“紅旗標準”也在實踐中被廣泛運用。[5]這在我國的法律中也有體現,《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體現了避風港原則,法釋[2020]十九號第九條則羅列了紅旗標準的具體判斷依據。現有規則還存在著一些缺陷,如“知道或應當知道”的界定不夠明確,使得在認定過錯時存在歧義。目前還未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事前審查義務,使得權利人的保護與技術進步之間的矛盾難以調和。
二、處罰網絡服務提供商的必要性
(一)保護被侵權人權利的必要
網絡侵權中著作權人的權利由于種種原因往往難以得到有效救濟。首先,一個不被侵權人重視的侵權行為常常可以造成巨大經濟損失,而直接侵權人的經濟能力卻常常無法填平被侵權人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被侵權人只能向直接侵權人進行求償,其損失就難以得到救濟。第二,由于網絡平臺的特殊性,一般不要求用戶具備相應的民事行為能力,常常出現“藏在網線后面”的侵權人實際民事行為能力不足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對侵權人(或其監護人)主張權利往往難以實現,或需要面對巨大阻力。第三,網絡平臺往往允許用戶匿名注冊并發表作品,就算求實名,注冊信息的真實性也難以保障。此時,被侵權人尋找直接侵權人需付出巨大成本,常常面臨無法找到具體侵權人的情況。
上述三種原因使得被侵權人向直接侵權人求償的效果并不理想。所以,為了保護知識產權、保障被侵權人的合法權利,需要對網絡平臺的行為進行一定限制。
(二)法經濟學角度考慮的結果
在網絡侵權的整個環節里,說網絡服務提供者所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如果缺少了網絡服務,很多侵權行為甚至無法完成。與此同時,由于網絡平臺有較高的技術支持和數據便利,其可以比較方便地利用技術手段在其可以控制的數據范圍內對潛在的或已經形成的侵權行為進行篩選和鑒別,同時利用其在自己平臺的操控能力進行排除。
責任的分配可能會相應地增加網絡服務提供商的運營成本,但達到同樣的效果,網絡平臺付出的可能成本遠遠低于權利人或其他社會主體所需付出的成本。所以將此種責任加在網絡服務提供商身上實際上是最為經濟的選擇。
三、網絡間接侵權責任制度的完善建議
(一)明確“知道”及“應知”的含義
2012年最高法出臺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的法律解釋(法釋[2012]20號),其中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或應知”網絡用戶利用網絡服務侵害網絡傳播權而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構成幫助侵權,需承擔侵權責任。此項解釋廢止了之前法釋[2006]11號中“明知”的規定。自此以后,學界對于“明知”和“應知”含義便一直爭論不休。與此同時,鑒于“間接侵權在客觀行為要件方面得到了滿足,對主觀過錯的認定成為認定其是否承擔間接侵權責任的關鍵”,[6]所以,厘清“明知”和“應知”的具體含義就顯得尤為重要。
2020年最高法曾對法釋[2012]20號作出修改,但修改后的法律解釋依然保持了“明知或應知”的規定,對兩者的具體含義也沒有做出解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七條也沿用了“知道或應當知道”的說法。一般觀點認為“明知”與“故意”相對,而“應知”則對應著“過失”“故意”和“過失”組成了過錯的兩種形態。[7]根據此種觀點,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確表示知道和依證據推定知道這兩種情況都被劃分到“明知”的范圍中,而由于過錯不知曉的情況則稱為“應知”。法釋[2012]20號第八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確定其是否承擔教唆、幫助侵權責任。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過錯包括對于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的明知或者應知”印證了這種觀點。然而,在接下來的第九條中規定:“人民法院應當根據網絡用戶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具體事實是否明顯,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構成應知”并列舉了幾條判斷因素,這些因素的列舉又好像是對紅旗標準的具體規定。根據這種邏輯,“應知”似乎就與“推定知道”畫上了等號。
綜上所述,為了能夠有效地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構成間接侵權,需要相關部門對“知道”和“明知”的含義具體解釋、加以明確。
(二)確立網絡服務經營者的事先審查義務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五條具體規定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通知-刪除”義務,最高法在法釋[2020]19號中也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事后采取措施防止危害擴大的義務做了規定,但對于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事前預防義務我國現有的法律還沒有具體規定。
但是,在實踐中,如果網絡服務提供者能夠利用其擅長的技術手段在侵權作品公開發表之前對其進行初步篩選甄別,將大大降低侵權作品的數量。并且由于網絡服務提供者對網站或者應用的管理地位,其可以相比權利人更早地發現侵權行為的發生,可以更早地防止侵權行為造成巨大損害。同時,由于網絡服務提供者從網絡服務中獲益,規定其承受一定的預防義務也符合正義的要求,只需注意此種義務的設定不要過于嚴苛以免過分加重服務商的負擔即可。
(三)制定“通知-刪除”機制的法定統一標準
根據現有的法律規定,“通知-刪除”規則是網絡服務提供者承擔責任的關鍵。一方面,此規則作為避風港原則在國內的轉化適用,在著作權人權利的保護和互聯網發展之間找到了一個相對不錯的平衡。另一方,此規則為判斷法律服務提供者是否“知道”提供了直接的參考依據。
但是如何能夠保證“通知”有效,不應該單純地依靠權利人與網絡服務提供者兩者完成,還應該制定相關法規對該機制的具體設立提供法律保障。應該出臺相關規定強制要求網絡服務提供商在其服務平臺設立符合規定的專門渠道,并規定一經權利人投訴,平臺在合理期限內未處理的視為知曉侵權行為。如此,一來為權利人可以有效通知服務商提供了渠道保障,二來可以督促網絡服務提供者盡快履行職責,避免損害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