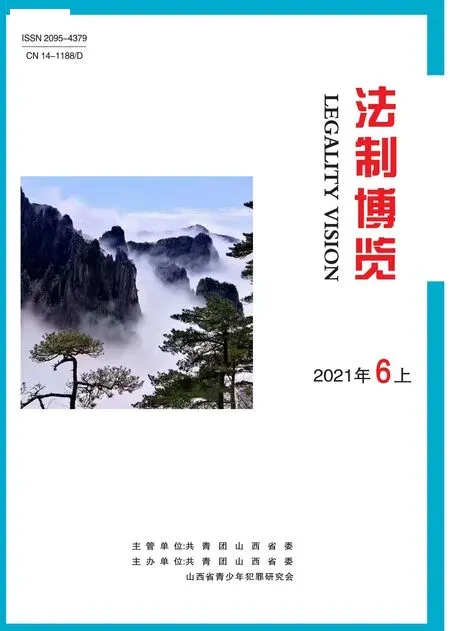無限防衛權的構成要件及相關問題分析
李廣帥
(貴州民族大學,貴州 貴陽 550000)
我國《刑法》針對出現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不予追究防衛者刑事責任,筆者稱之為無限防衛權。我國刑法對無限防衛權的規定較為原則,且用語模糊,不盡周延,導致理論上的爭議和法律實務中的困惑。這種情況顯然有悖于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妨害了司法公正。筆者試圖就如何正確理解和認定無限防衛權進行探討,以求對其有一個統一、完整、明晰的把握。
一、無限防衛權的基本概念
如何界定無限防衛權的內涵,理論界存在著不同認識,我們認為,無限防衛權是一種特殊的正當防衛權,它同樣被國家法律所認可,防衛人在面臨一些特定的、針對人身的暴力行為之侵害時所具有的采取相對充分的手段進行防衛的權利。
通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其特征如下:
(一)防衛行為是一種權利。無限防衛權是刑法賦予當事人的一種自力救濟權,是當人身權利受到暴力犯罪之侵犯時,而派生的救濟性權利。
(二)防衛原因的只有法律才能規定。具體為《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所規定之情形,除此之外,沒有無限防衛權的適用余地。
(三)保護對象的針對性。我們認為無限防衛權所保護的權利只能針對人身權利,而不包括其他非人身的權利。
(四)防衛行為程度的無限性以及行為后果的不可罰性。無限防衛權的行為雖然具有防衛性,但并不是要求權利享受著只能被動地抗擊不法侵害,行為人完全可以動用主動攻擊的方式侵害對方利益,故無限防衛權之行使可以采取主動的形式,無程度之局限,可以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不必要求防衛行為與不法侵害的程度相適應。
二、無限防衛權的構成要件
我們認為,無限防衛權不過是《刑法》二十條第一款的一種特殊形式,無限防衛權的成立要件,建立在一般正當防衛的既有要件之上,并把握無限防衛權的特殊性。因此,把無限防衛權的構成要件劃分為“兩類要件”進行分析更為妥當。
第一類是一般要件,即無限防衛權與一般正當防衛權構成相同的條件要求,主要包括防衛的意圖、對象、時機、限度等幾方面的條件。
1.確有不法侵害事實;
2.侵害事實在持續;
3.目的為:使得公共利益、國家或者他人的財產、人身、其他合法權益不受不法侵害,即防衛人須懷著保護合法權益的故意;
4.防衛行為要針對不法侵害人本人實施;
5.不能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
第二類是特殊要件,即只有針對《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時,才能實施無限防衛權。
1.只能針對特定的暴力犯罪實施
僅在面對暴力犯罪時,無限防衛權方能實施,除此之外沒有適用余地。
2.暴力犯罪必須達到足以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首先,針對的行為只能是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違法行為,就是說無限防衛權所要保護的合法權益只能是公民的生命權、健康權、自由權、性權利等。再者,這類暴力行為對公民人身權利的威脅必須達到嚴重的程度。如何認定暴力不法行為的程度,筆者認為司法者完全可以從刑法分則相關罪名、法定幅度以及具體案件中侵害人實際使用暴力的強度進行綜合分析。
三、無限防衛權認定中的相關問題
由于目前我國刑法中無限防衛權設立條款的法律用語不規范、詞義模糊不明,導致司法實務中的分歧和爭議,不利于法律的統一正確適用。依據筆者的理解,對這一條款做進一步的闡釋。
(一)如何界定《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規定中的“行兇”
“行兇”的叫法尚不是一個正式的法律定義,不過是人們的生活用語,既不是一個獨立的罪名,也不是一種獨立的犯罪行為。[1]從實質上說,“行兇”常常表示故意傷害或者故意殺人行為,法律卻將其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并列規定在一起,是不符合邏輯、不合適的。既然《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將“行兇”與“殺人”并列加以規定,我們應聯系上下文對這個詞作限制性理解,筆者認為,此處的“行兇”是不包括殺人行為在內的。是否包括一般的故意傷害行為呢?對此法律沒有明確的說明。從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等行為造成的結果看,都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那么“行兇”就行為方式而言,應當和后面列舉的這幾種罪行相似,從行為后果來看,應當是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由此可見,“行兇”專指嚴重摧殘他人身體的重傷害行為。
(二)對“殺人、搶劫、強奸、綁架”的理解
“殺人、搶劫、強奸、綁架”到底包括哪些內容?用體系解釋的觀點我們認為應該包含以上具體罪名也包含相應具體行為。
(三)“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包括哪些種類?
“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似乎是一個兜底規定,但也并非囊其所有,而具體包括哪些種暴力犯罪,法律沒有寫明。[2]我們認為,認定“其他嚴重暴力犯罪”要滿足下列要求:第一,暴力行為必須危及公民人身安全的,前面已述;其次,必須有暴力的手段。還要求,不法侵害人的危害性嚴重。對“嚴重”應理解為“正遭受著致命傷害或者生命安全的緊急威脅”,也就是說暴力的程度足以致人重傷害甚至造成死亡后果。
四、無限防衛權之審視
我國過去公民自身的防衛權意識不是特別強,司法機關在對正當防衛案件的掌握上也是過于苛刻,不利于公民個人防衛權的行使。[3]在這種背景下,立法機關修改防衛條件,尤其是設置第三款來賦予公民一定條件下的無限防衛權,應該是有積極的意義,但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度。在無限防衛權的運用中也存在這種可能,如果恣意濫用,過分行使該權利就會使得不法侵害人的合法權益無法得到保障。“危害社會秩序和制止違法犯罪主要是國家的職能,不能通過設置無限防衛權來轉嫁給公民個人。”公民只是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通過防衛權來保護自己的權利,在一般情況下,應該是主要通過國家的警察權來維護社會治安來獲得權利和自由。
無限防衛權就像一把雙刃劍,在鼓勵公民積極行使防衛權的同時,也可能導致防衛權的濫用。但從刑法修改到現在幾年的時間里,實際上防衛權被濫用的情形并不突出,反而是防衛權未充分行使。我國無限防衛權的設立主要在于鼓勵人們勇于同犯罪行為作斗爭。但過若干年后,通過法律的鼓勵和引導,當防衛權已經被自覺運用、行使了,甚至有時候被過度行使,到那時可以再考慮作出進一步限制和修改。至少從目前來說,我國刑法對無限防衛權的設置是較為妥當的,但在立法技術上尚有缺憾,尤其是無限防衛權的法條表述存在瑕疵,對于“行兇”的表述不嚴謹,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行為具體包含哪些暴力犯罪也不明晰,卻是由司法官掌握,由司法官結合具體的案情而自由裁量。但是我們看到,因為無限防衛后果的嚴重損害性,賦予司法官如此巨大的裁量空間與對眼前的司法官的整體職業素質并不合拍。在目前刑法規定的前提下,可以先由最高人民法院會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作出司法解釋,對相關法律法規作出合乎法理、與國民當前認知程度相適應的解釋,使得具體操作更加科學化、合理化、規范化。[4]
再者,從犯罪論體系的運用角度來說,我國通行的四要件犯罪論體系和德日三階層為代表的犯罪論體系也存在著先入罪后出罪的認定思路。[5]四要件理論先假定防衛人滿足犯罪的主客觀條件,預判其符合具體罪名的各條件后,而后審查其是否具有正當防衛的性質,再從犯罪中排除;德日三階層理論先把正當防衛行為作為犯罪進行該當性評價,而后對其違法性進行評價,因正當防衛不具有違法性而被排除出罪,從而終止犯罪的審查(就這種審查判斷步驟來說,其優越于四要件理論),但這兩種審查思路有罪推定的思維定勢,在眼前我國適用正當防衛政策相對嚴格的情況下,不利于公民大膽使用無限防衛權,也易于導致司法機關隨意對防衛人適用強制措施,故研究改進既有犯罪論,重視正當防衛的權利屬性,從權利和義務的角度的重構新的犯罪論也是當務之急。[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