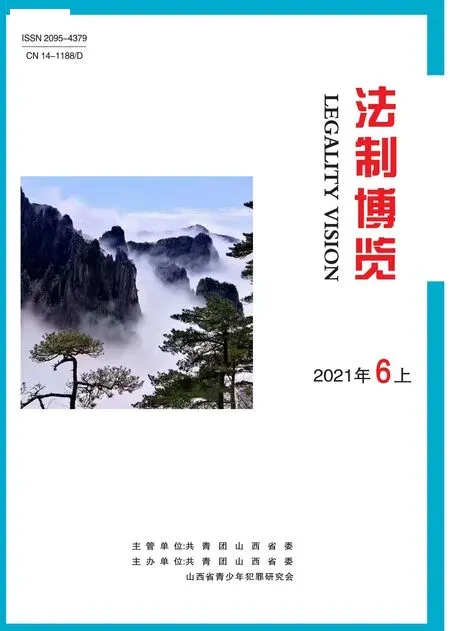犯罪低齡化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
梁一娜
(西北政法大學,陜西 西安 710063)
《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作出調整,十二周歲的未成年人在實施特別嚴重的犯罪后,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的,應當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針對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的問題,是否需要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在法律明確規定刑事責任年齡做出調整后,懲罰未成年人犯罪和保護未成年人權益沖突如何協調引發了激烈討論,降低年齡是從刑法的角度對犯罪低齡化的情形進行規制,從而達到對未成年人的威懾,使其出于畏懼心理而不敢實施犯罪行為,達到預防犯罪的效果。但從實踐來看刑法只是事后法,調整責任年齡不能杜絕犯罪低齡化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應對犯罪低齡化的問題,我們必須從原因分析出發,提出有效性的建議。
一、刑事責任年齡降低的必要性
近年來未成年人犯罪主要集中在十六周歲以上,不滿十四周歲實施嚴重犯罪的占比不到百分之一,但只要是犯罪行為均會對社會環境造成不利影響,給人民造成心理恐慌,尤其對被害人造成不可逆的傷害。如陜西某小學的校內強奸案,行為人的年齡均不滿十四周歲,這表明未成年人的惡性案件呈現出低齡化、暴力化以及復雜化的趨勢,這迫使我國必須對刑事責任年齡作出相應調整。此外低齡未成年人的惡性犯罪行為,由于沒有達到我國規定的刑事責任年齡,刑法無法對其行為進行規范調整,刑事處罰措施的缺失,減弱了刑事處罰對行為人的威懾作用。實施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沒有受到嚴厲的刑罰處罰。再加上非刑罰處罰措施在執行過程中的不到位,行為人并沒有受到實質性的處罰,并沒有因為自己的過錯而承擔相應的責任,使被害人家屬產生一種被告人“逍遙法外”“國家公權力沒有不遵守公平正義理念”的錯覺,而采用自己的方法去報復被告人,從而導致悲劇的發生,也就是被害人的“惡逆變”,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被害人的“惡逆變”。[1]
二、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的原因分析
(一)生長環境惡劣
在當前社會,家庭因素已經成為影響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家長是否認真行使監護責任、處理問題的態度都會影響孩子的成長。有些家長面對孩子的問題上常常采取打罵的方式進行處理,并不會心平氣和地和孩子溝通,有些家長的無限寵溺也會對孩子世界觀的形成產生不利的影響。還有家長因自己外出務工掙錢,將孩子交由長輩看管,也就是常說的留守兒童。長時間家庭教育的虧空以及長時間父母和孩子之間的不交流都會造成孩子囂張跋扈的性格。家庭在培養未成年人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家庭教育可以培養未成年人的性格、承擔過錯的方式,以及人生觀、價值觀,這對未成年人的成長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應對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的社會問題時,我們可以規制家長或者其他監護人的不作為行為,將不正確履行監護職責規定為犯罪行為。明確監護人的法定義務,因監護人的過錯造成不負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實施暴力化犯罪的,按照其過錯對監護人的過錯大小進行刑事處罰,增強其法定義務。此外未成年人的監護由政府負責的,相關直接責任人員對未成年人實施的犯罪行為確有過錯的,以玩忽職守罪或者濫用職權罪進行定罪處罰。[2]
近年來校園欺凌案件的不時發生,引發了國家和人民的高度重視。校園本應該是未成年人學習的地方,但由于家庭、社會的影響,再加上學校的管理疏漏,很容易造成校園霸凌事件的發生,并且常常表現為團伙性質。受欺負者是施暴者的同學,一群孩子對一個孩子的毆打、侮辱,受害者不敢反抗,施暴者還會對此情形進行手機錄像,并將其上傳至朋友圈以炫耀自己的強大。校園霸凌案件的時有發生要求教育工作者要完善學校的制度建設,關注學生的心理狀態,防止校園欺凌案件的發生,通過配備心理健康教育老師,及時對校園欺凌案件進行查處。國家也可以增加相關的法規制度建設,明確加強學校的補充責任,完善教育追責體系。
(二)非刑罰處罰規范不足
非刑罰處罰方式針對的是犯罪行為情節輕微,雖然可以免于刑罰處罰,因其社會危害性低,同時依照“教育、感化、挽救”方針,不執行刑罰而采取相對寬松的處分方式。[3]在我國刑罰處罰方式與非刑罰處罰方式是不可以同時適用的。可實施的具體非刑罰處罰方式包括監護人管教,或者由政府代行監護人的職責,對未成年人進行收容教養、賠禮道歉等。但是由于我國社會發展等現實問題,在實踐中對未成年人的犯罪行為往往采用非此即彼的方式,面對暴力的犯罪采取刑罰處罰方式,而對于情節較輕的未成年人犯罪采取的經常是“一放了之”。對于這種情形,我們可以向世界各國學習先進的治理經驗,比如可以增加非刑罰處罰方式的種類。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可以對具有社會危害性且悔罪性不強的未成年人的出行范圍作出具體的限制。比如將其限制在學習場所和生活場所,不允許其進入娛樂場所,如網吧、KTV等地方,并要求未成年人定期向法院進行報告,對其社會危險性定期進行考核,使其了解犯罪行為的嚴重性以及國家對其犯罪行為懲處的決心。[3]
三、刑事責任年齡降低與保護未成年人之間的沖突
刑法罪名認定的嚴厲和懲罰的嚴格,是公眾尊重和敬畏刑法的原因之一,也是刑法能起到預防犯罪的作用原因。[4]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會使未成年人由于敬畏心理而不敢實施犯罪行為,但是刑事責任年齡的降低會引起與保護未成年人理念之間的沖突。未成年人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力量,少年強則國強,未成年人身上肩負著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我們必須對未成年人進行合理保護。但是在司法實踐中的情況卻不容樂觀,未成年人沒有專門的訴訟程序,羈押期限、審判期限與成年人也沒有區別,審判程序也是依據成年人的訴訟程序進行,在貫徹懲罰犯罪的同時無法體現對未成年人的保護。
我國雖然設立了少年法庭,在實際使用的過程中由于少年法庭的數量較少,因此只能供少數未成年或者未成年主犯使用,難以對未成年人進行全面的保護,在法庭審判中未成年人被告的位置也與成年人無異,法官、檢察官、律師三方對立,未成年被告人處于法庭下方,處于接受訊問的位置。修正案通過以后明確對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未成年人的刑事處罰,但相應的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也不應懈怠,未成年人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也應當得到相應的保護。由于未達到年齡而不承擔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在社區矯正的過程中存在著“放羊式矯正”、考核評估的機制不產生法律約束力等問題,使得未成年人在矯正期間的文化學習、對法律的理解停留在表面,未成年人在社區矯正結束后仍然會繼續實施違法犯罪的行為。無論未成年人是否需要承擔刑事責任,都應該完善相對應的措施,以實現刑法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的功能。
我國18歲以下的青少年約4億,有效遏制違法犯罪低齡化趨勢是當前面臨的重大事情。[5]雖然我國刑法對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做出下調,由于導致犯罪低齡化的原因方方面面,我們仍需聯合家長、學校以及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做出改善措施,使青少年在承擔刑事責任的同時也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對于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無需承擔刑事責任的未成年人,也要使其感受到我國刑法懲治犯罪行為的決心,感受到刑法的威懾作用,在今后的成長過程做到遵紀守法,不會再出現誤入歧途的情形。此外要注重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結合,充分發揮我國刑法的價值,運用法律和非法律的手段,共同為了青少年的健康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