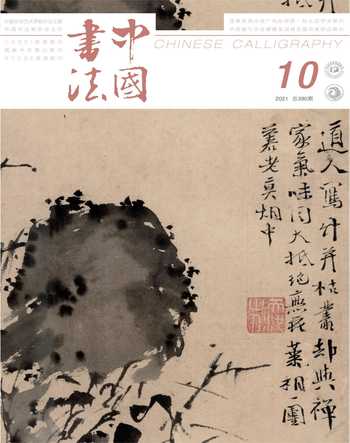隋代寫經書法之南北融合書風的發展
王沁園
關鍵詞:隋代 寫經書法 南北融合
自南北朝以來,儒釋道三教占據思想領域的主導地位,隋帝建都于北方,故自承接北朝一脈書風。隋文帝主張調和宗教與入學,采用三教并重策略,至隋后佛教進入極盛的階段,為之佛教造像更是漸增漸豐的狀態。且當時的官方有意識的倡導規范、嚴謹的寫經模式,亦得益于當時紙張的改進,出現官經生師和官經生。寫經書法出現制度化的規范亦是南北書風融合趨于穩定的一種表現。除此之外,由于隋文帝對佛教的極力推崇,令此時期的佛像、塔寺、經卷數目之巨,彰顯出隋代寫經氛圍的新潮,對南北書風的融合更是營造天時地利人和之景象。這種盛況有如:『文、煬二帝先后度僧尼二十余萬人,立寺三千七百余所,造像二十余萬軀,起塔于一百余州,修故經四千余部,譯經凡八十余部』[1]。
《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中:『開皇元年,高祖普照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象,而京師及并州、湘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并官寫一切經,置與寺內,而又別寫,藏于秘閣,天下之人從風而糜,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于六經數十百倍。』[2]這種景象可謂承傳南北朝寫經書法之后的再發展,據記載隋朝寫經書法有明確紀年的達九十多件,其中包含敦煌當地人書、官府書、傳自內地人書、寺院等,總結歸類此時期的寫經書法大約為一書風融合探索的幾大分支:第一類:『魏碑書』的經書;第二類:嚴謹規范經書;第三類:『端正秀美』的南方書風;第四類:平正娟秀的南方傳統經書——兼南北書風所長,渾厚剛勁不失細膩娟正。書風在隋代的探索并非皆成功,(此處的成功指延續至唐代『法度』化的楷書發展)。兼備南北方特點并在此基礎之上加之制度規范化,紙張的 改進令抄經書的行字逐漸趨于固定化。書風逐漸趨于統一。
第一類:『魏碑經書』的初探索,主以在魏碑書風的基礎上摻雜隸意,字形并無固態,《大般涅槃經》《大通方廣經》《大集經》等為代表。具備早期的魏碑用筆特點,卻在魏風的基礎上改善起收筆的方楞,氣息更為貫連,相較隋代其他寫經書風更顯沉穩厚重之感。
第二類:『嚴謹勁拔』的繼揚探索,主上承北周書風,入筆尖銳無回峰,字態平正,整體趨于統一,《十地論法云地》《佛說金剛般若經》《老子變化經》等皆有北周《大般涅槃經》寫本的意氣。這一類書風中也有風格的差異,《老子中卷變化經》的字勢傾斜,靈動流暢之感穿插于字里行間,但不失嚴謹挺拔。《十地論法云地》的嚴謹端正雖有些許僵硬,字勢與每行的字數趨于統一,也正是隋代寫經書法的進階表現。
第三類:『端正秀美』的南方書風再探索,主學南方原存『鍾王』周正之風,以妍美為長的自然書,《大智度論》《大樓炭經》等頗有《龍藏寺碑》之拘謹之氣。兩本經卷的書寫風格甚為相似,也有結構縱、橫式之分,相較來說《大智度論》更具端雅之態,起筆不蓋尖銳,稍有頓澀,收筆處向下再頓。《大樓炭經》雖稍顯縱勢,也具備秀美之風,較為嚴謹。
第四類:『南北交融』平正成熟化的探索,主以綜合時氣之風,嘗試將南北書風的各長相融,為逐漸規范化奠定基礎,《阿修羅經》《勝曼義記》等與較早出現楷書成熟化的《董美人》《龍藏寺》《啟發寺》等隋代代表性碑刻相近,這又從另一方面看出主流書風的影響力與書風之間存在相互借鑒學習的可能性,更有成于當時文化交流繁盛之象。
在上文中的四類探索可看出隋代寫經書風的多元化,但這種多元的存在又與前朝不同,即在繼承傳揚上再發展。以隋文帝八年《思益經卷第四》、十三年《大智度經釋卷論卷三十》等為南流美與北勁挺書風融合的初像,氣息流暢不失頓挫之遒美之感,頗具新意,與入隋之前的寫經書風有別,將南朝經書結構的端嚴與北朝經書線條的厚勁巧妙結合,又與北朝晚期《大般涅槃經卷第六》書風甚同,但隋代經書從點畫用筆中隸書用意逐漸減少,在此較之前朝更有上下『行氣』流動之感,比之后隋煬帝四年《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五》不難看出,隋代融南北書風的狀態逐漸趨于穩定,楷法逐漸占據主位。
寺院的僧侶書家對隋書的推進作用不可忽視,這其中僧智永、智果所書為佼者,隋煬帝對其評價甚高:『智永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正是因有一批高水準的『抄書手』,隋代寫經書法自有導向,風尚遂行。另有保存了六十余種大藏經都未曾收入的經典佛教刻石——房山石經,這些佛經不是歷代相傳已經佚失的,就是未曾有過記錄的譯本。規模之宏大乃前未有。
隋朝雖短,但確為唐代寫經書法完成純熟化的發展譜好前奏,尚有『楷隸互摻體』書法的風向,但獨為寫經書法發展加快進程,無可厚非的是隋代佛教的繁榮景象不僅為寫經書法吹了東風,更是掀起寫經書熱的小潮流,最為重要的是將南北書風融合于無形,逐漸退去寫經書中的隸書用意,規范抄經具體的行數字數,這無疑是搶占了寫經書法的先機。
至隋入唐之后,寫經書法逐漸出現『盛世』,規范制度化的專職機構為寫經書法的發展提供不可取代的地位,盛況如是出現官府寫經生與民間寫經生,(1)設立抄經機構『寫麟臺,門下省中設有專門的書法班子:『楷書』『群書手』『書手』等。(2)『楷書令史』為專門官吏;(3)『楷法遒美』為書寫優劣的標準;自是井然有序,用途各有不同,但書風已經現成熟穩定。官府寫經生大多由『楷書手』(隸屬秘書省)為主,其中《妙法蓮華經卷第五》款題:『上元三年五月十三日秘書省孫玄爽寫』即為可證。這種抄經組織自隋便有,《老子變化經》所題:『大業八年八月十四日經生王濤寫』署『秘書省』,另有其秘書下省的《妙法蓮華經卷第三》即有題:『上元三年八月一日弘文館楷書……寫』等。而民間寫經生與官府寫經生最大的區別即是初衷與用途,這是佛教興盛之下的產物——非官方抄寫經文的群體,當然存在非官方寫經生的年齡和職業區別導致抄經書的質量不同,例孩童習書時抄寫經書祈福、文人修身養性抄寫經書維系生計等之類。胡適先生言此為:『大概都由于不識字的學童、小和尚的依樣涂鴉,或者由于不識字的女施主雇傭商業化的寫經人潦草塞責,校勘功夫是不會用到這樣兩類的寫經上的』。例《大涅槃經卷第三十七》題:『經生敦煌縣學生……書』、宣和書譜載吳彩鸞書『唐韻』糊生計、《菩薩戒疏》『開鋪寫經』:『乾符肆年四月就報恩寺寫記』等民間經生書。這種佛教寫經因宗教興衰而定,可謂盛及唐代上下之末流。自有『李唐開國,高祖、太宗頗不崇佛,唐代佛教之盛,始于高宗之世此與武則天之母楊氏為隋代觀王雄之后有關。武周革命時,嘗藉佛教教義,以證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3]之論。
唐代成熟的寫經書法最為普知,若追溯其寫經書法及經僧的分部,早在西晉時期的寫經書法既有后來成熟之雛。其中初唐的《妙法蓮華經》卷一評價甚高,啟功先生評《序品》后半、《方便品》前半為:『筆法骨肉得中,意態飛動,足以抗顏、歐、褚,在鳴沙遺墨中實推上品。』[4]諸如此類的寫經高水準之作比比皆是。唐人寫經相較魏晉、隋代風格不同,字勢統一、端正,楷法較為嚴謹但不失熟練程度下的連筆流行性,與《三國志·吳志》相比不難看出,唐初的寫經書法雖『脫胎換骨』更有端韻,但捺畫與橫畫的部分尚有晉味,但不及《三國志·吳志》書的重心偏移的視覺感。更是與隋代的寫經書法幾類探索有接軌之意,且研究唐初期寫經書法中隋代接軌寫經書法之處,更趨于嚴謹。更有《靈飛經》《道德經》《大乘人楞伽經》等上乘之作。盛唐之后的寫經書更是呈肥滿之態,『緣明皇字肥,始有徐浩,以合君所好,經生字亦自此脂』[5]著實為時代使然。
唐人寫經未有兩晉南北朝時期的自由乖張的隸書用意,多是規范化之后的純熟書風,寫經書法興起雖早,但至唐代才完成純熟化的書風演變,這一過程中,由于魏晉南北朝時分裂的局面,縱使其寫經書法規模再龐大也難以成大氣候。楷書中隸書用意頗深、且有魏碑體寫經書法等風格迥異,固然有趣,難免有些許混雜,而隋代的寫經書實現了逐漸楷化的過渡探索,于文化大統一的文化融碑背景下,宗教的主心骨的轉變、發展也為寫經書法提供了優先發展的空間,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流行至隋唐時期三教鼎立,大乘化上的佛教文化初步自覺化,也與書法開始自覺化的過程不謀而合,文化藝術氛圍的覺醒、繁榮乃至書法。南北朝至隋的寫經書法得益于隋代科舉制度的初設令社會的一切開始走向制度化的道路,書者可通過『書學』進入仕途,書法被抬為一門學科,另設『抄經官職』、書法『博士』等,將書法書風、書體進行融合、探索式的發展,但因朝代不過四十年難以融南北之大成,但隋代對寫經書法相關的規范逐漸建立、紙張改進、抄書群體優化等一系列進程,相當于加快隸書『楷化』的進程,乃至唐代熟而生巧,此一階段的書風演變過程中隋代著實為寫經書法的中轉站,同為南北書風融合的中轉站,當可論隋代為南北『寫經書法』融合的先聲,至唐初期這種南北書風的融合可謂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