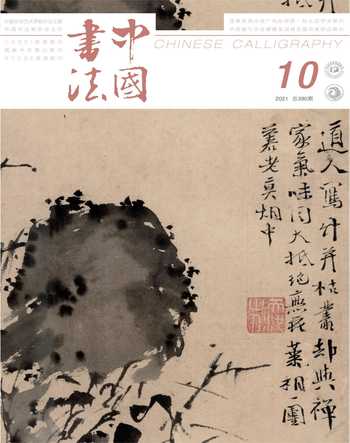『印從書出』在當代篆刻創作中的價值思考
陳靖
關鍵詞:印從書出 當代篆刻 書法意蘊
『印從書出』在當代的篆刻繼承與定位
印章歷經實用、實用兼及藝術、藝術兼顧實用,漸次演變為一種純粹意義上相對獨立藝術形式—篆刻。梳理篆刻藝術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逐漸轉向文人藝術,篆刻藝術在文人的參與下『印宗秦漢』『印從書出』『印外求印』思想理論轉變與探索過程。『印從書出』作為繼『印宗秦漢』后的又一篆刻創作理念,從最初的藝術評論到篆刻創作創新觀念,其內涵也在不斷地演變、發展。多元的文化語境造就了當代篆刻藝術的新格局,篆刻藝術的審美變化、新資料的出土發掘、篆刻創作者的自由選擇與探索等促進了『印從書出』的發展,展望當代篆刻創作,如何在『印從書出』的映照下創作出高質量的作品依然有其時代價值和意義。
毋庸置疑,當提及『印從書出』,談及『書』時第一會想到的便是篆書。因為無論是以實用為主的印章,還是以藝術創作或是欣賞的篆刻都與篆書密不可分。一位篆刻創作者篆刻成就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對篆書的理解和運用。篆刻創作者在進行篆刻創作的同時,在篆書上均是下過很大的功夫,當然這與清代中期篆書的復興有著很大的關系。誠然,只有對文字、書寫有所把握,方能對篆刻有深度的理解。
對于篆刻藝術的外在形式而言:『歷來總結篆刻藝術的三要素為篆法、章法和刀法。篆刻藝術的變化與發展自然也離不開此「三法」上的研究、探索與創新。』[1]文字『印化』的過程似乎在文字形態上做文章,這主要屬于『三法』中的篆法問題,然其中篆法的變化又是筆法的流露和外顯,進而影響乃至改變了章法之形式和篆刻作品之品位,這其中『書法』起到的是領銜作用。在當代篆刻創作中更需將『書』立于重要位置。
『印從書出』在當代篆刻的內涵與外延
書法對篆刻藝術的影響不唯是從藝術創作的角度而言的,書法與篆刻乃至此前實用印章的歷史也有著與生俱來的『血緣』關系。『印從書出』的內涵也在不斷豐富與拓展,『印從書出』的『書』從最初的篆書延展到整個書法語言的把握,以及在多元文化語境的當代篆刻中得以豐富。此亦如馬士達先生所言:『篆刻在本質上即是書法,是書法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有情有性的書法在印章方寸之地上的展示。』[2]
書法的形式語言
傳統書法形式語言的深入挖掘拓展了當代藝術的觀念,也在『印從書出』的理念下進一步擴充到篆刻藝術創作中來,使『印從書出』的內涵不斷豐富。如清人趙之謙所言:『刀法既知,章法又要,往往有刻極精能,而篆勢可淹厭可笑者,此則全恃學問,亦以學書為要。書得法,則結構自安,篆隸真行皆可悟入。』傳統的書法形式語言對篆刻創作者的影響從最初的篆書入印延伸到其他書體入印并追求各書體的內涵特征。如隸書之寬博與方勁古拙,草書之寫意與跌宕起伏。雖然隸書、行草書與篆刻的入印文字存在著較大的區別,然而其中的意蘊和藝術表達方法卻能提升、啟發篆刻創作。這些影響表面上不像篆書對篆刻的影響那么直接,實際上,對不同書體、不同藝術表達方式廣采博收,是篆刻創作者表現出自家風格的重要支撐。真正對書法融會貫通后才能做到入印文字虛實得宜、融匯己意,合若一家;章法變化,長短錯綜、參五取便;刀法上張弛有度,輕重巧施;提問題、立矛盾,而后一一解決,順自然之勢,得天然之妙。
從根本上講,中國藝術的本質是一個立體的、貫通的形式,因此一個篆刻創作者在進行篆刻創作時,也必須有其他書體書寫內涵的參與,而不僅局限于篆刻的圖示視覺借鑒。篆刻創作者篆刻風貌的形成源于對篆書的學習理解,而對書法整體意蘊的把握才是形成真正篆刻風格的核心組成部分。明人朱承爵《存余堂詩話》中言:『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3]『印從書出』延伸到當下,當不僅僅局限于文字的載體與書寫的內涵,更應當是對整個書法意境的把握,以及由此而誘發和開拓出的篆刻審美特征。
多元的文化環境
多元文化語境的影響以及新資料的發現拓寬了篆刻創作者的視野,篆刻創作者與時俱進,不斷進行著新的探索。先秦璽印鮮明的原創性和開放性、縱橫捭闔的章法空間關系、奇肆多變的文字結構;將軍印的『急就』鑿刻,妙趣橫生、自然天成;金石磚瓦陶文真率質樸,渾厚稚拙;在多元文化語境的影響給人以全新的演繹、表現方式,更為契合當代篆刻藝術的審美。文人篆刻繼『印中求印』之后,逐漸轉向『印外求印』。特別是清末以來,金石學、文字學復興;碑學書法的興起等,篆刻逐漸走上了『印宗秦漢』『印從書出』『印外求印』的復合型創作道路,篆刻藝術的形式與審美體系得以確立。
當代篆刻在書與印的自由表達上呈現出多種狀態。其一為根植傳統,別開生面。得益于書法上的素養,以書畫之意蘊融匯其中,以自家刀法與篆法逐漸形成自我面目。其二為繼承經典,厚積廣蓄。沿襲傳統印從書出,以經典印風、印式為追求古雅、雄渾之氣象而呈現個人面目。其三為求異出新,借古開今。借鑒中國傳統經典元素與西方構成藝術,以古代資源凸顯圖式視覺實驗性,力圖形成個人風格。
當代的篆刻創作者不再拘泥于某一印式,新的素材、形式,新的藝術語言進入他們的視野中助力了當代篆刻風貌的形成。陳繼儒說:『文人畫在筆墨不在蹊徑……』氣韻隱含于筆墨之中,氣韻須由筆墨出之,書法篆刻之道無不如此,使刀如筆,如何現筆墨?如何出氣韻?踐行印從書出,以書法為根基吸收消化印章以外的素材,轉化為篆刻語言,表現種種素材,使之成為篆刻中的元素。
『印從書出』在當代篆刻的意義與實現
『印從書出』的提出并非拋棄『印宗秦漢』,而是以『印宗秦漢』為基礎的『印從書出』,也引領了后來趙之謙『取法在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摹印家立一門戶』,提出『印外求印』的思想。周銘在《賴古堂印譜·小引》言:『學印者不宗秦漢,非俗則誣。』誠然『印宗秦漢』是篆刻創作根本與前提,而『印從書出』則是篆刻創作者有意將自己的篆書風格與篆刻風格相融合,『書以印入,印從書出』是篆刻思想在『印宗秦漢』后又一次的『解放』。而『印外求印』又是在『印宗秦漢』『印外求印』的基礎上進一步對篆刻語言形式的拓展。篆刻創作者不再滿足『書』對印章的把握,在『書』這一基點上擴大到『印外』的其他語言形式,開啟了『印外求印』的篆刻藝術創作觀念。因此,『印從書出』作為篆刻史上的一條單獨的藝術創作觀念不斷豐富與外延的同時,也在促進篆刻語言形式的豐富上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從文人篆刻的發展趨勢上看則是詩書畫印意蘊的融會貫通。
『篆刻』二字,簡言之分『篆』與『刻』兩個部分,『篆』是以篆書為主要書體。在當代的書法創作中,入印最為直接的篆書亦呈現繁榮景象,然在創作的深度與廣度上缺少功夫與內涵。當代篆刻的作品較之吳、齊更應在追求『印從書出』的內涵上下更深功夫,創作出符合時代『寫意』精神的作品。
現代篆刻的寫意性起源于二十世紀中葉,在吳昌碩、齊白石等人的努力下,將寫意性至臻純熟。這種寫意性也正是在『印從書出』與『印外求印』的依托下而形成的。吳、齊二人均在書法上是一流,其寫意性亦是在書寫之『寫』上而鑄就的。在當代篆刻創作的作品中,『寫意』的作品已占到了半數以上,在重要的書法、篆刻展覽中,此類作品在展廳中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最動人的作品也會是『寫意』創作中的精品,但細分析此類作品,李剛田先生深有感觸地說:『盡管寫意的篆刻作品從數量到形式表現上都占優勢,但這只是就作品形質而言,我們還不能說這是個寫意精神和創作激情高揚的時代。具有寫意精神與形質上寫意式的作品不盡重合。寫意式的作品并不一定具有真正的寫意精神,而工筆式的作品也未必沒有寫意精神,也即馳刀石上、刀刀生發間的激情體現。』
『寫意』內涵有二:一是表現篆刻創作者的思想上,二是篆刻的風格上。當然寫意風格是寫意思想的外在表現形式,同時,這種『寫意』也構成此后篆刻藝術審美特征的重要組成部分。篆刻藝術發展到丁敬、鄧石如諸人,他們在追摹秦漢印而不想局限于秦漢印的范式之中,力求在秦漢印的范式中著力強調『刀痕』進而發出了『古人篆刻思離群』與『何必墨守漢家文』之音。在實踐中丁敬也以夸張的切刀呈現于世而欲脫離秦漢印面目,愈發表現自我的求變之意。從整個的篆刻風格上亦是如此,篆刻創作者不再滿足于篆書字法、字形上的學習,而是要融匯書意,強調自我所欲表達的獨特藝術風格。篆刻創作者意趣的表達,即以刀表達作者之意。這種意并非不是隨意、偶然形成的,而是與中國人的人文精神、中國書畫等藝術相關聯的。因而篆刻所『寫』之『意』是與寫意的書畫意趣貫穿著的,篆刻所寫意的意境、情趣、氣質與書畫的筆墨『語言』。[5]筆墨所依托的傳統參照,更需要我們去開拓新的創作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