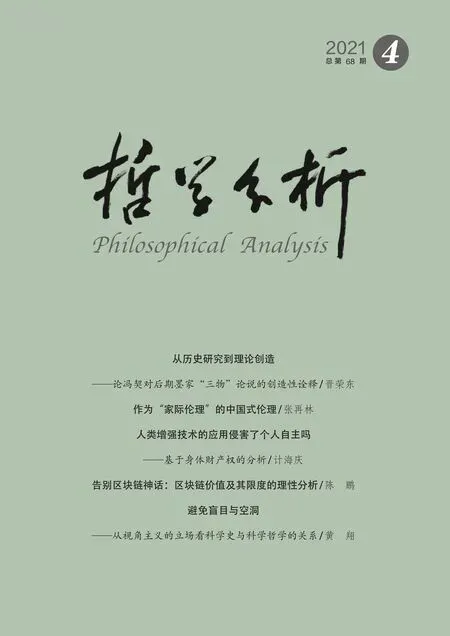理論智慧的能力之維
——從金岳霖到布蘭頓
黃遠帆
一、導 言
眾所周知,哲學的希臘詞義即“愛智慧”。但在當代語境,智慧作為哲學話題一度式微,此外,我們也不會將“智慧”作為一個對哲學工作的評價詞。近年來,不少英美哲學學者又重拾對“智慧”討論的熱情,論者紛紜。智慧研究的復興,大致有如下原因:(1)智慧話題與諸多現有的重要哲學話題具有交集,包括:德性倫理、德性認識論、知識的價值、知識種類、行動哲學、實踐理性,等等;(2)哲學對智慧的研究可以與經驗科學形成富有成效的合作,諸如心理學、認知科學等;(3)智慧的哲學研究可以產生應用價值,尤其對教育學和教育實踐具有潛在影響;(4)智慧話題在哲學史上是一個重要話題,重拾智慧話題能夠接續古今;(5)智慧研究可以促成中西方哲學的對話,對它的研究是貫通中西哲學的。比如,本文不僅討論了西方哲學對理論智慧的論述,也借鑒了儒家、金岳霖等中國哲學的資源。
雖然近年來對智慧的哲學研究在持續推進,但大多數研究針對的是“實踐智慧”(practical wisdom),而關于“理論智慧”(theoretical wisdom)的專門研究則并不多見。本文則嘗試給出一個對“理論智慧”的詳細刻畫。在具體刻畫前,有必要對本文的方法論做一個澄清。當代認識論發展中,“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是一度被奉為圭臬的研究方法。傳統對“知識”的定義為:“得到辯護的真信念”(JTB)。埃德蒙德·蓋梯爾(Edmund Gettier)在1963 年提出了“蓋梯爾反例”,對傳統的知識定義進行了挑戰。aEdmund Gettier,“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Analysis,Vol.23.No.6,1963,pp.121—123.自此以后,通過修正傳統定義來回應反例成為認識論的一種重要討論范式。21 世紀初興起的實驗哲學對概念分析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但歸根到底,兩者都是圍繞“直覺”在哲學工作中的作用展開的。邁克爾·翰濃(Michael Hannon)在2019 年的專著《知識何為?》(What’s the Point of Knowledge?)中提出了一種“功能先行”(function-first)的認識論研究方法。bMichael Hannon,What’s the Point of Knowledge?:A Function-first Epistem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9,pp.12—15.根據這個方法,在考察具體哲學概念前,我們應該探討我們擁有這個概念的意義何在?他關心的是,人類從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到社會化的進程中,為何需要“知識/知道”這個語詞,它扮演了什么功能?
根據功能先行進路,我們首先要給出一個關于所討論概念的功能假說,即它在人類社會實踐中扮演的角色。其次,立足這個假說,我們給出一個合適的概念界定。再次,我們應該核實這個假說在多大程度能夠符合我們的一般用法。翰濃提出,“知識”概念的功能是“標識出可靠的信息提供者”。他強調,功能先行進路與概念分析可以融合。傳統概念分析試圖提供一個覆蓋所有案例的充分必要條件。如果采納功能先行進路,我們不必訴諸可普遍化標準,而是評價這個定義多大程度能夠滿足功能假說。仿效翰濃,本文提出兩個關于“(理論)智慧”的功能假說:
H1:標識出卓越的范例。
H2:標識出有益的問詢對象。
這兩個假說可以找到文本上的支持。第一個假說主張一個共同體需要卓越的標準。這個標準不是專家層面的,而是代表了人類卓越成就的最高峰,我們需要一個語詞來標識這樣的人。我們往往把這類足以垂范的人稱為有智慧的人。琳達·扎格澤博斯基(Linda Zagzebski)對此有過論述。aLinda Zagzebski,Exemplarist Moral The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60—98.第二個假說主張我們借助“智慧”來標識有益的問詢對象。丹尼斯·維特康姆(Dennis Whitcomb)就提到,一個好的智慧理論要能解釋智慧者為何是一個好的建議給予者,或為何大家會傾向于向智慧者執經叩問。維特康姆提到,流行文化經常會塑造一些有智慧的圣賢者,為了洞悉真知,求道者會絡繹不絕地前去探訪。并且,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會主動向有智慧的人探詢建議。bDennis Whitcomb,“Wisdom” in S.Bernecker and D.Prichard(eds.),Routledge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102.本文不排斥概念分析方法,而是主張概念分析的結果應該符合概念的功能假說。
此外,哲學是智慧之學,追求智慧的目的也應與哲學的目的是一氣貫通的。金岳霖主張哲學以“求通”為目的:
哲學底目標可以說是通,我們不盼望學哲學的人發現歷史上的事實,也不盼望他們發現科學上的道理。他們雖然不愿意說些違背歷史或科學的話,然而他們底宗旨并不是在這兩方面增加我們底知識。當然學哲學的人也許同時是學歷史的人,他在歷史底立場上,也許求發現歷史上的事實;也許是學科學的人,在所習科學底立場上,也許求發現科學上的道理;然而在哲學底立場上他仍只是求通。c金岳霖:《知識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版,第6 頁。
本文所主張的“理論智慧”不僅滿足上文的兩個功能假說,而且也與金岳霖提出的哲學“求通”目標相契合。
二、智慧的一二之辯
在當代哲學關于智慧的討論中,對實踐智慧的關注占據了主導地位,可謂一時隆盛。實踐智慧和大多實踐導向的論題休戚相關。甚至,有學者主張,事實上只有一種智慧,即實踐智慧,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不在少數。比如,羅伯特·諾奇克(Robert Nozick)就主張:“智慧是實踐的;它應該是能幫助到我們的。智慧是理解良好生活的基礎,擁有智慧才能去處理重要的問題,擁有智慧才能避免陷入危險的困局。”aRobert Nozick,“What is Wisdom and Why Do Philosophers Love It So” in The Examined life,New York:Touchstone Press,1989,p.267.理查德·加略特(Richard Garrett)也提出類似想法,他指出智慧必然與“生活得好”(living well)有必然關系。bRichard Garrett,“Three Definitions of Wisdom”in Knowledge,Teaching and Wisdo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6,pp.221—232.再有斯蒂芬·格里姆(Stephen Grimm)也這么認為:“并不存在理論智慧這樣一種獨立的智慧種類,不存在一種可以脫離如何良好生活的智慧。”cStephen Grimm,“Wisdom”,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3.No.1,2015,p.140.我們將這類觀點稱作“單一智慧觀”,而將那些主張具有兩類智慧的觀點稱為“雙重智慧觀”。
諸多學者將莎倫·雷恩(Sharon Ryan)視為“單一智慧觀”的代表。但這種解讀有失公允。雷恩早期的觀點可以被粗略解讀為“單一智慧觀”。dSharon Ryan,“Wisdom”in Knowledge,Teaching and Wisdo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96,pp.233—242.但我們發現,雷恩后來的論述已經在試圖覆蓋理論智慧了。eSharon Ryan,“Wisdom,Knowledge and Rationality”,Acta Analytica,Vol.27.No.2,2012,pp.99—112.早期雷恩主要試圖揭示“智慧”和“生活得好”或“贊賞良好生活”之間的必然關系。維特康姆則認為“生活得好”或“贊賞良好生活”不構成“智慧”的必要條件。他構想了兩個反例:邪惡圣人與抑郁圣人。我們可以假想一個受人敬仰的有智慧的人,突然有一天罹患了抑郁癥,他不再能夠生活得好。維特康姆認為,即便如此,我們直覺上還會覺得抑郁圣人仍舊是個有智慧的人,還是會愿意向他探詢建議。我們還可以假想一個全知全能的諸如梅菲斯特這樣的魔鬼,他一方面是全知全能的,他知道所有一切關于如何良好生活的知識,但他卻仍舊選擇邪惡的生活方式。維特康姆認為,即便如此,我們無法否認一個全知全能的人是智慧的。
維特康姆的用意在于表明所有的智慧都不需要“生活得好”或“贊賞良好生活”這個必要條件。這個直覺要求是詭異的。一方面,我們很難認為一個自己都無法生活得好的人具備“實踐智慧”,這是有違我們樸素直覺的。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會在某個層面感到抑郁圣人或邪惡圣人還是有智慧的。事實上,我們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直覺沖突,恰恰是因為我們的智慧是有不同種類的。當我們覺得抑郁圣人或邪惡圣人不再具備智慧,此處的智慧指涉“實踐智慧”;而當我們覺得抑郁圣人或邪惡圣人仍具備智慧,此處的智慧指涉“理論智慧”。因此,筆者認為維特康姆的兩個案例并不能完全服務于他本身的目的——論證智慧可以完全脫離“生活得好”。但卻可以服務于本文的目的:我們直覺的不穩定反映了“智慧”不是單一的,而至少是雙重的。為了化解直覺張力,更好的提問方式是:抑郁圣人或邪惡圣人是否具有理論/實踐智慧?
為了拒斥“單一智慧觀”,維特康姆讓我們設想如下情況:假設張三和李四具有同樣程度的實踐知識。但是,張三比李四具備更多的非實踐知識——比如形而上學和認識論知識。此時,我們是否會認為張三比李四更有智慧?維特康姆認為答案是肯定的。筆者也認同他的直覺。如果這個直覺成立,那么我們可以說至少存在兩種智慧。也許會有人反駁:所有的理論智慧終究服務于實踐智慧,那么如果張三和李四擁有了同等的實踐智慧,誰擁有額外的非實踐知識就不那么相關了。aShane Ryan,“Wisdom:Understanding and the Good Life”,Acta Analytica,Vol.31.No.3,2016,pp.235—251.這種觀點的問題在于預設了理論智慧只有工具價值,而無內在價值。這個預設本身就極富爭議。因此,這類反駁的立足點就是存疑的。
格里姆也反對“雙重智慧觀”:“我反對古典傳統的兩種智慧觀,即實踐智慧和理論智慧二分,我不認為我們可以對它們分別給出自持的界定。”bStephen Grimm,“Wisdom”,p.139.他的具體理由是,如果承認理論智慧的獨立性,必然會導向一種對智慧的“種屬觀”(genus-species view),而這會帶來消極后果。格里姆認為,理論智慧是關于數學、物理、邏輯等學科的認知性知識。立足于此,我們似乎可以說,如果張三在數學、物理、邏輯等方面有著非凡建樹,那么他便擁有理論智慧。對此,格里姆提出三層詰難。首先,我們一般認為的智慧范例往往是諸如甘地、孔子這樣具有實踐智慧,而非理論智慧的人。其次,我們直覺上不會將擁有數學、邏輯、物理知識和擁有智慧畫等號。這個回應方式也適用于第二層詰難。復次,如果接受“種屬觀”,我們就無法區分一般的智慧和領域的智慧。筆者認為格里姆的論證依舊無法取消二重智慧觀。首先,眾人眼中智慧的范例是否僅限于具有實踐智慧的人,這是一個經驗問題,我們可以通過實驗哲學的方法來處理。至少亞里士多德認為,泰勒斯、阿那克薩戈拉是具有(理論)智慧的典范人物。其次,承認理論智慧并不必然導向“種屬觀”,我們完全可以在概念層面區分一般的理論智慧和特殊領域的理論智慧。
格里姆也意識到自己的態度可能太過激進。他提到,我們是否應該允許一種在最基本層面的關于物理或形而上學的理論智慧?但是,他認為即便存在這樣一種智慧,它也應該服務于實踐智慧,從而服務于良好生活。諾奇克也有類似看法:“如果根本性真理與指引生活不相關,或不與任何生活意義維度相關,那么智慧就不僅僅是知道根本性真理。”aRobert Nozick,“What is Wisdom and Why Do Philosophers Love It So”,in The Examined Life,New York:Touchstone Press,1989,p.269.但這種說辭仍舊非常可疑。它預設了理論智慧只有工具性價值,而無內在價值,卻未加論證。
此外,理論智慧與實踐智慧之間的價值關系是一個問題,理論智慧在概念上可否獨立于實踐智慧是另一個問題。即便格里姆的理論智慧工具價值論成立,也不必然推出我們無法在概念層面獨立刻畫理論智慧。我們真正的難題在于能否在概念層面對理論智慧給出獨立的刻畫。杰森·柏爾(Jason Baehr)認為我們無法做到。他考察諸多種可能的區分方式:關于實在的必然特征與偶然性事務;先天事務與后天知識;瞄準真理的推論與瞄準善的推論;正確的信念與正確的行動,等等。但他認為上述區分方式都無法成功。bJason Baehr,“Two types of wisdom”,Acta Analytica,Vol.27.No.2,2012,pp.81—97.本文并不打算為上述某個區分辯護,而是試圖提出一種對理論智慧的新理解方式。在此之前,本文先考察幾種主要刻畫進路:亞里士多德進路、命題性知識進路、能力之知進路。
三、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智慧觀
當代認識論對智慧的討論的范式主要來自亞里士多德。據郁振華分析,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我們可以發展出三種智慧類型:理論智慧、實踐智慧、制作智慧。c郁振華的《論三種智慧》一文對此做出了系統闡述。本文僅聚焦亞里士多德對理論智慧(sophia)的論述。
亞里士多德將“理論智慧”界定為“知識”(episteme)與“努斯”(nous)的結合。在亞里士多德的語境中,知識是必然、永恒的:“這是絕對意義上的必然的事物;永恒的事物也是非生產的、不朽的。”d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W.D.Ross(trans.),in R.Mckeon(ed.),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London and New York:Random House,1941,1139b20—24,p.1024.因此,知識是來自第一原則的推論。然而,亞里士多德認為,“智慧的人不僅僅知道如何通過第一原則來推論,還需要擁有關于第一原則的真理”eIbid.,1141a,p.1027.。那我們又當如何獲得第一原則,也即如何把握原因(aitia)?對此,亞里士多德主張我們要借助“努斯”——理性的直觀能力。
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理論智慧具有神圣的品格,因而其他理智德性的級別都低于理論智慧。他認為生活的終極目的是抽象的理論活動,也就是沉思活動,而沉思生活就是通過動用和發揮理論智慧實現的。亞里士多德如此描述沉思生活:
這種生活是人類生活的最高等級。如果有人能過上這樣的生活,那也不是他人性維度促成的,而是神性維度所成就的。這個充盈神性要素的活動要比遵照其他德性的活動更為高級,因為神性要素比其他要素的混合還來得更高級。aAristotle,Nicomachean Ethics,W.D.Ross(trans.),in R.Mckeon(ed.),The Basic Works of Aristotle,London and New York:Random House,1941,1177b27—1178a2,p.1105.
據此,實踐智慧低于理論智慧。道德德性的目的是社會的繁榮,而道德德性的統一就是實踐智慧。理智德性的目的是沉思生活,理智德性的統一形式就是理論智慧。沉思的目的指向宇宙的終極真理。因此,在邏輯上,具有神性的沉思活動可以獨立于道德實踐。他指出,泰勒斯和阿那克薩戈拉是理論智慧的典范,因為他們致力于“那些卓越的、令人傾羨的、困難的、神圣的、卻又無用的事物”bIbid.,1141b,p.1028.。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論述,將政治藝術或實踐智慧作為最好的知識是很奇怪的,畢竟人不是最完美的存在。因此,實踐智慧只對理論智慧具有工具價值。亞里士多德做了如下類比:實踐智慧對于理論智慧,就如同醫生的醫術對于健康的作用。前者無法決定或掌控后者,因為前者只對后者具有工具價值。
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智慧”對后世影響深遠。但我們能否對之全盤接受?本文持否定態度,有三點理由。
首先,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智慧預設了過多的論證負擔。他的理論智慧對象由終極實在和科學知識構成。亞里士多德對終極實在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必然原則、終極因、第一原則、始因,等等。在當代,多數學者都不再執著地認為理論智慧的對象是具有必然屬性的終極因。比如,雷恩就認為:“亞里士多德認為科學知識是必然真理以及必然真理的邏輯后承,然而這已然不再是一個被廣為接受的觀點。”cSharon Ryan,“Wisdom”,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Spring 2020 Edition),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pr2020/entries/wisdom/,first published in 2007,substantive version in 2013,p.5.但雷恩沒有道出亞里士多德界定困境的關隘。事實上,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智慧”是立足在兩個世界形而上學基礎上的。兩個世界形而上學認為有一個遠在彼端的理念世界,它是關于終極實在的世界,另一個是我們的日常世界。或者用哈貝馬斯的話來說,這預設了本質和表象的區分。這個預設會形成過多的形而上學負擔。尤其在后形而上學時代,這種區分被廣為拒斥。a更詳細討論可參見郁振華:《論理論智慧》,載《學術月刊》2020 年第10 期。
其次,亞里士多德的努斯概念很難在科學語境得到定位。亞里士多德對理論智慧的界定訴諸一種特殊能力:努斯。在后形而上學語境或科學時代的語境中,我們似乎很難在自然界鎖定這種認知官能。維特康姆指出:“對亞里士多德而言,所有具有理論智慧的人都能夠理性直觀到第一原則。但這看起來是錯的。一個擁有深層物理經驗知識的人可以被認為具有理論智慧。但是這種知識的獲得不需要理性直觀。”bDennis Whitcomb,“Wisdom” in S.Bernecker and D.Prichard(eds.),Routledge Companion to Epistemolog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100.
再次,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理論智慧只有內在價值,而無工具價值。理論智慧是最高的理智成就,其他理智德性可以服務于它,反之則不成立。換言之,實踐智慧等理智德性可以貢獻于沉思生活,顛倒過來是不可能的。這個論斷也不符合后形而上學時代對理論智慧的理解。我們一般還是會認為,理論智慧是可以服務于其他理智德性的。
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智慧有幾個重要洞見:首先,他同時顧及了“一般的理論智慧”和“領域的理論智慧”c參見郁振華:《論理論智慧》,載《學術月刊》2020 年第10 期。,即他區分了廣義和狹義的理論智慧。廣義理論智慧包括:數學、物理學、第一哲學或神學,而狹義理論智慧僅指涉第一哲學或神學。亞里士多德的這個區分是值得我們借鑒的。這個區分也能很好地回應格里姆認為“理論智慧”必然導向“種屬觀”的詰難。其次,不同于諸多當代學者將理論智慧的價值僅僅貶為工具價值,亞里士多德凸顯了理論智慧的內在價值維度。即便具有這些洞見,鑒于本節所論述的理由,我們仍舊無法在后形而上學時代全盤接受亞里士多德的理論智慧觀。
四、基于命題性知識的理論智慧觀
不少當代認識論學者都嘗試在一種后形而上學的意義上界定理論智慧。他們對理論智慧的界定有一個共同點——訴諸命題性知識。換言之,他們認為理論智慧的核心是可以被表達的命題性知識。雷恩是典型代表。她在不同階段有過不同的界定方式,我們分別來考察一下。
雷恩(1999)提出了一種領域導向的理論智慧:
TW1:S 具有針對x 的(理論)智慧,當且僅當他知道很多關于x 的內容。aSharon Ryan,“What is Wisdom?”,Philosophical Studies,Vol.93,No.2,1999,p.120.
雷恩的這個早期界定尚顯粗略。首先,她只關注了領域導向的理論智慧,而忽略了作為一般形式的理論智慧。一方面,雷恩將領域性理論智慧納入理論智慧的范疇是可取的,這是符合我們一般直覺的。另一方面,雷恩自己又有所動搖,她認為簡單地將理論智慧等同于專家知識有欠妥當。她指出,“智慧更多是一種博學多才的體現,而非僅僅對于專門知識的精通”。bIbid.,p.121.可見,TW1面臨著一多之辯的問題。其次,TW1也無法回應理論智慧不應是零星瑣碎(trivial)的。而根據TW1,如果張三對1號倉庫所有細節了如指掌,我們可以稱張三是有理論智慧的人。但這是很荒謬的。鑒于此,她提出了一個改良的版本:
TW2:S 具有(理論)智慧,當且僅當他擁有廣博的具有內在價值的知識。cIbid.,p.122.
根據這個界定,一個擁有理論智慧的人,擁有的知識不僅是數量可觀的,也不能是瑣碎的,而應具有極高的內在價值。至少,這個定義能避免將那些擁有大量瑣碎知識的人奉為智慧者。但這個界定仍舊是偏頗的,它忽視了理論智慧的工具價值維度。
雷恩(2012)也意識到之前界定的紕漏,給出一個新的刻畫:
TW3:S 具有(理論)智慧,當且僅當他擁有廣博的事實知識和理論知識(學術知識)。dSharon Ryan,“Wisdom,Knowledge and Rationality”,p.104.
TW3和TW2不同。TW2強調了理論智慧的內在價值,卻忽視了其工具價值。而在TW3中,事實知識加上理論知識,可以同時覆蓋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在后形而上學語境中,我們應該承認理論智慧具有工具價值。并且,這個界定可以覆蓋一般理論智慧和領域性理論智慧。因此,TW3是對TW2的改良和推進。
我們發現,從TW1到TW3,雷恩一直在嘗試修正對理論智慧的刻畫。從最初的領域性知識,到關注內在價值的知識,再到同時覆蓋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的知識。但是,這種推進似乎仍舊是停留于同一個層次的精雕細琢。雷恩始終將理論智慧理解為對命題性知識的擁有:從“領域性命題”到“具有內在價值的命題”再到“事實命題和學術命題”。
立足命題性知識解釋理論智慧到底有何問題?首先是來自無窮倒退論證的挑戰。我們假設張三被灌輸了大量的關于哲學的命題層面的知識、理論、策略、先驗真理。并且,張三過目不忘,記住了所有這些命題內容。這是否構成他成為哲學家的充分條件?顯然不行。賴爾將這個問題具體表現為無窮倒退論證。即對某個命題的理解可以是聰慧地,也可以是愚笨地。如果要聰慧地理解,根據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教條,我們還要再訴諸進一步的命題,對這個進一步命題的理解又要面臨同樣問題,那么就會形成無窮倒退。賴爾認為:“我們需要智力,不僅為了發現真理,更在于運用它們……對律令的運用等行為不是對它們的沉思。”aGilbert Ryl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The Presidential Addres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Vol.46.Aristotelian Society,Wiley,1945,p.6.如此,對命題的理解實際是一種能力的發揮。
除了無窮倒退論證,立足命題性知識的智慧還會面臨傳遞性難題。命題性知識是可以通過證言傳遞的。比如,張三知道“李四有一輛奔馳轎車”,那么王五可以通過張三的證言獲得同樣的命題“李四有一輛奔馳轎車”。假設命題性假說成立,理論智慧是命題性的,那么理論智慧也應該可以通過證言傳遞。我們假設張三是一個具有理論智慧的人,那么王五通過和張三的交流,也應該獲得理論智慧。但我們發現,即便王五和張三進行了深度交流,也不能保證張三的智慧可以毫無保留地傳遞給王五。因此,這也構成了對命題導向智慧觀的挑戰。
五、基于能力之知的理論智慧觀
通過上文考察,我們發現立足命題性知識的理論智慧是站不住腳的。有不少對理論智慧的界定已經跳出了這個范式,本節我們考察一些以“能力之知”為基礎的理論智慧框架。
柏爾認為可以通過三種觀念來理解理論智慧bJason Baehr,“SOPHIA:Theoretical Wisdom and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in K.Timpe &C.Boyd(eds.),Virtues and Their Vic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303—325.:(1)認知狀態(epistemic state);(2)認知能力(cognitive faculty/ability);(3)理智品質(intellectual trait)。認知狀態強調的是對理論智慧的把握,即達到一種對事物深刻認知或理解的狀態;認知能力指理論智慧實際是一種能力的展現;理智品質試圖表明理論智慧應該體現一種對深度理解狀態追求的動力。顯然,至少從第二點來看,柏爾采納的是反理智主義的理論智慧觀——拒斥將智慧還原為命題。在目前的討論范式中,有兩種進路具有以立足能力之知來界定理論智慧的潛質。
第一種范式肯認了理論智慧的非簡單命題化,但只強調它的工具價值。S.D.沃什(S.D.Walsh)的觀點可以被視為這種范式的代表。沃什認為,從儒家傳統里,我們也可以發展出理論智慧概念。aS.D.Walsh,“Contemplation and the Moral Life in Confucius and Aristotle”,Dao,Vol.14.No.1,2015,pp.13—31.他借助“實踐智慧”和“理論智慧”的區分,發展了“儒家實踐智慧”(Confucian phronesis)和“儒家理論智慧”(Confucian sophia)。沃什將“知天命”解讀為儒家對理論智慧的追求。沃什指出,知天命立足在“學”和“思”的基礎之上。《論語》(17.8)論述了“學”的重要性:“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直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b楊伯峻:《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版,第184 頁。在《論語》(2.15)中,孔子強調了“思”的必要性:“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c同上書,第18 頁。根據沃什的解讀,要達到知天命的狀態,需要一個艱苦卓絕的長期修行過程。顯然知天命不可能僅僅是對命題的持有,而應該是一種深度的理解能力。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種非命題導向的理論智慧觀。沃什借用孔子的“玉喻”(9.13)來進一步解釋。d同上書,第91 頁。孔子提問,如果有一塊美玉,我們是應該束之高閣,還是賣給商賈呢?孔子的答案是應該賣掉。沃什認為,孔子實際上是在用玉類比自己多年的德性積累。對于亞里士多德而言,沉思生活是自足和無用的。而孔子則愿意賣玉,這意味著他試圖將理論智慧貢獻于實踐生活。沃什認為,對儒家而言,我們需要沉思智慧來完滿地實現道德德性。這與亞里士多德的思路正相反。他指出,對孔子而言,對待這種實踐導向的儒家理論活動(theoria)的最佳方式是通過發揮道德德性,將它置入人類共同體的實踐中。與亞里士多德不同,儒家的理論智慧不是最高的理智德性,而是服務于我們道德實踐的。我們首先必須承認,在后形而上學時代,理論智慧應該可以具有工具價值。但這一進路的缺陷在于抹殺了理論智慧的內在價值維度,也沒有顧及領域性理論智慧。
第二種立足能力之知的可能范式有如下特征:它一方面覆蓋了理論智慧的內在價值,關注智慧的一般形式,另一方面卻忽視理論智慧的工具價值,也未對領域性理論智慧給予足夠的重視。金岳霖和懷特海(A.N.Whitehead)可被視為代表。我們可以將金岳霖的“求通”說解讀為他的理論智慧觀。a參見郁振華:《具體的形而上學:金—馮學脈的新開展》,載《哲學動態》2013 年第5 期。這又可以分為知識的“求通”和形而上的“求通”。金岳霖強調,知識的求通關注的不是具體學科中的理論的真假,因此,“它底目標不是真而是通”。b金岳霖:《知識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版,第13 頁。具體而言,就是道理或邏輯層面的“一致”,而非“真假”。此外,還有形上層面的“求通”。金岳霖認為,關于“有無在任何事物之前的事物或在任何事物之后的事物”c同上書,第545 頁。的問題,就是求通的問題。他強調這類問題是要窮,才能通。郁振華如此綜括金岳霖的形上求通說:“求窮通的興趣把我們從分別彼此的知識經驗的領域引向形上本體,去把握宇宙的總體或大全,即那超形脫相無彼無我的世界。”d郁振華:《具體的形而上學:金—馮學脈的新開展》,載《哲學動態》2013 年第5 期,第43 頁。懷特海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智慧是一種過程性能力之知,而非陳述性或事實性知識。智慧體現于對原則性命題的良好理解。他這樣表述命題性知識和智慧的區分:“知識減損之時,恰是智慧增益之時:細節為原則所收攝。”eA.N.Whitehead,The Aims of Education.,New York:Free Press,1967,p.37.在懷特海看來,理論智慧就是對這種統攝性原則的理解和把握。雖然金岳霖和懷特海沒有明述出來,但他們刻畫的理論智慧,無論是窮通還是把握形而上原則,都不僅僅是命題性知識,而是一種能力之知,并且這種智慧是有自持的內在價值的。但是,他們都聚焦作為一般形式的理論智慧,而沒有覆蓋領域性理論智慧,也未論及理論智慧的工具價值維度。
六、基于概念能力之知的理論智慧
上文中,我們考察了兩種立足能力之知的理論智慧觀。一方面它們跳出了命題性知識觀的窠臼,另一方面,它們都存在著各自的問題。本文試圖給出一個全新的界定。這個界定滿足三個理論訴求:(1)不陷入理智主義窠臼。(2)避免現有基于能力之知的進路之局限。(3)滿足關于智慧功能的兩個假說。
如果我們能夠意識到理論智慧是一種能力之知,而非對命題性知識的持有,那么我們已經走在了正確的方向上。但是本文主張,為了在概念層面和實踐智慧區分開來,理論智慧體現出的是一種概念能力之知(conceptual knowing-how)。下文試圖具體對“概念能力之知”給出一個刻畫。
賴爾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到概念能力之知,但我們會發現在他那里,這個概念只是隱而未發。賴爾論述過:“知道一個規則實際是能力之知。”aGilbert Ryle,“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The Presidential Address”,p.7.這個說法意味著對命題的把握是一種能力。假設張三知道規則“行星是天體”和規則“火星是行星”,卻不知道“火星是一個天體”。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能說張三真正掌握了知識,因為他并不真正理解“行星”。在本文看來,張三缺乏一種概念能力之知。
約翰·班森和M.A.墨菲特(John Bengson &M.A.Moffett,下文簡寫為“B&M”)對“概念能力之知”做過一個界定。我們首先來考察他們的界定。B&M 認為“理解力”和“能力之知”的歸賦(attribution)有著必然關系——理解力是一種概念掌握能力。他們主張,對于x 的能力之知需要理解x-ing,而這又需要我們合理地掌握一套概念。張三知道如何做加法,那么他必然掌握概念“加”,并以此來解決數學題。此處,所涉及的概念(“加”)是“能力基底概念”(ability-based concept):“一個概念C 是一個能力基底概念,當且僅當對這個概念的合理掌握蘊含了擁有以簡明方式來正確運用概念C 的能力。”bJ.Bengson &M.A.Moffett,“Know-how and Concept Possession”,Philosophical Studies,Vol.136,No.1,2007,p.44.B&M 將這個模式拓展到所有實踐中的能力之知。換言之,他們認為任何體現能力之知的活動都要預設擁有一定的理解力(概念能力之知)——無論是關于數學的能力之知,還是關于花樣滑雪的能力之知。
綜上,B&M 認為所有的一般“能力之知”都蘊含“概念能力之知”。一方面本文肯定B&M 對概念能力之知獨特性的揭示,另一方面本文卻不認同所有的能力之知都預設概念能力之知。概念能力之知具有程度的差異。數學和邏輯的能力之知是強的概念能力之知,而舉重或游泳時是否運用到概念能力之知則是存疑的。我們當然可以說,掌握扣籃能力往往需要理解“籃球”“籃筐”“籃網”這些概念,這些概念對于扣籃能力而言似乎又是極其邊緣的,微末瑣碎的,充其量只是背景性知識。鑒于此,我們會發現很多能力之知中,概念能力之知的作用幾乎是可忽略的。比如:舉重、游泳、人臉識別,等等。但在另一些能力之知中,概念能力之知幾乎就是全部,比如邏輯和數學運算能力。也許有人會反駁,確實有不少能力之知蘊含概念能力之知。比如,一個人如果具有政治實踐的能力之知,那么我們預設他對相關政治概念應該有深刻的理解;一個具有下象棋能力之知的人,也應該具有相關的概念能力之知。鑒于這些情況,根據概念能力所扮演的作用程度,我們可以形成一個光譜:
強概念能力之知→蘊含概念能力之知的一般能力知→強一般能力之知
強概念能力之知位于光譜的最左端,這意味著它主要訴諸心智和語言活動,原則上不用訴諸身體活動。光譜中間段的是一種概念能力之知和一般能力之知混雜的綜合性能力之知,在這種混合能力中,概念能力是必要而不充分的。光譜最右端是原則上不用訴諸概念能力的一般能力之知。B&M 忽視了光譜的最右端。即便如此,僅就混合能力(蘊含概念能力的一般能力)這一界定,我們就足夠用來支撐概念能力之知的獨立性,我們可以設想張三具有概念x 的概念能力之知,卻發揮不出關于x 的能力之知。換言之,在概念上,我們可以區分概念能力之知和非概念能力之知。而本文主張,我們可以借助“概念能力之知”來界定“理論智慧”。
本文試圖推進B&M 的工作,對概念能力之知給出更進一步的刻畫,而非僅僅通過理解力來界定。在這個方面可將羅伯特·布蘭頓(Robert Brandom)的概念理論引為同道。布蘭頓將“概念能力之知”視為智識者(sapients)的獨有品質。一只鸚鵡能夠對黑色物體做出反應“這是黑色!”;溫度計的指針可以準確指示溫度;鐵在潮濕環境下會生銹。但這不意味著鸚鵡懂得如何運用概念“黑”,溫度計理解概念“冷暖”,鐵理解概念“濕度”。對概念的掌握能力應該放置在概念的推論關系網絡中考察。理解“黑”意味著能夠從“這是烏紗帽”推論“這是黑色的物體”再推論“這是有色彩的物體”。在這個意義上,對于概念x 的能力之知的關鍵在于能夠使用x 進行推論——在什么條件下可以運用這個概念以及運用這個概念能得出哪些后果。布蘭頓如此表述:“掌握或理解一個概念就是掌握它所卷入的推論——在實踐的意義上去區分(一種能力之知)概念的應用所跟隨的結果,以及運用這個概念又是由什么其他條件得到的結果”aRobert Brandom,Articulating Reasons:An Introduction to Inferentialis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48.。布蘭頓對概念能力之知的界定又是進一步坐落在社會實踐框架內的。社會實踐在他看來是一種要求和給出理由的實踐。概念所卷入的推論都可以作為我們社會實踐中的“理由”。因此,概念理解和我們的說理活動是密不可分的。
回到本文關心的問題:僅僅掌握基本的概念所卷入的推論就能構成理論智慧了嗎?這個門檻顯然太低。對概念能力的掌握是有程度差異的。就“基因”而言,普通人和生物學家所掌握的廣度和深度是不同的。比如一個普通人可能可以通過“基因”推出“基因和遺傳相關”,而生物學家則可以在復雜的科學推論關系中順暢地運用它。這也適用于諸如“引力波”“磁場”“行星”“黑洞”等專門科學概念。文本試圖在理論智慧的框架內給領域性理論智慧留出余地。那么,對這些專門概念的牢靠掌握實際就是對特定領域的理論智慧的把握。人類的概念網絡是紛繁復雜的,有些概念在我們的說理推論網絡中占據核心位置,還有一些處于邊緣位置。那么掌握理論智慧就是掌握那些核心概念的推論能力。
我們如何處理對于一般理論智慧的界定?在概念網絡的核心收攝處,有著輻射性的基礎概念(形而上學概念):“形而上學”“知識”“第一原則”“真理”“經驗”“規律”“存在”“因果”“自由意志”,等等。對這些具有普遍性特質概念的掌握構成了一般理論智慧。至此,我們似乎已經可以通過概念的推論能力之知來界定理論智慧了。并且,這也能符合本文主張的關于理論智慧的第一個功能假說:標識出卓越的范例。前文主張(理論)智慧有兩個主要功能,另一個功能是:標識出有益的問詢對象。到目前為止,我們仍舊可能面臨反駁:一個自己具有很強概念推論能力者,未必能夠清晰地將自己的能力解釋出來。一個好的花樣滑冰運動員未必是好的教練,而一個好的教練未必是好的花樣滑冰運動員。也即,一個自身理論水平高超的人,未必能成為一個好的指導老師。反之,一個好的指導老師,也未必需要登峰造極的理論水平。那么,我們的“概念能力之知”能否回應這個問題?
實際上,布蘭頓對概念能力的界定不限于此。在布蘭頓的框架里,能夠自如運用概念的人是理性人,但更高一層次的應該是邏輯人。我們運用概念的時候,概念的推論原則是隱含在我們的概念運用活動中的。布蘭頓認為,借助特定的廣義邏輯語匯,這些隱含內容都可以得到明晰表達——以命題的形式呈現。這種概念表達能力就是第二層的概念能力之知。布蘭頓界定的廣義邏輯語匯包括:“條件句”“規范語匯”“表征語匯”“承諾”“資格”,等等。通過這些邏輯表達式,我們能夠將具體的推論擺到臺面上。這是一種對概念的明述能力。一旦我們能夠明述概念的推論規則,那么我們就可以明確地將之作為理由來表達,在這個意義上,邏輯人是具有自我知識的。他對自己為何如此使用概念是自知的,并且他可以將自己的使用規則表達為命題。鑒于此,邏輯人也理所當然可以向他人講明自己的推論規則——他能成為一個有益的建議提供者。要注意的是,建議給出者和信息提供者是不同的,前者針對的是“智慧”的功能,而后者針對的是“知識”的功能。當我們有理論困惑時,我們會尋求有益的理論建議者;當我們信息不足時,我們會尋找可靠的信息提供者。
另外,雷恩指出,智慧不需要強的知識條件。換言之,我們應該允許智慧者由于受時空語境限定,持有非必然為真的命題。我們目前的概念能力之知可否覆蓋這個面相?在布蘭頓看來,表達事業和批判事業是連續的。當我們發揮概念表達能力,將藏伏于概念使用中的推論內容用命題表達出來后,這些命題都是可以接受批評的。在布蘭頓的推論語義學框架內,概念的內容(意義)不是一個充分必要條件構成的定義,而是概念的推論規則。如果概念的內容(意義)是由充分必要條件構成的話,那就會涉及是否為真的問題。比如,對于概念分析而言,它的目標是找到一個顛撲不破的分析性真理。然而,一旦采納推論語義觀,是否為真的問題就被取消了。對于布蘭頓而言,推論規則是可錯的,因此也是可更正的。比如,“Boche”背后的推論規則是“如果張三是德國人,那么張三是Boche”,“如果張三是Boche,那么張三是殘暴的”。這個概念的使用規則蘊含歧視態度,因此我們可以直接拒斥這些規則——也即拒斥使用這個概念。
綜合上述考慮,文本給出一個最終的理論智慧定義:
核心理論智慧:
S 具有理論智慧,當且僅當他對形而上學概念具有充分的概念能力之知。
領域理論智慧:
S具有理論智慧,當且僅當他對特定領域的概念具有充分的概念能力之知。
通過“核心理論智慧”和“理論理智智慧”的區分,我們可以解釋為何理論智慧同時具備內在價值和工具價值。對于這個界定而言,其中關鍵的是對概念能力之知的具體刻畫。B&M 將之等同于理解力,但這個刻畫過于泛泛。本文試圖立足布蘭頓和當代概念工程(Conceptual Engineering)方法論的框架,從三個層次來刻畫這種概念能力:
概念能力之知:
S 具有關于x(核心或領域理論智慧)的概念能力之知當且僅當(1)他能運用x 進行推論;(2)他能將這些概念推論實踐背后所隱藏的推論規則表達出來;(3)他能夠修正和改良這些概念所涉及的推論規則。
概言之,概念能力之知包括:(1)概念運用能力;(2)概念表達能力;(3)概念修正能力。一個具有理論智慧的生物學家,他對“病毒”“變異”“傳染”等概念運用自如,他也應該能夠將蘊藏在這些概念使用背后的推論清晰表達出來,因此他能夠為他人解惑,進行教學,與同行交流。再者,他也應具備敏銳的糾察力,能夠及時洞察現有推論中的問題,并提出修正方案。概念運用能力和表達能力基本可以對應柏爾所說的理論智慧的能力維度。柏爾認為這些能力主要是理性能力(直觀理性、演繹理性、歸納理性、說明性理性),而本文則將之解讀為概念運用和表達能力。概念的修正和改良能力則可以覆蓋柏爾刻畫的理論智慧的理智品質。根據郁振華的解讀,這種理智品質實際是一種追求理論智慧狀態的動力。a郁振華:《論理論智慧》,載《學術月刊》2020 年第10 期。一方面,一個具有概念能力之知的人,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有限性,即對概念的掌握是可錯的,因此他擔負著去察覺和修正錯誤的概念實踐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概念能力之知亦能解釋理論智慧的動力維度。另一方面,一個具有概念能力之知的人,也是具有概念創發能力的——提出新概念就是創發性的體現。也許會有人進一步質疑,那么一個對“德性”“幸福”“應該”“義務”等概念具有充分概念能力之知的人,不應該是具有實踐智慧,而非理論智慧嗎?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一個倫理學教授,他有極高的學術造詣,對倫理學理論有創發性貢獻,但他同時在現實生活中又是一個行為不端的小人。那么一方面,他是具有理論智慧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不具有實踐智慧的,有可能是因為意志薄弱。因此,本文主張理論智慧應是價值中立的,它只應強調對概念本身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又不必然導向相關行動。
至此,本文給出了一個翔實的“理論智慧”刻畫方案。一個具有理論智慧的人也是一個具有廣泛和深入概念能力之知的人。值得一提的是,這個界定也能呼應金岳霖對于智慧“求通”的論述——我們對概念所卷入的推論的掌握必須是一致和融貫的,并且我們可以將這種推論關系一層一層窮盡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