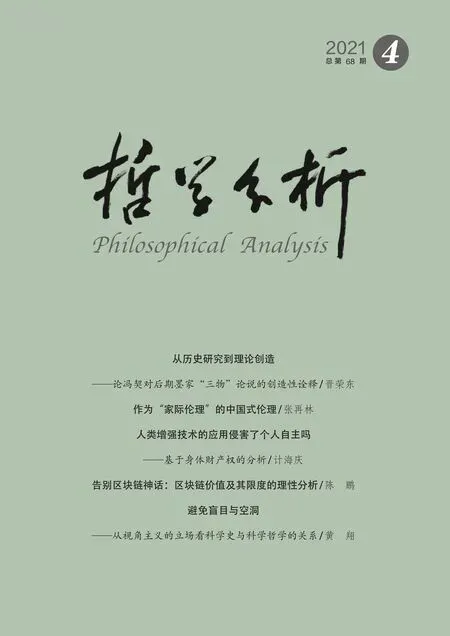羅蘭茨對延展認知的現象學闡釋及其局限
戴 潘
自從克拉克和查爾默斯的“延展認知”理論提出以來,學術界圍繞該理論的爭論汗牛充棟。羅蘭茨提出,這些爭論所圍繞的中心議題,從某個角度考察,可以歸結為“認知標志”問題。所謂“認知標志”,是指一個過程如果能被看作認知過程,或者必須具有大腦內部的生物學特征,或者必然擁有某種非派生性內容,只有大腦內部的狀態才能被看作認知,而大腦外部的環境要素則是非認知的。反對延展認知者認為,心智固然和外在環境之間存在著某種因果上的聯系,但是因果性并不必然推導出構成性,外在環境絕不可能成為心靈或者認知的一部分。如果我們認為認知的邊界必定在于人的頭骨或者皮膚,或者認為認知的標志必定存在著原生的非派生性內容,那么無論延展認知的支持者提出什么樣的論證,都無法說服他的反對者。因此,構建一種能夠讓爭論雙方都能承認的“認知標志”就成了當前要務。羅蘭茨指出,認知標志的提出對于延展心靈至關重要,但它本身不能由延展心靈推導出來,而是同樣能夠兼容傳統的認知觀。其最終目的就是,認知不僅包含了必不可少的大腦神經要素,而且對身體和環境結構的操縱和利用不只是整個認知過程在因果上的貢獻者,它們和大腦神經要素共同被視為整個認知過程的真正構成部分。本文將詳細梳理羅蘭茨的論證思路,展示出他的理論如何走向了現象學心靈的道路,并自然推導出延展認知的結論。
一、“認知標志”理論
認知標志可具體表述為如下4 個條件:
過程P 是一種認知過程,當且僅當:
1.P 涉及信息處理——對承載信息的結構進行操作和轉換。
2.這種信息處理具有適當功能,使主體或后續處理操作可以獲得在此處理之前不可用的信息。
3.這些信息是通過在過程P 的主體中的表征狀態的產生而獲得的。
4.P 是屬于那個表征狀態的主體的一個過程。aMark Rowlands,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Cambridge:The MIT Press,2010,pp.110—111.
其中,條件1 是經典認知觀與延展認知都承認的標準教條。條件2 中的“適當功能”概念來源于米利肯(R.Millikan),是指某物的適當功能是它應該做什么,或者它被設計去做什么。這個概念提醒我們認知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應是規范性的,即它規定了研究認知應該重點關注應該做什么,而并非認知實際上做了什么。某種信息處理若通過這種適當功能,無論在主體層面,還是在大腦神經的后續處理操作層面,都可以獲得若非此信息處理則不能獲取的信息,那么這個信息處理過程就被看作認知的。此外,在條件2 中,羅蘭茨強調了他對“個人層面”和“亞人層面”的區分。有一些認知過程是向主體層面即個人層面提供信息,但也有一些認知過程是向后續操作層面即亞人層面提供信息。后者是讓信息進入某種無意識的處理操作,主體是無法獲得這些信息的。條件3 則針對激進或溫和的“反表征主義”。當代某些學者認為,認知科學并不需要表征概念,但在這一點上仍然存在爭議。羅蘭茨提出,在他的理論中盡量避免將這種極具爭議的觀點作為前提。他反復強調,其認知標志也能夠兼容經典認知觀的基本假設,所以他仍然承認表征的存在。此外,在對條件3 的描述中,羅蘭茨區分了所謂的派生性表征與非派生性表征,以及個人層面表征與亞人層面表征。前一個區分是為了回應批評者所提出的真正的認知必定包含了非派生性內容,這是批評者用來批評延展認知的關鍵論證之一。羅蘭茨認為,如果堅持延展認知,那么外部信念狀態中的內容,作為一種派生性內容,其合法性就需要得到承認。但是,為了容納經典認知觀,羅蘭茨指出在標志中所提出的表征狀態就是批評者們所堅持的非派生性狀態(擁有非派生性內容)。而且無論是個人層面還是亞人層面,都可以擁有非派生性內容。個人層面的表征由于它們和諸如意識這樣的概念相互交織,因此是否可以進行自然主義說明是有爭議的,但是在亞人層面,表征則滿足廣泛的自然主義標準。他所提出的認知標志,是嚴格來源于認知科學實踐的。
他因此得出結論:任何能夠滿足認知標志的前三個條件的過程,都可以被視為認知過程。外部信息結構的操縱,不僅僅是作為外在的因果耦合元素而伴隨著內在認知過程,也并非它們提供了一個內在過程被嵌入其中的環境。它們是認知過程,是因為它們滿足認知標志的前三個條件。我們應該以“過程”而非“狀態”來解釋延展認知,只有提供了某個滿足認知標志諸條件的“過程”,它才能被看作認知的充分條件;而一個“狀態”要被看作是認知的,只有通過它對認知“過程”的貢獻能夠在一個有機體中實例化才得以可能。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糾纏于顱外狀態是不是一種認知狀態的爭論。羅蘭茨認為,首先,正如反對者們所堅持的,的確不存在任何純粹的顱外認知過程,認知過程要么是顱內的,要么是跨內部和外部成分的混合過程;其次,任何對外部信息結構的操縱,除非與適當的內部(即神經)過程相結合,否則永遠不能算作是認知的,即外部過程依賴于內部過程,沒有內在,外在就不能算作是認知;最后,一旦彼此相互結合,外部過程在其認知的程度上與內部過程無差,或者說“認知”的標簽既適用于純粹內部過程,也適用于內部和外部過程的混合。針對批評者提出的外部內容僅僅是具有派生性內容的批評,羅蘭茨則提出,盡管外部過程單獨看來確實是派生性的,但是因為任何認知過程都包含了不可消除的內在構成,那么包括內部與外部的整個過程則明確的含有非派生性的構成部分。也就是說,一個過程在其孤立狀態下或者與其他過程相結合的狀態下,能夠產生出一種帶有非派生性的狀態,那么該過程就被看作是認知過程。
二、認知所有權問題
以上我們介紹了羅蘭茨所提出的認知標志的前三個條件,而重點則在條件4中,條件4 所涉及的是認知所有權問題,這又可細分為個人層面和亞人層面所有權問題,以及兩者之間的關系。通過對所有權的探討可以自然而然地導出認知標志所攜帶的現象學意義。
認知所有權涉及主體的問題,羅蘭茨提出,所謂“主體”就是任何能夠滿足前三個條件的過程的個體,不存在沒有主體的認知過程,認知過程總有一個所有者,條件4 就試圖提出這個所有權問題。對于延展認知的論證來說,問題并不在于我們如何去理解什么是認知主體,而是在于一個主體可以擁有(或者實例化)其認知過程的意義。為了理解這個問題,我們要從認知的個人層面與亞人層面來分別探討其所有權問題。所謂個人層面,即是指使擁有這些過程的主體獲得信息的那些過程,它們是個人層面的認知過程,并且與這些過程是否也將信息提供給底層的后續操作處理無關。而所謂亞人層面,則是指只向剛才所提到的底層的后續操作處理提供信息的那些過程。作出這樣的區分是相當必要的,譬如它可以回應關于延展認知的“認知膨脹”反駁。認知膨脹批評主張,如果認知延展到了身體外部,那么這種延展就不存在任何邊界,最終導致整個世界都可能成為認知狀態的組成部分。羅蘭茨則提出,首先,他的延展認知是以過程為導向的,而非以狀態為導向,而任何認知膨脹論證都指的是認知狀態的膨脹,所以這個反駁是無效的;其次,僅僅在亞人層面可以存在膨脹的問題,但是在個人層面,膨脹并不存在。例如,當我們使用望遠鏡去觀察天體時,認知過程的確延展到了在望遠鏡內發生的信息過程,但在望遠鏡內發生的過程并不是個人層面的認知過程,而是亞人層面的。在提出這樣的區分后,羅蘭茨分別就兩者的所有權關系問題作了闡述:“亞人認知過程的所有權被理解為某種因果整合。當亞人的認知過程適當地融入個人的整體認知生活中時,它們就屬于個人。并且,當主體是個人層面認知過程的所有者時,也意味著亞人過程對主體所經歷的個人層面認知過程作出了適當貢獻,這些亞人過程就被適當整合。”aMark Rowlands,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pp.139—140.
羅蘭茨以一個思想實驗來說明亞人與個人層面所有權的關系:假設存在某種體外消化過程,即一個人的消化系統功能受到了破壞,那么我們可以通過將病人的消化過程轉移到另一個人的消化器官中去實現,但這并不表明這個消化過程是屬于他人的,它仍然是屬于那個病人的。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亞人過程被適當整合”,這種適當整合是通過條件2 中的適當功能來描述的,即如果某人體外的消化過程發揮了相對于他的其他生物過程的適當功能時,體外過程就被適當整合到這個人的整體生物過程之中。所有權問題并不是一個能用物理空間界限的方式來談論的主題,一個認知過程存在于哪里,只和它影響到該過程所做的事情,或者它影響的到底是“誰”,或者它到底對哪個“個人”的適當功能發揮作用有關。
當然,羅蘭茨也指出,對于認知過程來說,亞人過程是認知的,僅僅涉及信息處理是不夠的,而是僅當它們屬于一種能夠探測環境變化并隨之改變其行為的有機體才能成立。或者說,這些亞人過程是認知的,僅當它們與許多其他同樣的亞人過程相結合,能夠使個人意識的表征層面發生某種轉換,并對主體的個人層面的認知生活作出貢獻,以至于亞人和個人層面形成一個相對連貫的整體。因此,思考所有權的方式并非從亞人層面出發上升到個人層面,相反,對于前者的解釋是對后者的解釋所派生的,個人層面的所有權在邏輯上是在先的,只有先理解個人所有權,才能正確理解亞人所有權。那么接下來,問題的核心就轉向了如何解釋個人層面的所有權問題。
而傳統認知觀對于個人所有權的解釋,往往預設了一個固定的、在所有權問題上不存在爭議的參考框架,并且這個框架是由身體的感知覺輸入和運動輸出所提供的,任何過程必須被整合進這個輸入和輸出的框架之中,才能被算作是認知的。但是,這個框架本身的所有權并非自明,相反,輸入和輸出必須被整合到認知過程中去,才能被主體所擁有。羅蘭茨認為,認知過程的所有權必須用一種構成性的方式來理解,即分解為以下三個方面:對有機體擁有認知過程的理解;對有機體對環境檢測之擁有的理解;以及有機體對隨后的行為反應輸出之擁有的理解。如果按照構成性方式來理解,在個人層面的認知過程就必須涉及對一般的行動問題的理解,因為在個人層面,認知過程就是我們所做的事情——它們是行動。我們擁有認知過程,就是擁有自己的行動,而這是通過我們做這些事情來實現的。羅蘭茨認為,傳統上對所有權的認定可以通過“認知權威(cognitive authority)”來描述,即我對于對象有著明確的理論上的認識論通達。但是羅蘭茨指出,單憑這種認知權威無法為我們提供個人層面的認知所有權標準,我們關于所有權的思想只能從更為基本的層面中找到,認知權威是由這個更基本的層面所派生的,并且僅在我們的活動出了問題時,認知權威的問題才會出現。
總而言之,個人層面的認知和認知權威之間的聯系是一種更為根本的所有權意義的派生物,這種更為基本的所有權是使得我們能夠思考個人層面所有權的條件。這個更為基本的層次就建立在更基本的應對世界的活動之上,認知活動和應對活動是連續的,是以不同方式實現的本質上相同的活動。而這種更為一般的活動,羅蘭茨提出,就是現象學意義上的揭示或揭蔽活動(revelation or disclosure activity)的形式,認知所有權的最終基礎,就是揭示的觀念。“與許多應對活動一樣,認知過程也是一種揭示或揭蔽活動。構成認知的揭示或揭蔽活動并不局限于大腦——它們結合了身體過程和我們在這個世界中以及對這個世界所做的事情。”aMark Rowlands,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p.162.
三、作為“揭示活動”的知覺經驗
什么是揭示活動?羅蘭茨就揭示活動與認知的關系提出如下觀點:
1.應對和認知都是揭示或揭蔽活動的形式。個人層面是向某個人的揭示;亞人層面是向某物的揭示。認知過程本質上被主體擁有是因為揭示活動本質上被主體擁有。
2.認知過程被延展是因為它們是揭示的活動。生物體所進行的揭示活動可以止于但通常不限于生物體的皮膚。
3.因此,所有的認知過程都是被擁有的,許多認知過程都是被擴展的。
4.認知是揭示活動,因為認知是有意向的,意向地指向世界,應被理解為揭示活動。bIbid.,p.163.
羅蘭茨首先以知覺經驗為例來分析“揭示活動”。知覺經驗存在著兩個不同的維度,一方面它們是對世界的一種揭示,但同時也是向擁有它們的主體來揭示世界。對于知覺意向性的最大的誤解,是將知覺經驗,以及經驗所具有的主觀性屬性等同于我們所意識到的對象。比如我們看到一個西紅柿,在我的體驗中就會出現某種關于閃亮的紅色的“感覺質”,即擁有或者經歷這種體驗是什么感覺(what-it-islike-ness),正因為將它們看作意識對象,從而引發了如何在自然主義立場上來解釋感覺質的所謂解釋鴻溝的“難問題”。
但是羅蘭茨指出,對經驗的這種理解并不完整,它遮蔽了意識的更深層結構,從現象學的觀點來看,任何經驗都還存在著并不是我們在擁有該經驗時所意識到的東西,那就是意向行為本身。在對體驗的意向性分析中,不僅存在經驗(empirical)維度,而且存在不可消除的先驗(transcendental)維度。如果我們將經驗項看作意識的對象,那么先驗項就是使得該經驗項能夠如此的條件。在意識經驗中應該同時具備主體側與客體側兩個本質構成要素。主體側的意識行為,使得體驗成為對象恰好作為主體體驗的對象而被揭示給主體的過程。羅蘭茨用手抓取物體來作比喻,從經驗維度來說,思想就是手上抓到的東西,它是外在于手的,但是從先驗維度來說,就是肌肉、骨骼與手的關系,這種關系就是使得手能夠抓取東西的條件。
羅蘭茨從一種廣泛接受的關于意向性的結構模型(意向行為、意向對象、對象的呈現模式)出發,來思考知覺經驗,尤其是視覺經驗的本質構成。所謂呈現模式,就是將意向行為與意向對象聯系起來的東西,它包含在意向對象所呈現出來的“諸顯現”之中。例如,我們對一個紅蘋果的視覺體驗,可以被表達為具有紅色和閃亮這樣的“諸顯現”,紅蘋果對于主體的呈現模式,就包含于呈現出來的“諸顯現”之中。但呈現模式并不能簡單等同于“諸顯現”,這就涉及呈現模式的經驗意義和先驗意義(empirical and transcendental mode of presentation)的區分。僅僅在經驗意義上,呈現模式等同于“諸顯現”。因為,如果僅存在經驗意義上的呈現模式,譬如我們看到了紅蘋果的“某一顯現”,如紅色,并將經驗的呈現模式等同于“這一紅色顯現”,那么就必然存在著第二個呈現模式,它使得“這一紅色顯現”能夠以“這一紅色顯現”的呈現模式向主體呈現。接下來,如果我們要在意識中把握這第二個呈現模式,那么就必定存在著第三個呈現模式,以至于無窮。要解決這種無窮倒退,必定要假設存在一個最基本的、不可消除的呈現模式,即停止讓呈現模式不斷地落入我們的意識對象,而這就是先驗意義上的呈現模式,它是在經驗中不可消除的意向核心。經驗意義上的呈現模式,即諸顯現,只是意識對象,而并非可以構成意識對其對象指向性的先驗條件。一言以蔽之,在意向所指向的對象那里是找不到意向的指向性本身的。呈現模式的先驗意義,是使得世界對象以“諸顯現”的方式呈現給主體的條件,這就是向著世界的意向指向性,這種指向性包含在一種揭示或揭蔽活動之中。而我們已經指出,這種揭示活動既可以在大腦中,也可以在身體和在世界的活動中。所以知覺的揭示活動通常——但并非總是,也并非必然地——通過身體延展到了大腦之外,并延展到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中所做的事上。
四、從知覺到認知:對延展認知的現象學分析
在對視知覺的分析基礎上,羅蘭茨進一步將視角擴展到了對于認知的探究。他提出,與對視覺體驗一樣,在思想中同樣存在著經驗呈現模式,以及作為不可消除的核心的先驗呈現模式,并且通過這種先驗核心,作為“諸顯現”或經驗呈現模式之下的對象得以向我顯示。例如,我關于一個西紅柿的思想,就是關于西紅柿的“諸顯現”的思想,這就是西紅柿在思想中的經驗呈現模式,它們是我的意向指向的對象,是我的思想的對象。而思想的先驗呈現模式,憑借著我的視覺經驗的先驗呈現模式,使得西紅柿被我思想為落入這種經驗呈現模式之中的東西。
具體到認知過程,結合之前所談到的個人層面與亞人層面的區分,我們又可以將這種揭示活動區分為兩種形式,即載體—內容(vehicle-content)的區分,類似于經驗及其物理實現之間的區分,兩者都可以影響對象的揭示。在經驗的內容方面,是提供了使對象得以揭示或落入某種經驗呈現模式之中的邏輯上充分的條件。不同于內容,載體提供的則是因果上的充分條件。我們還以西紅柿為例,在經驗的內容方面指出存在著某種“what-it-is-like-ness”的東西,這種經驗呈現模式之所以提供了邏輯充分條件,是因為如果主體擁有這樣的呈現,那么在邏輯上,西紅柿對主體而言就必然被揭示為紅色的和閃亮的——即使這是一個幻覺,在世界的這個區域它仍然被揭示為紅色和閃亮。然而,在載體即物理實現方面,同樣也有世界之被揭示,例如我們可以在馬爾的視覺理論有關信息結構的連續轉換中找到對西紅柿的視覺體驗的揭示。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在主觀性現象上存在某種“解釋鴻溝”的原因。那么同樣道理,我們也可以從視知覺推廣到諸如思維、信念、記憶等認知過程,它們對于世界的揭示也可以區分為載體與內容。這些認知過程的內容是具有語義性的,語義內容為落入給定的經驗呈現模式下的對象之揭示提供了邏輯上充分的條件,而語義內容的載體則僅僅提供了因果充分條件。思想的語義內容之揭示是構成性的,而神經或功能機制的揭示是因果性的,因果性揭示和構成性揭示的區別,就是揭示的因果充分條件和邏輯充分條件的區別。
羅蘭茨指出,他所提出的延展認知,是關于認知載體的,而非關于認知內容的理論,或者說,延展認知對于世界的揭示是因果性的,而不是構成性的。要理解延展認知,就必須認識到認知載體一般來說并不局限在主體的大腦中,而且包含對于身體結構的利用以及對環境結構的操縱過程。在主體的意向狀態和過程的載體中所發生的揭示活動,就是延展認知的載體,它們都是因果性意義上的揭示。羅蘭茨進而區分了兩種不同的表達,即“穿行于”(traveling-through)和“通過……存在”(living through)。我們通常談論的是后者,例如意識是通過大腦而存在的,大腦是意識存在的物理基礎,意識是隨附于大腦的現象。這里存在的是一種單向的依賴關系,我們通常用隨附性等概念來描述這種關系,而“穿行于”則不同。羅蘭茨舉了三個例子來闡述“穿行于”的現象學意義。第一個是梅洛—龐蒂所提出的盲人手杖案例。從內在的先驗視角來看,手杖與必要的神經過程或其他生物學過程結合在一起,揭示或揭蔽了具有“諸顯現”或經驗呈現模式下的對象。從現象學意義上來看,它是載體,而非意識對象,盲人的意識穿行于手杖到達世界。第二個例子則是薩特對于書寫現象學的描述。薩特說,在我全神貫注書寫的時候,我并不理解我正在書寫的手,而只理解書寫的筆,我是在用我的筆寫出字母,而不是用我的手來握筆,我就是我的手。也就是說,在書寫過程中,手消失于這個復雜的工具系統中。因此,從現象學意義上來看,我的意識穿行于我的手傳遞給筆和紙。第三個例子是閱讀的現象學。當我在閱讀一本小說時,在沉浸于閱讀的過程中,盡管在某種意義上我也好像是“意識到了”書上的文字,但這些文字并非我審視的對象,我的意識是穿行于這些文字到達小說所描述的情節與人物的世界之中。
那么,所謂的揭示活動發生在什么地方?在盲人手杖案例中,它同時發生于大腦、身體、手杖以及手杖與世界的互動中,因為對象位于手杖的尖端,并且由于它對手杖的阻礙作用,盲人因此體驗到了對象處于世界的某個空間位置上。揭示活動就其本質來說,穿行于它的物質實現而到達世界。盲人的知覺意識確實也是通過手杖而存在,但在更基本的意義上,是穿行于手杖而到達世界。“穿行的概念,從根本上來說,不屬于經驗的現象學,而屬于作為揭示的意向的指向性的潛在本質,這是現象學的基礎……揭示活動本質上是世界性的。”aMark Rowlands,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pp.199—200.應該將其理解為意向指向性的本質結構,手杖和盲人的大腦一樣,都是揭示活動的所在地。所以,羅蘭茨說,不存在一種遠距離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 at a distance),意向性并不發生在虛空(void)之中,活動總是由某物完成。意向性與揭示活動就是一體兩面,只要有揭示活動發生的地方,就有意向的指向性發生。我們已經論證了揭示活動不僅發生在大腦之中,其載體存在于許多地方,“意向指向性的一般模型對于這些揭示世界的載體到底是什么類型并不關心,這些載體——無論是神經、身體還是環境——都有助于同一件事情,即對世界的揭示使其落入某種經驗呈現模式”bIbid.,p.214.。
在闡明了認知的現象學意義后,羅蘭茨回到了延展認知的經典論證,即奧拓和英伽關于信念的案例。羅蘭茨提出,克拉克和查爾默斯的延展認知版本認為,在奧拓筆記本中的地址就是奧拓的信念,但這并不準確,筆記本中的句子個例并不等同于他的信念狀態個例,延展認知不應該被理解為狀態的延展。羅蘭茨的延展版本是以過程而非狀態為導向的,因此延展應被解釋為:奧拓對他的筆記本的操作可被看作是他記憶起博物館位置的認知過程的一部分。奧拓通過身體對筆記本所進行的操作就是向他以因果方式揭示世界的載體的一部分,由此,奧拓對世界的意向指向性得以產生。這個過程同時包括大腦、身體以及環境過程,它們共同構成了揭示世界的整個過程的適當部分,都可被視為整個記憶過程的組成部分。堅持顱內中心主義的反駁者認為,由于奧拓對筆記本的訪問是通過外感知過程實現,而英伽則是直接訪問大腦內部記憶,因此奧拓對筆記本的操作不能算是認知。但是羅蘭茨指出,按照現象學的意向性說明,我們并不關心對于這些心理學類型的功能描述。奧拓在閱讀筆記本的時候,他并沒有意識到這些字母和單詞,而是意識到這些單詞所描述的東西。奧拓的意識穿行于這些單詞直達博物館地址,正如奧拓沒有“意識”到筆記本上的單詞一樣,英伽同樣也沒有意識到他的神經狀態,他的意識也是穿行于這些神經過程從而到達同樣的事實。只要他們兩人都沒有被某種障礙所阻滯,當事情按照它們應該的方向發展時,兩者并沒有本質區別,它們都是認知揭示的載體,都是一種對世界的揭示過程。
當然,揭示世界的形式多種多樣,不同的行動方式構成了不同的揭示方式,但只有符合“認知標志”的揭示行動才算是認知過程。羅蘭茨指出,認知標志中對于延展認知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所有權問題,現在我們可以在現象學意義上深化對這個問題的理解。簡而言之,如果一個認知過程向我揭示了世界,那么這個認知過程就是屬于我的。具體可以分為兩種情況:如果它是直接向我揭示世界,那么就是在個人層面,通過思想、感知、經驗等來實現;如果它是以間接信息狀態形式揭示,那就是在亞人層面將世界揭示給我的亞人認知過程。這些過程被看作具有“屬我性”(mineness),因為它們在將世界以直接方式揭示給我的那些個人層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經驗內容的“屬我性”是內建在經驗之中的,是作為擁有或者經歷某種體驗是什么樣子(what-it-is-like-ness)的一個部分,它不是我們能從第三視角來認識的對象,經驗的屬我性是現象學特征的一部分。揭示是關系性的,即它總是向某個人的揭示。當主體擁有某種“感受質”的現象特征時,這僅僅表明了世界就是如此被揭示的,并且它是“為我”而揭示的。所以,在認知載體對世界的因果性揭示中,盡管它們只是提供了因果的而非邏輯的充分條件,但是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并行的解釋,來說明為什么這些過程是“屬我的”,無論這個過程發生在大腦中,還是在身體或環境操作中。認知膨脹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只會發生在亞人層面。當我使用望遠鏡觀測天體時,望遠鏡構成了我以因果的方式揭示世界的一部分,是我的認知過程的一部分。但當我完成觀測時,望遠鏡中的光學過程仍然存在,但此時它已經不再構成揭示的一部分,也就不再是認知過程了,即使在亞人層面也不是。所以,膨脹問題就迎刃而解,認知的界限就是向我揭示世界的活動的界限。
羅蘭茨最后總結說,如果我們向內尋求意向性,將它看作我們內在對象,那么延展心靈理論就確實有悖常識。一旦將意向性理解為世界的揭示,那么無論具身認知還是延展認知,都可以極為自然地被推導出來。
五、總結:羅蘭茨的理論貢獻及其局限性
羅蘭茨試圖超越在認知研究中的自然主義研究進路,并認識到在純粹自然主義框架內很難真正理解心靈,轉而采取先驗的視角,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為根據胡塞爾的說法,自然主義的決定性限制就是它無法認識到意識的先驗維度,反而將意識看作世界中的對象。aD.Zahavi,“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in S.Gallagher,D.Schmicking(eds.),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New York:Springer,2009,p.5.羅蘭茨認為,對于“認知”這個概念的哲學理解,不是在進行研究之前就預先能夠給予規定的,反倒應該是在實踐的過程中自行呈現出來的東西。他貫徹了現象學的基本精神,即在一定程度上懸置我們關于認知的諸多自然主義態度,因此他并不是告訴我們認知到底是些“什么”(what),存在于“哪里”(where),而是告訴我們認知之“如何”(how),從我們與世界的直接應對入手,找到在此過程中直接被給予主體的是什么,以及這些被給予之物是通過什么方式來實現的。讓現象自身顯現,并在此過程中呈現出認識的可能性條件,在這一點上可以說,羅蘭茨的理論借鑒了現象學經典作家的諸多觀點,但他的理論也存在著局限性。
首先,我們可以看出羅蘭茨的論證大致借鑒了胡塞爾早期現象學的基本框架。他所利用的意向性標準模型,即意向行為、意向對象、對象的呈現模式,其呈現模式具有一種先驗(超越)的能力。這個模型大體上刻畫了一個對象呈現或者被給予我們的方式中所具有的意向性結構分析,并且其中所謂對象的呈現模式就是參與意向構成的東西,而非被意向構成的東西,它不是意向構成的結果——類似于胡塞爾的“立義”過程。當然,在胡塞爾那里并沒有所謂獨立的“呈現模式”一說,但在胡塞爾那里,先驗呈現模式也具有“超越論”含義,因此正是通過先驗呈現模式,對意識的感性材料進行超越性的統攝,雜亂的感性材料才被立義為意識對象。b參見倪梁康:《胡塞爾現象學概念通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年版,第468 頁。他看到了意向活動的關系性與生成性,也就是說,在意向性中必定存在著主體側和對象側兩個方面。在主體側是意識活動的呈現與意指活動方面,而在對象側則是意向對象方面。但這兩方面并非傳統的主客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是說任何一個意識對象都是由一個意識活動所構成的,意識活動和意識對象是一種本質上不可分的結構。那么只要符合這一現象學結構,至于在物理實現層面是通過什么載體而實現的,這并不重要。“認知體驗就有一種意向,這屬于認識體驗的本質,它們意指某物,它們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與對象發生關系。”a埃德蒙德·胡塞爾:《現象學的觀念》,倪梁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年版,第48 頁。對認知過程的考察不再是自然主義式的分析,而是體現出認知過程的雙向結構,從這種雙向結構中,認知的生成性被發現,而不再是一種局限在大腦內部的無生命力的東西。
其次,我們也可以很容易發現,在闡述作為一種行動的認知過程時,羅蘭茨對海德格爾思想的借鑒。比如海德格爾對行動中的此在與工具之間的關系的著名分析,即區分了工具的“上手性”與“在手性”。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提出,在我們日常生活與世界的應對過程中,“上手性”是一種更為原初的關系。當我們使用工具時,工具本身具有一種消失的趨勢,對于使用者來說,成為透明性隱退的狀態。我們是在更為基本的層面,而非原初通過對于諸如自我、意圖、意志等心理主義意義上的意識來解釋的。羅蘭茨這樣描述:“我們對自己行為的基本認識是由這種透明的空虛構成的,在這種空虛中,我是純粹朝向目標的指向性……在我沉浸應對世界的過程中,我的意識沒有明確的對象。我所使用的設備和讓我能夠使用它們的精神生活都是如此。我們可以說,我的意識是對世界的指向性,這種指向性通過它的對象指向我的目標。”bMark Rowlands,The New Science of the Mind:From Extended Mind to Embodied Phenomenology,pp.159—160.而當行動者對自身能動性采用一種心理主義的描述時,往往意味著行動者與工具之間的聯系被打破,以及工具與行動者及其意識狀態變為不透明時所產生的能動感。海德格爾曾經分析了三種工具性受阻的方式,只有在這三種情況下,“我”才能體驗到“我”的行動來源于“我”的精神。但是,所有在受阻狀態下有關行動者的現象學形式,都是某種更基本、更原初的現象學形式的派生。此外,羅蘭茨在將意向性描述為一種揭示或揭蔽的活動時,將廣泛的技術環境也包容進去,這顯然是海德格爾“技術乃是一種解蔽方式”的說法在認知領域的翻版。
羅蘭茨的理論也招致了一些批評,這里我們考察兩個批評c這兩個批評轉引自:劉好、劉宏:《作為一種顯現活動的意向性——羅蘭茨的意向性理論研究》,載《哲學動態》2015 年第8 期,第105 頁。第一個批評是由論文作者提出,第二個批評是由沙尼(Itay Shani)提出。,并指出這兩個批評的提出其實都是由于并沒有徹底貫徹現象學的精神導致,因此并不能駁倒羅蘭茨的基本前提。第一個批評認為,羅蘭茨在他的理論中提出,任何向我揭示世界的過程,就是認知過程,我對此過程就擁有所有權,但這些認知過程又必須滿足其所提出的認知標志的四條標準,才能被算作認知過程,其中第四條標準是說這個過程是屬于那個表征狀態的主體的一個過程,即主體對其擁有所有權,因此這里存在著將論證的結論當作前提的錯誤。但是筆者認為,這個批評其實是在用形式邏輯的原則來批評一種現象學語境中的主體行動問題,因此我們可以將這種似乎循環論證的現象看作一種“解釋學的循環”。羅蘭茨提出,認知科學不僅需要解釋世界,而且需要自我解釋,如果我們將第四條標準看作一種方法論原則,那么的確存在循環論證;但是,如果我們將其看作現象學意義上的解釋活動,那么主體恰恰需要進入這種解釋學循環之中,才能真正把握認知。海德格爾曾經提出過一個門把手問題:原始人在使用門把手時,其實他們并不是就將它定義為某種門把手,也不是有意制造出它,而是覺得這個門上的凸起部分可以幫助他們開門,后來才發現在這里可以安上一個東西,并把它叫作“門把手”,這就是門把手的由來。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任何能幫助我開門的東西,都是門把手,然而后來我們對門把手進行定義,門把手必須滿足能幫助我們開門的標準才能稱為門把手,但這里并不存在循環論證,我們在作任何定義之前,本來就已經有了某種“先見”。所以我們說,作為主體行動的揭示活動與作為認知標志的所有權問題的關系就應如此理解,它并不是形式邏輯意義上的循環。第二個批評認為,羅蘭茨對于工具的使用過于廣泛,而工具往往具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是作為對象的承載者和持有者,另一種是作為對象的傳輸者和發射者,兩個概念既有區別又有重疊。比如,我們通過望遠鏡來觀察天體,我既可以將望遠鏡解釋為實現了對世界之揭示的載體,也可以將望遠鏡解釋為信息的傳輸者;而真正承載了認知過程的,還是大腦內部的神經系統,因此在對象呈現給主體過程中,外部工具起了作用,但不能推導出它們就是認知內容承載者而進入認知過程。筆者認為,這個批評也是對羅蘭茨的誤解。羅蘭茨并非沒有注意到工具的區分,他曾明確提出了工具的兩種形態,即上文提到的“穿行于”和“通過……存在”,并嚴格區分了兩種表達的不同語境:前者是在現象學語境中,表達了認知揭示的先驗條件,是構成性的;而后者是在自然主義語境中,表達的是認知揭示的經驗條件,是因果性的。在現象學看來,這兩種情況本來就不矛盾,他們不是描述兩種不同的過程或狀態,而僅僅是描述同一種過程或狀態,但采取了不同的態度——前者是現象學態度,后者是自然主義態度。用其中一個去反駁另一個,顯然沒有意義,所以這個批評也不能成立。
當然,羅蘭茨的論證的確存在著某種曖昧之處。他一方面認為所提出的認知標志可以滿足廣泛的自然主義認知研究范式,另一方面卻堅持某種先驗維度。因此,這種論證是自然主義與先驗主義的某種混雜產物。堅持先驗維度,在自然主義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是否會損害羅蘭茨提出的“心靈的新科學”?或者是否與當前所謂“自然化現象學”相矛盾?筆者認為,首先,對于心靈的研究堅持某種先驗立場有其合理性,純自然主義框架在研究心靈問題上確實存在局限性;其次,不同的現象學家對于先驗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現象學本身也在不斷發展,現象學的先驗主義與自然主義未必就是對立的關系。比如,梅洛—龐蒂就在堅持先驗立場的同時,大量吸收了當時的經驗研究成果,在他的理論中,先驗與經驗完美融合在一起。現象學帶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拒絕像自然主義那樣將心靈和意識看作某種真正的存在實體——當然,并非身心二元論意義上的實體,而是一種實體性思維。所以,我們思考延展認知的方式決不能是那種實體性思維——比如心靈是一個實體,技術工具是另一個實體,所謂心靈的延展就是一個實體延展并與另一個實體相結合。在哲學中,解決疑難問題的關鍵往往在于視角的轉換,現象學的先驗視角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羅蘭茨的局限性在于,他對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思想借鑒僅僅停留在對認知的統觀思考之上,他的理論僅僅告訴我們意識的某種先驗性,試圖用這種條件來統攝一切認知活動,再從這種認知活動自然而然地推導出延展認知。從現象學角度來解釋一般的認知本身,這是一個突破,但是現象學在他的理論中更像是一種附加上去的先驗限定,他沒有真正從現象學進路對技術人工物如何在揭示世界過程中發揮作用作出更為詳細的描述,他對于大腦、身體和技術之間的本質聯系的討論,又回到了載體因果性層面,因此它們的關系很容易停留在一種外在的關系之上。比如,他論述人與技術之間的因果性關聯時,認為這些亞人過程必須對個人過程作出貢獻,才能被看作是認知,但是這種說法過于籠統。羅蘭茨自己也曾說,這個想法很簡單,卻很難精確描述。如果不能從一種內在共同構成的視角來看待這種關系,而仍然沿用類似于外部因果耦合的論證方式,那么他就依然回避不了批評者對他的批評,甚至還有可能退回到從功能主義來論證延展認知的老路上。他對心靈先驗性的強調與胡塞爾對先驗自我的強調如出一轍,在他那里,缺少了后來出現的身體和技術現象學的參與,即必須通過在人與技術之間的一種現象學關聯,才能真正實現認知的延展。比如,伊德在其技術現象學理論中借用了胡塞爾的自由變更概念,但是與胡塞爾利用自由變更來把握本質不同,伊德則利用自由變更來獲取現象所呈現出來的多重穩定性的復雜結構——現象并非只具有唯一的本質,而是可以顯現為不同的結構,顯現為多重可能性,具體顯現為何種結構則依賴于所使用的語境。因此,技術環境與人的身體的現象學關系,也是依賴于不同的原初生成性境遇,從而顯現出不同的本質結構,并非所有的人—技術耦合都可被看作延展認知系統,我們也無法給出延展認知的某種普遍條件。例如,伊德就將人、技術與世界之間的關系區分出以下四種:體現性的(embodiment)、解釋學的、它異性的、背景性的。其中,體現性關系就是指技術作為一種居間調節的裝置。在這種關系中,人類經驗是被處于居間調節的技術所改變的,人類與技術融合為一體,共同面對外部世界。這種關系可被形象地表述為:(人—技術)—世界。在這種人與技術的融合體中,人與技術產生了共生關系。如果說梅洛—龐蒂將身體與世界的關系用“意向弧”來加以描述,伊德則提出了工具本身也具有某種“意向性”,可以改變現象被揭示的條件,將其擴展為人—技術工具—世界三元的意向弧關系。
現象學家們彼此之間的差異就在于,如何尋找那個原初生發性的境遇。胡塞爾認為其根本在于純粹意識,海德格爾認為根本在于“在世界中存在”的此在,而梅洛—龐蒂則認為根本在于身體。所以,我們需要對身體與技術融合在認知的原初生發境遇中是如何被構成的進行更為詳盡的分析。即使在胡塞爾那里,我們也已經看到了這種分析的典范。胡塞爾在《觀念2》以及后期著作中,有著大量現象學構成的嘗試。在他的構成理論中,我們往往只關注他對超越的外物的把握,卻忽略了他對于身體的原初把握。身體也是隱匿在背景之中的,這種對于身體的描述非常類似于我們所使用的工具,工具隱匿于背景之中,但我們必須憑借它們才能得以行動。a參見王繼:《身體與世界的共構:胡塞爾〈觀念2〉中的身體問題》,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127 頁。當然,胡塞爾并沒有將視角延伸到工具之中,而只是論述了身體與物體、心靈、世界之間共同構造的關系。但是他在懸置了生理身體、外部世界以及心靈的前提下,一步步地將它們重新建立起來,通過回到原初直觀,發現身心原初乃是交織在一起,并且彼此構造、激活對方。如果能夠將這種方式轉移到對身體與技術融合的分析中來,并且不預設某種自然主義的前提,而是讓這種融合從現象的原初生發境遇中自行顯現,而不僅僅將其看作一種物理上外在的因果性耦合,那么我們就可以將延展認知建立在更堅實的基礎上。當然,這個任務很艱難,需要和身體現象學及技術現象學的密切合作才可能得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