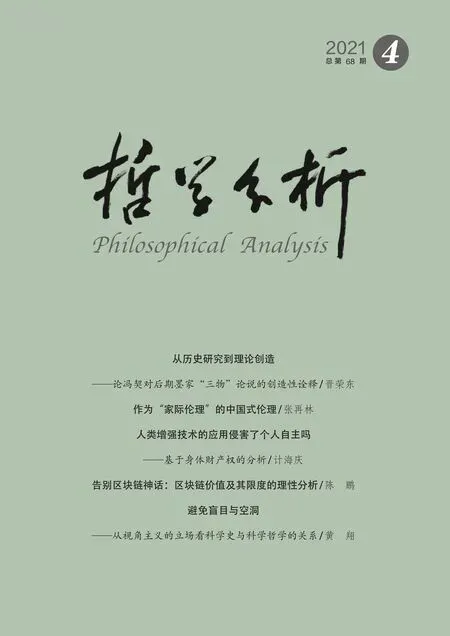作為“家際倫理”的中國式倫理
張再林
家是社會的細胞,又是社會的母體。對于重視“血緣根基”并以“家的精神”為其民族精神的中華民族來說,其對家更是備極頂禮。從中不僅產生了“家國一體”“齊家治國”的政治文化,還為我們推出一種極其獨特的中國式“家際倫理”。這種“家際倫理”與其說是一種抽象的“人際”倫理,不如說是一種原始而具體的家人之際的倫理。故這種“家際倫理”實際上是在夫婦之際、父子之際、兄弟之際第次展開的。
一、“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的夫婦倫理
《顏氏家訓》寫道:“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婦,有夫婦而后有父子,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親焉,故于人倫為重者也,不可不篤。”(《顏氏家訓·兄弟 篇》)
我們之所以對這一論述極其注意,不僅在于它為我們明確指出什么是最重要的家庭之際,而且尤其還在于它一反父權社會以“父子”獨尊的家際倫理,而把夫婦之際視為家際倫理真正的造始端倪。其實,這種合乎常理的夫婦優先的觀點并非顏氏孤明獨發,早在《周易》中它就被古人祭為不易之理。如《周易·序卦傳》提出:“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而在與《周易》互為發明的《周禮》中,這種夫婦優先則表現為禮以“婚禮”為根基。故《禮記》提出“夫昏禮,萬世之始也”,《禮記·郊特牲》提出“昏禮者,禮之本也”(《禮記·昏義》)。雖然在長期中國歷史上,父子之際成功實現了其位序上的“逆襲”,優先的夫婦之際完全讓位于其后的父子之際,但伴隨著明清之際借古人之酒杯澆今人之塊壘的“復古”思潮的興起,《易》 《禮》的夫婦優先觀點又一次重整旗鼓地異軍突起。如李贄稱“一夫一婦,家家之乾坤”a李贄:《李贄文集》第七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版,第97 頁。,“天下之定,觀乎家人;家人之正,始于男女”b同上書,第188 頁。,唐甄稱“蓋今學之不講,人倫不明;人倫不明,莫甚于夫妻矣”c唐甄:《潛書》,北京:中華書局1955 年版,第77 頁。,戴震稱“人之倫類肇自男女夫婦”d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版,第174 頁。,王韜稱“欲家之齊,則婦惟一夫,夫惟一婦。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天之道一陰一陽,人之道一男一女,故《詩》始《關雎》,《易》首乾坤,皆先于男女夫婦之間再三致意焉”e王韜:《弢園文錄外編·原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版,第3—4 頁。。
應該明確指出的,這種為古人強調的家際倫理的“夫婦優先論”,不僅包括發生學意義上的“優先”,而且還包括邏輯學意義上的“優先”,也即“原型說”意義上的“優先”。為了說明為什么夫婦之際是一切家際倫理的“原型”,就必須從古人所理解的夫婦之際的“際”的關系談起。
首先,正如列維納斯“他者”倫理學把男女中的女性視為“他異性”來源那樣,對于中國古人來說,夫婦之際亦同樣起始于所謂的“男女有別”。這種男女有別可見于“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禮記·坊記》)的周人同姓不婚制,可見于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男女不同席,不共食”“男女不交爵”,以至于古人認為“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禮記·昏義》)。唯有男女有別,才能使一種情感專一的對偶式夫婦關系得以建立,從而使我們人類自己告別了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婚制,并從中最終形成了一種本末一貫、枝葉分明的家庭家族的生命共同體。
其次,也正如列維納斯在強調女性“他異性”的同時并不忽視男女之間的“親密性”那樣,中國古人亦如此。由此就有了《禮記》所謂“為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禮記·喪服傳》),所謂“夫妻一體也”(《禮記·喪服傳》),就有了《詩經》所謂“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小雅·常棣》)、“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邶風·擊鼓》)、“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邶風·谷風》)這些無上的美譽,而“比翼鳥”“連理枝”等成語則代表了對這種親密性無人不知的隱喻。
這樣,在男女夫婦之際,我們看到了一種所謂的“親密的差異”。而這種“親密的差異”以其不無詭譎的非一非異,恰恰指向古人所謂“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荀子·榮辱》)這一人倫邏輯。顯然,這種邏輯與其說體現了一種美德倫理、規范倫理所遵循的意識之間“同一律”的邏輯,不如說體現了中國家際倫理所恪守的身體之間“模棱兩可”的邏輯。這使中國家際倫理一開始就打上了梅洛—龐蒂式“身體間性”的鮮明印記。
既然男女夫婦之際是一種“身體間性”,同時,既然男女夫婦的身體實際上是兩性欲望的身體,那么這就決定了,夫婦之際與兩性欲望關系,是須臾不可分離的。關于這種兩性欲望關系,彭富春先生寫道:“在性欲的關系結構中,欲望者是人,所欲物也是人。這使欲望者和欲望物各自都具有兩重身份。這就是說,一方面,欲望者既欲望他的所欲物,也被他的所欲物所欲望,因此欲望者同時也是所欲物。另一方面,所欲物既被所欲望者所欲望,也欲望他的欲望者,因此所欲物同時也是欲望者。這意味著,在性欲中的男女關系既不是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也不是主動和被動的關系,而是一種不可分離和共同生成的伴侶關系。……他們是具有差異的親密的一對。雖然你我差異猶在,但親密導致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a彭富春:《論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年版,第93—94 頁。
這種對男女欲望的“不同而一”的論述與黑格爾所謂的“愛的辯證法”何其相似,因為黑格爾亦指出:“愛的第一個環節,就是我不欲成為獨立的、孤單的人,我如果是這樣的人,就會覺得自己殘缺不全。至于第二個環節是,我在別一個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獲得了他人對自己的承認,而別一個人反過來對我亦同。因此,愛是一種最不可思議的矛盾,決非理智所能解決的……作為矛盾的解決,愛就是倫理性的統一。”a黑格爾:《法哲學原理》,范揚、張企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版,第175 頁。
當黑格爾為解釋男女欲望的“不同而一”而求助于一種不無新穎的“愛的辯證法”之際,中國哲學家焦循則從古老的《周易》里發現了揭開這一問題的真正隱秘。對于治易大師焦循來說,以“趨利避害”為宗旨的《周易》實際上是以如何實現我們的身體欲望為目的的。而這種欲望能否實現既不取決我的“己欲”,又不取決于非我的“他欲”,而是取決于“既遂己欲,又遂人欲”這一人我欲望兩相孚的“互欲”。凡遂的欲也即《周易》所謂主吉的利,凡不遂的欲也即《周易》所謂主兇的不利。當我們進一步追溯這種“互欲”如何可能時,焦循則告訴我們,正如《周易》一貫主張唯有陰陽相交才能實現遂欲的吉利那樣,其答案恰恰就在無師自通、無比自洽的男女夫婦的關系里,因為“夫婦者,一陰一陽之交孚也”b焦循:《易通釋》卷五,《易學三書》,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年版,第121 頁。。易言之,正是在男女夫婦兩兩相交的“互欲”活動里,才能使人我互欲的隱秘真正大白于世。
這樣,“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九章·抽思》)在男女夫婦之際的“互欲”里,一種愛的自組織型的雙向回饋的“無施不報”就應運而生了,成為夫婦際會的至為主要規定。從《禮記》中的必以昏(婚)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到《詩經》中的樛木高木能下曲,葛藟攀附而上“猶能庇其本根”(《周南·樛木》);從“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衛風·木瓜》),到“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鄭風·女曰雞鳴》;從愛情中女子雖可“守身如玉”但又可“以身相許”,到《紅樓夢》里林黛玉為報雨露之恩傾其一生“還淚”的故事;如此等等,無一不是對這種“無施不報”的如詩如歌的訴說。至于古代稗聞野史中所謂男女夫婦“對食”之說,則以其對“回饋”(“饋”有“食”義)無比生動逼真的表述而使“無施不報”之義得以真正顯豁。
人們看到,正是在這種愛的“無施不報”里,從中產生了周禮的“禮尚往來”之說,還有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恕之說。而孟子的“出乎爾反乎爾”理論的推出,更是以“無施不報”為依據的。它不僅告訴我們為什么“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離婁下》),為什么“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孟子·離婁上》),還告訴我們為什么“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它作為“無施不報”原則在君臣之際的一種體現,迥非那些流于“舔痔”之輩的后儒所能夢見。
二、“仁復藏果,果復藏仁”的父子倫理
如前所述,在夫婦之際,從其“親密的差異”導出“不同而一”。這種“不同而一”實乃“和而不同”的“和”的學說。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則使夫婦倫理與生生之理互為表里,由此就有中國古人的陰陽化生之說。這樣,在這種陰陽化生的生命里,誠如王船山所說,“天地率由一陰一陽之道以生物,父母率行于一陰一陽之道以生子”(《尚書引義卷四·泰誓上》)。通過一種黑格爾所謂夫婦關系的“現實化”、列維納斯所謂夫婦關系的“實體轉化”,我們家庭中的“孩子”出現了。進而,隨著“孩子”的出現,夫婦之際一變為父子之際。
既然夫婦之際關系是一切家際關系的“原型”,那么,這一“原型”對父子之際同樣成立。也就是說,無論是夫婦之際還是父子之際,二者都不謀而合地遵循著一致的邏輯。
因此,正如夫婦之際體現了一種非異非一的“親密的差異”的關系那樣,一種真正的父子之際亦完全如此。故一方面,在父子之際,古人強調子對父的“無違”“色難”“三年無改于父子道”“大孝終身慕父母”,強調“子為父隱”“父為子隱”,乃至更有甚者,在一些人眼里,舜對父的逆來順受、竊負而逃被視為孝道的至極代表。但另一方面,在父子之際,古人又主張“所謂肖子者,安能父步亦步,父趨亦趨,父與子異形離質,而所繼者惟志”(《尚書引義·皋陶謨》),主張“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主張“于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趙岐注孟子“不孝有三”),主張“父有爭子,不行無禮”(《荀子·子道》),“事父母幾諫”(《論語·里仁》),其中子對父的他異性的凸顯亦成為古人事父之道一大特點。
于是,正如夫婦之際“親密的差異”導出男女夫婦之間的“互欲”,這種“互欲”又一次出現在父子之際。故父子之際并非單向的父道獨尊的領域,而為一種雙向的“父慈子愛”的愛的共同體。在這方面,我們看到《詩經》中詩人歌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小雅·蓼莪》);在這方面,我們看到《禮記》釋者寫道:“以財言之,謂物為本。以終言之,謂初為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孔穎達釋《禮記·郊特牲》)。也正是從這種施、報關系出發,才有了孔子以子女“三年之喪”回報父母“三年之養”的“仁”的思想,才有了《孝經》“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的“孝”之道,才使“鴉有反哺之義,羊有跪乳之恩”成為人所皆知的人生警喻,才使“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不失為流淌在中華民族每個兒女心中最美的詩句。
張祥龍先生曾從人類學高度為我們力揭了人之所以要回愛自己父母的真正深意。他指出,也許是由于人類的直立兩足行走,它限制了人的骨盆開口處的寬度,寬度限制了產道,使人類的母親無法像包括黑猩猩在內的其他哺乳動物那樣順利生產,于是,就只能在嬰兒還極其不成熟的時候就生下他。結果就是,較之其他靈長類動物,人類撫育子女的時間更漫長,過程也更艱難。反過頭來,由于人類特有的深長的時間意識,致使他們能夠記得或想到,父母對自己曾有如海深的大恩,自己應該在他們年老時加以回報,此即孝意識的產生。結果就是,那些沒有能力覓食的老年人,從年輕的成年子女那里得到食物,正是受到他們子女的供養和保護,才使他們過了生育年齡后還可以繼續活著,并由于他們的知識和經驗而得到尊重。這一切告訴我們,正如人類學家指出的那樣,“人類終身都與兒子們和女兒們保持聯系”,并基于此,才使人類以其特有的人性而與其他靈長類動物大異其趣。a張祥龍:《孝道時間性與人類學》,載《中州學刊》2014 年第5 期。
因此,一種發端于夫婦之際的雙向回饋的“無施不報”生命運動在父子之際又得以豐富和繼續,以至于從張祥龍先生那里我們甚至可以產生這樣的結論:這種“無施不報”使我們既可以得出父母生出子女,又可以得出子女生出父母。
這不正是三百多年前明代著名哲學家蕺山先生非凡思想的再次表述嗎?因為當時蕺山先生在談到生命運動時就推出了著名的“果復藏仁,仁復藏果”的命題:
只此一點幾微,為生生立命之本。俄而根荄矣,俄而干矣,俄而枝矣,俄而葉矣,俄而花果矣。果復藏仁,仁復藏果。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是故知死生之說,是故知無死無生之說。b劉宗周:《劉宗周全集》第二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年版,第431 頁。
在這里,蕺山先生指出,我們人類生命運動如同一棵植物生成那樣,看似由因及果地先有“仁”后有“果”,實際上則是互為因果地“仁”與“果”的“互生”過程。這不僅意味著“實體性”模式的終結和“關系性”模式的誕生,而且還意味著正是在這種生命“互生”的過程中,生命開始與生命完成已不再判然有別,而是二者始終首尾相接,從而父代生命的死亡不再使父子生死兩隔,而恰恰是這種生死兩隔的終結和消解。這樣,人“必有一死”、人“向死而在”之說一變為“世代相生”的無死無生之說,也即生命的“生生不息”之說。
在王船山那里,蕺山的父與子“互生”的“世代相生”則是通過一種“父母感生”的“終始之無窮”的方式展開的,它進一步為我們彰顯、弘揚了父子際生命的“生生不息”的特征。故船山指出:“人之所自始者,其混沌而開辟也。而其現以為量,體以為性者,則唯陰陽之感。故溯乎父而天下之陽盡此,溯乎母而天下之陰盡此。父母之陰陽有定質,而性情俱不容已于感以生,則天下之大始盡此矣。由身以上,父、祖、高、曾,以及乎綿邈不可知之祖,而皆感之以為始;由身以下,子、孫、曾、玄,以及乎綿邈不可知之裔,而皆感以為始。故感者,終始之無窮,而要居其最始者也。”(《周易外傳卷三·咸》)
無獨有偶,這種父子之際“互生”所內蘊的“生生不息”之義既為中國古人所開啟,同時又在當代西方那些“家哲學”的先知先覺者那里得以揭示,這使它以一種普遍真理的方式貫通中西。關于后者,法國后現代哲學家列維納斯的觀點尤值得一提。這是因為,列維納斯不僅提出父子關系“過去每時每刻都從一個新的起點出發得到恢復(se reprend),煥然一新地恢復”a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朱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272 頁。,而與蕺山的生死首尾相接的觀點如出一理,而且還提出“與孩子的關系——就是說,與他者的關系,這并不是權能,而是生育——建立起與絕對將來或無限時間的關聯”b同上書,第260 頁。,提出“生育延續歷史,卻并沒有同時產生衰老;無限時間并沒有給予老去的主體帶來永恒的生命。無限時間穿越世代斷裂,它是更好的,它因孩子之不可窮盡的青春而充滿節律”c同上書,第261 頁。,由于強調父子相傳的“生育”,列維納斯的觀點最終與中國古人所發明的世代相生的“生生不息”的精義完全不期而遇了。
“自我的生育,乃自我的超越本身”d同上書,第271 頁。,一如列維納斯所指,一種所謂的“內在超越”由是應運而生。也就是說,當代新儒家所推出的“內在超越”之所以成立,與其說取決于一種其所謂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智的直觀”的“心體”,不如說最終有賴于一種家世學意義的“以似以續”的“身體”。正是在一種“兒子不是我;然而我是我的兒子”e同上。這一亦離亦即的父子之際,我們才能真正體驗到那種既內在又超越的生命的不可思議的神奇。
三、“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兄弟倫理
實際上,父子關系既導致了家的生命在縱向時間上的無限擴充,又使家的生命在橫向空間上無限的擴充成為可能。為了說明后者,就不能不談到兄弟倫理所涉的豐富內容。
也就是說,“父子關系作為一種無數的將來產生出來,被生產出來的自我同時既作為世界上的唯一者又作為眾兄弟中的一員而實存”a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第273 頁。,誠如列維納斯所示,父母結合經由“生育”不僅產生了“孩子”,而且這種“孩子”并非單數的,而是復數的,從而就使我們進而又從父子倫理過渡到兄弟倫理。
既然夫婦倫理是一切家際倫理的“原型”,那么,這一“原型”既對父子倫理成立,又對兄弟倫理同樣成立。唯其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詩經》還寫道“宴爾新婚,如兄如弟”(《邶風·谷風》),而有了新婚夫婦情同兄弟之喻;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詩經》還寫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大雅·思齊》),而聲稱夫妻準則可以直接運用于兄弟之際;以至于由此可見,一代國學大師錢穆所說的古人把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這一發現絕非虛語。
于是,一如夫婦之際為我們指向了非異非一的“親密的差異”,這一點對于兄弟之際亦同樣成立。故一方面,在兄弟之際,我們看到了古人有所謂的“骨肉”“手足”之喻,看到了《詩經》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小雅·常棣》)那樣的美譽,而《顏氏家訓·兄弟篇》所謂“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更是把兄弟之際這種無比親密性的描述推向了極致。但另一方面,這種兄弟之際的親密并不能使我們無視兄弟之際難掩的差異,因為較之于父子之際那種直接而無間的血緣聯系,在兄弟之際,其血緣聯系由于借助父親這一“中介”,的確出現了弱化的趨勢,并職是之故,才使列維納斯的家哲學把兄弟關系稱作家中“陌生人”的關系。b孫向晨《論家——個體與親親》,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 年版,第203 頁。
這樣,正如夫婦之際“親密的差異”實與男女夫婦之間的“互欲”互為表里那樣,這種“互欲”亦與兄弟交往的原則完全一致。我們看到,正是從這種“互欲”出發,才使古人提出“兄友弟恭”,把雙向回饋的“無施不極”視為兄弟之際所遵循的不可讓渡的絕對原理。與一種兄長的長我、愛我、佑我、伴我、助我相應的,則是兄弟的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的知恩之心,進而才有了如同深植于我們生命基因那樣的手足之誼、骨肉之情,而這種手足之誼、骨肉之情顯然與那種“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情不深”的世俗之情涇渭分明。也正是這種兄弟情深,才使戴震寫道“昆弟之情,洽之盡也”(《原善》),才使周公旦有了寧愿自己折壽也祈求兄長武王能夠延壽的一片深情,才使孔融、孔褒二人為救朋友競相赴死的同門爭義,才使伯夷、叔齊兄弟在繼承君位上相互推讓而具名揚千古之舉,也才使古人為我們留下“上陣父子兵”的同時亦留下了“打虎親兄弟”這一著名諺語。
必須指出的是,由于兄弟之情的“互欲”是一種平輩間的“互欲”,故較之上下輩的父子之情的“互欲”而言,這種“互欲”已清除了父子之際“尊尊”的孑遺,而更多地體現了一種平等的“朋友”友誼。這使“四海之內皆兄弟”在中國文化中成為可能的同時,也使中國古人從中實現了從“親親”的“齊家”到“仁民”的“治國”的成功切換與轉型。
中西文化往往是相通的,這一點在兄弟與朋友的內在聯系上表現得尤為分明。因為亞里士多德就指出:“兄弟之間的友愛,似乎與伙伴的關系相同,他們是平等的”a亞里士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苗力田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年版,第180 頁。,進而他還指出,正是基于這種平等,才使兄弟友愛與一種輪流執政、權力平等的城邦體制深深相契、息息相通。殆至列維納斯哲學的興起,這種兄弟與朋友的內在聯系又被進一步彰顯和發明。這表現為,列維納斯從西方“天父”的宗教學說出發,認為人類就是一個來自“一個父的共同性”,并由“兄弟”構成的大家庭,從而“人人皆兄弟”已不再是道德學家一種一廂情愿的臆想,而是以一種既生物又超生物的家庭生成法則為其堅實支撐的,以至于他提出:“人類自我在兄弟關系中確立,人人皆兄弟這一點并不是像一種道德成就那樣被添加到人身上,而是構成人的自我性。……在兄弟關系中,他人復又顯現為與所有他者血脈相連;在這樣的兄弟關系中,與面容的關系構造起社會秩序,構造起任何對話與第三者的關聯;憑借這種關聯,我們——或團體——就包含了面對面的對立,就使得愛欲性事物涌向社會生活,那充滿表示合乎情理的社會生活,它包含家庭結構本身。”b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第274 頁。至此,列維納斯漫長的家的探索之旅,終于從“親親”走向“博愛”,從“愛有差等”走向“社會平等”,并借以向我們表明了人類生于斯,長于斯的家與其說是一座血脈的鎖鏈鑄就的“圍城”,不如說是一種充滿無限可能性和通向更為廣闊世界的開放系統。
耐人尋思的是,這種對兄弟與朋友內在聯系的強調曾是中華文化的一大傳統。早在家道最為鼎盛的西周宗法制時期,除了對“兄弟”的大力提撕之外,關于“善兄弟為友”(《爾雅·釋訓》)的論述可謂比比皆是。如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孝友惟型”(《厝彝》),“惟辟孝友”(《史墻盤》),如《詩經·皇矣》曰“維此王季,因人則友,則友其兄”,《國語·晉語》稱文王“孝友二虢”(二虢為文王弟)。再翻開《尚書》,其中“善兄弟為友”之義更是觸目可見。《尚書·君陳篇》寫道:“孝乎唯孝,友于兄弟”,《尚書·康誥篇》寫道:“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清儒程瑤田由此得出:“宗之道,兄道也。大夫士之家,以兄統弟以弟事兄之道也”a程瑤田:《程瑤田全集》卷一《宗法小記》,合肥:黃山書社2008 年版,第137 頁。,查昌國教授亦明確斷言:“歷代注家都謂西周‘友’為兄弟規范,這一認識得到現代周史研究的進一步證實,是為確論”b查昌國:《友與西周君臣關系的演變》,載《歷史研究》1998 年第5 期。。
這種兄弟與朋友之間的不解之緣之所以可能,不僅在于西周的宗法制的核心是大宗統小宗,大小宗實際上是兄弟關系,而且還在于周人所謂的“友”既包括同胞親兄弟,也包括非同胞的同族兄弟,甚至包括通過聯姻的非同姓的兄弟。這也意味著,人們所尊先祖越是久遠,兄弟的范圍也越是廣泛,兄弟的血緣聯系也越為遞減,兄弟與朋友之間也越失去其界限,乃至四海之內皆可為兄弟,乃至“民吾同胞”“天下猶一家”這些說法絕非虛言。故《禮記·大傳》寫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在《禮記》中,古人的祖宗崇拜與其說旨在發思古之幽情地懷念其歷史上逝去的先祖,不如說旨在活在當下而普愛在先祖庇蔭下生活著的蕓蕓眾生、普羅大眾。
這不正可視為列維納斯“天父說”的中國版嗎?正如列維納斯從一種不無神化的父出發,從“親親”走向“博愛”、從“愛有差等”走向“眾生平等”,中國文化亦從一種“天祖合一”的“祖”出發,其路徑與列維納斯不約而同。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春秋之際,與儒家“親親”之說交相呼應,墨家的“兼愛”之說、“尚賢”之說亦在中國大地一呼百應、風起云涌,以至于一度出現了“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上》)這一蔚為壯觀的風景。究其原因,這不過是作為“兄友”之道的流風余韻,乃周人文化的歷史繼承和遺存。明乎此,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司馬遷筆下,在先秦之際有如此多的俠義之士的壯舉,如趙氏托孤的故事,“知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的豫讓的故事,“意氣兼將生命酬”“向風引頸送公子”的侯嬴的故事,從中使人感受到的與其說是英雄豪杰的驚天地、泣鬼神的“視死如歸”,不如說是以其“士為知己者死”的“無施不報”,讓人領略到那是西周宗法社會“家”的日薄西山之際,殘留在中國文化中的最后一抹壯麗余暉。
同時,明乎此,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中國明清之際“以復古為啟蒙”的回歸家的思潮中,人們除了看到對周人所厚的家的力挺外,還連同看到對周人所厚的朋友之倫異乎尋常之獨尊。關于這一點,何心隱指出:“天地交曰泰,交盡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學盡于友之交也”a何心隱:《何心隱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版,第28 頁。;后來的譚嗣同亦指出,“五倫中于人生最無弊而有益,無纖毫之苦,有淡水之樂,其惟朋友乎”b譚嗣同:《譚嗣同全集》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版,第350 頁。。這種對“家”與“友”不分軒輊的并重,不僅使我們走出“親親”與“兼愛”之間二律背反這一中國儒家思想的“阿克琉斯之踵”的陰影,而且一反“三順說”“三綱說”所帶來的積重難返的權力話語的獨斷,使長期湮沒無聞的社會平等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再次得以彰顯。
不無遺憾的是,在長期的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雖講“孝悌為本”,但實際上更多強調的是孝的父子之倫,而顧此失彼于悌的兄弟之倫,更遑論那種“善兄弟為友”的朋友之倫。這不獨有悖于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精神,也與人類現代的追求社會平等的精神背道而行。故在中國走向思想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既要認識到中國父子倫理的遺產之不可或缺,又要積極投身于對中國兄弟倫理深刻而豐富內容的深入發掘,唯此才能使我們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這一繼往開來的文化偉業。
四、結語
走筆至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結語:
其一,不難看出,這種家際倫理學就其直接置身于、直面于種種原始而具體的家人之際關系而言,是一種類似于列維納斯現象學的“面對面”的應對型、交往型的倫理學。用王陽明的表述,即它是一種“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和“只在感應之幾上看”的“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悌,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傳習錄》)的此感彼應的感應倫理學。
其二,在這種家際倫理學里,一種始于男女夫婦間的自組織的愛的雙向回饋是其最根本的法則。這種雙向回饋不僅以一種“無施不極”的方式,一以貫之于夫婦之際、父子之際、兄弟之際里,而且還以一種否定之否定的方式,體現在從夫婦間的非血親關系,中經父子間的血親關系,再通過“善兄弟為友”,最后到普天下眾生的非血親關系這一整個家的生命系統生成的“圓圈”之中,從中最終實現了從“親親”到“仁民”、從“愛有差等”到“眾生平等”這一人際關系的切換和轉型。
其三,一方面,這種愛的雙向回饋在父子之際沿著縱向時間軸線展開,使我們的生命生生不息通向其固有的無限性,另一方面,這種愛的雙向回饋又在兄弟之際沿著橫向空間軸線展開,使我們的生命光被四海得以永無止境地普遍擴充。故基于愛的雙向回饋的家際倫理以其既內在又超越、既具體又普遍、既生理又倫理,而成為一種真正克服了道德“二律背反”和忠實體現了人類“至善”的倫理。
最后,所有這一切,使得這種家際倫理學既不同于個體主義式的源于同一化、本質化知識話語的“他組織”的西方美德倫理學、規范倫理學,又不同于時興的社群主義化的非西方“角色倫理學”,因為后者雖然與家際倫理同樣重視人際之間的關系性、對話性,卻由于其倫理罔顧對有限生命的超越,并缺失人類德性的普遍性,而與中國傳統的家際倫理貌似相同,實則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