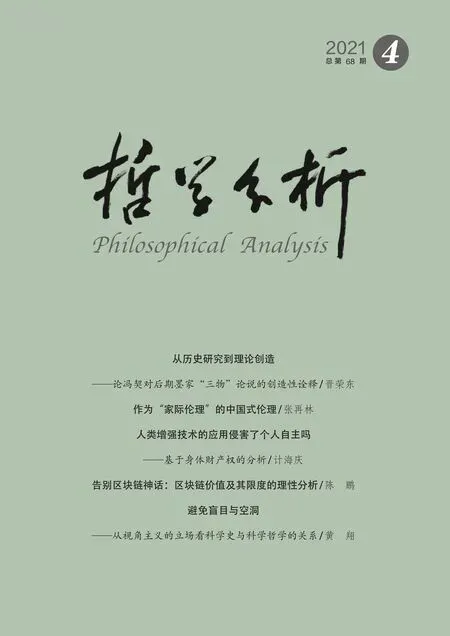避免盲目與空洞
——從視角主義的立場(chǎng)看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的關(guān)系
黃 翔
一、問題的緣起:從吉爾問題到加里森十問
起始于20 世紀(jì)60 年代英美科學(xué)哲學(xué)界中的歷史主義轉(zhuǎn)向的初衷是要警示規(guī)范性研究進(jìn)路避免與具體科學(xué)實(shí)踐相互脫節(jié)的危險(xiǎn)。它同時(shí)也在理論上為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之間提出相關(guān)性要求,十分生動(dòng)地表現(xiàn)在漢森(Norwood Russell Hanson)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沒有科學(xué)史的科學(xué)哲學(xué)是空洞的,沒有科學(xué)哲學(xué)的科學(xué)史是盲目的”這個(gè)著名的歷史主義洞見中。aNorwood Russell Hanson,“The Irrelevance of History of Science to Philosophy of Science”,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59,No.21,1962,p.574;Imre Lakatos,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Philosophical Papers,Vol.I,John Worral and Gregory Gurrie(e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102.歷史主義轉(zhuǎn)向與稍早在英美一些大學(xué)和研究機(jī)構(gòu)中出現(xiàn)的“科學(xué)歷史與哲學(xué)”(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HPS)研究方向一起試圖將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整合在一起的理想付諸現(xiàn)實(shí)。a美國(guó)從1958 年開始用“國(guó)家科學(xué)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支持HPS 研究項(xiàng)目,早期被該項(xiàng)目支持的科學(xué)哲學(xué)家包括Phillipp Frank,Adolf Grunbaum,Henry Margenau,Herbert Feigl,Ernan McMullin 等,科學(xué)史家包括Marshall Claggett,Cyril Stanley Smith,I.B.Cohen,Howard B.Adelmann,Robert E.Schofield 等(參見Margaret W.Rossiter,“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rogram at the Natiaonl Science Foundation”,Isis,Vol.75,No.1,1984,p.99)。1960 年,普林斯頓大學(xué)和印第安納大學(xué)開始開設(shè)HPS 專業(yè)。同時(shí),美國(guó)的科學(xué)史學(xué)會(huì)(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和科學(xué)哲學(xué)協(xié)會(huì)(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的年會(huì)也開始聯(lián)合舉辦。然而,無(wú)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shí)踐中,歷史主義洞見都遇到不少困難。在實(shí)踐中,HPS 的研究方向并不十分順利。盡管該研究方向產(chǎn)生了不少優(yōu)秀的研究成果以及史、哲兼優(yōu)的學(xué)者,但科學(xué)史家與科學(xué)哲學(xué)家們各自專注于自己的研究領(lǐng)域,相互之間疏于往來(lái)的情況仍然是常態(tài)。bSeymour Mauskopf and Tad Schmaltz(eds.),Integrat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roblems and Prospects,Dordrecht:Springer,2012,p.5.在理論上,無(wú)論是說(shuō)明科學(xué)史在哪種意義上為科學(xué)哲學(xué)的理論建設(sh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資源,從而使得科學(xué)哲學(xué)不再空洞,還是相反,去說(shuō)明科學(xué)哲學(xué)在哪種意義上為科學(xué)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論指導(dǎo),從而使得科學(xué)史得以避免盲目,兩者均非易事。
對(duì)于科學(xué)史是否以及如何能夠成為科學(xué)哲學(xué)的理論建設(shè)的資源,即如何避免科學(xué)哲學(xué)的空洞這個(gè)問題,科學(xué)哲學(xué)家吉爾(Ronald Giere)曾作出深入的分析,我們不妨將之稱為“吉爾問題”。cRonald Gie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Intimate Relationship or Marriage of Convenienc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24,No.3,1973,p.292;Ronald Giere,“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Thirty-Five Years Later”,in Seymour Mauskopf and Tad Schmaltz(eds.),Integrating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roblems and Prospects,pp.59—66.在他看來(lái),只有自然主義的科學(xué)哲學(xué)進(jìn)路才能解決這個(gè)問題。在稍早的一份研究中,筆者曾論證瓦托夫斯基(Marx Wartofsky)的歷史知識(shí)論作為一種自然主義的科學(xué)哲學(xué)進(jìn)路,可以被看作解決吉爾問題的一種成功的嘗試。d黃翔:《科學(xué)實(shí)踐與本體論歷史主義——以歷史知識(shí)論為例》,載《哲學(xué)分析》2020 年第4 期,第4—16 頁(yè)。除了瓦托夫斯基的理論,其他的一些歷史知識(shí)論進(jìn)路如Ian Hacking 的科學(xué)推理風(fēng)格理論、法國(guó)歷史知識(shí)論等,也可以被看作是對(duì)吉爾問題的回應(yīng)。
而對(duì)于科學(xué)哲學(xué)在哪種意義上為科學(xué)史的研究提供理論指導(dǎo),即如何避免科學(xué)史的盲目這個(gè)問題,可被看作吉爾問題的逆向問題。即使我們能夠成功地回應(yīng)吉爾問題,也不意味著就能夠解決其逆向問題。科學(xué)史界對(duì)科學(xué)哲學(xué)的抵觸理由與科學(xué)哲學(xué)界對(duì)科學(xué)史的抵觸理由有所不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來(lái)自兩個(gè)方面的考慮。首先,無(wú)論是邏輯經(jīng)驗(yàn)主義還是證偽主義的科學(xué)哲學(xué)都傾向于追求超越任何具體時(shí)空限制的普遍原則和真理,與科學(xué)史所探求的對(duì)具體歷史事件的理解在方法論層面上差異很大。許多科學(xué)史家認(rèn)為完全不受具體時(shí)空限制的真理是虛幻的和脫離實(shí)際的,而考察科學(xué)家們?nèi)绾芜M(jìn)行研究實(shí)踐才是客觀地理解科學(xué)。不難看出,持有這種態(tài)度的科學(xué)史家只能在科學(xué)哲學(xué)接受自然主義立場(chǎng)后才能接受與科學(xué)哲學(xué)的對(duì)話。其次,科學(xué)史家們會(huì)擔(dān)心科學(xué)哲學(xué)有可能帶來(lái)“輝格主義”(Whiggism)和“時(shí)代錯(cuò)亂”(anachronism)的后果。所謂“輝格主義”是指使用當(dāng)今科學(xué)的概念和標(biāo)準(zhǔn)來(lái)理解和評(píng)價(jià)昔日科學(xué)家們的工作的做法。a圍繞著輝格主義史學(xué)有很多討論,這里不多贅言。鮑勒(Bowler)和莫魯斯(Morus)給出了一個(gè)簡(jiǎn)潔而精確的刻畫:“在今日,任何把過(guò)去當(dāng)作一系列踏入今日的墊腳石并且堅(jiān)持今優(yōu)于古的史學(xué),可以被稱為‘輝格史學(xué)’”(Peter J.Bowler and Iwan Rhys Morus,Making Modern Science:A Historical Surve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p.2)。輝格主義科學(xué)史的一個(gè)目的是想說(shuō)明今日科學(xué)是如何歷史地形成的,然而,其做法卻很容易造成時(shí)代錯(cuò)亂而曲解真實(shí)的歷史事實(shí),因?yàn)榭茖W(xué)史中的許多科學(xué)家們并不具有今日科學(xué)的概念與表征,他們的研究目的也常常不是為了獲取被今日科學(xué)所接受的理論。科學(xué)史研究的一項(xiàng)基本要求是正確描述歷史事件,因而必須避免時(shí)代錯(cuò)亂的錯(cuò)誤。在一些科學(xué)史家看來(lái),科學(xué)哲學(xué)的對(duì)普遍性與規(guī)范性的要求常常是造成輝格主義和時(shí)代錯(cuò)亂的一個(gè)主要誘因。
然而,對(duì)輝格主義和時(shí)代錯(cuò)亂的防范并不成為科學(xué)史在理論上可以脫離科學(xué)哲學(xué)而不陷入盲目的論據(jù)。科學(xué)史家加里森(Peter Galison)指出,科學(xué)史在對(duì)科學(xué)發(fā)展過(guò)程的研究中,難以避免許多需要科學(xué)哲學(xué)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他列出了十個(gè)這樣的問題:
(G1)什么是與境(context)?無(wú)論是科學(xué)史還是科學(xué)哲學(xué),在研究過(guò)程中常常需要解釋其研究對(duì)象的產(chǎn)生和存在的與境。盡管科學(xué)哲學(xué)更加關(guān)注其研究對(duì)象的理論背景,而科學(xué)史家更多地將研究對(duì)象的政治、經(jīng)濟(jì)、意識(shí)形態(tài)背景當(dāng)作與境,然而,對(duì)于與境與研究對(duì)象之間的關(guān)系的理解,無(wú)論在發(fā)生論層面還是在本體論層面,都需要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共同提供說(shuō)明。
(G2)什么是“純科學(xué)”(pure science)?純科學(xué)是科學(xué)史中常用的概念,它代表一種科學(xué)的理想標(biāo)準(zhǔn),而這個(gè)標(biāo)準(zhǔn)隨著時(shí)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數(shù)學(xué)、物理、自然科學(xué)在不同的時(shí)代都曾被當(dāng)作純科學(xué)來(lái)看待。純科學(xué)的概念之所以重要,是因?yàn)樗俏覀兝斫饪茖W(xué)的一個(gè)基本概念,例如,我們用它來(lái)劃分“基礎(chǔ)科學(xué)”與“應(yīng)用科學(xué)”。對(duì)于純與不純的劃分也需要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共同提供說(shuō)明。
(G3)什么是研究對(duì)象?以往的科學(xué)史并不太關(guān)心如何確定研究對(duì)象的問題,因?yàn)榭茖W(xué)學(xué)科的劃分已經(jīng)自然地給出了頗為清晰的答案。然而,當(dāng)今的科學(xué)哲學(xué)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出發(fā),日益重視各種類型的科學(xué)實(shí)踐,并因此發(fā)展出許多不以學(xué)科劃分的科學(xué)史的研究對(duì)象,例如工具、概率、客觀性、觀察、建模、數(shù)據(jù)采集、思想實(shí)驗(yàn)等,試圖揭示這些研究對(duì)象的歷史發(fā)展軌跡。
(G4)怎么理解科學(xué)研究對(duì)象的本體論性質(zhì)?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科學(xué)研究的對(duì)象被看作是自然類,正確反映了自然本身的性質(zhì)差別。而在今日的科技發(fā)展中,新的人造研究對(duì)象不斷產(chǎn)生,從計(jì)算機(jī)模擬的虛擬對(duì)象到納米技術(shù),在其中很難嚴(yán)格地區(qū)分自然類與人造物。探討科學(xué)研究對(duì)象的本質(zhì)性特征的歷時(shí)性變化的歷史本體論,這一介于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之間研究領(lǐng)域,正在引發(fā)更多學(xué)者的注意。
(G5)科技應(yīng)該制造什么?既然人類制造人造物的能力日益精湛,已有能力改造甚至毀滅人類自身,科技制造什么的問題就上升為倫理問題,同時(shí)擺在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面前。
(G6)應(yīng)該制定什么樣的政策來(lái)對(duì)應(yīng)科技發(fā)展所帶來(lái)的文化、政治和道德風(fēng)險(xiǎn)?這個(gè)問題即是上個(gè)問題的延伸,也是政治學(xué)和科技政策的問題,涉及上至國(guó)家科技投入下至個(gè)人隱私保護(hù)等范圍極廣的問題域。
(G7)微觀史或案例研究能夠揭示什么?案例研究通過(guò)展示大量的細(xì)節(jié),增加我們對(duì)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實(shí)踐中具體事件的理解。實(shí)證主義者會(huì)認(rèn)為人們可以通過(guò)科學(xué)史案例歸納地得出對(duì)科學(xué)的一般性理解,但這種預(yù)設(shè)了普遍適用原則的看法,現(xiàn)在不再被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可。被多數(shù)學(xué)者所認(rèn)同的是,案例研究中的細(xì)節(jié)揭示了具體時(shí)間和空間下的事件如何與其他事件微妙地關(guān)聯(lián)或沖突的過(guò)程。案例研究所提供的這種理解到底建立在什么樣的說(shuō)明機(jī)制之上?它的有效性的界限在哪里?
(G8)科學(xué)實(shí)踐中哪些性質(zhì)具有一般性并且如何獲得一般性的?如果說(shuō)具體的科學(xué)實(shí)踐總是在特定的時(shí)間和空間中進(jìn)行的,科學(xué)實(shí)踐的目的卻并不局限于地方性,而總是在追求更為一般性的結(jié)果。科學(xué)家們總是試圖讓自己的研究結(jié)果被其他科學(xué)家們接受,并且應(yīng)用在更為廣泛的領(lǐng)域里。同時(shí),科學(xué)史中任何一個(gè)時(shí)間點(diǎn)上的科學(xué)知識(shí)無(wú)法完全反映在當(dāng)時(shí)的任何一個(gè)科學(xué)家的個(gè)人思想中,而必然具有集體性和社會(huì)性的特征以獲得其一般性。這種獲取一般性過(guò)程的機(jī)制是什么?
(G9)是否有可能使得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完全脫鉤?這個(gè)問題有兩個(gè)方面:首先,是否有可能在不使用任何哲學(xué)概念的情況下做科學(xué)史的工作?其次,是否可以在完全不涉及科學(xué)史或科學(xué)實(shí)踐的具體性質(zhì)的情況下做科學(xué)哲學(xué)工作,如建立結(jié)構(gòu)主義式的或弗雷格式的反心理主義邏輯—語(yǔ)義資源上的科學(xué)哲學(xué)研究?
(G10)什么是科學(xué)質(zhì)疑?質(zhì)疑是科學(xué)史研究難以避免的一個(gè)重要課題。科學(xué)家們?cè)谘芯窟^(guò)程中難免對(duì)實(shí)驗(yàn)數(shù)據(jù)或理論產(chǎn)生疑問,而面對(duì)不同觀點(diǎn)和理論時(shí)相互質(zhì)疑與討論也是科學(xué)實(shí)踐中一個(gè)重要的環(huán)節(jié)。疑問、質(zhì)疑以及相應(yīng)的爭(zhēng)論不僅是心理和社會(huì)性行為,也牽扯認(rèn)知與知識(shí)論問題。aPeter Galison,“Ten Problem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Isis,Vol.99,No.1,2008,pp.111—124.
以上十個(gè)問題是科學(xué)史研究中或多或少都要涉及的問題,而對(duì)這些問題的回應(yīng)也都難免需要哲學(xué)層面上的分析。b加里森承認(rèn)這十個(gè)問題并沒有涵蓋科學(xué)史需要科學(xué)哲學(xué)共同合作解決的所有問題,而只是其中一些較為重要的問題(Ibid.,p.112)。加里森以這種方式來(lái)回應(yīng)吉爾問題的逆向問題,即科學(xué)史研究在哪種意義上需要科學(xué)哲學(xué)的介入以避免盲目。加里森的回應(yīng)有兩個(gè)特點(diǎn)值得特別注意。首先,回應(yīng)提供了大量的科學(xué)史研究中的具體問題,而且這些涉及了方法論、本體論、價(jià)值論等不同層面上的問題相當(dāng)廣泛,綜合來(lái)看很有說(shuō)服力。反對(duì)科學(xué)哲學(xué)對(duì)科學(xué)史的相關(guān)性的立場(chǎng)不僅要論證問題(G9)中所說(shuō)的無(wú)需依賴哲學(xué)或科學(xué)哲學(xué)概念的純科學(xué)史的可能性,而且還要論證在獨(dú)立于科學(xué)哲學(xué)的情況下可以圓滿地回應(yīng)另外九個(gè)問題。不難看出其中的論證負(fù)擔(dān)是相當(dāng)大的。
其次,加里森并沒有給出科學(xué)哲學(xué)對(duì)科學(xué)史的相關(guān)性的一般性的論證,而只是給出了一些科學(xué)史需要科學(xué)哲學(xué)介入的問題域的例子。缺乏一般性的結(jié)構(gòu)或?qū)哟蔚脑虿糠值厥怯捎谑畣柗謩e涉及不同層面和不同種類的哲學(xué)問題,而問題的多樣性意味著哲學(xué)考量會(huì)以不同的方式介入科學(xué)史研究,因此,想要形成科學(xué)哲學(xué)對(duì)科學(xué)史的相關(guān)性的統(tǒng)一和一般性的刻畫頗為困難。當(dāng)然,缺乏一般性刻畫并不一定是加里森十問本身的致命缺陷,畢竟通過(guò)十問,加里森以歸納的方式展示了數(shù)量可觀的需要科學(xué)哲學(xué)參與的地方。然而,缺乏一般性的論證框架使得加里森的論證顯得零散雜亂,而且,如果能夠找到一種更為一般的論證框架,會(huì)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的關(guān)系。本文后兩節(jié)將論證,吉爾的視角主義理論以及分布式認(rèn)知的概念可以有效地為我們提供這里所需要的一般性框架。為此,我們先在下一節(jié)看一下什么是視角主義。
二、視角主義與分布式認(rèn)知
所謂“視角主義”(perspectivism),按照一般常識(shí)的理解,是指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lái)看待事物,從而對(duì)事物形成不同的看法。比如,使用同樣的透視原理,站在黃浦江擺渡碼頭和站在東方明珠塔上的觀景臺(tái)所看的黃浦江的景象是相當(dāng)不同的。這種常識(shí)性的視角主義在西方近代哲學(xué)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經(jīng)常被當(dāng)作關(guān)鍵性的隱喻。比如,萊布尼茨的單子便是從自己的視角來(lái)感受和反映周圍世界,因此,笛卡爾式的從上帝的全知全能的視角所給出的空間觀,在萊布尼茨看來(lái)并不能用來(lái)理解認(rèn)知資源有限的人類對(duì)空間的表征。aBas van Fraassen,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Paradoxes of Perspectiv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69.尼采則堅(jiān)持人類從知覺獲取的知識(shí)毫無(wú)例外地都是視角性的。bMatthew Meyer,Reading Nietzsche through the Ancients—An Analysis of Becoming,Perspectivism and the Principle of Non-Contradiction,Boston/Berlin:De Gruyter,2014,pp.198—201.
進(jìn)入21 世紀(jì)后,科學(xué)哲學(xué)領(lǐng)域也出現(xiàn)了不少視角主義理論。例如,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提出,由于科學(xué)觀察與測(cè)量是視角性的,因而建立在其上的結(jié)構(gòu)性表征也一定是視角性的。aBas van Fraassen,Scientific Representation:Paradoxes of Perspective.溫薩特(William C.Wimsatt)則認(rèn)為,擁有有限認(rèn)知資源的科學(xué)家們?cè)谔幚聿煌芯款I(lǐng)域的研究對(duì)象時(shí)常常使用局部適用的助勘式推理(heuristics)工具,而這些推理工具不可避免地?cái)y帶某種系統(tǒng)性偏差(bias),從而構(gòu)成了不同的研究視角。bWilliam C.Wimsatt,Re-Engineering Philosophy for Limited Beings—Piecewise Approximations to Reality,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吉爾則堅(jiān)持視角主義是理解科學(xué)的知識(shí)論和方法論維度的十分有效的本體論態(tài)度。cRonald N.Giere,Scientific Perspectivism,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這些理論的出發(fā)點(diǎn)和側(cè)重點(diǎn)并不相同,相互之間也存在著重要分歧。d例如,范·弗拉森不會(huì)同意吉爾的視角實(shí)在論的立場(chǎng)。然而,它們都堅(jiān)持科學(xué)實(shí)踐中的視角主義而不必落入極端相對(duì)主義和徹底的主觀主義。為了簡(jiǎn)便起見,本文采用吉爾的視角主義理論。在一篇討論文章中,美國(guó)得克薩斯大學(xué)的布朗(Matthew J.Brown)對(duì)吉爾的視角主義理論總結(jié)了六點(diǎn)基本特征:
(P1)日常和科學(xué)觀察,以及科學(xué)理論都是視角性的(perspectival)。
(P2)視角是人類的(包括生物的、認(rèn)知的和社會(huì)的)因素與世界之間的非對(duì)稱(asymmetric)的互動(dòng)。
(P3)視角是局部的(partial),擁有有限的正確性(limited accuracy)。
(P4)視角既不是客觀正確的(objectively correct),也不是唯一為真的(uniquely verdical)。
(P5)科學(xué)中對(duì)真理的判斷是相對(duì)于某一視角的,展示了該視角的適當(dāng)性(fittingness)。
(P6)科學(xué)表征不是“X 表征W”的二元關(guān)系(其中X 是表征項(xiàng),W 是被表征項(xiàng)),而是“S 為了目的P 使用X 表征W”的四元關(guān)系(其中S 是認(rèn)知主體,P 是某種行動(dòng)目的)。eMatthew J.Brown,“Models and Perspectives on Stage:Remarks on Giere’s Scientific Perspectiv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0,No.2,2009,p.214.
(P1)中所說(shuō)的觀察的視角性部分地由觀察者所處的空間位置所造成的視角差異所引起,部分地由觀察者的知覺器官的性能差異所造成。比如,人的視覺系統(tǒng)只能看到320 nm—780 nm 波長(zhǎng)范圍內(nèi)的光線,而無(wú)法看到超出此范圍的光線,如紅外線、紫外線,而有些動(dòng)物則可看到。再如,色盲的人無(wú)法看到非色盲的人看到的顏色。fRonald N.Giere,Scientific Perspectivism,pp.17—36.科學(xué)研究除了依賴直接的肉眼觀察外,更多地使用觀察工具和實(shí)驗(yàn)儀器。不同工具和儀器的工作原理和使用范圍不同,因而所獲得的觀察結(jié)果揭示了觀察對(duì)象的不同特征。比如,計(jì)算機(jī)斷層攝影即CT 與核磁共振MRI 現(xiàn)在已是醫(yī)學(xué)檢查常見的設(shè)備,前者使用X 射線探測(cè)身體部位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后者使用磁共振原理探測(cè)身體內(nèi)部的某些功能比如腦中血液循環(huán)功能等。aRonald N.Giere,Scientific Perspectivism,pp.49—57.在這個(gè)意義上,科學(xué)觀察都是視角性的。科學(xué)理論和模型之所以也是視角性的,是因?yàn)樗鼈兊慕?gòu)都是為了達(dá)成特定的認(rèn)知目的,其應(yīng)用范圍也是有限的,表征了世界的某些而不是全部的特征。它們就像人們?yōu)榱瞬煌瑢?shí)用目的而繪制的各種類型的地圖,可以正確地表征特定目的想要知道的某些信息,而忽略甚至扭曲其他相關(guān)信息。bIbid.,pp.71—80.
(P2)是說(shuō)視角性是人與世界的互動(dòng)過(guò)程中人這種認(rèn)知資源有限、卻又不斷發(fā)展新的認(rèn)知工具和手段的認(rèn)知能動(dòng)者在面向世界時(shí)的一種無(wú)法避免的局面,而視角性又只是人而非世界本身的特征。(P3)意味著視角主義不必是一種否定科學(xué)實(shí)在論的社會(huì)建構(gòu)論立場(chǎng)。從一個(gè)特定視角出發(fā)的認(rèn)知過(guò)程如果能夠被足夠的理由支持則可以獲取關(guān)于認(rèn)知對(duì)象的局部真理。對(duì)同一對(duì)象的其他視角的認(rèn)知不必導(dǎo)致極端的相對(duì)主義。不同視角之間可以相互比對(duì)、相互理解并形成對(duì)同一對(duì)象的更為深入的認(rèn)識(shí)。比如,醫(yī)生可以通過(guò)CT 和核磁共振這兩種不同視角拍下的片子,對(duì)生病部分的結(jié)構(gòu)和生理功能作出更為全面和更為可靠的判斷。(P4)否定了對(duì)普遍適用的合理性規(guī)則和萬(wàn)物理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的實(shí)在性和可能性。(P5)表明了視角主義的真理觀,即真理都是相對(duì)于某一視角的。以科學(xué)定律為例,視角主義認(rèn)為科學(xué)定律不是無(wú)條件的為真的判斷,而只是表征模型中嚴(yán)格為真的部分。cIbid.,pp.69—71.
(P6)中所堅(jiān)持的四元關(guān)系的表征概念將認(rèn)知主體S 和表征目的P 納入為表征的構(gòu)成性因素,強(qiáng)調(diào)了表征模型在建構(gòu)過(guò)程中由于實(shí)用目的和主體的認(rèn)知資源的不同而擁有不同的認(rèn)知視角的事實(shí)。從這一事實(shí)出發(fā),還可引出吉爾很強(qiáng)調(diào)但布朗未能列入的另一個(gè)視角主義的特征,即分布認(rèn)知的特征:
(P7)認(rèn)知科學(xué)中的分布認(rèn)知理論為視角主義提供了有力的認(rèn)知模型。dIbdi.,pp.96—116.
所謂“分布認(rèn)知”是指一個(gè)認(rèn)知過(guò)程由分布于大腦內(nèi)外的不同類型的認(rèn)知資源共同構(gòu)成。比如,認(rèn)知科學(xué)中的聯(lián)結(jié)主義認(rèn)為,大腦中的信息處理不是以神經(jīng)元之間的串行傳遞的方式進(jìn)行的,而是由分布于不同的神經(jīng)元組并行或同時(shí)處理的。再如,認(rèn)知科學(xué)家哈欽斯(Edwin Hutchins)對(duì)軍艦導(dǎo)航的認(rèn)知過(guò)程的著名研究表明,認(rèn)知個(gè)體只是復(fù)雜的航行認(rèn)知系統(tǒng)的一部分,無(wú)法單人獨(dú)立地完成導(dǎo)航認(rèn)知任務(wù)。導(dǎo)航認(rèn)知系統(tǒng)由分布于不同認(rèn)知個(gè)人、技能、工具、技術(shù)等認(rèn)知資源構(gòu)成,而社會(huì)和文化因素在整合各種分布認(rèn)知資源的過(guò)程中起到重要的調(diào)節(jié)作用。eEdwin Hutchins,Cognition in the Wild,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1995.在吉爾看來(lái),科學(xué)知識(shí)是通過(guò)各種不同的分布認(rèn)知系統(tǒng)而產(chǎn)生的。這些系統(tǒng)之所以不同,是因?yàn)樗鼈兏髯赃\(yùn)用了不同的物質(zhì)、技術(shù)和理論資源,從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視角。
三、視角主義與加里森十問
具有這七個(gè)特征的視角主義為我們?cè)谝粋€(gè)比加里森十問更具一般性的意義上來(lái)理解科學(xué)哲學(xué)與科學(xué)史的關(guān)系提供了有用的理論平臺(tái)。簡(jiǎn)單來(lái)說(shuō),雖然科學(xué)哲學(xué)與科學(xué)史可被看作在元層次上反思科學(xué)的兩種不同的研究視角,但它們也有共同關(guān)心的問題——例如加里森十問中的問題,因而需要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鑒,否則將難以獲得對(duì)科學(xué)更為深入、全面的理解。
首先,我們不妨先看一看為什么科學(xué)史、科學(xué)哲學(xué)可以被看成是反思科學(xué)的不同的認(rèn)知視角。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盡管研究的對(duì)象都是科學(xué),但各自關(guān)注科學(xué)的不同特征。科學(xué)史關(guān)注歷史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及其原因,科學(xué)哲學(xué)關(guān)注科學(xué)知識(shí)之所以可能的理由。兩者使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科學(xué)史強(qiáng)調(diào)對(duì)事件的正確描述和對(duì)相關(guān)原因的揭示,科學(xué)哲學(xué)則使用概念分析的手段厘清科學(xué)研究中的知識(shí)論和方法論規(guī)范性及其本體論基礎(chǔ)。因此,兩者很自然地分屬兩個(gè)不同學(xué)科,各有自己的研究傳統(tǒng)與研究團(tuán)隊(duì)。從吉爾的視角主義的理論看,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均滿足上述(P1)—(P7)的關(guān)系,即因?yàn)樗鼈兊难芯磕康牟煌⒎椒ǜ鳟悾罱K的表征成果各自揭示了科學(xué)的不同特性,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視角。
其次,我們?cè)谶@一節(jié)中從分布認(rèn)知的概念出發(fā),重點(diǎn)考察這兩種研究視角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鑒的可行性。平心而論,兩個(gè)學(xué)科中的學(xué)者們大多都會(huì)在理論上承認(rèn)最低限度地了解對(duì)方的研究對(duì)于本方的研究來(lái)說(shuō)會(huì)有所幫助,否則難以避免盲目與空洞。絕大多數(shù)科學(xué)哲學(xué)大家都熟稔科學(xué)發(fā)展的重要節(jié)點(diǎn),其中還有不少人是對(duì)某些科學(xué)史案例的資深研究專家;而科學(xué)史大家們也無(wú)不對(duì)所研究事件或人物的思想背景和哲學(xué)理解如數(shù)家珍。然而,在當(dāng)今的實(shí)踐中,科學(xué)史家與科學(xué)哲學(xué)家在如何借鑒對(duì)方的研究成果的問題上并未形成明顯共識(shí)。一方面,對(duì)一些科學(xué)哲學(xué)家們有意識(shí)或無(wú)意識(shí)地預(yù)設(shè)發(fā)現(xiàn)與境(context of discovery)與辯護(hù)與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間的二分,并把科學(xué)史歸于前者的做法,科學(xué)史家們難以茍同,認(rèn)為這種做法所得出的“哲學(xué)結(jié)論”不可避免地誤解歷史事實(shí)。另一方面,科學(xué)哲學(xué)家們也會(huì)對(duì)一些史學(xué)家所堅(jiān)持的純描述性的敘事如何與哲學(xué)所關(guān)注的規(guī)范性問題相關(guān)聯(lián)感到困惑。如何在科學(xué)史家和科學(xué)哲學(xué)家之間找到共識(shí),正是吉爾與加里森等學(xué)者想要解決的問題。
為了理解視角主義如何有助于解決這個(gè)問題,我們需要更進(jìn)一步地探討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這兩種認(rèn)知視角是如何形成其視角性表征的。一般來(lái)說(shuō),按照(P6)中所說(shuō)的四元視角表征概念中的表征者S 和表征目的P 的不同,我們可以把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成果分成以下三個(gè)種類:(A)純科學(xué)史,即不依賴于科學(xué)哲學(xué)的科學(xué)史;(B)純科學(xué)哲學(xué),不依賴于科學(xué)史的科學(xué)哲學(xué);(C)科學(xué)史+科學(xué)哲學(xué)(即依賴于科學(xué)史的科學(xué)哲學(xué)或依賴于科學(xué)哲學(xué)的科學(xué) 史)。
從表面上看,第一節(jié)中提到的反對(duì)輝格主義的史學(xué)家們的理想成果應(yīng)該屬于(A)類,在其中,任何發(fā)生在研究對(duì)象之后的科學(xué)和哲學(xué)思想都不應(yīng)該被引入到研究中。然而,現(xiàn)在越來(lái)越多的學(xué)者意識(shí)到這種反輝格主義立場(chǎng)過(guò)于理想化,很難在絕大多數(shù)的科學(xué)史研究中被嚴(yán)格地執(zhí)行。a較為早期的質(zhì)疑反輝格主義科學(xué)史的例子有A.Ruppert Hall,“On Whiggism”,History of Science,Vol.XXI,1983,pp.45—59;Adrain Wilson and T.G.Ashplant,“Whig History and Present-Centered History”,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XXXI,1988,pp.1—16;較 為 近 期 的 例 子 包 括Nick Tosh,“Anachronism and Retrospective Explanation:In Defence of a Present-Centred History of Science”,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4,2003,pp.647—659;Laurent Loison,“Forms of Presentism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Rethinking the Project of Historical Epistemolog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0,2016,pp.29—37.一方面,今日的科學(xué)和哲學(xué)思想為理解科學(xué)變化、發(fā)展乃至進(jìn)步的歷史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資源。當(dāng)今物理學(xué)史很少可以脫離日后的牛頓理論來(lái)理解開普勒的天文學(xué),而沃森—克里克的分子遺傳學(xué)也常常在生物學(xué)史中被用來(lái)幫助理解孟德爾的經(jīng)典遺傳學(xué)的合理性。bDavid Alvargonzález,“I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ssentially Whiggish?”,History of Science,Vol.LI,2013,p.88.另一方面,在方法論層面上,科學(xué)史研究需要給出兩個(gè)層面的解釋:一個(gè)是解釋研究對(duì)象中的當(dāng)事人自己對(duì)事物的看法,例如,解釋牛頓自己的看法;另一個(gè)是站在觀察者的角度上解釋研究事件的前因后果,例如,解釋引起牛頓這樣認(rèn)為的原因以及牛頓的看法對(duì)他人的影響。這后一種解釋常常難以避免使用當(dāng)今的科學(xué)和哲學(xué)概念。cNick Jardine,“Etics and Emics(Not to Mention Anemics and Emetics)in the History of the Sciences”,History of Science,Vol.XLII,2004,pp.261—278.然而,對(duì)反輝格主義立場(chǎng)的質(zhì)疑并不意味著科學(xué)史無(wú)法進(jìn)行(A)類研究,而只意味這類研究的范圍實(shí)際上要比多數(shù)反輝格主義史學(xué)家認(rèn)為的狹窄很多。這類研究可以包括對(duì)前人成果的發(fā)掘和整理,比如達(dá)爾文的各種手稿的整理和出版、近代翻譯西方科技書籍的目錄整理和文獻(xiàn)翻印等,也可以包括對(duì)與科技相關(guān)的各類事件的編年式的整理——比如英國(guó)皇家學(xué)會(huì)成員的歷年變動(dòng)記錄、墨海書館的運(yùn)作和管理情況等。這些工作涉及基本資料的發(fā)掘與積累,無(wú)疑是科學(xué)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而其工作過(guò)程并不一定需要參考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成果,甚至無(wú)需以當(dāng)今科學(xué)和哲學(xué)的概念為標(biāo)準(zhǔn)。盡管這種工作未能給出對(duì)研究對(duì)象深入的理解,但畢竟為科學(xué)史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起點(diǎn)。
20 世紀(jì)上半葉堅(jiān)持發(fā)現(xiàn)與境與辯護(hù)與境二分的科學(xué)哲學(xué)大多屬于(B)類。20世紀(jì)下半葉歷史主義轉(zhuǎn)向在揭示了這種研究很容易造成脫離具體科學(xué)實(shí)踐而淪入空想的危險(xiǎn)的同時(shí),也質(zhì)疑了發(fā)現(xiàn)與境與辯護(hù)與境二分的普遍性和合法性。然而,對(duì)此二分的質(zhì)疑乃至揚(yáng)棄并不意味著對(duì)(B)類工作的合法性的否定。科學(xué)哲學(xué)對(duì)與科學(xué)相關(guān)的本體論、知識(shí)論和方法論的理論性概念(如推理、說(shuō)明、因果性、傾向性等)的分析與技術(shù)層面上的探討,仍然形成了對(duì)理解科學(xué)的基本特征的一種重要的反思視角,有其不可否認(rèn)的合法性。加里森在其第九個(gè)問題(G9)中所提出的結(jié)構(gòu)主義式的或建立在弗雷格式的邏輯—語(yǔ)義資源上的科學(xué)哲學(xué)研究,對(duì)于特定的研究任務(wù)來(lái)說(shuō)有其技術(shù)性和工具性的意義。實(shí)際上,上述對(duì)(A)(B)兩類研究視角的合法性的分析可以被看作視角主義對(duì)(G9)的回應(yīng):視角主義承認(rèn)不依賴科學(xué)哲學(xué)的科學(xué)史和不依賴科學(xué)史的科學(xué)哲學(xué)在特定的研究任務(wù)中具有其合法性和可行性,盡管它們并不涵蓋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的所有領(lǐng)域。
我們所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是(C)類研究成果,這里有兩點(diǎn)值得特別注意。首先,(C)正是吉爾問題和加里森十問所要論證其合法性的研究領(lǐng)域。對(duì)吉爾問題的回答需要論證為什么一部分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依賴于科學(xué)史。加里森提出的十個(gè)問題試圖展示一些科學(xué)史研究中所遇到的問題依賴于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其次,從視角主義的觀點(diǎn)看,由于(A)和(B)分別形成了兩個(gè)在元層次上反思科學(xué)的不同視角,(C)的可行性實(shí)際上必須建立在兩個(gè)視角之間成功的相互交流與合作之上。在這個(gè)問題上,(P7)中的分布式認(rèn)知起到了關(guān)鍵作用,它要求我們說(shuō)明科學(xué)哲學(xué)和科學(xué)史這兩個(gè)研究和認(rèn)知視角是如何部分地分布于對(duì)方的研究之上。對(duì)吉爾問題的回答要求我們合理地說(shuō)明科學(xué)哲學(xué)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與科學(xué)史合作以及如何合作。拉卡托斯、勞丹(Larry Laudan)和夏皮爾(Dudley Shapere)等人提出的內(nèi)在主義科學(xué)史觀是一種說(shuō)明方式。根據(jù)這種觀點(diǎn),科學(xué)史為科學(xué)哲學(xué)提出的合理性或方法論原則提供經(jīng)驗(yàn)證據(jù),因而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部分地分布于科學(xué)史研究中。然而,內(nèi)在主義科學(xué)史觀遇到許多質(zhì)疑,比如,它所預(yù)設(shè)的內(nèi)在史和外在史的二分難以成立,它所給出支持科學(xué)哲學(xué)的例子常常對(duì)歷史事實(shí)作出過(guò)于簡(jiǎn)單化甚至扭曲的解釋等。aSteve Fuller,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2nd edition,New York,London:The Guilford Press,2005,pp.33—47.本文第一節(jié)曾提到的歷史知識(shí)論可被看作一種更為可行的對(duì)吉爾問題的回應(yīng)。歷史知識(shí)論試圖通過(guò)對(duì)科學(xué)實(shí)踐中的知識(shí)論和方法論規(guī)范的歷史發(fā)展來(lái)理解科學(xué)知識(shí)的規(guī)范性特征,因而其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分布于科學(xué)史中。b除了前注提到的拙文外,對(duì)歷史知識(shí)論基本觀點(diǎn)的介紹可參見Uljana Feest and Thomas Sturm,“What(Good)is Historical Epistemology?”,Erkenntnis,Vol.75,2011,pp.285—302;Hans-J?rg Rheinberger,On Historicizing Epistemolgy—An Essay,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與此類似,加里森十問展示了對(duì)這十個(gè)問題的回應(yīng)不可避免地要部分地分布于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中,同時(shí)也形成了對(duì)(C)領(lǐng)域的合法性的支持。在第一節(jié)中我們?cè)f(shuō)過(guò),加里森十問顯得零散并缺乏一般性的結(jié)構(gòu)或?qū)哟巍囊暯侵髁x的觀點(diǎn)看,缺乏一般性的一個(gè)重要原因是科學(xué)史因其不同的研究目的P 會(huì)形成不同種類的表征成果,這就造成了科學(xué)史會(huì)以不同的方式分布于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中。科學(xué)史的不同目的首先展現(xiàn)在它所針對(duì)的不同讀者群。我們不妨簡(jiǎn)單地考察以下三類讀者群。
第一,針對(duì)普通大眾的科學(xué)史有科學(xué)傳播和科學(xué)普及的功能。一般來(lái)說(shuō),這種讀物難以避免使用今日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回顧科學(xué)的發(fā)展過(guò)程。以幫助讀者了解并接受科學(xué)為目的的科學(xué)史常常會(huì)正面弘揚(yáng)科學(xué)精神,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的客觀性與合理性;而以促進(jìn)讀者用客觀和積極的態(tài)度參與對(duì)科學(xué)和技術(shù)的公共反思的科學(xué)史會(huì)更加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技術(shù)的社會(huì)性影響,以及科技實(shí)踐與決策中的風(fēng)險(xiǎn)性和不確定性。不難看出,這種科學(xué)史或多或少地涉及(G5)和(G6)中所關(guān)注的科技應(yīng)該制造什么以及如何制定合適的科技政策的問題。
第二,一些科學(xué)史以培養(yǎng)某一學(xué)科的專業(yè)人才為目的,它的讀者群是有志于本學(xué)科研究的初學(xué)者或?qū)Ρ緦W(xué)科感興趣的其他專業(yè)的學(xué)者。比如,李約瑟的《胚胎學(xué)史》原本是他的《化學(xué)胚胎學(xué)》一書的前180 頁(yè)的內(nèi)容,其寫作目的就是要讓日后從事胚胎學(xué)研究的學(xué)者知曉本學(xué)科所討論的問題的來(lái)龍去脈。aJoseph Needham,A History of Embryology,New York:Abelard-Schuman,1959.這種科學(xué)史不可避免地涉及了(G1)(G2)(G3)和(G4)中的問題。它從特定的學(xué)科為出發(fā)點(diǎn)界定了什么是本學(xué)科研究的與境和研究對(duì)象,對(duì)象的相關(guān)性質(zhì)來(lái)自對(duì)象本身還是來(lái)自研究者的概念系統(tǒng),以及對(duì)本學(xué)科來(lái)說(shuō)什么是基礎(chǔ)性問題等。由于這些問題涉及科學(xué)哲學(xué)和一般性哲學(xué)理解,作者對(duì)這些問題的回應(yīng)不可避免地要分布于科學(xué)哲學(xué)中。
第三,學(xué)術(shù)性要求最高的科學(xué)史以專業(yè)內(nèi)同行學(xué)者為讀者群。科學(xué)史專業(yè)研究當(dāng)然包括除了上述(A)類研究中的原始資料的發(fā)掘和整理的基礎(chǔ)性工作,但這類研究不必依賴科學(xué)哲學(xué)。科學(xué)史專業(yè)研究更重要的工作是給出科學(xué)歷史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和變化趨勢(shì)的因果說(shuō)明。引起科學(xué)發(fā)展和變化的因素既有理論、技術(shù)、物質(zhì)條件因素,也有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和文化因素,因此,加里森十問中的許多問題都會(huì)在這類研究過(guò)程中出現(xiàn)。比如,對(duì)科學(xué)歷史事件發(fā)生和變化的與境的理解牽扯(G1);又如,新的科學(xué)儀器和理論的發(fā)展常常會(huì)拓展新的研究領(lǐng)域并引入了新的研究對(duì)象,這就涉及(G3)和(G4);再如,許多理論的變化是由出自不同理由的質(zhì)疑所引起的,這又涉及(G10)。
除了不同讀者群,科學(xué)史撰寫方式也展現(xiàn)了不同研究目的所引起的不同表征結(jié)果。吳以義在其構(gòu)思精巧的新著中,展示了蔚為大觀的多種科學(xué)史寫法,如史論、編年史、通史、斷代史、列傳、專門史或?qū)n}研究、通俗史、前規(guī)范時(shí)代史、技術(shù)史、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史等。a吳以義:《什么是科學(xué)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0 年版。這種研究和寫作方式上的多樣性同樣與加里森十問中的問題密切相關(guān)。以之前未曾提及的(G7)和(G8)為例。科學(xué)史的多樣性意味著具體案例研究,即微觀史與通史或斷代史等更為宏觀的歷史研究,同樣是必要的,它們各自揭示了科學(xué)的不同特征,特別是具體細(xì)節(jié)與一般性特征之間的張力和相互依賴的辯證關(guān)系。正是因?yàn)榭茖W(xué)史的多重寫作方式,宏觀史及其試圖揭示的科學(xué)發(fā)展的一般性特征會(huì)被要求不能與微觀史所展示的科學(xué)實(shí)踐的具體特征相沖突,與此同時(shí),案例研究所給出的科學(xué)實(shí)踐的具體細(xì)節(jié)只有在更為一般性的理論和概念的背景下才能給我們提供更為深入的理解。實(shí)際上,科學(xué)史寫作的多元性同時(shí)也意味著除了加里森十問外,還會(huì)有其他科學(xué)史的問題需要分布到科學(xué)哲學(xué)的研究中才能獲得答案,例如,技術(shù)史與科學(xué)史之間的關(guān)系需要我們反思技術(shù)與科學(xué)之間的本體論關(guān)系,前規(guī)范時(shí)代史和中國(guó)古代科學(xué)史需要我們理解西方近代科學(xué)與非西方、非近代的其他種類的“科學(xué)”之間的本體論和方法論上的區(qū)別等。
四、結(jié)語(yǔ)
以上討論表明,視角主義為我們理解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提供了十分有用的理論平臺(tái)。首先,作為兩種在元層面上反思科學(xué)的認(rèn)知視角,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有其各自獨(dú)立存在的領(lǐng)域,即(A)與(B)。然而,科學(xué)史和科學(xué)哲學(xué)想要深入地理解科學(xué),就需要走出各自的領(lǐng)域,否則將難以避免盲目與空洞。(C)是科學(xué)史與科學(xué)哲學(xué)這兩種認(rèn)知視角相互交流和相互合作的領(lǐng)域,吉爾問題和加里森十問所關(guān)注的焦點(diǎn)就在于揭示這個(gè)領(lǐng)域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吉爾的視角主義理論堅(jiān)持領(lǐng)域(C)的建構(gòu)與運(yùn)作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分布式認(rèn)知的過(guò)程,在其中持有不同認(rèn)知目的研究者以不同的方式來(lái)進(jìn)行分布式認(rèn)知的實(shí)踐。這就為看上去頗為零散的加里森十問提供了更為一般性的理 解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