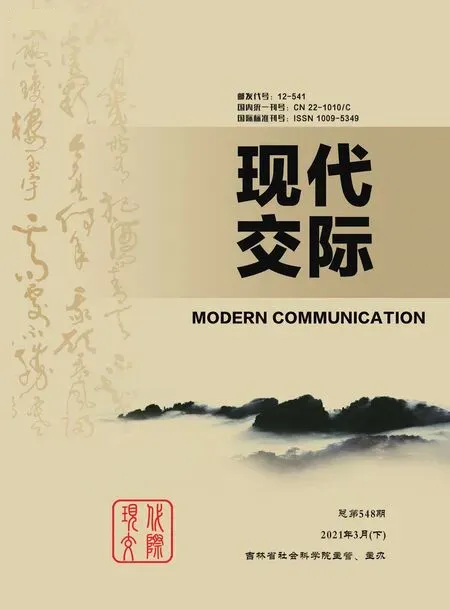藝術人類學視角的東北口傳藝術研究
——以滿族說部為例
邱振博 許冠華
(吉林藝術學院東北民間藝術研究中心 吉林 長春 130000)
口傳藝術,是東北民間廣為流傳、影響深遠的一種“活態藝術”,作為東北口傳藝術中最具代表性的系列作品,“滿族說部”更是飽受贊譽,富育光先生稱其為“北方民族的百科全書”,米哈伊洛維奇甚至將其中有的作品譽為“美不勝收的史詩”和“滿族的《奧德賽》”。[1]本文通過采用藝術人類學從“藝術周邊”看“藝術中心”的策略,對東北口傳藝術滿族說部的歷史淵源、文化脈絡等方面進行發掘,深刻地理解其民族審美心理及藝術呈現特征,為東北更多“活態藝術”的研究提供新的突破點。
一、滿族說部的歷史淵源及存續現狀
1.滿族說部的歷史起源
滿族說部的歷史淵源可上溯到遠古時期。縱觀歷史,在滿文出現之前,滿族先民沒有統一流傳的文字。據漢文獻記載,肅慎一族未創制本族文字。大多數先民多采用結繩記事、刻木記事等原始的方式記錄事件。女真雖有完顏希尹創字,但由于金朝滅亡,加之造字規則煩瑣,存在著書寫不便、難于記憶等缺點,至明正統十年(1445)后,便逐漸被廢棄不用。[2]但所幸滿族先民所使用的語言皆系一脈相承的滿—通古斯語族,這也就為滿族文化的以口頭講述或說唱方式的傳承奠定了基礎。這些口口相傳的神話、家史、英雄傳,便是滿族說部的歷史起源。
2.滿族說部的概念發展
自1986年富育光先生正式提出“滿族說部”這一概念,至今已有三十余載,在發掘整理“滿族說部”作品的同時,其概念范疇也在逐漸拓展豐富。從最早作為滿族民間文學出現,到1999年“獨立情節、自成完整結構體系、內容渾宏”這三點滿族說部藝術核心特質的提出,再到2011年明確其為“以神話、傳說、民間故事、史詩、長篇敘事詩等方式被民眾保留下來,散韻結合的綜合性口頭藝術”[3]可以看出,“滿族說部”這一概念已經完成了從田野中來再到田野中去的積淀,也就是說,對其概念的定義,已經由最初遺存的傳統語言藝術,進化為著眼其萌生、傳承、發展的“活態藝術”,在如今“非遺時代”對“活態藝術”的研究熱潮下,無疑為滿族說部開辟了藝術人類學這一嶄新的研究視野,而針對滿族說部的藝術人類學研究,也會為東北地域文化的深度發掘帶來新的契機。
3.滿族說部的存續現狀
1981年金啟孮先生赴黑龍江省富裕縣三家子地區展開田野考察。雖彼時“滿族說部”的概念尚未被正式提出,但金啟孮先生所發掘的故事中,由總穆昆達(即部族頭領)在祭祀中講述的家族史,便可視為滿族說部的前身。在明確滿族說部的概念之后,大量的滿族口傳故事被搜集整理,截至2018年,已有54部、2000多萬字的滿族說部作品整理問世。但是,由于滿族說部講說與傳承人多系年長者,其過世即意味著失傳。如吉林烏拉街滿族鎮舊街村滿族著名民俗專家趙文金老人因病去世,使吉林烏拉街打牲衙門傳承二百余載的滿族說部《鰉魚貢傳奇》未能搶救下來[4],故對于滿族說部的保護與傳承仍不可懈怠。
二、滿族說部的文化脈絡
1.萬物有靈——原始信仰的生發土壤
從精神文化角度來看,對滿族及其先民影響頗深的便是古老且神秘的原始信仰——薩滿。神話是原始信仰誕生的搖籃,更是信仰原始的表現形式,這一點在滿族說部神話故事的內容中,都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以滿族說部中的代表作品《天宮大戰》為例,其為原始創世神話,即滿族說部中神話故事的起源,更是滿族原始信仰的源泉所在。《天宮大戰》中所描繪的造人、創世景象,皆反映出滿族及其先民精神文化中萬物有靈、祖先崇拜等有關原始薩滿信仰的萌芽;而在滿族說部傳承的過程中,神話故事隨著原始信仰的進一步發展,逐漸成為宗教禮儀的法典和祭祀中講古、說史的頌唱活動,如《烏布西奔媽媽》在黑龍江和吉林琿春一帶多以《媽媽墳傳說》《娘娘洞古曲》《祭媽媽調》等講述與詠唱形式流傳著,并與祖籍海東的滿族諸姓薩滿《祭媽媽神》的祭禮相互融合。[5]綜上所述,滿族說部中的神話故事深刻地影響著滿族精神文化的發展,為其內涵不斷豐富提供不竭活力。
2.漁獵農耕——生產生活的真實還原
物質決定意識,漁獵游牧的生產模式,亦決定了滿族說部的內容。首先在滿族說部的內容上,有許多說部故事都對漁獵生活有著高度的還原。如《東海沉冤錄》中記述:“樹林里的野獸多,水里的魚也多,多到一瓢可以舀上來十幾條。”這樣的自然環境,即決定了滿族先民的漁獵生活。《蘇木媽媽》中記述的獵達大會,這場一年一度的大會是為了選舉出部落中獵手的頭目,即獵達。因為基于當時的漁獵生產,部落需要一位勇猛的獵手,帶領族人狩獵,保障部族的生活;同時,這位獵達更是部落的守衛者,保護部落不受猛獸和外族的襲擾。因此,這場大會備受部族重視,故事有云:“九十歲的老瑪發啊,手握長長的大布勒,連連地吹了三響。唐闊羅哈喇,愛曼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薩滿們,敲著熊皮鼓在助威。”由此可見,漁獵是部落的立身之本。除去漁獵,滿族說部中還有關于滿族先民游牧與農業發展的記述,《扈倫傳奇》中記錄的葉赫一部,便是一個游牧部落;《東海沉冤錄》中“朱棣、娟娟等人走進一座小泥屋,見里面放著女真人自己造的石磨,用來碾米磨面”。可見,在滿族先民部落中,農耕取得了一定的發展。
3.騎射征戰——體制變革的歷史紀實
滿族說部對滿族社會體制的變遷,做出了忠實的反映和記錄。在神話故事中《天宮大戰》中,女神阿布卡赫赫與惡神耶路里斗爭、阿布卡赫赫被男性神阿布卡恩都哩取代,都在反映著滿族先民在斗爭中由母系氏族社會過渡到了父系氏族社會;《女真譜評》提到,完顏一部在征戰中完善了“猛安”制,國家的雛形便誕生了;但是,隨著朝代的更迭,滿族先民從統治階級淪為了被統治的民族,戰亂使得人口銳減,社會制度也急速倒退,歌謠《半拉哈的土地》有云:“半拉哈的土地,半拉哈的江河,我愛你十年整了,我守你十年整了,哈番帶我們離開,像割我們的肉,像剜我們的心,跪拜一次,向你永別。”在這種場景下,滿族先民回歸原始社會,母系權力再度占據上風,原始部落由女王掌權,女王擁有至高權力。而在《東海窩集傳》中,父系與母系權利的斗爭再度上演,其開篇就提到烏神闊瑪發與佛赫媽媽有關于男權與女權的論戰,其后在丹楚集中力量推翻女王時,更是付出了血的代價,最終實現了母權向父權轉變的歷程。綜上所述,滿族說部內容源自歷史變遷,但其所蘊藏的思想內涵卻直指社會制度的變革,真實地反映了滿族及其先民的制度文化發展之路。
三、滿族說部的藝術特征
1.民族性與時代性
首先滿族說部藝術萌發于以滿族為核心的北方民族,其本身內容與內涵都脫胎自滿族的文化生活,在藝術形成的過程中,更是被打上了獨屬于滿族的獨特烙印,如《天宮大戰》《西林安班瑪發》《尼山薩滿》等神話作品,是對滿族原始薩滿信仰的反映;《女真譜評》《東海窩集傳》《東海沉冤錄》《薩大人傳》等家傳故事和英雄傳作品,是對滿族獨特的漁獵生活及社會發展變遷的記錄。
滿族說部本身內容也在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補充,不同時代,所孕育的作品風格與題材也不盡相同。如《天宮大戰》屬于原始時期生產力低下環境中產生的作品,著力突出原始信仰的至高無上,而《烏布西奔媽媽》《恩切布庫》《西林安班瑪發》等史詩作品,是在生產力水平、思維觀念、意識達到了一定發展水平條件下產生的。如果生產力水平過低,也產生不了史詩,因為史詩是民間文學集合的產物,沒有一定的民間文化素養的培養和民間文學作品的積累是產生不了這樣的鴻篇巨制的;[6]《薩大人傳》《碧血龍江傳》則講述的是近代前夜及近代對于外來入侵的抵抗與斗爭。因此,在滿族說部藝術萌發的過程中,最為突出的特征便是民族性與時代性。
2.間接性與廣闊性
滿族說部中夸張的語言描述,可以引發讀者無限的聯想與想象,不同的受眾,對于滿族說部中描繪的宏大宇宙,及各種光怪陸離的神魔形象,都有著自己的理解與具象化,這一點在無數以滿族說部為原型進行創作的東北民間藝術中有著極其鮮明的呈現。如針對滿族說部中的諸多女神形象,關氏滿族剪紙傳承人關云德老師的作品就更加充滿野性,著力對如“鷹爪”“鹿角”“馬蹄”等具有動物特征的造型進行突出刻畫,而東遼剪紙中的女神形象則盡可能地突出女性的柔美,將女神那種超然不凡、高雅輕靈的氣質作為表現的重點。通過這些藝術創作我們不難發現,民間藝術家們對于形象的不同理解,皆源自與滿族說部語言的間接性。
滿族說部的語言,亦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其構筑的宏大神話宇宙與記錄史實的現實宇宙都有著極其龐大的容量。從《天宮大戰》到《恩切布庫》《西林安班瑪發》《烏布西奔媽媽》,其情節一脈相承,從創世女神到被派下凡間充當薩滿的女神,其用語言構建的神話宇宙是延續的,是不斷發展的。而從《紅羅女三打契丹》,到《女真譜評》,到《東海沉冤錄》《東海窩集傳》,再到《薩大人傳》《碧血龍江傳》,則可以視為滿族及其先民的發展傳承的紀實文學,其從唐渤海國,到遼金,再到明清,形成了一個較為完整的歷史時空。同時,滿族說部的廣闊性更表現在它不僅能描繪外部世界,而且能夠深入思想內涵,直接揭示歷史發展與社會演進的本質,如神話故事中蘊含著母系與父系的斗爭、人與自然的斗爭,家傳史和英雄傳中蘊含著古代社會民族內部矛盾、近代社會中華民族與外部的矛盾等。
3.通俗性和口傳性
滿族說部在當代的呈現中,逐漸褪去了一些儀式化,具有了極強的通俗性。滿族說部的藝術呈現多是一種貼近生活的通俗化傳達,其使用口語化的措辭、方言中的詞匯,將滿族說部的內容聲情并茂呈現于田間、山野、村舍、炕頭。如口語化的表達沒有文學表達的華麗辭藻,一般簡單直接,更多時候會使用“了”“呢”“吧”“呀”“么”等語氣助詞,以實現語言中情感的傳遞;同時,更多獨屬于地方的特色的詞匯,也在講述的過程中被大量的應用,如“整”“膈應”“麻利”“扒瞎”等動詞、形容詞進一步拉近了與滿族說部欣賞者的距離。
而在傳承中,“滿族說部”多采用口傳心授的方式。其內容主要依靠記憶,通過家族親屬的世代相傳,以及生產生活中口口相傳,形成了廣泛且深遠的影響。在這種傳承的過程中,由于記憶的模糊,口音不同,以及主觀對故事的理解的不同,不同區域有著不同名稱,但情節大相徑庭的滿族說部故事,如《尼山薩滿》又叫《音姜薩滿》《陰間薩滿》,這些都是滿族說部在傳承中口傳性的體現。
四、結語
通過對滿族說部文化土壤及活態傳承過程的研究,不難發現,滿族說部不僅僅是根植于東北地區的原生態藝術,更是一個承載了民族史志與地域文化的巨大寶藏。對這個寶藏的發掘,不僅僅是對于東北口傳藝術的傳承與發展,也是對東北歷史沿革的追溯,還是對東北文化形象的重塑,更是對中華民族精神內涵的豐富。
在如今“非遺時代”對“活態藝術”的研究熱潮下,從藝術人類學視角出發,對民間的“活態藝術”展開研究,已經成為一種時代趨勢。在這種趨勢的引領下,越來越多的學者走出了書齋,將關注的重點轉移到了田野中去。但是,藝術人類學的研究,仍需要緊跟時代發展的步伐,這就要求研究者必須與時俱進,不僅要對早先的田野調查資料進行深度分析,尋找構建“藝術民族志”所需要的元素,還要繼續推進田野考察的步伐,以更加專業的視角和理論體系,對東北地區更多的“活態藝術”進行發掘和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