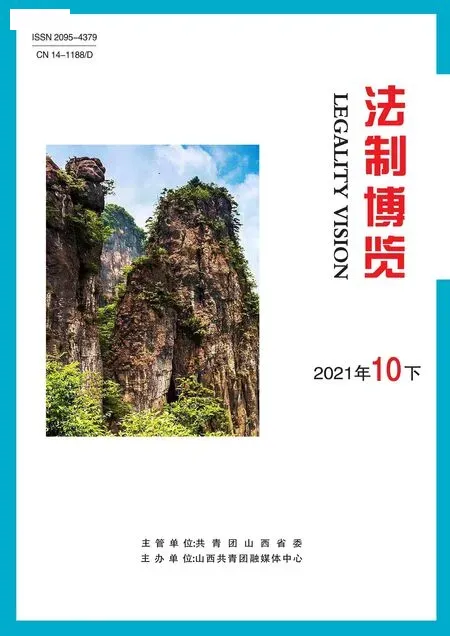民商法中連帶責任問題研究
劉 雪
(吉林財經大學,吉林 長春 130000)
在民商法體系中,連帶責任是至關重要的制度體系之一,其最主要目標在于對受害人進行更加全面的補償和幫助。通過民商法的連帶責任能夠追究當事人法律責任,同時也能給債權人提供更加健全的權益保障,但是受到民商法連帶責任本身的影響,在連帶責任認定和審理過程中仍舊存在一些問題,因此本文針對民商法中連帶責任進行研究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一、民商法中的連帶責任概述
在我國現有法治體系中連帶責任出現及發展的時間較長,例如,先秦時期的商鞅變法已經實施了“連坐制度”,這也是連帶責任的體現之一。先秦時期商鞅變法中提出的“連坐制度”,主要目的是解決當時社會環境之下所頻頻發生的形勢與財務糾紛,即使當事人本人并沒有參與犯罪,但是也會因為與犯罪者存在一定的聯系而受到牽連,在實施過程中連坐制度異常嚴格,能夠對各類犯罪行為進行強有力的威懾[1]。
社會發展至今日,連帶責任與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系,這也導致了對現有法律的需求,同樣也需要做出適當的調整,連帶責任的表面意思在于二者之間的關系,在民商法的法律體系中,更加側重于有過錯方和無過錯方的共同承擔責任,如果存在多主體責任劃分不明的情況,每一個參與的糾紛中的主體都有可能承擔賠償責任。由此,我們可以得知,在我國現行的民商法中,連帶責任能夠更加清晰、有效的分別風險因素,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至關重要的一點在于民商法的連帶責任能夠對各類侵犯他人權益的風險進行評估和分析,以保障權益受到損害一方的合法權益和救濟效果。例如在進行連帶責任的劃分時,債務人與擔保人成連帶關系,二者需要對同一債務承擔必要的償還義務,因此在法律關系中需要對債務人以及擔保人的違約風險進行評估;如果債務人發生違約情況,不論是債務人還是擔保人都要承擔與之相應的違約懲罰和義務,全面保障債權人的應有權益。另外,大多數情況下,連帶責任更加側重于呈現權益對立的雙方進行外部法律責任的承擔,侵權雙方需要在連帶體系內部進行責任劃分,更好地實現對被侵權者的救濟和補償[2]。
二、民商法中連帶責任問題分析
(一)連帶責任的司法解釋問題
在我國現有民商法的解釋體系中,連帶責任的范圍相對廣泛,但是在實際案例中并沒有針對連帶責任進行義務與權利開展司法認定時仍舊需要以實體法和程序法作為重要的輔助和媒介,如果單一依靠民商法進行連帶責任的判定,則很容易發生形式化的法律判斷問題,無法充分體現出審判的公平性效果,對侵權責任進行處理,也往往停留在表面形式的層面。例如在很多侵權事件的判定和審理過程中,法院需要充分應用現有審理條件,建議債權人共同侵權人進行全部起訴,此種形式賦予了債權人的充分自由,同樣也不會受到法院的規范約束和控制。因此在民商法侵權相關案件中,侵權者可以以現有的各類法律條款為依據,爭取訴訟權,同時也可以在實體法的基礎上,獲得民事實體權利,但是如果債權人只是想起訴共同侵權人中的一部分侵權人時,則需要應用連帶責任進行法律的確定,對案件進行更加公平、合理的審理。
(二)共同侵權責任確定
在共同侵權責任確定方面,我國現行《民法典》已經列出了更加明確的規定,所有的侵權人都要承擔與之相對應的責任,但是在實際法院審理開展過程中,對所有侵權人進行責任劃分相對困難。出現此類問題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全體侵權人的人數和基數相對較多,而債權人往往無法更加全方位地了解所有侵權人的具體信息和侵權內容等,特別是在涉案證據方面相對單一,無法提供更加全面的證據內容,使得法院在進行審理判定時無法直接判斷其法律責任。除此之外,我國民商法并沒有針對連帶責任的侵權行為進行更加詳細的說明與解釋,如果涉及侵權的人員相對較多,而大多數侵權人也不愿意承擔責任,則多數侵權者會選擇進行部分承擔,極容易導致一部分侵權人承擔了不屬于自身的法律責任,影響了法律的公平性和責任判定的合理性。
(三)共同侵權責任大小
在很多實際發生的侵權案例中,無法直接應用民商法連帶責任的形式對侵權人的責任水平進行有效判定,同樣也缺少必要的法律進行參考。在責任劃分方面過于模糊,往往會導致侵權人在責任承擔方面界限不明顯,嚴重危及法律的公平性效果。從現有連帶責任的侵權責任大小方面看,侵權人責任分攤以及后續的侵權行為,并沒有過多的重視在責任大小方面進行判斷,往往會局限于對全部責任人進行全部責任的承擔,這樣難免會產生新的糾紛。
三、民商法中連帶責任問題改善對策
(一)引入實體法和程序法
前文中強調在民商法連帶責任,特別是共同侵權責任確定方面,如果單一依靠民商法進行認定,則往往無法對侵權人的責任進行更加精準有效的判斷,因此在進行連帶責任的認定過程中,可以積極引用實體法和程序法,提高認定的保障性效果。實體法能夠有效劃分責任人的具體義務以及權利,應用實體法和程序法能夠保障案件的審理過程合理有序發展。例如,張某和王某兩人前往酒店私自翻看人員入住登記記錄,在確定人員名單之后搶劫了住客李某,并且在搶劫過程中對李某進行人身威脅;案件發生之后,李某選擇報警,張某和王某作為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捕,同時李某要求酒店承擔賠償責任。在這一案件的審理和受理過程中,可以積極應用實體法和程序法進行連帶責任的精準認定,因為確實是酒店管理方面出現了疏忽與遺漏問題,應為李某遭受的搶劫事件承擔連帶責任,同樣需要對李某進行相應賠償。
(二)共同侵權人的責任司法認定
對共同侵權責任進行司法認定,往往面臨侵權人數相對較多這一前提,因此可以將相關責任的具體應用標準進行引入,在立法時可以針對當事人所提出的諸多合理要求,為立法和司法提供更加合理有效的設計,反之在司法層面也能夠為案件當事人提供更加健全有效的服務。立法者需要始終站在公平的角度,全面平衡連帶責任訴訟的公平性效果,確保法律程序以及相關構件越發完善,而立法過程也要緊密聯系案件的實際,確保程序法的具體流程能夠與民商法的相關規定相符合[3]。與此同時,由于民商法體系龐大,各類連帶責任類型多樣,因此在實際案件審理和處理過程中,需要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作出更加科學合理的確定。例如在針對合伙型企業進行連帶責任的判斷時,可以根據侵權人在企業中的出資比例進行權利的劃分和確定,而法院則可以在審判過程中按照責任人的出資比例判斷和明確責任劃分;如果所發生的連帶責任問題屬于保證情況,則要判斷保證的歸屬方,進一步劃分連帶責任的保證性問題還是一般保證性問題,最大程度上體現司法法律的嚴謹性和合理性[4]。
(三)明確劃分共同侵權人的責任
在針對共同侵權責任人進行責任大小的判定時,往往無法直接應用民商法進行公平有效地判斷和認定,因此可以根據不同侵權案件的嚴重程度進行標準劃分,讓侵權案件的受理有相應的法律條款進行參考。如果某一案件中共同侵權責任人相對較多,則可以應用侵權行為法進行責任標準的劃分與解決,反之在公共訴訟或單獨訴訟等諸多情況中,可以對侵權責任進行單獨性的劃分;如果某一案件中共同侵權人的人數遠遠超出了常規標準或案件情節嚴重,則可以對共同侵權人進行全體起訴;法院方面可以針對案件的具體情況、債權人受影響的程度進行單獨起訴,或以第一責任人的形式進行起訴。
四、總結
在我國社會政治體系的完善和發展過程中,各類民生問題增加,類型趨于多樣,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我國法律體系的完善與發展。從當前我國民商法的角度看,連帶責任的判定尤為重要,但是在很多層面中缺少連帶責任的有效規定。本文首先概述了民商法中的連帶責任,其次著重分析了民商法中連帶責任問題,最后有針對性地提出連帶責任問題的改善對策,需要進一步引入實體法和程序法,對共同侵權人的責任進行司法認定,明確劃分共同侵權人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民商法連帶責任的作用和價值,促進我國法律體系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