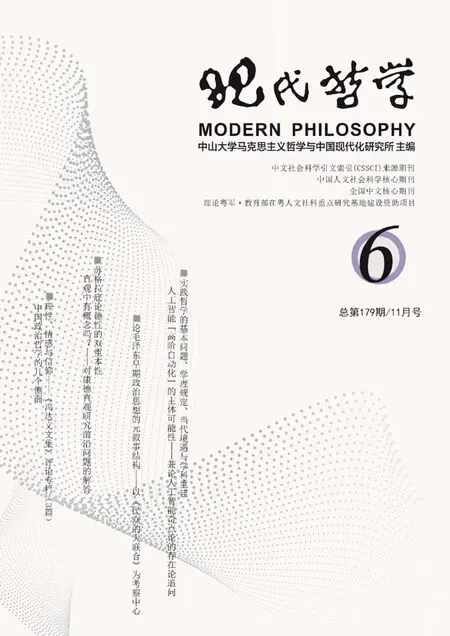政治理性視閾下的民主制理論
——兼論費(fèi)爾巴哈人本學(xué)對(duì)青年馬克思的影響
盛福剛
一、序 言
《萊茵報(bào)》被查封停刊后,馬克思由社會(huì)舞臺(tái)退回書房,并于1843年春在克羅茨納赫花了約半年時(shí)間寫了一部對(duì)黑格爾法哲學(xué)進(jìn)行批判性反思的手稿《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在現(xiàn)存的手稿中,馬克思對(duì)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內(nèi)部國家法”(第260-329節(jié))的部分章節(jié)逐一進(jìn)行批判,針對(duì)黑格爾在家庭、市民社會(huì)和政治國家分離的基礎(chǔ)上擁立的君主立憲制,構(gòu)建了“(真正的)民主制”理論,希冀消解人在政治領(lǐng)域的異化。對(duì)此,列寧在《卡爾·馬克思》(1914)中有個(gè)著名的論斷,即青年馬克思存在從唯心向唯物、由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chǎn)主義轉(zhuǎn)向的階段,并斷定《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時(shí)期的馬克思是一名革命民主主義者,青年馬克思思想轉(zhuǎn)變的完成是在《德法年鑒》時(shí)期。近年來,關(guān)于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從政治解放轉(zhuǎn)變?yōu)樽非笕说慕夥诺难芯坑l(fā)受到國內(nèi)學(xué)界的關(guān)注。促使馬克思由國家哲學(xué)進(jìn)入對(duì)市民社會(huì)的批判性分析的契機(jī)何在,成為國內(nèi)學(xué)界研究的熱點(diǎn)之一(1)國內(nèi)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促使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由政治解放轉(zhuǎn)變?yōu)樽非笕说慕夥诺钠鯔C(jī),在于1843年夏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對(duì)亨利希、孟德斯鳩、盧梭等人著作的摘錄之中。多數(shù)是依據(jù)蘇聯(lián)學(xué)者拉賓和MEGA2Ⅰ/Ⅱ卷編輯在考證《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克羅茨納赫筆記》《論猶太人問題》三部著作執(zhí)筆順序上的不同見解展開的研究,結(jié)論各異。(參見王代月、孫菲菲:《〈克羅茨納赫筆記〉:馬克思早期政治哲學(xué)批判的轉(zhuǎn)折點(diǎn)》,《求是學(xué)刊》2016年第2期;陳浩:《〈克羅茨納赫筆記〉與三種社會(huì)形態(tài)理論》,《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2年第1期;王旭東:《論馬克思〈克羅茨納赫筆記〉中的思想轉(zhuǎn)向——兼評(píng)拉賓的“交叉說”》,《現(xiàn)代哲學(xué)》2019年第2期。)。
在這一問題域下,國內(nèi)學(xué)者對(duì)民主制理論的評(píng)價(jià)褒貶不一,主要存在三方面的聲音:一是認(rèn)為《德法年鑒》時(shí)期,青年馬克思的理論轉(zhuǎn)變是從青年黑格爾學(xué)派自我意識(shí)的唯心主義轉(zhuǎn)向費(fèi)爾巴哈式的自然唯物主義、從民主主義轉(zhuǎn)向共產(chǎn)主義,并且將《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時(shí)期的民主制定義為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主義政治立場(chǎng)的理性觀念論(2)參見張一兵:《青年馬克思的第一次思想轉(zhuǎn)變與〈克羅茨納赫筆記〉》,《求是學(xué)刊》1999年第3期。;二是認(rèn)為馬克思直至《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階段仍然堅(jiān)持著黑格爾的倫理國家觀,采用“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的二元框架來解決人的政治異化問題,馬克思在《德法年鑒》中由“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的二元框架走向市民社會(huì)的一元論(3)參見韓立新:《從國家到市民社會(huì)——〈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導(dǎo)言〉研究》,《河北學(xué)刊》2016年第9期。;三是認(rèn)為馬克思的民主制理論“必須同時(shí)是國家的去政治性和社會(huì)的去私人性”,馬克思在民主制中完成了普遍性與特殊性、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的真正統(tǒng)一,換言之,真正的民主制是一種“去政治的政治哲學(xué)方案”,蘊(yùn)含了日后關(guān)于共產(chǎn)主義的一些最基本觀念的萌芽(4)參見方博:《去政治的政治哲學(xué)方案——馬克思的“真正的民主制”》,《學(xué)術(shù)月刊》2018年第3期。。
基于以上對(duì)《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民主制理論的解讀,筆者試圖通過追問以下幾個(gè)問題闡明本文的立場(chǎng):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構(gòu)建的民主制理論是否關(guān)涉了私有財(cái)產(chǎn)和階級(jí)問題,將民主制視作資產(chǎn)階級(jí)民主主義的立場(chǎng)是否妥當(dāng)?《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期間的民主制的理論結(jié)構(gòu)是否是一種二元框架,《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論猶太人問題》是否存在從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的二元框架轉(zhuǎn)向市民社會(huì)一元論?《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期間的民主制是否可以視同一種“去政治性”的哲學(xué)解決方案?如果民主制是一種“去政治性”,是否意味著實(shí)質(zhì)上否認(rèn)了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序言》中的自述,即通過對(duì)黑格爾法哲學(xué)的批判性分析得出的“結(jié)果”?(5)“為了解決使我苦惱的疑問,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duì)黑格爾法哲學(xué)的批判性分析,這部著作的導(dǎo)言曽發(fā)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鑒》上。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gè)結(jié)果:法的關(guān)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fā)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zhì)的生活關(guān)系,這種物質(zhì)的生活關(guān)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jì)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huì)’,而對(duì)市民社會(huì)的解剖應(yīng)該到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中去尋求。”(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頁。)最后,筆者將尋根朔源,探尋馬克思的民主制與費(fèi)爾巴哈的人本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闡明馬克思由《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時(shí)期對(duì)國家哲學(xué)的批判轉(zhuǎn)向《德法年鑒》時(shí)期對(duì)市民社會(huì)的批判過程中費(fèi)爾巴哈哲學(xué)的影響。
二、《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的民主制
客觀精神合乎理性地發(fā)展,即在作為實(shí)體意志的現(xiàn)實(shí)性的現(xiàn)代國家階段,客觀自由或普遍實(shí)體性意志的自由和主觀自由或個(gè)體追求私利私欲的意志自由達(dá)成統(tǒng)一,是黑格爾《法哲學(xué)原理》中的邏輯出發(fā)點(diǎn)。
(一)黑格爾的政治國家觀
黑格爾認(rèn)為,作為“需要、勞動(dòng)、私人利益和私人權(quán)利”等領(lǐng)域的市民社會(huì)是私利私欲的戰(zhàn)場(chǎng),其原則主要有兩方面:其一,市民社會(huì)的個(gè)人是把追求自身特殊利益作為目的的私人,是“各種需要的一個(gè)整體以及自然必然性與任性的一個(gè)混合體”;其二,每個(gè)特殊的個(gè)人必須通過他人的勞動(dòng)與需要,即形式上的普遍性為中介,才能使自身有效并且使自身的特殊需要得到滿足,此時(shí)的黑格爾又將市民社會(huì)稱之為“外部的國家”(6)《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29、330頁。。但市民社會(huì)中的個(gè)人會(huì)在一切方面盡量滿足自身的需要和主觀偏好的同時(shí),受制于普遍性的權(quán)利;在這些謀求私利以及相互對(duì)立的個(gè)體關(guān)系中,市民社會(huì)本身會(huì)呈現(xiàn)出荒淫和貧困等景象(7)《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1頁,第383頁,第446、450頁,第449頁。。正是由于市民社會(huì)內(nèi)含著其自身無法消融的矛盾與缺陷,客觀精神需要進(jìn)展到作為市民社會(huì)的外在必然性和內(nèi)在目的的國家領(lǐng)域;只有在國家中,個(gè)體的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之間才能達(dá)成真正的統(tǒng)一。黑格爾并非想通過消解個(gè)體的特殊需要和特殊利益來實(shí)現(xiàn)統(tǒng)一,而是讓個(gè)體融入國家成為其中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讓國家本身成為其真實(shí)的內(nèi)容和真正的目的,從而個(gè)體的使命在于過上一種普遍的生活,以普遍利益為其出發(fā)點(diǎn)和歸宿(8)《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1頁,第383頁,第446、450頁,第449頁。。而黑格爾讓個(gè)體參與到政治國家構(gòu)建的方式是等級(jí)代表制度或者說是等級(jí)要素,即作為一般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中介機(jī)關(guān)。等級(jí)又區(qū)分為作為供職于政府機(jī)關(guān)的普遍等級(jí)暨官僚等級(jí)、在立法權(quán)意義上獲得政治意義和實(shí)效的私人等級(jí)。私人等級(jí)又分為建立在實(shí)體性關(guān)系上的等級(jí)、建立在特殊需要和以這些需要為中介的勞動(dòng)上的等級(jí),后者需要通過從市民社會(huì)的各種同業(yè)公會(huì)和自治團(tuán)體中選派議員的方式參與國家的普遍事(9)《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1頁,第383頁,第446、450頁,第449頁。。
(二)馬克思對(duì)黑格爾倫理國家觀的批判
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馬克思對(duì)黑格爾法哲學(xué)的批判可以歸結(jié)為兩個(gè)方面:第一,徹底揭露和批判作為從市民社會(huì)中抽象出來的,作為一種普遍理性和市民社會(huì)相對(duì)立的政治國家;第二,為揚(yáng)棄這種政治異化尋找解決方案或者說是一種可行性的路徑。
黑格爾將作為國家成員的一切人都單獨(dú)參與一般國家事物的咨議和決定,并以自己的知識(shí)和意志去影響國家事物的看法,稱之為“沒有任何理性形式(可是只有這種形式才能使國家成為機(jī)體)的民主因素”(10)《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31頁,第383頁,第446、450頁,第449頁。,將參與國家事物的成員限定于君主(王權(quán))、作為普遍等級(jí)的官僚等級(jí)(行政權(quán))和作為私人等級(jí)代表的議員(立法權(quán))。馬克思認(rèn)為,黑格爾正是將個(gè)人的現(xiàn)實(shí)生活和國家生活在市民社會(huì)中的分離作為前提,使國家成為作為實(shí)際的國家成員的“抽象的規(guī)定”;還認(rèn)為黑格爾面臨著一種二推難題,即作為實(shí)際國家的國家成員的一切人是通過議員參與還是一切人都參與的問題本身就是抽象的政治國家范圍內(nèi)的問題(11)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145頁,第96、97、98頁,第42、99頁,第42頁。。這種難題產(chǎn)生的前提正是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的分離和對(duì)立,“私人等級(jí),即市民社會(huì)……也就是國家的對(duì)立面,是同國家分離”,“市民社會(huì)和政治國家的分離必然表現(xiàn)為政治市民即國家公民脫離市民社會(huì),脫離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經(jīng)驗(yàn)的現(xiàn)實(shí)性,因?yàn)閲夜褡鳛閲业睦硐胫髁x者,是完全另外一種存在物,一種與他的現(xiàn)實(shí)性不同的、有差別的、相對(duì)立的存在物”,“市民社會(huì)在自己的政治行動(dòng)中所陷入的原子論,必然產(chǎn)生于下述情況:個(gè)人賴以存在的公團(tuán)、共同體,市民社會(huì),是同國家分離的,或者說,政治國家是從市民社會(huì)中得出的抽象”(12)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145頁,第96、97、98頁,第42、99頁,第42頁。。
馬克思進(jìn)而將這種從家庭和市民社會(huì)中抽象出來的政治國家,作為一種抽象的政治國家和家庭、市民社會(huì)相分離相對(duì)立的現(xiàn)象,稱之為家庭和市民社會(huì)在政治領(lǐng)域的異化(Entfremdung),“政治國家的彼岸存在無非是要肯定這些特殊領(lǐng)域自身的異化”,“黑格爾把這種現(xiàn)象說成令人詫異的東西,但這絲毫也不能消除上述兩個(gè)領(lǐng)域(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引者注)的異化”(13)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145頁,第96、97、98頁,第42、99頁,第42頁。。換句話說,它是從家庭和市民社會(huì)得出的抽象,是二者在政治領(lǐng)域異化的產(chǎn)物。對(duì)馬克思而言,黑格爾構(gòu)建的政治國家或者說現(xiàn)實(shí)的政治制度就是一種國家制度,對(duì)市民社會(huì)而言是一種彼岸之物,“對(duì)其他領(lǐng)域(家庭、市民社會(huì)——引者注)來說,它(政治國家——引者注)是作為普遍理性、作為彼岸之物而發(fā)展起來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政治生活就是人民生活的經(jīng)院哲學(xué)。君主制是這種異化的完備表現(xiàn)”(14)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145頁,第96、97、98頁,第42、99頁,第42頁。。
如何揚(yáng)棄這種政治國家作為國家實(shí)際成員的政治異化現(xiàn)象?對(duì)此,馬克思可謂煞費(fèi)苦心。與其后在《德法年鑒》《巴黎手稿》中通過對(duì)市民社會(huì)進(jìn)行批判性分析,尋求人的解放的現(xiàn)實(shí)路徑不同,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階段倒向了人的政治生活和由此結(jié)成的政治領(lǐng)域,認(rèn)為只有政治生活和政治存在才能表征人的共同性的類本質(zhì)。揚(yáng)棄政治異化只有依靠人自身的政治屬性,揚(yáng)棄政治異化的歷史任務(wù)在于如何讓國家制度復(fù)歸到作為實(shí)際的國家成員的一切人身上。
馬克思此刻認(rèn)識(shí)到,人的政治屬性才是人的真正的普遍本質(zhì),而國家作為人的政治屬性的集合,本身應(yīng)該是人的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馬克思認(rèn)為,在文明時(shí)代的現(xiàn)代國家中,作為人的對(duì)象性本質(zhì)的國家卻同人相分離,對(duì)象性的本質(zhì)演變?yōu)橐环N外化的、異化的產(chǎn)物。“我們的時(shí)代即文明時(shí)代,卻犯了一個(gè)相反的錯(cuò)誤。它使人的對(duì)象性本質(zhì)作為某種僅僅是外在的、物質(zhì)的東西同人分離,它不認(rèn)為人的內(nèi)容是人的真實(shí)現(xiàn)實(shí)。”(15)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頁,第42頁,第150頁,第112頁。在馬克思看來,黑格爾在法哲學(xué)中同樣犯了“相反的錯(cuò)誤”,他將原本歸屬于人的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的國家從家庭和市民社會(huì)中抽象出來,外在于市民社會(huì),并作為承擔(dān)著普遍理性的倫理國家對(duì)立于、異化于市民社會(huì)。
馬克思高度肯定了黑格爾的法哲學(xué)語境中承擔(dān)著普遍理性的政治領(lǐng)域,他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找到的揚(yáng)棄政治異化的路徑是政治領(lǐng)域本身的復(fù)歸,歷史任務(wù)就是讓國家制度回歸到人的本質(zhì),從而消解國家制度或政治國家彼岸性質(zhì)。真正成為人的本質(zhì)或者說類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政治領(lǐng)域是國家中唯一的國家領(lǐng)域,是這樣一種唯一的領(lǐng)域,它的內(nèi)容同它的形式一樣,是類的內(nèi)容,是真正的普遍東西,但因?yàn)檫@個(gè)領(lǐng)域同其他領(lǐng)域相對(duì)立,所以它的內(nèi)容也成了形式的和特殊的。”(1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頁,第42頁,第150頁,第112頁。對(duì)馬克思而言,最大的任務(wù)是如何讓國家中唯一的“類的內(nèi)容、真正的普遍東西”的政治領(lǐng)域由一種“形式的和特殊的”異化存在復(fù)歸為內(nèi)容的和普遍的東西。途徑不是下沉到市民社會(huì)中需要解決方案,因?yàn)榇藭r(shí)的馬克思仍然沉浸在黑格爾構(gòu)建的普遍理性的國家哲學(xué)之中,而是借助于作為政治存在的個(gè)人構(gòu)建一種新型的政治社會(huì)。
(三)民主制理論中的“變體”
黑格爾的法哲學(xué)方案以市民社會(huì)和政治國家的分離為前提,馬克思正是在揭露和批判這種二元性中構(gòu)建了獨(dú)特的民主制理論,希冀以此揚(yáng)棄政治異化,實(shí)現(xiàn)政治領(lǐng)域(或國家制度)向人的本質(zhì)的真正回歸。簡(jiǎn)言之,馬克思的民主制理論是通過普遍選舉,達(dá)成市民社會(huì)變體為政治社會(huì)。不同于從市民社會(huì)(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中抽象出政治國家(politische Staat)的黑格爾,馬克思使用的是政治存在(politische Existenz)和政治社會(huì)(politische Gesellschaft)。
馬克思說:“換句話說,選舉是市民社會(huì)對(duì)政治國家的非間接的、直接的、不是單純想象的而是實(shí)際存在的關(guān)系。因此顯而易見,選舉構(gòu)成現(xiàn)實(shí)市民社會(huì)的最根本的政治利益。通過不受限制的選舉和被選舉,市民社會(huì)才第一次真正上升(erheben——引者注)到自身的抽象,上升到自己真正普遍的本質(zhì)的存在的政治存在。”(1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頁,第42頁,第150頁,第112頁。馬克思在引文中闡述的正是民主制理論的核心要義,市民社會(huì)通過“不受限制的選舉和被選舉”,上升到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中作為其自身抽象、對(duì)立面的政治存在,而這種政治存在才是真正普遍的類存在或類本質(zhì)。簡(jiǎn)言之,市民社會(huì)變體或升格為政治社會(huì)后,方能將政治存在設(shè)定為自身的本質(zhì)存在,以追求普遍物為自身的最終旨?xì)w;而原本的市民存在或私人等級(jí)則降格為非本質(zhì)的存在,追求私利私欲不再是其自身的目的,普遍的政治理性得以在普遍政治存在的共同體中達(dá)成。
市民社會(huì)上升為政治存在,即市民社會(huì)變體為政治社會(huì)。變體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作馬克思對(duì)黑格爾的理論體系的承襲。在黑格爾的法哲學(xué)中,私人等級(jí)或者說市民社會(huì)以單個(gè)人為形式,被抬舉到參與立法權(quán)中的普遍事物,在立法權(quán)的等級(jí)要素中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時(shí),不應(yīng)該把自己表示為無機(jī)的合眾(Menge),而只能將自己表現(xiàn)為某種普遍物的成員,并以追求普遍物為自身的本質(zhì)目的(18)參見《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第446頁。。市民社會(huì)中作為私人等級(jí)以追逐私利私欲為目的的私人,變身為政治國家中以追求普遍物為本質(zhì)目的的國家公民的政治行動(dòng)被馬克思定義為變體(Transsubstanziation)(19)黑格爾將官僚等級(jí)定義為普遍等級(jí),這部分等級(jí)沒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以追求普遍利益為目的。如何從市民社會(huì)中選出某一個(gè)個(gè)體,使之和某一官職相聯(lián)系并參與到國家的實(shí)體關(guān)系中,作為普遍性保證的手段之一便是考試。但在馬克思看來,這無非是官方“對(duì)世俗知識(shí)變體為神圣知識(shí)的確認(rèn)”。(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5頁。);“‘等級(jí)’要素是市民社會(huì)的政治存在,是市民社會(huì)變體為政治國家”(2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2頁,第42頁,第150頁,第112頁。,“相反,私人等級(jí)要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就必須不再是已有的樣子,不再是私人等級(jí)。只有這樣,它才能獲得自己的‘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這種政治行動(dòng)是完完全全的變體。在這種行動(dòng)中,市民社會(huì)應(yīng)該完全擺脫作為市民社會(huì)、作為私人等級(jí)的自身,它應(yīng)該表現(xiàn)自己本質(zhì)中的這樣一個(gè)方面,這個(gè)方面不僅與它的本質(zhì)所具有的現(xiàn)實(shí)的市民存在毫無共同之處,而且還與它直接對(duì)立”(2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頁,第146頁,第150頁,第41頁,第40頁,第40頁,第97—98頁。。與現(xiàn)實(shí)中的市民存在毫無共同之處并且與之相對(duì)立的人的本質(zhì)方面,指的就是在“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附體后,私人等級(jí)變體為普遍的政治存在。
市民社會(huì)中的全體成員如何才能由私人存在整個(gè)變體為政治存在,政治社會(huì)何以可能?在馬克思看來,這關(guān)涉到人自身有意識(shí)地參與國家(22)區(qū)別于把人變?yōu)橹黧w化的國家,馬克思的民主制理論是“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即國家作為人的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產(chǎn)物,再將國家復(fù)歸給人自身。(同上,第40頁。)。“國家成員這一概念已經(jīng)有了這樣的含義:他們是國家的成員,是國家的一部分,國家把他們看作自己的一部分。既然他們是國家的一部分,那么不言而喻,他們的社會(huì)存在就已經(jīng)是他們實(shí)際參與國家。他們不僅是國家的一部分,而且國家也是他們的一部分。要成為某種東西有意識(shí)的一部分,就要有意識(shí)地掌握它的一部分,有意識(shí)地參與它。沒有這種意識(shí),國家的成員就無異于動(dòng)物。”(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頁,第146頁,第150頁,第41頁,第40頁,第40頁,第97—98頁。這時(shí)在馬克思的設(shè)想中,作為實(shí)際的國家成員要想意識(shí)地參與國家,成為國家的積極成分,就要通過上文中所說的“不受限制的選舉與被選舉”,使市民社會(huì)中的市民或者說私人整體地普遍地參與立法權(quán)后,市民社會(huì)的成員由為私利私欲廝殺的市民存在變體為以追求普遍物為自身的本質(zhì)目的的政治存在。這種政治存在的共同體就是實(shí)現(xiàn)了普遍政治理性的政治社會(huì)。
由此,一切人對(duì)一切人的戰(zhàn)爭(zhēng)狀態(tài)中的市民社會(huì)得以解體,與此同時(shí),作為抽象的政治制度與市民社會(huì)相對(duì)立的政治國家也隨之消失、解體(24)“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國家就消失了。這可以說是正確的,因?yàn)樵诿裰髦浦校螄易鳛檎螄遥鳛閲抑贫龋呀?jīng)不再被認(rèn)為是一個(gè)整體了。”(同上,第41頁。)。市民社會(huì)變體為政治社會(huì)后,“但是,這種抽象之完成同時(shí)也就是抽象之揚(yáng)棄。市民社會(huì)把自己的政治存在實(shí)際設(shè)定為自己的真正存在,同時(shí)也就把不同于自己的政治存在的市民存在設(shè)定為非本質(zhì)的存在;而被分離者中有一方脫落了,它的另一方,即對(duì)方,也隨之脫落。因此,選舉改革就是在抽象的政治國家的范圍內(nèi)要求這個(gè)國家解體,但同時(shí)也要求市民社會(huì)解體”(2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頁,第146頁,第150頁,第41頁,第40頁,第40頁,第97—98頁。。
國家制度復(fù)歸于實(shí)際國家成員的市民社會(huì)中的個(gè)人后,抽象的政治國家不復(fù)存在,“在民主制中,國家制度、法律、國家本身,就國家是政治制度來說,都只是人民的自我規(guī)定和人民的特定內(nèi)容”(2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頁,第146頁,第150頁,第41頁,第40頁,第40頁,第97—98頁。。政治異化得以揚(yáng)棄后,作為政治制度的國家本身變體為人民的自我規(guī)定。區(qū)別于把人變?yōu)橹黧w化的國家的黑格爾法哲學(xué),馬克思的民主制理論是“把國家變成客體化的人”(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頁,第146頁,第150頁,第41頁,第40頁,第40頁,第97—98頁。,即把國家作為人的類本質(zhì)的對(duì)象化產(chǎn)物,復(fù)歸給作為國家成員的人民,換句話說,即市民社會(huì)中的各個(gè)人(Individuum)。消解了國家公民和私人的分離和二元對(duì)立后,“國家制度在這里(民主制——引者注)表現(xiàn)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chǎn)物”(2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頁,第146頁,第150頁,第41頁,第40頁,第40頁,第97—98頁。。
(四)民主制理論中的去私人性
馬克思認(rèn)同黑格爾在《法哲學(xué)原理》的第303-311節(jié)中所述,在市民社會(huì)中,私人等級(jí)要想在立法權(quán)的等級(jí)要素中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由私人等級(jí)變體為政治存在必須要揚(yáng)棄市民社會(huì)、私人等級(jí)和私人權(quán)益。“市民社會(huì)和政治國家的分離必然表現(xiàn)為政治市民即國家公民脫離市民社會(huì),脫離自己固有的、真正的、經(jīng)驗(yàn)的現(xiàn)實(shí)性……市民要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就必須拋棄自己的等級(jí),即拋棄市民社會(huì),拋棄私人等級(jí),因?yàn)檎沁@個(gè)等級(jí)處在個(gè)體和政治國家之間”(2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6頁,第146頁,第150頁,第41頁,第40頁,第40頁,第97—98頁。,黑格爾認(rèn)為,這些議員一經(jīng)被選出,他們和原本自身所屬的同業(yè)公會(huì)之間的關(guān)系不是全權(quán)委托或代理人的關(guān)系,他們也不會(huì)為某個(gè)自治團(tuán)體或同業(yè)公會(huì)的特殊利益而反對(duì)普遍利益(30)參見《黑格爾著作集》第7卷,第450頁。。換句話說,被選出的議員脫離了市民社會(huì)和私人等級(jí)。另一方面,市民社會(huì)中的剩余成員仍然活在私利私欲的戰(zhàn)場(chǎng)中,過著為一己私利相互爭(zhēng)斗的戰(zhàn)爭(zhēng)生活。
黑格爾在其法哲學(xué)中,將參與國家普遍事物的等級(jí)限定于君主、普遍等級(jí)和市民社會(huì)中的等級(jí)要素。換句話說,黑格爾構(gòu)建的國家哲學(xué)中,作為政治公民即國家公民參與政治國家構(gòu)建的除君主以外,只有官僚等級(jí)和從市民社會(huì)中選出的議員(包含兩院,即上議院和下議院或參議院和眾議院)。市民社會(huì)中只有極少部分人在立法權(quán)的等級(jí)要素中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實(shí)現(xiàn)變體,由私人等級(jí)變體為政治存在的國家公民。此外,黑格爾還刻意貶低人民在政治國家中的地位。馬克思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批判政治國家作為從市民社會(huì)中的抽象,外在于市民社會(huì)并與其相對(duì)立、相異化。
不同于黑格爾,馬克思構(gòu)建的民主制理論是讓市民社會(huì)整體地變體為政治社會(huì),實(shí)現(xiàn)變體的途徑是讓作為市民社會(huì)中的全體成員通過不受限制的選舉和被選舉參與立法權(quán)的政治行動(dòng),進(jìn)一步則是讓全體人民參與立法權(quán)從而獲得政治意義和政治效能的設(shè)想。“因此,市民社會(huì)希望整個(gè)地即盡可能整體地參與立法權(quán),現(xiàn)實(shí)的市民社會(huì)希望自己代替立法權(quán)的虛構(gòu)的市民社會(huì),這不外是市民社會(huì)力圖賦予自己以政治存在,或者使政治存在成為它的現(xiàn)實(shí)存在。市民社會(huì)力圖使自己變?yōu)檎紊鐣?huì),或者市民社會(huì)力圖使政治社會(huì)變?yōu)楝F(xiàn)實(shí)社會(huì),這是表明市民社會(huì)力圖盡可能普遍地參與立法權(quán)。”(3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7頁。這里,前一個(gè)“立法權(quán)的虛構(gòu)的市民社會(huì)”指的是黑格爾法哲學(xué)中,通過立法權(quán)的等級(jí)要素所表現(xiàn)的市民社會(huì),并不能代表現(xiàn)實(shí)的市民社會(huì),即市民社會(huì)中全體人民通過整體地普遍地參與立法權(quán)后獲得的政治存在,及由此結(jié)成的政治社會(huì)。政治社會(huì)完成后,政治國家的彼岸性質(zhì)消除的同時(shí),市民社會(huì)的私人性質(zhì)也將隨之消除。“它們(家庭、市民社會(huì)——引者注)的私人性質(zhì)將隨著國家制度或政治國家的彼岸本質(zhì)的消除而消除,政治國家的彼岸存在無非是要肯定這些特殊領(lǐng)域自身的異化。”(32)同上,第42頁。
三、民主制的理論溯源
為什么馬克思要通過民主制理論揚(yáng)棄異化,使抽象的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達(dá)成和解,消除兩者的對(duì)立和分離?原因就在于馬克思對(duì)費(fèi)爾巴哈人本學(xué)的受容(33)本節(jié)的寫作多次受到日本學(xué)者渡邊憲正教授(日本關(guān)東學(xué)院大學(xué))的提點(diǎn),借此機(jī)會(huì)表示誠摯的謝意。關(guān)于馬克思對(duì)費(fèi)爾巴哈哲學(xué)的受容及批判過程,參見[日]渡邊憲正:《近代批判とマルクス》,東京:青木書店,1989年。。
(一)馬克思恩格斯論《基督教的本質(zhì)》
1843年春,費(fèi)爾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質(zhì)》再版后,馬克思恩格斯一度成為費(fèi)爾巴哈忠實(shí)的擁躉。馬克思從《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二版序言中了解到費(fèi)爾巴哈正在準(zhǔn)備一部批判謝林的著作后,于1843年10月初致信費(fèi)爾巴哈,表達(dá)了他對(duì)費(fèi)爾巴哈的仰慕之情,并懇請(qǐng)其為《德法年鑒》賜稿,“您的任何稿件都是我們最為歡迎的,想必您手頭就有一些現(xiàn)成的東西”(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頁。。1844年8月,馬克思二度致信費(fèi)爾巴哈,就借人本學(xué)思想這一“天才的闡述”(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5頁。批判鮑威爾一事提前征詢他的意見,還稱贊了《基督教的本質(zhì)》在德國手工業(yè)者中的影響力(3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16頁。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fèi)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xué)的終結(jié)》中也曾談及這部書對(duì)馬克思的影響:“這部書(《基督教的本質(zhì)》——引者注)的解放作用,只有親身體驗(yàn)過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時(shí)大家都很興奮:我們一時(shí)都成為費(fèi)爾巴哈派了。馬克思曾經(jīng)怎樣熱烈地歡迎這種新觀點(diǎn),而這種新觀點(diǎn)又是如何強(qiáng)烈地影響了他(盡管還有種種批判性的保留意見),這可以從《神圣家族》中看出來。”(3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頁
不僅僅是《神圣家族》,馬克思在手稿《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闡述的民主制理論同樣留有人本學(xué)的烙跡。他將國家制度與人民的關(guān)系類比成宗教與人的關(guān)系,并得出如下結(jié)論:同人創(chuàng)造了宗教一樣,國家制度同樣是人民創(chuàng)造的產(chǎn)物,“正如同不是宗教創(chuàng)造人,而是人創(chuàng)造宗教一樣,不是國家制度創(chuàng)造人民,而是人民創(chuàng)造國家制度。在某種意義上,民主制對(duì)其他一切國家形式的關(guān)系,同基督教對(duì)其他一切宗教關(guān)系是一樣的”(3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頁。。馬克思在此處雖然沒有標(biāo)明出處,但人創(chuàng)造了宗教的思想,即宗教中的上帝是人的類本質(zhì)的觀點(diǎn),明顯受到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批判的影響。
國內(nèi)有學(xué)者將對(duì)青年馬克思和費(fèi)爾巴哈哲學(xué)關(guān)系的探討歸結(jié)為蘇聯(lián)的“傳統(tǒng)的解讀模式”,認(rèn)為青年馬克思在1843年至1845年根本不存在“費(fèi)爾巴哈階段”(39)參見王東、林峰:《馬克思哲學(xué)存在一個(gè)“費(fèi)爾巴哈”階段嗎?——“兩次轉(zhuǎn)變論”質(zhì)疑》,《學(xué)術(shù)月刊》2007年第4期。;有的更是認(rèn)為,馬克思和費(fèi)爾巴哈哲學(xué)的關(guān)系是“一個(gè)不成問題的問題”,徹底否定了費(fèi)爾巴哈人本學(xué)對(duì)青年馬克思的影響,即“在對(duì)自己發(fā)展的回顧中,馬克思提到了黑格爾,但并沒有提到費(fèi)爾巴哈……這些空泛的、抽象的說教并不能成為馬克思思想的真正的動(dòng)力”(40)參見俞吾金:《讓馬克思從費(fèi)爾巴哈的陰影中走出來》,《南京社會(huì)科學(xué)》1996年第1期,第11頁。。如果完全否認(rèn)費(fèi)爾巴哈的影響,無法圓融地解釋馬克思恩格斯的自述;但馬克思在哪一階段開始借鑒人本學(xué),學(xué)界尚留有較多的研究余地(41)還有的學(xué)者從人本學(xué)出發(fā)探討馬克思和費(fèi)爾巴哈的關(guān)系,但也只是從唯物史觀形成后,以掙脫了費(fèi)爾巴哈之后的馬克思視角去看待費(fèi)爾巴哈,即從《關(guān)于費(fèi)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shí)形態(tài)》出發(fā)解析馬克思對(duì)費(fèi)爾巴哈人本學(xué)的超越。參見鄧曉芒:《馬克思人本主義的生態(tài)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現(xiàn)實(shí)》2009年第1期。。以下,筆者以學(xué)界論及較少的《基督教的本質(zhì)》和《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的關(guān)系為題,論證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倫理國家理念時(shí)創(chuàng)立的民主制理論是費(fèi)爾巴哈人本學(xué)的歸結(jié)。
(二)概論費(fèi)爾巴哈的人本學(xué)
費(fèi)爾巴哈的人本學(xué)可以歸結(jié)為對(duì)象性本質(zhì)即人的本質(zhì),起點(diǎn)是對(duì)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他曾將黑格爾的“邏輯的形而上學(xué)的真理的思辨宗教哲學(xué)”斥為“迂腐”(42)參見[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榮震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84年,第1頁。,試圖將宗教從思辨的宗教哲學(xué)中解放出來,解放的路徑則是人本主義哲學(xué),即將屬神的宗教本質(zhì)歸結(jié)為屬人的本質(zhì)。
依費(fèi)爾巴哈的觀點(diǎn),人通過對(duì)象認(rèn)識(shí)自我,人與對(duì)象的關(guān)系就是人和自身本質(zhì)之間的關(guān)系,關(guān)于對(duì)象的意識(shí)就是人的自我意識(shí)。他主張人通過感性直觀(五官)感覺和認(rèn)識(shí)的對(duì)象不只是某種外在的事物,而且有內(nèi)在的“自我”,主體和對(duì)象具有同一性。費(fèi)爾巴哈做過一個(gè)非常形象的比喻,人通過手感覺到的不僅僅是石頭或木頭等物體,還有自身的觸覺;通過耳朵感覺到的不僅僅是流水潺潺和秋葉瑟瑟的聲音,還有愛情等自身豐富的感情;還可以通過食物感覺自身的味覺。
另外,關(guān)于理性和概念的起源,他批判思辨的唯心論者試圖從孤立的、獨(dú)立存在的實(shí)體中導(dǎo)出觀念,主張人是兩性結(jié)合的產(chǎn)物,只有通過人與人的交往,才能獲取概念和理性:“我所以確知有在我之外的其他事物的存在,乃是由于我確知有我之外的另一個(gè)人的存在,我一個(gè)人所看到的東西,我是懷疑的,別人也看到的東西,才是確實(shí)的”(43)參見費(fèi)爾巴哈:《未來哲學(xué)原理》,洪謙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5年,第64—65頁。。由此,費(fèi)爾巴哈進(jìn)一步闡述個(gè)別的孤立的個(gè)人意味著有限性和限制性,并不是完善的真正的人,不具備人的本質(zhì),而自由和無限性存在于社會(huì)性之中。具體而言,“人的本質(zhì)只是包含于團(tuán)體(Gemeinschaft——引者注)之中,包含人與人的統(tǒng)一之中”(44)同上,第78—79頁。。費(fèi)爾巴哈將這種通過人與人的統(tǒng)一獲得的人的本質(zhì)或固有的人性歸結(jié)為理性、意志和愛(心),這種在人里面又超乎個(gè)別的人之上的本質(zhì)(實(shí)體)就是類本質(zhì)或類共同(Gattungswesen)(45)關(guān)于人的本質(zhì),參見[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29—31頁。。他還曾在批判施蒂納時(shí),公開宣稱自己是共產(chǎn)主義者:“他是人,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因?yàn)椋M(fèi)爾巴哈把人的實(shí)體僅僅置放在社會(huì)性之中——,他是社會(huì)的人,是共產(chǎn)主義者。”(46)為反駁“唯一者”施蒂納的批判,費(fèi)爾巴哈在《維干德季刊》第2卷中發(fā)表了“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論《基督教的本質(zhì)》”一文。(參見《費(fèi)爾巴哈哲學(xué)著作選集》下卷,榮震華、王太慶、劉磊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62年,第435頁。)
在《基督教的本質(zhì)》中,費(fèi)爾巴哈將表述對(duì)象性本質(zhì)的人本哲學(xué)用于批判性地剖析基督教(宗教)的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認(rèn)為宗教的對(duì)象性關(guān)系就是人和自身本質(zhì)的關(guān)系。人的宗教意識(shí)就是人的自我意識(shí),指出黑格爾的精神哲學(xué)中被當(dāng)作上帝(絕對(duì)精神)的自我意識(shí)其實(shí)就是人對(duì)上帝的意識(shí)。基督教中屬神的三位一體(圣父、圣子和圣靈)不外乎是屬人的本質(zhì),即理性、愛和意志的統(tǒng)一。換句話說,宗教信仰的對(duì)象內(nèi)在于信徒自身,人和上帝發(fā)生的關(guān)系,就是人和人所固有而又客觀的本質(zhì)的關(guān)系,“主體必然與其發(fā)生本質(zhì)關(guān)系的那個(gè)對(duì)象,不外是這個(gè)主體固有而又客觀的本質(zhì)”(47)[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在宗教關(guān)系中,人的本質(zhì)超越了個(gè)體的、現(xiàn)實(shí)的、屬肉體的人的局限性,被對(duì)象化為一種區(qū)別于個(gè)體(主體)的獨(dú)自本質(zhì)(實(shí)體、上帝),信徒敬拜的就是其自身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48)[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
在上帝是人的本質(zhì)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這一命題中,作為主詞的上帝被作為賓詞的本質(zhì)所規(guī)定,賓詞決定著主詞,主詞和賓詞實(shí)現(xiàn)了顛倒;另一方面,人的本質(zhì)具有無限性,因此上帝這一實(shí)體可以擁有無限多的賓詞,如善和美等(49)[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上帝之所以具備人格,原因在于人自身放棄的人格,人將自身的知識(shí)、思維、美感和善等抽取出來賦予上帝,由此上帝變成了全能的無限的、至善至美的存在(50)[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宗教是人的自我分裂,人抽取出自身固有的本質(zhì)賦予上帝,由此上帝具備了理智(理性)、道德、愛、美和善等屬人的品格。
費(fèi)爾巴哈另一方面指出人將自身本質(zhì)賦予上帝的同時(shí),意味著將意識(shí)或個(gè)性留給自身。當(dāng)宗教作為實(shí)踐和主觀立場(chǎng)時(shí)又表現(xiàn)出非本質(zhì)的一面,即主觀性或心情的全能。人之所以需要宗教,在于人不幸時(shí)需要感知上帝,所以信仰訴諸的不是理智而是一種心情全能,信則得安寧和福樂。此時(shí),宗教不再屬于人的本質(zhì)領(lǐng)域的理智和愛,而是屬于心情這一自私自利的主觀領(lǐng)域(51)[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
費(fèi)爾巴哈由此揭露了思辨的宗教哲中內(nèi)含的矛盾,指出黑格爾哲學(xué)中上帝的自我意識(shí)無外乎是人關(guān)于上帝的意識(shí),即將上帝的自我意識(shí)和人的意識(shí)之間的矛盾歸結(jié)為作為實(shí)體的愛和主體的信仰之間矛盾。這樣一來,宗教關(guān)系中這一矛盾的解決被完全納入到認(rèn)識(shí)論的領(lǐng)域,人對(duì)上帝的認(rèn)識(shí)程度關(guān)乎到人和自身固有本質(zhì)的統(tǒng)一程度,只有認(rèn)識(shí)到上帝乃是人自身的固有本質(zhì),就能內(nèi)在地達(dá)成本質(zhì)與意識(shí)的統(tǒng)一、屬人的本質(zhì)與自己(主體)的統(tǒng)一,人的宗教意識(shí)也隨之得以消解,個(gè)人得以解放。“人對(duì)上帝的知識(shí)乃是人對(duì)自己、對(duì)自己所固有的本質(zhì)的知識(shí)。只有本質(zhì)與意識(shí)的統(tǒng)一,才是真理”,而且“只有這樣,我們才獲得了屬人的本質(zhì)與屬神的本質(zhì)的真正的、在自身之中得到滿足的統(tǒng)一——屬人的本質(zhì)與自己的統(tǒng)一。”(52)[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另一方面,在費(fèi)爾巴哈看來,作為實(shí)體的愛(上帝、類概念)和信仰(心情全能)之間的矛盾(53)費(fèi)爾巴哈對(duì)思辨的宗教哲學(xué)中信仰和愛的矛盾的揭露,即“愛使人跟上帝、上帝跟人同一化,因而也就是使人跟人同一化,而信仰卻使上帝跟人分離開來……解除共同的紐帶。由于信仰,宗教跟人的道德性、理性、簡(jiǎn)單的真理感相矛盾;而由于愛,宗教又跟這個(gè)矛盾相對(duì)抗”。(同上,第321頁。)是個(gè)偽命題,費(fèi)爾巴哈將其稱為“不真的本質(zhì)”(54)《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二部分的大標(biāo)題為“宗教之不真的(或神學(xué)的)本質(zhì)”。(同上,第247頁。),并多次將上帝(神)和人之間的對(duì)立或矛盾界定為“虛幻的對(duì)立”“子虛烏有和絕頂荒謬”(55)[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
(三)馬克思對(duì)人本學(xué)的汲取
費(fèi)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zhì)》將神學(xué)歸結(jié)為人本學(xué),認(rèn)為神是人的本質(zhì)或類本質(zhì)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并進(jìn)一步闡明屬神的三位一體就是理性、愛和意志的統(tǒng)一,而這些屬性正是存在于人之內(nèi)但又超乎個(gè)別人之上的類存在(56)[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費(fèi)爾巴哈指明,作為人的絕對(duì)本質(zhì)的上帝,其實(shí)就是人的本質(zhì)。屬神的本質(zhì)正是屬人的本質(zhì),當(dāng)然此處的人區(qū)別于個(gè)體的、現(xiàn)實(shí)的肉體的個(gè)人,是抽象的、獨(dú)立的類存在物。包括基督教在內(nèi)的宗教的秘密在于人使他自己的本質(zhì)對(duì)象化,他又成為這個(gè)對(duì)象化了的人格本質(zhì)的對(duì)象(57)[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宗教把人的力量、屬性、本質(zhì)規(guī)定從人里面抽出來,將它們神化為獨(dú)立的存在者——不管是像多神教中那樣將其中每一個(gè)都當(dāng)作一個(gè)存在者,還是像一神教中那樣歸并為一個(gè)存在著——,因而,在解釋這些屬神的存在者并將其還原于人時(shí),也必須注意這個(gè)區(qū)別”(58)[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33頁,第43頁,第57—59頁,第60—61頁,第247頁,第302頁,第44、17頁,第30—31頁,第44、63頁,第32頁。。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之所以能夠揭露黑格爾倫理國家的神秘面紗,闡明它是從家庭和市民社會(huì)歸結(jié)的抽象(59)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99頁。、是其在政治領(lǐng)域異化的產(chǎn)物,借助的正是費(fèi)爾巴哈的人本學(xué)理論,將他對(duì)基督教本質(zhì)的揭露和批判用于國家制度的批判,不是國家制度創(chuàng)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創(chuàng)造了國家制度。但迄今為止的政治制度都是宗教領(lǐng)域,是同人民的塵世生活相對(duì)立相疏遠(yuǎn)的普遍性的天國,是神的領(lǐng)域。民主制是一切國家制度的本質(zhì),它同其他國家形式的關(guān)系,正如類本身同自己的特殊的種的關(guān)系(60)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2頁。。馬克思正是要通過民主制消解作為類存在的國家制度與家庭、市民社會(huì)之間的疏離與對(duì)立,將抽象的政治制度復(fù)歸給人民。之所以能夠消解上述兩個(gè)領(lǐng)域之間的異化,根本原因在于他受費(fèi)爾巴哈的影響,認(rèn)為這種對(duì)立正如人的本質(zhì)和人的個(gè)體之間的對(duì)立、類與種之間的對(duì)立,是一種內(nèi)部矛盾、虛幻的假象,可以通過改革人的自我意識(shí)解決。
費(fèi)爾巴哈將宗教中的上帝歸結(jié)為屬人的本質(zhì)的理性、愛和意志,使上帝下降為人或者說把人變?yōu)樯系郏谷伺c上帝合為一體。從而,宗教關(guān)系轉(zhuǎn)變?yōu)閭€(gè)體的人與人的本質(zhì)之間的關(guān)系,宗教對(duì)象成了人自身內(nèi)在的對(duì)象,人認(rèn)識(shí)的上帝就是他自身的精神、靈魂,關(guān)于上帝的意識(shí)其實(shí)就是人的自我意識(shí)。“上帝之意識(shí),就是人之自我意識(shí);上帝之認(rèn)識(shí),就是人之自我認(rèn)識(shí)。”(61)[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43頁,第54—57頁。
費(fèi)爾巴哈認(rèn)為,在上帝是人的本質(zhì)這一主賓結(jié)構(gòu)中,作為主詞的上帝其實(shí)是被規(guī)定者,而規(guī)定者成了作為賓詞的本質(zhì)。他進(jìn)而得出上帝應(yīng)該屬于賓詞,而不屬于主詞的結(jié)論;作為賓詞的人的本質(zhì)成為真正的主詞,由此實(shí)現(xiàn)了主賓倒置,既然上帝被人的本質(zhì)規(guī)定著,那么起決定性作用的應(yīng)該是人的本質(zhì)(62)[德]費(fèi)爾巴哈:《基督教的本質(zhì)》,第43頁,第54—57頁。。馬克思之所以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能夠逆轉(zhuǎn)黑格爾倫理國家觀中闡述的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huì)的決定關(guān)系,原因之一正是借用費(fèi)爾巴哈關(guān)于主賓結(jié)構(gòu)倒置的分析,得出了政治國家這一實(shí)存是市民社會(huì)的抽象本質(zhì)的結(jié)論。國家作為主詞成了被規(guī)定者,賓詞卻是規(guī)定者,而第一本質(zhì)的國家就應(yīng)該屬于賓詞而不是主詞,真正的主詞應(yīng)該是市民社會(huì),市民社會(huì)決定著政治國家。恩格斯非常精準(zhǔn)地概述了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實(shí)現(xiàn)的這一轉(zhuǎn)變:“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huì)、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的領(lǐng)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從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看來(這種觀點(diǎn)也是黑格爾所尊崇的),國家是決定的因素,市民社會(huì)是被國家決定的因素。”(6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8頁。由此可見,馬克思在與黑格爾國家哲學(xué)實(shí)現(xiàn)決裂,轉(zhuǎn)向?qū)κ忻裆鐣?huì)的批判的過程中,對(duì)費(fèi)爾巴哈的人本學(xué)理論的借鑒不容小覷。
費(fèi)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zhì)》中主張,神是人的類本質(zhì)(理性、愛或意志)的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從而得出神是人的類本質(zhì)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的結(jié)論。將神復(fù)歸于人自身或者說揚(yáng)棄異化的路徑便是人自身的意識(shí)改革,讓人自身意識(shí)到神是人的類本質(zhì)的產(chǎn)物。如上節(jié)所述,馬克思在論述市民社會(huì)變體為政治社會(huì)時(shí),背后關(guān)涉到人的國家意識(shí)。換句話說,市民社會(huì)中的個(gè)人只有有意識(shí)地參與國家,有意識(shí)地掌握它的一部分,政治社會(huì)才能變?yōu)楝F(xiàn)實(shí)。市民或私人通過改革自身關(guān)于國家的意識(shí)變體為政治公民,可以說這與費(fèi)爾巴哈所主張的意識(shí)改革別無二異(64)例如,馬克思在克羅茨納赫與《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手稿同時(shí)期寫就的致盧格的信中有如下表述:“意識(shí)的改革只在于使世界認(rèn)清自身的意識(shí),使它從對(duì)于自身的迷夢(mèng)中驚醒過來,向它說明它自己的行動(dòng)。我們的全部意圖只能是使宗教問題和政治問題具有自覺的人的形態(tài),像費(fèi)爾巴哈在批判宗教時(shí)所做的那樣。”(《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9頁。)。
在費(fèi)爾巴哈看來,在表述上帝是人的本質(zhì)這一命題時(shí),由于作為上帝的賓詞的人的本質(zhì)是由哲學(xué)的抽象來媒介,從而產(chǎn)生了主詞和賓詞;實(shí)存和本質(zhì)之間的區(qū)別或分離,便產(chǎn)生了實(shí)存或主詞不同于本質(zhì)或賓詞的虛幻對(duì)立。同樣受費(fèi)爾巴哈的影響,此時(shí)的馬克思認(rèn)為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的對(duì)立,只是一種基于實(shí)存和本質(zhì)之間的區(qū)別或分離而產(chǎn)生的虛幻假象。馬克思在此階段沒有否定政治理性,而是通過民主制改革人的國家意識(shí),在他主張的政治社會(huì)中人人都能參與政治生活,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之間的異化也隨之得以消弭。我們可以將馬克思的民主制理論視同費(fèi)爾巴哈的人本主義一元論在政治社會(huì)中的表達(dá),是黑格爾倫理國家觀的替代方案(65)馬克思在《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批判大綱》時(shí)期表述社會(huì)形式時(shí)曾采用三階段論:人的依賴關(guān)系階段(原始共同體)——物的依賴關(guān)系階段(市民社會(huì))——個(gè)人全面發(fā)展階段(共產(chǎn)主義)。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展望未來社會(huì)時(shí)也存在一個(gè)樸素的三階段論:政治和私人領(lǐng)域同一的中世紀(jì)(一元)——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產(chǎn)生分離和對(duì)立的現(xiàn)代社會(huì)(抽象的二元)——市民社會(huì)力圖使自己變?yōu)檎紊鐣?huì),或者市民社會(huì)力圖使政治社會(huì)變?yōu)楝F(xiàn)實(shí)社會(huì)(一元)。(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147—148頁。)。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同樣攝取了費(fèi)爾巴哈的宗教批判,并將其轉(zhuǎn)變?yōu)閷?duì)市民社會(huì)生活和政治生活二元性的批判。在國家中,人是一種類存在物(共同本質(zhì));在市民社會(huì)中,人踐行的是主觀的或?qū)嵺`的宗教立場(chǎng),即祈禱自身得以救贖的心情全能的信仰。在這種意義上,馬克思將市民社會(huì)成員和公民比作特殊宗教的信徒和政治人之間的矛盾,將費(fèi)爾巴哈揭露的作為人的類本質(zhì)的愛和信仰之間的矛盾用于剖析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之間的分裂。正如政治解放完成后,國家成了純粹的普遍性領(lǐng)域(神域),而市民社會(huì)成了私人生活(信仰)領(lǐng)域,政治解放正是宗教關(guān)系的完成。在這種意義上,民主制國家以一種世俗的方式實(shí)現(xiàn)了“宗教的人的基礎(chǔ)”,馬克思由此稱民主制國家才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國家”(66)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3—34頁。。
四、結(jié) 語
馬克思的民主制理論設(shè)想通過不受限制的選舉與被選舉實(shí)現(xiàn)全民參政議政,由此實(shí)現(xiàn)市民社會(huì)變體為政治社會(huì),政治國家的彼岸性質(zhì)消弭的同時(shí),市民社會(huì)中的私人性質(zhì)也隨之得以揚(yáng)棄。民主制的設(shè)想本質(zhì)上不同于西方現(xiàn)行的民主政治,因此不能將其視作資產(chǎn)階級(jí)的政治立場(chǎng)。關(guān)于民主制的二元結(jié)構(gòu)問題,馬克思在尋求人的解放的過程中,確實(shí)經(jīng)歷了從《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時(shí)期的黑格爾的倫理國家觀批判向《德法年鑒》時(shí)期市民社會(huì)批判的轉(zhuǎn)變,但這種轉(zhuǎn)向并不是由二元論轉(zhuǎn)向一元論。馬克思希冀通過民主制理論實(shí)現(xiàn)政治社會(huì),可以說是市民社會(huì)中的去私人性質(zhì),政治國家中去抽象的政治制度的一元結(jié)構(gòu),“即人的自由產(chǎn)物”(67)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頁。。作為民主制理論本質(zhì)上仍然屬于黑格爾的普遍政治理性,與其說這是一種“國家的去政治性和社會(huì)的去私人性”,不如說是一種“純政治性”的政治哲學(xué)的假想方案。費(fèi)爾巴哈認(rèn)為宗教是人的本質(zhì)對(duì)象化的產(chǎn)物,關(guān)乎上帝的意識(shí)就是人的自我意識(shí);受其影響,馬克思認(rèn)為政治國家其實(shí)是家庭、市民社會(huì)的抽象,人民創(chuàng)造了國家制度。另外,馬克思借助費(fèi)爾巴哈在人本學(xué)中關(guān)于主賓結(jié)構(gòu)倒置的分析,顛倒了黑格爾法哲學(xué)中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的決定關(guān)系,市民社會(huì)決定著國家。民主制之所以可行也是受費(fèi)爾巴哈的影響,馬克思認(rèn)為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huì)之間的對(duì)立和異化是基于實(shí)存和本質(zhì)之間的區(qū)別或分離而產(chǎn)生的虛幻假象,可以通過改革選舉和改革人的國家意識(shí),使抽象的政治制度復(fù)歸于人。
馬克思在《論猶太人問題》中發(fā)現(xiàn),市民社會(huì)中的私人等級(jí)和私人本質(zhì)實(shí)質(zhì)上就是各個(gè)人基于特殊目的追逐的私有財(cái)產(chǎn),在政治上揚(yáng)棄私有財(cái)產(chǎn),非但沒有揚(yáng)棄私有財(cái)產(chǎn),反而以私有財(cái)產(chǎn)為基礎(chǔ),他寄予厚望的民主制等同于完成了的政治解放。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xué)批判》中論述的民主制是在人的自由解放維度下的政治社會(huì),而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將費(fèi)爾巴哈的基督教批判轉(zhuǎn)變?yōu)檎闻泻褪忻裆鐣?huì)批判,將民主制限定于僅實(shí)現(xiàn)了政治解放的政治國家,并將宗教解放歸結(jié)為人的解放。馬克思對(duì)政治理性的揚(yáng)棄暗含著對(duì)費(fèi)爾巴哈宗教批判的再批判,筆者將另稿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