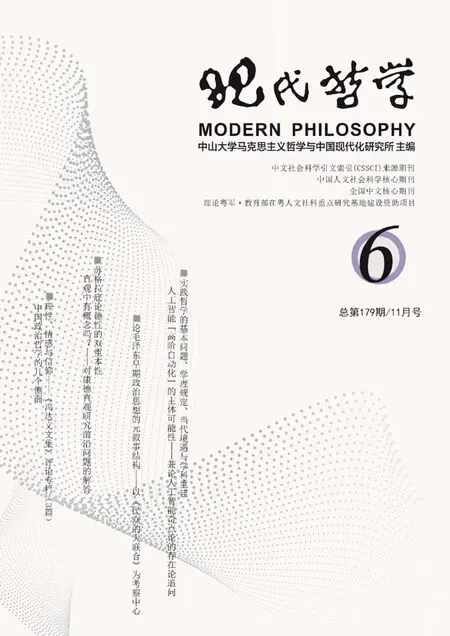責任,抑或是愛?
——列維納斯與馬里翁論人格個體化
余君芷
現象學從起初便與個體化問題結下不解之緣。我們甚至可以說,對主體的個體化思考的不斷深入是推動現象學發展的一個核心動機。以個體化問題為線索,我們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現象學在一代代現象學家中的傳承和變革。列維納斯和馬里翁的個體化理論作為其中的典型示例同時,也表現出一種現象學的卓越性——二者的個體化理論都具有兩個面向:自我的個體化和他人的個體化。馬里翁認為,列維納斯的個體化理論并不徹底。他基于對此的詳細批評,提出自己的個體化理論。然而,一些學者如格施萬特納(C. M. Gschwandtner)和君特(L. Guenther)認為,馬里翁對列維納斯的批評并不公正,并且馬里翁自己的個體化理論相對于列維納斯而言反而是一種倒退。基于對列維納斯和馬里翁的個體化理論的詳細考察,本文試圖指出,格施萬特納和君特實際上錯失了馬里翁與列維納斯的根本分歧所在——人格個體化問題。
一、列維納斯:自我與他人在責任中個體化
列維納斯的個體化理論建基在對傳統西方哲學的總體化傾向的批判之上。“總體”作為一個“統治著西方哲學的概念”,使得“個體被還原為那些暗中統治著它們的力量的承擔者”,以致“個體正是從這種總體中借取它們的(在這一總體之外不可見的)意義”(1)[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朱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頁,第33、48頁。。盡管個體概念是西方哲學的一個重要主題,但支配西方哲學史的理性認知范式通過概念化把諸個體整合進一個總體,使它們的個體性消失在其中(2)[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朱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前言第2頁,第33、48頁。。列維納斯認為,胡塞爾的超越論現象學以及海德格爾的存在論現象學便是這種總體化的代表。胡塞爾所提出的“視域”概念正是那種總體,個體存在者在其中被衡量并且被賦予意義(3)[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朱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6頁。。個體存在者被視為意識構造的成果,但“個體化所具有的實際性在此被翻轉為有關個體的概念,并因此而被翻轉為有關個體之死的意識,在此意識之中,個體的獨特性喪失于其普遍性之中”(4)[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伍曉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201頁。譯文有改動。。在海德格爾處,存在本身相對于存在者具有優先性,這就意味著“與作為一個存在者的某人的關系(倫理的關系)從屬于與存在者之存在的關系”(5)[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7頁。。然而,“存在拒絕接受任何形式的特殊化,也從不進行特殊化”(6)[法]列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吳蕙儀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頁。列維納斯的這個判斷過于絕對,海德格爾強調存在問題并不能以一種單純是形式的、抽象的、理論的方式來通達,而是要回到此在的實存的基本經驗去探尋,此在在“向死而在”中個別化。([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363—365頁。)。
列維納斯認為,總體化的哲學并沒有給真正的個體留下空間。在西方哲學轉向主體性哲學以后,個體概念作為總體化工具尤其成問題。列維納斯將個體所基于的總體批評為“無人稱的”,更確切地說是“非人格的”(7)[法]列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第二版序言第1頁,正文第4頁;[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7頁、33、232頁等。,個體由此喪失了其個體性和人格性。對列維納斯而言,真正的個體應是獨一無二的、不可替代的,作為個體的主體應當是人格性的。它的個體性不來自比較,也不來自被涵括在某個概念的外延中,也不來自它偶然的或本質的屬性(8)[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前言第3頁;[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31—33頁。。這樣的個體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倫理和正義要求這樣的個體性作為它們的可能性條件(9)[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236頁;[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146頁。。那么,作為個體的主體,其獨一無二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如何被建立的?列維納斯的回答是:通過與他人的關系。但這種關系不能重新構成一個總體,而應允許自我與他人之間留有絕對的距離,不會彼此吸收或消解、而是彼此保存,同時二者又有直接的的關聯(10)[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81—185頁。。在這種關系中,自我與他人都是獨特的,也是人格性的。這是列維納斯一貫堅持的論題。雖是如此,列維納斯對于這個論題的具體論述在不同時期有著不同面貌(11)關于列維納斯前后期理論的一些主要變化及其原因和理論后果,參見余君芷:《論列維納斯哲學中“愛欲”理論的轉變》,《理論月刊》2019年第12期。。
列維納斯早期著重于探索主體逃離其實存的牢籠的可能性。雖然主體通過具有身體而在匿名的存在(il y a)中具有一個位置,使主體能夠占有它自身的實存(existence),但主體從此就被束縛在它的實存之上,“如同自我(moi)被牢牢地系縛于無人稱的自身(soi)”(12)[法]列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第102頁,第108—109頁,第117頁。。主體厭倦其實存,卻無法擺脫這個重負,因此主體渴望一種逃離。這種困境的出路在于主體與他人之間的具有超越性的關系,一種“無媒介、無協調人的關系”,“令人敬畏的面對面(face-à-face)”。在《從實存到實存者》(13)筆者以為《從存在到存在者》譯為《從實存到實存者》更為恰當,因此在正文中選用《從實存到實存者》的譯法,在注釋中保留引文所出自的中譯本的書名譯法。和《時間與他者》中,愛欲(éros)是這種關系的代表(14)[法]列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第118—119頁;Emmanuel Lévinas, Le temps et l’autre, 9ème éd.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pp.79-81.。在愛欲關系中,他人的他異性(alterité)與形式上、邏輯上的差異之間有著根本區別,他人的他異性從女性(feminité)概念得到規定(15)Ibid., p.14.。在列維納斯早期著作中,“個體化”這個術語并不常見,但主體對自身實存的占有——成為一個“實存者”——就是一種個體化。后來,“個體化”概念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并且列維納斯早期的主要思想都被吸納到他之后的論述之中。
到《總體與無限》時期,“個體化”成了列維納斯一個正式術語。自我通過身體來占有它的實存,這個事件被細致地描述為一種“家政”“內在生活”“心靈現象”“享受的自我主義”,它以“自身聚集并擁有表象”(16)[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為特征。這種內在生活就是自我的個體化原理(17)[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這種個體化并不是作為概念的個體化,自我由此獲得的獨一無二性(unicité)是一種外在于任何種屬的獨特性(18)[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
自我在內在生活中的個體化,已經以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面對面關系為前提(19)[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面對面是一種倫理關聯,其實質是話語,他人在其中作為“面容”自身顯示為絕對的他者,與自我保持著絕對的距離即保持著超越,因此他人與自我并不構成一個總體(20)[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他人顯示為坦率的對話者,并且面容本身已經是一種原初的表達、一種促使我對他負責的命令和呼喚(21)[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面對面作為自我個體化的前提,并不是在存在者層面或者存在論層面的奠基,而是為自我的內在生活提供倫理正當性。一方面,面容的坦率和赤裸是一種擺脫了任何形式的、憑其自身的顯現;另一方面,這種赤裸也是一種赤貧,他人作為陌生者和一無所有者來臨到我,向我投來懇求和要求的目光(22)[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他人的這種“臨顯”質疑自我享受的合法性,質疑我的自由并使我羞愧;但同時,他人的在場也為自我的內在生活的自由授權,即賦予其倫理正當性:自我的家政是為了歡迎他人,將自我所占有的東西呈交給他人,以此回應他人的面容的呼喚,對他人負責——這也是自我的言說的實質(23)[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在面對面的關系中,他人作為人格性的存在者呈現自身,自我也在他人對我的呼喚(appel)之中作為能負責者(responsable)而達到自身最終的實在,也就是人格性的實在(24)[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但在《總體與無限》中,愛欲關系已不再是面對面關系的典范,而是與其截然不同,愛欲中的他人是“非人格的和非表達的”(25)[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
自我和他人的個體化的根本來源在于作為話語關聯的面對面關系。在面對面關系中,自我 “作為對話者,作為不可取代的、獨一無二的存在者,作為面容”(26)[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132頁,第33、129頁,第95、97頁,第133、150頁,第10、11頁,第41、185頁,第50—51頁,第51、60、64、158頁,第122、163頁,第244、255頁,第241頁(譯文有改動)。而具有個體性。 “作為面容”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表達,它意味著當自我作為出發點時,他人作為面容向自我展現;反之,當他人被放到自我的位置上,自我相對于他人來說就是他人的他人,自我作為面容向他人展現。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上述引文所表達的自我的個體性同樣適用于他人。
與《總體與無限》相比,《別于存在》的論述更多集中到自我之上,“獨一無二”成為形容自我的高頻詞。《總體與無限》將自我規定為在家政中自身聚集的同一者(le Même),而在《別于存在》中,自我這種同一性被明確否定了(27)[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192頁,第146(譯文有改動),第146頁。。在此,自我的獨一無二是一種“沒有同一性的獨一無二”,即“作為不具同一性者,此一者(l’un)[自我]超出了那在自身之內并且為了自身的意識,因為此一者已經是對他者的替代”。
自我“不具有同一性”,意思是不具有傳統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同一性,后者意味著自身對自身的認同或者自身到自身的返回。對列維納斯而言,自我是身體性的主體,在身體性的完全被動性即感受性中,自我暴露于他者對自我的傳喚(assignation)(28)傳喚(assignation)是一個法律用語,意為傳訊某人到法庭接受審判。這與《總體與無限》中所說的“末世論審判”相呼應,主體正是在這種傳喚中從總體超拔出來,在對責任的承擔中具有無可替代的個體性。([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234—236頁。),這種傳喚并不將我帶回到自身之上,而是“從我身上剝除所有同一性的本質”(29)[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128頁。László Tengelyi認為,這是列維納斯在自我的同一性問題上相對于《總體與無限》作出的最大改動。實際上,列維納斯一直堅持自我的非同一性,即自我在其自身性中的分裂,只是在不同時期對這種非同一性有不同論述。在《從實存到實存者》中,這種非同一性表現在自我對自身實存的厭倦;在《總體與無限》中,這種非同一性表現在生育之中;在《別于存在》中,這種非同一性表現在自我總是處于他人的呼喚的擾亂之中。(László Tengelyi, “Einzigkeit ohne Identit?t bei Levinas”,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VI, 2006, p.66;[法]列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第107—109頁;[法]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第260頁。)。自我向自身返回的通路被阻斷,自我由此被“去中心化”,成為一個“為他”的主體,自我從而具有一種更根本意義上的同一性、自身性和主體性(30)[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193—252頁,第141—142頁,第265—284、251—252、214頁,第209—210頁。。自我在被動性中的暴露是無法逃避和拒絕的,這種被動性本身就是對他者的傳喚的回應、對他者的責任的承擔;因為這是完全的被動性,所以無論自我愿意與否,自我的主體性都在于獻出自己而為他人受苦,以至于以自身替代他人的程度(31)[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193—252頁,第141—142頁,第265—284、251—252、214頁,第209—210頁。。正是在這種對他人的傳喚的回應、對他人的替代中,自我被個體化,以至成為“獨一無二者”,成為人格性的主體,(32)[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193—252頁,第141—142頁,第265—284、251—252、214頁,第209—210頁。。他人作為面容向我發出呼喚,他的個體性不是個體對象的個體性,而是一種“極端的獨特性”(singularité extrême),它是他人對我的傳喚本身,并且他“在我將他作為τóδε τι[此,某]而指出之前就已經傳喚了我”,“他在被認出之前就命令了我”(33)[法]列維納斯:《另外于是,或在超過是其所是之處》,第193—252頁,第141—142頁,第265—284、251—252、214頁,第209—210頁。。
綜上所述,主體的個體化通過與他人的關系來達成,這的確是列維納斯一貫的堅持。雖然列維納斯在不同時期對這種關系有不同描述,但與他人的關系始終具有一種神學深度。這不但體現在列維納斯對諸如“臨顯”等神學術語的直接借用,以及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模型(無論是早期的愛欲關系,還是后來的面對面關系)對圣經的明顯參照,更體現在上帝被列維納斯視為他人相對于自我的絕對的他異性、超越性和在先性的前提,也是自我向他人負起責任并在責任中替代他人的根本動機:“上帝并不單純是‘首要的他人’或‘最卓越的他人’或‘絕對的’他人,而是異于他人,而且是另一種方式的他人,這另一種方式的相異性先于他人之相異性、先于對鄰人的倫理責任,這上帝和所有的鄰人都不一樣,他超越甚至于不在場,甚至于可能和il y a(有、存在)之冥然兀在(remue-ménage)融合起來。在此融合中,對鄰人的替代得以‘破出存在’,也就是說贏得了尊嚴;在此融合中,無限之超越得到顯耀。”(34)[法]列維納斯:《論來到觀念中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15—116頁,第114頁。因此,上帝也是自我與他人在彼此關聯中得以個體化的根本原因,只是上帝并不是作為在場的存在者起作用,而是作為“無限”,作為一種“卓越意義上的善”(35)[法]列維納斯:《論來到觀念中的上帝》,王恒、王士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15—116頁,第114頁。。
雖然列維納斯的個體化理論涉及自我和他人,但實際上在《總體與無限》和《別于存在》中,列維納斯對個體化的論述主要還是集中在自我身上,對他人的個體化著墨不多。這成為馬里翁批評列維納斯的出發點。
二、責任的個體化的不充分性
馬里翁對列維納斯的批評著眼于他人的個體化問題。在《圣愛緒論》的第六章《愛的意向性》中,馬里翁將他人的顯現方式規定為他人施加到自我之上的意向性,即“反意向性”(contre-intentionalité)(36)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他人對我的注視在我之中激起一種責任感,我感到自己對他人負有無限的責任,我對這種責任的意識超過了對我自己的意識,它壓垮我,拆解純粹自我的意向性,使我向他者敞開(37)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它阻止了超越論意識向自身的返還,使自我意識到自己對另一個意識有所意識(38)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在這種意識中,對于自我而言,他人具有優先性和在先性(39)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 104, p. 108-109, p. 110, p. 114, p. 115, p.116, p.117.。
這里表現出對列維納斯的面容理論的明顯繼承。然而,馬里翁認為,“反意向性”雖然在自我之中產生某種特殊感受,卻不足以使他人個體化,因為命令涉及所有他者,它激起的是義務(devoir)。義務具有形式普遍性,不取決于具體涉及的是哪個個人。律法的命令感觸我(m’affecte),在我之中產生一種敬重,這種感觸使得普遍的命令在我之中具有一種類似我的感受的特殊性(particularité),但此敬重并不是對某個體他者的敬重,而是對普遍律法的敬重,某個他者的面容只不過是律法的普遍者借以感觸我的一個中介。這里有一種對他者的中性化(neutralisation),他者的面容仍是可替代的。如果要使命令導向對他者的個體化,就需要從義務過渡到責任(responsabilité),即我并非通過他人來服從命令,而是通過命令直接對他人負責。然而,在責任中,他人被中性化的疑慮仍然沒有消除,這里仍存在替代的可能性,因為責任的無條件性——只要是一個面容,我都對其負有責任——蘊含了一種普遍性(40)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117, p.119.。責任雖能觸及如其所是的他人(autre comme tel),卻不能觸及對我而言是嚴格不可替代的某個他人(tel autre),不能達到一種“原子級的特殊性”(particularité atomique)、一種“這性”(l’haecceitas)(41)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3ème éd. ré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ditions de la Différence, 2007, p.117, p.119.。
在另一處文本《從他人到個體》中,馬里翁通過梳理列維納斯各個時期的個體化理論來詳細說明這一觀點。他認為,列維納斯出發點在于用倫理學來克服海德格爾的實存的匿名性,(42)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他試圖建立實存者(existant)相對于實存(existence)的優先性,即自我通過其身體性的受苦(souffrance)把實存占有為“我的”實存(43)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但自我在這個意義上的個體化是不完善的,所以列維納斯將自我對他人的通達視為個體化的途徑,在這種情況下,自我和他人都被個體化(44)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列維納斯首先將這種情形規定為愛欲關系,在其中,他人作為“女性”與自我面對面。但馬里翁認為,將他人規定為“女性”相當于將他人“中性化”,因為這里并不涉及某個不可替代的他人;并且,因為愛欲關系指向生育,他人只是通向孩子的一個環節,所以在愛欲之中重新建立起一種匿名性,我并不與一位獨特的他者有關系(45)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
在《總體與無限》中,列維納斯分析的重點轉向面容。面容所發出的命令“你不可殺”使得自我體驗到他人的反意向性,它被視為他人的人格性的顯現。但面容的困難在于它只表明這是他者,卻不表明是哪位他者:“我,我自己,被面容的呼喚個體化,但面容,它自己,仍然是無人的面容(celui de personne)。就此,唯我論被重新建立,只是倫理學的唯我論代替了認識的唯我論。”(46)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馬里翁認為,面容的個體化并不徹底,是因為面容缺乏明確的辨識,它只是作為一個命令被聽見,但它不能被賦予一個專名,也不處于任何關系系統中(47)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他進而提出三點理由來解釋為什么面容仍然是無人格的、匿名的:首先,面容所宣告的“你不可殺”這條命令是一條普遍應用的命令,對任何一個他者都適用,他者并沒有顯示出任何個體性,都只是匿名的;其次,面容具有欺騙的可能性,它“壓制、掩蓋了個體性,即便——毋寧說,因為——它開顯了無限者及其匿名的超越性”;再次,列維納斯的“分離”的概念僅僅加深了自我的個體化,而不是他者的個體化,因為倫理學總是指涉道德律,道德律的普遍性要求對他者的特定性不予考慮(48)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所以,面容所隱含的這種普遍性最終不但掩蓋他人的個體性,也會掩蓋自我的個體性(49)J.-L. Marion, “D’autrui à l’individu”, Studia Phaenomenologica II, 2002, pp.13-14,p.15,p.16,p.17-18,p.21,p.23,p.24,p.24,p.27,pp.29-30.,因為對自我的考量也會上升到普遍性的層面。
馬里翁認為,列維納斯在《別于存在》中建立了愛的統一含義,愛因此變成本源的,并且愛使得自我與他人個體化。馬里翁還提到,在一場辯論中,他向列維納斯提出將愛放在第一位、倫理學放第二位,列維納斯表示同意,并說作為愛的“對象”的他人是獨一無二的。從內容來看,《從他人到個體》似乎只是闡述了列維納斯在他思想發展過程中如何一步步克服之前階段的困難,最后達到“自我和他人在愛中個體化”。我們很難說這是列維納斯自己的觀點。一是因為列維納斯在《別于存在》中談到愛不過是寥寥數句,并且涉及愛的文本中也無跡象表明列維納斯將愛視為比倫理學更為本源,或是把愛規定為自我與他人的個體化原理。二是因為列維納斯的贊同僅是口頭的,并沒有其他文本進一步闡明這種贊同。但我們能確定的是,《從他人到個體》提供了迄今為止對列維納斯個體化問題的最為全面的批評。而“自我與他人在愛中個體化”,毋寧是馬里翁自己的觀點。
三、馬里翁:愛的個體化
馬里翁的這個觀點先是在《愛的意向性》中得到表述。上文提到,馬里翁將他人的顯現規定為“反意向性”,即他人施加在自我之上的意向性。自我與他人的“目光的交叉”被規定為愛,自我與他人的“原子級的特殊性”(“這性”),只有在愛中才能被達及;他人要求這樣的“這性”,因為只有這樣,命令才能夠使我體驗到他人的目光施加于我(50)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pp.110、119、121,pp.122-125.。馬里翁對 “這性”的追求相比于列維納斯似乎是一種倒退,因為對列維納斯而言,他人在傳喚中的個體性比他作為“此,某”的個體性更加本源。然而,馬里翁所說的“這性”與列維納斯說的“此,某”的個體性不是同一回事,后者指傳統存在論中的單個存在者或對象意義上的個體性,前者指一種嚴格的不可替代性。對馬里翁而言,愛是責任的條件。在他人的目光之中,他人親身呈交出他自己,并在這種呈交之中達到最后的個體性,自我亦是如此,自我和他人對彼此而言都不可替代——這也屬于愛的規定(51)J.-L. Marion, Prolégomènes à la charité, pp.110、119、121,pp.122-125.。但這個觀點并不能使馬里翁的個體化理論與列維納斯的拉開距離。把個體化的動機僅限于對反意向性的回應,馬里翁似乎只是將列維納斯所稱之為“責任”的東西冠以“愛”的名稱。然而,這一點在之后發生很大變化。馬里翁通過他的“現象學三部曲”——《還原與給予》《既給予》(étantdonné)《論多出》(Desurcrot)——建立了被給予性現象學框架,并用它來分析愛的現象。 “自我與他人在愛中個體化”的觀點在《情愛現象學》中發展成更復雜的理論。
在上述“三部曲”中,馬里翁試圖提出一種比胡塞爾的超越論還原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論還原更根本的還原即“向被給予性的還原”。這種還原旨在使現象擺脫前兩種還原所施加的先天限制,使現象真正按照其最本源的自身被給予性顯現(52)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這種能夠按其被給予性自身顯現的現象就是“充溢現象”(le phénomène saturé),即直觀充滿并溢出意向的現象(53)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馬里翁按照被給予性等級從低到高的順序,列舉出充溢現象的五種類型:事件、偶像、肉、圣像(面容)、啟示。其中,啟示集中了前面四種充溢現象的特征以及它們的最大化程度(54)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馬里翁規定現象的被給予性等級是基于它們的個體化程度(55)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可見,在馬里翁處,個體化是被包含在現象的自身展現的本質內涵之中的。
充溢現象的顯現要求一種純粹接受的主體,這種主體接受那自身給出者,也從自身給出者處接受它自己。馬里翁將這種主體稱為委身者(l’adonné)(56)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對馬里翁而言,胡塞爾的超越論自我以及海德格爾的此在都具有個體化和唯我論的疑難,而委身者擺脫了這些疑難,它在獲得個體性規定的同時也保留了被給予者的他異性,走出唯我論的困境(57)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2e éd. Corrigé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8, p.28, pp.314-315, pp.318-335,p.325,p.390,pp.348-369.。
充溢現象的個體化不僅包含現象本身的個體化,而且包含委身者的個體化。當委身者接受那自身給出者并使其現象化時,委身者自身也因此被現象化。這種模式被馬里翁稱為“顯影”(révélation),自身給出者和委身者既是“被顯影者”(révélé),也是彼此的“顯影劑”(révélateur)(58)J.-L. Marion, De surcrot: études sur les phénomènes saturés,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1, pp. 61-62.“顯影”和“顯影劑”都是攝影的術語。。自身給出者和委身者的顯影強度是正相關的,當委身者更多地、更大強度地現象化自身給出者,委身者自身也會更大程度地被現象化(59)J.-L. Marion, De surcrot: études sur les phénomènes saturés, pp. 63-64.。由于個體化程度是衡量現象被給予性程度的指標,因此當顯現的充溢現象被給予性程度越高,個體化越充分,委身者的個體化程度也越高。
馬里翁正是將“向被給予性的還原”以及“充溢現象”的理論應用到對愛的分析之中。在《情愛現象學》中,本源的愛的現象是通過“愛洛斯還原”(la réduction érotique)來通達的(60)[法]馬禮榮:《情愛現象學》,黃作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307、364—371頁。(黃作將馬里翁譯為馬禮榮。)。愛洛斯還原就是向被給予性的還原在交互主體性——即一個委身者向另一個委身者給出自身——上的應用(61)同上,第40—41頁;J.-L. Marion, étant donné: essai d’une phénoménologie de la donation, pp.442-443.。它是一個復雜的、多階段的過程(62)對愛洛斯還原的過程的概述,參見余君芷:《愛洛斯還原不是一種現象學還原嗎?——與Claude Romano商榷》,《安徽大學學報》2019年第2期。。在它的終點處,愛的現象完全自身展開,而處于愛洛斯還原中的自我與他人都會達到各自的和彼此的最后的個體性,也就是人格(la personne)(63)對于“La personne”(person)一詞,黃作譯為“個人人身”。筆者以為,這個譯法并不能很好地體現出這個術語本身所帶有的神學意味(畢竟在《情愛現象學》中,這個術語是與啟示現象密切相關的),也不利于我們考察列維納斯和馬里翁的個體化理論之間的關聯(下文將指出,這個術語實際上是二者的分歧的焦點所在)。所以,本文將此術語譯為“人格”,指“人的位格”。的個體性。因此,愛洛斯還原也是自我和他人的最終個體化的進程。
愛洛斯還原也是通向啟示、通向上帝的進程。愛洛斯還原雖然從兩個委身者之間的關系出發,卻最終展示出上帝作為最初的和最終的愛者,是愛的現象的根源,是愛洛斯還原整個動力機制的推動者(64)[法]馬禮榮:《情愛現象學》,第407—408、418—419頁。。對上帝的通達正是自我和他人最終個體化的條件。愛的現象的通達和啟示現象的通達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因為愛洛斯還原的諸階段之中,事件、偶像、肉和圣像的現象依次展開直至啟示,正對應了啟示現象的特征,即它集中了前四種充溢現象的特征。在每一個階段,都有所對應的充溢現象的個體化。
由于篇幅問題,我們在此無法詳細說明愛洛斯還原每一階段如何依次對應于各個類型充溢現象的個體化(65)參見余君芷:《愛洛斯還原是根本的還原嗎?——基于個體化問題的考量》,博士學位論文,中山大學哲學系,2019年。。我們只需要指出最關鍵的一點:雖然自我和他人的最終個體化即人格的個體化需要經過事件、偶像、肉和圣像等環節,但并不是其中某個環節達成的,而是通過用信心領受彼此的誓言、作出一種以忠誠委身為特征的“有預支的決斷”(résolution anticipatrice)并將誓言委托給一位永久保證此誓言的第三者(最終是上帝)來達成的(66)[法]馬禮榮:《情愛現象學》,第364—371、400頁。。雖然馬里翁描述愛洛斯還原的不同階段時都使用了“源初的個體性”“最后的自我性”等字眼,但這僅僅意味著在愛洛斯還原開啟以后,我們進入一個源初的和最后的現象領域,這個現象領域本身仍需要一個最后的過程才能完全自身展開,所以我們不能將過程中的某個環節視為自我和他人的個體化進程的盡頭。自我與他人的人格個體化以通達啟示即上帝的神圣位格為條件,但這個條件本身作為在先者卻在愛洛斯還原的最終處得到開顯(67)同上,第407頁。,這表明愛洛斯還原的根本性。
四、模糊的焦點:人格問題
馬里翁對列維納斯的批評遭到格施萬特納和君特的反對。她們試圖通過梳理列維納斯的個體化理論來表明,馬里翁對列維納斯的批評是不公正的,因為列維納斯對他人的描述中那些被馬里翁視為中性的、匿名的要素,實際上構成而不是抹消了他人的獨特性。并且,她們反對馬里翁“他人在愛中個體化”的觀點,馬里翁所說的愛反而會給他人帶來列維納斯所反對的那種總體化的暴力(68)Christina M. Gschwandtner, “Ethics, Eros, or Caritas? Levinas and Marion On Individuation of the Other”, Philosophy Today, Vol. 49, Núm.1, Abril 2005, pp.70-87; Lisa Guenther, “‘Nameless Singularity’: Levinas on Individuation and Ethical Singularity”, Epoché, Vol. 14, Issue 1, 2009, pp.167-187.。誠然,格施萬特納和君特確實指出了馬里翁在論證細節方面的一些問題,然而,她們的批評錯失了馬里翁與列維納斯的分歧的焦點,因此只是流于表面。這里不打算展開這些細節問題,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被錯失的焦點之上。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馬里翁并不否認列維納斯在個體化問題上的成就,他只是要在此基礎上前進一步。這可以從馬里翁對列維納斯理論的評價、吸收和利用中看出來。《愛的意向性》和《從他人到個體》中,馬里翁對愛的個體化的構想都不是在否定和拆毀列維納斯的個體化理論,而是把愛作為自我和他人在責任之中個體化的根據。列維納斯所說的自我被他人的面容所表達的誡命所“鎖定”從而被個體化這種情況,被吸收到《情愛現象學》的交叉現象的個體化環節之中(69)[法]馬禮榮:《情愛現象學》,第176—195頁。。所以,馬里翁批評的關鍵不在于列維納斯的理論是否個體化,而是他所說的個體化究竟到了什么程度。這就涉及一個問題:怎樣的個體化才是最終的、最根本的個體化?馬里翁將最終的個體化規定為人格層面的個體化,只有愛能通達這種個體化。而在列維納斯處,人格個體化是在面容中發生的。所以,馬里翁和列維納斯個體化理論的分歧正是在此,這也是格施萬特納與君特所錯失的關鍵之處。這就是為什么盡管她們指出了馬里翁的批評的不妥之處,但仍不能使之失效。
然則,令人驚異且困惑的是,“人格”(la personne)概念這個如此關鍵的焦點,在列維納斯和馬里翁處卻是“模糊的”,因為我們不能從二者的文本中找到對人格概念的任何正面規定。他們使用這個概念,仿佛這個概念是自明的一般。然而,從使用的語境看,我們確實能夠看出二者對于人格的理解的相同與相異。相同之處在于:第一,二者所說的人格并不是指經驗科學意義上的、個體的心理特征總體,而是一個形而上學概念,它指的是主體的最深層、最本源的層面,這也是主體的最本己、最根本的個體性所在;第二,二者所說的人格都具有神學的深度,上帝被二者視為人格的展現的根本條件。相異之處在于:在列維納斯處,人格更多地與倫理和責任相關;而在馬里翁處,人格更多地與愛相關。由此可見,列維納斯和馬里翁的人格概念各自承接了猶太-基督宗教所賦予的一部分形而上學和神學內涵,他們的不同側重卻表現出猶太教精神與基督教精神之間的張力。
這樣一種承接不禁使我們想起雅尼各(D. Janicaud)所提出的“法國現象學神學轉向”的著名批評。然而,現象學并非在法國現象學處才“轉向”神學,而是在其創立者處就已經與神學有著密切關聯,并且這種關聯在整個現象學發展歷程中就沒有斷過。問題的關鍵毋寧是,現象學對于神學的提及究竟是不是以一種違背現象學原則的方式進行的?這里是不是涉及把神學的超越性非法走私到對源初現象的探尋之中,把所要驗證的命題偷偷地當作前提,從而形成一種無效的虛假論證?對神學元素進行描述是一回事,用現象學的方法發現其來源以及證成其真理性則是另一回事,而后者勢必游走在非法的超越性的危險邊界之上。如果人格作為人的最本質的主體性層面的這個規定來源于上帝的啟示,那么對于這個規定的證成必須基于對啟示的證成。要注意的是,這里說的證成并非指的是證明上帝的實有的存在,而是建立一種對具有絕對超越性和神圣性的位格的被給予性的現象學闡明,這種闡明可以提供在體驗的內在性中所展開的現象與這種內在性所不能涵括的絕對超越性和神圣性之間的明見關聯。這種證成和闡明意味著,人格和啟示在主體的內在性之中都有對應的體驗,并且這種體驗自身表明為一種源初的、終極的體驗,是其他一切體驗的根據或根源。這是一切涉及神學意義的人格概念的理論所繞不開的難關,也是決定列維納斯和馬里翁在人格個體化問題上孰高孰低的關鍵。這也是我們進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