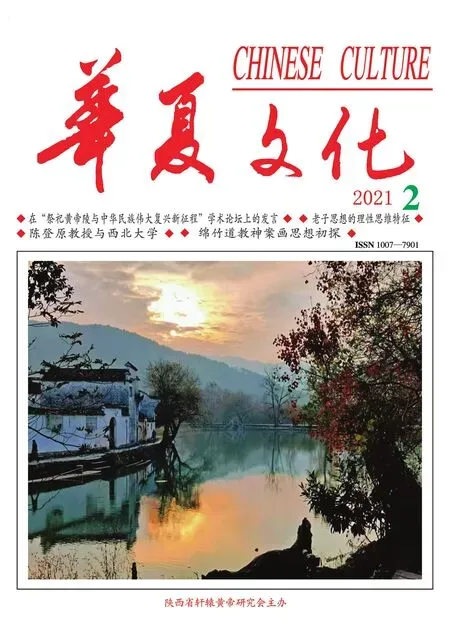陳登原教授與西北大學
□薛淇文
陳登原先生是中國現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出版有《天一閣藏書考》《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國土地制度》《中國田制叢考》《中國文化史》《中國田賦史》等學術論著,在學術界久負盛名。1950年,他應著名史學家、西北大學校長侯外廬的邀請,到西北大學任教,工作至1964年退休。當時的西北大學雖是教育部直屬的十四所重點大學之一,但是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原西北聯大與國立西北大學時期的著名學者陸懋德、黃文弼、蕭一山等多已經離開西大。陳登原先生的到來,充實了西北大學的師資隊伍,為歷史學科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成為西北大學歷史學第二代學人的重要代表。
一、在西北大學的教學工作
陳登原先生談及自己的人生感悟時,曾言:“第一就是要教好書,作為教師,教書是天職。”(張思恩:《師恩難忘深情濃——回憶先師陳登原教授》,《光明日報》2015年10月1日07版)在西大任職期間,他在教學上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
第一, 參與歷史系的教學發展規劃并承擔相應的教學任務。自1953年起,他與歷史系的林冠一、姚學敏、冉昭德、陳直、劉清揚等先生共同承擔本科生一、二年級的“中國通史”課程,每周六個學時。1955年,學校進行教學改革,他考慮到史料學與史學史是歷史專業的必修課程,對學生未來的學術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因此單獨開設“史料學與史學史”課程,并計劃與林冠一、黃暉、陳直、冉昭德、劉清揚、姚學敏共同開設專題講授。(《本校1955年教學計劃和長遠規劃》,1955年,西北大學1956-25,西北大學檔案館藏)他每次上課都會準備內容豐富翔實的講義,特別是對一些重要史料的出處,提供了史書資料的名稱及卷次,以便于學生進一步學習時加以參考。在當時學校對各單位組織的教學評估中,陳登原先生的講課受到學生們的廣泛好評。
第二, 為學校選購圖書,使歷史系擺脫了教學資料匱乏的困境。1956年12月,限于歷史系圖書資料的缺乏,教師學習、備課遭遇困境。在劉端棻校長的關懷和支持下,歷史系經過認真討論,特請陳登原教授負責、劉士莪作為副手,一起前往江浙一帶為西北大學歷史系選購圖書。在選購的過程中,古舊書的刻印、地址、年代、函冊、印紙、版本、定價等多方面,陳登原都要親自過目,反復考慮后再做決定。這次江浙之行為西北大學歷史系選購了線裝書七八百種,平裝和精裝書千余冊,其中包括用330元買了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和廉價的“竹簡齋”二十四史, 以及一些叢書、類書、金石、文字、筆記等。這些圖書開闊了師生的學術視野,也緩解了學校因缺少圖書資源給學術研究和教學所帶來的不便。
第三, 積極為學校培養急需的骨干人才,提高西北大學的學術影響力。1956年,陳登原先生與馬長壽被西北大學認定為具有科學研究能力的、少數可以培養科研人才的學者。陳登原先生經常指導并帶領劉清揚、侯志義、李之勤等青年教師進行學術研究。1956年1月,他指導劉清揚助教研究“中國封建社會解體的過程及資產階級的形成”課題,1957年指導李之勤講師并參與研究“清代秦嶺地區的木廠與木工起義”課題,旨在為更恰當地估計清代前期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水平提供資料。1961年,陳登原先生受邀前往東北文史研究院講學,主講中國土地制度史與歷史軼事與典故,同受邀的還有華東師大的鐘泰,北師大的陸懋德,北大的朱謙之等學術名家。由于他的推薦,次年文史所也邀請陳直去所里講《漢書》,提升了西北大學學人群體的學術影響力。
在陳登原先生等知名學者的努力下,西北大學的歷史學科在全國范圍內備受贊譽,當時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就曾專門對來校學習的彭樹智說:“你們西大歷史系真是藏龍臥虎之地”,并表達了對于陳登原、馬長壽、冉昭德、陳直諸先生的推崇。陳登原先生在西大歷史系所做的工作為日后西大史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用唯物史觀指導史學研究
新中國成立后,陳登原先生已年過半百,將近半個世紀形成的學術研究范式與方法早已融入身心,但是他依然積極接受馬列主義,在他所關注的經濟史和歷史人物研究等領域主動利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史學研究。
侯外廬于1954年首次提出“皇族所有制”問題后,引發了學術界對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問題的討論,陳登原先生積極參與了對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內容、形式和特點等問題的討論。他1957年在《人文雜志》創刊號上發表的《試論西晉占田制度》一文,將占田制與南朝占山封澤類比,指出占田制不是分配一般的土地,而是對豪強承包的荒田向農民做出某種程度的開放;發表于《人文雜志》第2期的《明清兩代的私租與田價》一文,通過研究明清時期田價的起落探析歷史的演進,得出“土地改革成為農民正義的要求”的結論,進而指出地主階級阻礙工商業發展,明清兩代起義軍對土地兼并有抑制作用。作為從民國時期轉變而來的史家,陳登原先生在探討“五朵金花”問題時立足于具體歷史時段,用“小而窄”的視角探討大問題。1958年,他在《歷史研究》上發表《唐均田制為閑手耕棄地說》,指出武德均田不過是將無主荒地、閑地、逃戶死口的田宅等分與農民,從理論上回應了古今之辨的相關論爭,并指出既不應將古代制度格外美化,也不能將其一筆抹煞,唐初均田對農民生產生活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這些成果體現了他對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接納與運用,也讓他原本的經濟史研究得到了理論上的指導和升華。
在歷史人物研究方面,陳登原先生積極參與討論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等學術熱點問題。在學習了毛澤東有關農民戰爭的論述后,陳登原先生結合自身以史料考證見長的學術特點,對一些著名農民戰爭和農民領袖進行史料考證和整理,發掘了許多農民起義的史料與事跡,糾正了一些史實錯誤。他在1957年《人文雜志》上發表的《關于李自成之死》一文,對關于李自成之死的多家說法予以條分縷析的考證,排除其為村民所殺的說法,同時指出“李自成為僧說”是人民群眾的美好愿望。同年在《西北大學學報》發表的《關于張獻忠“屠僇生民”的辨正》一文中,他抨擊了舊史家對于張獻忠的歪曲記載,并對張獻忠殺人一事進行考證,指出張獻忠殺人超過十分之六是情理上的荒唐。這些著述都是陳登原以扎實的考證功底并結合唯物史觀進行研究的重要成果。
三、《國史舊聞》的史學成就
陳登原先生史學成就的代表作是他始撰于1938年,完稿于1967年的四冊七十四卷近三百萬字的巨著《國史舊聞》。這部恢宏的著作,雖重在史料的收集、分類和編排,然每個條目下都有作者的評說,實際上是一部記載漢代以后中國歷史的貫通之作。
具體而言,這部著作所取得的史學成就主要體現在,在史料運用上除了充分利用“正史”資料之外,還更多地關注和收集了人們以往所未曾重視的野史材料。陳登原先生完成這部通史巨著依靠的是自己多年整理的史料,所用的方法是抄史料摘錄卡片。“在沒有電腦的時代,這是一個很好的整理資料的方法。陳先生就給學生說你每天抄三張卡片,三年以后你就可以‘橫行霸道’。《國史舊聞》就是他多年來抄的野史資料加以分類的成果。”(劉寶才口述,薛淇文整理:《劉寶才先生采訪錄》,2020年1月)
《國史舊聞》的案語評述也是其一大特點,如他介紹“山人與道號”時在列出有關史料后,案語指出山人有三種類型:“盧藏用者,蓋有山人之實,而無山人之名;太白先生則有山人之名,而無其實;李泌則名實兼至。”(陳登原:《國史舊聞》第3分冊,第144頁)另,《國史舊聞》的許多論斷也多為學者所接受,其案語的被引用達1600余次,特別是他評價秦始皇的案語云:“始皇剛毅戾深,樂以刑殺為威,專任獄吏而親幸之,海內愁困無聊”,廣為人們所熟知。陳氏的案語評述往往一語中的,撥撩紛亂,不泥成論,獨辟新論,正如有的學者評價說:陳氏“博采群籍,條理井然,足見用力之深,我們深為敬佩。”李澤厚在被問及向年輕人推薦哪些書時,也認為“《國史舊聞》是很好的書,值得讀一讀”。(蕭三匝:《改良不是投降,啟蒙遠未完成》,《南方周末》,2010年11月4日,31版)
陳登原先生是20世紀中國史學界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在眾多領域都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的研究風格源于乾嘉,建國以后,他在學術觀上用唯物史觀指導學術研究;在著史方法上,堅持以史料為導向,完成理論與現實的統一;在研究內容上,他既書寫單一的歷史事件也著述大部頭的通史巨制。陳登原先生的學術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后完成轉型與升華,這與他主動接受新鮮事物,有崇高的學術理想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