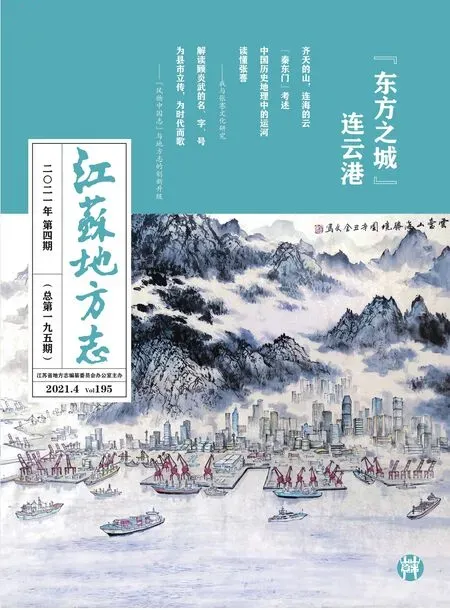親近馬家蕩
◎李廣榮
(江蘇鹽城 224005)
馬家蕩,位于阜寧西南,鹽城、淮安、揚州三市交界地。一直以來,我在文里畫中與馬家蕩一次次深情相見,在我的詩意念想里,她是“浪翻葉色千層碧,波映花光一片紅”的蓮花水國佳境,“馬蕩夏蓮”嫩蕊凝珠、玉潔冰清、清香襲人、風姿綽約,她是一位裊娜娉婷、含羞帶俏的佳人,一幀精美的掛軸,但與我隔著時空的彼岸。
(一)
南宋建炎二年(1128),黃河奪淮以后,巨量的泥沙隨著黃滔侵噬著蘇中、蘇北大地,馬家蕩亦也未能幸免。大量的沙土,隨著泛濫的洪水沖進了地勢低洼的馬家蕩,原來清淺的地方淤積成陸地,積壓的湖水又在蕩區東奔西突,沖刷成縱橫的河道。據《鹽城縣志·湖鄉分志》記載:“自壩水不常東注,(馬家)蕩已涸為田,孫家莊在蕩中,今則陸地可至,非復當日茭葦盤錯,鳧雁為鄰,有滿目汪洋之嘆矣。夫蕩亦非自古有也,舊時鹽邑諸水皆西北匯射陽湖,后黃決入淮,河堤屢潰,射湖淤溢,水無去路,橫溢散漫沒及田廬,潴蓄于卑洼之方,浸淫為蕩。二百年來,田沉水底,桑麻繡壤一望蒲荷,滋者亦澤藪為膏腴。”由此可見,馬家蕩在黃河奪淮的七百多年時間里,黃水泛濫,加速了馬家蕩地區的淤塞,也給馬家蕩地區帶來深重的災難,古詩中有“射陽積雨千村哭,一村無有稻一斛”的描述。到了清咸豐五年(1855),黃河北徙,馬家蕩基本形成了今日的風貌。
馬家蕩的形成,有一個動人的傳說。明朝時候,鎮江金山寺頹塌,誰也不愿修繕。此時,有一馬蕩人叫馬良,他為人耿直,樂善好施。這天,他到鎮江游玩,見天色已晚,便走進一家大客棧,只見客堂里坐了一屋子人,全是鎮江有名的財主富商。其中有幾個認識馬良的,連忙趨向施禮,紛紛邀請馬良坐首席。馬良向左右掃了一眼,只見唯有一席空著,心中正覺奇怪,還未來得及細問,就被眾人連請帶拉地在空位上坐了下來。
馬良剛一坐下,一個和尚捧著文房四寶,就跑到了馬良面前。馬良問起緣故,這才知道,今晚是金山寺住持請客,化緣重修金山寺,疊造一座小土山。按照事先商定的辦法,哪位施主若肯坐首席,就承擔這個工程的大部分資金。所以這個首席一直空著,誰也不敢去坐。剛才大家推推搡搡請馬良坐上首席,這叫明抬舉、暗作踐。馬良聽了,心里著實吃了一驚。但想想也是個機會,何不趁此戳戳這些沽名釣譽、奸猾偽善之徒?馬良不緊不慢,接過紙筆,灑脫地寫了下去。眾人以為寫的是所捐錢財的數目,再一看,都嚇呆了,原來化緣簿上面寫著的是“馬良獨修金山寺”七個大字。這時有個聞名江南的大富翁,氣得搖頭晃腦,大罵“狂生”,責問馬良:“獨修金山,土從何來?”馬良微微一笑,提筆在紙上又加上一句“不用江南一鍬泥”。
馬良回到家中,他說到做到,動工取泥,組織上萬人從蘇北運土南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雇了幾百條大船,日夜兼程運往鎮江。幾年以后,他家的千畝良田變成了一片洼地。馬良又拿出最后剩下的150兩銀子,為金山寺寶塔裝了頂。這時,馬良家財用盡,無法生活,只得四處討飯,最后餓死在金山腳下。后人為了紀念他,在金山上修建了一座馬良廟。而修建金山寺取土后的洼地則成了茫茫水蕩,后人為了紀念馬良,便將這片水蕩稱為“馬家蕩”。今天,在碧水環繞的蕩中小洲上,豎立了一尊馬良白玉塑像,并建有馬良亭,以此紀念這位值得驕傲的馬蕩人。
(二)
馬家蕩在鹽城市阜寧縣馬家蕩鄉境內,處于三市四縣接壤地帶,東與建湖縣毗鄰,西與淮安市接壤,南與揚州市寶應縣隔蕩相望,為古射陽湖的一部分。射陽蕩、收成蕩、沙莊蕩、青溝蕩在此交匯,連成一片,縱橫百余里,是蘇中里下河地區一片廣闊的沼澤地。這一帶溝河縱橫,蕩灘連片,素有“八八六十四蕩,馬家蕩是首蕩”之稱。蕩區面積近3萬畝,蕩蕩是水面。歷史上曾發生多次水旱災害,“雨澤時行,汪洋一片,旱年隨處可以步履”。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溢淮南老壩口,嘉慶十三年(1808)淮決荷水塘,道光十五年(1835)大旱,光緒二年(1876)春鹵水倒灌,這里的人民流離失所,衣不遮體,食不果腹。“彌望蕩中蘆葦,實為大利所在,然每屆夏秋,亦為土匪嘯聚之所。”馬家蕩民眾飽受兵匪之苦。1933年夏,泗陽匪首張志高洗劫益林后,逃竄到馬家蕩。官兵追剿,大軍云集,攻破土圩。1944年1月,國民黨抗日將領馬玉仁殉國后,其外甥計雨亭率余部千余人進駐,是年10月,接受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部隊的改編,成為一支重要的抗日武裝。1949年11月,人民政府開始剿匪,歷時3個月,勝利結束。至此,馬家蕩才真正擺脫了天災匪害,舊貌換新顏。
馬家蕩有著別具一格的原生態蕩灘自然風光。這個美麗的地方,河道縱橫,水清見底,菱藕吐艷,野鶩翻飛。葦蕩深處,春見水草豐茂,夏見濃蔭匝地,秋則蒲蘆搖黃,冬則蘆花飛揚,宛若世外桃源。這里港汊密集,葦蕩無垠,是魚、蝦、蟹棲身之福地,也是家禽飼養的天然好場所,既宜長菱藕、慈姑,又宜河蚌育珠,30公里的經濟林道猶如一條綠色長帶,延綿在錦繡大地上。
馬家蕩自然村落形似水中之龜,俗稱“龜地”,有久雨不沉的說法。如今4個漁民新村依河傍水,排列整齊的白墻紅瓦房臨水而立,正如詩篇里描繪的“散落漁村浮碧瓦,參差云樹宿黃鶯”。這里糧田成片,魚池成方。暮秋時節的水鄉,阡陌黃花爭吐艷,金黃稻穗飄芳香,老農播種迎晨月,少壯捕魚帶晚航,景色令人陶醉、令人神往。
如果把高遠湛藍的天空比作幕,遠遠的水天相接處作為背景,養殖的水產是情感,整個馬家蕩就是一幅鋪陳在淮東大地的水墨畫,白茫茫的蕩面似一張撐開的宣紙,潑上墨,便是一首唐詩,一闕宋詞,或豪放,或婉約,盡顯風情。偶爾見劃槳的小木船蕩漾其間,寧靜,幽遠,一幅古舊的風景鎖住所有的華麗,面對這份自然的和諧,我只想垂下生命之竿,釣一蕩純凈自然的優雅清白,釣一闕秋水長天的悠然意境。滾滾紅塵,也許只有晨起漁樵、暮弄炊煙的古老意境,更能修心養性。
(三)
深秋時節,我站在馬家蕩的堤岸,極目遠眺,河道、田野、池塘相互交錯,想當年,清人呂符惠“移舟更向花深處”,一定是美不勝收。而我則在“十里芙蕖冉冉香,平湖清淺漾波光”的美好詩句里,醉了情懷。一陣微風,幾枚蘆花飄落發間,更似進入夢境。擇水而居,蘆花永遠都散發著水樣的樸素情懷。秀頎的秸稈,素淡的莖葉,水白色的蘆花,一團團輕柔如絮,蓬松疏慵著,隨時都可以臨風飄舉。想折幾根蘆花帶回家,但她們開得太熱烈了,輕輕一碰,四處飛揚。我想,或許她們是馬家蕩上的凌波仙子,有了她們,馬家蕩便增添幾分仙風道骨的韻味。我與蕩,相看兩不厭。
秋季正逢富饒而完美的頂峰。一蕩秋水澄澈見底,兩岸叢樹碧綠夾黃,黃色野菊開得正歡,馨香迷人。以前馬家蕩兩岸的村民,除了種植莊稼,閑暇之余,就是靠捕魚為生。如今的馬家蕩已成為養殖水產的天然好處所。近年,經過開發利用,通過“植草、移螺、調水、稀放”標準生態養殖,“馬家蕩”牌大閘蟹和各種魚類水產已成為“綠色產品”而名揚海內外。據說,馬家蕩大青蟹是中國名貴產品,歷史悠久。蟹體肥大,蟹豐腴,肉質細嫩,口味鮮美,素以青殼白肚、黃毛金勾,又有“黃毛金勾蟹”的雅號而馳名中外,蜚聲大江南北。“海溪湖中皆有蟹,不及蘆葦蕩中蟹”,可見蕩蟹是海蟹、溪蟹、湖蟹中的極品。
柔軟的陽光順著蕩水輕輕地流淌,在眼睫閃動的瞬間,隨處可見為捕捉蟹子掛網籠的木樁,高高低低地插在蕩中央。長腿的白鷺高高地立在木樁頂端,如放哨的戰士,守護著一方領地。不時有水鳥掠過平靜的蕩面,驚起圈圈水暈、點點漣漪。鳥兒在蒼茫的天與蕩間尋找著屬于自己的方向,蕩水永遠是它們的天堂。
大閘蟹上市的旺季,漁人們正將剛從綠色網籠里倒出來的蟹子,按大小公母挑揀,分類上市。待至大閘蟹等水產品收獲之后,進入冬天,蕩內水位下降,水草、蚌螺顯現,大量候鳥來此覓食過冬。萬只候鳥在蕩內集聚、水中嬉戲,那時又將是馬家蕩另一道靚麗的風景。
蕩水在秋光里沉靜,天然的原生態養殖,將馬家蕩打磨成一塊無瑕的美玉,蘊含著飽滿的靈性。可喜的是,隨著歲月更替,滄海桑田,馬家蕩濕地在時代的變遷中,在政府的規劃和建設中,變換了著裝,更改了容顏。馬家蕩不僅僅只是押寶在風光旖旎的蕩里,集“觀魚、垂釣、農家樂”為一體的休閑度假場所,而且現時已經開發出新景區:月牙湖抱起一輪豐滿的摩天輪,傳遞著五湖四海游客的笑聲;三面金像的觀世音菩薩,使你無論從哪個方向去仰望,都是如意吉祥;遠處的古式高腰石橋與近造的西方廊橋相依相伴,中西合璧;淮東古寺的千年銅鐘,叩響歲月沉轉的巨門……馬家蕩的鸕鶿打撈起濕漉漉的回憶,只只都是磨滅不了的鄉愁。而今,馬家蕩正以篤定的步伐,一步步向成熟邁進,成為鹽阜地區的旅游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