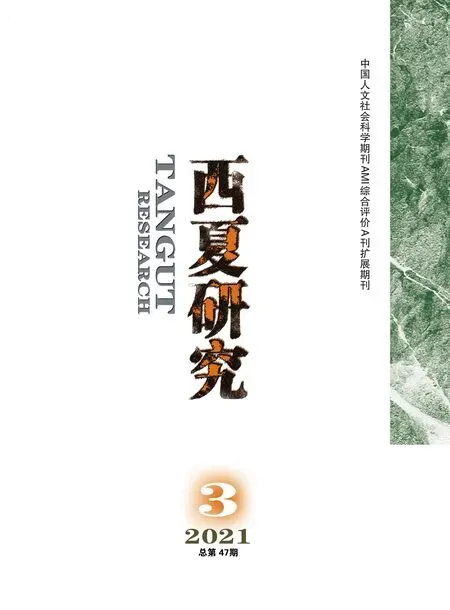西夏社會的借貸自由與債務負擔
——《天盛律令》“催索債利門”的制度透視
□張映暉
《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以下簡稱《天盛律令》)是一部在舊律令的基礎上斟酌損益而成的律令集合,它即是一部反映政權意志的法律文本,又是一部集中體現11—12 世紀西夏社會普遍社會意識和社會制度的百科全書,其編纂體例大體仿照唐朝“以類相從”的模式。[1]2150
《天盛律令》的“催索債利門”集中規定了民間借貸的主體資格、借貸契約形式以及債務負擔的程序與償債措施等內容①。已有學者對“催索債利門”中的具體問題展開論述。史金波結合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貸糧契對《天盛律令》“催索債利門”中的契約制定制度、最高利率、債務清償、違約責任等方面做了述論[2]208-249。趙彥龍在契約制度的文化背景下結合出土的西夏契約文書對“催索債利門”中的借貸制度、違約責任、借貸利率等進行了考察[3]105-111。邵方從西夏“民間契約的書寫格式”、“官私放貸利率”、“違反契約的處罰規定”等方面對“催索債利門”中的各項制度進行梳理和研究[4]95-98。于光建從“債權保障”的角度分別從“契約擔保”、“刑事處罰”、“同借者連帶賠償”等六個方面對“催索債利門”中的各項制度做了剖析[5]108-126。對“催索債利門”中的各條規定進行整合以后,能夠非常清晰地看到一條主線。從借貸契約成立到借貸契約履行,從償債的責任認定到償債的具體措施都有明確的規定。對比同時期宋朝的借貸案例,討論西夏民間借貸秩序,嘗試挖掘這些制度產生的自然地理和歷史社會基礎,這也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
一、催債索利與借貸自由的西夏視野
從《天盛律令》“催索債利門”的內容來看,西夏政府注重保護商事主體的意思自由,主體之間的借貸遵循自愿的原則。這不僅體現在商事主體的范圍方面,也體現在借貸契約的形式和內容方面。與同時期的宋朝相比較,西夏法律對商事主體的資格限制較為寬松,貴族、僧侶、官僚以及庶民都可以參與私人借貸活動。“因負債不還給,十緡以下有官罰五緡錢……”[6]188說明官員也可以是借貸者。此外,西夏的貴族和僧侶是糧食出貸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2]224,而且部分官僚也參與了放私債取利的活動[7]3902。同時期的宋朝,法律規定在任官員不能參與商事活動。《宋刑統?雜律》:“監臨官于部內放債者,請計利以受所監臨財物論。”[8]413放債收利屬于官員的非法所得。南宋《慶元條法事類?出舉債負》也有類似的規定,“諸命官舉債而約于任所償者,計本過利五十貫,徒二年”[9]902-903。值得注意的是,西夏社會中的“卑幼”在不經過自家“尊長”同意的情況下,也可以參與借貸活動。雖然西夏政府嘗試禁止這種社會現象,“催索債利門”中明確“卑幼”私自借貸屬于“不應做”的范疇[6]191,甚至受到“十三杖”的懲罰[6]190,但另一些規定似乎縱容了這一現象的發生,“同居飲食中家長父母、兄弟等不知,子、女、媳、孫、兄弟擅自借貸官私畜、谷、錢、物有利息時,……借債者自當負擔”[6]190-191。同樣,類似于奴仆的“諸人所屬私人”,不能私自借債,但是在有“執主者”的情況下,是可以借債的[6]190。相對比而言,宋朝在法律上反復強調,“卑幼”在不經過家長同意的情況下“私舉公私財物”是無效的[8]205、412。《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多個判決例能說明這一點,“業未分而私立契盜賣”一案中,在祖父去世“服尚未滿”的情形下,行為人私自“立契盜賣田產”,買主明知而交易,“法官”認定該買賣為“違法典賣”,“用錢不追,業還主”[10]303;“母在與兄弟有分”一案中,“法官”提到,“未有父母在堂,兄弟五人俱存,而一人可典田者”,判決“錢沒官,業還主”[10]301。相對來說,“催索債利門”中對商事活動主體資格限制寬松,這更容易促成借貸和買賣關系的成立。
在借貸活動中,契約雙方的自由意愿一般通過紙質載體(例如書面契約)來體現,作為日后雙方在契約履行過程中的證據。“催索債利門”中明確規定,諸人在發生類似買賣、借債等“牽連”時,“各自自愿,可立文據”,“于買價、錢量及語情等當計量……官私交取者當令明白,記于文書上。以后有悔語者時……”[6]189“人口、田宅、畜物”等交易活動更是如此,法律要求必須簽訂書面契約,規定“諸人將使軍、奴仆、田地、房舍等典當、出賣于他處時,當為契約”[6]390。從西夏契約文書上可以看出,幾乎每一份正式的契約文書上都有“本心服”的字樣[2]211,表示契約的簽訂出于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催索債利門”將“誣指”他人欠債的行為等同于“枉法貪贓”[6]190,也就是在非出于對方本意的情況下嘗試占有對方的財產。同樣,西夏法律也禁止在未經他人同意的情況下以他人名義進行借債。“諸人于官私處借債,本人不在,文書中未有,不允有名為于其處索債。”[6]190在田宅的買賣、典當等方面,西夏律令對于中原“親鄰之法”作了一定的“變通”,側重尊重當事人的意愿。從當時南宋的一份判決書來看,“親鄰之法”在法律實踐中得到落實,當時的“法官”援引了一條法令:“諸典賣田宅,四鄰所至有本宗絲麻以上親者,以帳取問……”只要沒有“別戶田間隔”且不超過法定的期間,“親鄰”可以優先“執贖”[10]309。對于類似的情形,《天盛律令?租地門》規定:“諸人賣自屬私地時,當賣情愿處,不許地邊相接者謂‘我邊接’而強買之、不令賣情愿處及行賄等。違律時庶人十三杖,有官罰馬一,所取賄亦當還之。”[6]495杜建錄先生指出,“這里西夏限制土地買賣中的‘親鄰權’,當從防止強買的角度規定”[11]48,《嵬名法寶達賣地文契》中“‘他人先召有服,房親后召’反映了西夏在土地買賣中先問四鄰,后問房親”[11]32。從“防止強買”的角度來看,“西夏限制土地買賣中的‘親鄰權’”,在一定程度上尊重交易當事人的交易自由。
二、催索債利與債務負擔的西夏方案
上述“契約自由”的實現不僅僅依賴西夏政府頒行的法律制度,還以契約雙方按照約定履行義務為前提。《天盛律令》規定,在債務人到期不能如約履行債務時,債權人不能“強力”用債務人的屋舍、畜物和田地等財產來抵債。在借貸活動中,行為人如果違反這種規定,那么其可能面臨著“本利債量減算”的后果。[6]191
(一)催索債利過程中的官方介入
按照《天盛律令》的規定,法律注意區分債務人“負債不還”的不同情形。分別是“賴債不還”和“無所還債”。對于第一種情形,“不還債”被看作是一種“犯罪”,“諸人對負債人當催索……因負債不還給……若違律時,使與不還債相同判斷”[6]188。在這種情況下,債權人可以向西夏政府有關部門尋求救濟,政府“當以強力(對債務人)搜取問訊”,根據不同情形,分別給予債務人不同程度的懲罰,債的“本和利”依然應當還給債權人。對于第二種情況,主要指債務人在契約約定的日期未能還本付利時,則視情形判定。在這里,西夏政府對于借貸過高利息的規定有時候決定著債務的到期日,因為超過最高利息的數額不受法律保護。例如,有借貸契約這樣約定,“天慶寅年正月二十九日立契約者梁功鐵,今從普渡寺中持糧人梁任麻等處借十石麥,十石大麥,自二月一日始,一月有一斗二升利,至本利相等時還,日期過時按官法罰交十石麥,心服”[2]210。結合《天盛律令》“催索債利門”的規定以及一些借貸文書可以發現,“本利相等”可以看作是西夏政府認可的對于債務人欠債不還的懲罰標準之一。例如,有糧食借貸契約中約定,“日過時,一石還兩石”[6]211,也有貸物契中約定,“……借貸七千七百卷[計],期限同月十五日當聚集還。過期時一[計]還二計數,共還一萬五千四百卷”[2]248。“催索債利門”中多次提到,私人借貸的利息超過“本”以后,“應告于有司”[6]188-189,這在法律上限制了債權人牟取暴利的行為,“利息上限”也成為西夏政府干預民間借貸活動的“臨界點”。
(二)催索債利的順位與連帶責任
在“欠債不還”的情況下,西夏法律規定,應該給債務人三次寬限期,到期仍不能還債,則債權人可以申請政府代為“催索債利”。在償債的順位上,分別是“借債者(債務人)”、“同去借者(類似擔保人)”和“持主者(委托人)”②。“催索債利門”規定:“借債者不能還時,當催促同去借者。同去借者亦不能還,則不允其二種人之妻子、媳、未嫁女等還債價,可令出力典債。若妻子、媳比所典錢少,及確無有可出典者,現持主者當還債。”[6]189在提到“卑幼”私自借貸官私錢物時,再次明確了償債的順位,在家長不負擔的情況下,“借債者自當負擔。其人不能,則同去借者、執主者當負擔”[6]191。這里的“執主者”與上述“持主者”的身份相同。但是,“催索債利門”中反復提到的“持主者”似乎在西夏的借貸契約中無法找到。從西夏的借貸契約上可以看到,契約的尾部先后列明“立契約者(債務人)”、若干“同借者”以及若干“知人”[2]210-215。按照史金波先生的研究,“所有糧食借貸契約的契尾第一個簽名的是借貸者”,“為了保證本利的歸還,債主除要求借貸者本人簽字畫押以外,還要求家屬或至親簽字畫押”,也就是上述“同去借者”,“同借者類似擔保人,當直接借貸者發生無力還債、死亡、逃亡等意外時有借貸連帶責任,負責償還”,最后面“知人”的作用“僅僅證明契約行為,不負契約實施的連帶責任”。[2]236-240結合唐宋的借貸契約內容、宋朝的相關規定以及宋代的契約糾紛能夠發現,上文的“持主者”也就是西夏借貸契約以及買賣契約中的“知人”,與唐宋私契中的“見知人”同義[11]350-351。“見知人”在商事實踐中可能承擔著“牙人”的職能。例如,《名公書判清明集》“重疊”一案中,行為人將田宅先后典賣給兩個買主,發生糾紛以后,按照契約內容,“法官”追問身兼“牙人”和“見知人”身份的王安然,結合其他證據證實了其中一份契約的真實性[10]302。在“買主偽契包并”案中,買主偽造契約試圖吞并他人田產,官府認定,契約上沒有家主“知押”及牙人的“證見”,遂認為此契約無效[10]305-306。“母在與兄弟有分”案中,“法官”認定“牙人”敗壞某家不肖子弟,促成交易,“勘杖六十,仍舊召保,如魏峻監錢不足,照條監牙保人均備”[10]301-302。從宋代律令中可以發現,“牙人”和“見知人”不僅僅承擔著上述“撮合”以及“見證”契約成立的作用,在契約的履行過程中還需要承擔擔保責任。《續資治通鑒長編》中記載:“宋元祐五年(1090),戶部言:‘抵當財產……若有折欠,出賣不敷,如本主并保人填納不足者,勒元檢估吏人、牙人均補。’”[7]10865-10866紹熙二年(1191),宋廷規定:“在法:違欠茶、鹽錢物,止合估欠人并牙保人物產折還,即無監系親戚填還,及妻已改嫁,尚行追理之文。……人戶欠負客旅及店鋪價錢……有已經估籍家產,償還不足,依舊監系牙保等……”[12]6695從這些規定中可以看出,“牙保”、“見知人”或“執主者”于債權人承擔的可能不僅僅是有限的償還責任,應該和債務人一起承擔連帶責任。
(三)債務負擔過程中的個體識別
在債務負擔方面,“催索債利門”的相關規定突出個人責任。在債務人與“家長父母、兄弟等”家庭成員同居飲食的狀態下,卑幼不經過家長同意私自借貸,“家長同意負擔則當還,不同意則可不還。借債者自當負擔”[6]191。同樣的道理,“諸人所屬私人(奴仆)”也不能用“頭監(主人)畜物中還債”[6]190。按照上述還債順位,如果“借債者”和“同去借者”不能還債,則不能向兩者的家人索債,但是可讓他們的家人“出力典債”,這里的家人包括“妻子、媳、未嫁女”等[6]189,這里不包括“借債者”和“同去借者”的父母。“出典工門”中明確規定,“諸人不許因官私債典父母”[6]390。與執主者對債務承擔連帶責任相區別,執主者的家人對于債務僅僅承擔有限的擔保責任,以“消費”所借貸錢糧為限。“執主者不能時,其持主人有借分食前借債時,則其家中人當出力,未分食取債人時,則勿令家門入。”[6]189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西夏法令的規定,債務主體“同去借者”、“執主者”與“借債者”承擔連帶責任,但是,上述“卑幼”私自舉債情形中,在“同去借者”與“執主者”不能負擔的情況下,兩者“出工抵債”僅僅限于“分食”所借錢糧的情形。這體現的是一種“過錯責任”,“分食”也說明“同去借者”和“執主者”有貪利之心。宋代也有類似的規定,《宋刑統》“典賣指當論競物業”中指出:“如是卑幼骨肉蒙昧尊長,專擅典賣、質舉、倚當……其卑幼及牙保引致人等,并當重斷,錢業各還兩主,其錢已經卑幼破用,無可征償者,不在更于家主尊長處征理之限。”[8]206這條規定雖然沒有進一步明確“卑幼破用”錢財以后的償債程序,但是可以推斷出后果,家主不助還債,卑幼和牙人應當承擔非法舉債的責任。
(四)作為終極措施的出工抵債
在償債的方法上,《天盛律令》“催索債利門”規定的“出工抵債”頗具特色。查閱中原宋朝的法典可以發現,宋朝開國之初,在債務人無所還債的情況下可以“役身折酬”,與西夏律令中規定的“出工抵債”具有相似性。但是,《宋刑統》中規定“出工抵債”的主體是“戶內男口”[8]412,《天盛律令》“催索債利門”中規定的可出工抵債的主體包括借債者、同去借債者以及執主者并他們的妻子、兒媳和未嫁女等[6]189。顯然,西夏的男丁和成年女性都可以“出工抵債”。這與西夏的社會習俗和社會制度有關,“全民皆兵的制度”使得“人人能斗擊,無復民兵之別”[13]193-194,女性也是軍隊的一員[14]118-122,自然也是一種社會勞動力。《天盛律令》“棄守大城門”規定:“守大城者,當使軍士、正軍、輔主、寨婦等眾人依所定聚集而住……”[6]197這里提到的“寨婦”就是女性。出工抵債者大多為失去田宅、牲畜等財產的貧民,以自己的勞動及所得償還債務,“典押出力人類似債務奴隸,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奴隸,典押出力人償清債務后可離去,借貸方也可以出錢贖回典押人”[15]44。從律令的內容中也可以發現,債務人及擔保人等“出工抵債”的計量方法依據“盜償還工價”之法進行。《天盛律令》“盜賠償返還門”對此有詳細的規定,用以將債務人和擔保人的勞動量折算為財產[6]174。考察宋朝后來的一些規定,政府明確催索實踐中禁止通過“質當人口”的手段來典債。宋至道二年(996)閏七月,宋太宗下詔:“江、浙、福建民負人錢沒入男女者還其家,敢匿者治罪。”[16]99《慶元條法事類》“出舉債負”明確強調:“諸以債負質當人口,杖一百,人放逐便,錢物不追。”[9]902上述償債方法上的差別、債務負擔的機制以及借貸自由的制度設計可能是由西夏獨特的生產方式、自然地理條件、人口狀況決定的。
三、催索債利與西夏社會的立體透視
通過上述考察可以發現,西夏政府似乎在保護借貸主體的意思自由方面具有更為寬廣的視野。但是,與同時期宋朝進行制度上的對比,其殘存的半奴隸制形式的“出工抵債”又令人頗為費解。同時,在卑幼私自舉債情形下,責任承擔的個體識別似乎又與夏仁宗(曾以“天盛”作為年號)的“儒學情結”存在一定的對立,因為儒家相對注重整體的親倫關系。其實,這些看似“另類”的制度設計決定于西夏特殊的自然地理、土地所有制以及人口狀況。
首先,西夏獨特的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糧食相對匱乏,這也導致了部分民眾需要采取“貸糧”的方式來維持基本的生活。貴族、官僚以及僧侶占有大量的土地,他們成為出貸生活資料的主要群體。反映在契約制度上,體現為參與商事活動的主體較宋朝來說更為廣泛。雖然,按照《宋史》的記載,西夏“甘、涼之間”以及“興、靈”兩州皆引河水灌溉,“歲無旱澇之虞”[16]14028,但是這四個州的面積只占全境的一小部分。《續資治通鑒長編》中提到:“夏國賴以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東則橫山,西則天都、馬銜山一帶,其余多不堪耕牧。”[7]11129按照吳天墀先生的研究,就西夏全域來說,“農作物種植的面積不大,收成遠遠不夠人民生活的實際需要”[13]156,再加上“頻繁的氣象災害”經常引起饑荒,這成為西夏“最為棘手的社會問題”,除官方的救濟(例如賑濟、貸糧于他國、榷場貿易等)[17]118-120之外,在市場上進行借貸也成為部分貧苦民眾維持生活的手段。根據史金波先生的研究,“黑水城出土的糧食借貸契約數量最多,有110 多號,300 多件,約占全部契約的2/3,不僅數量大,類型也多,比敦煌石室所出糧食借貸契約多”[2]245。其中的貸糧食者“實際上是缺乏種子或口糧不得已而舉債的貧困者”,而在出貸者群體中,有皇族、國師等,而且利息都很高[2]223-225。由于“黨項貴族大土地占有制是西夏土地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夏皇族對于佛教的重視又使得佛寺和僧侶占有大量的田產,除此以外,自耕農和半自耕農的數量很少[15]1-15。根據吳天墀先生的論述,“西夏統治階級對于擴大農耕土地增加農業收益很感興趣,在諒祚統治初期的國相沒藏訛龐,憑借武力侵耕宋朝麟州西界屈野河外的肥沃土地,‘令民播種,以所收入其家’,把所占的耕地,‘宴然以為己田’”[13]160。在這種情況下,西夏的貴族、官僚和僧侶掌握著大量的生活資料,民眾在缺糧的時候只能向這些富戶借糧。可以說,達官貴族的牟利心理與廣大貧困民眾的謀生需求推動了西夏民間借貸的“繁榮”。
其次,區別于同時期宋朝的財產制度,西夏的卑幼可以擁有一定數量的“私財”,這一點在契約制度和催索債利的實踐中體現為卑幼不經過家長的同意可以“擅自借貸”,家長也可以不助還債。在“別籍異財”的風尚下,責任承擔過程中的“個體識別”亦在情理之中。如上文指出的,在同時期的宋朝境內,法律禁止卑幼私自參與商事活動,最直接的原因是“父母在,無私財”[10]367,卑幼不能在尊長在世的時候分家析產,這種制度設立的出發點是,父母與子女在“同居共爨”的生活狀態下,“均其貧富,養其孝悌”[10]278-279。從宋朝律令的規定也可以發現,“別籍異財”屬于“十惡”之一[8]11,宋太祖在開國之初更是明確,“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其罪死”[7]231。相對來說,在西夏社會中,父母同意的情況下可以“別籍異財”[6]390。《天盛律令》“出典工門”規定:“諸人父母不情愿,不許強謂‘我另往別住’,若違時徒一年。父母情愿,則罪勿治。”[6]390“罪則不同門”規定:“諸人父母不情愿,不許強以謂我分居另食,若違律時徒一年,父母情愿則勿治罪。”[6]609從“謀逆門”中也可以看到,犯“謀逆”之罪者,其部分同居親屬和不同居親屬的待遇是不一樣的,祖父母、父母、兄弟等“非同居”親屬的財產“勿沒收”[6]111。這說明,在西夏社會生活中,存在著祖父母、父母與子孫“非同居”的情況。這種現象從一些出土的西夏戶籍文書中也可以推斷出,按照史金波先生的研究,黑水城出土的戶籍文書表明,當時該地戶均人口數較少,“可能當時男子結婚后分家另過”[2]80。分家析產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尊長對于卑幼的借貸行為不一定要承擔責任,財產仍然由家庭所有,債務人家資盡償的情況下,“出工抵債”對于債務人和“同去借者”是不得已的手段,但是對于“執主者”來說,也是基于“過錯促成交易”的一種變相懲罰,其家屬僅僅在“分食債利”的情況下承擔責任。
最后,西夏以畜牧為主的生活方式、多元的民族成分以及不均勻的人口分布使得“出工抵債”成為實現社會治理的一種手段。與同時期的宋朝主要“以農業為主”不同,“畜牧業是黨項羌族傳統的經濟生產方式,在西夏整個社會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15]144-155。這一點在刑罰內容上也有所體現,一些重大的犯罪諸如十惡中的“背叛”、“惡毒”、“不道”等,《天盛律令》規定,將行為人的親戚“入牧農主中”,強制其從事畜牧和農業勞動[6]115-119。相對而言,西夏農業生產不發達,且“居民中的漢人一般都是農業勞動者,大多數黨項羌和吐蕃、回鶻人民則以畜牧業為主”[13]161。又由于西夏的農耕牧區很有限,按照杜建錄先生的研究,“西夏除了沿邊山界以外,無論是河套平原還是河西走廊,實際上都是沙漠綠洲”,“荒漠與半荒漠約占西夏全境的4/5 以上”[18]37,剩下的適宜放牧和耕種的地區很少,這些地區也是“官僚貴族和軍隊”集聚地。貴族和官僚占有大量生活資料,“在貴族地主土地上進行生產的主要是人身依附性很強的農奴”[15]9,普通民眾很容易破產進而“出工抵債”。對于當時的宋朝來說,“以一家一戶作為生產單位的個體小生產”需要社會勞動力的增加[19]27。從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五代戰亂以后,宋朝為恢復生產采取了一些發展人口的舉措[20]474-476,勞動人口增多的同時,墾田面積也擴大了”[19]67-71,更為尊重自由的生產主體,在這種情況下,“以債負質當人口”顯得有些不合時宜。此外,過于多的破產民眾也可能成為西夏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出工抵債”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
結語
西夏的“借貸自由”與西夏社會生活資料分配的不均勻緊密相關。按照馬克思的說法,當部分人將多余的生產資料轉化為商品以后,伴隨著貨幣的出現,“高利貸資本”就產生了[21]437。但是,無限制的利率將會拉大社會的貧富差距,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政府對于借貸利率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著社會矛盾。在西夏社會中,有限的農耕和牧區、繁重的賦役、頻繁的戰爭以及不時降臨的天災更加拉大了貧者與富者之間差距。其中,西夏按照每個“租戶家主”的財產規模納稅[15]18,繁重的賦役可能促使一些家庭進行“分家析產”,以此可減輕一定的稅負。在這種財產所有制下,債務負擔的過程中傾向于一種“個人責任”。對于極度貧困者來說,“出工抵債”似乎是償還債務的唯一手段。
注釋:
①在E?И?克恰諾夫翻譯的《西夏法典》中,這一門類的標題被翻譯為“追繳債息”。見E?И?克恰諾夫俄譯、李仲三漢譯《西夏法典——天盛年改舊定新律令》,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E?И?克恰諾夫將“持主人”翻譯為“委托人”。見E?И?克恰諾夫俄譯、李仲三漢譯《西夏法典——天盛年改舊定新律令》,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0頁,其職能可能類似于中原唐代借貸契約尾部的“知見人”,見張傳璽主編《中國歷代契約會編考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