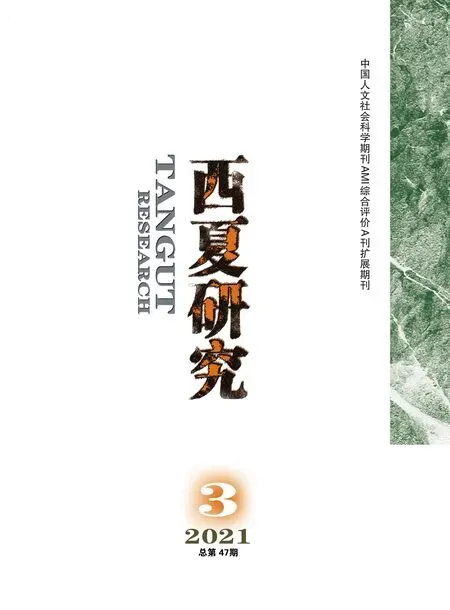北宋在河套南部的屯戍活動對當地生態的影響
□保宏彪
河套地區屬于典型的溫帶大陸性氣候,自東向西呈現出半干旱、干旱兩個氣候帶,由南向北逐漸稀疏的地表植被勾畫出一條鮮明的農牧分界線,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為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1]373河套南部地處黃土高原腹地,地形破碎、溝壑縱橫為主要地貌特征。宋夏時期,河套南部成為雙方激烈爭奪的重點地區。北宋為鞏固在河套南部的統治,組織駐軍進行大規模屯戍活動,以屯墾和筑堡為代表的粗放式土地經營和掠奪式森林資源開發對當地生態造成嚴重破壞。伴隨唐代中后期以來氣候逐漸轉冷的趨勢,河套南部農牧業生產因氣溫和濕度的間歇性波動呈現出南北拉鋸的局面[2],頻繁出現的嚴寒、暴雨等極端天氣和過度屯田、廣筑堡寨、修筑道路、興辦馬政四種人為因素對河套南部地表植被造成巨大破壞,加劇了河套南部的生態惡化。
一、北宋在河套南部的屯戍活動
在宋夏雙方激烈爭奪河套南部的過程中,北宋為鞏固延、宥、麟、府等邊防重鎮,組織當地駐軍開展了以屯墾和筑堡為代表的大規模屯戍活動。
(一)北宋在河套南部組織屯田
北宋政府為滿足數量龐大的邊防駐軍糧草供給,除安排長途轉運外,還組織各地駐軍進行屯田,以期減輕供給壓力。景德二年(1005),鎮戎軍知軍曹瑋奏請在西北邊軍中招募弓箭手屯墾自衛,“有邊民應募為弓箭手者,請給以閑田,蠲其徭賦,有警,可參正兵為前鋒,而官無資糧戎械之費”[3]4712。宋真宗采納了這一建議,“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出戰馬一匹。設堡戍,列部伍,補指揮使以下,校長有功勞者,亦補軍都指揮使,置巡檢以統之”[4]1338。弓箭手作為北宋鄉兵的一種,分布于陜西路、河東路沿邊地帶,隨著北宋西北防線的拓展向新邊發展[5]。弓箭手按照地形、部族屯居,有利于發揮土著熟悉地情、勇保鄉里的長處,人數一般在兩百人至六百人之間[6]。因為北宋禁軍戰斗力普遍不強,所以亦兵亦農、耕戰結合的弓箭手成為開發西北、鞏固邊防的一支核心力量[6]。弓箭手屯田不但有利于增強堡寨防御能力,而且減輕了轉運糧草所帶來的財政負擔,對鞏固北宋邊防意義重大。弓箭手屯田初見成效后,這一制度開始在宋夏沿邊諸州廣泛推行。
熙寧五年(1072),“趙禼為鄜延路,以其地萬五千九百頃,募漢蕃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其能省募兵之費,褒賞之”[3]4713-4714。在趙禼屯田之前,“時陜西曠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禼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略安撫使郭逵言:‘懷寧寨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無閑田。’禼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余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為八指揮,詔遷禼官,賜金帛”[3]4268。熙寧七年,“(呂)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余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陜西”[3]4270。元豐五年(1082)正月,“鄜延路經略司乞以新收復米脂、吳堡、義合、細浮圖、塞門五寨地土,招置漢蕃弓箭手及春耕種,其約束、補職,并用舊條,從之”[3]7758-7759。種世衡修筑青澗城(治今陜西省清澗縣)后組織駐軍屯田二千頃[7]5,范仲淹擔任延州知州時也曾大興營田[3]10270。
(二)北宋在河套南部修筑堡寨
河套南部“橫山亙袤,千里沃壤,人物勁悍善戰,多馬,且有鹽鐵之利,夏人恃以為生”[4]7894,具有重要戰略價值。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和李德明簽訂和約,“而以靈、夏二州及山界蕃漢戶并授德明”[3]10501。李德明得到戰斗力強悍的“山訛”后實力大增,相繼侵占銀、宥二州,“則橫山之地已囊括其中”[4]7894。西夏以橫山為跳板,才能向南擴大戰略空間。北宋如想扭轉頹勢,就必須奪回橫山地區,“橫山強兵、戰馬、山澤之利,盡歸中國,其勢居高俯視興、靈,可以直覆巢穴”[4]7894。因此,宋夏雙方圍繞橫山展開反復爭奪,修筑堡寨成為北宋鞏固橫山邊防的重要舉措。
康定元年(1040),西夏大舉進犯延州。當時,“延州諸寨多失守,(范)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3]10270。范仲淹采取持久防御的戰略方針,“于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為六,各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眾寡,使更出御賊。時塞門、承平諸寨既廢,用種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沖,大興營田,且聽民得互市,以通有無。又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定軍”[3]10270。范仲淹借鑒種世衡在青澗修筑城池的成功經驗重建塞門、承平等要塞鞏固邊防,通過弓箭手屯田、開放邊民互市、增設鄜城軍等手段提升堡寨自給自足能力,有效抵御了西夏進攻。
慶歷元年(1041)八月,西夏東侵麟、府二州,妄圖擴大橫山地區戰略縱深。“康德輿無守御才,屬戶豪乜啰叛去,導夏人自后河川襲府州,兵至近道才覺,而蕃漢民被殺掠已眾。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縱游騎鈔麟、府間,二州閉壁不出。民乏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時豐州已為夏人所破,麟、府勢孤,朝廷議棄河外守保德軍未果,徙(張)亢為并代都鈐轄、管勾麟府軍馬事。”[3]10488面對復雜形勢,張亢“單騎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門啟,既入,即縱民出采薪芻汲澗谷。然夏人猶時出鈔掠,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筑東勝堡;下城旁有蔬畦,為筑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為筑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穫于外,腰鐮與衛送者均得”[3]10488。西夏攻陷豐州導致麟、府二州糧道斷絕,張亢利用有利地形在府州城外修筑東勝、金城、安定三座城堡,使之成為且耕且戰的重要陣地。張亢謀劃出擊琉璃堡,“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人棄堡去,乃筑宣威寨于步駝溝捍寇路”[3]10488。張亢修筑宣威寨后,“乃修建寧寨。夏人數出爭,遂戰于兔毛川①。……不逾月,筑清塞、百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3]10489。張亢在與西夏的反復爭奪中先后修筑堡寨十余個,有力鞏固了麟、府二州邊防。
慶歷二年(1042)正月,宋真宗為反擊西夏而詔令沿邊各路發兵征討。范仲淹上書反對出兵,認為“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入,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也。況邊備漸修,師出有紀,賊雖猖獗,固已懾其氣矣。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來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若臣策不效,當舉兵先取綏、宥,據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計,則茶山、橫山之民,必挈族來歸矣。拓疆御寇,策之上也”[3]10270。宋真宗采納范仲淹建議,改武力征討為積極防御和招撫為主的政策。范仲淹奏請修筑承平、永平等堡寨后,“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候,城十二寨,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3]10270。元祐二年(1087),蘇軾在《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札子》中認為北宋在鞏固橫山邊防過程中所推行的積極防御和招撫為主政策促成了宋夏議和,“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余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虜中匹帛至五十余千,其余老弱轉徙,牛羊墮壞,所失蓋不可勝數,饑羸之余,乃始款塞”[8]552,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夏沿邊堡寨在軍事、經濟兩個方面的重要意義。
二、北宋時期河套南部生態破壞的表現與原因
(一)河套南部生態破壞的表現
根據氣象學相關研究來看,中國歷史時期的氣候變化可分為冷暖、干濕兩種波動形式。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廣泛應用考古資料、物候材料和歷史文獻,勾勒出中國近5000年氣候周期波動性變化的基本狀況,定義了中國氣候變化的“四暖四寒”模式[9]。具體來說,唐代中后期氣溫逐漸降低,兩宋正式進入寒冷期[10]。在氣候轉寒的過程中,北宋時期河套南部植被逐漸稀疏,對土地的粗放式經營和對森林資源的掠奪式開發不斷加劇水土流失,生態環境持續惡化。楊蕤通過分析西夏文獻《圣立義海》和《月月樂詩》所反映的物候、氣象信息,認為西夏時期具有干冷的基本氣候特征[11],這一結論對北宋時期的河套南部氣候具有一定參照意義。在《宋史·五行志》中留下了一些有關北宋時期河套南部出現嚴寒和暴雨引發洪災的記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極端氣候對當地生態的破壞性影響。
建隆三年(962)春,河套南部出現嚴重的“倒春寒”現象,“延、寧二州雪盈尺,溝洫復冰,草木不華”[3]1341。農歷二月至三月,延、寧二州出現厚達30多厘米的積雪,本已解凍的溝渠再次結冰,草木無法正常發芽。極端嚴寒打亂了當地正常的農業生產節奏,必然對當年糧食收成造成嚴重影響。除嚴寒之外,河套南部水循環也在氣候轉寒過程中出現紊亂,夏季暴雨逐漸增多。短時暴雨與過度屯墾所導致的水土流失、河道淤積誘發嚴重水災,給河套南部農業生產和社會經濟造成嚴重損失。太平興國六年(981),“鄜、延、寧州并三河水漲……延州壞倉庫、軍民廬舍千六百區”[3]1321。“三河水漲”現象的出現,源自水土流失導致河道淤塞。延州作為北宋在河套南部重要屯田區,粗放式耕作方式下的大規模屯田對當地自然植被造成嚴重破壞。缺乏植被覆蓋的山坡地帶的水源涵養能力大為降低,大面積的裸露地表逐漸干燥沙化,泥沙在風力、水流作用下順著山坡進入延河,由此引發的流域性水土流失嚴重破壞當地生態。在這一局面下,本就千溝萬壑的黃土丘陵地形更加破碎,風力、水流侵蝕日趨嚴重,河岸下切速度大大加快。這一現象除導致河床抬高、河道淤塞的嚴重后果外,還因風力、水力剝離地表營養層而加速土壤貧瘠,使當地的屯田活動陷入“越墾越荒、越荒越墾”的惡性循環。太平興國九年(984)八月,“延州南北兩河漲,溢入東西兩城,壞官寺、民舍”[6]1322。延州遭受嚴重水災,官舍、民居遭受嚴重破壞。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保安軍積雨河溢,浸城壘,壞廬舍,判官趙震溺死,又兵民溺死凡六百五十人”[3]1325。“積雨河溢”反映了河道淤塞嚴重的事實,因為河水含沙量大,所以巨量泥沙涌入河床后產生淤積,不斷抬高的河床導致河水溢出。地處黃土高原腹地的保安軍生態相對脆弱,宋軍的大規模屯田對當地自然植被造成巨大破壞。大中祥符九年(1016)七月,“延州洎定平、安遠、塞門、栲栳四寨山水泛濫,壞堤、城”[3]1325。從范仲淹記述延州至橫山旅途所見的文字中可以管窺當地區域性水土流失之嚴重:“夾以峻山,暑雨之期,湍流大石。秋冬之流,屈曲如繞,一舍之程,渡涉十數。山川之惡,諸處鮮立……”[7]16
(二)河套南部生態破壞的原因
現代地理學研究表明,荒漠化或沙漠化是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兩項因素累積的結果[12]。在河套南部這一生態脆弱地帶,農牧交錯區域出現荒漠化趨勢。因為氣候變異和自然環境的演變過程十分緩慢,所以人為因素的加入會激發并加速荒漠化進程,從而在較短時間內造成較大規模環境破壞和質的蛻變②。在影響河套南部生態的諸多人為因素中,過度屯田、廣筑堡寨、修建道路、興辦馬政嚴重破壞自然植被,加速了生態惡化趨勢。
1.過度屯田
如前所述,熙寧年間太原知府呂惠卿在葭蘆、吳堡兩座堡寨之間的木瓜原屯墾取得成功后,認為屯田對解決西北邊軍生計大有裨益,奏請在陜西路加以推廣。然而,樞密院經過核算卻認為木瓜原屯田得不償失:“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余人,馬二千余匹,費錢七千余緡,谷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余束;又保甲守御費緡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強民為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谷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3]4270因此,“(樞密院)慮經略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宋神宗)詔諭惠卿毋蹈前失”[3]4270。
除經營不善外,呂惠卿屯田失敗的原因還可能與氣候和地形兩大因素有關。在氣候方面,對于溝壑縱橫的黃土高原來說,水源的匱乏和有限的耕作技術使“靠天吃飯”成為河套南部屯田區的普遍現象。唐代中后期以來氣候逐漸變冷的大背景加劇了當地干燥少雨的氣候特征,誘發農業生產的“廣種薄收”現象。為保證河套南部駐軍的糧食供給,只能通過廣開屯田、大范圍種植增加產量。在地形方面,北宋駐軍在河套南部開墾的屯田大多為零散的山間坡地,并非平原地區平坦開闊的“膏腴之地”。淺薄的土壤層不能儲存足夠水分和養料,貧瘠的土壤肥力難以滿足大規模種植的需要,不得不以深植和燒荒之策進行補救。通過氣候、地形兩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北宋駐軍在河套南部的粗放式耕作為黃土丘陵帶來地表植被破壞、涵養水源能力減弱、區域水土流失加劇等一系列惡果,對當地生態造成災難性影響。
2.廣筑堡寨
河套南部的黃土丘陵具有干燥少雨、植被稀疏、風力強勁的特點,為數不多的森林資源對這一生態脆弱地區意義重大,對涵養水源、攔蓄地表徑流、防止水土流失、減輕水災具有重要作用[13]。北宋時期的河套南部零星分布著一定規模的森林植被,鄜、延二州以北“多土山柏林”[4]768。淳化五年(994),宋琪在分析西北番情時談及延州通往夏州的三條道路沿線“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狹不得成列”③。遺憾的是,寶貴的森林資源卻因北宋駐軍廣筑堡寨而慘遭破壞。
北宋出于鞏固宋夏邊防的戰略需要,在以延州為中心的河套南部依據有利地勢廣筑堡寨。“周美襲取承平寨,王信筑龍安寨,悉復所亡地,筑十一城”[3]10200。韓絳欲取橫山,采納種諤之策修筑啰兀城和撫寧堡[3]10303。徐禧進取橫山后耗時十四天構筑永樂城[3]10722-10723,該城由六座堡寨組成,寨之大者周九百步、小者五百步,堡之大者二百步、小者百步,用工二十三萬[3]10723。隨著宋夏對峙局面的發展,北宋在西北地區修筑的堡寨“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余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14]1722。曾鞏曾對當時西北堡寨的數量進行估算,“蓋秦鳳、鄜延、涇原、環慶、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百七十有四,熙寧較于嘉祐為一倍,元豐較于嘉祐為再倍”[15]174。李健超據此統計,北宋時期西北堡寨的數量至少在500 個以上[16]548-554,其中河套南部就有軍、堡、寨、鎮129個,涉及鄜延路3軍(綏德軍、保安軍、威德軍)、1鎮(豐林)、7城、31寨、24堡,環慶路1軍(定邊軍)、2城、4寨、10堡[17]233,多為“相視道路通達,水草豐足,良田可耕,險固可守。異時無煩朝廷饋餉,緩急聲援可以相接”之地[4]11728。河套南部修筑堡寨時經常開山毀林,“其土功自以為百萬計,仍須采山林以修敵柵、戰樓、廨舍、軍舍及防城器用”[4]3513,對當地森林資源造成嚴重破壞。元豐年間(1078—1085),鄜延路修筑堡寨時因敵柵、戰樓、樓櫓三大設施和板筑工藝需要大量木材,樞密院下令“須預計材植防城樓櫓并板筑之具,況見今修葺沿邊城寨及樓櫓之類,若以此為名,選將佐量帶兵甲領役兵于邊界采木”[18]9651,導致林地面積急劇縮小,自然植被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
北宋在河套南部廣筑堡寨,對當地森林資源的軍事性、掠奪性消耗,使過度砍伐成為影響生態的主要因素之一,終釀生態惡化苦果。大規模修筑堡寨對當地自然植被造成重創,大量林木遭到砍伐后導致水土流失和水災頻發。缺乏森林保護的裸露地表在風力、流水侵蝕下干燥疏松,暴雨后經地表水沖刷大量進入河道,泥沙淤積抬升河床引發洪水。
3.修建道路
北宋為保障河套南部物資運輸,除積極整修原有道路外,還增筑新路完善交通網絡。在筑路技術相對落后、環保意識較為淡薄的北宋時期,修路過程中的開山毀林之舉對河套南部生態造成巨大破壞。在千溝萬壑、土質疏松的黃土高原,缺乏植被保護的路面通過風力裹挾、雨水沖刷的共同作用產生水土流失,成為生態惡化的重大隱患。
總體來看,北宋在河套南部整修、增筑的道路主要為以下四條。
首先,北宋為鞏固沿黃防務,整修了麟、府二州與河東路之間的道路[2]。麟、府二州作為河套南部邊防重地,北鄰黃河,南接延州,東臨河東,西望夏州,與銀州共同防守宋夏邊境,為增強沿黃防線的防御能力,確保糧草、錢餉、食鹽等物資迅速運抵前線,必須便利麟、府二州與河東路諸州的交通聯系。
其次,北宋增筑了由順寧寨(位于今陜西省志丹縣西北)經金湯城(治今陜西省志丹縣西南)、白豹川(位于金湯城西南)通往慶州的通道[2]。這條路線串聯了保安軍、延州至慶州的戰略防線,對協防保安軍、延州、慶州具有重要意義,為鹽、靈、鄜、寧、環、儀六州提供戰略呼應,有助于鞏固河套、隴東邊防。
其三,北宋增筑了由保安軍(治今陜西省志丹縣)經荔原堡(位于今甘肅省華池縣東南)通往柔遠寨(位于今甘肅省華池縣)的通道和由保安軍經華池(今甘肅省華池縣東南)前往慶州的道路[2]。這條道路拓展了河套防線與隴東防線的戰略縱深,對河套防線的夏、延、靈三州和隴東防線的鄜、寧、環、慶、儀諸州意義重大,為有效協防保安軍、延州、慶州提供了有力支撐。
最后,北宋增筑了由綏州(治今陜西省綏德縣)經義合寨(治今陜西省綏德縣義合鎮)、吳堡寨(治今陜西省吳堡縣北)、定胡寨(治今山西省離石市西)、石州(治今山西省離石市)通往汾州(治今山西省汾陽縣)的道路[2]。便利隔河相望的綏、汾二州交通對于鞏固河套防線、加強鄜延路與河東路協防意義重大,河東諸州所產糧食、草料、錢餉、食鹽等物資可經由此道運抵綏州,為宋夏對峙和對夏戰爭提供充足的后勤儲備。
4.興辦馬政
北宋在曠日持久的宋夏戰爭中損耗了大量馬匹,因為喪失了漢唐以來的傳統牧馬之地,所以不得不利用河套南部零星分布的草場興辦馬政。雖然過度放牧對河套南部生態造成破壞的程度不及屯田,但還是應該引起注意。
北宋馬政要求各地駐軍以就近放牧方式飼養軍馬[3]4929,草場緊張必然導致過度放牧現象。在黃土高原腹地,只有個別水源較為豐富的谷地或迎風坡地才會形成一定規模的草場。水草相對豐美的延州、綏州、保安軍就存在載畜量過大的問題[2],眾多馬匹放牧于一處對當地的脆弱生態形成巨大壓力。王安石變法期間曾以“保馬法”力推民間養馬,使馬匹作為主要畜力進入河套南部農耕領域,在加速當地農業開發的同時,擴大了生態破壞的范圍[2]。河套南部作為北宋對抗西夏的戰略前沿,修筑了星羅棋布的堡寨,為數眾多的駐軍和弓箭手在附近的谷地、坡地進行墾殖。北宋所實行的“給地養馬”之法,雖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馬政繁榮,卻也對河套南部生態造成消極影響。宋哲宗即位后廢除“保馬法”,馬政混亂使北宋掌握的馬匹數量越來越少。為緩解馬匹緊缺的窘境,宋哲宗于紹圣三年(1096)接受韓筠建議推行“給地牧馬”之法,“凡授民牧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3]4943。邢州知州張赴認為授田一頃為官牧一馬,“較陜西沿邊弓箭手既養馬又戍邊為優”[3]4943。因此,北宋以租錢方式在陜西設置蕃落十指揮,養馬三千五百匹[3]4937。在農牧業的共同作用下,生態脆弱的河套南部自然植被受損嚴重,基本喪失自我修復能力。
興辦馬政過程中出現的過度放牧現象導致草場退化,進而引發水土流失,水土流失最終影響農業生產。為保證農業收成,只能繼續擴大開墾,從而深陷惡性循環。
三、結論
河套南部地形破碎、溝壑縱橫的地貌特征和生態脆弱的客觀現實,決定了當地的農牧業生產只能堅持因地制宜、合理開發的原則,在保護地表植被的前提下宜農則農、宜牧則牧。北宋為在與西夏爭奪河套南部的軍事斗爭中占據優勢,組織駐軍開展以屯墾和筑堡為代表的大規模屯戍活動。由于缺乏生態觀念,對土地的粗放式經營和對森林資源的掠奪式開發嚴重破壞了河套南部生態,引發區域性水土流失。結合自唐代中后期以來氣候逐漸轉冷的大背景,頻繁出現的嚴寒、暴雨等極端天氣和過度屯田、廣筑堡寨、修筑道路、興辦馬政四種人為因素,擴大了水土流失的消極影響,加劇了河套南部的生態惡化。
注釋:
①兔毛川位于今陜西省北部窟野河上游。
②王玉茹、楊紅偉《略論國家行為與西北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中國社會歷史評論》2006年第5期。參慈龍駿《我國荒漠化發生機理與防治對策》,《第四紀研究》1998年第2期。
③脫脫等《宋史》卷二百六十四《宋琪傳》,第9130頁,中華書局,1977年。延州通往夏州的三條道路分別為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川縣入綏州至夏州、正北行四五百里入平夏州南界、西北行四五百里入夏州西境。參何玉紅《宋代西北森林資源的消耗形態及其生態效應》,《開發研究》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