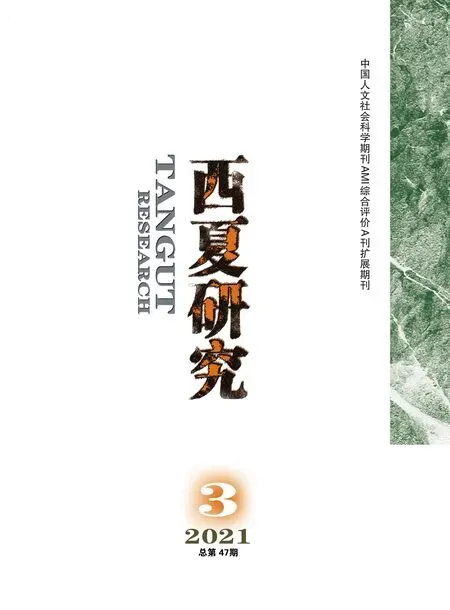二十年來國內西夏軍事研究回顧與展望
□劉宇麗
古往今來,軍事對一個國家和政權的發展壯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西夏自李元昊建立政權后,歷時近兩百年而亡,在此期間,西夏在軍事上建立了強大的軍隊和詳備的軍事制度和法律。西夏軍事制度在吸收中原軍事文化基礎的同時保留著自己的民族特色,創造了豐富的軍事文化遺產。考察這一問題有助于全面認識西夏的歷史和文化,對我們探究西北少數民族與中原軍事文化的交流融合也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西夏軍事研究回顧
湯開建《二十世紀西夏軍事制度研究》一文,按時間順序回顧了20 世紀國內外西夏軍事研究的成就與不足,認為這一時期西夏軍事研究對原始資料重視不夠,導致相關研究除了對監軍司、邊防制度、武器裝備等個案問題的研究較為深入外,其余內容大多流于簡單的論述,研究水準尚處于初級階段[1]44-56。進入21世紀以來,在西夏學研究熱潮逐漸高漲的背景下,西夏軍事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國內諸多學者都對此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數量及質量均有大幅度的提升,內容涉及西夏的軍隊數量、軍事制度、軍隊裝備、軍事戰爭、軍事地理等諸多方面,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西夏軍事研究體系。
(一)專著類
自1908 年俄國探險家科茲洛夫率領的探險隊在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發現了一批軍事文書和法律文獻后,西夏軍事研究獲得了豐富的原始資料,相關研究開始逐步興起和發展,西夏軍事研究的成果因之逐漸增多,專門探討西夏軍事的綜合性著作開始出現。如王天順《西夏戰史》(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 年)將西夏戰爭劃分為五個階段展開論述,討論了西夏王朝及其前身夏州政權將近三百余年的戰爭史實,并基于以上史實探討了西夏的戰爭地理、戰爭機制以及戰爭中的經濟與民族因素等問題,總結了西夏戰爭具有三個顯著特點:其一是以小國寡民與土廣民眾的大國長期對抗,其二是西夏薄弱的經濟力量極大地制約著它的對外戰爭,其三是西夏在戰爭中占據著有利的地理地形,提出西夏的對外戰爭是黨項族中以拓跋部為首的統治集團組織領導的、多民族參加的戰爭。這部專著以傳統史料為依據,梳理了西夏戰爭史,是有關西夏軍事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為此后的相關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鑒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西夏軍事研究進入了發展階段。胡若飛《西夏軍事制度研究〈本續〉密咒釋考》(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3 年),該書上篇為西夏軍事制度研究,分為通則和專題研究兩大部分。該研究結合夏、漢史料,詳細闡述了西夏職官的分類、官員的赴任期限、上朝規定、朝中坐次、平級調任以及各級軍政機構的公文行文規定、功臣封號等內容,不僅考察了具有軍籍、官品、庶人身份的人員范圍,同時還對西夏軍事機構、番官名號以及軍律與軍抄等個案問題進行了詳細探討。尤樺《〈天盛改舊新定律令〉武器裝備條文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年),上篇對《天盛改舊新定律令》(以下簡稱《天盛律令》)武器裝備條文進行了逐一注解考釋,發現了《天盛律令》兩種譯本關于西夏裝備武器的翻譯存有很大差異和沒有翻譯出來的問題,如不能簡單地將西夏的鎧甲和馬鎧譯為“披”和“甲”,“渾脫”簡單譯為“囊”也不能準確表達其材質和民族特色。下篇對西夏各類武器裝備的歷史沿革、形制特點及其配備和管理制度展開了專題研究,不僅考證了鎧甲和馬鎧等重要軍事防護裝備,而且辨明了其具體構造,展現了西夏的武器裝備種類齊全、體系完備等特點。
一些西夏史研究的通論性著作中也涉及了西夏軍事相關的內容。李錫厚、白濱《遼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在第十二章《西夏的政治制度》中簡要探討了西夏軍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軍隊數量、配置與兵種,以及軍事法典等內容,認為文獻中關于西夏軍隊數量的不同記載恰巧說明西夏在不同時期的軍隊數量,以此說明西夏后期軍隊數量達到六七十萬,軍餉則取之于平民,軍隊的普通兵士一般沒有固定的廩給;史金波《西夏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在第九章中,論述了西夏軍隊的建制、兵種、數量、基層軍事組織軍抄及其軍事戰備、戰略戰術等內容,討論了西夏用兵采用運動戰、劫取敵軍糧草、斷絕水源以及預設埋伏、誘敵中計等策略,進一步說明西夏能在一些重大戰役中取得勝利是與黨項族社會經濟發展、黨項族尚武精神、西夏統兵將帥對歷史上軍事經驗的系統借鑒和總結、建立適應于當時條件的軍事制度和軍事組織、西夏統治者的知人善任、將領的運籌帷幄以及精良的武器裝備等多重因素有關;湯開建《黨項西夏史探微》(商務印書館,2013年)中的《西夏篇》,收錄了作者幾篇關于西夏軍事方面的學術論文,對西夏軍事制度以及宋夏戰爭提出了一些獨到見解,如關于李繼遷反宋戰爭的性質問題,與多數學者支持的“反對民族壓迫的正義戰爭”觀點相反,湯開建教授認為這是一場非正義的割據戰爭。
(二)論文類
除著作外,西夏軍事方面的研究論文散見于歷年各類期刊。根據其研究內容,大致可歸類為軍事制度、軍事戰爭和軍事地理及其他研究三個方面。
1.軍事制度研究
軍事制度一直是西夏軍事研究的重點,研究成果豐碩,主要從兩個方面展開討論。
一是綜合研究,是對西夏軍事制度整體狀況進行論述。湯開建《近幾十年國內西夏軍事制度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寧夏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一文,在肯定學者們對西夏軍事制度研究做出努力的同時,也對軍事制度的定性、軍事組織發展、中央兵和地方兵的界定以及軍隊數量等問題提出了一些看法,文章對部分學者在沒有充分材料的支撐下就對西夏社會性質和軍事體制進行定性提出質疑。劉建麗《略論黨項夏國的軍事制度》(《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 年第6期)一文,探討了西夏的兵制與軍隊、兵種、戰術等軍事制度以及軍事法規的制定等問題,討論了西夏戰爭動員、戰術運用方面的特點,認為乾順時頒行《貞觀玉鏡統》的原因是當時嚴峻的軍事形勢、“尚文重法”的立國方針以及改革與發展的需要,提出西夏完善的軍事制度在西夏政權發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總結了《貞觀玉鏡統》在中國軍事史上的重要地位。陳廣恩《從〈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看西夏軍事制度的幾個特點》(《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04 年第1 期)一文,概括了西夏軍事制度具有全民皆兵制、女兵制度、軍事外交和軍法靈活、重視騎兵建設等特點。
二是專門研究,即對軍事制度中的軍事組織機構、兵役兵種、邊防與建制、后勤和裝備等方面的內容進行分析和考論。
軍事組織機構西夏監軍司作為軍政合一的邊防管理機構,學界歷來對此頗多關注,相關研究不僅涉及軍事機構的設置,同時也論及政區演變及相關的地理地望。當前,西夏地方軍事組織機構研究還處于一個文獻解讀的階段,西夏監軍司的研究也還有很多尚待解決的問題。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對地方軍事指揮機構及基層軍事組織所在政區、機構數量、駐地、所在地理地望等內容的探討。魯人勇《西夏監軍司考》(《寧夏社會科學》2001年第1期)論述了西夏前中期監軍司數量、名稱和駐地的變化,認為西夏中后期監軍司的移置、增減與政權形勢的變化有關,對西夏中期所置的十七監軍司與西夏政權建立時的十二監軍司做了比較,發現不同名的有十五個,其中宥州嘉寧監軍司撤置,甘州甘肅軍司更名為肅州監軍司,左廂神勇軍司移至夏州并更名為東院,右廂朝順軍司改名為西院,白馬強鎮軍司改名為北院,南院、南地中、北地中、沙州、羅龐嶺、年斜屬于增置的六個軍司。魏淑霞《制度史視域下的西夏監軍司探析》(《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9 年第9 期)進一步討論了西夏監軍司的職官設置在發展過程中突破了以武職為主設官的限制,名稱更加豐富,其職能也由最初單一的軍事攻防拓展到集軍事與行政一體的職能,而這種變化與西夏中后期軍事機構的變革和政治形勢有關。相關研究還有,姜歆《從〈天盛律令〉看西夏的軍事管理機構》(《西夏研究》2013 年第4 期)探討了西夏監軍司的名稱、駐地、數量和軍事職能,認為西夏軍事管理機構具有完備的法律規定和簡單有效的管理體系。張多勇、王志軍《西夏左廂神勇—年斜(寧西)監軍司考察研究》(《西夏學》2017 年第1 期)認為傳統文獻中的左廂神勇監軍司就是出土文獻中的年斜(寧西)監軍司,其地望位于榆林市榆陽區常樂鎮常樂古城。張多勇《西夏宥州—東院監軍司考察研究》(《西夏學》2016年第2期)對魯人勇提出的西夏中期撤置宥州嘉寧監軍司、左廂神勇監軍司移置夏州并改名為東院的推測提出質疑,認為西夏在后期將宥州監軍司更名為東院監軍司有較大可能。張多勇、楊蕤《西夏綏州—石州監軍司治所與防御系統考察研究》(《西夏研究》2016 年第3 期)對西夏綏州防御系統到北宋建立的綏德軍防御系統的變遷進行了闡述,北宋綏德軍防御系統的建立使其在拓邊橫山的戰爭中取得實質進展,顯示西夏軍事實力開始弱化。同時,通過實地考察認為石州監軍司的地望應位于橫山縣波羅鎮東古城遺址。張多勇《西夏白馬強鎮監軍司地望考察》(《西夏學》2015 年)認為白馬強鎮監軍司的地望位于今阿拉善左旗的察汗克日木古城。
西夏軍隊中最小的單位是軍抄。近年來在整理文獻資料的過程中,陸續翻譯了一批西夏軍事文書,為研究西夏基層軍事組織軍抄以及軍籍登記制度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原始文獻資料,因此,學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給予更多關注。有關軍抄問題討論最多的是史金波先生,其《西夏軍抄文書初釋》(遼夏金元歷史文獻國際研討會,2008年)一文,結合新出土的軍抄文書探討了軍抄中的正軍、輔主和負擔問題,提出漢文文獻有關軍抄的記載中沒有輔主的原因可能是當時中原地區對西夏軍抄組織的結構不甚了解而致漏載。一個軍抄中出現多個輔主的現象與正軍的戰具配備和身份世襲等因素相關。提出西夏有“軍”身份的人不同于普通的軍抄士兵且西夏軍籍與戶籍相輔相成的觀點。他的《西夏文軍籍文書考略——以俄藏黑水城出土軍籍文書為例》(《中國史研究》2012 年第4 期)則通過對西夏文軍籍文書的翻譯和初步研究,認為西夏有著嚴格的軍籍登記制度,軍籍登記有一定的格式。這些文書還反映了西夏晚期黑水城地區軍隊質量下降、戰斗力削弱的現象,具體表現為首領軍力偏小、抄的人員偏少、軍丁人員偏老、軍隊裝備較差等情況。史金波《西夏文軍抄賬譯釋研究》(《歷史研究》2019 年第3 期)一文對西夏軍抄有進一步的研究,對文書中以“溜”為單位的軍抄賬、以“甲”為單位的多首領軍抄賬、軍抄戶籍賬以及軍抄財務賬幾類軍抄賬分類并進行了考釋,通過對這些文書的分析,探討了軍抄人員的組成、軍籍和戶籍等問題,并認為西夏兵丁有錢糧補給,西夏軍隊“人人自備其費”的說法值得進一步商榷。翟麗萍《試述西夏軍抄》(《西夏學》2017年第1 期)一文,對軍抄的組成持有不同的觀點,通過其研究認為軍抄是由正軍和輔主組成的,而輔主包括正輔主與負擔,輔主要來源于社會地位較低的平民。
兵役兵種西夏屬于全民皆兵制,凡成丁男子都要服兵役,兵員數量龐大。彭向前《釋“負贍”》(《東北史地》2011 年第2 期)一文,通過文獻考辨,論證了漢文文獻中“負贍”是正確的寫法,而“負擔”是“負贍”的形訛。“負贍”相當于西夏語詞中的“輔主”,并主張直接采用宋人的相關記載,譯為“負贍”更為合理,否定了西夏軍抄是由正軍、輔主、負擔構成的觀點。田曉霈《西夏“水軍”新考》(《史志學刊》2019年第3期)對西夏存在數量不多的水軍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西夏沒有正式的水軍建制,宋史材料中的“水軍”是渡河作戰的西夏步騎兵和主管河渡事物的津渡官。何玉紅《西夏女兵及其社會風尚》(《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 年第5 期)認為西夏罕見的女兵現象可以從西夏婦女獨特審美觀、婚姻觀和崇尚殉情的社會風尚中體現。西夏婦女勇健無畏、剛烈驍勇、任俠果敢的獨特風尚形成,源于西北社會固有的民風、地理環境、戰爭軍旅生活及其統治者強烈的民族意識等諸多因素。相關研究還有,姜歆《〈天盛改舊新定律令〉征兵制度探析》(《西夏研究》2019 年第2 期)將西夏的征兵制度與宋、遼的征兵制度加以比較,認為西夏的征兵制度與宋的募兵制度不同,而與遼的征兵制度相近,西夏與遼的征兵制度都體現了適用于游牧民族政權的特點。邵方《西夏的兵役制度論》(《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通過分析法典中的相關軍事法條,論述了西夏兵役制度的發展過程,認為其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體現了黨項族的尚武習俗和游牧特征。李煒忠《西夏“輔主”考論》(《黑龍江史志》2014 年第23 期)梳理了文獻中關于輔主的記載,考察了輔主在軍隊和社會中的地位,認為輔主社會地位遠遠低于正軍。
邊防與建制西夏立國后,為嚴防周邊民族政權的侵擾,建立了一套以堡寨、城司、城溜、更口、烽火等為依托的較為完整的邊疆防御體系。陳廣恩《關于西夏邊防制度的幾個問題》(《寧夏社會科學》2001 年第3 期)探討了西夏邊防軍的選派、職責、賞罰以及邊防制度的特點等問題,認為西夏邊防軍主要包括監軍司所轄的監軍司兵和駐防各地的巡檢兵,其巡防任務艱巨、職責繁雜,邊防軍的裝備和給養實行自備和國家統一供給相結合的方式,其邊防制度具有靈活、實用、合理的特點。許偉偉《西夏邊防的基層軍事建置問題》(《西夏研究》2019 年第1 期)探討了西夏沿邊堡寨城司、城溜、更口、哨卡、烽火、口鋪的基層軍事建置情況及其功能,從邊境地區的防御作戰、管理敕禁、貿易、使節往來以及管理邊地部族人口和財產、維護邊境治安等方面,說明西夏邊防基層軍事機構的內外聯動構成了強有力的前沿防御體系。許偉偉《西夏中期河西地區的軍事建置問題——以西夏法典〈天盛律令〉為中心》(《西夏學》2019年第1期),認為西夏右廂河西地區的軍事建置主要包括南院、西院、卓啰、肅州、瓜州、沙州、黑水、啰龐嶺等監軍司和與監軍司級別相當的大通軍、宣威軍以及城司、堡寨、口鋪、軍溜等基層軍事建置。
后勤和武器裝備后勤補給是從物質、技術等方面保障軍隊建設和作戰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基礎性的軍事活動,有戰爭和軍隊即應有后勤活動[2]。賈隨生、李園《西夏軍事后勤供給概論》(《寧夏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概括了西夏軍事后勤最主要的特點是其后勤物資的供應是由國家、宗族和部落民共同承擔,說明其軍事后勤雖具有機動靈活的優越性,但只適合短期的流動作戰;西夏軍事后勤供給前期具有較大優勢,中后期國家負擔后勤的比重增加,是宋夏戰局發生逆轉的重要原因之一。賈隨生《淺論西夏軍事后勤制度的形成與完善》(《固原師專學報》2004 年第2 期)一文,提出西夏軍事后勤制度在元昊時期形成、仁孝時期完善的觀點,并對后勤供給的主要物資及其管理有更為詳盡的論述。西夏的武器裝備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西夏所產的“夏國劍”和馬匹都聞名當世。姜歆《論西夏將兵的裝備》(《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探討了西夏將兵裝備主要來源于貿易、掠奪、戰爭所獲、生產四個方面,其將兵的裝備有利于騎射,其兵器精銳,甲胄堅良。尤樺《西夏棍棒類兵器及其相關問題考論》(《西夏學》2019 年第1 期)對棍棒類兵器的種類、形制、功能進行了考證,提出《天盛律令》卷五“軍持兵器供給門”漢文譯本中翻譯成“長矛杖”的兵器譯成“長槌杖”更為準確的看法;考證了西夏鐵鏈枷兵器的使用方法,探討了西夏將鐵鏈枷從城防戰具推廣至前線對戰;論述了西夏的骨朵在形制和功能方面繼承唐、宋之制,骨朵除可作戰爭兵器、儀衛武器、杖擊類刑具之用,同時還出現在佛教繪畫中。尤樺《西夏渾脫考述》(《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2 期)論述了西夏渾脫不僅是具有地域特色的交通和生活用具,同時在西夏軍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認為渾脫作為輔助性軍事裝備,具有渡水、偷襲、建浮橋、消防滅火等功能,作為武器裝備具有促使軍事戰術靈活多變的作用。蘇冠文《西夏軍隊裝備述論》(《寧夏社會科學》2000 年第6期)一文,探討了西夏戰馬、甲胄、兵器、指揮用具和西夏裝甲騎兵的征戰能力,體現了西夏在冷兵器時代就已經擁有高水平的軍隊裝備。尤樺《西夏武器裝備法律條文與唐宋法律條文比較研究》(《西夏學》2016 年第2 期)從武器裝備的配備種類、發放和保管方式等方面將西夏與唐、宋武器裝備法律條文進行對比,發現西夏的有關武器裝備的法律條文相比唐、宋相關律法在編撰內容上有很多不同,且條文規定更為詳細和靈活。陳廣恩《西夏兵器及其配備制度》(《固原師專學報》2001年第4期)、《關于西夏兵器的幾個問題》(《青海民族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西夏兵器及其在中國兵器史上的地位》(《寧夏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三篇文章探討了西夏兵器的種類、制作方法、配備情況等問題,認為西夏兵器以冷兵器為主、兵器的制作有專門的工匠、兵器的配備注重實用,體現了明顯的等級特征;西夏武器配備經歷了從無到有、從簡到精、最后制度化的過程;西夏兵器不僅提高了軍隊戰斗力,同時對中原王朝兵器創新產生了較大影響。
關于軍事制度方面的研究還涉及軍事職官、兵符等問題。尤樺《西夏察軍略論》(《西夏學》2013 年第1 期)對“察軍”是漢文文獻中“監軍”的這一推測提出了質疑,認為察軍主要指的是西夏軍隊中監察軍隊統領和上報軍功軍績的重要職官,有記錄、上報將卒功勛、監督軍事行動以及協助軍事主帥共同處理軍中事務等職責;察軍與將軍互相牽制,并有可以直接向京師及西夏統治者匯報的特權,其成為了中央和地方連接的重要紐帶。魏淑霞《西夏職官中的宗族首領》(《寧夏社會科學》2015年第5期)認為西夏建立后將部族首領納入職官體系經歷了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西夏時期的首領既是部族的首領,擁有自己的部族,同時又是西夏行政職官中的一員,受西夏政府的管理,其權限由最初的主軍權擴展到更廣泛的政治領域。陳瑞青《西夏“統軍官”研究》(《寧夏社會科學》2016 年第1 期)一文指出,統軍官分為常設和戰時兩個系統,常設在中央主要是掌管禁軍的統軍司,在地方為監軍司的都統軍、副統軍;戰時系統則是由多個監軍司抽調兵馬組成的統軍司,并認同元代的“鈐部”是西夏的“統軍”的這一說法,考論了統軍官的選任主要是委以豪右,體現西夏將領用人特色的同時也增加了政治風險。張笑峰《西夏的兵符制度》(《西夏研究》2019年第4期)一文,概述西夏的兵符種類有起兵符契、起兵木契、發兵諭文和符節,并以《天盛改舊新定律令》為研究的文獻依據,考論了西夏兵符管理和派遣都有嚴格的規定,發兵時執符者丟失兵符的處罰辦法以及西夏兵符嚴格的合符制度,發現發兵諭文是符節的重要補充,發兵諭文和符節有著密切的聯系。
2.軍事戰爭研究
遼、宋、夏、金時期是中原王朝與周邊各個少數民族政權戰爭沖突不斷的對峙時期,西夏也時常因領土擴張和利益沖突與周邊各個民族政權發生戰爭。
軍事戰爭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
其一是論述西夏與周邊民族重要戰爭經過、勝敗原因和影響等問題,包括與宋、遼、金以及蒙古發生的歷次大小戰爭。李蔚《略論蒙夏戰爭的特點及西夏滅亡的原因》(《固原師專學報》2000年第4 期)指出,蒙夏戰爭持續時間長,其戰爭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認為西夏為蒙古所滅的原因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同時西夏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激化,實行“附蒙侵金”的錯誤政策以及蒙古滅夏戰略戰術的成功運用也是其重要的原因。魏淑霞《熙寧變法與宋夏戰爭》(《西夏研究》2010 年第4期)從熙寧變法的角度梳理宋夏之間發生的戰爭,認為熙寧年間王安石變法重點對西北地區進行的軍事改革取得了較好的成效,使得熙寧變法后的北宋逐漸扭轉了在宋夏戰爭中的被動局面,大大提高了北宋對西夏的防御和作戰能力;哲宗時期平夏城之戰的勝利徹底改變了宋夏之間的攻守態勢,拉開了北宋奪取橫山地區的序幕。母雅妮、郝振宇《宋夏三川口之戰的歷史影響》(《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以三川口之戰為切入點研究了宋夏戰爭對中古時期河西絲路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但同時論及因西夏控制了河西絲綢之路又促進了北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張玉海《簡論宋夏平夏城之戰》(《西夏研究》2010 年第4 期)探討了平夏城之戰的始末及其影響,認為北宋在平夏城之戰中采取了集中兵力、多路協同作戰以及章楶“筑壘加淺攻”戰術等手段,使其充分發揮了自身優勢從而取得了戰爭勝利,這次戰役標志著北宋對西夏邊防政策的轉變和宋夏攻守態勢的轉換。蘭書臣《宋夏好水川之戰再探》(《軍事歷史研究》2019年第3期)指出,好水川之戰西夏勝利的重要原因包括元昊及其謀士的能謀善戰、進攻方向和戰役地點的選擇合理、通信工具和手段的運用恰當以及西夏“鐵鷂子”的突擊作用,而北宋戰役失敗后,“歲幣”大幅增加,其整體上對夏已處于守勢。雷家圣《高遵裕與宋夏靈州之役的再探討》(《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一文提出,高遵裕作為外戚掌兵是戰役失敗主要原因的說法值得進一步商榷,認為靈州之役失敗是由于北宋動員兵力過于龐大,而后勤供給超出負荷所導致的。趙一《安悆墓志考釋——兼談宋夏靈州之役》(《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一文,通過對墓志中記載的元豐四年宋夏靈州之役的考釋,總結了宋軍靈州戰敗主要原因是糧草不繼以及攻城武器的缺乏;除宋夏戰爭外,夏遼、夏金之間以及西夏與蒙古之間的戰爭,從根本說,是由不同政權之間的利益矛盾引起。陳德洋《試論金宣宗時期的金夏之戰》(《西夏學》2013年第3期)一文認為金宣宗時期金夏交惡進而發生戰爭主要是由于西夏報復金朝未盡宗主國之責,深層次的動機則在于領土擴張和經濟掠奪,指出金夏交戰造成了雙方國力的消耗,使得蒙古有了可乘之機,致使西夏最終被蒙古滅亡。陳德洋《遼興宗時期遼與西夏戰爭瑣議》(《西夏學》2019 年第2 期)分析了遼重熙年間遼伐夏最深層次的原因是遼自圣宗以來國家正統意識加強的結果。
其二是關于宋夏戰爭中各方戰略決策等問題的探討,主要包括交戰雙方在政治和軍事戰略決策的實施對戰爭走向和結局的影響等內容。林鵠《從熙和大捷到永樂慘敗——宋神宗對夏軍事策略之探討》(《軍事歷史研究》2019 年第2 期)一文從宋神宗對西夏軍事策略上的個性和心理方面分析其對戰爭成敗的重要影響,認為神宗個人對滅夏的焦急心態和盲目自信的作風是熙寧、元豐年間宋對西夏軍事行動失敗的重要因素。王戰揚《北宋中后期對夏戰爭的軍事決策及其成敗》(《東岳論叢》2019 年第9 期)一文,認為北宋中后期西夏軍事決策日益受得重視,北宋對夏戰爭的多次失敗與決策者和統兵官決策失誤及戰術上的輕敵妄進之舉等因素有關,總結了戰爭成敗與中央和邊防之間互動以及戰前決策有重要聯系。
其三,宋夏戰爭作為北宋和西夏重要的政治、軍事問題,對北宋的文學、經濟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出現了將宋夏戰爭與北宋農業經濟、文學、貿易結合起來研究的新視角。程龍《北宋西北沿邊屯田的空間分布與發展差異》(《中國農史》2007年第3期)一文討論了宋夏靈州之戰后,北宋屯田由戰時臨時補給措施轉向常規的補給方式,結論是慶歷時期的屯田開始以鄜延、涇源路兩大中心區域向東北、西南擴展,北宋中后期西南屯田的發展相比東北進展更為順利。宋華、郭艷華《論宋夏戰爭奏議文書寫之“剴切”文風》(《北方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研究了宋夏戰爭的奏議,從戰爭文學的角度討論了奏議文書展現出切合事理、犯言直諫的“剴切”文風的問題。張帆《仁宗朝宋夏戰爭之下的茶馬貿易》(《茶葉》2020年第2期)認為仁宗時期茶馬貿易受宋夏戰爭的影響主要以走私貿易為主,直到慶歷年間宋夏和談后,貿易才恢復正常;茶馬貿易是西夏主動求和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維系雙方穩定關系的紐帶。
3.軍事地理及其他研究
軍事活動與軍事地理關系十分密切,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與軍事活動有關的地理問題,包括戰爭的地點、路線,軍事城堡要塞地望考察等內容。余軍《西夏若干城寨地望研究述要》(《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1期)對蒙古攻伐西夏過程中所涉及的力吉里寨、落思城、乞鄰古撒城、兀剌海城、克夷門等西夏城寨地望的不同說法做了綜述,認為其方位說法不一的根本原因是各類史籍記載混淆不清。李玉峰《西夏瓦川會考》(《河北北方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通過考察,作者認為西夏瓦川會地望在馬銜山山界中,即今甘肅榆中縣新營鎮。瓦川會是控扼河湟與北宋聯盟的關鍵軍事據點,同時也是民間貿易集會的場所。張多勇、龐家偉、李振華、魏建斌《西夏在馬啣山設置的兩個軍事關隘考察》(《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 期)一文對凡川會、龕谷川相關城、堡寨遺址進行實地考察,認為汝遮谷即為榆中縣新營鄉的清水河谷地,汝遮谷與龕谷峽是榆中盆地南通馬銜山的兩個要道,龕谷寨是現今的小康營,龕谷關與凡川會是西夏防止吐蕃翻越汝遮谷的兩個重要軍事關口。尚平《宋夏好水川戰場位置再探》(《寧夏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9期)結合考古資料和地理信息資料梳理了好水川之戰的相關史實和地名問題,認為羊牧隆城址在今西吉縣興隆鎮北石寨鄉,今好水川是宋時籠落川,宋時的好水川是今西吉縣興隆鎮所在的什字路河。張多勇《宋夏對峙時期清遠軍考察研究》(《西夏研究》2018年第4期)一文,通過實地考察認為北宋修筑的清遠軍城在今甘肅環縣甜水堡南3千米的古城堡城址處,西夏清遠監軍司在位于甘肅環縣甜水堡瓦渣城遺址,清遠軍可能在天盛年間改名為南院監軍司。張多勇、馬悅寧、張建香《西夏對宋構筑的鐵鉗左翼——金湯、白豹、后橋考察研究》(《寧夏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對宋夏對峙時期西夏的金湯、白豹、后橋古城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認為金湯古城位于陜西省志丹縣金湯村、白豹城位于陜西省吳起縣白豹村、后橋古城位于陜西省吳起縣廟溝鄉橫山寨,這三個城寨是西夏攻擊北宋的前沿陣地,同時也是西夏進行邊境貿易的場所,北宋為防御西夏的三個城寨構筑了“大順城防御系統”和“懷安防御系統”,有效抵御了西夏的進攻。李雪峰、艾沖《西夏與遼朝交通干線“直路”的開辟與作用》(《甘肅社會科學》2019 年第6 期)考察了西夏開辟“直路”經歷的動態變化過程,提出“直路”的南段由地斤澤轉向西南至靈州城,北段由地斤澤轉向東北經勝州到遼都臨潢府城的觀點;“直路”不僅是西夏與遼之間的交通要道,同時也是構筑西夏東部駐防體系的基石。張多勇《西夏通吐蕃河湟間的交通路線及沿路軍事堡寨考察》(《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0 年第3 期)一文對文獻中“西藩、夏賊往來便道”進行考證,認為甘肅永登縣水磨溝即為西夏通河湟的便道,因其經過莊浪河谷的卓啰監軍司,將其命名為“卓啰軍道”,并對水磨溝一線的軍事堡寨的地望以及莊浪河谷的西夏遺址進行考察,論證了西夏卓啰和南監軍司的駐地位于莊浪河谷地和水磨溝的交匯地的羅城灘古城。
除此以外,軍事情報、通信相關問題也是西夏軍事研究的重要內容。尤樺《西夏烽堠制度研究》(《西夏學》2017年第1期)梳理了現存西夏烽堠遺址,考論認為西夏烽堠修筑多以夯土版筑、有連續性,并定期派遣專人管理,其具有軍事通信、偵察和防御的職能。王凱《西夏對域外信息的收集》(《西夏研究》2019 年第4 期)認為西夏通過使者、諜者、商人、僧侶等途徑能夠準確獲取敵方關于軍事防備和出兵駐軍的情報,對西夏在戰爭中占據主動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二、研究特點、問題及展望
西夏軍事研究作為西夏學中一個重要的內容,由于其涉及到許多基本的問題,同時還受到資料的限制,所以早期研究一直處于初級階段[1]44-46。但近二十年以來,在西夏學學科體系不斷完善、研究理論和研究領域不斷開拓創新的背景下,西夏軍事作為西夏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積極開展相關研究,出現了不少專題論述和以西夏軍事角度為選題的學位論文。據粗略統計,中國知網收錄的論文中,涉及西夏軍事研究的將近有兩百余篇,相比前期數量有明顯的增加。分析以上研究成果,可看出目前西夏軍事研究已經步入了發展階段,并大致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在材料的運用上。相比前期研究中更多的選擇《西夏紀》、《西夏書事》等清人著作作為研究的史料依據,近二十年學界更注重原始出土西夏文獻的運用。相關研究一方面在繼續挖掘《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等漢文文獻史料的同時,充分利用西夏文獻尤其是黑水城出土的世俗文獻等西夏學原始資料和考古資料如文書、碑石、題記、石窟壁畫等史料展開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其次在研究深度上,相比前期內容大多流于簡單的論述,近年來西夏軍事研究在宏觀概括的基礎上更深入到具體問題中。回顧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一些文章在總結前人成果基礎的同時利用新材料提出了新的觀點,如學界對于黑水城出土西夏軍事文書的性質判斷爭論已久,至今沒有定論,陳瑞青認為黑城出土的7 件軍籍“文書”并非西夏軍籍,而是軍抄首領官向上級報告所管軍抄年校情況的告稟文[3],這個結論具有一定的說服力。第三,這一時期研究的視角也更為開闊,研究方法更為多樣。比較注重跨學科研究,如在邊防城堡寨遺址的考察、監軍司政區劃分等問題中運用了地理學的理論方法,注重從不同的視角去研究問題。如從軍事史、制度史、法制史、文學史等角度去研究軍事制度和戰爭,運用對比研究的方法探討各政權在軍事制度和軍法之間的淵源和差異等,這些研究突破了傳統軍事制度和戰爭史研究的局限,為西夏軍事研究的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西夏軍事研究在取得成績的同時,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其一是由于資料的限制,西夏軍事研究還不夠深入和系統,一些基本問題還存在爭議。其二,在資料使用上,由于西夏文文獻解讀困難,致使一些出土文獻和考古資料還沒有被充分利用。其三,研究內容不平衡,相比西夏軍事制度、宋夏戰爭、監軍司、武器裝備等,其他如戰略戰術等相關研究非常薄弱。
展望未來,西夏軍事研究還有很大進步空間,也仍有很多需要探討和研究的課題。今后西夏軍事繼續深入研究還需從以下三個方向努力,一是充分利用和挖掘新舊材料,將漢文史料、西夏文文獻和考古資料三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是西夏軍事深入發展的必要途徑。二是加強對西夏文軍事文獻的解讀和整理,為西夏軍事研究提供基礎資料。最后跨學科研究是今后西夏軍事研究的一個方向,在理論上盡可能吸收軍事學、地理學、文獻學、民族學等多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識,結合這些理論知識進行分析有助于更加全面認識西夏軍事的整體面貌。四是在材料較為有限的情況下,從不同的視角探討問題,如從橫向上與同時期的宋、遼、金等民族政權進行比較研究,探究其共性與個性,從而拓寬學術研究的視野,還可以從整體上把握研究對象,將西夏軍事放在西夏社會歷史發展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乃至10—13 世紀西北地區大背景下予以考察。相信未來在這些方面的努力下,西夏軍事領域必將有更廣闊的發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