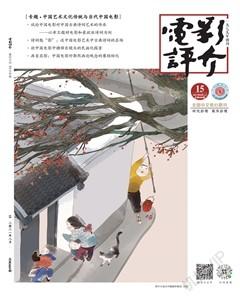“電影詩人”劉浩銀幕世界中的社會生態、文化裂變與文學意味
作為當下中國最活躍的小成本獨立電影創作者之一,劉浩自完成處女作《陳默和美婷》(劉浩,2002)以來,就一直關注小人物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他的影片充滿對社會生態的關注、對文化在現實中裂變的感知以及對電影文學性的體察。2021年6月,從影20年的劉浩攜新作《詩人》(2021)歸來,再次以獨特的“文人氣質”帶給觀眾無限驚喜。
一、“文人電影”傳統中的社會生態表現
劉浩1999年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是業內正宗的“科班導演”,但他的電影卻具有“文人氣質”,也被許多影評家稱為“文人電影”。“文人電影”被許多學者認為“是一個便于中國電影流派討論的一個有用的分類觀念”[1],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鄭正秋、張石川等中國第一代電影人與左翼電影工作者相互影響的時期。這一時期的中國早期電影在形式與內容上同時受到新派文明戲、左翼話劇與傳統戲曲的影響,也在精神與思想上受到解放舊思想、以先進文明啟發觀眾理念的鼓舞,出現了最早的“文人電影”。這一時期的“文人電影”中的“文人”主要指夏衍、鄭伯奇、沈西苓、洪深、田漢等以文人或話劇工作者的身份進入電影行業的“非科班”電影人,他們來自由左翼作家聯盟發展而來的左翼電影聯盟,大多擔任編劇工作,也有如沈西苓或洪深等編導全能的電影人。“文人電影”的創作主旨在于在市民文化中揭露現實黑暗、激發民眾救亡愛國的熱情。“文人電影”工作者為加深觀眾對現實的認識程度,創作了《狂流》(程步高,1933)、《春蠶》(程步高,1933)、《上海二十四小時》(沈西苓,1933)、《鐵板紅淚錄》(洪深,1933)等一系列以新思想影響和改造電影,從而改造社會的“文人電影”。可見,“文人電影”之名雖然來自于并非電影科班出身的左翼文藝工作者以文人身份加入中國早期電影創作的實踐,但“文人電影”的基因中蘊藏了中國現實主義影片對現實的關懷。換言之,只要對社會生態進行廣泛的感知和體察,無論電影是由導演還是編劇主導,主創人員是出身科班還是由文字工作者轉變而來,這樣的電影都可以被看作是“文人電影”。改編自同名小說、講述云南小村落中貧困農民故事的《好大一對羊》(劉浩,2004)先后斬獲了2005年加拿大維多利亞國際電影節金獎、2005年法國維蘇爾電影節最佳亞洲電影獎和2005年美國華盛頓國際獨立電影節評委會獎等獎項。此后,劉浩的《底下》(2007)、《向北方》(2014)、《詩人》等作品頻繁出現在海外各大電影節中,他從籍籍無名到聲名鵲起,成為最有代表性的中國獨立導演之一。
《底下》關注社會邊緣北漂青年的內心深處與情感生活。盛好與賈豪租住在北京一間由住宅改成的地下室中,這里陰暗逼仄、潮濕喧擾,如同兩人出現問題的感情與希望渺茫的未來。一天,一名不速之客闖入兩人居住的地下室,控制了盛好與賈豪,并要求感情已經近乎破裂的兩人在他面前表演做飯等“溫暖”的日常生活與愛情場景。《底下》的成本只有7000余元,它是劉浩利用7個月的空閑時間用高清數碼攝像機拍攝的,影片描繪了一對在社會轉型期的青年之間的熱情和悲涼。影片故事似乎并不“現實”,對闖入者身份與目的的討論在緩慢的節奏中一再被懸置,取而代之的是盛好與賈豪貌合神離的感情線索:賈豪的一再失約與敷衍令盛好失去對他的期待,賈豪親自為盛好下廚,溫馨的午餐氛圍卻被闖入者打破;闖入者命令兩人假裝恩愛,已經徹底失望的盛好卻難以進入預設情景,勉強“入戲”的賈豪也終于難以獨自堅持。在數碼攝影機渲染出的高飽和度色彩與暗色調中,地下室是電影最主要的敘事空間。影片對一對北漂青年的情感剖析在壓抑的紅色和不安的藍色中慢條斯理地進行,這段分分合合的感情故事充滿了現實故事特有的詩意,最終在情感的失落中凸顯出北漂青年在漂泊中無處歸依的迷茫心境。北漂青年懷著夢想到都市打拼,卻缺乏足夠的經濟基礎在大城市安身立命,理想與現實的落差往往造成他們心理上的漂泊感與現實行動的遲滯,這也使“北漂人”與“打工人”成為中國社會性話題中的新問題。劉浩進行獨立電影創作的現實背景,與左翼電影聯盟組建的背景有頗多相似之處:繁榮的市民文化與商品社會催生出多元電影創作,而娛樂化傾向明顯、遠離現實或脫離現實的商業故事片在電影市場中占有主流地位。劉浩與早期“電影文人”一樣,開始在“一種玩物怡情的游戲,供人娛樂的倡優、雜技”[2]的娛樂性,以及電影本身的媒介屬性與藝術屬性外,自覺關注電影對社會現實的表現,令電影樸素而準確地具有社會屬性的補充。
《向北方》則在充滿文人氣息的氛圍中關注“失獨”這一社會性話題。影片靈感來自劉浩偶然看到的一份新聞簡報,通過一名身患頑疾的平凡女孩小艾勸父母艾亮和柳慶再生個孩子的故事,表現了一個家庭、一座城市乃至一個時代的隱秘“心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結果之一便是眾多的獨生子女家庭,但獨生子女的意外死亡造成了難以解決的“失獨”問題。《向北方》中的小艾是一名普通的紡織廠女工,她鼓勵人至中年的父母再生一個孩子,但長期分居的父母的關系已然破裂。目前,中國失獨家庭至少已超百萬,而“失獨家庭”的老人在失去唯一的孩子后很容易面臨養老、看病等問題,陷入老無所依的困境。劉浩始終堅持通過“文人電影”這一手段來關注當下普通人的內心世界,尤其是那些容易被忽略的邊緣人形象。影片對家庭場景的描繪充滿真實生活的質感,演員的表演簡單而樸素,在自然的表情動作與導演細膩而寫意的鏡頭語言中深刻反映出小艾一家各個生活成員的內心世界,以及中國家庭與社會中無數個體生命的人生萬象。
二、新境況下傳統社會文化的裂變與重組
社會文化積淀著社會公眾最深層的精神追求。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社會文化作為代表社會形態、經濟基礎、市場形態等社會因素獨特的精神標識,成為維持社會基本秩序穩定的基石。隨著改革進程的推進與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人們在享受當下科技進步、時代開放、多元化的同時,外來文化、亞文化等各種新文化也給社會文化帶來沖擊。在家庭結構小型化、傳統文化的轉型、消費主義的盛行與文化的市場化等變化中,傳統的社會文化面臨著市場與消費的沖擊,發生著各種裂變現象。中國電影在市場化轉軌之后,也被納入文化工業并成為大眾文化消費的重要部分之一。面對傳統社會文化的裂變,中國電影重要的內在任務便是在新的社會文化完全樹立起來之前,以對各種生活方式的關注重構社會文化,潛移默化地推進社會發展轉型中的文化融合與創建和諧社會局面,實現大裂變底色下的社會文化局部創新、協調、多元、開放、共享、富有活力的發展。劉浩自身數十年的“北漂”經驗,令他將對社會文化變化的體察成功加入電影中,反映出傳統社會文化的裂變與重組歷程。
1999年即將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時,劉浩根據自己在積水潭橋邊租房的“北漂”經歷,編寫了《陳默與美婷》的劇本,并艱難地在幾年時間內以捉襟見肘的資金完成了影片的后期剪輯。這部屢獲大獎、驚艷柏林的作品,在送去國外電影節前由于經費缺乏,甚至沒有獲得送審資格。2002年,《陳默和美婷》作為劉浩的處女作一舉獲得2002年度柏林國際電影節青年論壇最佳亞洲電影獎以及2002年度柏林國際電影節處女作特別鼓勵獎。劉浩由自身經歷出發講述了一對“北漂情侶”的悲歡離合。互不相識的年輕人陳默和美婷在北京忙碌著各自的生活,出身農村、懷揣明星夢的陳默在街頭賣花,知青后代美婷則在發廊給人洗頭。兩人意外相識后開始以扮演對方父親/母親的游戲在大城市中相互取暖,但美好的生活很快被打破:陳默被同鄉李斌騙走了準備給哥哥治病的2000元錢,爭執中深受重傷,在美婷懷中慢慢死去。劉浩賦予了這個寓言色彩的故事濃烈的現實主義質感,陳默跟著李斌替大小餐館、煙雜店送啤酒,攝影機也以尊重生活、還原真實的原則展現了20世紀90年代北京的老街老巷;然而電影鏡頭對原生態的生活的提煉和加工,又使得原本冰冷落寞的城市充滿熟悉的市儈風情。20世紀90年代的北京在文化裂變觀點下,正是所謂后工業社會在消費上呼喚和構建中產階級及其相關文化之時,然而在并無可與之對應的事實的中國,“盡管消費主義的狂潮席卷并改寫了中國城鄉的價值觀念及日常生活,但正是消費方式與消費‘內容,成為中國社會日漸急劇的階級分化的外在指征;服裝品牌、生活方式與居住空間,不僅成為現代社會所謂不同趣味的標識,而且成了階級身份的象征”[3]。陳默和美婷的打工仔身份與經濟基礎使他們無法在經濟上共享方興未艾的消費都市,但拓展自中國香港與中國臺灣、拓展與構筑著個體空間的大眾文化卻成為陳默、美婷與劉浩共享的全系社會文化,對卑微個體的關注與描寫,比被經濟條件分裂為不同階層的大都市更能有效地拓展“個人”的文化與心理空間。在陳默與美婷、劉浩與其他獨立電影導演無法被定位于中產階級的大眾文化所規訓時,陳默與美婷只能在狹小出租屋內相互取暖,而因資金問題一再擱淺的《陳默與美婷》花費3年時間才制作完成并與觀眾見面。也許正是因為如此,一抹赤裸裸的市井風情從此在劉浩的電影中扎根,直到20年后的新作仍然如此。
2021年6月5日,從影20年的劉浩攜新作《詩人》歸來,影片中再次浮現出《陳默與美婷》式粗鄙而生動、懷舊而悵惘,卻使人心安的氛圍感。《詩人》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80到90年代之交的國營煤礦,煤礦工人李五在目睹一名來煤礦體驗生活的老詩人前呼后擁的狀況之后,想要通過成為著名詩人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李五的妻子陳蕙在紡織廠印染車間工作,她為了丈夫的詩人夢想默默付出,李五也如愿成為一名小有名氣的詩人。然而在90年代,詩歌與文學的熱潮褪去,李五在無人理睬的境況中與妻子、詩歌分崩離析。《詩人》以20世紀90年代初新詩熱潮減退,新詩歷史轉型為背景,同時穿插了對中國傳統婚姻與家庭關系的思考,以及對國營企業在市場浪潮中衰退的哀悼。市場化變革改變了社會對文學的追求整體,然而文學作為曾經全民族的精神寄托,塑造了民族的整體氣質。面對這種情況,劉浩以詩歌與詩人的境況號召觀眾要堅定自身文化自信,以詩歌、文學、電影等手段重塑民族精神家園,在新時代重新創造出符合時代發展要求、引領時代潮流的先進文化。
三、電影形式中的文學性與文學意味
電影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優秀的電影必定具備描述生活、提煉生活與自然真正本質的意義,這也是電影文學性與文學意味的來源。電影的文學性可能與電影劇本的文學性有關,但它并不是電影原作、劇本、臺詞等文字的簡單構成,而是根植在電影形式中的表意功能與特性。“文學性”概念最早出現在俄國形式主義理論中,語言學家與文學理論家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研究總體文科科學時提出:“文學科學的對象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4]在這一意義上,建立在視聽形式上的電影與建立在文字語言上的文學是兩種具有不同形式與特性的藝術,在“文學性”或“人文性”方面建立了獨特的聯系。以獲得第58屆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簽約獎和團結獎、第17屆法國維蘇爾國際電影節金三輪車獎、埃米爾·集美獎、巴黎東方語言獎等獎項的《老那》為例,這部電影在一種了無痕跡的原生態的造型敘事中,關注退休老人的社會關系、家庭氣氛與感情生活,塑造了和藹可親,卻因老友失散與愛侶過世倍感寂寞的善良平凡老人老那形象。劉浩在尊重生活原本樣貌的前提下,以還原生活的記錄式畫面與嚴肅的藝術創作態度,令影片表現出既有人間煙火,又如詩歌般緩慢流淌的文學氣質。片頭,退休工人老那與車間老領導老張一起結伴步行去南城批發市場買菜,老那在過馬路時看到了數年未見的初戀情人李瑩。回家后老那興致勃勃地為春節回家的兒女準備大餐,眾人圍坐在桌前吃飯的場景令人想起李安的《喜宴》(李安,1993)及《飲食男女》(李安,1994),從高空懸吊俯拍的鏡頭中,圓桌、層層疊疊的豐盛菜肴與家人充滿中國傳統文化中意蘊無窮的團圓意味。老那與李瑩見面后,原本寂寞的兩位老人相互慰藉,兩人于除夕夜在一家“老字號”肯德基分享年輕人的洋快餐;雙方兒女阻止兩人交往后,老那又以想進托兒所尋找青春的名義住進了托兒所,繼續與李瑩往來。很快,兩人的“地下戀情”再度被子女察覺。劉浩以不攜帶過多個人立場與情感的鏡頭默默觀察著老那的生活,將文學式深入淺出的詳細描寫融入電影鏡頭對世俗百態的影像描繪之中。老那和李瑩發現彼此都患上了輕度老年癡呆癥早期傾向,兩人為了不影響、拖累兒女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想出許多詼諧的妙招強化思維,延緩病情發展,老那甚至用自創的腦筋急轉彎難倒了醫生。在影片的最后一幕,起夜的老那終于忘記了自己的房間,最后躺在了小兒子的床上。《老那》將老年人不愿拖累子女的心情,以及老年癡呆癥的內容設想以這樣一種冷漠、旁觀而準確的表現方式表現出來,凝視銀幕的觀眾仿佛立在床邊的兒女一樣看著渾然不覺的老那。這種將老年人在脫離社會后的精神空虛、情感困境與年紀漸長造成的身心問題等設想與構思表現出來的形式,就可以看作電影的文學性與文學意味。
劉浩的其他影片中也充滿了對文學與電影之間可能性的連接:《陳默和美婷》中的菊花茶象征著美婷靈魂的純潔與對美好的堅持;《向北方》中小艾在向父母言明自己的病,希望父母適時放棄自己時,原本融洽溫馨的飯桌氛圍突然沉重,小艾放下碗筷回房間放起了父母初見時聽的曲子,父親也突然也不吃了,邀請母親跳舞,兩人伴隨著音樂從餐廳一直跳到了陽臺。這些鏡頭或場景以樸素的畫面細膩地體察著厚重復雜的情感,將人性的溫暖與涼薄、人生的無常與恒常以純凈而富有表現力的鏡頭語言呈現出來,充滿人文與文學的厚重意蘊。
結語
劉浩的每一部影片都以文人般的關懷體察和感知復雜而深刻的社會現實,從北漂青年、貧困農民到失獨家庭等人群。劉浩始終直面擺在中國全社會面前的民生問題,并以獨立電影人的視角觸摸邊緣人物的內在心境,在具有樸素現實感與情感感染力的視聽呈現中體現出豐富多元、意蘊深遠的電影文學氣質。
參考文獻:
[1]林年同.中國電影的空間意識[C]//香港中國電影學會.中國電影研究.香港:香港中國電影學會,1983:81.
[2]林年同.中國電影美學[M].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187.
[3]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31.
[4][俄]什克羅夫斯基.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M].方珊,譯.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23.
【作者簡介】? 楊卿楠,男,四川西昌人,四川傳媒學院國際教育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8年度四川省教育廳一般項目課題“基于新媒體平臺的藝術類大學英語教學模式研究”
(編號:18SB0342)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