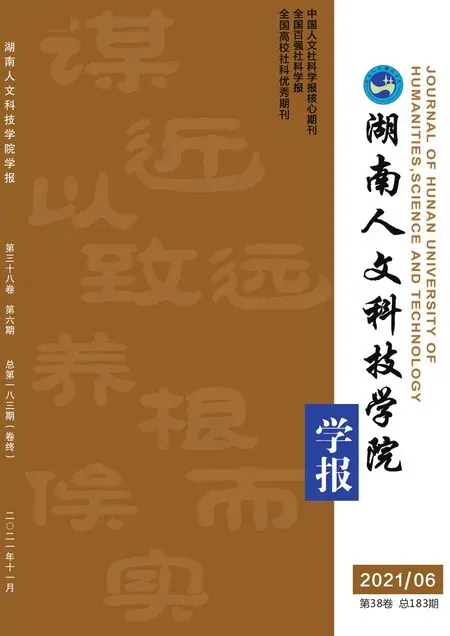論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及其對湘軍的影響
范大平
(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南 婁底 417000)
清王朝至道咸時期,已日益呈現出衰落之勢,政治腐敗,經濟蕭條,內憂外患,危機四伏。面對危局,思想文化界一些學者受傳統儒學“修齊治平”德治思想的影響,試圖從學術層面探尋社會危機產生的根源及其解決的辦法。于是,已獨霸學壇百余年之久的漢學作為學界主流地位發(fā)生動搖,并被學界斥責為瑣碎拘執(zhí)、失道誤國,造成社會道德淪落、人才匱乏的嚴重后果;與此同時,被壓抑日久的宋明理學等學術思想開始復蘇,出現所謂“理學中興”的局面。正是在此背景下,羅澤南先以“醇儒”之身坐館授徒20余年,同時精研理學,著書立說;后以一介書生投筆從戎,率徒編練團勇,倡辦湘軍,轉戰(zhàn)數省鎮(zhèn)壓太平天國。羅澤南是晚清理學和湖湘經世學者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治學嚴謹,尊崇宋儒之學,探其精微,得其奧義,并結合自己的教育實踐和認識體悟,形成了以程朱理學為基礎并深受湖湘文化影響的具有一定特色的理學經世思想。羅澤南將其理學經世思想充分運用于文化教育與治軍打仗,通過其與弟子的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實踐,成就了“理學名師”與“湘軍之母”的名聲,取得了“大小二百余戰(zhàn)鮮有敗績”的驕人戰(zhàn)績。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及其實踐對湘軍的崛起與湖南社會文化風氣的轉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 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及其基本特征
羅澤南尊崇程朱理學,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朱熹等理學大師的著作均作過深入的探究和剖析,著述頗豐。體現其理學經世思想的主要著作有:《人極衍義》《西銘講義》《周易本義衍言》《周易附說》《皇輿要覽》等,對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張載的《西銘》、朱熹的《周易本義》等著作作了深入的研究和闡發(fā),尤其對理學的基本范疇、基本命題大都作了詳盡的闡述,并“將周、張、朱等人思想中的精微之處進一步挖掘出來,特別是對周敦頤的‘主靜察幾’之說、張載的‘民胞物與’思想進行了反復的申論”[1]。羅澤南在取各家之學特別是程朱理學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理解和認識,形成了具有一定創(chuàng)意和特色理學思想。同時,羅澤南作為素有經世傳統的湖湘學者,其理學思想又呈現出強烈的經世氣息,并通過其著書授徒、投身軍旅、創(chuàng)辦湘軍等政治、軍事、文化教育活動,實現他經世致用的理想抱負。可以說,以儒學正統和程朱理學為思想基礎,以經世致用為價值旨歸,是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的基本特征。
(一)捍衛(wèi)儒學正統,倡崇程朱理學
儒學發(fā)展到宋、明,出現了學術轉型,理學成為思想文化的正統,被統治者奉為圭臬。但到清代中后期的乾嘉時期,以考據學為代表的漢學流行,而理學被壓抑,士子或熱衷研讀心學,或醉心于詞章。道咸時期,隨著社會危機的加深,漢學作為學界的主流地位發(fā)生動搖,于是,學術界“理學復興”應運而起。羅澤南是晚清“理學復興”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堅持捍衛(wèi)儒學正統為己任,正學術、斥異學,大力倡崇程朱理學,猛烈批駁陸王心學。
素以“崇正學、辟異端、正人心、明圣教為己任”的羅澤南,針對其時學界俗學斑雜、風氣不正的局面,認為匡時濟世必先正學術,才能正人心,而正學術首先就要辨明正統。為此,他認為:“議淫邪遁之詞,甚為難辨。知言之功,當自何始耶?曰:不消急要去辨別他底,惟先深格物致知工夫,將圣賢大中至正之道,辨得明白,表里精粗,毫無蒙蔽,則彼說來前,便能燭其病之所在”[2]285羅澤南與傳統士人一樣,極力推崇 “萬世圣人”的孔子和“亞圣”孟子,但他對宋儒更為注重,把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看作孔孟的繼承人,直接傳承了他們的“大中至正之道”,以為宋儒理學 “發(fā)堯舜之薪傳,續(xù)孔孟之微脈,圣賢之道,益以大明于天下”[3]206其中,羅澤南對宋儒最推崇的是朱熹,認為“非朱子無以發(fā);濂洛之蘊奧,非朱子無以明”“夫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格致之旨,孔孟之嫡傳也”[4]267。
羅澤南認為,要堅持正統儒家的“大中至正之道”,就必須在辨明儒家正統的同時,找出異端學說的謬誤所在,從而不為異端邪說所迷惑。他認為佛、老之學是雜學、俗學;佛老之學不絕而盛行天下,則必然造成巨大的社會危害。因此,應堅決排斥。同時,為了防止宋、明以來流行的心學危害“儒學正統”,羅澤南對陸王心學也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在《姚江學辨》開篇即言:“吾謂陽明《傳習錄》、《大學問》論學諸書,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日無善無惡。無善無惡,陽明所不常言也。其說本之告子,出之佛氏。常言之,則顯入于異端而不得托于吾儒也。然而千言萬語闡明致良知之旨,究皆發(fā)明無善無惡之旨,陰實尊崇夫外氏,陽欲篡位于儒宗也。”[4]209他認為“陽明悖古圣之明訓,信外氏之邪說,謂性之本無善無惡,發(fā)用也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是則天下之為仁、為義、為忠臣、為孝子、為信友、為悌弟,皆非本體所固有,不過因乎意念之所動也;為奸、為宄、為盜賊、為寇攘、為篡逆,亦發(fā)用上所有也。圣如堯舜,于性何與?暴如贏楊,于性何傷?不將率天下之人淪三綱敦九法,至于人將相食而不止哉! ”[4]211
(二)傳承傳統理學思想,對程朱理學作出具有創(chuàng)意的闡釋
羅澤南作為一位恪守程朱理學的思想家,一方面堅持儒學正統,極力尊崇程朱理學,傳承程朱衣缽;另一方面,他又結合自己的治學體驗,對程朱理學作出了具有創(chuàng)意的深入探究、發(fā)掘和闡釋,并形成了具有一定特色的理學思想體系。
在理氣論方面,羅澤南繼承了程朱理氣論的基本思想內涵。“太極”“理”與“氣”,是程朱理學中關于哲學世界觀、本體論的基本范疇。羅澤南對朱熹之論“太極”以及“理”與“氣”等哲學本體論范疇加以深入的闡發(fā),并提出“天地人一太極” “理在氣先,不離不雜”“氣化萬物,理為主宰”等思想觀點。他認為:“天、地、人,一太極也。至哉!道乎無聲無臭,綱維二五,根抵萬化。至誠無息,天以誠而運也;至順有常,地以誠而凝也。”[3]189在“理”與“氣”的關系問題上,羅澤南在朱熹的理氣觀的基礎上構建了“理氣不離不雜”的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認識格局,認為:“蓋理也者,所以宰夫氣者也;氣也者,所以載夫理者也。無理,氣無所宰;無氣,理無所附。二者不相雜,亦不相離者也。是故陰陽異位,道無往而不存也;動靜殊時,道無往而不在也。散之萬殊,統之一致也,非默契天地之化育,孰能識其微哉?”[3]190在“理”與“氣”在哲學本體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們如何形成世界萬物的問題上,羅澤南把“理”與“氣”在天地萬物中的具體作用概括為8個字,即“氣化萬物,理為主宰”。他認為:“天地之大,無非此理之所充周;古今之久,無非此理之所運量也。是以人生其中,莫不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莫不得天地之理以成性。”[5]又言:“理在天地間,初無偏、全之分,有是氣即有是理。氣之清者,此理固無不存;氣之濁者,此理亦無不在。惟其氣有清濁之殊,故其理有明蔽之異。”[2]306并說明了氣在具體物質成形中的作用:“天地之氣,萬有不齊。和風甘雨,其氣清明;陰霾濁霧,其氣昏暗;迅雷烈風,其氣震蕩;愆陽伏陰,其氣偏戾。天時有不齊也,西北之地高俊,其氣多剛勁;東南之地平衍,其氣多柔弱。得山之氣者,其人多雄健,其惡者為粗頑;得水之氣者,其人多秀麗,其惡者為淫靡。故數里之間,其氣多有不同,地勢有不齊也。天地之氣各殊,故人之稟之者,其氣質亦不相俟矣。”[2]307
在心性論方面,羅澤南繼承和發(fā)展了宋明理學的人性論思想,提出“性即理”的命題,并對“氣質之性”的意蘊作了具有一定新意的闡發(fā),提出了“心為身之主宰”和“心也者,理之次舍也”的思想觀點。“把心性關系置于身、心、行、道這樣一個更廣的思維空間中考察,強調理為心性本體,讓他的心性論與理氣論順利地建立起連接。”[6]然后,羅澤南又進而從天地人的關系將萬事萬物變化與人的身體結構運動聯系起來加以論述。他在《人極衍義》中說:“人身一天地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吾形,得天地之理以成吾性。精氣,其天之覆幬也乎;骨肉,其地之持載乎;聲音,風雷之鼓蕩乎;血液,雨露之涵濡乎;毫發(fā),草木之榮滋乎:經絡,山川之條理乎;呼吸。晝夜之循環(huán)乎;寐興,寒暑之往來乎;老幼生死,元會運世之遞降乎。曰仁、曰禮,元亨之通乎;曰義、曰知,利貞之復乎。天地,一大人也;人,一小天地也。心天地之心,行天地之事,其量固未嘗或隘也。蓋天地人同一太極也,理之一也,天地人各一太極也,分之殊也。”[3]190
在人性論方面,羅澤南主張性善論。他綜合了孟子性善論,在承襲宋儒理學把人性歸諸于 “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 的基礎上,深入闡發(fā)了其意蘊及二者的關系。他把人性之善惡、智愚、勇怯等歸之于氣性的差異,并認為應實行人為干預而求其變。其曰:“人性皆善,何以人之善、不善若是之不同與?曰:性善者,天命之本然也。有善、有不善者,氣稟之各異也。氣有清有濁,斯人有智愚也;有純有雜,斯人有賢否也;有強有弱,斯人有勇怯也。故上哲之資清而純,下愚之資濁而雜,其中人,則毗陰、毗陽,或靜、或躁之不同。氣稟拘于生初,物欲蔽于后起,斯人之才遂至于千變萬殊而不可紀極然。而物與人分明暗也,圣與凡分通塞也。暗者不可使之明,塞者猶可使之通。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為所囿者,變化之道,是在乎人為也。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3]191于此,羅澤南從儒家人性論的視角出發(fā),在肯定人“性善”的前提下,解釋和肯定了“氣”與人為因素對人性的“善惡、賢愚、勇怯”的影響。
在道德論方面,羅澤南堅持傳統的儒家道德觀,竭力維護程朱理學倫理的純正性,把“仁”作為最高道德規(guī)范,批駁了陽明心學“以仁義禮智為表德” “天下無心外之物”和“良知”論觀點,充分論述和深入闡發(fā)了“仁愛”“禮樂”“義利”等關系范疇。羅澤南認為“仁義禮智未發(fā)之中也,大本也”,而“陽明悖古圣之明訓,信外氏之邪說,謂性之本無善無惡,發(fā)用也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是則天下之為仁、為義、為忠臣、為孝子、為信友、為悌弟,皆非本體所固有,不過因乎意念之所動也;為奸、為宄、為盜賊、為寇攘、為篡逆,亦發(fā)用上所有也。圣如堯舜,于性何與?暴如贏楊,于性何傷?不將率天下之人淪三綱敦九法,至于人將相食而不止哉”[4]211!
在認識論方面,羅澤南以“格物致知”作為基本方法論原則,將認識論與道德論結合起來,體現出其理學思想的基本特征。他說:“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7]
(三)以經世之學充實程朱理學,并將其運用于教育、政治、軍事實踐
明末清初以來,湖南學界受船山思想影響,一直具有著濃厚的經世傳統,在晚清由空疏流弊的“純學術”向“經世致用”的學術轉向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涌現出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唐鑒、曾國藩、劉蓉、左宗棠等一大批經世派大家,以至孟森在明清史講義中說:“留心時政之士大夫,以湖南最盛”。羅澤南當時雖以塾師身份名聲不顯,但實則為其時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幾十年的教育、政治、軍事實踐中,主動用經世之學來充實程朱理學,在注重以儒家道德和程朱理學思想修身養(yǎng)性的同時,積極倡導經世實學并竭力躬行之,“凡天文、輿地、律歷、兵法,及鹽、河、漕諸務,無不探其原委”[8]。羅澤南的經世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社會政治思想、軍事思想、教育思想及其實踐之中,并通過其撰寫的《皇輿要覽》一書而集中體現。《皇輿要覽》共9卷33篇,內容豐富,涵蓋廣博,縱論山川河流、水患水利、漕運鹽政、少數民族防務及國內外形勢,將羅澤南的理學經世思想予以充分展現。
羅澤南的經世思想,首先體現在他的社會政治思想中。羅澤南雖曾長期坐館授徒,卻又密切關注社會時政。他的社會政治思想,首先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合理性的理論前提和基礎上展開的。羅澤南認為,君主的職責就是“代天理物”,應該像愛護父母一樣愛護老百姓。如果君主勤政愛民,修已安民,以禮儀教化百姓,就能恢復其善良本性,老百姓也就會擁戴君主,遵守社會秩序;而如果君主安于享樂,不修德愛民,不勤政安民,那就會背棄天道,違背民意,社會就會動蕩不安。因此,君主就一定要修身養(yǎng)德,而為人臣者就應該勇于上疏進言。他說:“乾父坤母,化生萬物;四海黎獻,盡屬天地之赤子。然天雖生此民,厚生正德,有非天之所能為者,則命此有德之君以統治之。故君行政以治民,實為代天理物,而有父母斯民之責。”[9]羅澤南還認為,在國家治理上既要注重“保民而王”,對民施仁政,行教化,但又不可廢法度。而國家的運行管理還必須要有德才兼?zhèn)涞娜巳危虼耍e賢任能。他認為:“賢人登庸,天命以存;不肖在位,天命以亡。進退一世,人才以寅亮天工,典至巨,系至重也。是故五臣舉,虞治盛;伊傅起,商道隆;呂周夾輔,王化大行;方召佐命,宣王中興。是皆賢才之贊襄,開至治于千古。”[3]196此外,羅澤南還認為,要維護封建統治秩序,就必須使老百姓有安定的生活;而要使老百姓生活安定,就必須以封建土地制度作為切實保障。針對當時“天下之田,又多為富者所占” 的土地兼并嚴重狀況,羅澤南提出了“復封建”“復井田”的主張,他認為“蓋封建者,井田、學校之所由行也。不封建,則不能井田,貧富不均,養(yǎng)民之道失矣;不井田,則不能學校,庠序無法,教民之道失矣。”[3]197
羅澤南軍事思想,是其經世思想的重要內容。羅澤南一生雖然直接從事軍事活動的時間不長,但他非常重視軍事,在當塾師的時候就注重訓練門徒軍事武備;以后投筆從戎,在組建湘勇練兵、統兵治軍的過程中,將其理學經世思想完整地運用于軍事,成為赫赫有名的一代“儒將”。羅澤南軍事思想內容豐富,頗具特色。他注重軍隊思想政治工作,嚴肅軍紀。他與其弟子率領的軍隊往往在行軍作戰(zhàn)之余,講學論道,以儒家忠孝仁義之倫理道德教導軍隊士兵。此外,他對戰(zhàn)爭的目的和性質、戰(zhàn)爭與思想政治的關系、戰(zhàn)略戰(zhàn)術、戰(zhàn)備、軍事形勢與地理等問題,也都有深刻的理解和闡述,形成了別具一格的戰(zhàn)爭理念與軍事思想。例如,他認為:“兵也者,所以行天之討者也。方命虐民,罔畏天威,以兵靖之,而后可以禁萬民之亂。御戎之法,不在邊錘,而在朝廷之政事也;戰(zhàn)勝之道,不在殺戮,而在德威之素著也。是故佳兵者不祥,有德者無敵。圣王之征天下也,以仁義為本,以節(jié)制為用,除暴安民,不得已而用之,故戰(zhàn)則必克也。不以好大勤遠略,不以太平忘武功。”[3]199他還認為,戰(zhàn)爭性質直接影響戰(zhàn)爭勝負結果,仁義之師因為深得人心,必然可以贏得戰(zhàn)爭的勝利。“惟孟子之言,乃天理人心之至。義旗一麾,天下自然響應,蓋大公無我之心,天下共知,我?guī)熚磩樱弴瘢缬幸I而望者,沛公寬大長者,遂能收人心于秦、項之余,況夫以純王子心,行政王之政者哉!仁以勝暴,此戰(zhàn)國時之第一著,亦古今之第一著,惜乎無有能用之者。”[2]278在戰(zhàn)術上,羅澤南主張以靜制動的作戰(zhàn)方針。曾國藩曾在奏稿中稱:“羅澤南自與此賊接仗以來,專用以靜制動之法,每交鋒對壘,賊黨放槍數次,大呼數次,而我軍堅伏不動,如不敢戰(zhàn),往往以此取勝。”[10]此外,羅澤南還非常重視注重軍事地理形勢的研究,注重考察山川河流、地理形勢和輿地制圖,并在軍事戰(zhàn)爭中加以適當運用。他說:“統籌天下之大局,黃河北條之水也,秦晉、燕趙之險憑之;大江南條之水也,巴蜀、荊襄、徐揚之險憑之。河水渾濁,操舟維艱,長江數千里,一帆可以上下,故東南爭戰(zhàn),必恃水陸之兼濟。”[11]
羅澤南教育思想,是他在長期的為學治學、座館授徒的教育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羅澤南從4歲開始“受命讀書”,19歲課館授徒,在辦團練之前,他長期作為塾師,培養(yǎng)了一批既遵循儒家倫理道德又有經世濟世之志的學生。羅澤南教育思想包含為學治學、教書育人的方方面面的內容。他認為,為學治學一定要為“圣學”、為“正學”,而要為“圣學”、為“正學”就必須首先立志,即其所謂“人之為學,必先立志。志不立,雖以至易為之事,逡巡畏縮,廢然而無所成。志一立,雖以至難為之事,鼓舞而不可御”[12]。在論及為學治學時,羅澤南還強調講求經世之學。他說:“吾人為學,固當于身心下工夫,而于世務之繁瑣、民情之隱微,亦必留心窮究,準古酌今,求個至是處,庶窮而一家一鄉(xiāng)處之無不得其宜,達而天下國家治之無不得其要。此方是真實經濟,有用學問。”[13]羅澤南在長期的教育教學實踐中注重倫理道德教育,勇于探索,善于總結,教育方式方法靈活多樣,寓教于樂,并自編輔導講義:《西銘講義》和《小學韻語》。由于教學得法,效果良好,羅澤南日益成為湘中有影響的塾師名儒,身邊逐漸聚集起一群有志士子門徒,成為日后湘軍名將的搖籃。
二、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對湘軍的影響
以儒學正統和程朱理學為思想基礎,以經世致用為價值旨歸的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通過其長期座館授徒、組建湘勇、統兵打仗以及成就湘軍的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實踐而熠熠生輝,在晚清的湖南乃至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對湘軍的影響至深,其影響的對象上至湘軍將帥,下至普通士兵;影響的方面涉及湘軍的組建訓練、軍隊建制、軍事理念、治軍與行軍打仗及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
(一)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對湘軍將帥及相關名臣的影響
羅澤南的學識淵博,是湘中有名望的塾師鄉(xiāng)紳,教書授徒20余年,其弟子友人為數眾多。曾國藩、劉蓉、郭松燾、胡林翼、左宗棠等“中興名臣”都與其交往甚密,而羅門弟子更是遍及三湘,據他的好友劉蓉說:“從之游者數百人”。其中,因投身湘軍而留名史冊的有:王錱、李續(xù)賓、李續(xù)宜、蔣益澧、劉騰鴻、楊昌浚、李杏春、鐘近衡、鐘近濂、易良干、謝邦翰、羅信東、羅鎮(zhèn)南、朱宗程等,共達16人之多。這些后來成為湘軍著名將領的他們之所以能“以書生拯大難、立勛名”,與其在不同程度上受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的影響有直接的關系。正如曾國藩在《羅忠節(jié)公神道碑銘》中所言:“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理學家門,下多將才,古來罕有也。”羅澤南向弟子傳授學問,與一般的塾師不同。他不僅授以弟子科業(yè),而且將義理經世之學傳之,并且自己也身體力行。羅門弟子在羅澤南的影響下,以程朱理學為治學和立身處世的標準,以經世致用為價值取向。王鑫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得同邑羅羅山先生師事之”“日夜與講明善復性、修己治人之道”,“每恨相從之晚也”[14]40-42。李續(xù)宜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從羅澤南游,“日與講論正學,自以躬之所行,不逮所言”[15]。同年,師從羅澤南的鐘近衡將自己每天的言行見聞記錄下來并考察得失,因此得到羅澤南的特別稱許:“吾門為己之學,鐘生則可望乎!”[16]謝邦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從羅澤南讀書于朱氏別塾,“朝夕講習,以圣賢之道相儆醒”[17]。正因為如此,當太平天國起義爆發(fā)后,羅澤南最初興辦團練,他們就都毫不猶豫地追隨羅澤南投身到鎮(zhèn)壓太平軍的活動中去了。也正是這一大批弟子在同太平軍作戰(zhàn)中追隨羅澤南左右,而后來又大多為官一方,他們訓練民團,安撫百姓,興辦教育,推行洋務,為晚清“咸同中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關于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對羅門弟子的影響,《清代名人傳略》評價:“羅雖然是一位學者,卻有經世之才,尤精于兵書戰(zhàn)略。羅澤南諸如此類的成就與品質才干,在他多年教書的生涯中,也許已影響了他的學生。”[18]事實上,在后來與太平軍的爭斗中,羅澤南的弟子們平時在師門所學習積蓄的學識與經世才干,特別是軍事才干得到了充分施展。如王鑫在羅澤南門下求學時就注重研究兵法,后來帶兵時結合自己的體悟寫出了《練勇芻言》《陣法新編》等兵書。在對兵士的訓練上,他注重明恥教育與軍事教育的結合,認為“將兵者練固不可廢,而訓尤不可緩”[19],“日教練各勇技擊陣法”“至夜,則令讀《孝經》、《四書》,相與講明大義”[20]。他充分利用忠孝仁義廉恥的儒家倫理道德來驅使士兵為其拼命,因此,王錱所統領的湘勇兇狠異常,少有敗績。又如,李續(xù)賓在羅澤南的影響下,也注重研習輿地學,“摩繪地圖九百余紙” ,曾國藩見之,“自謂所藏皆不能及也”[21]。李續(xù)賓對兵法也深有研究,在帶兵之前就著有《孫子兵法易解》。在羅澤南帶兵期間,李續(xù)賓一直跟隨其左右,深受其思想影響。“羅公善言易,攻戰(zhàn)之暇日相與講習討論”, 續(xù)賓“于屈伸消長之機、進退存亡之道,頗能默契于心”[22]。因此,對于羅澤南的作戰(zhàn)意圖,李續(xù)賓總能全面領會。這些,為日后李續(xù)賓成為湘軍名將打下了良好基礎。羅澤南戰(zhàn)死后李續(xù)賓接統其軍,“治軍一守羅澤南遺法”[23]。在他的率領下湘軍“益發(fā)揚而光大之”[24]。曾國藩曾說:“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chuàng)之者羅忠節(jié)公澤南,大之者公(指李續(xù)賓)也。”[25]在羅澤南死后,羅氏弟子王鑫、蔣益澧、楊昌浚等深為左宗棠所器重。
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對其弟子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這些弟子因戰(zhàn)功成為地方大員后對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活動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首先,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對吏治進行了整頓。他們擔任地方官員后,大多以整頓吏治為要務,興利除弊。如蔣益澧在署理浙江巡撫時,“遴鄉(xiāng)士之樸誠者,予以厚資,令微服赴郡縣密考牧令政績”。其次,積極倡導和推行團練。羅澤南及其弟子本身就是靠團練起家,因此對辦團練極為重視,每攻克一地他們都要“召見士紳,慰免以忠義,出示令行團練法,以自相保衛(wèi)”[26]。再次,積極興辦地方文化和教育事業(yè)。羅澤南及其弟子在為官之后,極其重視恢復地方文化教育,注重弘揚儒家道德禮儀。積極興辦義學、書院,恢復科舉。1853年羅澤南駐軍衡州時,修復了石鼓書院。次年,又出資興建灣州義學。李續(xù)賓與曾國藩、胡林翼共同出資興建箴言書院。蔣益澧任浙江巡撫時“增書院,設義學,興善堂”并修復貢院,補行鄉(xiāng)試;其任廣東巡撫時,又極力恢復廣東地區(qū)鄉(xiāng)試。羅澤南及其弟子每占領一地,都竭力宣傳忠孝仁義廉恥的儒家倫理道德。1857年,王錱路過一陳姓村莊,見當地編輯的《崇仁志》上有理學、忠孝、仁義的目錄,就對村民說:“爾輩今日尚知有此六字乎?堯、舜人皆可為,特患志不立耳。”[27]
羅澤南與曾國藩、劉蓉、郭松燾、胡林翼、左宗棠等一群有著共同學術旨趣的友人一起,不僅以經世實學著稱于晚清,而且還積極從事軍政文教事業(yè),竭力為清王朝濟時救弊,為所謂的“咸同中興”盡心盡力,死而后已。正如梁啟超所言:“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咸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其后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28]曾國藩與羅澤南家鄉(xiāng)相近,少年時即仰慕其名,一起創(chuàng)辦湘軍,南北征戰(zhàn),對羅尤為倚重,對羅的過早陣亡甚為痛心,以挽悼之:“步趨薛胡,吾鄉(xiāng)矜式;雍容裘帶,儒將風流。”曾國藩所作的《羅忠節(jié)公神道碑銘》對羅澤南給予了高度評價,曰“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勛。朝野嘆仰,以為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學者久矣……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圣;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羅澤南與劉蓉同為湘鄉(xiāng)究心圣賢、砥礪品性之人士,兩人相互督促,并引以為知己。在《春日懷劉大仙霞》一詩中,澤南發(fā)抒二人惺惺相惜之意,“男兒莫受虛名累,七尺頑軀忍拋棄。叱咤風云生遠心,酒酣拔劍蛟龍避。兩地相思二月天,班超投筆誰少年?誰少年?默無語,讀書之樂樂千古,篝燈獨聽瀟瀟雨。”[29]羅澤南與郭松燾、胡林翼、左宗棠的關系也十分密切,胡林翼武昌被太平軍攻克告急時,羅澤南毅然率部從南昌急忙回援,以至命殞武昌。羅逝世后,郭松燾專為其撰寫年譜。左宗棠在湖南組建“楚軍”,就是以羅澤南弟子王鑫的老湘營為班底的。左宗棠不輕易服人,但對羅澤南卻極為贊賞。
(二)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對湘軍創(chuàng)建、訓練及治軍的影響
羅澤南在興辦團練、訓練湘勇、初創(chuàng)湘軍及其以后領兵打仗、治理湘軍的過程中,始終以捍衛(wèi)封建綱常禮教為旗號,以理學經世思想為精神靈魂,注重思想教育和意志磨礪,嚴肅軍紀軍風,從而練就了一支勇猛異常、“少有敗績”的湘軍勁旅,成就了“湘軍之母”“一代儒將”的名聲。事實上,湘軍將領中,大多有“儒將”而兼“悍將”之謂,這是士人出身的湘軍將領最根本的人文特質。羅澤南、曾國藩、胡林翼、劉蓉、左宗棠、王鑫、李續(xù)賓、蔣益澧、楊昌浚等都是以文才為前提,以德才為根本,滿腹經綸,深明忠義,智勇雙全,可謂文經武緯之才。曾國藩、羅澤南統領的湘勇以理學經世思想融合湘中地域血性文化精神,作為立軍之本,大力倡導“以禮治軍”,注重發(fā)揮精神文化的教育作用,將剛毅血性文化精神與“公誠道義”之儒學倫理融為一體,并升華為“湘勇精神”[30]186。
羅澤南興辦湘勇早于曾國藩,已是公論。羅澤南坐館授徒時,即教授門生既習文,又習武。咸豐二年(1852年),太平天國起事初入湖南,羅澤南應湘鄉(xiāng)知縣朱孫詒之請組織編練湘勇時,招募的大都是能吃苦耐勞農民,而領兵的多為理學士子,此所謂湘軍“選士人,領山農”之先例也。羅澤南以捍衛(wèi)儒家道義和程朱理學為號召,常以封建理學、綱常名教以及湘文化與湘中地域血性文化對將士進行思想灌輸和精神訓導,整肅軍隊,嚴明軍紀。他在帶兵打仗的過程中,也常向士卒陳說忠孝節(jié)義,通過其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兵卒日觀月摩,漸而化之。王定安在《湘軍記》中說:“湘軍創(chuàng)立之初,由二三儒生被服論道,以忠誠為天下倡。生徒學弟,日觀月摩,漸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恥,急王事,以畏難茍活為羞,克敵戰(zhàn)死為榮。”又言:“當湘軍興起,山農柔懦者亦頗畏遠征,及援江西,士人輕死陷陣,疊克縣城。國藩聞而樂之,益以忠義激勵將士。而塔齊布、羅澤南、李續(xù)賓、李續(xù)宜、劉騰鴻、蕭啟江之倫,皆崇紀律,重廉恥。于是,隴畝愚氓,人人樂從軍,聞招募則爭出效命,無復綠營征調離別可憐之色。其后湘軍戰(zhàn)功遍天下,從戎者益眾。”[31]168正是羅澤南組編的這班鄉(xiāng)勇人馬,日后成為曾國藩辦理團練、訓練湘軍的最初班底。因此,羅澤南“湘軍之母”的稱謂可謂實至名歸。作為湘軍早期的主要統領和曾國藩倚重的得力悍將,羅澤南及其弟子參與了對太平軍的多次戰(zhàn)斗,“師弟戮力,轉戰(zhàn)大江南北,師碚而弟子繼之”[32]。羅澤南從軍雖僅有短暫的4年,然其與弟子轉戰(zhàn)兩湖、江西、安徽,挽危救急,歷經大小200余戰(zhàn),克復20余城。在羅澤南武昌陣亡后,按羅澤南遺言,其所部主力由李續(xù)賓統領,再克武昌,后又回援江西,并參與安慶之戰(zhàn)。在對太平軍的戰(zhàn)爭后期,羅澤南弟子王鑫、蔣益澧、楊昌浚、劉典等將領深為左宗棠所倚重,為平定浙江和最后掃平太平軍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三)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對湘軍組織結構與兵制的影響
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為指導創(chuàng)辦湘勇,對湘軍組建方式、組織結構、體制機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羅爾綱曾經說:“有清一代的軍制,咸豐前是綠營制度的時代,咸、同以至光緒甲午為湘軍制度的時代,甲午戰(zhàn)后為興練新式陸軍的時代,而論其轉變,則以湘軍為其樞紐。”[14]58湘軍軍制雖然最后是由曾國藩決定的,但羅澤南及其弟子在營制與訓練方式、軍事機制等方面的最初創(chuàng)造性貢獻,可以說是世所公認的。正如王定安在《湘軍記》中所說:“湘軍初興,王鑫、羅澤南皆講步伐,諳戰(zhàn)陳,深溝固壘,與賊相據。曾文正采其說立營制,楚師之強,莫與京矣。”[31]359
湘軍的編制以營為基本作戰(zhàn)單位,營以下為哨。哨以下陸師為隊,水師為船,騎兵為棚。湘軍之制起子陸師。湘軍陸師營制,是1852年由朱孫治奉命募招湘勇時,與羅澤南、劉蓉、王鑫等人一起制定的,最初為每營360人。1853年底,曾國藩移駐衡陽后又與羅澤南、劉蓉、郭嵩燾等改定營制,規(guī)定湘軍陸師每營加長夫120人,抬槍16人,成500人之數[33]。同時,還定出了湘軍的軍餉規(guī)制,規(guī)定陸師營官每月薪水銀50兩,辦、幺銀150兩,夫價銀60兩,共計260兩。凡幫辦、書記、醫(yī)生、工匠薪水設置與辦旗幟等,另補費用統統包括在內。其它各弁兵每月餉銀為:哨官9兩、哨長6兩、什長4兩錢、親兵護勇4兩5錢,伙勇三兩三錢,長夾三兩。如此,則奠定了湘軍的軍制。也因此,《清史稿》說:“曾國藩立湘軍,則羅澤南實左右之。”[22]11949
自羅澤南創(chuàng)建湘勇始,以封建人際關系和鄉(xiāng)土文化觀念為紐帶,來協調湘軍內部關系和構建軍隊體制、運行機制。在創(chuàng)建湘軍過程中,羅澤南、曾國藩鑒于清軍內部“敗不相救”的弊端,因而招募將士即以封建人際關系和鄉(xiāng)土文化觀念為紐帶,通過同鄉(xiāng)、鄰里、同族、親友、同學、師生等關系將其網羅在一起。統領由曾國藩挑選,營官由統領挑選,哨官由營官挑選,什長由哨官挑選,丁勇由什長挑選,形成以血緣、親緣、地緣、學緣關系為基礎的利害攸關、便于掌控的軍隊組織系統。曾國藩、羅澤南的同鄉(xiāng)、友人、弟子與湘軍其他將領相互之間姻親關系就非常普遍。這種封建社會與生俱來的對血緣姻親關系、同鄉(xiāng)關系、師友關系的認可和強化,使湘軍將士行倫普遍一致、思想高度認同,造就了一支異常強悍的地方武裝。在對太平軍的戰(zhàn)爭中,這支軍隊內部關系雖然也很復雜,也出現過像王鑫等個別將領難以統馭的現象,但總體說來,各統領、營、哨之間還是能首尾相顧、互相呼應的,很少發(fā)生見死不救的情況,也大都能服從曾國藩的調度。也正因為如此,湘軍在對太平軍的作戰(zhàn)中,充分展現出不同于清八旗子弟兵的強悍的戰(zhàn)斗力[30]151-152。
三、結語
羅澤南是晚清理學經世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也是近代湖湘文化與湘中地域血性文化孕育出來的典型人物。尊崇程朱理學、捍衛(wèi)封建綱常、重視思想教育、堅持忠義血性、倡導經世致用、熱心文治武功,是羅澤南基本的文化品格及其理學經世思想的精神內核。以儒學正統和程朱理學為思想基礎,以經世致用為價值旨歸,是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的基本特征。
他早年坐館授徒20余年,培養(yǎng)出大批學徒,其中涌現出王鑫、李續(xù)賓、李續(xù)宜、蔣益澧、劉騰鴻、楊昌浚等著名湘軍將領;同時精研理學,著書立說,撰寫有《小學韻語》《人極衍義》《西銘講義》《周易本義衍言》《周易附說》《皇輿要覽》等著作。中年后,又以一介書生,投筆從戎,率徒編練團勇,倡辦湘軍,轉戰(zhàn)兩湖、江西數省,救急挽危,歷經大小200余戰(zhàn),克復20余城,為鎮(zhèn)壓太平天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羅澤南以理學經世思想為導引,首興湘勇,對湘軍的創(chuàng)建、訓練、治軍及其內部組織結構與軍制的確立,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贏得了“湘軍之母”“湘軍儒將”的稱謂,也可謂名至實歸。自羅澤南創(chuàng)建湘勇始,湘軍即以封建人際關系和鄉(xiāng)土文化觀念為紐帶,來協調湘軍內部關系和構建軍隊體制、運行機制,形成以血緣、親緣、地緣、學緣關系為基礎的利害攸關、便于掌控的軍隊組織系統。羅澤南理學經世思想對曾國藩、劉蓉、郭松燾、胡林翼、左宗棠、王鑫、李續(xù)賓、李續(xù)宜、蔣益澧、劉騰鴻、楊昌浚等湘軍將帥及相關名臣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對晚清學術風氣的轉變與近世湖湘經世派文化的興盛有著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