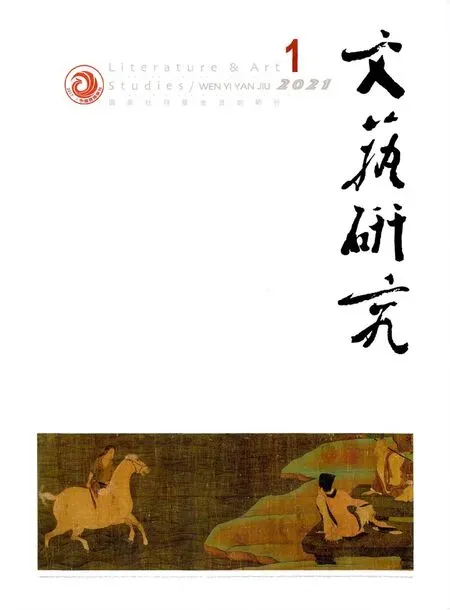“可能不可能”與“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
——圍繞AI和電影的跨學科對話
黎 萌 西南大學文學院、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研究中心
陸 丁 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劉 暢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
孫騫謙 中央美術(shù)學院人文學院
趙 斌 北京電影學院中國電影文化研究院
AI是目前的熱門概念,電影研究中一些相當有影響力、相當流行的學說也關(guān)注這個話題,形成了“后電影”“后人類電影”等廣為人知的理論。AI電影是一個典型的跨學科論題,是今天的電影與計算機科學、神經(jīng)生物學、心理學、哲學等眾多學科交叉的領(lǐng)域。圍繞這個問題也出現(xiàn)了一些爭議,諸如此類電影的可能性與倫理性。為此,本刊藝術(shù)哲學與藝術(shù)史研究中心組織五位相關(guān)學者以此為題,舉辦了首期跨學科論壇,討論角度涉及心靈哲學、倫理學、語言哲學、視覺藝術(shù)研究、電影史論等。最終文稿由黎萌整理。
一、AI與“后電影”狀況
黎 萌AI技術(shù)的發(fā)展及其在電影中的運用,帶來了人們關(guān)于“電影之后”或未來電影的一些猜測。這使“后電影”概念在目前備受關(guān)注。但對于這個概念,AI并非必需的技術(shù)背景。相反,“后電影”是一個具有強烈現(xiàn)代主義色彩的術(shù)語,是在AI技術(shù)影響電影之前就已出現(xiàn)的、對媒介競爭和電影技術(shù)變革的一種反映。“電影之死”的主題在電影理論中反復出現(xiàn)。遠在AI技術(shù)來臨之前,蘇珊·桑塔格在《百年電影回眸》中就有關(guān)于“電影之死”的感慨,認為電影在電視媒介的沖擊下成為沒落的藝術(shù)。這種在本體論意義上對于電影藝術(shù)的看法,顯然與某種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觀念有深切聯(lián)系。這也影響到電影史學家。深受格林伯格“純藝術(shù)”思想影響的西特尼的美國前衛(wèi)電影史《視覺電影》,就以某種“純粹性”為標準來構(gòu)建其心目中藝術(shù)電影的歷史。他完全排除了錄像和計算機動畫之類手段。他的前衛(wèi)電影史還排除了安迪·沃霍爾的《切爾西女孩》等使用多重投影的電影,如果不注意“純藝術(shù)”以及由此而來的“純電影”觀念,他對藝術(shù)電影的取舍標準就會非常令人費解。這類觀念使得“后電影”的危機感不可避免,正如最近的電影理論文集《后電影狀態(tài)》中指出的,“后電影”概念主要聚焦于所謂電影特有的兩個經(jīng)典標志——電影的攝影索引和電影機制,而今天這種攝影索引和電影機制都處于危機狀態(tài)。對競爭媒介的抵制和焦慮不僅存在于電影理論界,也反復出現(xiàn)在電影創(chuàng)作之中。比如柯南伯格的《錄影帶謀殺案》、詹姆斯·卡梅隆的《終結(jié)者》系列。奧利弗·斯通的《天生殺人狂》也許是最好的例子:后電影化的技術(shù)被妖魔化,與男女主人公不可思議的病態(tài)暴力聯(lián)系在一起,以至于有評論家稱它是一部關(guān)于電影末日的電影。盡管“后電影”這個術(shù)語如今非常流行,我認為它對于今天的電影理論談不上有非常豐富的蘊涵。“后電影”與特定時期的電影藝術(shù)觀念有關(guān),即一種現(xiàn)代主義的電影觀念,同時又是一種本質(zhì)主義的電影觀念,例如“純電影”。它所依賴的論證也是經(jīng)典電影理論中極為常見的,從20世紀初期的歐洲電影先鋒派到后來的阿恩海姆、蒙太奇學派理論家以及克拉考爾等人都使用過。哲學家卡羅爾將之概括為一種媒介本質(zhì)主義論證:這種論證假定了藝術(shù)媒介具有某種本質(zhì)性特征,這種特征決定了當運用這種媒介時應(yīng)該強調(diào)什么或不強調(diào)什么,一部作品的價值往往取決于在多大程度上凸顯了或?qū)崿F(xiàn)了這種本質(zhì)。例如杜拉克強調(diào)電影的本質(zhì)是視覺性而反對講解,克拉考爾強調(diào)攝影術(shù)的本性是紀錄而不是造型,并且相關(guān)特征決定了一部電影是不是“電影性”的。這類思想路徑在后來遭到了很多質(zhì)疑和拒斥。如果你并不持有這種電影觀念,比如你更贊同的是丹托路徑的關(guān)于運動影像藝術(shù)的開放得多的概念,你可能就不會接受“前電影”“真正的電影”和“后電影”的區(qū)分。回到我們關(guān)心的AI背景,“后電影”這類概念的啟發(fā)可能就在于提示我們?nèi)チ粢夂拖胂螅涸谟忠淮胃锩缘募夹g(shù)浪潮之下,電影可能呈現(xiàn)什么新樣態(tài),可不可能出現(xiàn)AI電影,如果可能的話,真正的AI電影會是什么樣。
劉 暢什么叫真正的AI電影呢?這可能有歧義,一個意思是以AI為主題的電影,比如《機器姬》 《AI》等等。另一個意思,即我們今天想討論的AI電影,不是以AI作為主題,而是AI作為作者的電影。在這個意義上,AI電影“可能不可能”的問題,也就是AI有沒有可能成為電影作者。
陸 丁還可以問,AI能否得到一種新電影?問題不在于電影生產(chǎn)的自動化,而在于電影會變成什么樣。畢竟,數(shù)碼代替膠片,不是制作電影的新方式問題,而是產(chǎn)生了不一樣的電影。例如,可以與沉浸式觀看方式對比。戴上頭盔、借助捕捉眼動而生成的非線性或多線的故事是電影嗎?就好比說,漫畫是(再現(xiàn)性)圖畫嗎?它們所涉及的認知狀態(tài)是完全不同的。AI生成腳本容易理解,處理符號是簡單的功能,處理卡通畫面也是。但有“自動”剪片機嗎?完全從無到有地生成真電影,要怎么做?也許只能是某種推送機制,針對某種收集偏好的素材庫——類似APP(當然了,APP也不只是推送)。
孫騫謙什么意義上的電影可以稱之為AI電影?有沒有“AI導演”“AI攝影”?哪些電影環(huán)節(jié)可以用AI來完成,或只是輔助?AI是能完整呈現(xiàn)一個電影,還是以人機嵌入的方式?如果只能人機嵌入,AI能編寫腳本,或生成鏡頭、場景,或取代服裝、化妝、道具等工種,但還是只有人能夠理解完整的場景。劉暢提到AI作為電影作者的問題,在人類作者的情況下,對電影的理解總是涉及對電影作者的意圖的理解。黎萌曾提到美學中的“虛構(gòu)者悖論”,我覺得似乎可以成為一個討論的切入點。或許我們可以從這個問題開始吧?
二、可能不可能:意圖、理解與創(chuàng)造性
黎 萌“虛構(gòu)者悖論”與AI電影并沒有直接聯(lián)系,但它引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藝術(shù)作品的理解中作者意圖的地位。20世紀70年代,美學家拉德弗德發(fā)表了論文《我們怎么能被安娜·卡列尼娜感動?》,第一次以悖論形式提出:我們怎么會因為自己明知不存在的東西而產(chǎn)生真情實感?他構(gòu)造出三個直觀上正確、然而合起來不相容的前提:其一,虛構(gòu)作品的讀者/觀眾往往會體驗到被明知是虛構(gòu)的對象所感動的情感,例如恐懼、憐憫、愛慕;其二,在日常生活中,被感動的一個必要條件是被感動的人相信引起自己情感的對象存在;其三,虛構(gòu)作品的讀者/觀眾知道這些對象是虛構(gòu)的,他們不相信這些對象存在。拉德弗德最終復活了一個柏拉圖式結(jié)論:我們被藝術(shù)作品以某些方式感動,盡管極其自然因而完全可理解,但還是使我們陷入了矛盾與混亂。此后許多理論家嘗試用各種方式來消除這一悖論,大致上可以歸結(jié)為三種途徑。第一種被稱為“幻覺說”,它否認第三個前提。這類學說認為,虛構(gòu)作品的觀眾例如電影觀眾,由于各種原因形成了假的、錯誤的信念,或幻覺;觀眾在某種意義上相信虛構(gòu)之物存在。比如柯勒律治說詩歌的讀者之所以被打動,是因為他們“懸置了懷疑”。電影理論中最流行的也是這種學說,并且,電影在視聽方面的逼真性使得許多理論家堅信電影比文學之類更容易造成真假不分的幻覺,電影觀眾處在這種幻覺之中,并進而對最容易引發(fā)這類觀影幻覺的電影——經(jīng)典形態(tài)的好萊塢電影進行批評。第二種途徑被稱為“虛構(gòu)說”,它拒斥第一個前提。這個路線的理論家斷言,我們對安娜的憐憫并不是真正的憐憫,而是虛構(gòu)出來的、類似于憐憫的東西。我們的情感反應(yīng)本身是虛構(gòu)的,是在與作品互動的虛構(gòu)世界中產(chǎn)生的情感,而不是真實世界中的情感,哪怕它帶有種種真實情感的附隨現(xiàn)象。第三種路徑被稱為“思想說”或“想象說”。它拒斥第二個前提,認為觀眾的情感是真實情感,但這種情感不依賴于觀眾相信情感對象實存的信念,觀眾的想象也可能引起真正的情感。不過這種學說也承認,想象引起的情感與信念引起的情感在重要方面有差異。因此,第二種學說和第三種學說的差異,最終取決于對情感本身是什么的理解。后兩種學說都反對“幻覺說”,否定虛構(gòu)的觀眾陷于真假不分的幻覺或具有錯誤信念。對此我也是贊同的。因為觀眾熟悉我們文化中欣賞虛構(gòu)的慣例,這種慣例也使得作者創(chuàng)作虛構(gòu)的意圖區(qū)別于撒謊。在此,正如哲學家塞爾在《論虛構(gòu)》中分析的,理解虛構(gòu)作品的作者意圖對于正當?shù)挠^眾反應(yīng)極為重要。回到AI背景下,觀眾如何理解一個AI作者的意圖?
孫騫謙黎萌說的問題有許多發(fā)展方向。在藝術(shù)作品總是一個人工產(chǎn)物的情形之下,我們關(guān)注意圖——比如制作者在制作這個作品時,他背后可能涉及一些情感方面的表達或傳達。意圖本身還包括結(jié)構(gòu)的意圖等等。作品的誕生背后總是有制作者意圖的存在,在日常的各種制作甚至活動中,人類意圖成為必要條件。在早期的AI討論中,關(guān)于AI產(chǎn)物是否能存在意圖有一些疑慮,與此相關(guān)的一個經(jīng)典話題即塞爾的“中文屋”思想實驗,其背景是圖靈測試。圖靈的方法是讓一個人分別和人與機器交談,在一定時間后,正常的交流者無法辨別剛剛說話的哪個是機器、哪個是人,便可說這個機器達到了智能標準。塞爾嘗試通過中文屋實驗對圖靈測試進行反駁:假設(shè)一個密閉屋子里有一個人,有一本中文符號操作手冊,設(shè)想屋里的人可以熟練地基于這個手冊進行符號操作。這個有人的屋子就類似于圖靈測試中的機器,甚至可以設(shè)想這個屋子通過了圖靈測試,也就是說在交流時,對方?jīng)]能識別出它是機器而不是人。機器就像中文屋,在里面拿著手冊操作的人使用的那些符號是中文,這個人不過是根據(jù)說明書做一些符號操作,但在外面與之交流的人卻以為這是非常完整的用中文說話交談的過程,就像我們現(xiàn)在的交流過程一樣。塞爾提出疑問:在這樣的情形下,按照我們對智能、對人類心智的基本理解,會認為這個中文屋具有智能嗎?這個面對符號的個體其實并不懂得這里輸入/輸出的符號是什么,并不懂得這種輸入/輸出的反應(yīng)是一種言語反應(yīng)或說話過程。在我看來,中文屋首先針對的是圖靈那個時代及其后小半個世紀對AI的理解,即將智能體的本質(zhì)視為一個符號處理和符號加工過程。如果這樣,我們所謂的處理信息、解決問題,本質(zhì)上就是我們作為一個機器在內(nèi)部會有符號的出現(xiàn),然后這些符號基于算法的轉(zhuǎn)換得到一些問題求解的方式。這樣來想,人就是一個圖靈機式的個體。反過來想,AI就是某種意義上可以匹配于人的智能的機器,它是一個符號操作者,同時它有與人類似的思維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在中文屋的思想實驗中,我們看到的是,如果我們接受塞爾的這種直覺,那么在中文屋這里并沒有真實意義上的智能,有的只是一些完全的符號操作過程和完全的問題求解而已。基于規(guī)則的有效的符號操作,并不構(gòu)成智能的充分條件。相應(yīng)地,圖靈測試也不具備幫助我們測試智能與非智能的充分程序。這其實是認知科學中稱之為“認知主義”或“計算主義”的最早一批對AI的考慮。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到現(xiàn)在,無論是對認知還是對人工智能的理解,已經(jīng)有了革命性的變化。但至少,它提供的框架對于思考AI電影有一些啟示,所以當黎萌提起虛構(gòu)者悖論時,我的第一個反應(yīng)就是中文屋實驗。當我們面對一部AI電影,我們沉浸進去,無論這背后是否有個欺騙者,這背后的意圖是不重要的。但這個前提是作品的誕生總有制作者意圖的存在。如果AI電影的產(chǎn)生并不包含背后某種意圖的支持,制造這部電影的AI就是一個符號處理、符號加工的機器罷了,它所制造的東西是否承載意義?主角的一顰一笑,是否是我們所理解的開心或悲傷的表情?里面的話語是否具有我們所理解的含義?這當中我們看到的是符號加工的產(chǎn)物,作為產(chǎn)品的電影、作品無非是一個巨大機器運作出來的產(chǎn)品。這里如果談?wù)撘饬x,如果意義背后依附于對某些事物的理解以及相關(guān)的意圖的話,那么它是否構(gòu)成一個我們所理解的電影?這是成疑問的。單純的符號、影像的操作和運轉(zhuǎn),如果不承載意義,大概很難成為通常意義上的一個藝術(shù)作品。即便它可能通過某種電影意義上的圖靈測試,例如觀看者可能分不清它是人拍的還是機器自動生成的,可是它承載意義嗎?如果它本質(zhì)上無法承載意義,又能夠叫電影嗎?
陸 丁孫騫謙的討論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方向。通常我們在心靈哲學中處理這個問題時,是承認這里存在困難的,還有繼續(xù)討論的余地。如果我們不是上手就先開始討論藝術(shù)作品這么高度人文化的例子,如果是AlphaGo這樣的例子,你會覺得它是在下圍棋嗎?還是說它僅僅只是在執(zhí)行某種算法?其中有什么關(guān)鍵性差別呢?是因為AlphaGo自己有一個判別棋步的好壞的標準。中文屋中,這個人是在機械地執(zhí)行符號對應(yīng)的規(guī)則和流程,也就是說,他自己是沒有判斷的。但是如果像AlphaGo一樣,屋子里這個人能夠有某種意義上的判斷,可以去判定自己的某一特定執(zhí)行是對還是錯,那么我們在什么意義上說他不懂中文呢?如果取一個比較寬容的態(tài)度,他懂的是一種很奇怪的中文,甚至是另外一種中文,這對于語言來講的確是不太夠用的,因為語言是一個規(guī)則系統(tǒng),你會覺得他懂的不是我們這種中文。如果換成電影,情況就要好得多。所以我們看到,AlphaGo的棋走出來之后,有人說它下得很像是日本國手吳清源,有人說它下的是另外一種圍棋。如果現(xiàn)在的AI算法是帶有判斷和標準的,它在生成特定影像序列的時候,能夠判別不同系列的待選方案的好壞,這時就很難講它不是在拍電影而只是在執(zhí)行一個算法。反過來,如果說這時候它拍的是“另外一種電影”,按照現(xiàn)在的藝術(shù)風氣,這基本上就不能算是一種批評了,而應(yīng)該是一種贊美。這里面的確還是有些問題的,但是,它有一個判別標準,有一個待選方案的甄別標準,那么,在什么意義上能說它是在拍電影而不是在執(zhí)行算法,還可以做更細的討論。這里不能一棍子打死。如果此時AI的算法不是像中文屋例子中設(shè)想的機械執(zhí)行,而是有比如某個語言層次的模塊去進行判別——去給不同的選項賦值,然后判別不同選項的好壞,就不能簡單地說它沒有意圖。它其實可能有意圖,不過這個意圖不用非得像我們正常人或人類作者的意圖一樣:比如從生活環(huán)境中來,有他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之類。原則上并不能說AI一定做不到這一點——這里還得不到這么強的結(jié)論。從這個角度講,直接從中文屋這個路線、從意圖角度來批評AI能不能生成電影,這種理論是不夠強的。
劉 暢從論證上講,我覺得陸丁是有道理的。黎萌和孫騫謙起了一個很好的話題,涉及一個類比。黎萌講的虛構(gòu)者悖論,涉及三個前提和它們導致的悖論。第一個前提是假如我們被某人真正感動,前提是這個人必須真正存在,而且,例如要感到憐憫,這個人必須真的存在并且真受苦了。第二個是我知道安娜這個人物并不真實存在;既然她并不真實存在,也就不存在這個人物真實受苦的過程。因此,我不應(yīng)該感到憐憫。第三,事實上,我讀了安娜的故事之后確實感到憐憫。于是出現(xiàn)了一個悖論。孫騫謙則做了一個類比式的悖論的論證。第一,我們被一個藝術(shù)作品所觸動或感動,前提是我們相信這是一個真實作者抱著真實的意圖,經(jīng)過真實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過程做出的作品。對于這個作品,作為一種理性的回應(yīng),我會感到感動。接下來的問題要做成一個悖論性的形式。我知道某一幅畫、一首詩或一個電影短片是由AI完成的。下一個前提是,AI并非一個真正的作者,它并不具有真實的意圖。但是,假設(shè)我看了這個AI做出的作品,我又受到了感動,或者至少獲得了某種審美的愉悅,這就同樣可以對應(yīng)到一個悖論式的結(jié)構(gòu)。但我覺得這里的問題恰恰在于,安娜作為一個小說人物顯然滿足一個前提,即這個人物并不真實存在。問題在于,假如按照剛才的類比方式制造一個悖論的話,這里就有一個嫌疑。你已經(jīng)預設(shè)了AI不是一個真正的作者,它就并不具有真正的意圖,這么一來就可以類比到剛才引入話題的虛構(gòu)者悖論。但這是可以訴諸直覺的一種論證。你給我看一個短片,我感到拍得挺好,然后你告訴我這個片子其實是AI做的,一般人的反應(yīng)通常是先感到驚訝,隨后會有點受騙上當?shù)母杏X。這種感覺如果構(gòu)成一種直覺的話,分析這種直覺的來源,也許一種解釋是因為我們會先入為主地有這種比較自然的想法,即它不是真正的作者。這種直覺依賴于這種想法。假如AI真正通過某種技術(shù)手段完成了這部短片,它也真正創(chuàng)作了,卻不具有真正的意圖。這里就是一個訴諸直覺的論證。假如像陸丁剛才講的那樣,他一開始就覺得這種直覺是站不住腳的,是因為我們的開始并非從直覺開始,而是從對直覺的反思開始,我們的第一反應(yīng)可能是要不要把這個電影當成電影。這是我們反思的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我們也許可以由此借AI的這種狀況來追問什么是電影,什么不是電影,怎么去界定電影。
趙 斌對于虛構(gòu)者悖論,我從精神分析語言學角度來看。對一個悖論的解決或消除,大家有不同的方法或切入點,每個切入點聯(lián)系著不同的理論領(lǐng)域,它們帶來的可比較性可能取決于哪種理論提供的解決辦法更優(yōu)。我覺得這個悖論以及今天要討論的話題,都與人的自我意識有關(guān)。在“安娜不存在”這個判斷中,作為自然語言來描述大概是沒問題的,但細分起來也許要一分為二。首先她的確不存在,這種不存在是要求本體論承諾的。說她的確不存在是依據(jù)我們現(xiàn)實的感知,或一種本體論的表達,是一種純形式邏輯的東西。從精神分析學角度講,就是一個關(guān)于象征界的知識。而當我們在日常語言中使用時,我也可以說她存在,這是因為自然語言本身包含著矛盾的東西,當我們說她存在,是假定了在一個完整的虛構(gòu)世界當中她存在。這里有一個常識性經(jīng)驗,即我們在談?wù)摯嬖跁r是從一個實用主義的角度講我們感知存在,存在最后被我們說出來,這可能是我們在經(jīng)驗邏輯中理解存在的重要途徑,甚至可能是唯一途徑。所以第一個前提是在經(jīng)驗邏輯和形式之間出現(xiàn)的一種分裂,但有意思的是,我們在不同語境中使用它時,這兩者之間的關(guān)系有點精神分析式的關(guān)系,都是壓抑。我們在邏輯哲學中可能更看重本體論承諾的含義,純粹的形式推演,而在精神分析學中我們往往會從第二個角度,建立一個封閉、虛構(gòu)的場域,我們可以在里面談安娜存在。這本身就是一種語言的分裂。關(guān)于第二個命題,對不存在的人不感到憐憫,我想借助蒯因關(guān)于“飛馬”的爭論,即虛構(gòu)兩個人,用推演的方法。對這個命題的理解可以有兩個角度,一是在純形式的符號意義上討論,我們不能談?wù)撘粋€不存在的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在我們的觀念之中是根本無法言說的話題。另一個是在經(jīng)驗邏輯來講,其實可以談?wù)摬淮嬖诘臇|西。飛馬在現(xiàn)實中不存在,但這個名稱能在我們的想象中喚起某種東西,即插接或雙重圖像,所以我們可以去感知它。“對不存在的人不憐憫”,在我們的常識之中是對的,因為飛馬雖然激起我們的一個圖像或想象,但它不夠鮮活,它召喚的強度不夠。我對不存在的人不感到憐憫,這個問題非常大,就是說能否激起共情,比如憐憫,其實與存不存在沒關(guān)系。唯一有關(guān)的是這個東西有沒有以一種想象的能指的方式在我腦海中激起一個鮮活的世界,強度夠不夠。存在不是我能產(chǎn)生情感投射的一個必要條件,也不是一個充分條件。第三個就是我對安娜感到憐憫。黎萌曾介紹分析哲學中對此的一些有趣的看法,特別是卡羅爾所說的“此憐憫非彼憐憫”,即在虛構(gòu)世界中對人的憐憫和在現(xiàn)實中對真正的人的憐憫不太一樣。但可能有另一種解決方式,如果我們覺得“憐憫”這個概念有問題,就像理論家說的虛構(gòu)與現(xiàn)實之間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鴻溝,我多少覺得這種論證方式是循環(huán)論證。因為首先做了一個本體論上的切分,然后在實在領(lǐng)域或自然領(lǐng)域中遵循這個領(lǐng)域本身的樣子去討論它,肯定會覺得此憐憫非彼憐憫。既然我們尊重日常語言,既然能使用“憐憫”一詞,肯定是提取了各種情境下憐憫的一種共性。當然,在不同情境中,例如在虛構(gòu)背景下和現(xiàn)實生活中,對不同的人的憐憫肯定是有差別的,但我們要提取這種共性。問題出在“安娜·卡列尼娜”這個人名。從形式角度來講,這就是一個具體文藝作品中的人,但深究一步,我其實并未對這部作品中的人產(chǎn)生任何情緒,可能我更愿意說自己是憐憫安娜所代表的某一類人。這也是共情意識或憐憫本身的應(yīng)有之義。每句話背后都有一個純形式的推論和一個基于日常經(jīng)驗的邏輯,二者之間經(jīng)常會打架,這種悖論可能是在某一層面的語義上的,走到最后可能會違反我們的常識邏輯。關(guān)于判斷AI的標準,我更愿意回到一個關(guān)于連續(xù)主體的問題,就是一個完整的形而上意義上的人,具體說來可能與語言工具有關(guān),包括:有沒有自反性的語言使用,有沒有自我意識,是否可以構(gòu)成一個連續(xù)的主體。這可能是未來AI能否出現(xiàn)一個奇點、一個超級AI的大爆發(fā)的判斷標準之一。如果把AI分解成具體的可執(zhí)行的任務(wù),AI大爆發(fā)已經(jīng)是一個事實。所以我更感興趣的還是AI是否會有自我意識。剛才提到的中文屋測試,我覺得這個人不是不懂中文,而是不懂指向現(xiàn)實的、有現(xiàn)實參考的、有意義的語言。這可能跟使用者的主體意識、自我意識有關(guān)。這可能是我們判定AI能否達到奇點的一個重要標準吧。
劉 暢陸丁開頭的開放論證,我是贊同的,但不贊同其結(jié)論。我們當然有很多共識,例如AI作為人的技術(shù)工具,可以在、實際上已經(jīng)在電影中得到很多運用。但如何理解“作者”概念?例如一個拍攝自然風光的攝影師。所有自然題材的景致、景物都不是這個攝影師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因為他取了這個景,把它作為一個作品呈現(xiàn)給我們,我們會認為這個攝影作品的作者并不是大自然,而是攝影師這個人。同樣,讓AI不斷地隨機運行,它可能產(chǎn)生一千首唐詩,如果AI團隊從中挑選出十首詩讓我們?nèi)ゲ履氖自娛茿I寫的,我們有可能猜錯。但問題在于現(xiàn)在的AI自己并不是一個作者。這不是因為它不夠強大,而是因為它是否通過測試這一點是由人來決定的。這就與我們一般講的創(chuàng)作非常不同。對于人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給了我們藝術(shù)品和工業(yè)品的區(qū)分。工業(yè)品就是有一條流水線,我只負責這個環(huán)節(jié),在完成后交給下一個。所有人都在這條流水線上,并不對最后做成什么樣負責。在這個意義上它不是一個藝術(shù)作品。對于藝術(shù)作品,你看了可能不理解,可能不贊同,甚至覺得它不算藝術(shù)作品。但作者是要對這個藝術(shù)作品負責的,由他來判斷這個作品是完成了還是沒有完成。而這樣的能力是我們目前的AI不能具有的。并且,假設(shè)給AI再裝上一個程序,使其不僅能制作這樣一個作品,并且讓它再加上一個對自己的判斷:這是或不是一個作品。像這樣的環(huán)節(jié)在我看來并沒有意義,因為看它做出的是不是一個作品,最后是由人說了算的。這點也和AlphaGo 的例子不太一樣,AlphaGo下棋的規(guī)則非常清晰明確,指向也非常清楚,即圍棋的輸贏,這兩點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都不具有。在規(guī)則性方面,假如規(guī)則完全確定了,我們所說的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造性也就無從談起了。另外,它也明顯不指向一個明確的輸贏。現(xiàn)在我們說AlphaGo當真就是在下圍棋,甚至將之當作一個AI類型的棋手,這些假定都可以接受。但不能因此就類比過來,說AI就能完成一個短片,它現(xiàn)在是作為一個AI類型的電影作者。因為按我們現(xiàn)在對藝術(shù)作品的理解,它們并非是按明確的規(guī)則來鎖定標準,即一旦滿足了這樣一些標準,無論是誰做的,就能算是作者。這樣的標準在我們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是沒有的。進一步講就更為復雜,我們?nèi)ダ斫饣蜩b賞一個藝術(shù)作品時,很多豐富的因素都會影響到藝術(shù)作品的標準和所謂作者的標準。
孫騫謙劉暢的討論剛好可以銜接AI的另一個問題——框架問題。劉暢提出藝術(shù)作品的評價不像下圍棋,有輸或贏的標準。藝術(shù)作品評價的標準、審美價值的維度會很豐富,因時因地而異。這個問題確實足以幫助我們認識到基于規(guī)則或基于特定的輸贏框架和某種意義上缺乏既定規(guī)則的人類實踐的直覺上很有效力的一種標志。這個標志在AI中對應(yīng)的就是我之前和黎萌交流過的框架問題。框架問題的基本想法是什么呢?今晚聊天室里有些朋友也提到,這里涉及的AI主要是通用人工智能。目前學界的說法包括弱人工智能、強人工智能、專用人工智能、通用人工智能等等,通常把強人工智能說成通用人工智能。這里界定的通用人工智能就是在給定一個情境下可以處理一般任務(wù),而不是完成一項有規(guī)則規(guī)定、有相關(guān)參數(shù)在先制定的任務(wù)。這里涉及信息相關(guān)性的問題。在一給定情境下,為了完成某個計劃中的目標,什么信息是相關(guān)的?什么是不相關(guān)的?目前主流手段所構(gòu)造的AI是否能鑒別出來?直到當前,人們?nèi)灾饕直^態(tài)度。哲學家丹尼特用一個生動的故事來呈現(xiàn)這個問題。科學家構(gòu)造了一個機器,這個機器就做一件很簡單的事,就是活下去。這個機器需要能源——電力。遠處房間里放著蓄電池,機器人需要把那個蓄電池取出來換上。蓄電池放在一個小推車上,小推車壓在一個定時炸彈的啟動裝置上。一旦小推車輪子離開,炸彈就會爆炸。并且,如果一直壓著這個啟動裝置,一段時間后定時炸彈也會炸掉。科學家連續(xù)造出三個機器人,生存任務(wù)一直失敗。第三個機器人可以推導出怎樣行動可以達成目標,也能推導出這樣的行動可能的副作用,并且還能判定這些后果與其生存目標的相關(guān)性,如此強大的AI,卻連一個只要神志正常的人就能輕松判斷的事都無法完成。這里暴露的就是相關(guān)性問題。人面對一個復雜場景,要完成一個任務(wù),有很多因素,我們能夠在第一時間內(nèi)做出有效的行為選擇。這個選擇不一定是好的,但至少是有理性下限的。如果說下棋的輸贏判斷很簡單,那么,對藝術(shù)作品價值的判斷卻是非常復雜的。這種復雜性不必神秘化,它就是缺乏劉暢所說的某種既定標準或條件,即可以在參數(shù)輸入或一開始設(shè)計時能夠約束它的條件。如果說這時的AI有一個生產(chǎn)或制造出一個藝術(shù)作品的好的意圖,它能生產(chǎn)出一個我們覺得好的藝術(shù)作品嗎?藝術(shù)作品的質(zhì)量判斷的復雜性以及依賴性,使得生產(chǎn)出一個好作品就像機器人能夠安然無恙地從有炸彈的環(huán)境中把蓄電池取出來一樣,并且機器人導演或編劇所面對的情況比取電池的那個機器人復雜得多。假設(shè)我們對AI電影做一個界定,說AI電影是由AI編劇和導演創(chuàng)作出的電影,而不是AI僅僅作為剪輯、場景生成等等輔助手段,當然,作為手段涉及的是所謂“認知增強”的另一個話題,即讓我們的電影制作者具有更強大的能力和工具。我們所謂的AI電影不是這種情形,而是由AI編劇、導演等等創(chuàng)作出來的一個產(chǎn)品。即便它有一個做出好電影的意圖,它真能生產(chǎn)出好電影嗎?即便它做出的產(chǎn)品得到了我們認可,恐怕也只是歪打正著的巧合。在這個意義上說,利用框架問題能進一步挑戰(zhàn)的是,AI電影作為一個有價值的產(chǎn)品,這件事可能存在嗎?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三、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我們?nèi)绾握務(wù)撐磥恚?/h2>
黎 萌在談“可能不可能”的問題時,大家聊到了各個層面,除了科學技術(shù)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從何謂作者、何謂創(chuàng)造性、意圖、理解等問題來探討AI電影和一般意義上的AI藝術(shù)。下面要談“該不該”的問題。應(yīng)不應(yīng)該無限制地推進機器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假設(shè)機器具有超過人的認知能力和藝術(shù)“創(chuàng)造”能力,是否應(yīng)該說機器的藝術(shù)創(chuàng)造比人的更有價值?是否應(yīng)該讓它取代人的創(chuàng)造,就像今天可以用機器代替我們進行工業(yè)生產(chǎn)一樣?這些問題的一個背景是目前聲勢浩大的“后人類主義”思潮。后人類主義恰恰對這類問題有明確回答:不僅能夠,而且應(yīng)該。“超人類主義”最早的含義只是設(shè)想人對自身的超越,這個含義在后來發(fā)生了重要變化,主要指通過技術(shù)手段改善/增強人類,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人工智能。在《變種異煞》等科幻片中可以看到對未來社會的這種人類優(yōu)生學想象。在“超人類”的基礎(chǔ)上,一些理論家進一步提出了“后人類”概念。目前的超人類主義和后人類主義不僅是在做一種科幻式的文學或藝術(shù)想象,而是嚴肅地提出這就是人類未來的發(fā)展方向——不僅技術(shù)上是可能的,并且是應(yīng)該的。目前超/后人類主義的共同目標主要是突破人類局限,特別是延長壽命和增強主義。這類目標的可行性論證主要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是技術(shù)上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是倫理的可行性。技術(shù)的可行性論證主要包括奇點理論、思維上傳、基因工程與各種增強技術(shù)的發(fā)展。假設(shè)我們從技術(shù)上能這么做,這對于人類未來的生活究竟好還是不好呢?后人類主義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也提出了倫理方面的理由,主要涉及:滑坡論證;基于后現(xiàn)代主義多元化立場對人類中心地位的反對,例如《賽博格宣言》;“增強主義”是有絕對價值的理想,能帶來人類未來的進步和福祉。這類觀念的擁躉眾多,但也不乏質(zhì)疑和批評。比較有代表性的批評主要來自政治學領(lǐng)域,例如福山提出了一種基于后果論的批評,認為這種通過生物技術(shù)來實現(xiàn)的增強/進步會剝奪人類的價值。桑德爾對這種增強主義的動機提出批評,認為它表達或促進的態(tài)度是錯誤的、不道德的。我們?nèi)绾卫斫狻霸摬辉摗钡膯栴}?我的一個直覺是,對于用AI來替代我們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這件事,例如拍電影,我不會覺得毫無問題,不像用它來替代我完成工業(yè)品的生產(chǎn)那樣容易接受。聯(lián)系到前面的意圖問題,我們通常覺得藝術(shù)品的創(chuàng)造背后有作者的情感表達等。對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而言,我可能是個平庸的作者,但我有強烈的表達愿望。即便AI有遠遠超出我的藝術(shù)才能,我也不認為它真的可以或者應(yīng)該代替我創(chuàng)作。我的創(chuàng)作有內(nèi)在的目的,不完全能根據(jù)創(chuàng)造的結(jié)果來衡量。
陸 丁黎萌的視角轉(zhuǎn)移到了創(chuàng)作者立場,即:AI即使能生成電影,也不能取代人能創(chuàng)作的電影。這個我覺得沒有問題。但這與AI電影“應(yīng)不應(yīng)該”有區(qū)別。不是所有人都是創(chuàng)作者,特別是電影。我看了一個好電影,不會想到自己要去拍。所以這個論點雖成立,但不能用來論證AI電影應(yīng)不應(yīng)該。這和前面孫騫謙說到電影價值或藝術(shù)品價值有關(guān),似乎我們讀者在接受一個作品時,有一個維度涉及我們和作者之間的關(guān)系。讀小說時,我在某種意義上與作者達成某種關(guān)系。剛才聊天室有人說“安娜是虛構(gòu)的,但托爾斯泰是真的”,確實如此。這樣的影響是,面對AI做出的東西,我無法跟機器達成這樣的關(guān)系。這就很像和中文屋例子很相似的黑白屋思想實驗。一個人在一間純黑白的屋子里面學習顏色概念,等他走出屋子后看到真正的紅色,是否增加了知識?類似地,如果一個編劇從生下來就待在一個屋子里,那里只有各種小說、戲劇、小說理論和戲劇理論,他能寫出一個好劇本嗎?我的意見是他可以。我們可以想象一個人生下來屋子里就只有圍棋,他可以學會下圍棋。可能對劇本屋子的疑慮度會增加,但我覺得可以接受。那個人一定不能成為文化意義上的領(lǐng)導者,像托爾斯泰或魯迅這樣的人,但我們對作者的要求似乎不需要這樣,假設(shè)他是普魯斯特那樣的作者,或假設(shè)他完全生活在純文字的想象中,也是可能的。電影反而會加強這個例子,他可以在屋子里看電影。如果一個人生來從來沒出過屋子,他就在屋子里看電影,看紀錄片或動畫片、廣告,所有的影像,他拍的電影一定不是好電影嗎?如果排序的話,最不可疑的是圍棋,其次不可疑的是電影,再往后才是小說。這是因為影像的力量,它是模擬的,和文字不大一樣,那么他在某種意義上模仿或改造其影像記憶的時候創(chuàng)造出有價值的東西,是完全可信的。如果這個直覺可以接受,那么AI和這個人沒有太大差別。這是一種理想化狀態(tài)的AI,但沒什么原則問題阻止我們認為AI能夠做到。孫騫謙剛才提到計算框架,即現(xiàn)在我們做AI幾乎沒考慮到常識的問題,就像他所說的正常的成年人之類,要包括能識別出這是一個定時炸彈。但如果它是個手雷呢?如果這個人恰好沒有關(guān)于武器的知識呢?這里的問題不在于計算框架,而在于缺少一個知識庫,這個知識庫在原則上并不很難。把這個知識庫補上之后,這個AI就至少能像人一樣去做判斷了。
趙 斌關(guān)于電影的純粹實驗性寫作,以上從完全假定的邏輯上講是可行的。但回到普魯斯特的極端例子,我們判斷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一種真正意義上智能的行為,通常與兩個條件有關(guān)。普魯斯特至少有一個藝術(shù)視野、批評視野,會有一種自反性判斷,這是純意識的方面。另一個條件與行動有關(guān),例如電影《她》當中,那種不太適于用文字書寫方式寫信的人,最后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寫出有文學色彩的信,匯成書出版。從電影作為純視聽媒介來說,可能AI去仿造它更為容易,但還必須考慮現(xiàn)實因素,如工業(yè)的因素等等。如果僅僅考慮影像,制作的問題就純粹變成影像加工。這不是理論上行不行的問題,會有許多廣義的因素,時間、政治、經(jīng)濟、工業(yè)等等。用AI做電影,我們需要輸入素材,然后輸出。如果這個過程在耗費勞動力方面比直接拿著DV去拍攝和剪輯還高,在理論上的可能性就會大打折扣。前些年討論CGI的問題時,大家也有這種浪漫的未來主義的希望,但最后發(fā)現(xiàn)我們可能在一些特殊的段落當中才需要這樣的東西。現(xiàn)在雖然有人機互動,但完整地由機器人創(chuàng)作一部電影的可能性還不大。在這個過程中電影的形態(tài)可能也會改變。這種方式可能是超越既定歷史框架的,可能又是一種突破規(guī)則。活人的創(chuàng)作力也在成幾何級數(shù)地往前發(fā)展,還需要考慮行動力的問題。現(xiàn)在大眾文化中普遍有一種危機感,包括AI可能取代藝術(shù)家等,其實更嚴重的問題是對人的生命安全的威脅。AI除了要有自我意識之外,還得有充分的行動力,這是和技術(shù)可能性相關(guān)的。簡言之,素材方面,AI需要輸入,例如感知、掃描等多樣化方式,然后是內(nèi)部軟件運行、計算問題,再有就是輸出,怎樣更好地付諸行動。很多電影中把自我意識的出現(xiàn)和充分的行動力跳過去了。同時也應(yīng)該考慮到人的智能是一種群體性的屬性,與實踐、對話都有關(guān)系。
劉 暢現(xiàn)在出現(xiàn)了一個有意思的局面。黎萌合乎邏輯地提出先后討論“能不能”和“該不該”,“該不該”的前提是“能不能”。在后一個問題上,我們有了分歧。我比較悲觀,認為大概不會有以AI作為作者的電影;陸丁認為我們應(yīng)該心態(tài)開放,因為AI未必不可能成為作者,所以他同樣對“該不該”的問題持開放態(tài)度。如果說首先就不可能,又如何去討論“該不該”的問題呢?我覺得黎萌是轉(zhuǎn)換了一個角度去理解。我們先是把廣義上的AI視為一個機器,它不是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主體,我們說它不可能是作者。現(xiàn)在轉(zhuǎn)換一個角度,不是讓AI向人靠攏,而是讓人向AI靠攏。這就是超人類或后人類,即我們主動把自己機器化。這當然也涉及滑坡論證:一個人的胳膊變成機器,心臟變成機器,最后我的大腦芯片化了,整個成了一個硅基的存在物。我到底是人還是機器,已經(jīng)說不清楚了。這就把我們原本設(shè)定的在人與機器之間的溝壑給填平了。這樣我們首先要問:人應(yīng)不應(yīng)該機器化?再一個與之相連的問題:該不該有這一意義上的機器/人作為作者的電影?趙斌剛才從專家的角度,特別是從電影門類的特殊性講到了技術(shù)上有沒有可能,以及“該不該”。當然首先還是“能不能”,如果技術(shù)上完全達不到,我們就不必為“該不該”憂心忡忡。而我想換個角度。無論是現(xiàn)在意義上的AI還是后人類或機器/人,我們要不要把它當作人,或在更嚴謹?shù)囊饬x上把它當作一個主體?我特別贊同趙斌最后說的那一點,即人類群體或主體間性對人、對主體性的建構(gòu)性作用。主體性實際上是基于主體間性的一個概念。舉例說,奴隸完全滿足人的生物學標準,但卻被當作會說話的牛馬,他并不因為某方面的能力特別強就能獲得人的地位,被其他主體當作一個主體來對待。所以我覺得生物學標準不算一個標準,不管是硅基的還是碳基的,不管具體實現(xiàn)你的能力的生物學基礎(chǔ)是什么,我們所理解的主體都不能還原到這上面來理解。到底怎么理解主體以及藝術(shù)作品的作者?我給出一個特別“搗漿糊”的結(jié)論:誰是不是人,取決于他是不是被當作人,是不是被其他人當作我們這個文化共同體中的一員看待。所以趙斌說得挺好,就像《她》這個電影所說的,究竟這個AI程序是如何在技術(shù)上實現(xiàn)的,并非我們所關(guān)心的問題,最后男主人公與她戀愛,他愛的是一個人,這個被愛的人是被當作一個主體來看待的。這取決于什么,不是今天的我們所能判斷的,而是取決于未來的人怎么看待超人類、后人類。這不由我們決定,也不由那個物質(zhì)基礎(chǔ)決定,而是由未來決定,未來的人與人之間、主體與主體之間會形成什么樣的關(guān)系,會不會把一種在物質(zhì)基礎(chǔ)上異于自己的東西也當作我們的一員,這是判斷AI是否被當作主體的標準。反過來,會有一個可能冒險的推論,即它在生物學上已經(jīng)與我們非常不同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開放的結(jié)局,未來那個混合著今天意義上的AI和人的那個東西,會不會被當成主體,并從而被當作一部作品或一部電影的作者,也許要按照未來的人的“生活形式”(維特根斯坦語)來決定。我沒有確定結(jié)論,并且覺得今天的我們也很難得出一個確定結(jié)論。
陸 丁我覺得AI在原則上可以拍電影。其實我相當期待AI拍出來的電影。徐冰的《蜻蜓之眼》把許多監(jiān)控錄像剪在一起。如果是AI來做,它也許在某種意義上會做得更好,當然前提是這個AI如AlphaGo,知道怎么下贏一盤棋。設(shè)想工程師設(shè)計這個AI是為了做一個社會調(diào)查,如果它要提交一個影像報告,它未必做不出一個有意義的影像作品來。當你看到這個作品時,即使你知道這是一個AI的作品,你與專業(yè)棋手看見AlphaGo的棋一樣會有敬畏的感覺。它能做到你做不到的事情,提供一個你也許無法發(fā)現(xiàn)的角度,或沒有辦法發(fā)掘的事實。這樣有什么不好呢?這甚至不需要你認為它是一個人,只需要認為它能提供的東西對你來說有意義就行了。我不知道我的立場算不算后人類,就像黎萌剛才所說的,在人類的界限中還是可以有一種增強主義,但不必走到賽博格的路線上去。在這種進步主義態(tài)度中,AI和AI作品可以成為其中一個非常有機的部分。對于人類界限,我個人的理解就是肉體上的界限,在精神上可能是沒有什么邊界可言的。如果完全退回到我必須得是個人、必須得回到當下的標準或者好壞的理解所允許的作品才是好作品,那么我不能同意這樣的態(tài)度。總是會有我現(xiàn)在沒有想到或沒有留意到的那種“好”。
劉 暢我的結(jié)論也是一種開放的看法。差別在于,我認為既然能拍出電影的AI還沒有出現(xiàn),就應(yīng)該留待未來的人去回答是否接受把AI當作作者。各種工具幫助人類去完成人自己不能完成的一些事情,比如用氣壓計測氣壓,用溫度計量溫度,這些工具在某些方面的能力顯然都超出了人,更不用說還有其他各種自然物種,比如我們沒有狼的爪牙之利。但是,不會因為在某些方面一些非人類的存在者的某些能力超出人類,就構(gòu)成它已經(jīng)是人或人需要向它學習。但這還不是我們要談的作者標準或主體標準的問題。它能力很強,可以幫助我們,我們可以向它學習,這些都不是問題。關(guān)鍵是我們要不要把它理解成一個主體。
孫騫謙從剛才劉暢的說法中提煉出一個命題:由于主體性在這個角度下源于主體間性,那么未來的AI是否能具有人的地位,尤其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地位,有賴于在那個時候構(gòu)成人類共同體的成員。我反對這一點。大家都很熟悉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在自我意識階段,兩個個體相遇,誰首先放棄他的生命原則,他就能取得主人的地位。但主奴關(guān)系并不能為主人賦予充分意義上的主體地位。主人就是主人發(fā)布的命令,主人的意志是奴隸要無條件貫徹、無條件地視為自身意志的意志。主人意志的根據(jù)是什么?在這樣的背景下,或者是主人能提供根據(jù)為他當下的意志辯護,那么這是無窮倒退,因為根據(jù)的根據(jù)還需要進一步的根據(jù);或者是,到了某個點為止,主人的意志就是意志本身,主人的意志就實現(xiàn)了自我辯護。一種意志的自我辯護是一種任意性,主奴關(guān)系中主人的意志和命令并沒有得到進一步的辯護,而是成為一種任意的東西。主人并未獲得一種基于自身或自身建立的主體性或自主性。奴隸反抗主人,最后達成的局面是平等的理性主體之間的互相承認。在這樣的理性主體相互承認的境況下,才會有充分意義上的主體性。在這種平等的理性主體相互承認的溝通之中,才會有法權(quán)意義上的真實主體存在。回到現(xiàn)在的問題,這種社會意義顯然不夠了,除此之外還需要認知意義。一個狼孩至少有一個在認知意義上成為理性主體的潛能。如果你不承認一個AI是人,不承認它具有與你對等的主體性地位,那么你這個已經(jīng)獲得既有主體性地位的人類,其實在面對AI時是在扮演主人的角色。這就回到黑格爾辯證法的第二點,主奴關(guān)系下主人是一個主體嗎?恐怕談不上。恰恰是,只要有了人類的基本認知構(gòu)造和認知能力的個體,這就成為這個個體是否能獲得人類共同體所承認的主體性的試金石了。從這個意義上,你們之間形成平等主體之間的相互承認,你否認它,當自己是主人,當它是奴隸,當它是你的意志的一個貫徹工具,那么你的主體性也被取消了。我不同意劉暢的另一點是,需要有承認資格的人類來認可AI算是人,而是反過來,如果我們?nèi)祟惒徽J可它們是人,人類也就不成其為人。此外,關(guān)于“該不該”的問題,還是在于真正的強AI是否能夠?qū)崿F(xiàn)。在這一點上很難講,人機接口也好,人機交互也好,我不確定這些說法所說的強度是否能達到物種演化意義上把人換了一個物種。但至少在功能上,如果說我們這個物種具有認知,這個認知至少具有模塊性,是一個積累的產(chǎn)物。兩個物種具有的認知是不同的、有差異的。在認知狀況的一個階段看,認知增強能不能達到將人更新了一個物種的程度,是不清楚的。我的基本想法是,不論是技術(shù)演化還是物種演化的迭代過程,都是一種試錯,即具有實驗性,本身是高度偶然性的產(chǎn)物。如果讓我來說技術(shù)迭代、技術(shù)演化的軌跡和方向,我不能預測。在不同的處境下有不同的倫理問題。如果真出現(xiàn)超人類或后人類,他們面臨的倫理問題會是什么?我只能說不知道,因為我無法預測它們本身,也就無法預測在那樣的社會下倫理會呈現(xiàn)怎樣的面貌。
趙 斌討論后人類處境有其哲學上的脈絡(luò)。歐陸哲學的幾大派系都在清點黑格爾之后的關(guān)于主體性的話題。還是要區(qū)分一般意義上的人和主體。比如主奴問題,給小白鼠電擊,小白鼠會覺得自己是被奴役的,它明顯知道有一個與自我意識相對立的他者。我們講思維上傳,比如有一個平行大腦,或者我把我等同于小白鼠,小白鼠認為一個東西在一端操縱著我,或者小白鼠感到這不是我在動而是電流在刺激我,它有一個清晰的自我意識的話,這個過程是非常單純的。更復雜的是,如果小白鼠誤認為這種外來的力量是本源的自我意志,即一個把外在力量內(nèi)化的過程。當然這個過程中會有些剩余,拉康和馬克思都對此有所反思。但從一個理論模型來講,它構(gòu)成了一直以來都有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這些與電影關(guān)系非常密切,例如拉康的“鏡像”,阿爾都塞的“機器”。我們?nèi)绻裥“资笠粯幽弥謾C藍牙,頭上插著電纜,電纜連接一個受控于他人的裝置,這個系統(tǒng)就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象征機器。這是人的一個過往處境。至于未來怎么判斷,我非常贊同剛才幾位老師的話。人文科學或藝術(shù)和哲學,這些浪漫的、詩意的或超越性的精神力量,或藝術(shù)中最高級的東西,其實都與肉身的有限性有關(guān),它回溯地塑造著我們的一些邊界。因此我對這個問題的探討一方面是不太清楚,另一方面是不斷用大家提醒的東西去反省自己過去的所知。
劉 暢后人類、后電影及AI都涉及一個基本問題:我們怎么談?wù)撐磥怼rq謙也談到,從兩方面來說我們談?wù)撐磥矶疾豢赡堋R环矫妫@然不能設(shè)想我們今天就能決定未來,好像我們能預測未來就是這樣而去談?wù)撍偃缥磥砭褪沁@樣,談?wù)撐磥砭蜎]有意義。另一方面,就因為這樣,我們不能假裝自己是已經(jīng)跳到未來回過頭來看今天的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談?wù)摰闹皇墙駮r今地能談?wù)摰模磥戆l(fā)生什么,我們只能等等看。這涉及一個問題:我們既然沒有等到未來,又要談?wù)撍敲茨軌蜃屛覀冋務(wù)摰拇_定性基礎(chǔ)是什么?無論鼓吹超人類、后人類,還是福山、桑德爾等的比較保守的看法,他們所基于的基礎(chǔ)都有點本質(zhì)主義。鼓吹后人類的人似乎默認增強主義是未來的方向,因此我們就要發(fā)展,既是應(yīng)當也是能夠的。福山和桑德爾假定了一種本質(zhì)意義上的所謂人性。我不愿意如此看待這個問題。剛才孫騫謙講的演化很有啟發(fā),但我覺得用生物演化來類比社會的演化,基本上是不成的,不能跳躍太大。孫騫謙所說的路徑依賴,要是類比到社會演化或者變化,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每一個變化不僅從它自己的變化脈絡(luò)來講是路徑依賴的,關(guān)鍵在于,在人這里格外突出的是,你可以說它是“演化依賴”。多少年以前無論有過什么預測、感慨,完全不能代替以后出生的人的心智、他對世界的體驗方式、他的意義觀。關(guān)于什么是本質(zhì)的人性,最好不要預先為未來的人去做判定。涉及“后人類”之類話題,既不要預先說我們要發(fā)展的方向就是要增強,也不要說守著固定的人類本性。這兩者我都不贊同。特別是涉及藝術(shù),首先要談就是最真切的感受是什么,那就更沒有必要預設(shè)人性的本質(zhì)或者歷史的本質(zhì)。我認為涉及AI還有一個問題——“會不會”。有必要把“能不能”和“會不會”的關(guān)系,以及“該不該”和“會不會”的關(guān)系區(qū)分開。回看技術(shù)對人類的影響,包括正在發(fā)生的各種影響,經(jīng)常地我們看到技術(shù)對我們的影響是:我們?yōu)槭裁磿l(fā)展成這樣,生活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就只是因為技術(shù)提供了這種可能。就因為我們“能”,所以我們就“會”,所以也就這么做了,這中間沒有“該不該”。基于我們現(xiàn)有的理解,我們能夠正當?shù)鼗卮鸬膯栴}恰恰是“該不該”,而不能夠正當?shù)鼗卮稹皶粫薄A⒆阌诂F(xiàn)有的理解,我們可能不知道未來注定會怎樣發(fā)展,但基于我們對心智和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可以判斷它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AI制造出來的東西,它本就“應(yīng)該”是平庸的。它不是跟“能不能”相關(guān),而是跟“該不該”相關(guān)。什么意思呢?黎萌提到了這個問題,指給我看一幅畫,不說是人畫的或是AI畫的。當然,在你告訴我這個答案之后呢,我的感受會發(fā)生變化,這是很自然的。我們談創(chuàng)造,當然就涉及能力的問題。這種能力歸根結(jié)底要有一個基本的要求,即要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一個既定的框架。AlphaGo走出了任何人完全意外的一步,不可理解的一步,但是它走了制勝的一步。它在局部意義上突破了我們的理解,突破了我們的期待,我們?nèi)匀徽f它有創(chuàng)造性,它不是隨機的或誤打誤撞的一步。但在電影或廣義的藝術(shù)的背景下,因為沒有一個最終輸贏作為評判標準,就得落實到我們的感受上。假如杜尚完全超出我們的理解,我們卻依然將之視為藝術(shù),是因為我們不是把杜尚當做機器編好的程序出問題了,我們準備好了將之理解為一種藝術(shù)。AI能夠把一些東西挑選出來,讓藝術(shù)家覺得有創(chuàng)造性,但我覺得使之成其為有創(chuàng)造性的,仍是將之挑選出來的藝術(shù)家。在這個意義上講,我仍然不覺得AI會獨立地具有創(chuàng)造性。我認為,AI恰恰為我們理解今天什么是電影、什么是藝術(shù),提供了一個維度或一個契機。我們向來都談?wù)撌裁词呛秒娪埃F(xiàn)在因為有AI,有未來的手段,就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但實際效果仍是今天的我們?nèi)绾稳ミM一步反思今天的電影,今天的我們?nèi)绾卫斫饨裉斓碾娪啊?/p>
黎 萌我們只能在反思的意義上討論這個問題,而不是猜測,這一點我完全贊成劉暢,說得非常好。也非常感謝今天各位的思考和深入討論,我自己得到了非常多的收獲。感謝《文藝研究》雜志及其藝術(shù)哲學與藝術(shù)史研究中心給我們提供了這次可貴的交流機會。也非常感謝在線上聆聽和參與討論的朋友們,特別是許多在聊天室里踴躍提問和發(fā)言的朋友,實際上我們今天在兩條線上展開了熱烈的交流,讓我感到了大家對這個問題的興趣和活躍的思考。希望今后有更多機會進一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