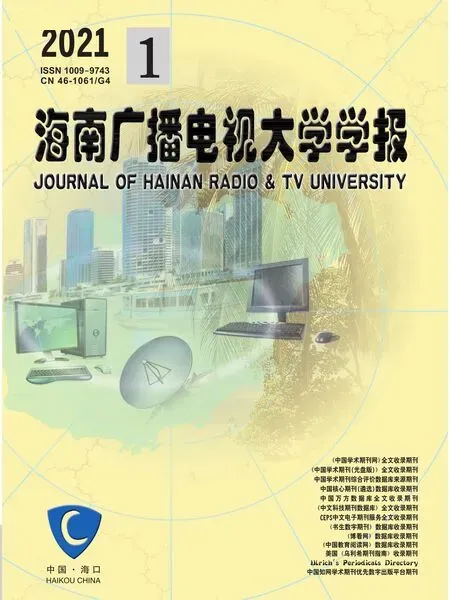人類學視閾下川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
胡 帥,韓夢姣
(四川文理學院 體育學院,四川 達州 635000)
一、引 言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民族文化瑰寶,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1]。川東地區地處川內外交流互通的重要節點,高山大川的自然環境和獨特的人文風情共同在此塑造了厚重的傳統文化沉積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川東體育非遺正在邂逅一個傳承與發展的新機遇。以文化人類學相關理論為導引,從宏觀上對川東地區體育非遺的演變、傳承主體、文化功能進行解讀,從微觀上重現其在組織功能、經濟結構、現代文化、生活方式、人口結構等方面流變,試圖避免前人研究對文化政策解讀的拘囿,從整體觀出發正確把握體育非遺的發展方向。
二、人類學視角下川東體育非遺傳承的宏觀邏輯
(一)文化變遷的視角——川東體育非遺演變的過程邏輯
川東體育非遺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在具有相對穩定性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發生著變遷。文化的流變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時代背景的變遷,張繼焦將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6次文化轉型歸納為:文化自滿、文化自卑、文化自省、文化自立、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2],這一過程也基本符合當地體育非遺的演變規律:川東傳統體育發軔于商周時期,高山大川的阻隔使當地孕育出的傳統體育文化具有鮮明地域性與民族性特點,如在“武王伐紂”中“前歌后舞”的巴渝舞,即是當今眾多體育非遺舞蹈項目的原型;在奴隸社會后期至封建社會的漫長時期內,部分項目在歷史的長河之中徹底消亡,但陸續又有眾多新興項目補充進來,如明清時期的余門拳、“湖廣填川”時期的譚氏子孫龍等;鴉片戰爭以來,包括川東傳統體育在內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在列強的堅船利炮之下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民眾被籠罩在強烈的文化自卑氛圍中;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沖突愈發激烈,引發了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自省,費孝通先生提出了著名的“文化自覺”理論,呼吁大眾重新重視自身文化,政府、精英與民眾也開始重新審視在“文革”時期被批為“四舊”的川東傳統體育;當今,世界各國民粹主義抬頭、貿易保護主義的復辟促使社會各階層從傳統文化中尋找中華文化的未來,增強文化自信成為川東地區美麗鄉村精神文明建設中的重要內容,部分延續至今的傳統體育項目被申報為省級、市級體育非遺,傳統體育的復興成為當地文化發展的新常態。
(二)主位與客位視角:川東體育非遺傳承的主體與社會話語
所謂“主位”與“客位”,即是以“自我”與“他者”身份探討體育非遺傳承的兩種視角。在川東體育非遺的現實傳承中,“主位”與“客位”的社會話語權分配是不均衡的——作為“他者”,政府和企業可以在保護和利用體育非遺的過程中占據主動,學者亦可以從主觀出發對體育非遺的相關現象“下定義”,而作為“自我”的傳承人與族群成員,并沒有在體育非遺傳承過程中獲得足夠的社會話語,從而導致川東多個地區體育非遺項目由于過度的外力干預產生了“異化”現象。這種話語權分配格局的形成,一方面由于出于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和文化研究等現實驅使的“他者”,相比較于孕育出體育非遺的川東鄉村中的“自我”,擁有更多權力與資源,從而可以掌握更多社會話語;另一方面,青年一代族群成員對自身民族文化的漠視,以及在認識層面文化自覺的不足、意識層面的文化迷失、實踐層面文化自信的缺乏,也是形成話語體系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三)文化功能視角:川東體育非遺的多重功能
文化功能主義學派認為“觀察一個民族的文化生活,要把它視為一個功能的統一體[3]”,這正是文化人類學“整體觀”的寫照,也與黑格爾的“存在即合理”理論不謀而合。川東地區體育非遺并非被束之高閣的文化標本,而是深植于民族內心的“身體記憶”。以石橋火龍為例,當地人在正月十一到十五期間定期舉行,這一展演項目吸引了央視等眾多媒體報道,無形之中提升了川東民眾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元九登高”起初是為紀念詩人元稹而自發形成的,后來演變為以民眾切身參與、親身實踐為主的大眾健身活動,對民眾全民健身觀念的形成具有積極意義。整體來看,川東體育非遺項目因其輻射地域、項目特點而具有娛樂身心、增強體質、提升民族認同等多重功能。正是由于兼具符號性與實用性雙重特色,川東體育非遺能夠聯系本地經濟與文化發展實際,實現其改革和創新的發展訴求。
三、人類學視閾下對川東體育非遺傳承阻礙的微觀剖析
(一)體育非遺與組織功能:體育非物質文化相關組織功能消失
在相當長歷史時期中,“家族”是川東地區文化生活組織的基本單位,血緣親疏是其組織內核,經濟聯結是其組織基礎,文化一致是其組織的外顯。體育非遺作為家族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將較為松散的個體凝聚成具有共同價值觀念、行為習慣的統一體,其組織功能主要表現為通過節慶活動、祭祀活動、農事和戰爭等活動中的文化實踐規訓家族成員日常行為,實現社會組織的有效管理與協調一致。部分非遺項目中道具制作與儀式展演人員僅限家族內部成員,傳承人的遴選也多限于家族內部,這雖使文化輻射范圍受到限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體育非遺在家族內部組織功能的發揮。伴隨川東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傳統家族式的社會組織形式早已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則是以小家庭為基本組織單位的新的社會構成形式,體育非遺也逐漸突破了家族壁壘,而成為社會大眾所共有的文化遺產,組織主體由各家族族長讓位于政府和社會力量,這勢必帶來體育非遺在傳統家族中組織功能的淡化,導致個體與家族聯結的離散。
(二)體育非遺與經濟結構:支撐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運作的傳統經濟結構斷裂
體育非遺項目的開展需要相關經濟支撐[4],川東體育非遺項目的正常運作與其背后的經濟結構密切相關。自其形成伊始至“文化大革命”,家族在體育非遺的正常運作中扮演著核心角色,傳統體育的啟動資金多來源于家族共同收入以及成員的“份錢”,其運作架構在家族經濟結構之上;經歷“文革”十年浩劫,諸多傳統體育項目因被視作“迷信”“四舊”而發展停滯,傳統的家族經濟也遭到重大破壞,這從根本上動搖了體育非遺在農村的發展根基;改革開放以來,川東社會結構由家族向家庭的轉向愈發明顯,農村地區農業生產實行“大包干”,切斷了個體與家族之間經濟紐帶,支撐體育非遺運作的傳統資金鏈條也由此發生了斷裂[5];而現階段,川東體育非遺“造血”功能發展尚不均衡,部分項目運作資金僅依靠政府經費資助和非遺項目補助,缺乏長期性和穩定性,仍未形成依靠自身營利、輔以政府補助、動員各路資金的理想化資金支撐結構。
(三)體育非遺與現代文化:現代文化的交流傳播導致了傳統文化結構變遷
從商周至秦漢,川東地區地處大國勢力夾縫地帶,兼并戰爭時常發生,至元末明初和元末清初,戰亂導致的人口銳減促使當地官府實行“湖廣填川”的人口遷移政策,社會動蕩與人口遷移雖加劇了地域文化碰撞與融合,但并未從根本上動搖川東傳統體育文化的框架結構,反而磨礪出當地民眾熱情、尚武、堅韌的文化內核,展現了傳統文化所具有的韌性與張力。漫長的集權統治雖賦予川東社會巨大的文化慣性,但在現代文化巨大的外力沖擊下,傳統文化在結構層面正在發生速度驚人的滑移。現代文化對傳統文化結構的沖擊體現在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和意識文化多個層面:崇尚競技與競爭的西方體育文化滲透,正在蠶食川東體育非遺的發展空間,動搖了其展演與傳習的固有制度;計算機、智能終端和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川東青年一代文化交互方式,塑造著有別于傳統體育的文化行為;現代文化裹挾著五花八門元素,不斷刺激著民眾的視覺神經,使其對自身文化興趣與傳承意識日趨淡薄。
(四)體育非遺與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變遷加速了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與當代社會脫離
如果說組織功能、經濟結構的變遷是從根本上改變了體育非遺面貌的直接因素,那么生活方式的改變則是川東體育非遺與當代社會脫離的間接因素。當代川東民眾的生活方式正在經歷著由傳統向現代、由趨同向個性、由單一向多元的演變過程。生活方式的變遷對川東體育非遺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川東體育非遺項目本身的展演形式與基本套路相對固定,導致文化供給的單一化與民眾需求多元化之間的對立,即表現出一定文化滯后性;其次,伴隨著生產力發展與生產效率提高,川東民眾的娛樂休閑時間分布更為廣泛,并體現出碎片化特點。諸如石橋火龍、元九登高、游百病等節慶類型的非遺項目多在固定日期舉辦,而在重大節日之間的休閑娛樂空檔期,其他類型的非遺項目沒有及時補充進來,導致現有體育非遺活動舉行中周期性明顯的尷尬局面,體育非遺“存在感”的下降必然加速其與當地社會的脫離。
(五)體育非遺與人口結構:勞動人口的遷徙導致了體育非物質文化沒落
伴隨城鎮化快速推進,作為經濟基本要素之一的勞動力開始在區域間自由流動,整體展現出由農村向城市、由西部向東部遷徙態勢。成都、重慶等周邊強二線城市對川東地區青年勞動人口的虹吸作用極其顯著,而根植于農村、興盛于農村的體育非遺也隨著人口外流開始出現加速沒落趨勢。以極大地融合了巴楚文化特點的譚氏子孫龍為例,至今仍然僅在家族內部進行傳承,器物形制和展演流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著古老傳統,講究、忌諱與當地其他的舞龍活動存在明顯差異[6],在2009年被列為省級第一批擴展項目保護名錄。然而,青年人口的流失使得這一珍貴的非遺項目呈現出后繼無人局面,寶龍的制作工藝面臨失傳、舞龍的人群也缺少了新鮮血液的注入。川東體育非遺項目“身心相傳”“口耳相授”的獨特傳承形式,決定了“人”作為其唯一載體地位,人口流動所帶來的傳承人缺失對地域性體育非遺延續所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
四、基于人類學視角的川東體育非遺傳承框架
(一)解構:重視多行為主體參與,建立健全體育非遺動態進入與退出機制
體育非遺發展不應局限于某一家族或某一個體,促進文化共享、重視多方協作、整合多方力量,是實現非遺堅守和價值創新的抓手。在實際操作中,應當進一步鞏固政府在體育公共服務中供給地位,同時注重傳承人、普通民眾在非遺保護與傳承中的主體地位。在這方面,石橋火龍依靠政府品牌打造和對民眾的賦權,極大提升了社會影響力,每年社會捐資達150萬元以上,確保了人才隊伍培養和非遺項目的傳承,成為多行為主體參與的成功典型。
體育非遺進入與退出動態機制建設是其永葆活力的保證。日韓等國家的非遺保護經驗給予我們的啟示是:“非遺”是一種文化保護與傳承的積極機制,而不應成為文化的免死金牌。對于因信息流通、資金支持等方面存在困難而傳承困難的項目,應積極鼓勵其申請“非遺”,為其提供合理的進入機制與傳承平臺;而對于傳承狀況較差、傳承人缺失、社會影響力低下的非遺項目,應當建立合理的退出機制,最終實現川東體育非遺的活態傳承。
(二)整合:在特色小鎮建設中,營造以體育非遺為核心的文化生態
近年來,國家體育總局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運動休閑特色小鎮試點工作,川東地區擁有四川省四大運動特色小鎮之一的渠縣賨人谷運動休閑小鎮,更兼具樊噲鎮、臨巴鎮等文化創意型特色小鎮,以及羅江鎮、八臺鎮等特色旅游休閑小鎮。特色小鎮是人口聚居區、文化聚集區、新興產業聚集區,是經濟、文化、社會區域均衡發展的重要一極[7]。特色小鎮建設中,磚瓦是“硬件”,而文化是“軟件”。體育非遺的傳承與發展應當抓住特色小鎮建設機遇,將具有地域特色的川東體育非遺項目加以引進,構建起以傳統文化為內核的文化生態。
川東體育非遺與休閑旅游結合早有先例,閬中古城對巴象鼓舞、馬象鼓舞、竹馬牛燈等體育非遺項目引入堪稱典范。在特色小鎮建設引入體育非遺項目過程中,首先應當防范過度商業化對傳統文化的侵蝕,使川東體育非遺保持原生形態,其次應當促進企業與非遺傳承人之間互利共贏,給予非遺項目傳承人足夠的社會話語權。
(三)再生產:形成體育非遺產業發展模式
對體育非遺的解構與整合是其現代傳承的前提,但文化再生產環節的缺失使體育非遺依舊擺脫不了造血功能不足的窘境[8]。在邁向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新時期,“關起門來搞非遺”是不合時宜的,支撐其運作的傳統經濟結構已經不可持續。川東體育非遺項目所具有的健身、娛樂、觀賞等多重價值決定了其在文化產業經濟中擁有的巨大潛力與發展空間,探索并形成一整套文化產業經濟的發展模式是必要的。
生產具有吸引力的“文化產品”是體育非遺文化產業形成的關鍵。成熟的文化產業發展模式應當由核心頭部文化和周邊產業集群共同構建——以頭部文化為標桿,帶動周邊產業發展;再以周邊產業為基石,進一步鞏固頭部文化的核心作用。目前,川東地區部分體育非遺項目已經具備作為頭部文化的基礎條件,應當充分利用其品牌效應輻射旅游、餐飲、住宿等周邊行業。而另一方面,周邊產業的日趨繁榮能夠進一步提升體育非遺辨識度,促進其有效傳承和合理創新,最終形成以體育非遺為核心的產業發展閉環。
五、結 論
基于文化人類學相關理論對川東體育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現狀進行了復現,從文化變遷、主客位、文化功能視角論述了川東體育非遺的傳承邏輯,認為組織功能、經濟結構、現代文化、生活方式、人口結構的變遷是導致川東體育非遺傳承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最后對川東體育非遺的傳承提出建議:重視主體參與和機制建設、營造體育非遺文化生態、發展體育非遺產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