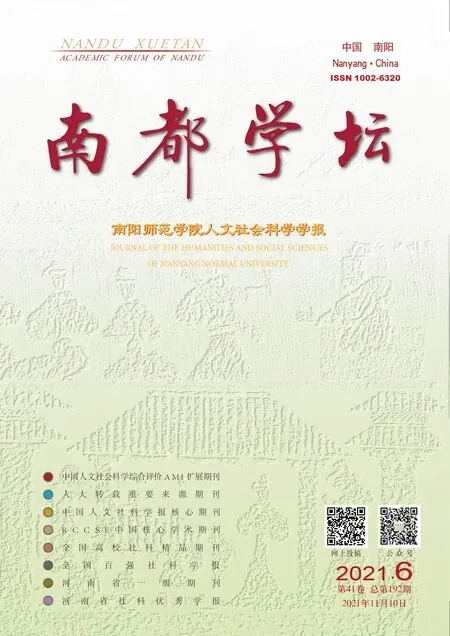控制與失控
——論《弗蘭肯斯坦》的藝術內涵
李 明 珠
(河南財政金融學院 公外部,河南 鄭州 450046)
《弗蘭肯斯坦》是一部書信體小說,通過不同的寫信人之口,講述了年輕科學家弗蘭肯斯坦發現了生命的奧秘,決定通過解剖學、化學和物理學手段創造出一個“新人類”的故事。可人造人因為外貌丑陋、體格嚇人而被創造者嫌棄,被所遇之人驅趕。因此這個人造怪物產生了憤怒和報復的情感,最終與弗蘭肯斯坦同歸于盡。小說的作者瑪麗·雪萊誕生于社會名流家庭,在文壇交游廣泛。盡管有著不幸的童年和成長經歷,但是憑借時代和家庭環境的塑造,她成為英國文學史中極具個性的女作家,成名作《弗蘭肯斯坦》同樣在文壇獨樹一幟,小說中呈現的恐怖氛圍和悲觀情緒構成了獨特的審美風格。
李艷博士在《恐怖審美范疇研究》一書中寫道,“恐怖是一種認知的情緒”[1]98。也就是說,恐怖是審美經驗的一種,它并不只是一種生理反應,而是一種高級的認知過程。在面對怪物或者其他的激發人強烈應激心理的審美對象面前,人們感受到的不僅是驚嚇,還有無助感、厭惡感、幻滅感甚至是因為反感而想要去解構恐懼以及由此產生的興奮與緊張。在閱讀《弗蘭肯斯坦》這一類的藝術作品的時候,恐怖對象和讀者之間又保持了一種安全的距離感,使觀賞者能夠坦然獲得“跌宕起伏”的審美體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一過程也是控制理念的體現。讀者在審美過程中既有被閱讀距離控制的安全感,又享受了荷爾蒙暫時失控帶來的快感,這便是恐怖藝術的魅力所在。
控制論是一門研究機器、生命社會中控制和通訊的一般規律的科學,也是研究動態系統在變化的環境條件下如何保持平衡狀態或穩定狀態的科學。這是一個廣義的、統一的控制論,可以指導或剖析一切可能的控制系統。它的適用范圍包括自然科學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控制論思想體系是一個蘊含豐富的寶庫,幾乎任何學科都可以從中獲益。”[2]8本文所探討的小說文本屬于文學范疇,主題卻是關于科學技術和人類造物的,故本文擬從賽博格系統、暴力循環系統、時代與人倫、敘事系統四個角度入手,運用控制論原理,對該作品進行文本解讀。
一、科學怪人——賽博格(Cyborg)系統
賽博格的概念并不新鮮。在安迪·克拉克眼中,它就是“人機雜糅和肉體與電路實體混合的圖像”。在瑪麗·雪萊的現代科幻開山之作《弗蘭肯斯坦》中,年輕的發明家弗蘭肯斯坦用尸塊拼接和電流刺激創造出的怪物就是一類“賽博格”。科技的每一次突破和發展都意味著人類對生存環境和所處世界的重新認識。表面上看,科技演變會重塑產業模式和社會結構;但更多的時候我們因為無法超越科技便會對未知和消解充滿恐慌。控制論當中有一個“熵”的概念,即導致系統衰退的因子。歷史周而復始,卻只有一首主題歌,那便是生存和死亡的交替,這是一個受“熵增”影響的過程。人們會對賽博格系統感到疑慮或恐懼,因為那不是真正的人類,對于人類自己創造的非自然生物人們當然希望他是可控的,是文明秩序的一部分,而不是可能給文明社會帶來毀滅的“熵”。但是事物是具有兩面性的,“賽博格”給制造者的反饋有好有壞,需要人類加以甄別和利用。
時至今日,人類通過非生育手段創造“新人類”的努力也不是一天兩天,人類機器化或者機器類人化的夢想也都希望變現。在人工智能領域,有一項重要研究內容,即學習系統的建立。所謂學習系統,指的是在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下,不斷使知識完善的系統。而學習系統的核心部分,就是學習環節,它對環境中的信息進行搜索、篩選、思考,以產生、修改和補充知識。在《弗蘭肯斯坦》一書中,第十一章“初識人類”就展示了科學怪人強大的學習能力。這個“不可靠元件組成的可靠機器”[3]在探索和認識自身所處的世界里充滿了能動性,顯示出強大的自學習、自適應的智能。創造“他”的人恐怕也沒有預料到這個怪物會進化出自由意志,到最后成了不可控制的悲劇:這是“賽博格”這類人造物不可避免的命運。
“在控制論中,現實世界的三大系統,即生命系統、人類社會系統與人工物系統,作為一個控制系統,都是處在原因與結果的相互作用中,它們的運動與變化的目的性就是通過這種相互作用——反饋作用來實現的。”[4]很多關于《弗蘭肯斯坦》的論文會提到怪物的身份認同及建構問題。在筆者看來,這是對控制源的追溯。如果說怪物的身體是一個巨大的控制系統,那么創造和把握這個系統的人和怪物之間又構成了一個循環和反饋的結構。小說中寫到弗蘭肯斯坦創造怪物,又被怪物嚇得想要毀滅他,以實施自己的“操控權”。而怪物逃離實驗室,反抗人類的操縱也是生命體自發的反應。在人類社會中,身份的認同是歸屬感和安全感實現的必要條件,它們聯系起個人與社會,是人類百萬年來自我馴化的證明。這意味著社會或集體也正是通過身份認同牢牢控制和把握了個體自由,而這種自發形成的被控與反控在怪物身上也是同樣存在的。一開始怪物渴望融入人類社會,被接納被愛護,但人類給他的反饋只有驚懼和排斥,甚至意圖在肉體上消滅他。在尋求支持而不得的情況下,怪物轉而報復自己的創造者,在此過程中迸發出令人驚詫的創造力。這個怪物被賦予了和創造者一樣的名字,怪物的反抗也是人類的反抗。我們需要社會體系的庇護和其提供的生存機會,同時也想最大程度逃離由此而來的束縛與掌控。從“賽博格”身上映照的,是人類自身的局限性。
二、暴力的循環——人性之懼
埃利希·弗洛姆在他的《人之心——愛欲的破壞性傾向》一書中探討過一個問題:人是狼還是羊?最后他得出人同時具有“墮落綜合征”和“生長綜合征”兩種人格傾向的結論。在合適的環境和條件下,人會爆發出暴力或者仁慈的心理特征。比如小說主人公之一弗蘭肯斯坦,他并不是什么陰險狡詐的“大惡人”,強行創造怪物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科學理想和狂熱的探索目的。但這個動機卻驅使他做出了錯誤的選擇并造成之后對他所愛之人生命的剝奪。生育本來是一個自然的生理過程,但是在父權社會的審美標準、意識形態影響下成了一種暴力模式。小說中類人生物的創造者弗蘭肯斯坦是個男人,創造怪物的“子宮”是個實驗室。對生育權利的渴望以及男性沙文主義的自大讓弗蘭肯斯坦想要操縱生死,這種行為就是一種“主觀暴力”。回顧人類歷史,回應暴力的往往也是暴力。弗蘭肯斯坦的怪物最初也天真懵懂如同稚嫩孩童,試圖接近人類,滿足自己學習和交流的欲望。沒想到這種嘗試換來的是人類的攻擊和驅趕。這里面有男人、女人、小孩;暴力形式涵蓋語言暴力、肢體暴力、冷暴力。身為怪物,你的善舉就不是善舉,乃是挑釁。人們感到身處危險的境地,自然就產生對暴力的反對。再到后來實在不行怪物便期待擁有一個與之匹配的女怪物共度余生,弗蘭肯斯坦在同情和自責下先是同意了他的請求但又因為顧慮和不信任出爾反爾。這更激發了怪物——人造人的暴力報復,繼而殺死了弗蘭肯斯坦的未婚妻伊麗莎白。可以看到,暴力的反饋和循環路徑非常清晰。暴力的來源之一是恐懼,而恐懼會讓人不擇手段。小說中這份恐懼也許來自自身的軟弱無力,比方說弗蘭肯斯坦對自己作品的無力把控和怪物無法自我復制,連另一半都要向人類乞求的可悲弱勢地位。“創造生命意味著超越人的現狀。超越像骰子被拋出杯子,一個生靈被拋進了世間……創造生命的要求是軟弱無能的人所缺乏的某種品質。破壞生命只要求一種品質——暴力的使用……一個不能創造的人打算去破壞。在創造和破壞中,他超越了作為單純創造物的作用。”[5]15弗洛姆的這番話適用于生命系統、人類社會系統與人工物系統,無一例外。
人類在自然力量面前是弱小的,所以在超越自然的產物面前難免底氣不足。“科學怪人”的故事不僅僅是一個科幻或者是恐怖的故事,而是對人類社會的一次概括和總結。人性當中對暴力和快感的追逐讓人類有了自毀的傾向,文明世界本該屬于秩序和條理,但最終卻因為“熵增”又回到混沌和無序。怪物本身就是對“熵”的隱喻。“人的歷史是鮮血寫成的歷史,是連綿不絕的暴力的歷史,在這樣的歷史中,幾乎永恒的暴力一直被用來屈服人的意志。”[5]1有意思的是,因為需要安全感和歸屬感,很多時候人對于暴力本身是持否定態度的,但是由于死亡的司空見慣,在特定時期人類又會對暴力麻木不仁甚至甘之如飴。這才是暴力真正可怖的地方。
三、瑪麗·雪萊——被時代困住的預言家
瑪麗·雪萊幼年喪母,其生母是著名的“那個時代的精神”——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此人是聲名遠播的女權主義者,有著轟轟烈烈卻并不美好的人生經歷。父親威廉·戈德溫是當時英國最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和哲學家之一,在瑪麗生母去世后娶了女鄰居。19世紀工業文明迅速崛起,當時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決定了瑪麗的生母及她本人的不平凡。“正是因為科學革命的變革使人們對世界的認識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提出了新的解決客觀世界問題的新的方法與原則,改變了人類的價值觀與人生觀,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社會的進步與變革。”[6]也就是說,人類思想的解放往往與科技的發展有重大聯系。這依舊是一個有著學習—反饋路徑的系統,在這個系統里,被探討的熱點之一就是男權話語體系中女性的突圍。
“桑德拉·吉爾伯特和蘇珊·古巴在《閣樓里的瘋女人》一書中寫道:‘女人是沒有歷史的男人,至少是沒有《希臘羅馬名人傳》那種歷史。’ 對瑪麗·雪萊來說,失去母親的痛苦、父親再婚后自己被排斥在家門之外的感覺、這種出生時沒有歷史的想法——或者至少與被壓制或被改變的歷史綁縛在一起——可能帶有一種特別的辛酸。”[7]幾千年來,女性一直是以屈從和依附的姿態出現在社會生活當中,18—19世紀的女性即便有獨立思想的萌芽,也難免走回頭路,陷入兩難的境地。在早期歷史中,出于人性的需求,女性自然希望和男性結為同盟,以使整個族群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個合作體系展現出另外的黑暗——它對男女兩性的束縛傳遞出“自我犧牲”這么一種反饋,導致承擔著生育重擔的女性迫切希望對體系做出調整,甚至是重新建構。提到生育,瑪麗·雪萊走上了和她母親相似的道路,這條路很難說是自我放逐還是追求獨立自主。事實上,瑪麗·雪萊經歷了三個孩子的夭折,“母職”在她身上更多是一種精神和肉體的折磨。從這一點出發,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弗蘭肯斯坦》里會有兩性結合之外的人造人,以及滲透全篇的凄涼、恐怖、哀怨的基調。瑪麗·雪萊應該閱讀或者了解過科技革命后的諸多新生學科知識。在歐洲濃厚的宗教背景下,物理、化學、生物、天文、醫學與新的疆域、新的研究方法互相交雜,有力推動了新觀念的誕生或者對舊觀念的新詮釋的出現;這些新理念反過來也會促進宗教思想的分化。“科學怪人”這一類經典文學形象之所以能夠立得住、站得穩,離不開其時代背景和發展規律的支撐。人類身處在大大小小的系統里,不斷通過自己的智慧與學習能力改造環境,影響世界潮流。瑪麗·雪萊通過對人性底色和時代發展規律的深刻洞察,創造出她文學生命中的孩子——《弗蘭肯斯坦》,預言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可能圖景。
四、創造者的名字——讀者與作者的交流
在這個角度,筆者又要回到最初探討的主題——恐怖藝術。不同于愛倫·坡,斯蒂芬·金或者H.P.洛夫克拉夫特,瑪麗·雪萊是位女性作家,她的作品盡管有恐怖情節,實際上卻是人類發展轉折期的見證。申丹教授在闡述西方敘事學理論時引入了“敘事交流”這一說法。該交流過程為“真實作者→隱含作者→(敘述者)→(受述者)→隱含讀者→真實讀者”[8]75。《弗蘭肯斯坦》一書中不同寫信人站在不同位置陳述故事經過,會讓讀者在重疊和交換中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表達的理念與價值觀。在本書的敘事交流體系中,瑪麗·雪萊用自己19年的人生閱歷用心和讀者交流,但是能讀懂她的理想的讀者并不等于真實的讀者。當時就有人質疑怎么會有人寫出“如此惡心的東西”,還有人相信這是異教徒的陰謀。出版商一開始也無意于發表女人寫的東西,畢竟當時女人是屬于廚房和育嬰室的。女人的價值也不在于寫作或其他社會活動,而是安心待在家,做“房中天使”。辛苦創作的結晶得到這樣的反饋也許是意料當中的事情,然而瑪麗想要的遠不止這些。從開始的匿名發表,到后來的雪萊作序,再到最后署名瑪麗·雪萊;《弗蘭肯斯坦》終于有了自己的位置。“正如吉爾伯特所指出的,瑪麗·雪萊非常理解父權社會中的姓名和社會合法性之間的關系。”[8]無論是“科學怪人”,還是瑪麗·雪萊,抑或者瑪麗·戈德溫,被創造的總會被賦予創造者的名字。
當讀者在觀賞小說里的怪物和恐怖形象時,沒有多少人會仔細剖析自己的感受。“恐怖藝術中作為恐懼對象的怪物是在歷史的流變中,不斷被文明的秩序和理性話語建構起來”[1]91的。怪物是和正常人對立的陌生、異化的“他者”,是畸形和混亂的代表,是反叛性、矛盾性的代言人。讀者有自己的價值判斷和人生經歷,也處在既定的社會系統里。“新的怪物會不斷地從社會矛盾的肌體中產生出來,成為新的歷史時期秩序的對立面,這些怪物代表了現存秩序的空白、未知、騷動和抵抗,是對秩序進行瓦解的力量,同時也是現代復雜構成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因為將秩序的混亂不斷地揭示出來,正是現代性的要求。”[1]93所以,恐怖的東西并不恐怖,刺激人心智的也不一定非得是怪物。這些都是表象,背后對現行系統運作的困惑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才是恐怖感的來源。而這種恐怖感的創造者,不一定是瑪麗,更有可能是讀者自己。
五、結語
人類已經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每一次戰爭的背后除了對資源的掠奪還有國際秩序的重新洗牌。過往的歷史無法改變,未來的到來無法阻擋。科學技術的每一次發展都會給人類帶來某種程度的反噬,我們正處在信息技術爆發和競爭加劇的歷史時期。當吃飯、生育這些動物本能不再困擾人類,是不是就迎來了人類最終的解放?如此,《弗蘭肯斯坦》留給我們的思考已經不是文本所能控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