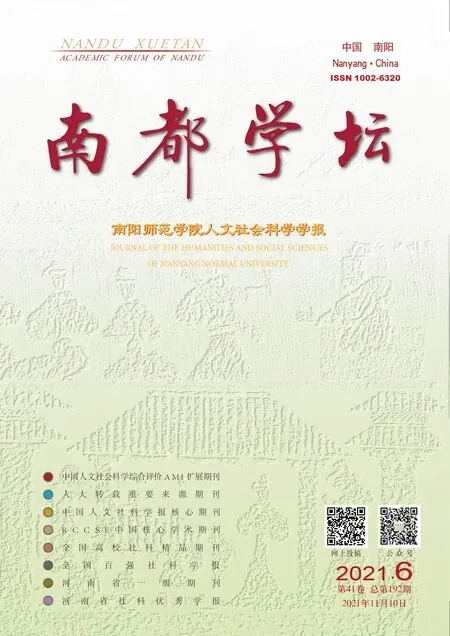遏制虐童的域外經(jīng)驗及其啟示
蔣 娜, 江珞伊, 陶 歡
(1.北京師范大學(xué) 法學(xué)院,北京 100875; 2.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北京 100009;3.沈陽市沈河區(qū)政務(wù)服務(wù)中心,遼寧 沈陽 110066)
隨著近年浙江溫嶺、紅黃藍幼兒園等虐童案屢見報端,虐童的刑法規(guī)制問題愈受關(guān)注。由于相關(guān)犯罪入罪門檻高,絕大多數(shù)虐童案被非罪化處理[1],這有悖于我國1991年批準(zhǔn)的《兒童權(quán)利公約》之要求。時值該公約生效30周年之際,在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quán)原則指導(dǎo)下,完善防治虐童的刑法規(guī)制是提升人權(quán)保障效能的關(guān)鍵。本文在考察域外法治經(jīng)驗的基礎(chǔ)上,對我國刑法及相關(guān)配套措施提出妥善建議,以期裨益于保護兒童的最大利益。
一、刑法規(guī)制虐童的域外經(jīng)驗
遏制虐童是各國面臨的共同難題。域外相關(guān)國家或地區(qū)基于《兒童權(quán)利公約》的要求,在有關(guān)法治實踐中積累了較為豐富的檢驗,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法律規(guī)范或制度機制。
(一)虐童罪行的立法模式和規(guī)范
縱覽域外相關(guān)國家或地區(qū)的刑法規(guī)制,出于對虐童行為的性質(zhì)與兒童權(quán)益的保護范圍等問題的理解不一致,不同國家或地區(qū)采取的立法模式和規(guī)范內(nèi)容各有特色,大致可以劃分為以下兩類情況。
第一類是將虐待兒童行為單獨作為犯罪規(guī)定在侵犯公民權(quán)利罪中,采用此類立法例的包括德國、我國香港、澳門地區(qū)等。如香港地區(qū)在刑事立法上,以“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的罪名規(guī)制虐待兒童行為,規(guī)定在《侵害人身罪條例》第212章第27條中(1)該條規(guī)定,“任何超過16歲而對不足該年歲的任何兒童或少年人負(fù)有管養(yǎng)、看管或照顧責(zé)任的人,如故意襲擊、虐待、忽略、拋棄或遺棄該兒童或少年人,或?qū)е隆⒋僦略搩和蛏倌耆耸芤u擊、虐待、忽略、拋棄或遺棄,其方式相當(dāng)可能導(dǎo)致該兒童或少年人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損害(包括視力、聽覺的損害或喪失,肢體、身體器官的傷損殘缺,或精神錯亂),即屬犯可循公訴程序?qū)徲嵉淖镄小薄T诹啃躺希绻袨槿藢ζ浔旧砭拓?fù)有提供日常生活照顧義務(wù)的兒童停止撫養(yǎng),或者故意阻止兒童得到一些機構(gòu)的救助,依照簡易程序定罪后處以監(jiān)禁3年,若以公訴程序?qū)徖恚商幈O(jiān)禁10年。參見何劍《論“虐童”行為的刑法規(guī)制》,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3年第2期,第49-56頁。。香港在虐待兒童防治方面逐步從簡單走向多元,從治療為主轉(zhuǎn)變?yōu)轭A(yù)防先行,逐漸形成了多方合力的受虐兒童保護生態(tài)系統(tǒng)[2]。第二類是將虐待兒童行為包含在虐待類罪名中,采用此類立法例的包括俄羅斯(2)如《俄羅斯聯(lián)邦刑事法典》第117條規(guī)定,虐待罪的對象包含未成年人、孤立無援者、依賴犯罪人的從屬地位者、被綁架或劫持者等。、日本等國家。
不同國家或地區(qū)立法對虐童的刑法規(guī)制,除歸類不同外,在犯罪的構(gòu)成要件上差異也較大,主要表現(xiàn)如下。
1.犯罪主體和對象范圍
在犯罪主體方面,普遍從對未成年人養(yǎng)育或照顧的責(zé)任角度進行限制(3)如我國澳門地區(qū),構(gòu)成虐待罪的主體為照顧、保護或有責(zé)任指導(dǎo)或教育、或因勞動關(guān)系而對未成年人負(fù)有責(zé)任的人員。;犯罪對象范圍上,除保護兒童人身安全外,部分國家明確了兒童心理健康的保護。德國規(guī)定的虐待被保護人罪中,既涉及對兒童造成身體傷害的行為,又規(guī)范對兒童心理發(fā)育的損害(4)該款規(guī)定,“行為人因其行為致被保護人死亡或嚴(yán)重之健康損害或身體或心理發(fā)育上的嚴(yán)重?fù)p害的,處 1 年以上自由刑;犯第一款之罪情節(jié)較輕,處3個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犯第三款之罪未遂的,處 6個月以上 5 年以下自由刑”。參見莊敬華、徐久生譯:《德國刑法典》,中國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頁。。美國在罪名設(shè)置中未使用具體罪名來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的不法行為,而主要是通過襲擊罪、毆擊罪、加重毆擊罪規(guī)制此類行為。現(xiàn)代美國刑法吸收了民法中的內(nèi)容,將襲擊分為“毆擊未遂襲擊”和“暴力威脅襲擊”,前者造成了被害人身體傷害的危險,后者則是引起了被害人的心理恐懼[3],毆擊罪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犯罪在客觀方面需要施虐者實施不法行為,并不需要與兒童的肉體有實際接觸,但需要發(fā)生侵害事實。我國臺灣地區(qū)以妨害幼童發(fā)育罪規(guī)制虐待兒童行為,該罪名在2012年修正法案前僅規(guī)制虐待身體的不法行為,并未涉及心理上的虐待,但由于許多的臺灣虐待兒童案件中施虐者并未對兒童造成肉體傷害,而是對兒童的心理造成創(chuàng)傷。自2012年修正案后,身心健康同為妨害幼童發(fā)育罪的保護法益(5)該法第286條規(guī)定,“對于未滿十八歲之男女,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致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fā)育,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并科300萬元(新臺幣)以下罰金”。。
2.行為方式
日本刑法在規(guī)制虐待兒童行為類的犯罪時,并未直接設(shè)立虐待罪和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而是針對行為類型不同規(guī)定了不同的罪名,如通過暴行罪、傷害罪等罪名體系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型的犯罪[4]。傷害罪類似于我國刑法中的故意傷害罪和過失傷害罪,而暴行罪是日本的獨特制度。暴行罪規(guī)定在《日本刑法典》第208條(6)《日本刑法典》第208條:“實施暴行而沒有傷害他人的,處2年以下懲役、30萬日元以下罰金,或者拘役或科料。”,暴行罪的成立不僅需要施害者對被害人的身體實施非法的有形的力(根據(jù)日本的判例得知并不要求這個有形的力與被害人的身體有實際的接觸),同時還要求施害者所實施的暴行是在一定限度內(nèi)具有對行為對象造成侵害事實的危險而不是實際的侵害事實,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傷害罪的未遂。暴行罪規(guī)制的是造成侵害事實前的暴行,防止他人的身體外部受到非法的有形的力的攻擊,其保護的對象不僅限于兒童,其他弱勢群體亦都在此罪名保護的范圍之中。相比于保護法益同是人身健康權(quán)利的其他罪名,暴行罪成立的標(biāo)準(zhǔn)更低,在規(guī)制虐待兒童犯罪中補充了一般違法行為的虐待和真正地造成侵害事實的虐待之間的處罰漏洞。
3.完成形態(tài)
虐童情節(jié)惡劣或后果嚴(yán)重的,應(yīng)當(dāng)構(gòu)成犯罪,是世界各國刑事立法的普遍共識。但對于未遂如何處理,是否構(gòu)成犯罪,包括我國在內(nèi)的很多國家沒有明確規(guī)定,致使虐待兒童未遂是否構(gòu)成犯罪很大程度上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但也有一些國家如德國和日本將虐待兒童未遂應(yīng)受刑罰處罰予以明文規(guī)定(7)《德國刑法典》第 225條規(guī)定了虐待被保護人罪,涵蓋的對象包括“不滿十八周歲或因殘疾、疾病而無防衛(wèi)能力之人”,行為人對這些人實施虐待行為,或者惡意地疏忽其照料義務(wù),以致?lián)p害被害人健康的,構(gòu)成該罪,一般情況下處 6 個月以上 10年以下自由刑;犯本罪未遂的,亦應(yīng)處罰。再如,日本暴行罪的設(shè)置,并不要求虐待行為這一有形的力與被害人的身體有實際的接觸,同時強調(diào)施害者所實施的暴行是在一定限度內(nèi)具有對行為對象造成侵害事實的危險而不是實際的侵害事實,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傷害罪的未遂。《德國刑法典》第 225條:“不滿十八周歲或因殘疾、疾病而無防衛(wèi)能力之人,他們處于行為人的照料或保護之下或?qū)儆谛袨槿说募彝コ蓡T或被照料義務(wù)人將照料義務(wù)轉(zhuǎn)讓給行為人或在職務(wù)或者工作關(guān)系范圍內(nèi)下屬,行為人對這些人實施虐待行為,或者惡意地疏忽其照料義務(wù),以致?lián)p害被害人健康的,處 6 個月以上 10年以下自由刑;犯本罪未遂的,亦應(yīng)處罰。行為人因其行為致被保護人死亡或嚴(yán)重之健康損害或身體或心理發(fā)育上的嚴(yán)重?fù)p害的,處 1 年以上自由刑;犯第一款之罪情節(jié)較輕,處 3 個月以上5 年以下自由刑;犯第三款之罪未遂的,處 6個月以上 5 年以下自由刑。”。
4.刑罰設(shè)置
我國把虐待罪行的刑罰配置在一個刑罰區(qū)間,并未根據(jù)涉案情節(jié)及要素對刑罰區(qū)間進行細(xì)分,致使虐待行為的量刑范圍過大,難以把握。而德國、韓國等在立法中對虐童行為進行細(xì)化分類,并針對既遂、未遂和量刑情節(jié)等問題細(xì)化法律規(guī)范(8)韓國2012年《兒童虐待特別法》加重對虐待兒童行為的處罰力度:“虐童”刑期將由“5年以下”提高到“10年以下”,罰金將從“3000萬韓元以下”上調(diào)至“5000萬韓元以下”;兒童服務(wù)及教育機構(gòu)從業(yè)人員“虐童”,將從重懲處并禁止10年以內(nèi)從事相關(guān)職業(yè);對隱匿“虐童”實情的機構(gòu)負(fù)責(zé)人將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和“1000萬韓元以下”罰款;所有“虐童”罪犯都將接受200個小時以上的再犯預(yù)防教育。。
就規(guī)范虐童行為而言,各國或地區(qū)有關(guān)刑法規(guī)制的范圍、對象、重點或懲罰力度等有差別,但一般都入罪并入刑。而各國或地區(qū)防治該行為的實踐差距,主要源于防治該行為的有關(guān)制度機制迥異,由此產(chǎn)生的實際效果也不盡相同。
(二)防治虐童的權(quán)利保障機制
有效的權(quán)利保障機制是遏制虐童類行為的利器。總體上,域外相關(guān)國家或地區(qū)在虐童防治方面設(shè)置的權(quán)利保障機制,內(nèi)容豐富且頗有特色。
1.保障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的機制
生命權(quán)方面,部分國家將殺害兒童的行為單獨規(guī)定為犯罪,如俄羅斯和我國澳門地區(qū)等將母親生產(chǎn)時或生產(chǎn)后的殺嬰行為單獨規(guī)定為犯罪,分別規(guī)定在《俄羅斯刑法典》第106條和《澳門刑法典》分則第131條。
健康權(quán)方面,主要從對兒童的照顧責(zé)任的角度(9)例如,日本刑法第217條規(guī)定遺棄罪,規(guī)制“遺棄因年老、年幼、身體障礙或者疾病而需要扶助者”行為。,在規(guī)定了遺棄罪的基礎(chǔ)上,還設(shè)置了保護責(zé)任者遺棄罪,規(guī)制對于老年人、幼年人、身體障礙者或者病人負(fù)有保護責(zé)任而將其遺棄,或者對其生存不進行必要保護的遺棄行為。還有國家明文禁止未成年人紋身或飲酒(10)英國1969年出臺禁止未成年人文身法,禁止不滿18周歲的未成年人紋身;1997年出臺沒收酒類(未成年人)法,可以沒收18周歲以下飲用的酒類。參見謝望原《英國刑事制定法精要》,中國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242頁。。
2.性自由權(quán)保障機制
兒童的性自由權(quán)不僅在強迫性行為中受到侵害,也可能在虐待行為中受到侵害。如日本在刑法典中明確規(guī)定未滿13歲的,即便同意,也不影響強奸罪或猥褻罪的成立,并且在草案中將年齡提高到了14歲,進一步擴大了保護的范圍。我國澳門地區(qū)刑法典中除了規(guī)定奸淫未成年人罪、兒童之性侵犯罪、作為未成年之淫媒罪外,還設(shè)有對受教育者及依賴者之性侵犯罪,旨在規(guī)制行為人濫用“教育或扶助”關(guān)系而與14歲至16歲的未成年人發(fā)生性行為。我國香港地區(qū)除奸淫幼女罪、與未滿16歲女子非法性交罪以外,還單獨設(shè)有拐帶未滿18歲未婚女子與人性交罪、對不滿16歲兒童嚴(yán)重威脅罪、導(dǎo)致或鼓勵兒童賣淫罪。
3.訴訟權(quán)利和教育矯正機制
日本對少年保護案件、少年的刑事案件,以特別法的模式進行專門的明確規(guī)定(11)如《少年法》《少年審判規(guī)則》規(guī)定少年實施犯罪行為時和少年保護案件的特別程序;《少年院法》規(guī)定了少年院和少年鑒別所的設(shè)置、管理、收容、在少年院內(nèi)進行教育矯正的基本原則等;《少年保護案件補償法》對少年保護案件單獨規(guī)定了補償程序。。俄羅斯在刑法中對于未成年人的刑事責(zé)任,單獨在刑法典內(nèi)設(shè)為獨立一編,未成年人受害人的保護適用特別程序,納入其刑法典第十九編之中。
(三)防治虐童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約機制
通過兒童保護機構(gòu)介入,監(jiān)督制約家庭或?qū)W校、醫(yī)療等機構(gòu)中密切接觸兒童的強勢群體濫權(quán),也是域外諸多國家或地區(qū)的普遍做法。其主要表現(xiàn)在如下方面。
1.強制報告制度
美國最有特色的制度是強制報告制度,聯(lián)邦政府兒童局在1963年制定舉報法范例后[6],大多數(shù)州也要求“有理由相信”或“有理由懷疑”兒童受到虐待或忽視時要舉報,對于知情不報者,法律上也規(guī)定了極其嚴(yán)厲的監(jiān)督和懲戒措施。它在主體上,把強制報告者的范圍從醫(yī)生,擴展到與兒童有相關(guān)聯(lián)系的人;內(nèi)容上從實際發(fā)生的身體虐待,延伸到只要舉報者有相當(dāng)?shù)睦碛蓱岩蓛和媾R精神、性或肉體上受虐待的風(fēng)險即可。與之類似的有,日本2004年《虐待兒童防止法》規(guī)定“認(rèn)為有虐待的必須舉報”,并把虐童的標(biāo)準(zhǔn)范圍擴大到了語言暴力。
2.犯罪評估模式
在我國香港地區(qū),社會福利署設(shè)置了獨立的部門保護兒童,該署所制定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多次修訂后對虐待兒童類的行為進行了界定、分類,同時《指引》也在調(diào)查取證程序、保密和案件的評估模式上進行了明確規(guī)定。其中的評估模式為其中的一大亮點,社署接到虐待兒童類案件的舉報后會進行初期、中期和深度三次評估。初期評估具體指的是,社署人員對舉報的虐待兒童類案件進行介入,隨之進行中期評估也就是對案件涉及的家庭和受虐者進行調(diào)查,如有需要將進行跨界別個案會議,也就是深度評估該案的虐待不法行為是否需要歸為刑事案件。
3.兒童性犯罪登記制度
美國和加拿大都設(shè)有性犯罪者登記處(SOR)來監(jiān)控性犯罪者,使用登記處記錄和跟蹤居住在社區(qū)的性犯罪者,以保護社區(qū)免受危險和暴力性掠奪者的侵害。199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雅各布·韋特林(Jacob Wetterling)針對兒童的犯罪和性暴力犯罪者登記法,該法案要求所有州都要開發(fā)追蹤社區(qū)內(nèi)被判有罪的性犯罪者的系統(tǒng)。緊隨其后的是1996年頒布的梅根法,它要求所有州都必須公開某些注冊數(shù)據(jù)。2003年,美國聯(lián)邦政府要求每個州建立和維護互聯(lián)網(wǎng)SOR作為社區(qū)通知的主要手段,不遵守這項法律的州將面臨失去對其項目的聯(lián)邦資金的風(fēng)險。美國和加拿大的設(shè)置有所不同,在美國性犯罪者登記和通知系統(tǒng)在所有50個州、哥倫比亞特區(qū)和美國領(lǐng)土上運行,并向公眾開放,加拿大的SOR對普通公眾是不可訪問的,目的是為了協(xié)助執(zhí)法機構(gòu)調(diào)查性暴力案件。但總體而言,SOR通常是基于這樣的觀點,即性犯罪者具有持久的犯罪傾向,因此為了公共安全的利益,他們的隱私權(quán)和行動自由應(yīng)該受到嚴(yán)格限制。人們認(rèn)為SOR既可以作為對犯罪者的威懾,也可以作為警方的調(diào)查工具。
二、與我國有關(guān)刑事規(guī)制的比較
域外196個締約國或地區(qū),除美國從未簽署之外,都已批準(zhǔn)了《兒童權(quán)利公約》(簡稱《公約》),中國于1991年12月29日批準(zhǔn)《公約》。在《兒童權(quán)利公約》的基礎(chǔ)上,各締約方規(guī)定了嚴(yán)厲的罪名和刑罰,加以規(guī)制侵害幼童類的犯罪行為,趨向于將侵害幼童人身法益的犯罪圈擴大,對虐待兒童采取零容忍。
(一)立法模式和規(guī)范
我國刑事立法通過故意殺人罪、強奸罪、虐待罪、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拐賣婦女兒童罪、組織殘疾人、兒童乞討罪、雇用童工從事危重勞動罪等保護兒童的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勞動權(quán)、性自由權(quán)等權(quán)利,但是仍存在不足之處。
第一,家長或托管機構(gòu)等人員對兒童實施輕微暴行的行為,因為沒達到我國所設(shè)置的輕傷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都未加以刑法規(guī)制。我國刑法規(guī)制虐童的罪名中沒有類似美國、日本的襲擊罪和暴行罪(12)美國和日本都分別設(shè)置了襲擊罪和暴行罪,這兩個罪規(guī)制的是對兒童造成侵害事實前的不法行為,成立的標(biāo)準(zhǔn)更低,補充了一般違法行為和真正地造成侵害事實的虐待之間的處罰漏洞,就傷害罪無法規(guī)制的兒童所受的輕微傷程度的不法行為,加以合理的罪名和刑罰。,部分受虐兒童肉體傷害不重但性質(zhì)較為惡劣的行為,并不滿足虐待類罪名中情節(jié)惡劣和故意傷害罪中的傷害的標(biāo)準(zhǔn),只能認(rèn)定為無罪或通過《治安管理處罰法》進行行政處罰。盡管此類虐待的違法性程度,遠(yuǎn)遠(yuǎn)高于處罰法所界定的“虐待”,但仍無法依照這些罪名進行規(guī)制。
第二,《刑法修正案(九)》以前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的主體,僅限于家庭造成兒童保護缺位,托管機構(gòu)侵害兒童人身法益僅以尋釁滋事罪予以規(guī)制。《刑法修正案(九)》明確了虐待兒童類犯罪的主體,不再完全受家庭成員身份的限制,有監(jiān)護、看護義務(wù)的非家庭成員,也被納入刑法規(guī)制虐童的主體范圍,修改后的虐待罪及新增的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更有利于對虐待兒童類犯罪進行規(guī)制,但修改后的法條對于虐童的內(nèi)涵和范圍仍缺少明確規(guī)定。
第三,在保護對象上,我國現(xiàn)有虐待罪保護的對象范圍過窄,在這方面德國、我國澳門地區(qū)的立法值得借鑒(13)德國虐待被保護人罪將一切需要刑法保護的弱勢群體歸納在虐待被保護人罪的行為對象范圍里,我國澳門地區(qū)刑事法律上以“虐待未成年人、無能力之人或配偶又或使之過度勞累罪”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的犯罪。。
(二)權(quán)利保障機制
我國通過立法程序把《公約》規(guī)定轉(zhuǎn)化為國內(nèi)法,例如《未成年人保護法》《預(yù)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民法典》《民事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形成了較完備的保護兒童權(quán)利的法律體系(14)除刑事立法中的相關(guān)罪名外,2001年公布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22條明確規(guī)定“禁止歧視、虐待、遺棄女嬰”。2006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了《未成年人保護法》,《公約》規(guī)定的“兒童最大利益”“兒童的生存權(quán)和發(fā)展權(quán)”等基本原則在這部法律中得到了體現(xiàn)。2012年3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guān)于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落實《公約》第37條、第40條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更好保障未成年人的訴訟權(quán)利和其他合法權(quán)益。。同時,《勞動法》《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等規(guī)范(15)《勞動法》第15條規(guī)定“禁止用人單位招用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禁止使用童工規(guī)定》明確“國家機關(guān)、社會團體、企業(yè)事業(yè)單位、民辦非企業(yè)單位或者個體工商戶均不得招用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禁止任何單位或者個人為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介紹就業(yè);禁止不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開業(yè)從事個體經(jīng)營活動”。對于招用和介紹不滿16周歲未成年人就業(yè)的,上述法律規(guī)定了明確的法律責(zé)任。,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相關(guān)司法解釋,也以《公約》的精神、原則和規(guī)定為指導(dǎo),進一步細(xì)化了對兒童權(quán)利的保護。
對兒童的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勞動權(quán)、性自由權(quán)等權(quán)利的保護,在我國立法中有所體現(xiàn),但保護范圍主要限于上述基本實體權(quán)利,在兒童訴訟權(quán)利、涉兒童犯罪的特別程序方面較少[5],對其心理層面的矯正和疏導(dǎo)也不足。時常在兒童權(quán)利受實際侵犯后,才能訴諸法律的保護,從而缺少對兒童權(quán)利予以系統(tǒng)性保障(16)如澳門的《教育制度及社會保護制度》還規(guī)定在刑法對虐待兒童者定罪處罰后,還需為對受虐兒童的心理進行疏導(dǎo)和修復(fù)。俄羅斯、日本等國家對涉少年刑事案件的訴訟權(quán)利和教育矯正機制的特殊規(guī)定都值得我國借鑒。。
(三)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約機制
我國現(xiàn)有規(guī)定側(cè)重事后處罰,而忽視事前預(yù)防,缺少相應(yīng)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約機制。虐待行為與一般性的傷害、殺害等行為不同,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往往存在一定的監(jiān)護關(guān)系,具有隱蔽性和長期性,除施虐者和受虐者,第三人很難發(fā)現(xiàn)。作為被害人的兒童處于成長期,由于能力限制或?qū)彝コ蓡T的依賴、恐懼等情感,被虐待的兒童不能或不愿意控告家庭成員對自己所實施的虐待,同時因進入犯罪圈的門檻較高,使得大量的虐童行為被非犯罪化處理,這是由于長期以來未正確地正視兒童的合法權(quán)益所導(dǎo)致的。虐待兒童行為往往滋生于一定的家庭環(huán)境中,其發(fā)生和發(fā)展往往有跡可循。程度嚴(yán)重的虐待行為往往從一般虐待發(fā)展而來,在虐待發(fā)生的初期,如果盡早得到發(fā)現(xiàn)和矯治,從源頭對滋生虐待的環(huán)境進行改良,可以從根本上減少虐待行為案件的發(fā)生,切實保護兒童的權(quán)益;從單個案件的角度來看,在虐待行為尚未發(fā)展的初期,對相關(guān)人員進行教育和矯正,可以更有效地避免虐待行為的發(fā)生。
由此可見,我國和域外有關(guān)法治實踐相比,尚存在規(guī)制虐童的刑法網(wǎng)格粗疏、有關(guān)兒童權(quán)利邊界不清,缺少對家庭、社區(qū)、教育或司法機構(gòu)的有效監(jiān)督制約制度等問題。這違反了我國批準(zhǔn)的國際公約之要求,也影響相應(yīng)刑法規(guī)制充分發(fā)揮優(yōu)勢,或提升針對虐童的整體性治理效能,更不利于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在我國的實現(xiàn)。
三、我國刑法規(guī)制虐童的完善方向
作為簽署和批準(zhǔn)《公約》近三十年的締約國,未來中國在刑法規(guī)制虐童方面,還應(yīng)參考域外經(jīng)驗,著力做好如下方面完善工作。
(一)織密規(guī)制虐童的刑法網(wǎng)格
1.拓寬主體范圍
《刑法修正案(九)》增設(shè)了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將負(fù)有監(jiān)護看護義務(wù)的人員納入虐待兒童類犯罪的主體受刑罰規(guī)制,盡管如此,刑法所規(guī)制的虐待兒童類范圍仍不全面,發(fā)生在家庭的虐待兒童是典型的虐待兒童,但非典型虐待兒童的施虐主體不只是包括通過契約建立的監(jiān)護看護人,還包括其他人。因此,筆者認(rèn)為要擴大虐待兒童犯罪的主體,從而解決虐待兒童類犯罪主體的局限性。我國刑法可以將第260條虐待兒童主體的適用對象從負(fù)有監(jiān)護看護義務(wù)的人員改為非家庭人員,擴大虐待兒童施虐主體的范圍。
法律的滯后性與生俱來,它需要不斷更新以適應(yīng)現(xiàn)實社會的發(fā)展。針對目前發(fā)生的虐待兒童案,施虐者不再局限于家人、老師,施虐主體的多樣性要求結(jié)合當(dāng)前的狀況,刑法擴大虐待兒童類犯罪的主體范圍符合當(dāng)前社會發(fā)展的趨勢。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所規(guī)制的虐待兒童主體,并未包括所有的非家庭成員,除了具有監(jiān)護、看護關(guān)系的人員,刑法仍然需要對實施虐待兒童行為的其他施虐者進行規(guī)制。如果將刑法第260條的主體擴大至所有的非家庭成員,不再局限于監(jiān)護、看護關(guān)系,那么刑法對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和非家庭成員的身份暴力實施虐待兒童的行為都可以加以規(guī)制,從而解決虐待類犯罪主體的局限性的問題。將主體范圍擴大到所有的非家庭成員,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審判非典型虐待兒童類犯罪之時,可以不再局限于監(jiān)護看護關(guān)系,虐待兒童情節(jié)惡劣的就可依照第260條定罪處罰。
2.擴展對象外延
虐待行為從字面意義上來看極易被理解為限于對兒童身體上的折磨和傷害,但對于正在成長發(fā)育的兒童來說,肉眼可見的身體傷害可能僅僅是其中的一部分,心理發(fā)育上的傷害對其今后成長的影響是巨大且難以估量的。
與我國修改后的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相比,保護范圍上,被保護的法益不僅包括被保護人的肉體健康,同時把被保護人的心理健康也列入其中。兒童作為虐待罪的主要受害主體,相比于被保護人的肉體的健康,施虐者對受虐兒童的心理健康造成的損傷更具有潛在、延展的無法預(yù)測的危險。因此,將兒童的心理健康納入被保護的法益中合理且可行。
3.關(guān)于罪名優(yōu)化
(1)增設(shè)虐童罪的考量
每當(dāng)媒體曝光虐待兒童案,多數(shù)國民們希望刑法分則中增設(shè)虐童罪。關(guān)于是否增設(shè)虐童罪,支持者以虐待兒童零容忍為出發(fā)點,主張虐待兒童事件頻發(fā)導(dǎo)致大量的兒童遭受虐待的折磨,現(xiàn)有的罪名無法有效地規(guī)制虐待兒童犯罪,因此,支持增設(shè)虐待兒童罪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犯罪。反對者則認(rèn)為,罪名的增設(shè)不能因為國民的需求去貿(mào)然地感性立法,刑法分則中是否需要增設(shè)新的罪名需要經(jīng)過嚴(yán)謹(jǐn)?shù)耐评恚鲝埛謩t中的現(xiàn)有的罪名在虐待兒童類犯罪方面可以全面地進行規(guī)制,沒必要在刑法分則中繼續(xù)增設(shè)罪名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犯罪。
考慮到刑法體系的平衡以及罪名的概括性原則,當(dāng)下針對規(guī)制虐童類犯罪,不需要增設(shè)虐童罪。增設(shè)了虐童罪,必然會與目前現(xiàn)有的虐待罪和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有交叉沖突,反而會不能實現(xiàn)希望刑法有效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犯罪的目的,同時會造成法官在審判實踐中的混亂。刑法分則的罪名根據(jù)其所保護的法益,按照明確的規(guī)則和標(biāo)準(zhǔn)進行合理的分類,使刑法罪名體系條理清晰,系統(tǒng)化。若在刑法的罪名中增設(shè)虐童罪,將與虐待罪和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共存在刑法分則侵犯公民人身權(quán)利、民主權(quán)利一章,那么針對家庭暴力中父母或托管機構(gòu)老師虐待兒童行為,將被這三個虐待類罪名進行重復(fù)評價,并且對司法實踐的罪名選用上造成困難,造成刑法的體系冗雜失衡。
(2)將輕微傷暴力虐待兒童行為入刑
故意傷害罪、虐待罪、虐待被監(jiān)護、看護人罪都屬于刑法中保護兒童的身體健康法益的罪名。這三個罪名的立法宗旨都包含了全面多方位的保護兒童的軀體免遭侵害,但從我國目前刑法中規(guī)制虐待兒童類的犯罪來看,針對輕微傷暴力虐待兒童行為,刑法并未提供有效的保護。
我國的刑法對于嚴(yán)重虐待兒童的不法行為進行嚴(yán)厲處罰,但是畢竟當(dāng)下以極端的暴行虐待兒童的行為不是特別常見,反而是輕微傷暴力虐待兒童所占比例較大[7]。按照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若行為人對他人實施了具體的侵害行為,主觀上也持有傷害他人的態(tài)度,但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阻卻了侵害事實的發(fā)生,本應(yīng)將認(rèn)定為犯故意傷害罪的未遂犯,作為犯罪來論處。但是實際上,刑法針對這種使用暴力卻未造成侵害事實的不法行為不進行規(guī)制,而采取的是行政處罰。
這些使用暴力虐待兒童行為,雖然肉體的傷害沒有達到輕傷,但是,因為兒童作為行為對象的特殊性,虐待兒童行為對孩子們的的肉體、心理和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性都造成了特別大的傷害,不能適用成年人認(rèn)定輕傷的規(guī)則。兒童的身體承受力遠(yuǎn)低于成年人,兒童的傷害鑒定標(biāo)準(zhǔn)應(yīng)特殊化,同時,超過限度的虐待兒童行為具有法益侵害性,在對孩子造成傷害的同時還打亂了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具有刑法上的可罰性。對于此類輕微傷暴力虐童,域外很多國家或地區(qū)將此進行犯罪化處理,如上文所述日本設(shè)立了暴行罪規(guī)制那些對肉體施加暴力卻沒有達到傷害罪成立標(biāo)準(zhǔn)的虐待行為。因此,刑法可考慮將輕微傷暴力虐童入刑。
同時,大量的案件都由于孩子們?nèi)怏w受傷程度并不符合虐待類罪名的成立標(biāo)準(zhǔn),無法加以刑法規(guī)制。筆者認(rèn)為,相比于被保護人的肉體的健康,施虐者對受虐兒童的心理健康造成的損傷更具有無法預(yù)測的嚴(yán)重的危害,應(yīng)加以保護,若始終將此作為非犯罪化處理,不加以刑法規(guī)制,只會導(dǎo)致國民始終認(rèn)為虐待兒童不是犯罪。我國在遵循秩序和正義原則的同時,學(xué)習(xí)域外刑法對輕微傷暴力虐待兒童的規(guī)制,對國民的行為進行規(guī)范和指引,完善國民的法律意識,可預(yù)防輕微暴力虐待兒童的發(fā)生。其次,在虐待兒童類的犯罪主體方面,德國和我國澳門、臺灣地區(qū)刑法將家庭成員、家庭以外的未成年人都界定為犯罪主體,從而全方位地保護未滿18歲者的人身權(quán)利。
4.完善刑罰配置
(1)未遂犯的處罰
這些條文的規(guī)定將虐待兒童未遂的行為明確劃入了犯罪圈,將此行為是否構(gòu)成犯罪認(rèn)定的權(quán)力從司法領(lǐng)域劃入立法領(lǐng)域,使得司法適用更為明確,進一步強調(diào)和保護了兒童的安全和利益。
(2)明確虐童的入罪入刑標(biāo)準(zhǔn)
目前,我國的非刑事性立法,如《侵權(quán)責(zé)任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治安管理處罰法》針對虐待兒童行為都明確了相關(guān)規(guī)定。刑法與這些非刑事性立法并不對立、排斥。面對種類復(fù)雜、情節(jié)惡劣的虐童案件,刑法對虐待兒童行為進行規(guī)制,可以補強我國現(xiàn)行兒童立法體系的缺弱,全面地保護孩子們的合法權(quán)益。
(二)兒童權(quán)利邊界與最大利益
1.嚴(yán)格劃清有關(guān)兒童權(quán)利邊界
在虐待兒童行為及相關(guān)兒童犯罪的規(guī)制方面,要始終明確兒童權(quán)利保護的特點,兒童與成人權(quán)利保護的區(qū)分在于兒童特殊的年齡階段所決定的較差的認(rèn)識能力和辨認(rèn)能力、正在發(fā)展的學(xué)習(xí)能力和邏輯思維,并且重視責(zé)任人對兒童心理健康和思考方式的影響[8]。從兒童未來發(fā)展、成長及兒童作為受害人的易受侵害性的角度來看,保護兒童不應(yīng)僅關(guān)注對其生命權(quán)、健康權(quán)、性自由權(quán)、勞動權(quán)等實體權(quán)利的保護,不能認(rèn)為兒童權(quán)利保護與成人的區(qū)分僅在于保護對象的年齡上,應(yīng)重視兒童的心理健康、訴訟權(quán)利和矯治教育等方面的特殊性,在保護兒童權(quán)利時,認(rèn)清這些權(quán)利在兒童被害人犯罪中的特殊性,明確兒童與成人權(quán)利保護的差異[9]。基于此,方能正確劃定兒童保護的權(quán)利邊界,針對兒童保護制定相應(yīng)規(guī)范。
2.認(rèn)真落實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公約》未指明兒童最大利益內(nèi)涵,但實踐中我們欲全面保護兒童的利益,就需把其最大利益放在首位考慮[10],尤其是刑法規(guī)制虐童中更應(yīng)將其作為依據(jù)。通過刑法規(guī)制在事前預(yù)防虐童的發(fā)生,就顯得比事后嚴(yán)懲虐童更重要且尤為迫切。例如,基于此原則對相關(guān)法律予以修改或刪除,設(shè)置專門管理虐童風(fēng)險的全國性機構(gòu),逐步構(gòu)筑以預(yù)防虐童為主、標(biāo)本兼治、預(yù)防和救濟并重的完善法律體系。
(三)加強對權(quán)力的監(jiān)督與制約
1. 完善虐童的事前預(yù)防和配套措施
預(yù)防虐待兒童犯罪不應(yīng)只注重懲罰施虐者,還應(yīng)注重制定科學(xué)并有效的非刑事規(guī)則。美國和我國香港地區(qū)設(shè)置相關(guān)配套措施對虐待兒童進行事前預(yù)防,以刑法為主的同時輔以配套措施進行防治。我國的《未成年人保護法》中也規(guī)定了報告制度,但未詳細(xì)地規(guī)定虐待兒童報告的主體和事項,以及不舉報虐待兒童情況后所承受的后果[11]。該規(guī)定在虐待兒童的事前防范上,未充分達到救濟效果,過于籠統(tǒng)且不具有強制性。筆者認(rèn)為,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的強制報告制度和香港地區(qū)的評估制度,設(shè)立專門的維護兒童權(quán)益的機構(gòu),該部分負(fù)責(zé)針對虐待行為的評估和舉報受理等工作,出臺相應(yīng)的規(guī)定,明確受理舉報的條件,即舉報者有相當(dāng)?shù)睦碛蓱岩珊⒆泳哂性馐芫瘛⑿浴⑷怏w上的受虐待的可能性,就可以舉報,從而喚起國民保護兒童權(quán)益的意識,確保每個可能遭受或具有遭受虐待危險可能性的孩子得到保護,同時法律可以規(guī)定對具有報告義務(wù)的卻逃避的知情者負(fù)有一定的責(zé)任。同時,該部門可以進一步負(fù)責(zé)虐待行為的評估工作,其作用與功能可參照專家證人或鑒定人員,從兒童保護的角度對虐待行為的類型、范圍、程度等進行判斷,向法庭提出自己的建議,從而幫助法官認(rèn)定和判斷行為的性質(zhì)和程度。
2.積極探索完善對家庭、社區(qū)、教育或司法等相關(guān)機構(gòu)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約制度
我國社區(qū)監(jiān)督或為可行的制約方案[12]。例如,新設(shè)一個向公眾開放的有關(guān)犯罪者登記處,將為參與兒童保護的機構(gòu)或人員提供額外的避險工具,將有助于主動預(yù)防和減少虐待兒童的行為或風(fēng)險。而探索構(gòu)建社區(qū)監(jiān)督體系化的制度,可形成網(wǎng)格化、無遺漏的管理分布,以有利于統(tǒng)一管理虐童行為人在社區(qū)的情況及其流動等。
四、結(jié)語
針對在世界各國蔓延的虐童現(xiàn)象,域外相關(guān)國家或地區(qū)法治實踐經(jīng)驗豐富,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法律規(guī)范或制度機制,為我國保障兒童最大利益的刑事法治改革提供了有益啟示。為提升人權(quán)保障水平和刑事法治能力建設(shè),我國亟需汲取域外相關(guān)規(guī)制經(jīng)驗,在現(xiàn)有的刑法實踐和體制框架下,織密規(guī)制虐童的刑法網(wǎng)格、嚴(yán)格劃清有關(guān)兒童權(quán)利邊界、認(rèn)真落實兒童最大利益原則,積極探索完善對家庭、社區(qū)、教育或司法等相關(guān)機構(gòu)的權(quán)力監(jiān)督制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