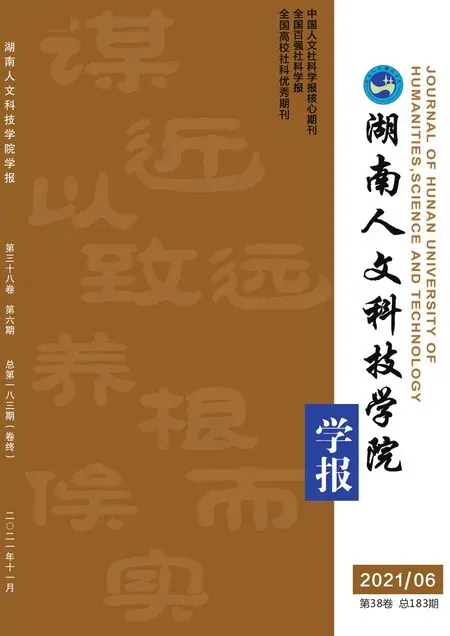意識中的故事
——論《隊列之末》的內心對話
萬正發
(1.湖南人文科技學院 外國語學院,湖南 婁底417000;2.湘潭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湖南 湘潭411105)
福特·馬多克斯·福特的四部曲小說《隊列之末》包括《有的人不》(1924)、《再無隊列》(1925)、《挺身而立》(1926)和《最后一崗》(1928)。小說的故事背景設定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前后,表現了愛德華時代文化的崩潰和新時代價值觀的痛苦呈現。小說主人公克里斯托弗·提金斯本是一位天真、睿智、保守的貴族子弟,歷經不幸的婚姻、父母的離世、謠言的攻擊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最終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沖破世俗的束縛,和女主人公瓦倫汀隱居田園。
福特被認為是小說家中的小說家,似乎他的小說是被用來研究的,而不是給普通讀者閱讀的。該小說于2012年被BBC拍成5集電視劇,但是在國內仍然沒有受到觀眾的青睞,這是為什么呢?因為,從情節上看,這部小說講的就是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之間的三角戀故事:一個英國紳士在火車上被一個富家女勾引,被迫與之成婚,婚后遭遇妻子的背叛、社會的排斥與不公等種種的不如意。經過戰爭的洗禮,他認識到生命可貴、愛情價高,于是選擇和自己喜歡的、也情投意合的女孩在一起。這樣的情節自然不夠吸引人,但這不妨礙這部小說成為偉大的著作。小說長達八百多頁,卻并沒有跌宕起伏、懸念叢生的故事情節。因為小說重點要表達的不是故事,而是主人公的意識和思想。在這種以主人公自我意識為中心的小說里,情節不再要求是具有懸念的,而是基于人物主觀性的內在發展及其對意義的追求[1]。小說敘事的重點是人物意識的發展以及他們對敘述的外部事件的主觀反應。
蘇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發現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并不是一個意識在獨白,而是眾多意識在進行對話。巴赫金認為,如果過去的小說是一種受到作者統一意識支配的獨白小說,則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的是一種“多聲部性”的小說、“全面對話”的小說,即復調小說[2]2。對復調小說來說,重要的不是主人公在世界上是什么,而首先是世界在主人公心目中是什么,他在自己心目中是什么[2]82。復調理論不能只停留在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論述中,它有更普遍的意義。在《隊列之末》中,也可以看到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發現。福特將主人公的現實,以及外界和周圍的日常生活都融入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從作者的視角轉移到了主人公的視角。
一、主人公意識的獨立性和開放性
對于復調小說的作者來說,主人公不是“他”,也不是“我”,而是不折不扣的“你”,也就是另一個貨真價實的“我”,主人公是作者與之對話的對象[2]103。小說中的主人公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看法、自己的意向性,并使用自己的個人語言。這樣,主人公在小說中獲得了自己的生活,他們成為了“他者”,一種根據其自己的聲音和自己的語言生活在敘事中的自主意識。主人公可以體現自己對世界的看法,并代表他們對世界的個人觀點。復調小說非常重視主人公的自我意識,雖然對于作者來說,主人公的意識是他人意識,但具有特殊的獨立性,這就是復調小說的意識存在方式與獨白型小說的意識存在方式最大的不同。在獨白型小說中,不同的聲音和意識,盡管表面上形式多樣,實際上都是作者意識的不同表現而已,并沒有相對獨立的地位[3]105。復調小說并不重視描寫客觀的世界,而是注重世界在主人公的意識中呈現的方式。具體地說,一切作者和敘述者對主人公的評價,主人公的自我評價,以及主人公周圍的外部世界和日常生活,都被納入到主人公的自我意識之中。概述之,整個世界都通過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呈現出來[2]85。
福特在《隊列之末》的敘述中退后一步,為小說的人物賦予獨立的聲音和空間,通過人物的意識,過濾敘述中的每個事件。無論是從小說人物的視角敘述,還是跟隨人物的意識流,他都以第三人稱寫作。即使福特仍然希望讓我們聽到他的聲音,他都會使用第三人稱總結人物的思想,而不是直接將它們呈現給我們。作者運用自由間接言語和內聚焦敘事來描繪人類意識的深度,并通過其主觀視角和現實感來表現一切。通過這些方式,他能夠向我們展示人物感知到的事件,也就是意識中的故事。
在復調小說中,意識或思想從來都不是穩定的,而是未完成的,變化的,或者說它是一個伴隨著生命活動的過程。每個觀點都在和與之對立的觀點進行無止境的對話[3]112。《隊列之末》充分發揮了對主人公的不同解釋和評價,這些解釋和評價完全是主觀的,有時甚至是相互對立的。可以說,這部小說中沒有最終的真實,因為從其他人物的角度來看,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語氣和思想都可以具有不同的意義、意圖和重要性。可見,小說中主人公的意識不僅具有獨立性,而且具有開放性。例如,小說中提金斯孩子的父親身份、提金斯父親的自殺以及母親的死因從未得到作者的確認,而僅由其他主人公的多重意識進行了廣泛討論。讀者無法獲悉這些問題的絕對或確定的答案,答案只存在于每個人物與自己進行的無止境的持續內心對話中。無論是提金斯還是他的哥哥馬克,都試圖在他們各自的自我意識中對其他人物的行為進行多次的推理和討論,以期實現最終的真實。但是,他們唯一能實現的是主觀的和個人的真實,這樣的真實只是他們所認為的真實,是他們意識中的真實故事,代表的是他們的思維方式和他們的復調性意識。
二、主人公意識的復調性
每個人的存在都是與他人的共在,“我”的生存離不開“他人”,“我”需要通過傾聽“他人”的聲音,并與“他人”對話交鋒才能實現自己的存在價值;“我”也必需借助“他人”的眼光、傾聽“他人”的評判,積極地與“他人”對話才能清晰地認識自己[4]。這里說的“我”和“他人”都是存在于主人公意識中的聲音,也就是說,在主人公的意識中通常存在相互矛盾并形成爭論與對話的不同品格。小說《隊列之末》中的每個主要人物都有機會通過內聚焦敘事以自由間接引語的形式來闡釋自我,將主人公意識中的不同品格表達出來,使主人公的自我意識呈現出兩重性,即存在“另一個自我”的“他人”與“我”進行對話。這樣,讀者在主人公的意識里,往往能聽出兩個相互爭論的聲音。例如,在第一部《有的人不》的敘事中,繼高爾夫事件之后,提金斯在杜舍門牧師家的早餐宴上又與瓦倫汀偶遇,宴后和瓦倫汀同行前往溫諾普夫人住處的途中,提金斯的內心產生了對瓦倫汀非常復雜、矛盾的情感:
他朝著溫諾普小姐的后背說:“該死,你的眼睛!讓他們責問你的貞潔吧!你為什么要在公共場合對陌生男人說話呢!……和好出身的英國男人說話,那會奪去你的貞潔的!……嗯!那就讓它被奪走好了……你被牽連的越深,我就越是一個可恥的壞蛋……”[5]108
這段用直接引語表達的內心對話反映了提金斯對瓦倫汀愛恨交加、激情與理性并存的糾結、矛盾與掙扎心理。對他來說,和自己喜歡的女孩一起散步自然是愉快的,但他又為瓦倫汀的聲譽考慮,責備她不該在公共場合主動和他這個陌生男人說話,而他的內心又是向往她和他說話的。可見,他的內心活動是多么的復雜多變、矛盾對立。再如,提金斯傷愈后重赴戰場的前夜,在是否確認與瓦倫汀的情人關系上,內心也是猶豫不決:
“我支持一夫一妻制和貞潔,所以不要提這件事。當然,如果他是個男人,想要個情人沒什么問題。再說一次,不要提這件事……”[5]281
此時提金斯的內心非常纏繞。對于是否和瓦倫汀建立情人關系,他的頭腦同時在說“要”和“不要”,兩條線攪在一起,像一首賦格的兩個主題。小說中存在多處像這樣具有矛盾性的兩個聲音甚至多個聲音的相互爭論。小說描寫主人公多重意識的目的是為了呈現各種聲音之間的對立,揭示它們的正面與反面,洞察心態中的自尊與自卑,同一情緒中的惶恐與自慰,這就是人類思想的對話本質,這種對話既包括自我的內心對話,也包括自己和他人異質思想之間的對話。
三、主人公意識的多聲部內心對話
在復調型小說里,主人公意識具有獨立性和開放性,它與作者意識構成了一種新型關系,也就是對話關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通過對人的心靈奧秘的揭示,最終是把“人身上的人”逼出來,也就是把人的尊嚴和價值、精神與心靈的全部豐富性,在這種沒有窮盡的對話中展示出來[2]343。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福特也感受到了自己時代的對話性,并發現了不同聲音之間的特殊對話關系和對話互動。他不僅呈現主要人物的觀點,而且描繪次要人物的觀點,并在這些觀點之間形成對立和對話。福特敘述的焦點是人物的內在和心理洞察力,在他的小說中,人物的自我意識通過內心對話得以呈現。因此,構成敘事的大多數對話都發生在人物的腦海中,而且很多對話都是針對人物自己的內心對話。在《隊列之末》中,人物以對話形式表達自己,他們都擁有一個對話的自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復調小說一樣,《隊列之末》的核心主題之一也是理解人類思想的對話本質。在對話的過程中,人物自由地相互展示自己,讀者只有通過對話滲透人物的個性才能獲得人物的真實生活。
在第二部《再無隊列》中,西爾維婭前往戰爭前線的法國魯昂看望提金斯時,小說的敘述由三個不同的視角重疊展開,從而突出了四部曲本身的對話性。西爾維婭交給提金斯她截留的一系列信件,其中包括她已經讀過的來自馬克的一封信。在提金斯閱讀這封信時,西爾維婭同時從記憶中復述了這封信的內容,使讀者可以從馬克、提金斯和西爾維婭的多重視角閱讀它。當西爾維婭回憶馬克的信時,讀者可以看到不同視角之間的對話,同時西爾維婭也能夠從馬克的視角來認識自己,因為信中提到了她。讀者可以一并看到馬克在信中對西爾維婭和瓦倫汀的敘述與西爾維婭對馬克敘述的反應。此外,讀者可以想象提金斯讀信時的視角,了解提金斯對信中所涉及事件的感受。在這個場景中,小說以立體的方式使三種不同的意識重疊,將不同風格和聲音的思想呈現在讀者面前。這樣,不同視角和聲音對同一事件進行評論,從而在西爾維婭的意識中形成一種內心對話。在四部曲中,某些事件會反復發生多次,每次都為復調的敘事中已經存在的意義層次增添不同的視角和意義。例如,第四部《最后一崗》又恰好代表了對先前小說事件的另一種解釋,這次的視角來自在前三部中沒有足夠空間展開敘述的次要人物,包括提金斯的哥哥馬克和他的愛人萊奧尼、瓦倫汀、西爾維婭、提金斯的兒子小馬克、老農民雇工岡寧等。
四部曲本身的核心思想是以對話為基礎的,其所表達的英國傳統道德價值崩潰、戰爭的徒勞與創傷、生活的重建等主題都是在主人公意識的多聲部內心對話中呈現的。其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提金斯和瓦倫汀之間的愛情具有思想上的對話性。提金斯對瓦倫汀的愛不是性的渴望,而是對話的向往。他想追求她,以便與她進行終生對話。因此,愛本身被描述為兩個“他者”之間的對話:
你追求一位年輕姑娘為的是能夠完成你和她的談話。要不和她住在一起,這是做不到的。而你要是不追求她,也就不能和她住在一起……這說的是那種意味著你們靈魂最終交融的親密對話。你們必須要一起等待一周、一年或者是一生,才能開始那場最終的親密對話……
事實上,那就是愛吧。[5]629
在這里,對話式交流被認為是“靈魂最終交融”,是真愛的本質。真愛不是西爾維婭式的占有和毀滅,而是瓦倫汀式的對話和責任。因此,愛情的最終宣言是與之溝通交流的欲望,與另一種意識進行終生對話,以使自己更加深入了解對方和自己,找到情感的寄托和責任的擔當,發現生活的意義。
小說中的人物甚至能意識到自己潛意識的另一個自我,同一人物的兩個自我之間展開內心對話。例如,第三部《挺身而立》中瓦倫汀意識到自己內心掙扎的意識和自我意識:
……她到底想要什么,居然連自己都不知道?她聽見自己幾乎是帶著哭腔說著,所以,很明顯,她情緒在波動:“聽我說,我反對這一切,反對我父親把我變成的這樣子!……我根本就不應該在這所學校里,我也不應該是現在這樣!”看到瓦諾斯多切特小姐迷惑的表情,她自語道:“我說這一大堆到底是為了做什么?你還以為我在試圖和這所學校脫離關系!我是這么想的嗎?”[5]534
此處瓦倫汀不僅對自己說話,還直接與另一個自我進行交談,并提出質疑。在這段文字中,瓦倫汀的無意識自我的隱藏欲望與她的理性之間發生沖突,通過這一沖突她試圖理解自己情感的本質。提金斯、瓦倫汀、西爾維婭等主要人物以及麥克馬斯特、坎皮恩將軍等次要人物都經歷了內在的心理沖突。例如,當坎皮恩將軍寫信給陸軍部長匯報關于提金斯的情況時,他發現在問及自己該做什么,就好像他在和一個陌生人或其他意識說話一樣:
寫到每句話的結尾他都在想——他帶著越來越強烈的滿足感寫著信!——他沒用來寫信的那半邊腦子在說,“我應該拿這家伙怎么辦?”或者“怎么才能確保不把那女孩的名字攪進這一團糟里?”[5]464
坎皮恩將軍不僅直接向自己講話,而且似乎也受到了他的思想分裂的影響。 另一種思想,不是他的意識和理性的思想,而是他無法控制的思想介入并直接質疑他。此外,像瓦倫汀一樣,提金斯也意識到自己在內部對話中展開的雙重自我和內心掙扎:他對自己喊著,“老天有眼!這是癲癇嗎?”他祈禱著,“上帝保佑的圣人,救我出去吧!”他喊著,“不,這不是!我完全可以控制我的頭腦。我最重要的頭腦。”[5]494小說多處可見提金斯的內心矛盾、分裂的心態和永無止境的自我分析,這些自我分析以自我對話的方式表達出來。提金斯意識到自己思想的雙重性,同時用對話的方式對自己說話。
有時,人物還會考慮和評價不在場的其他人物的言語和思想,這些不同的思想在人物的意識中形成沖突和對話。在第二部《再無隊列》中,提金斯的妻子西爾維婭就經常和另一個自我以及已經死去了的康賽特神父進行多聲部對話:
西爾維婭心中泛起種種情緒……在提金斯的身邊,她對自己說:“會永遠這么下去嗎?”……她說:“神父!你曾經很喜歡克里斯托弗,讓圣母幫助我克服吧。這會毀了他,也會毀了我。但是,噢,該死的,別這樣!因為這是我生存的全部意義。”[5]400
上述西爾維婭和康賽特神父之間的對話是在西爾維婭的腦海中發生,康賽特神父不僅不在現場,而且已經不在人世。但是,西爾維婭與死去的神父之間建立了真實的對話,理所當然地考慮了他的思想和他對提金斯的立場,這樣就并不需要神父的實際在場。這樣的對話通常是在兩個以上的意識之間發生:人物、另一個自我以及其他人物的視角。而且,多聲部對話性敘事彌補了人物之間缺乏交流的缺陷,而這種想象的交流在小說中建立了一種新型的對話,即主人公意識的多聲部內心對話。
四、結語
福特小說《隊列之末》的貢獻不限于印象主義、時間轉移、內聚焦敘事等十分現代的手法,還在于其呈現了對話性對立的多種聲音、視角和觀點,體現了人類思維和思想的對話本質。福特使小說人物擺脫了作者的控制和判斷,并使他們的聲音和意識完全獨立。《隊列之末》并不關注懸疑的情節,而是人物意識的發展以及他們對敘述的外部事件的主觀反應。通過對人類意識的本質以及對意義、自我分析和內省的本體追求,人物的聲音和意識在不斷對話的過程中呈現出來。對話的方式不是對白,也不是獨白,而是通過有意識和無意識自我之間的內心對話來表達自我,充分展現了人物性格的復合性。人物內心的多聲部對話本質啟發我們觀察以其他意識作為鏡像反映的自我,不僅在社會現實中也在自我意識中與“他者”展開充分對話,尊重他人的差異和個性,而不是將自己的動機、理由和感覺歸因于他者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