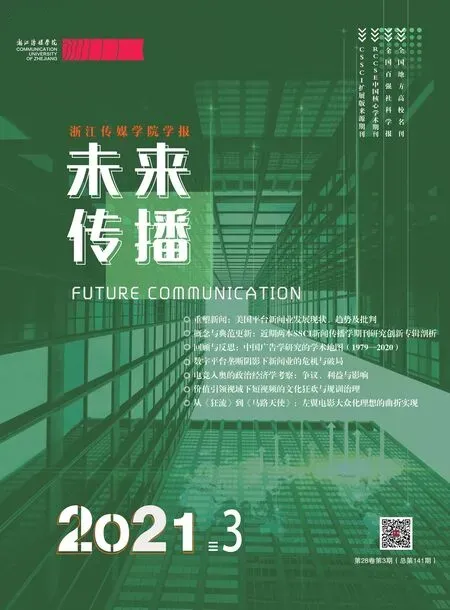作為哲學的影像空間:電影《暴雪將至》中的“異托邦”建構
王 健
(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福建福州350117)
福柯的“異托邦”空間理論對外部真實空間進行了“差異地學”研究,在他看來,客觀存在的空間未必就是唯一的、最本質的空間,空間之外仍然存在斷裂性、顛覆性、差異性的“異托邦”。在這個特殊的空間形態中,社會文化常態、權力關系被顛覆,中心價值也被解體,主體陷入了一種失語的狀態。因此,“異托邦”往往呈現出的是一個異類的、被漠視和遺忘的文化現象。福柯認為:“在所有文化中,在所有文明中,都存在著這樣一些真實的場所、有效的場所,它們被書寫入社會體制自身內,它們是一種反位所的場所,它們是被實際實現了的烏托邦。”[1]也就是說,這個另類空間是真實存在的,是一種與主流文化價值和社會秩序對立的基地。
電影《暴雪將至》將時間的坐標定位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變革的轉型期,在此期間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引發了一系列社會矛盾,因此,這一特殊的時間節點所帶來的不穩定性和危險性,使得影像文本中的現實空間呈現出一種與現實文化話語相抗衡的“異托邦”特質。無論是陰冷潮濕的雨天街道還是行將拆除的國有工廠都構成了一種“異質—對抗”的空間關系,空間成為影片生成意義的一個重要符號表征。《暴雪將至》作為一部集犯罪與懸疑、推理為一體的類型片,雖然延續了傳統類型片的敘事邏輯,正如布雷蒙所分析概括的“敘事序列”:“可能性”(欲望、需要等)——“采取行動”——“行動結果”[2],但是,在設置情節、揭示懸念、匯聚外部張力的同時,影片更注重對社會空間內人物的行為動機進行闡釋,“可能性”成為敘事環節中最重要的矢量。而恰恰正是這一“異質空間”(瀕臨拆除的工廠、泥濘骯臟的案發現場、不斷游動的警車等)源源不斷地產生著沖突與對抗,使得主體被迫參與到事件的進程中,構成了影片傾向于社會批判的文本建構邏輯。
另外,基于電影中的現實社會空間,經由敘事的表意功能、影像符號的意涵指涉,使得空間內部發生畸變,并宣告與日常生活經驗下的現實空間決裂,第二道的“異質空間”由此生成。但是這個空間是一種心理補償式的、幻覺性的“異托邦”,是異質的影像內部的文本空間。例如片中余國偉作為勞模站在主席臺上慷慨陳詞,但是時隔多年,卻被告知當年從未舉辦過所謂的“表彰大會”,導演無意告訴觀眾真相,而是將“真與假”并置在了一個開放性的系統內,營建出一種“去年在馬里昂巴德式”的內心世界,虛構與真實、時間與空間的常規秩序被顛倒,一個異類的、具有象征意味的文本空間被建構起來。
綜上,影片共指涉了兩種“異托邦”。第一種是功能性的物理空間也就是電影文本中呈現的現實空間,作為被劃定為反常態的真實位所,直接參與到敘事流程中成為故事發生的真實場景,或者從視聽表征層面上構成聲畫系統從而連接成電影整體;第二種是敘事流程本身所構成的文本空間,亨廷頓認為:“異質空間存在于空間之間,在空間的關系之中。”[3]電影中的現實空間與文本空間在功能層面發生關聯,前者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景觀,所表露出的意識形態被凝聚在了影像的文本內;后者文本空間成為電影中現實空間建模的依據和參照。因此,這兩種同為“異位”的空間是辯證的、耦合的,現實空間側重于文化地理學的范疇,強調空間地理本身的特質,而影像的文本空間則是一種符號化的隱喻意指。
下文將進一步厘清電影中“異托邦”的建構邏輯,并結合《暴雪將至》文本本身去分析影片中異質化的現實空間與文本空間、電影敘事與空間的關聯,從而去論證電影中異質空間的文化指涉功用。
一、 “異托邦”的建構邏輯:現實主義與“吸引力電影”
近年來,以電影《鋼的琴》《白日焰火》《地久天長》為代表的一系列根植于本土文化語境、反映中國社會現實癥候的國產影片引發了國內廣泛的關注和討論。這類題材的影片通常將故事的背景定位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中,這個時間節點所呈現出的嬗變與疏離使得影像文本趨于一種對記憶與想象的解讀,是一種對“無意識”的表述。“人與空間”的關系成為影像文本的建構邏輯,從而在異質、變異的空間中生成主體的生命體驗,并且通過隱喻、象征的意義闡釋其對社會現實的思考。
分析這類影片的共性,很容易將它們歸納到具有一定社會批判傾向的現實主義電影行列,《暴雪將至》所反映的便是在中國社會轉型期中,工人所面臨的主體身份危機和生存困境,影片中呈現的現實空間在不斷變革的社會進程中是滯后的、另類的,攝影機在廢棄的工廠、泥濘的街道上游移。也正如當年意大利新現實主義提出的主張——“到街頭去”,因為空間社區本身的物質性就使其被賦予了某種真實的、現實的意義,這種鏡頭下的“異質空間”也恰恰符合主體在主流社會秩序中所面臨的處境。凱文·林奇指出:“似乎任何一個城市,都存在一個由許多人意象復合而成的公眾意象,或者說是一系列的公共意象,其中每一個都反映了相當一些市民的意象。”[4]因此,現實空間直接指涉的是個體和群體在日常生活中真實的感知、體驗和記憶,它同時也覆蓋了整個權力、知識體系下的社會關系,成為現實主義電影中一個概括的、綜合的重要組成因素,而電影中異質的城市空間作為常規秩序的對立面也使得現實主義更具有社會批判意義。
將“異質空間”與“現實主義”并置的原因在于,首先現實主義電影的認識論是感知與物質現實的同一性,而其本身的文化性使之具有一種人道主義的社會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場。羅西里尼指出:“電影應當成為一種同其他手段相同的手段,它也可能比其他手段更為有用,用它來譜寫歷史,留下正在消失的社會痕跡。”[5]現實主義電影將視線投射在被排斥和被禁止的對象上,去觀照秩序之外的空間里的邊緣人群,這一點與福柯所描述的異質空間是契合的。福柯指出:“有一些特權性的或神圣的或禁忌的場所,它們服務于那些處在與其所生活的社會和人類背景相關的危機狀態中的個體,諸如青春期的男女、排經期的婦女、老人等等。”[6]在異質空間中,這些特殊的人群在社會實踐中被聯系在了一起,也正如福柯分析“異托邦”的多樣性形態時提出的危機異位和偏離,現實主義電影中所建構的也正是這種危機、另類的“異托邦”。例如在電影《鋼的琴》的開始,主人公組建的樂隊正在追悼會上演奏挽歌,而畫面的后景儼然就是工廠冒煙的煙囪,它暗含了一種曖昧的、隱喻的空間指涉,而架構起全片主要矛盾的也正是國企改革背景下小人物所面臨的生存困境,空間成為影片中重要的意指符號。
電影中“異托邦”的建構邏輯遵循的是福柯對于社會歷史進程中的“斷裂”所做的思考,福柯認為:“在一個社會的歷史中,這個社會能夠以一種迥然不同的方式使存在的和不斷存在的‘異托邦’發揮作用;因為在社會的內部,每個‘異托邦’都有明確的、 一定的作用。”[7]這里所指涉的“異托邦”就是由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斷裂”所造成的,例如影片中的廠房、煙囪等異質空間,它們象征的是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的陣痛,具有明顯的社會歷史屬性,是作為社會歷史中“斷裂”而存在的。包括《暴雪將至》《地久天長》《三峽好人》在內的現實主義電影,它們關注的都是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生存境遇,遵循的是一種小寫的歷史觀,這一點與福柯的“異托邦”理論是相似的,他并不拒絕關注社會的連續性,但這種“大歷史”的前提必須是基于“斷裂”。從這一點來說,福柯對于“斷裂”“邊緣”的關注恰恰是與《暴雪將至》的時代主題相契合的,這也使得影片中的現實空間具有了內部的意義,它不再是單純的現實物理空間,更是連接著社會歷史的“異托邦”。福柯的“異托邦”理論之所以與電影具有同構性,是因為在福柯看來沒有一種文化不生產異質空間。那么作為文化的電影,同樣是在生產異質空間,這也由此構成了電影《暴雪將至》的“異托邦”建構邏輯,并且作為哲學的影像空間也為電影的本體研究提供了思路。
回到電影文本本身,主人公余國偉作為一名編制外的工廠保衛科協查人員一心想借“連環殺人案”展現自己的才能,從而破格進入到體制內成為一名真正的警察,“編制”構成了空間內部的權力關系,因為“編制”在中國社會生態里象征著話語權,它使得主體在身份上擁有某種合法性。在影片空間的建構中就被嵌入了這層權力關系——例如案發現場反復游動的警車,作為一個封閉的禁區,它對外界是排斥的,是暴力、霸權的象征,人們是無法自由進入的,片中余國偉多次鉆入警車,以體驗和享受短暫的“編制內”快感來獲得心理補償。但是,工廠、街道所呈現出的卻是另一種“編制外”的末日景觀,這兩種空間在影像文本中并置、疊加,權力沖突和社會矛盾在其中也由此被表露出來。我們生活在一組關系之中,這些關系確定不同的基地, 且彼此之間不可跨越, 更不相重疊,所以空間要經由關系而確定。[8]因此,也正是這兩種極端的、各自對立的場域所表征出的空間關系建構起了這個象征權力沖突和社會矛盾、充滿怪異與荒謬的“異托邦”。
可以得出結論,在這幾部影片中,“空間”以獨具個性的面貌傳遞著某種意識形態話語,經由電影語言在視覺和聽覺層面上的整合,形成了風格化的或者是奇觀化的“吸引力電影”。“吸引力電影”是早期的電影觀念,“這種觀念就是不把電影看作一種講故事的方式,而是看作向觀眾呈現一系列景觀的方式,因為電影所制造的幻覺力量和異國情調可以讓觀眾為之著迷”[9]。之所以將它們稱之為“吸引力電影”,是因為盡管這幾部影片被打上的標簽是情節劇,但是電影空間的指涉意義是大于情節本身的,是空間中的異質,偏離建構起了電影的敘事系統。例如,《暴雪將至》的敘述邏輯并非是遵照情節線索找出殺人兇手,而是傾向對“誰造就了兇手”進行社會推理,強調社會背景的“催化”作用,以此來分析在這一“異托邦”中人的異化過程,空間就成了一種“無形的力量”,隱喻與象征都被隱藏在了空間的視覺效果中,敘事對于觀眾而言就不再僅僅是靠外部的情節張力來推動,更多的是依賴觀眾在空間內部進行感知上的探索。
電影《暴雪將至》中的“異托邦”建構方式具體是從兩方面進行的。一方面是從“作者論”角度,在影像空間的建構上鑲嵌了電影作者的世界觀和哲學觀,由素材以及個人的創造力和執行力去生成現實空間的內部意義,就像上文列舉的電影《鋼的琴》,它傳達出的同樣是現實主義精神。另一方面是從“觀眾認知學”層面,電影中異質空間作為一種刺激性、奇觀化的視覺效果,會與觀眾產生凝視與敘事上的關聯,是觀眾心理決定了電影敘事意義的生成,是觀眾的知識建構起了敘事流程本身所構成的文本空間。此部分的論述旨在揭示電影中的“異質空間”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作者與觀察者在情緒上共同合力的結果。這不僅有助于下文對《暴雪將至》在空間建構上進行美學與敘事分析,也有助于發掘觀眾心理在潛意識狀態下對空間所產生的感知與理解,這是一種對空間符號的解碼與破譯進入到第二重文本的方法論。
二、“異托邦”的空間敘事:漫游與觀察
“都市漫游者”一詞最早在19世紀由波德萊爾提出,他認為漫游者是都市現代性的產物,他們在人群中不斷張望、游蕩,并以此為武器去對抗資本主義的“異化”。本雅明在此基礎上認為,“漫游者”是在都市環境下衍生出來并具有一種社會批判意識的特殊人群。一方面,漫游者與空間是一個永恒的關系,是一群危險和偏離的個體在現代性的城市經驗中以游動的視點去感知現實空間的真理游戲;另一方面,漫游者行走與凝視的漫游過程本身就構成了一種作為敘事策略的話語,是通過漫游者的敘事視角生成了文本空間。
(一)漫游者與空間:感知、體驗
在福柯看來,“異托邦”并非一個純粹的空間概念,而是聯系著社會實踐中某些特殊的人和事。[10]《暴雪將至》在人物設定上將一些與時代相悖的、處于危機狀態的人置身于文本空間內,他們之中有保衛科科長、娼妓、下崗工人,還有行將退休的老警察,他們都是以一個“漫游者”的身份,穿梭在這個另類的、排他的空間中,包括視覺隱喻下具有時代特色的筒子樓、舊工廠、理發店、舞廳,這些空間都凝聚了令人在感知、身份、欲望上產生情感的事物,譬如男子失業導致情緒失常捅死妻子、工廠在爆破中被拆除以及舞池里男女相擁,寓意著在轉型的“末日”到來前,一群危機個體在“抱團取暖”,這個異質空間所蘊含的危險性符號,都經由漫游者游動觀察的視點生成了一種“漫游者”與空間緊密聯系的文本機制,即以人物為視點,去探索可感的社會空間。
《暴雪將至》塑造了一個“唐吉訶德”式的漫游者形象,余國偉作為一名體制以外的保衛科干事,時常沉湎于自己“余神探”這個稱謂中,試圖以一己之力去偵破案件,從而進入警察編制內。他就像堂吉訶德一樣,在理想與現實之間,試圖用一種英雄主義的“騎士精神”去挑戰現有的秩序。因此,余國偉本人就構成了一個“異托邦”,他同時構成了一個兩種文化與話語并置的斷裂帶。在這個歷史時期的界限中,余國偉試圖從被他者主導的話語體系中抽離,進入到權力體制下的國家機器中去,即使對“殺人案”的偵查并非他的職責所在,他也盡心盡責,將被納入警察編制的希望寄托于對此案的偵破,日常中的一舉一動也儼然一副警察的模樣,他手持警棍手銬,隨時暴力執法,也正是通過自身建構起的心理補償與幻覺空間來表達其對當下處境的抵抗,一種文本意義上的反諷油然而生。余國偉本身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符號,導演嘗試通過對空間環境的營造去建立起主體之間的關聯,以證實世界是一種符號的“相似性”存在,貫穿全片連綿不斷的雨水、廣播中對“大雪”的預報,都將來自于大自然的“風暴”指向了大環境中所有人的命運,這種詩意的空間意象隱喻了社會“風暴”下的“命運共同體”,他們每個人都是漫游者,是空間的中介者和反思者。
“漫游者”作為一個解讀現代性空間的符號指向,在影片中它們都是以一種批判的、流動性的眼光去審視城市空間中的現代性癥候的,并且在現代化進程中,用自己的思考方式對空間進行破壞和重建。
(二)漫游者與敘事:斷裂、風格
漫游者作為敘事主體,為影片提供了一個異于常態的、與“英雄神話式”崇高美學相悖的敘事視角來實現對現實空間的重新認識;而作為敘事客體,漫游過程同樣也構成了以漫游者為中心的敘事策略,空間內潛在價值與隱喻意義也經由這種敘事思維被發掘出來。下面將闡述《暴雪將至》的敘事策略并分析與之相匹配的影像風格,因為文本空間的建構也正是敘事與視聽要素高度統一的結果。
《暴雪將至》在敘事模式上呈現出一種斷裂的特質,這主要體現在故事的結構、情節的組織、事件的貫通上突然出現了某種“意圖性”的畸變,即表層的敘事指向由外部張力作用下的“邏輯推理”邁入展示主體內心思想“異化”流程的“社會推理”,情節動力驟然地被置換為“心理沖擊力”。這種敘事策略所產生的裂隙,使得影片具有了兩種敘事模式沖撞后才能迸發出的“異質”景觀;而這一“異質”景觀也使得影片突破、超越了類型電影的“敘事神話”,轉向一種觸發觀眾深層次思考的“介入式”“沉浸式”的電影哲學觀。另外,經由導演創造的視聽感知空間,無論是鏡頭語言還是聲、光、環境共同作用下所產生的空間壓迫感,都將觀眾對影片的認識納入人物和環境的整體觀范疇中,使之成為一種貫徹導演敘事意圖的重要“環境張力”。
作為導演董越的處女作,《暴雪將至》無論是情節的設置,還是節奏的把握、視聽的構思都是一部完成度極高的作品。但是,導演無意只是通過敘事來呈現事件,而是更重視文本所產生的語境,使意義大于事件本身。整部影片都圍繞著“追兇”來鋪陳情節。“欲望”作為驅動文本發展的動力機制使得主人公余國偉迫切想通過偵破此案來獲得認同感,這種敘事的邏輯似乎更接近一種近似“存在主義”的表述,一種主體對自我存在價值的找尋,并在這一進程中自己將自己異化。余國偉的探案過程,也正是他“異化”的過程,為了引誘罪犯,他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愛人燕子,他的徒弟小劉也因他而死,這種近乎病態的渴望使他自己也變成了一名親手葬送兩條人命的“作惡兇徒”。影片的前半部分,充滿了探案過程中的對抗和沖突,余國偉在這一敘事序列中充分展示了自己獨到的探案才能,案件經由他的視點變得撲朔迷離,謎底也漸次被揭開,情節所蘊含的豐富信息量使影片節奏緊張而富有張力。從余國偉指導徒弟模擬案發現場尋找線索到工廠追兇,劇情的發展在環環相扣中不斷向前推進,輔之以影像中的雨水、泥土、建筑所呈現出的質感,在觀眾看來故事似乎要被推向“白熱化”。
但是峰回路轉,敘事結構由于徒弟小劉在追兇過程中的死亡發生了斷裂,兇手的逃脫使得余國偉對案件的偵查陷入了停滯,這個意外性干擾因素使影片后半部分的敘事強度被削弱,進而轉向了一種趨于靜態的內心寫實,敘事的重心也由快節奏的“推理”“懸疑”位移到克制的情緒化表達上去,余國偉病態的欲望與燕子得知自己其實是誘餌的絕望,共同構成了后半部分的情緒張力,一種人物與空間呈現出的“異化”關系被凸顯出來。也正是由于“情節張力”到“情緒張力”的變異,使得外力作用下的敘事調性轉入體驗和反思個體內心矛盾中去,影片背后深層的思想也由此得以釋放。
漫游者在漫游和觀察中與現實空間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即便這個空間浸染了主流的權力秩序,漫游者依然可以在此過程中通過注入某些話語策略來開拓屬于自己的空間,現實空間的“異質”特征也由此被表述出來。譬如,片中“警車”只是一個實質的空間片段,但在余國偉看來則是一個象征了權力與話語的、具有幻覺性質的“異托邦”。另外,通過畸變、斷裂的敘事策略去發掘文本背后的社會倫理價值,這種以漫游者為敘事視角的實踐方式直接構成了“異質”的文本空間,從而得出結論:異質空間在某種意義上,是相對弱勢者的社會實踐在主流社會的宏大敘事所建構的空間中造就的空間斷裂帶。[11]
三、“異托邦”的空間隱喻:廢墟與寓言
我們在全文中不斷地將福柯的哲學思想落實到具體的影片中去分析,不是為了將其規約為一篇電影批評性質的文章,而是運用一種實證性策略,來論證福柯提出的“異托邦”概念在電影研究中具有的理論價值。在下文,我們會把《暴雪將至》中所呈現的“異托邦”空間形態歸納為一種符號意義上的“廢墟”,以期在符號的意指功能中,窺見偏離、荒涼的物質碎片背后所潛藏的寓意和象征,并在隱喻的意義和觀眾的經驗意義上進入到影像深層的第二重文本。作為以影像化表達為基礎的藝術,電影意象是真實性、假定性、象征性與隱喻性的統一。[12]因此,對于電影而言,表層的空間影像遠非只是被作為一種敘事功能的物質載體,同樣也是一種散發著社會文化性、具有深層指涉作用的表意圖像。
電影透過文本的表層結構將不同的物質場景加以整合和重建,使之具有了一種隱匿的影像修辭。例如,影片中的工廠、鐵路、街道本身是毫無意義的物質載體,但是如果將這些空間在敘事流程中并置和疊加,讓彼此間產生聯系,那么這個重構的空間身上的意涵就能夠被激活。福柯認為,“異托邦”有權力將幾個相互間不能并存的空間和場地并置為一個真實的地方。[7](55)就他的觀點而言,“異托邦”表達了一種一般空間所沒能反映出來的文化意指,它的定位應該是并置和疊加,是在不同場所的并置和疊加中構成象征符號系統。福柯舉了個例子,認為“花園”就是帶有復雜疊加意義的異位,“波斯人的傳統花園是一個神圣的空間,在它的長方形內部, 應該集中四個部分, 代表世界的四個部分”[7](56)。所以,影片中“異托邦”的本質實則就是類似于“花園”一樣的理念凝結體,是被組建的整一性意識形態載體,換言之,工廠、街道、鐵路這些景觀的疊加構成了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正是歷史過渡時期的縮影。我們可以將這個異質的“世界”歸納為本雅明口中的“廢墟”。
本雅明在《德國悲劇的起源》中論述了巴洛克悲悼劇里所充斥著的廢墟意象,他把“廢墟”作為一種形而上的對象,它代表在整體意義上的崩塌,而以破碎的“寓言體”來表述,用“寓言”的方式來表達“廢墟”的存在。[13]“廢墟”在建筑學意義上指的是建筑物在遭受破壞后的剩余物,但是,從文化研究的立場來看,“廢墟”是一個抽象概念,象征著一個時代消逝的衰亡意象,它代表的是同一位所的文化遷移。在《暴雪將至》中隨處可見的廢墟景觀,暗含了歷史行程中的不同意義和價值觀,或者是不同的歷史的運作狀態,在時代更迭的夾縫中,它就構成了一種既象征著衰亡又象征著新生的“異托邦”。導演通過引入一件猶如寓言般荒謬的“兇殺案”,來打破“舊秩序滅亡,新秩序建立”的和諧統一模式,從而穿透人性深層去暴露社會轉型期中人的異化和疏離,并借助“廢墟”來表現社會變革下主體文化身份認同的困境。在這個怪誕離奇的“兇殺案”中,探案者、殺人者、受害者似乎都無法跳脫出宿命論的桎梏,就像余國偉不僅是探案者也是間接殺人的“兇手”,這就是寓言中典型的異化邏輯,以一種“不可理喻”的姿態來達成反諷與玩味之感。
故此,電影中“廢墟”與“寓言”的關系,可以得出一個推斷:“寓言”用“言此及彼”的策略來展現“廢墟”的狀態;而“廢墟”則用一種時間的批判性分析將過去與現在聯系在一起,從而生成一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隱喻和寓意。
《暴雪將至》中的“廢墟”景觀作為體現影片特質的重要元素,它通過象征這個時代衰亡的社會意象來透視人的生存狀態,用荒蕪、破碎的空間碎片來表現疏離、偏執的“寓言體”。影片為展現人物與環境的關系使用了大量具有縱深感的中景構圖,將空間重新組織和編碼,使得人物的生命體驗與現實物象緊密地維系在一起,構成了一種新的意涵系統。首先,“人”作為時代危機下的個體,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異質空間”,攝影機將之投射到空間意象中便構成了一種兩重空間的“合成”效果,巧妙地指代了兩個空間的生態關系,由此迸發出強烈的超乎聲畫組合意義的深層心理認知。其次,這種“合成”效果的主旨不再僅僅是為了呈現故事,而是經由這種共時性關系來強調空間自身的表現力,觀眾可以在這種被稱為“空間蒙太奇”的并置影像中汲取更多信息,從而通過某種價值尺度對之進行思考和評說。在電影的開始部分有一組鏡頭,余國偉出獄后行走在殘破的圍墻邊緣,他扭過頭將視線聚焦到了過去的自己:一輛摩托車在攝影機的注視下駛過圍墻,隨后視野開闊起來,摩托車與廢舊的工廠景觀逐漸融為一體。這種模糊了現在與過去界限的“合成”方式,既是時間的延伸,也是空間的轉換,在詩意化的視覺意象呈現中,凸顯了“廢墟”所具有的隱喻和寓意指征,對人與空間關系的思考由此也成為貫穿整部影片的問題域。
本部分引入“廢墟”與“寓言”這兩個概念,旨在強調一種用意識、注意、感性的方式去提煉影像中本質理念的方法論,而“廢墟”與“寓言”指涉的也正是本質化的空間隱喻,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影片開頭的片段,用一種“空間蒙太奇”的感知方式來領會“廢墟”傳達的理念。這是一種類似于柏格森的直覺主義觀點,這種無意識的思維定式,將影像表征的外在聯系和客觀聯系轉向內在的深層意旨。一方面,“廢墟”是從影片中現實空間里抽象出的概念,它已然超出了空間地理的范疇,是理念的凝聚;另一方面,“寓言”實則就是文本空間的敘事邏輯,是一種包含了象征、隱喻的意指方式,兩者在電影文本中互滲、交織,終極意義下的空間隱喻由此生成,一道“異托邦”之門緩緩開啟。
四、結 語
《暴雪將至》這部電影用一種歷史的敘述去思考權力與知識的關系,影片通過描寫社會轉型期中主體的身份危機,來營建出一個昔日的主流話語被邊緣和禁止后所產生的“斷層”和“差異”,也就是福柯所提出的“異托邦”。這個異質空間帶有明顯的批判性,是對主流意識形態下歷史書寫的消解,它強調少數、邊緣人群的歷史經驗,在對現實的表述和敘事中,蘊含著大量的異質元素和策略,由此構成了影片的“異托邦”空間形式:首先表現在影像中具有特殊文化意味的現實空間;其次是經由敘事策略對客觀世界進行的重塑形成的文本空間,并在此基礎上升華到空間隱喻形式即“廢墟”與“寓言”。這條線索同時也構成了文章的行文邏輯,即先分析電影中“異托邦”的建構邏輯,再深入到文本中闡釋“異托邦”在影片中的實踐方式,最后從空間實踐中深化出深層的符號隱喻意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