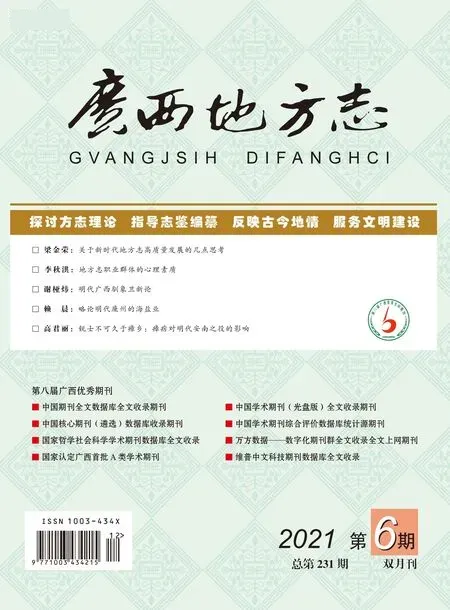明代廣西馴象衛新論
謝椏煒
(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 廣西 南寧 530006)
中國是亞洲象的重要分布地,古代中國人很早就開始了馴象活動。《呂氏春秋·古樂》記載:“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說明至遲在商代,中國人就已經開展了馴象活動。宋代首設養象所,象儀列為大駕鹵簿的最前列[1]。至明代,受氣候變遷和人為因素的影響,野象僅在嶺南西部及云南等地有分布。明太祖朱元璋設置馴象衛,以捕捉、馴化、進貢野象。對于馴象衛,已有學者對其進行探究,但在具體的設置時間、初設時的功能及其轉變等問題上仍然存在爭議。劉祥學的《明代馴象衛考論》[2]一文,詳細分析了馴象衛的建置沿革、遷移原因、職能演變、防區及地位演變,但其中有些觀點卻缺乏史料支撐,略顯片面。其他學者都是在研究廣西衛所制度時稍微涉及馴象衛,內容較為簡略,范植清《明代廣西衛所的設置與遷徙》[3]一文即是如此。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有關爭議問題進行梳理,并進行相關論證,以求教于方家。
一、馴象衛設置時間考證
至正二十七年(1367),朱元璋派湖廣行省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攻取廣西。洪武元年(1368)七月,“廖永忠下象州,廣西平”[4]。十一月,朱元璋派遣中書省照磨蘭以權“赍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溪洞官民”,為保障安全,特派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戶劉惟善率兵護送,在護送的過程中擊敗了當地首領潘宗富,“兩江之民,由是懾服”[5]。為了鞏固明朝在廣西的統治,從洪武元年開始,明朝政府在廣西設置了一系列衛所,且對廣西的行政區劃做了調整,“元置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治靜江路,屬湖廣行中書省。至正末,改宣慰使司為廣西等處行中書省。洪武二年三月因之。六年四月置廣西都衛,與行中書省同治。八年十月改都衛為都指揮使司。九年六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6]。明中后期,又設置了廣西總兵官和兩廣總督。明代廣西共設置10衛22所,包括19個守御千戶所、1個軍民千戶所、2個屯田千戶所[7]。
洪武前期,明廷在廣西設置的衛所已經初具規模,但其主要分布在桂東,至于少數民族聚居的桂西,則多是土官治理,僅邊緣有幾個衛所。為了加強對桂西的控制,明廷在桂西地區陸續設立衛所,馴象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設立的。對于馴象衛的具體設立時間,《明實錄》中未有明確記載,只能根據現有史料進行推測。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十九年八月丙戌,命營陽侯楊通、靖寧侯葉升領兵捕象于廣西左江之十萬山。”[8]可知馴象衛至遲在洪武十九年(1386)已經設立。永樂年間,解縉在《知思明府黃公神道碑》中寫道:“后十八年為洪武丙寅,十萬山象出害民稼穡,詔兩通侯率兵二萬余驅而捕之,建立馴象衛。”[9]洪武丙寅即洪武十九年。清乾隆年間所修《橫州志》同樣記載道:“馴象衛,明洪武十九年置于思明府。”[10]范植清等持此觀點,但劉祥學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嘉慶年間謝啟昆所修《廣西通志》卷93《輿地略十四·物產五·太平府》先是記載“洪武十八年,十萬山象出害稼,命南通侯率兵二萬驅捕,立馴象衛于郡”,后又記載“洪武十九年,置衛于思明府鳳凰山”,所列的時間、地點前后矛盾,而且根據《明史》所載洪武朝封侯中未見“南通侯”,故認為謝志不可靠;而嘉靖《南寧府志》記載洪武十二年(1379),“移軍上思州鳳凰山駐扎,取交趾象,因名”,嘉靖年間距離洪武時期較近,故可信度更高[11]。范玉春認同這個推論,并在《明代廣西衛所的建置沿革及其時空特征》一文中進行引用[12]。
但是劉祥學的論證依然存在問題。首先,嘉慶《廣西通志》中出現了《明史》中未出現的“南通侯”,并不一定是所撰內容不可靠,也可能是在抄寫資料時出現筆誤。對比嘉慶《廣西通志》有關馴象衛的內容和上文解縉所撰碑文的內容,可以看出二者在文字表達上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嘉慶《廣西通志》很有可能參考了解縉碑文的內容,那么“南通侯”也有了相應的合理解釋——它是解縉碑文里“兩通侯”的誤寫,而解縉碑文里的“兩通侯”是指《明太祖實錄》中的營陽侯和靖寧侯,這種推論應是符合邏輯的,故而劉祥學僅憑此點認為嘉慶《廣西通志》的記載不可靠顯得過于武斷。其次,雖然嘉靖《南寧府志》的確有關于洪武十二年捕象的記載,但并不能因為嘉靖年間距離洪武時期較近而認為其更具有可信度,從而忽略對其他史料相關內容的參考比對,例如永樂年間的解縉碑文。再次,針對劉祥學認為嘉慶《廣西通志》記載的時間、地點前后矛盾的問題,筆者認為并不矛盾,一是洪武十八年出兵捕象在前,洪武十九年設立馴象衛在后,中間有一個時間差很正常;二是思明府是土府,太平府是流府,土府需接受流府的管轄,因此謝啟昆在“太平府”條下記載“立馴象衛于郡”與后面說“置衛于思明府鳳凰山”,并未構成實質上的矛盾。此外,劉祥學通過洪武十二年朱元璋調整廣西衛所、試圖加強桂林的統治力量來說明此時設置馴象衛的合理性,認為它反映了朱元璋加強對桂西統治的需求[13]。但從地圖上看,思明府處于廣西的西南邊陲,與東北部的桂林相去甚遠,并無明確史料證明馴象衛的設置與加強對桂林的統治存在關系。另外,劉祥學僅以嘉慶《廣西通志》的錯誤就認為其不可靠,進而直接否定“馴象衛于洪武十九年設置”這個觀點,忽視了《明太祖實錄》、乾隆《橫州志》等眾多史料的相關記載,顯得有些片面。最后,針對劉祥學引用嘉靖《南寧府志》關于洪武十二年“移軍上思州鳳凰山駐扎,取交趾象,因名”的記載,《明史》中卻有不同的內容:“上思州(元屬思明路),洪武初廢。二十一年正月復置,屬思明府。”[14]洪武初年上思州即被廢除,直到洪武二十一年才復置,可見洪武十二年時上思州并不存在,故劉祥學引用嘉靖《南寧府志》的記載并不準確,以此為證據推論出洪武十二年置馴象衛的說法也存疑。相對而言,馴象衛于洪武十九年置于思明府的說法更為可信。
除了上述兩種設立時間,《大明統一志》記載:“馴象衛,橫州治東,洪武二十一年建。”[15]王彤在《中國歷史時期馴象的區域變遷初探》一文中引用了該說法[16]。但是根據史料,這并非始設馴象衛,而是將馴象衛遷往橫州。洪武二十一年(1388),“復置馴象衛指揮使司于廣西龍州之左江”[17],同年七月“其馴象衛軍士,令于南寧屯種”[18],“洪武二十二年遷南寧屯種,尋遷橫州,徐指揮建衛”[19]。馴象衛始建于思明府,后因各種原因裁撤、復置并遷移,洪武二十一年復置于廣西龍州,之后遷往南寧屯種,因與南寧衛重疊,最后遷至橫州,一直延續到明末。故洪武二十一年并非馴象衛的初置時間,而是重置時間。
二、馴象衛的職能及其變遷
關于馴象衛的職能,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時朝廷大輅,用象挽之。凡朝會,亦用象陳列殿陛兩墀及闕門之外。于是復置衛,令謫戍之人充衛卒,專捕象。每象以一奴畜之,俟其馴擾始入貢。”[20]“先是置馴象衛,使專捕象。”[21]根據記載,馴象衛最初并無其他職能,只是一個專事捕象的特殊衛所。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才“詔總兵官左都督楊文,置龍州軍民指揮使司,調馴象衛官軍筑城守御”[22],使其具有了軍事功能。部分學者認同此觀點,但筆者認為此結論依舊存在問題。劉祥學在其《明代馴象衛考論》中提到,沒有鎮戍任務不等于無鎮戍目的。一方面,桂西地處明代邊疆地區,本身自然環境惡劣,軍隊駐守困難,多設置土官管理,明廷對其控制相對較弱,且少數民族眾多,民族關系復雜;另一方面,桂西南與交趾接壤,且存在邊界爭端。在這種背景下,馴象衛的設置必然具有軍事意義。洪武五年(1372),《明史》中就有討伐“廣西洞蠻”的記載。另據《明實錄》記載:“洪武二十一年秋七月丙子,敕廣西都指揮司,凡百夷戰象之夫,悉放還,其馴象衛軍士,令于南寧屯種。……及西平侯沐英破百夷,獲其人,亦送本衛役之,至是始罷遣。”[23]說明在洪武二十八年明確其守御任務之前,馴象衛一方面擔負捕捉、馴服大象的任務,還曾將在云南俘虜的百夷馴象者押送到馴象衛服役,另一方面還在南寧等地進行屯墾。此外,馴象衛的士卒達到20100多名,遠超當時一衛5600人的配置標準,而且其捕象的數量并不多,顯然其設置于桂西南邊境地區并非只是馴象,而是還有其他目的。筆者認為,明廷之所以將其稱為馴象衛,而且聲明其目標任務只是捕象,一方面可能是因為明廷禮儀確實需要一些馴象,另一方面也有假借捕捉、馴服大象之名,加強對當地土司的鎮撫以及對交趾的防范。在明代桂西地區尤其是左右江一帶,少數民族首領較為強勢,明朝統治者只能通過“析其種落,大者為州,小者為縣,又小者為峒,推其雄者為首領,籍民為壯丁,以藩籬內郡”[24]的方法實行間接統治,因此土司的歸順與否關系到邊境地區的穩定。同時,土司還是明代廣西邊境的重要保障力量,明人稱交趾不敢覬覦內地,是因為“土酋兵力之強,足制其死命也。若自弱其兵,輕撤其陣,恐中國之邊患,有甚于土司矣”[25]。因此,為了同時達到控制邊境土司和維護邊防的目的,設置性質較為特殊、軍事色彩不明顯的馴象衛,顯然是最好的選擇。事實上,馴象衛除了名義上的馴象職能,還有鎮撫邊境土司、防范交趾的目的,只是初期其軍事職能較為隱蔽而已。
洪武后期,馴象衛的鎮戍職能大為增強。洪武二十九年(1396),從馴象衛調“軍士五千人隸奉議衛,尋增設中左、中右、中前、中后四千戶所”[26]。宣德初年,馴象衛“隨征交趾,失陷大半,且原為捕象而設,少攜妻子,故多絕,未全勾補”[27]。這說明在洪武后期至永樂年間,馴象衛的主要職能已經由原來的捕象為主、鎮戍為輔,轉變為以鎮戍為主,其本身也逐漸由原來的特殊衛所轉變為普通衛所,而且因為其最初以馴象為主的性質,導致其戰斗力有限,在奉命征戰中傷亡慘重且難以得到有效補充。明中后期,隨著衛所制度的廢弛以及對大象需求的改變,馴象衛的人數越來越少,“前后發到旗軍二萬一百四十六名。成化二十三年,止存六百一十九名。弘治十八年,止存五百四十名”,嘉靖四十三年后,“見存三百二十四名”[28]。馴象衛逐漸衰落,直到明朝滅亡。
導致馴象衛職能轉變的原因有如下幾點:首先,明廷對象儀的重視程度發生變化。大象自古以來被看作權勢和財富的象征,由于其身體龐大、體態威嚴,常被用于宮廷儀仗中,以顯示帝王至高無上的權威。明初朱元璋制定了詳細的象儀,《明史·儀衛志》記載:“洪武元年十月,定元旦朝賀儀。金吾衛于奉天門外分設旗幟,宿衛于午門外分設兵仗。……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左右。”[29]因為是初設制度,故而執行嚴格,對大象的需求量較大,各地的貢象頻繁,馴象衛也很受重視。至明朝中后期,大象的展演活動已經極少,演象所也幾近荒廢,據史料記載:“今京城內西長安街射所,亦名演象所,故大慈恩寺也。嘉靖間毀于火后,詔遂廢之,為點視軍士及演馬教射之地。象以非時來,偶一演之耳。”[30]明中后期對象儀的簡化或省略,使得正統以后明廷很少下令馴象衛貢象,而且隨著明朝朝貢體系的建立,東南亞各國往往進貢足夠數量的成熟馴象,再加上大象較長的壽命和自我繁衍,這些都使得馴象衛的原有職能不斷淡化。
其次,當朝統治者態度的轉變也對馴象衛職能的轉變產生著影響。與明太祖時期對象儀的嚴格要求不同,明成祖更重視社會經濟的發展,明太祖時期的大批貢象會消耗大量的糧食,而明成祖遷都北京后,京師的氣候與南方不同,為保證大象的存活,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從而增加了財政負擔。永樂時曾有御馬監索取白象的食谷,戶部將此事報告給明成祖,成祖曰:“此所謂率獸食人者,勿聽。”隨后召見御馬監的官員,責備他們說:“汝輩坐食膏粱,衣輕暖,豈知百姓艱難?計象一日所飼谷,當農夫數口之家一日之食。朕為君,職在養民,汝輩不令朕知而為此事,是欲朕失天下心。如復敢耳,必誅不宥。”[31]除了明成祖,明中后期的許多皇帝也對象儀并不熱衷,統治者的態度影響了馴象的發展,對大象的需求也有所減少。
再次,廣西邊疆形勢的變化也是促使其職能轉變的重要原因。明中后期,因為對少數民族的壓迫剝削日益嚴重,廣西少數民族起事和土司的反抗斗爭頻發,正統七年(1442)爆發的大藤峽瑤民起事,時間持續上百年,涉及藤縣、貴縣、桂平、平南等地,對明朝在廣西地區的統治構成嚴重威脅。在這種情況下,鎮撫地方成為廣西各地衛所的第一要務。為了鞏固對廣西的統治,明廷不得不賦予馴象衛更多的鎮戍職能,這也促使了其職能的轉變。
三、馴象衛駐地遷移的原因
馴象衛自設立后,其駐地逐漸東移。但是關于馴象衛駐地遷移的原因,則無史料明確記載。有人認為馴象衛駐地的變遷,與桂西土司勢力太強有關,因為要避其鋒芒[32];一些人則認為與廣西少數民族的反抗斗爭有關[33]。但是筆者認為,這些都并非主要原因。首先,馴象衛的駐地變遷是在洪武二十一年左右,此時明朝剛建立不久,處于上升期,實力較為強盛,因此明太祖對廣西地區采取的是加強控制的政策,即使因為地形、氣候、土司勢力強等原因暫時無力對桂西進行政治軍事滲透,那也只是因為明初在桂西暫未形成完整的衛所防御體系,而非馴象衛東遷的原因。其次,對于廣西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唐宋時期采取羈縻制度,元朝實行土司制度,明承元制,采用“以夷治夷”的土司制度,使得洪武前期桂西局勢較為穩定,即使存在一些斗爭,但未達到足夠迫使衛所駐地遷移的程度。筆者曾考慮馴象衛東遷是否與廣西一些土司在“改土歸流”后的“復土”有關,但是洪武前期改土歸流的地區并未涉及馴象衛所在的區域,而且隨著王朝勢力的深入,土官逐漸納入王朝官僚體系,構成王朝體制下并行不悖的二元政治治理模式[34],故而將馴象衛東遷的原因歸結于桂西少數民族的反抗和改土歸流后的“復土”,顯然不太恰當。
探究馴象衛東遷的原因,還需從其職能來分析。首先,馴象衛最初的職能主要是捕捉、馴服大象,隨著思明府境內大象數量的減少,其駐地的遷移勢在必然。王彤在《中國歷史時期馴象的區域變遷初探》一文中提到因氣候因素而導致馴象地區的變化。秦漢以后,中國進入一個長時段的寒冷期,森林植被萎縮,大象由于食物不足和人類的捕獵,在長江流域地區趨于滅絕,而嶺南地區較為濕熱,人口稀少,植被破壞也較輕,故仍有較多的野象[35]。明代文獻記載了不少廣西南部野象活動的信息,據《明史》記載:“思明州,元屬思明路,洪武二年屬思明府,萬歷十六年三月來屬。東有逐象山。東北有明江,自思明府流入。”[36]馴象衛因而設立于此。之后隨著對廣西地區的開發以及大量捕象,使得大象的生存范圍日益萎縮,繼而向其他地方遷移。洪武二十二年(1389)廣東雷州衛一次即貢象132只,隨后明太祖下令讓廣西思明府、太平府等地的土官率領土兵到橫州馴象衛,匯合官兵前往北部灣沿岸捕象[37]。這一現象說明思明府周圍的野象數量已經不多。野象分布范圍的萎縮和數量減少,導致馴象衛駐地的變遷。明前期馴象衛幾經遷徙,最后到達橫州。
其次,馴象衛短暫遷駐龍州左江和后來派兵到龍州筑城守御,應與控制龍州土司勢力和防范安南有關。明代安南(亦稱交趾)疆域東臨南海,西接老撾,南接占城,北部與廣西思明、南寧以及云南臨安、元江等地接壤[38]。而廣西與安南接壤的絕大多數地方都是土司地區,明廷對這一地區的軍事管控不足。明朝建立后,中國與安南建立了宗藩關系,安南雖然對明朝稱臣納貢,卻拒不歸還元末時侵占的中國土地,因此明朝對安南有所戒備合乎情理。洪武二十一年(1388)馴象衛短暫駐扎龍州左江,隨后遷往南寧屯種,最終遷至橫州。但是隨著洪武后期龍州土官趙宗壽的反叛,明太祖派兵征討,并下令楊文征調馴象衛官軍在龍州筑城守御[39],顯然是為了加強對龍州土司勢力的管控并防范安南。
至于馴象衛最終東遷到橫州的原因,除了上述野象活動范圍的遷移,筆者認為還有以下兩點:一是軍事防衛的需要。橫州隸屬南寧府,而南寧自古便是桂西南的要害之地:“南寧故稱邕管,牂牁峙其西北,交阯踞其西南,三十六洞錯壤而居,延袤幾千里,橫山、永平尤要害。……又郡地夷曠,可宿數萬師。”[40]洪武三年,有廣西省臣上書:“廣西地接云南、交阯,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狼戾多畔。府衛兵遠在靖江數百里外,卒有警,難相援,乞立衛置兵以鎮。”[41]于是明朝設立南寧衛。但是桂西地區形勢復雜,僅靠南寧衛不足以對當地土司形成威懾,且其東部為大藤峽地區,該地以瑤民居多,起事頻繁。如果將馴象衛遷至橫州,不僅能避免其與南寧衛駐扎一地,還能與南丹衛、向武所相聯系,形成桂西地區的鎮戍屏障。這樣既有利于各衛所間相互配合,維護桂西地區的穩定,又有利于從西面圍堵大瑤峽起事瑤民向外圍擴張,防止廣西境內的起事瑤民向北部灣畔的廉州府境內滲透。二是保護水路交通的需要。橫州位于南寧和貴縣之間,處于控制郁江水道的重要位置,特別是烏蠻灘更是郁江水道的要沖,但是此前卻沒有衛所軍隊駐防,不利于保障郁江水路的安全。郁江江面寬闊,上達南寧,下通廣州,在以水路為主的古代,是重要的交通樞紐,故將馴象衛遷此,有利于保護水路交通的安全。
需要指出的是,劉祥學提出的因為思明府水路交通不便、糧餉運輸困難導致馴象衛駐地遷移的觀點不能成立。劉祥學指出,因為馴象衛原位于思明府,位置偏僻,水路交通不便,糧餉運輸困難,故而有必要做出調整[42]。但是思明府位于左江附近,其支流明江也可以通航,可通過水路直達南寧,遠未達到因交通不便而妨礙馴象衛糧餉運輸和解送大象的地步。
綜上所述,明代廣西馴象衛設立后,其職能經歷了由馴象為主到鎮戍地方為主的轉變,其本身也由一個特殊衛所逐漸演變為普通衛所,這與明朝朝貢體系建立后馴象來源多元化以及統治者逐漸重視發揮馴象衛鎮戍地方的職能有關。特別是桂西南地區既與安南毗鄰,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政治形勢錯綜復雜,明朝勢必要強化對該地區的管控,馴象衛職能的轉變也就成為一種必然趨勢。而洪武年間馴象衛駐地的遷移,既與思明府境內野象數量的減少有關,又與桂西南地區軍事部署的調整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