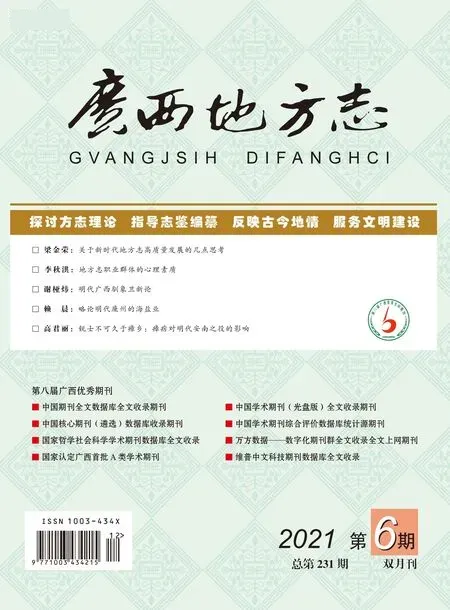銳士不可久于瘴鄉:瘴癘對明代安南之役的影響
高君麗
(暨南大學文學院,廣東 廣州 510630)
自古以來,安南都被中原王朝認為是“瘴鄉”或“瘴海”,有“銳士不可久于瘴鄉”[1]6760之說。中原王朝的南下大規模的軍事活動,莫不受到瘴癘的限制影響,因爆發大規模的疫病,造成眾多人員傷亡,所以中原王朝絕不輕易開展南下大規模戰役。關于明代永樂年間的安南之役,目前學界已經從戰爭爆發的原因、安南政策的轉變、出兵人數、與鄭和下西洋的關系、郡縣其地的統治政策及其影響等方面做了詳細深入的論述。①戰爭原因參見廖小健:《論1406年明朝與安南戰爭的原因》,《印度支那》,1988第1期,第11-15頁。政策轉變參見朱亞非:《明初中越關系與成祖征安南之役》,《煙臺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第60-68頁;張清濤:《論明成祖對安南政策的轉變及安南之役》,《安順學院學報》,2018第4期,第91-94頁;劉涵:《明洪武到宣德朝安南政策研究》,東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9年。出兵人數參見王桃:《明成祖出兵安南人數考述》,《華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第153-155頁;與鄭和下西洋的關系參見楊永康、張佳瑋:《論永樂“郡縣安南”對“鄭和下西洋”之影響》,《文史哲》,2014年05期;統治政策和影響參見陳文:《試論明朝在交阯郡的文教政策及其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8第2期;郭聲波、魏超:《安南屬明時期政區地名變動初探》,《東南亞研究》,2012年第4期,第106-111頁。但是少有研究者從疾病史的角度談論瘴癘對安南之役的影響。因此本文從疾病史的角度,探討一下瘴癘對安南之役影響,以及導致兩國關系變化的因素。
一、前代經驗:銳士不可久于瘴鄉
安南,在今越南北部。古稱“交趾”“交阯”或“交州”。五代以前,皆屬于中國領土重要組成部分,隸屬中央管轄。但由于距離中原王朝的統治中心較遠,自然環境、文化風俗與中原地區迥異,天高皇帝遠,中央難以管控,離心力強。五代十國時期,交趾趁中原戰亂之際脫離了中國的統治,建立起獨立自主的國家。雙方經過多年的博弈較量,一直到南宋孝宗時期,南宋才承認安南獨立自主的地位。自此以后,安南“奉正朔”,成為朝貢體系中的一員,和中原王朝維持相對穩定的宗藩關系。
在中原人眼中,安南是令人聞風喪膽的瘴鄉。學者張文曾在《地域偏見與族群歧視:中國古代瘴氣與瘴病的文化學解讀》一文中說過:“從有關史實看,瘴氣一說之產生,源于中原王朝在嶺南一帶進兵受阻后的歷史記憶。”[2]在中原王朝與安南的多次軍事較量中,中原王朝多次損失慘重。東漢建武年間馬援平定交趾的征側、征貳反叛時:“二十年秋,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3]840北宋太平興國五年(980)宋朝和交趾爆發的宋黎戰爭。作戰中,侯仁寶貪功冒進,不聽部下勸阻,急于行軍,援軍遲遲不來,導致“時諸軍冒炎瘴,又多死者”。[1]491瘴癘給軍隊巨大打擊,《安南志略》記載:“交趾炎熱瘴癘,士卒未戰死者十二三。”[4]381戰后,好言時務、身居諫官的大臣田錫諫言:“交州謂之瘴海,得之如獲石田。愿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度之廣,愛人惜力,無屯兵以費財,修德服荒,無略內以勤遠,亟詔執事,寬其誅鋤,又何必蕞爾蠻陬,勞于震怒,此大體之一也。”[1]496
熙寧八年(1075)十一月到熙寧九年(1076)十二月之間,宋越熙寧戰爭爆發,熙寧九年六月,張方平在《上神宗論交趾備御九事》論述了瘴對作戰的重要影響,他認為:“竊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謂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以后氣候始肅。”[1]6763“今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久于瘴鄉。”“儻今冬蠻未撲滅,則前春兵須抽退,更圖后舉,臣竊難之。”[1]6760-6761顯然,“銳士不可久于瘴鄉”這一認知,是歷代南下戰爭受阻后的結果。
二、瘴癘對安南之役的影響
(一)乘冬月瘴厲肅清:安南之役的作戰方針
明永樂四年(1406)七月到五年(1407)六月,明朝和安南爆發了戰爭,史稱“安南之役”。這場戰爭改變了朱元璋制定的兩國外交原則和格局,安南從獨立自主的國家,變成了明朝的一個省,實現了“奉正朔”到“建郡縣”的轉變。然而,明朝對安南的統治只維持了二十年,最終不得不放棄“郡縣其地”的做法,將明朝所有的軍隊、官員從安南撤回。這個過程,瘴癘于無形中影響著明朝政府的軍事活動,進而影響了政府的決策。
安南之役雖是明朝主動進攻的,但卻是安南黎氏多次挑釁后的結果。永樂四年七月,朱棣部署軍隊完畢,以朱能為東征夷將軍,沐晟為左副將軍,張輔為右副將軍,分東西兩路,從廣西和云南兩路夾擊,直取安南。朱能是朱棣最信任的大將之一,被朱棣看作是“輔我成業者”[5]卷20,但令誰都想不到的是,朱能剛到廣西不久,就患病去世了。《明史》記載:“十月行次龍州,卒于軍。年三十七。”[6]4086《明太宗實錄》記載:“戊子,征討安南總兵官成國公朱能以疾卒于龍州,右副將軍新城侯張輔代總其眾以進,且遣人馳奏。”[7]865黃道周的《廣名將傳》記載:“又明年,安南黎氏弒其主,且拒皇命,詔拜征夷將軍總兵討之上。親餞龍江,師抵廣西,而能病瘴,以兵屬副軍而卒。”[5]卷20
東征夷將軍朱能感瘴而死,加重了朱棣對瘴癘的擔憂和焦慮。同十月二十五日,朱棣敕書張輔、陳旭等人,命張輔為征夷將軍,陳旭為右參將,并對作戰方針做了重要指示:“爾等宜立志自強,取法前人,乘來冬月瘴厲肅清,同心協謀,殄除逆賊,建萬世勛名,以副朕之委任。”[7]878朱棣的指令,源于他熟讀兵書和歷代典故,對瘴癘有一定的認知。
永樂四年(1406)十一月壬午,朱棣下令:“聞官軍與賊相持,賊計正欲延緩,以待瘴癘,破之宜緩,必以明年二月滅賊班師。”[7]885以班師督促張輔速戰速決。十二月,張輔軍隊駐扎在富良江北,遣驃騎將軍朱榮破安南軍于嘉林江,與沐晟合軍進攻多邦城。安南軍驅象迎戰,張輔畫獅蒙馬,以神機火器作為掩護,沖破重圍,大破敵軍。結果“斬其帥二人,追至傘圓山,盡焚緣江木柵,俘斬無算。進克東都,輯吏民,撫降附,來歸者日以萬計。遣別將李彬、陳旭取西都,又分軍破賊援兵。季犛焚宮室倉庫逃入海,三江州縣皆望風降。”[6]4220這一戰,張輔基本按照朱棣“乘來冬月瘴厲肅清,同心協謀”的指示,一路勢如破竹,避開瘴癘盛行季節,基本奠定了明軍的勝利局面。
(二)恐瘴癘雨潦:班師回朝時間延后
1.催促班師回朝
按照朱棣的計劃,本該于永樂五年(1407)二月班師回朝,可是因為安南殘余勢力未消,回朝的時間一推再推。朱棣不得不多次就如何應對瘴癘與何時班師對張輔等人多次催促提醒。
永樂五年正月初九日,朱棣對軍隊運糧問題做了部署,同時提醒張輔等將領把握時機及時班師,因為:“今天氣向暖,軍士不宜多留,宜晝夜用心,嚴督諸將,火速火速,急忙急忙,平定地方,剿滅賊寇,及早班師,恐瘴癘雨潦,不便,故勅”。[8]卷2這年春天,張輔帶領軍隊乘勝追擊,清遠伯王友“悉破籌江、困枚、萬劫、普賴諸寨,斬首三萬七千余級”。進而拿下東潮、諒江諸府州,與黎季犛戰于木丸江,“斬首萬級,擒其將校百余人,溺死者無算”。黎季犛逃至富良江入,張輔與沐晟夾岸迎戰,柳升等人以戰船橫擊“大破之,馘斬數萬,江水為赤,乘勝窮追”。此時的明軍有如天助,本來天旱江水淺,敵軍不得不棄船逃跑,突然下大雨,水漲船高,“遂畢渡”。[6]4221雖然明軍勝利在望,但是黎季犛逃脫,其殘余勢力仍然十分頑固,張輔希望將其剿滅殆盡,所以將回朝的時間推遲到了十月份。
朱棣十分害怕瘴癘會影響軍隊,永樂五年二月十五日,小心囑咐張輔等人:“前者勅爾于二月中班師。今曾日彰來奏賊之殘黨尚未盡滅,欲大軍鎮守,且言交趾無瘴癘,丘溫、龍州數處,此時瘴癘雨潦正作,爾等宜詳審會議,度事相機,可班師即班師,如未可班師,果無瘴癘,則擇高亢向陽之地,屯營駐兵,則百疾不作,尤須嚴固守備……俟十月班師,交人為黎賊困虐已久,撫治之道,必先寬恤,故勅”。[8]卷10“擇高亢向陽之地”是古代行軍經驗的總結。古人一般認為,瘴癘的發生與水土、氣候、草木、陰陽等因素有關。宋代的許洞在《虎鈐經》中總結特別到位:“結營須象山川,卑濕之地,其濕燥毒氣,襲人口鼻者,則山瘴之瘧癘生焉。又若寒暑之氣不節,夏寒冬燠,或夏傷于大暑,熱氣盛藏于皮腹之間,加以士卒之眾,氣相蒸為溫臭,則時疫生焉,抑又所營之地,士卒不便水土之性,溫涼之氣,致陰陽二氣紊亂,于腸胃間則霍亂吐瀉生焉,斯之三者,眾氣生疾之地十有五六焉,故臨戎之士得不預備之乎。”[9]卷10
永樂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朱棣勅令張輔、陳旭、劉儁等人:“見今擺堡,但有瘴癘去處,止令土軍在彼守堡,土軍蓋練習風土,其余守堡官軍移散于無瘴地面,或出或入,權蹔屯駐,侯瘴癘清時,仍令各還原堡,其來降大頭目,仍以好屋宇居其家小,令其子侄親人看家,遣之來朝”。[8]卷2遭遇瘴癘,土軍駐守原堡,其他軍隊暫時撤離,這樣的安排,顯然是認為土著對瘴癘有免疫能力,瘴癘只針對外來人員。五月,“獲季犛及其子蒼,并偽太子諸王將相大臣等,檻送京師”。[6]4221宣告安南之役的勝利。
2.將士受到瘴癘的侵襲
夏天是瘴癘的高發時期,事態也正如朱棣所擔心的那般發展:“今瘴癘大發,軍士病且甚,一旗有一二十名者有之,有二三十名者有之,豈可不思處置,爾宜急與西平侯沐晟等審思詳慮,如有善策,從便行之,隨即奏來,務在兩無所妨。”[8]卷2明代的《武備志》提到:“每五十授以一旗”。[10]卷42一旗的士兵大約五十人,其中有十二到二十三名左右人員感染瘴癘,感染率在24%-46%之間,算是比較高了。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在交通和信息傳播手段不發達的古代,信息傳遞具有明顯的滯后性,所以朱棣授予張輔、沐晟等人便宜行事的權力。在此之前,朱棣希望張輔等人班師回朝,張輔言殘余勢力未盡數掃除,并說交趾無瘴,丘溫、龍州數處瘴癘正作,丘溫、龍州等處是回朝的必經之路,由此影響了軍隊的行程,張輔懇請留苗軍在交趾。朱棣批復:“朕聞有瘴,則促使班師,及奏無瘴,則唯令留鎮,朕之此心,無非欲為軍士之便。”[8]卷2
張輔欲掃清殘余勢力,故遲遲不愿班師。現如今感染瘴癘的人數如此之多,朱棣非常生氣,怒斥張輔等人:“今瘴癘如此,爾等乃坐視不顧,惟事飲酒,忿爭私氣,又不預為奏聞,兼往來之人,相傳不一,不知爾等用心何為?”[8]卷2從朱棣的話語來看,張輔等人應對瘴癘缺乏積極的防護措施,朱棣因此十分生氣和萬分焦慮,需要迅速了解具體情況,所以他說:“朕命爾為將,軍中利害,必預先奏聞,今不見奏聞,但人來言瘴癘,有無難信,果有瘴無瘴,從實具奏,庶不負朕委托之意”。[8]卷2不久,張輔就交趾瘴癘的問題,給了朱棣明確的回復。確認了交趾地平無瘴,但憑祥、丘溫、雞翎、坡壘、龍州等地,瘴癘難行。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勅諭總兵官張輔:“從征將士,遠離父母妻子,跋涉山川,勞勚筋骨,勤苦至甚,方今夏熟,即揀高爽之地,以休息之,養威畜銳……”“但俟瘴癘肅清,即便班師。”[8]卷2
隨著天氣變熱,感染瘴癘的人數增多。永樂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朱棣下詔:,“今天氣炎暑,雞翎、坡壘等處皆有瘴癘,爾等不用心計較,又不奏來,往往差人至中途,間多染瘴癘,成疾一二十人之中止有一二人得達者,然亦因病不支。”[8]卷2張輔的應對自然是滯后無效的,因為瘴癘阻礙了交通路線,致使消息無法傳達回中央。朱棣又說:“凡有所問,皆昏憒不能荅,應致人如此,爾等何不仁之甚,今后果系緊要事務,不可緩者,則差人來,如非緊急重事,可以緩者,姑俟秋涼,途中瘴癘稍清,卻一一奏來,若由廣東路便無瘴,奏事者則由廣東而來,故勅。”[8]卷2事情分輕重緩急,緊急之事,需要繞過煙瘴之路,從廣東路立即上報,若是非緊急的事情,可以等到天氣涼爽再報。
永樂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眼看就到了預定的班師日期,朱棣勅令總兵官張輔、右參將陳旭、兵部尚書劉儁及交趾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提醒他們:“今冬月瘴癘肅清,可及期遣行,不可稽緩”。[8]卷2但朱棣從內官苗貴那得知新安、建平、涼江等府及東湖太原等州以及生蕨等江蠻民不服,聚眾作亂后,嚴厲要求張輔等人:“勅書到日,即便設法剿捕惡徒,必使盡絕,班師之日,毋得更留余孽,庶幾可釋前罪”。[8]卷2因為此時天氣已經轉涼,瘴癘最輕,朱棣稍微寬心,希望他們能剿滅殘余勢力。
但天氣一熱,朱棣又開始焦慮了。永樂六年(1408)春三月十三日,又下詔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交阯布政司奏坡壘、丘溫、隘留三處乃交阯咽喉,其地瘴癘,官軍難處,欲于近附思州、太平、田州等處量起土庫,設立衛所,如陜思、西潼關、四川瞿塘之例,軍隸民,廣西隸交阯為便,爾等其議行之”。[7]1046勝局已定,殘余勢力已基本剿滅,班師在即,朱棣思考長治久安之策,仿照關陜地區的衛所制度,由土兵把守要害之地。同月二十二日,敕交阯總兵官新城侯張輔等曰:“得奏班師,去冬朕念將士久勞在外,命爾等及時班師,今天氣已熱,瘴癘方作,而始就道,踰其時矣,宜善加撫恤,無間將校軍士,但有一人病瘴死者,爾等不得為全功”。[7]1049殘余勢力已清,已經可以班師,可是此時“瘴癘方作”,張輔平定安南,實現了自宋以來郡縣安南的抱負,功勞相當大,朱棣一句“爾等不得為全功”,目的是督促張輔重視瘴癘問題。同年夏天軍隊班師回朝,接受封賞。
班師回朝這個問題,從預計的永樂五年二月,一直拖到了永樂六年夏天,才得以實現。阻礙班師回朝有兩個因素,一是黎氏殘余未清,二是歸途有瘴癘。兩個因素相互影響和作用,給軍隊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銳士不可久于瘴鄉”成為時刻縈繞在朱棣心頭的噩夢。從中也可以看出,瘴癘是影響中原王朝駐軍嶺南地區及以南地區的主要因素。
三、安南之役后的余波
安南之役對于明朝來說,是幾百年來前所未有的偉大勝利,平定黎氏集團后,明朝政府將中原制度照搬到了安南,永樂五年六月設立交趾布政司。然而,安南脫離中國統治多年,民族意識日益增強,加之派往安南的地方官良莠不齊,從而激起了安南的反叛。永樂六年冬,安南陳氏故臣簡定舉起反叛的大旗,朱棣于第二年春復命張輔佩征虜將軍印,帥師征討。結果“獲簡定于美良山中,及其黨送京帥”。[6]4221叛亂首領已經抓到,簡定所擁立的新皇帝陳季擴也請降,太子朱高熾將張輔召還:“永樂八年二月十七日,皇太子諭英國公張輔:‘……然數年之間,跋履山川,沖冒瘴癘,勤勞為甚,子旦夕在念,余未嘗忘之,茲命召還,良用慰懌……’”[8]卷2“跋履山川,沖冒瘴癘”基本概括了幾年來瘴癘對行軍打仗的影響。
安南時叛時降,陰晴難定。軍隊后勤供給是個大問題,從廣西運糧到安南,需要經過涉雞陵、隘留、丘溫、憑祥、龍州、太平等地,這些都是有名的瘴區。永樂八年(1410)夏四月初七,禮部啟交阯布政司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趁著皇帝召集諸將商議運糧之事,建議:“今詢得瀘江北岸小河直通盤灘,下至新安府靖安州萬寧縣,抵廣東欽州水路,止十站,欽州至靈山縣,靈山縣入廣西橫州,陸路止三站,通計十三站,比舊行之路水路減半,乞令廣東、廣西二布政司差官量道里,設水馬驛站遞運所,并相其要害去處,設衛所巡檢司,鎮御盜賊,既免瘴癘,又便往來。”[7]1336新路線的開辟,既縮短了路程,也繞開了主要瘴區。永樂九年,張輔和沐晟在安南一同平叛,四月,“以瘴癘徙交阯鎮夷關于松嶺高爽之地”[7]1466。因張輔處置了當時臭名昭著的宦官黃中,軍隊士氣大振,其年七月于月常江破賊帥阮景異,獲船百余,生擒偽元帥鄧宗稷等人,又捕斬別部賊首數人。只可惜,“以瘴癘息兵”。[6]4222瘴癘這種無法克服的外在條件,成為明朝軍隊無法平定安南之亂的原因之一。
永樂十六年二月,交阯嘉興州四忙縣原土官知縣車綿子、車三等人殺流官反叛,知縣歐陽智、豐城侯李彬派都督同知方政率兵討伐,結果車三等人逃遁,方政因“山林深阻,瘴癘方作,官軍搜索不獲,遂引還”[7]2063,李彬只能派人招諭。永樂十七年五月,安南領黎利占據可藍冊,李彬遣都督同知方政、都指揮師佑等領軍剿叛,捕獲其偽禁衛將軍,但阮個立等逃匿老撾,于是留都指揮黃成、朱廣于可藍堡守備,方政等人回交阯,黎利卷土重來,殺了王局巡檢梁珦等人后逃跑,張誠領兵追擊,叛賊皆敗走,只可惜“緣暑雨水溢,嵐瘴方作”。李彬只得向朝廷“請俟秋進兵”[7]2137,朝廷同意了這個請求。由此可知,瘴癘阻礙了明朝軍隊平定叛亂,安南軍隊趁著瘴癘爆發和明朝軍隊周旋,明朝軍隊飽受其害。瘴癘也成為阻礙明朝對安南進行直接統治的重要因素。
四、余論:瘴癘對明代周邊關系的影響
北方軍隊對南方地區的不適應是研究者的共識。北方軍隊對南方瘴癘的畏懼,可以說是刻在骨子里的。明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丘浚曾有一個非常經典的論述,他認為:“大抵南蠻與北狄不同,蠻性陰柔,倚山為軍,來則入山遠避軍,去則外出虜掠,如蠅蚋然,揮扇則飛散,收扇則復集,剿滅之甚難,且其地多瘴癘,中原之人憚入其地,未至固以怯畏,一入其地,氣候不齊,蒸濕特甚,往往不戰而死,既不可速戰,又不可持久,所以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蠻者也。”[11]卷22所以歷朝歷代,中原王朝很少向南方邊遠之地發起進攻,更不用說蠻荒之外的安南了。
基于軍事的不利,明智的統治者都會選擇和安南保持友好的宗藩關系,只要安南履行“奉正朔”的義務即可。明初朱元璋將安南列為十五個不征國之一亦是基于這個考慮。朱棣在安南雖取得了一時的勝利,但因為瘴癘時發,明朝軍隊無法將叛亂者一網打盡,瘴癘嚴重時只能退兵,而安南叛軍相對適應當地瘴癘環境,明軍卻無可奈何,安南用兵問題一直困擾著明朝統治者。宣德二年(1427)冬十月,成山侯王通私自與安南的首領黎利議和。在沒有皇命的前提下,王通卻獲得了大多數將領同意議和的支持,原因也很簡單:“諸將校以我軍相持日久,且瘴癘時作,死亡甚多,遂從通議,與利連和而擅退兵”。[8]卷6可以說,將士“苦瘴癘久矣!”瘴癘是議和主要原因,宣德三年(1428),王通因私自議和被處死。
王通雖死,但明朝軍隊在安南上耗費太多,明朝政府早有從安南撤離的意圖。所以當安南向明朝政府提交議和的書信時,朱瞻基聽從了楊士奇、楊榮等人的意見:“陛下恤民命以綏荒服,不為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為美談,不為示弱,許之便”。[6]4135楊士奇的觀點,與歷代的大臣對安南的認知如出一轍——安南為瘴海,得之無用,不如棄之。從此以后,明朝和安南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宗藩關系。瘴癘也就成為一道無形的屏障,維護著宗藩關系的穩定。雙方盡管在邊境上時常有摩擦,但和平共處的大方向一直沒有變!
值得一提的是,廣西和云貴地區多瘴癘,與之聯系密切的老撾、緬甸等地也是有名的瘴區:“外藩煙瘴,以緬甸為甚,中土煙瘴,以廣西為甚,連毗而及于滇黔粵東,瘴之名目不一,總之是炎方,郁熱所蒸之毒氣。”[12]雜述3“征剿云南邊境,云南、老撾等處,其地瘴氣甚毒,進者必死,若不得已而征之,必須調各處土兵資以饋餉。”[13]卷44故而除安南外,明朝與老撾、緬甸等地的軍事活動也多因瘴癘而無功而返。比如,與緬甸息息相關且曠日持久的麓川之役,明軍多次軍事行動因瘴癘而受阻:“正統六年(1441)二月,上命定西伯蔣貴為總兵,驥總督軍務。五月至云南,賊困大候州甚急。眾謂:瘴月不宜進兵……(驥)命都指揮馬讓率大理諸衛兵六千赴援”。[14]卷19下甚至在征麓川期間,鎮守云南的黔國公沐晟也因瘴癘退兵,最后憂懼而亡,麓川之役對西南、緬甸社會都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鑒于瘴癘造成的軍事行動上的不便和國家綜合利益,明朝政府在處理周邊的關系時,多次以政治、外交等和平的方法解決多方之間的矛盾和沖突,盡可能避免大規模的軍事活動。瘴癘成為明朝與周邊外交格局形成過程中一雙看不見的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