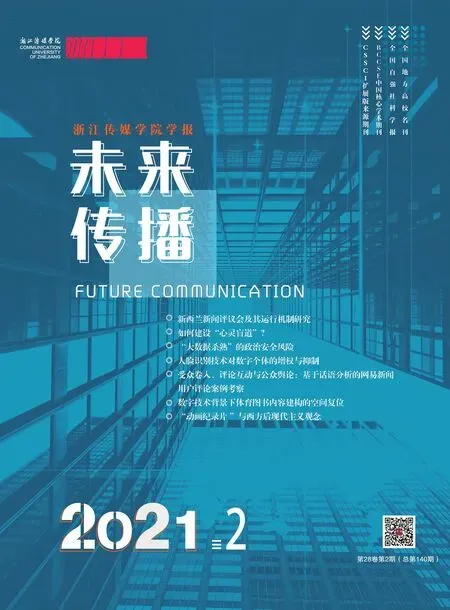新世紀現實題材電視劇中產話語的審美文化癥候
戴 碩
(浙江傳媒學院電視藝術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21世紀以來,伴隨著改革開放釋放的經濟發展紅利,我國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了大幅度提升,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召喚以及全球化、城市化、工業化等多種社會趨勢的合力助推下,我國社會階層也發生了重構。改革開放之前的“兩階級一階層”的超穩定社會結構,在我國對意識形態的松綁中也悄然解體,更加多元的社會階層開始涌現,我國中產階層的異軍突起成為其中最鮮明的社會景觀。
社會學領域從中國中產階層的測量標準、規模、定義等本體層面,進行了大量實證性研究,中國社科院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遷研究”課題中,將中產階層界定為“包括擁有一定私人生產資料的自雇者(如個體戶)和中、小雇主(如中、小私營企業主)群體。其間的主體是指占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以從事腦力勞動為主,主要靠工資及薪金謀生,具有謀取一份較高收入、較好工作環境及條件的職業就業能力,對其勞動、工作對象擁有一定的支配權,具有維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消費能力及相應的閑暇生活質量,以其具有的專業知識,對社會公共事務形成權威評價,并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社會地位分層群體”[1]。而從文化研究視角來看,中產階層在當下中國盡管已然成長為一個階層實體,但在目前的中國語境中,其更像是一個文化概念,是一種由大眾文化話語建構出的“想象的共同體”。媒介基于不同的訴求,按照自身的觀察與想象,在文本中構建起了中產階層的主體形象和生活方式,而這種急速擴張的中產話語,也反哺了現實中正在成長的中產階層的身份認同和文化意識。
在大眾文化不同文本形態對我國中產階層的陳情與代言中,國產電視劇無疑是其中最具視聽直觀性和媒介影響力的形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國家話語、商業邏輯和創作旨趣的合謀中,我國電視劇的內容創作與意義生產,漸趨呈現出鮮明的中產階層文化優先取向,新興中產階層在影像中獲得觀照或建構。從《牽手》《來來往往》《中國式離婚》《蝸居》《北京青年》《浮沉》《杜拉拉升職記》《手機》《離婚律師》《大丈夫》,到近兩年的《虎媽貓爸》《中國式關系》《歡樂頌》《我的前半生》《美好生活》等,可以說,在都市情感劇,乃至職場劇、商戰劇、青春偶像劇等都市題材亞類型中,構建中產階層形象、渲染中產階層生活方式的劇集已成主流。
審慎地檢視當下中國電視劇的中產影像后,不難發現,盡管創作者趨之若鶩地在現實題材中建構中產階層形象,使該類劇集出現了題材井噴,但我們不免遺憾地承認:當下中國電視劇對中產階層的影像書寫,其癥候大于成就,粗陋之作多過精品力作。與其說是電視劇中中產形象的“千帆競發”,毋寧說是一種話語泡沫的形成,一種新神話的崛起。國產電視劇對中產階層形象建構與生活方式的塑造,存在廣泛誤讀和抒情過度的問題。就中產影像審美文化癥候大致呈現出的特征,本文將作具體分析與闡述。
一、單向度“賦魅”:魅化想象中的中產幻象
如果向普羅大眾調查對中產階層的認知,他們大概會對這個階層勾勒出大同小異的“畫像”:工作體面,薪水可觀,學歷很高,住高檔小區,有名車相伴,衣食住行講究格調。總而言之,這個群體優雅得體、消費超前、品位不俗、自律克己。可以說,這些光鮮的標簽性詞匯,即使說不是全部,也至少代表了大多數國民對中產階層的“刻板印象”。媒介具有建構“擬態真實”的效果,這些刻板印象顯然來自于傳媒與影像的建構。電視劇中產階層的影像書寫,主導了社會民眾對這個群體的認知與想象。
而中產影像的失真,自然也導致了大眾對中產階層的認知誤差。當下民眾對中產階層無限風光的認識,根由正在于表現中產階層的電視劇過度拔高美化這一階層群體的生活,使之呈現出超脫平民的“魅影”,或者說是刻畫出了一副“單面人”或“半張臉”。學者王曉明在對20世紀90年代文化和文學進行分析總結時,曾用“半張臉的神話”來概括傳媒和文學對于所謂“成功人士”符號化生活的斷章取義,可以說,眼下電視劇對中產階層的描繪,就時常陷入到這種迷戀和自我陶醉的創作傾向中,大量表現珠光寶氣的豪門恩怨和所謂“瑪麗蘇”“霸道總裁”的浮華敘事自不待言,縱然是一些整體品相尚可、寫實性較強的現實題材作品,也常常落入對中產階層無法自持的“賦魅”過程。
如電視劇《歡樂頌》所樹立的中產階層“標桿”——安迪,就帶有創作者的美化傾向。安迪這個角色氣質出眾、才華過人,具備謹慎克制、積極進取的性格特征,自美國哥倫比亞商學院畢業后,先是成為華爾街高管,歸國后又成為投資公司首席營銷官。安迪既有縝密理性的頭腦,工作嚴謹而高效,又不乏生活的浪漫情趣,喜歡讀書,每天堅持跑步,為人和善寬厚,即使是童年陰影遺留下的心理創傷,也令這個角色顯得楚楚動人。很明顯,創作者在她身上寄托了不少對中國中產階層的浪漫想象,甚至達到了一種精英膜拜的傾向。與《歡樂頌》相似,《我的前半生》中的賀涵則是活脫脫的男版“安迪”,同樣的留學歸國、公司高管,以及相似的生活旨趣,典型的“鉆石王老五”,職場上殺伐決斷,情感上也柔情繞指,人物性格與魅力近乎無可挑剔。問題是:這些如此完美的中產神話在多大程度上具備現實觀照性和平民階層流動的示范意義?在這種“半張臉”的塑造中,其更飽滿的性格“顆粒度”被無視,而只有幾多性格高光被“提純”,成為概念化和標簽化的顯影。
當然,在中產階層的美化中,也并非全無對其困境、焦慮或煩惱的描繪,但這些都僅作為主人公無關痛癢、無傷大雅的小問題而存在,甚至構成塑形主人公形象魅影的敘事動力。例如,《歡樂頌》中安迪因童年遭際留下的心理障礙,《我的前半生》中賀涵在兩個女性間的游移,《婚姻保衛戰》中對于夫妻家庭角色分工的過度糾葛。這些浮于表面的一己悲歡和杯水風波,并非是對生活真相的揭露,也沒有呈現出中產階層的另外“半張臉”,僅僅強化了一種虛假主體的神話。
那么,這種“單向度”的中產幻想是如何被制造出來的?仔細分析的話,大致可以從創作主體認知、消費邏輯主導和意識形態整合等多個角度作解讀。從創作者角度來說,由于對中國中產階層認知的單一和乏力,他們只將視角局限于中產階層的符號化生活,人為地拔高和夸大中產階層的個體形象和生活方式,最終呈現出抒情過度的表征。例如,部分電視劇創作者標榜“唯美主義”創作態度,但就在過度浪漫、唯美和詩意的影像表達中,個體復雜的生活狀態和文化心態也最終流于空泛。創作者對中產階層單面形象的過度美化,對其優雅生活方式的盲目推崇,更是源于消費主義時代的資本邏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逐漸從生產為主導的社會開始向消費為主導的社會轉型,消費主義構成了整個社會的巨型話語體系。中產階層發軔于西方消費社會中,其講求炫耀性消費和地位區隔的本體屬性,通常也令自身成為消費社會的寵兒和代言人,因而大眾媒介和影像中的中產階層個體往往成為商品符號的負載。
對電視劇中中產階層時尚新潮生活的表現,持續刺激著觀眾的消費欲望,中產階層的身體修辭和生活方式,成為各路消費品牌爭相植入的載體,不同品牌堂而皇之地出現在敘事縫隙中,在不同時空里打下文化消費的地標。很大程度上,在觀眾對“半張臉”的中產影像的“凝視”中,消費主義邏輯以“腹語術”的修辭手段,對觀眾的消費行為進行了規訓。而對于中產階層“美好生活”的過度渲染,也承載著意識形態整合社會各階層目標的訴求。當階級斗爭的話語體系被共同富裕的話語體系所取代,表征著現代性的中產階層就成為普羅大眾觸手可及的身份想象。電視劇虛構出的中產階層完美客體以其溫情脈脈的美妙絮語,為不同階層編織出了一個玫瑰色的幻境。
二、“中產趣味”的話語擴張
如果說“半張臉的神話”概括了電視劇中中產影像對個體形象不同切面的選擇性失衡,那么“中產趣味”的廣泛擴張則是影像對中產階層趣味與生活方式過度放大的表征。作為曾經的學術語匯,如今“中產趣味”這個概念無疑以一種曖昧不明、自命不凡的面孔出現于各種大眾傳媒中,成為媒體渲染或推崇某種生活方式時的理想標簽。然而,在這種溫情脈脈的語詞擴張中,究竟潛藏著怎樣的精神圈套與話語陷阱則值得學者反思。
事實上,在晚近的美學與文化研究中,“中產趣味”一直作為學者反思與批判的指涉而存在。美國文學批評家馬泰·卡林內斯庫(Matei Cǎlinescu)在其《現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從美學角度分析了媚俗藝術的發生機理,并指出其背后的精神實質即“中產趣味”,卡林內斯庫也不啻用“偽藝術”“壞趣味”等詞對這種“中產趣味”做出了負面的價值判斷,“媚俗藝術實際上是中產階級的趣味,而中產階級趣味是現今我們社會中大多數人的趣味”[2]。美國當代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則引用了美國大眾文化研究學者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在《大眾文化理論》中的經典論述,來闡發“中產趣味”的精神實質,“大眾文化的花招很簡單——就是盡一切辦法讓大伙兒高興。但中產崇拜或中產階級文化卻有自己的兩面招數:它假裝尊敬高雅文化的標準,而實際上卻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3]。
依照這些經典社會學者的論述,“中產趣味”已然構成了大眾文化意識形態中的典型癥候,而“中產趣味”背后的精神本源則是一種享樂主義價值觀。在丹尼爾·貝爾看來,20世紀初,新生中產階級逐漸放棄資本主義勃興階段的新教倫理與禁欲準則等清教傳統,一種鼓吹享樂主義的價值觀開始盛行。享樂主義的價值體系摧毀了傳統新教倫理的社會道德基礎,而又支撐和確立了全新的價值準則,正是嚴肅藝術家培育的現代主義、“文化大眾”所表現的乏味形式的制度化以及市場體系所促成的享樂主義生活方式,才構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矛盾。貝爾的觀點得到了馬泰·卡林內斯庫的呼應,在他的論述中,享樂主義構成了一種媚俗藝術和“壞趣味”的心理基礎,“要理解媚俗藝術的本性,我們必須分析構成中產階級心智特征的那種特有的享樂主義。其基本特征也許是,它是一種中間路線的享樂主義,這絕佳地體現在常常可以在媚俗藝術中見到的‘平庸原則’(越是在精致和過分復雜的媚俗藝術形式中,越是容易發現這種平庸性)。堪與這種享樂主義的膚淺性相媲美的,惟有它渴求普遍性與總體性的欲望,以及它獲取漂亮垃圾的無限能力”[2](264)。
由此,我們對“中產趣味”的基本面向也可以得出自己的判斷:它是在洶涌澎湃的商品大潮下基于享樂主義價值觀而興起,謳歌中產階層的浮世欲望,渲染中產生活的品位與格調,對消費主義營造的中產符號化生活大唱贊歌,構建起中產神話的話語泡沫。與此同時,它缺乏思辨性與批判性,缺乏底層立場和價值情懷。不少文化研究者均指出,當下文藝創作者存在“精神中產化”的傾向,落實于創作中則是“中產趣味”的風行,由此也喪失了自身的批判身份和價值堅守,制造起消費主義的能指狂歡,在空洞的符號化編碼中取悅大眾,透支文藝創作的生命力。而中產階層“溫吞水”式的生活,也使得他們對社會痛點的脫敏,對真實社會問題洞察力與解剖力的匱乏,失去了書寫痛感經驗的能力。在電視劇中中產階層影像書寫中,這種“中產趣味”儼然構成了迅速擴張的意識形態。不少都市情感劇、偶像劇、職場劇和商戰劇等體裁的作品,能夠顯而易見地看到創作者的“中產趣味”,在現代化都市的目不暇接的商品盛宴和布爾喬亞式情調的影像中,創作者對浮華生活的耽溺與張揚昭然若揭。
電視劇中“中產趣味”的話語擴張,說到底則是止步于對中產階層欲望敘事的迷戀,一方面在衣食住行的“炫耀性消費”中,營造起享樂主義的消費觀念和階層區隔,同時在情感領域完成欲望本體的自我放逐。就其根本而言,“中產趣味”的影像書寫并不追問存在的意義,也不承擔反映生活真相的責任,而是在放大了的欲望狂歡中,迎合新興中產階層的想象性身份建構。而電視劇影像中的“中產趣味”也構建出一個新的審美話語霸權,在審美的異化和泛化中消解了自身的意義空間。學者張清華曾不無激憤地指出:“‘中產階級的生活’是好的,但‘中產階級的文化與藝術趣味’卻是十足有害的,是站在社會進步與藝術本質的對立面的東西。”[4]當創作者沉淪于中產趣味的審美幻象時,一個可見的后果就是對個體生命的真實經驗,乃至底層經驗的“不可見”。由此,對于電視劇中“中產趣味”的話語擴張,也是值得創作者警惕和反思的命題。
三、大女主:女性“在場的缺席”
女性性別敘事,向來是電視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產階層女性通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有著獨立的人格精神,也大都具備與男性平等對話意識,往往構成了影像“現代性”的符號存在。總體而言,當代中國電視劇對于中產階層女性的言說,傳遞了一定的啟蒙精神,女性自我成長和反抗意識在這些劇中開始蘇醒。但與此同時,由于集體無意識中根深蒂固的男權觀念,電視劇中中產影像對女性的表現依舊存在被遮蔽的狀況。
當代中國現實題材劇對女性形象的全面表現,應當說源于1990年的《渴望》。這部劇刻畫了一個集中華傳統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形象劉慧芳,她的善良、隱忍、敢于犧牲曾感動過無數觀眾,該劇萬人空巷帶來的“舉國皆哀劉慧芳”成為那個年代的一道盛景。但在該劇廣受好評的同時,不少人也認為劉慧芳的形象消解了女性本該覺醒的主體意識,在傳統道德規范下壓抑著本身的自然需要,是一種女性解放觀念的倒退。20世紀90年代,都市劇中也開始呈現更多的中產階層女性。如《公關小姐》中展現了以周穎為代表的時尚新潮、充滿現代意識的中產職業女性群像,在表現這些新女性在職場中雷厲風行、獨當一面的同時,劇中也對她們在愛情、家庭中的矛盾糾葛進行了心理探尋。20世紀90年代末的《牽手》,就站在兩個不同的女性視角,對新出現的婚外戀現象進行了剖析。該劇并未懸浮于外在欲望的敘事,而是由表及里,深度反思婚姻出現裂痕的個體與社會成因,以較大筆墨塑造不同女性的價值理想和追求,尤其是對中年的中產女性在得知丈夫對婚姻和家庭的背叛后,從失落痛苦到直面問題,最后找尋到真正屬于自己的人生之路這一過程表現得淋漓盡致。該劇也成為塑造女性成長較為經典的作品。
進入21世紀以來,中產影像中的女性呈現出越發獨立,甚至強勢的表現,女性角色在情感關系中開始占據更多話語權和主動性。例如,《空鏡子》中的姐姐孫麗是名利場上的賭徒,情感世界的玩家,她漂亮出眾、思想前衛,將不同的男性玩弄于股掌間;《中國式離婚》中的林小楓性格脆弱而敏感,疑神疑鬼甚至歇斯底里,對丈夫缺乏基本的信任,而她在婚姻中的控制欲使其成為可怕的神經質形象;《蝸居》中的海萍性格張揚跋扈、自視甚高,在家庭關系中同樣處于支配地位,對丈夫頤指氣使、怒其不爭。除此之外,《婚姻保衛戰》中的蘭心、《虎媽貓爸》中的畢勝男、《小別離》中的方圓、《大丈夫》中的顧曉珺等皆不再是傳統文化期待視野中“溫良恭儉讓”的理想女性,無不是性格獨立、風風火火的形象——在職場上獨當一面,在家庭關系中也居于主動的一方,在此類劇中通常也會配置一個“懼內”的丈夫。
然而這種女性形象的張揚,在近些年電視劇中產影像中愈發劍走偏鋒,并與“大女主”創作趣味合流。所謂“大女主”劇并沒有學術上的周延界定,更多是行業中約定俗成的叫法。簡而言之,這類劇通常以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女性為絕對主角,敘事模式是以該女性從底層平民或人生谷底通過自我奮斗,一步步“逆襲”至巔峰,最終以實現個人目標而宣告劇情結束。這類劇自后宮劇《甄嬛傳》為濫觴,尤以古裝題材為最盛。現實題材電視劇對中產階層女性的表現,也受到這波創作風氣的影響,如《女不強大天不容》《我的前半生》《歡樂頌》等均是在“大女主”電視劇受追捧的市場語境下出現。
應當說,“大女主”中產影像的修辭策略,使女性意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顯和啟蒙,女性價值得到肯定,傳統倫理道德對女性的規訓在這些影像中得到了部分反撥和糾偏,紛雜斑駁的新中產女性形象充盈在當代都市影像中,豐富了女性形象的譜系。但部分劇集在對中產女性意識啟蒙的同時,潛意識中的男權觀念也沉渣泛起,對女性真正的個人成長表現匱乏,女性意識和男權邏輯呈現為“在場的缺席”和“缺席的在場”兩種話語密碼,男權社會的道德秩序和倫理規范在潛移默化中發揮著作用,“大女主”們開啟“主角光環”的背后,依舊是男性角色的強大助攻。例如,電視劇《我的前半生》中,羅子君在丈夫出軌離婚后,這個與社會脫節多年的中年女性,瞬時陷入了情感與生活的雙重困境。為了走出陰霾,羅子君在被動中開啟了自己的奮斗歷程,該劇也將羅子君的成長作為全劇探討的命題。進入職場后,羅子君一路順風順水,在短時間里迅速適應職場節奏,漸入佳境,生活與情感上的困境也煙消云散,但事實上,在羅子君上升過程中的每一步,都伴隨著閨蜜唐晶以及唐晶男友賀涵的幫助與扶持,甚至很多理應由羅子君親歷的錘煉和改造,也被創作者巧妙避開,而交由男性角色賀涵來逐個化解。不得不說,這樣的女性成長命題是平面的,表現是孱弱的,其內里則是“灰姑娘”和“瑪麗蘇”的邏輯驅動。可以說,盡管很多電視劇試圖表現中產階層女性通過自身的奮斗“逆襲”,但事實上在大多數電視劇中,男性依舊是這些女性關鍵時刻的“解藥”,女性角色的步步為營也仰仗于男權的“寵幸”與栽培,女性敘事在男權邏輯的語境下發生發展。在一些電視劇中不少女性形象甚至呈現出近乎無所不能的特點,其“神性”特征掩蓋了其本色的人性特質,這其實是在虛假情境中弱化了對女性地位和存在境遇更有價值的思考,就其本質而言則是女性全貌的被遮蔽。
四、告別悲劇:“溫暖現實主義”的批判無力
享樂主義價值觀的盛行,不僅帶來了電視劇中“中產趣味”的肆意擴張,也帶來了中產影像審美風格的集體轉型。一個典型癥候就在于,在電視劇中產影像中,悲劇意識逐漸缺席,輕喜劇元素以泛在化姿態出現,本應真實展示現實生活、表現中產階層神話背后真相的電視劇,越發在不疼不癢的喜劇式大團圓中,獲得虛假的滿足。用學者戴錦華的話來說,是對現實主義進行了一種“情節劇式的遮蔽”。而與之相呼應,“分享艱難”、強調痛感敘事的現實主義悄然退場,取而代之的則是以快感消費為主導的所謂“爽劇”模式盛行,一種被稱為“溫暖現實主義”的創作論調甚囂塵上,為這種避重就輕書寫現實的中產影像披上了一層冠冕堂皇的保護色。
有學者認為,當下電視劇正在進入一種“輕時代”,“這個輕主要體現在基本上都是輕喜劇,一本正經、嚴肅端莊的劇不太容易被看好,收視率好的大部分是輕喜劇風格的作品,它有喜劇性,有喜劇狀態、喜劇情調”[5]。盡管“輕時代”并不是周嚴的學術界定,卻大致描繪出了當下電視劇的一種審美趨勢。調性的輕盈、輕喜劇元素的內置,普泛化于當下多種類型電視劇的創作中,包括都市題材、農村題材、古裝題材等,而尤其在表現中產階層為形象主體的都市題材中,這種風格最顯突出。
包括《奮斗》《我的青春誰做主》《媳婦的美好時代》《婚姻保衛戰》《咱們結婚吧》《大丈夫》《裸婚時代》《好先生》《辣媽正傳》《男人幫》等在內的大量中產階層影像,都呈現出了輕喜劇化的審美取向。這些電視劇普遍追求臺詞對白詼諧幽默,情節設置無關宏旨,視聽風格明亮輕快,讓觀眾在一種輕松愜意的審美心境中觀賞劇集。應當說,在當下焦慮情緒構成時代癥候的語境下,適度的輕喜劇元素,可以相對紓解大眾的情緒,讓工作勞動的民眾緊張一天的神經得到舒緩,這多少具有正向建構意義。但當這種輕喜劇元素開始喧賓奪主,甚至不求題材、情境匹配度,泛濫成災地介入到創作中時,就不得不值得警惕了。
從另一個面向來看,當這些表現中產階層的影像以輕喜劇風格出現時,就在嬉笑打鬧中消解了現實的沉重感。當前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改革也進入深水區,各種矛盾浮出水面,利益博弈此消彼長。對于成長中的中產階層來說,同樣面對著各種現實的“不能承受之重”。但在這些中產影像中,現實中的真問題難尋蹤跡,一些創作者不再觸碰真問題和“硬骨頭”,回避錯綜復雜的現實矛盾,即使對這些問題偶有涉及,也多是在輕喜劇的風格下蜻蜓點水式的化解,抑或隔靴搔癢地閃爍其詞,劇中復雜的社會畫卷常常淪為可有可無的背景。此類劇集在臺詞上追求段子式的對白,表演上偏愛過度夸張的漫畫式風格,情節上高度依賴巧合、誤會,人為制造戲劇沖突,為了喜劇效果不惜犧牲邏輯真實與細節真實,而故事也最終在兜兜轉轉后,以大團圓的方式為觀眾安放起情緒的釋放與宣泄空間。顯然這種表現中產階層形象的現實題材劇,很難被視為真正的現實主義,甚至有懸浮離地的“偽現實主義”的傾向。
輕喜劇元素大舉在電視劇中粉墨登場,必然迎來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的退場。在諸多審美范疇中,悲劇由于對人性、社會的矛盾與沖突有著力透紙背的展示,通常具備其他審美范疇難以比擬的情感沖擊力和思想深刻性。“任何一種審美文化,如果缺少了悲劇,那它就失去了一種最具表現力的審美范疇,它不但在藝術上變得單調貧乏,而且在文化上多少有點‘病兆’。因為這樣的文化失去了自我反思與批判的沖動,喪失了以悲劇這種獨特方式來凈化主體心靈的可能性。”[6]而隨著大眾文化和消費社會的降臨,享樂主義成為世俗社會所推崇的新宗教,大眾文化娛樂至上和消遣屬性決定了悲劇意識成為多少“不合時宜”的存在,而對于人性真實磨難與處境的過多展示,也不可避免會沖擊意識形態的合法化資源,因此,悲劇性作品在審查環節也面臨著進退維谷的尷尬境地,在多種合力主導下,告別悲劇成為文藝創作的新趨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喜劇性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主導類型”[6](316-317)。
隨著悲劇意識與悲劇精神的消退,對現實題材的書寫不可避免地成為單向度的敘事。然而近年來所謂“溫暖現實主義”的概念開始出現,成為一些電視劇回避現實苦難的“遮羞布”。對于這個概念,并沒有學理性的界定,更像是在市場與創作者合謀下,聯手打造出的一種營銷概念,其本質也是某種話語圈套。對于現實主義的概念,中外藝術創作者和文藝理論家多有界定,但無論是從哪個層面來定義,現實主義包含的三個基本價值立場是不變的:一是真實性,即按照生活的本來面貌來描寫;二是典型性,這是從藝術形象刻畫的層面而言;三是批判性,這是從與現實的關系而言,應該大膽暴露現實問題,揭示真相。因此,從現實主義批判性的本體層面來看,為之加上“溫暖”的定語,這本身就存在二元對立的悖論性。
從真實的創作情狀來看,現實主義應當呈現社會中的“真善美”,既可以展示社會問題,也可以發掘生活中的溫暖,但首要前提和基礎在于真實。“溫暖現實主義”隱藏的邏輯則是“善”字優先,倫理評判先于創作邏輯,當創作者在對現實書寫之前,已經預設了“溫暖”的意識形態,就無疑給自身回避現實矛盾、掩蓋社會苦難、粉飾浮華圖景,找尋了絕佳的庇護。很大程度上說,我國當下的現實題材電視劇影像,尤其是中產影像并非不夠溫暖,而是太過“溫情脈脈”,大部分劇作均停留在對生活的淺層掃描,對于真正的社會問題和生存困境卻閃躲回避、不敢直視,甚至用一種濫情的方式強行拔高升華。這固然有面臨審查的剪輯因素存在,但更多的是電視劇創作者甘于在中產話語泡沫中精神放逐,這可以被看作是近年來現實主義創作中的一種“癌變”,理應引起電視劇創作者們的警惕。
五、結 語
應當說,當代中國電視劇對于中產階層形象的塑造和想象不乏亮點,這些作品在人物塑造、敘事激變和審美現代性反思等層面,基本秉持著現實主義的創作態度,刻畫出中產階層在欲望中的沉浮和救贖。但就更多的電視劇作品來說,則陷入形象塑造的單向度,敘事配方式與套路化,謳歌感官欲望,張揚享樂主義,以情節劇式的輕喜劇和大團圓沖淡應有的悲劇精神等,這些問題在當下電視劇中俯拾即是,令人堪憂。而這些創作面貌對中國中產階層的健康培育很難起到積極正向的作用,這都是值得創作者深思的命題。
目前,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推進和物質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發展與壯大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已經成為主流話語的內在訴求。可以想見,我國現實題材電視劇主創團隊將會更多聚焦于這個群體,而在新時代的背景下,如何在影像中準確書寫我國中產階層的精神面貌與生活狀態,將是我國影視創作者責無旁貸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