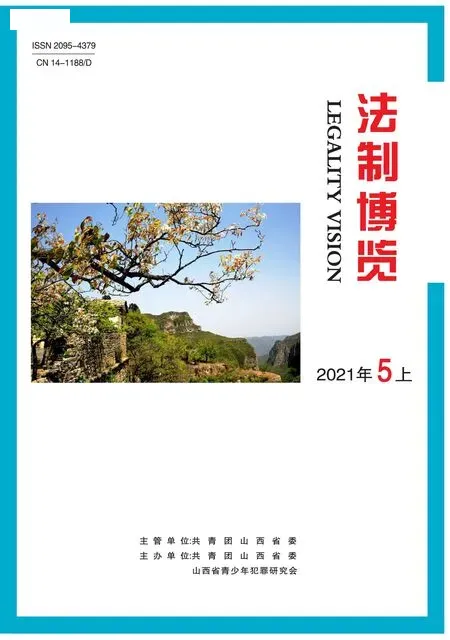“套路貸”犯罪的刑事法律規制研究
鄧懋豪
(云南財經大學法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1)
一、“套路貸”犯罪概述
(一)“套路貸”概念
“套路貸”并不是法律概念,而是網絡環境下對非法貸款的一種稱呼,但由于“套路貸”具有高度概括性質,已經被“兩高兩部”采納,并出臺《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指出“套路貸”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以民間借貸為名,引誘和逼迫被害人簽訂借貸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額度、惡意違約等方式形成虛假債務關系,并利用司法訴訟為威脅,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違法犯罪行為。
(二)“套路貸”特征
相比其他貸款方式而言,“套路貸”有著相應特征:一是隱蔽性,“套路貸”時常披著合法外衣、行非法之實,利用無息、低息等方式吸引客戶,誘騙被害人簽定借貸協議,看似屬于民間借貸行為,實則是為了侵犯被害人財產,但整個過程不易察覺,諸多被害人落入陷阱;二是連續性,“套路貸”從放貸、中介、擔保、討債都經過嚴密設計,不同環節都有專人負責,違法犯罪行為具有連續性。同時,“套路貸”往往侵犯多個被害人,犯罪行為具有持續性;三是團伙性,“套路貸”涉及環節較多,不同環節都具有相應的負責人,往往都由專業犯罪團伙負責運營,在內部劃分“介紹人”“業務人”等多個角色,團伙成員分工明確、各司其職。
(三)“套路貸”分類
“套路貸”違法犯罪行為復雜多變,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進行多種分類:一是根據討債方法進行劃分,分為騷擾類和暴力類,騷擾類是以軟暴力、威脅等方式,逼迫被害人償還不合理債務,暴力類則是以暴力手段反復要求被害人償還虛假債務;二是根據侵犯財產種類不同進行劃分,分為現金類和財產類,現金類直接以侵犯被害人現金為主,要求被害人償還虛假債務或高額債務,財產類則是以抵押物為主,目的是侵占被害人的房產、汽車等貴重物品;三是根據被害人主體進行劃分,劃分為一般主體和學生主體。一般主體是以普通社會民眾為侵犯對象,學生主體則是以學生身份為特定侵犯對象[1]。無論哪種“套路貸”,都已經涉嫌侵犯他人的財產安全,都是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
二、“套路貸”犯罪刑法界定爭議
(一)以詐騙罪定性
在一般情況下,司法機關通常以詐騙罪認定“套路貸”行為,但部分學者卻提出反對觀點,認為詐騙罪存在著被害人自愿行為,而在“套路貸”犯罪中,被害人并不存在自愿行為,是迫于暴力、軟暴力手段才交出財產。但事實上,詐騙罪中的自愿行為并不是劃定罪與非罪的標準,倘若存在自愿行為即構成詐騙罪,而不存在自愿行為并不構成犯罪,顯然不符合立法宗旨,在“套路貸”中,放貸人利用欺騙手段誘使貸款人借款,其目的已經達到,顯然符合詐騙罪的本質,認定詐騙罪并無異議。在我國立法尚未出臺新罪名之前,以詐騙罪認定“套路貸”最為適宜,但隨著“套路貸”行為日益猖獗,國家也可以選擇新增罪名,遏制頻繁發生的“套路貸”行為,最大限度保障公民的財產安全。
(二)以非法拘禁罪定性
非法拘禁罪看似與“套路貸”關聯不高,但在部分“套路貸”案件中,犯罪分子利用暴力手段催收,甚至以脅迫的方式將被害人強行帶至某處地點看管,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就涉嫌觸犯非法拘禁罪[2]。在“套路貸”司法實踐中,以非法拘禁罪論處的案件并不多見,但依然不能切斷“套路貸”與非法拘禁罪的關聯,并且最高法曾出臺司法解釋,認定以索要不被法律保護的債務而非法拘禁他人的行為,以非法拘禁罪論處。顯然“套路貸”屬于不受法律保護債務的一種,倘若放貸人實施非法拘禁的行為,就應該以非法拘禁罪論處,倘若放貸人索要的財產金額遠遠超過債務本身金額,也可以以綁架罪論處。值得注意的是,倘若放貸人以暴力、威脅方式,向被害人或親屬索要財物,以非法拘禁罪論處,但如果以殺害或傷害被害人為借口,向親屬索要財物,可以以綁架罪論處。
(三)以尋釁滋事罪定性
目前,以尋釁滋事罪定性的“套路貸”也并不多見,主要是在部分案件中,放貸人對被害人實施了毆打等暴力行為,或利用嚴重的軟暴力行為,嚴重影響被害人的正常生活。比如在被害人門外噴漆,在被害人樓下叫罵等,不僅侵犯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對社會公共秩序造成破壞,也會被認定尋釁滋事罪。但是,在多數司法實踐中,司法機關認為軟暴力是“套路貸”的一種常見行為,是“套路貸”的構成要件,并不會針對軟暴力行為進行單獨定罪,普遍將整個過程認定為詐騙罪,僅有少數司法案例以詐騙罪、非法拘禁罪、尋釁滋事罪數罪并處。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由于“套路貸”行為日益猖獗,司法機關應該加大打擊力度,合理利用現有法律法規,更廣泛地采用數罪并罰方式,加大對“套路貸”的打擊力度。
三、“套路貸”犯罪刑法規制完善對策
(一)積極出臺指導意見
面對“套路貸”愈演愈烈,我國現行法律對“套路貸”的規制并不完善,即便查處了大量的“套路貸”犯罪行為,但關于“套路貸”定罪和量刑并未明確。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應積極出臺指導意見,針對“套路貸”行為定性和量刑出臺司法解釋,為地方司法機構在審理“套路貸”案件時提供明確指導,減少區域之間“套路貸”案件定罪量刑不統一現象[3]。同時,司法解釋應結合實踐中“套路貸”案件,細化“套路貸”司法規制細則,找出“套路貸”案件規律,以明確的法律規范實施精準打擊,既要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要讓涉嫌“套路貸”違法犯罪行為得到應有的處罰。
(二)增設非法放貸罪
“套路貸”屬于非法放貸的一種,容易與民間借貸行為混淆,應增設非法放貸罪,準確區分合法放貸與非法放貸界限,針對民間借貸經營行為、管理行為、交易行為予以明確,以嚴格的程序防止合法民間借貸朝著非法方向發展。可以參照我國香港特區《放債人條例》,要求從事信貸服務的機構及組織必須依法注冊登記,凡違反合法放貸程序的機構都將被取消信貸服務資質[4]。同時,涉嫌“套路貸”行為一經查處,該機構的管理者、經營者及行為實施者均要受到法律處罰。除此之外,“套路貸”中非法討債行為對被害人合法權益侵犯嚴重,非法放貸罪要明確討債行為時間、方式、程度,一旦超越法定討債程度,就將被認定為非法放貸罪。
(三)妥善處置涉案財產
一直以來,我國對“套路貸”的財產界定都存在不明確的現象,時常將合法財產、個人財產都認定為涉案財產,司法機關在審理“套路貸”案件中,要充分利用查封、扣押等手段,及時凍結放貸人財產,并通過全面的調查,合理區分合法財產與非法財產,對偵查過程中尚未追繳到案或未能足額退賠的違法所得記錄在案,要求司法機關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責令退賠,彌補被害人的損失[5]。此外,檢察機關也要構建常態化的監管機制,針對在偵查、起訴、執行等階段的財產進行常態化調查,利用健全的制度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妥善處置涉案財產。
四、結論
近年來,“套路貸”給司法實踐造成了極大的問題。由于我國刑事立法中關于“套路貸”的相關規制尚不健全,不同地區對待“套路貸”的懲處方式存在不一致,是單獨以詐騙罪論處,還是配合非法拘禁罪、尋釁滋事罪,在學術界和司法實踐中都存在爭議。對此,我國要完善“套路貸”犯罪刑法規制,進一步明確“套路貸”犯罪刑法規制,最大限度減少或消除“套路貸”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