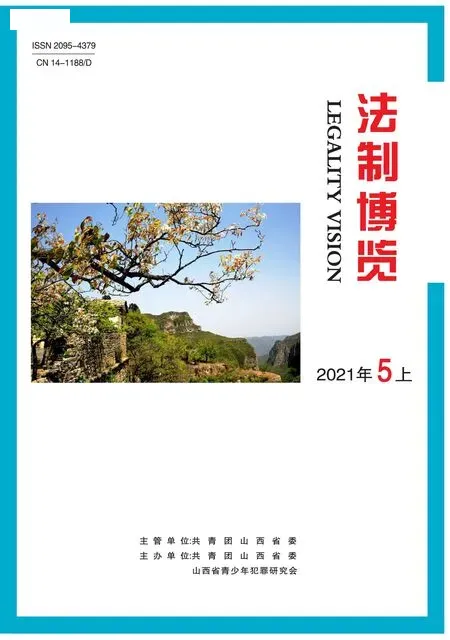合同任意解除權的使用條件、現實問題及完善措施
杜 璐
(中鐵一局集團物資工貿有限公司法律合規部,陜西 西安 710043)
一、合同法中任意解除權概述
“任意解除權,從本質上來說就是法定解除權的一種,因而它擁有我國一般法定解除權的特征”[1]。根據《合同法》的相關規定,合同雙方的每一方都有權解除合同。但是合同任意解除權與合同其他傳統法定解除權相比較來說,其特點還是非常顯著的,即不以合同對方違約或者不可抗力為前提,而是按照一方當事人自己的意愿而單方解除合同。然而,傳統法定解除權卻要求,只有合同在受到各種因素影響導致無法落實時,合同主體方可提出解除合同。當然,合同任意解除權也有一定的適用范圍,在我國法律大環境下,任意解除權一般用于委托合同、承攬合同、不定期租賃合同、無期限倉儲合同、無期限保管合同、貨物運輸合同等。
二、《合同法》中的任意解除權的行使條件
(一)限制合同任意解除權范圍
合同任意解除權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于合作一方的任意解除合同,導致被解除方可能會產生經濟損失,因而這對被解除方來說是相對不公平的。在實踐中為了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因而需對合同任意解除的適用范圍作出限定,以限制一些別有用心地利用合同任意解除權中存在的漏洞滿足自己的私利。比如同為經營物資設備租賃的公司,A公司指使他人以承租人的身份與B公司惡意高價簽訂未約定租賃期的不定期租賃合同,后又行使任意解除權,使B公司喪失了其他商業機會,減少了收益,達到了A公司惡意競爭的目的。
(二)任意解除權的使用時間
“按照《民法典》規定,任意解除權在使用時根據合同不同類型稍有區別。比如無期限倉儲合同,法律明確規定應給予必要的準備時間,不定期租賃合同應當在合理期限前通知對方。再比如委托合同、承攬合同等,法律規定可以隨時解除合同,但在實踐操作上,還是應給對方充足的處理后續工作的時間”[2]。綜上可見,我國相關法律已就任意解除權的使用時間做了比較明確的規定,但是我們也需看到,這方面還應進一步細化、補充和完善。
(三)任意解除權使用主體
任意解除權的使用主體會因合同類型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比如倉儲合同、不定期租賃合同、委托合同。合同雙方均可行使,這是因為合同簽訂的基礎就是雙方的相互信任,因而雙方都擁有任意解除權。但是,如果合同的簽訂是建立在單方信任的基礎上,那么實際上單方擁有任意解除權是相對公平的,比如承攬合同。
三、合同法中解除權運用存在的問題
(一)合同任意解除權存在濫用的現象
鑒于合同任意解除權的特殊性,權利人在使用時應本著誠信的原則,在使用之前應先通知對方,再合理合法地使用,這才是任意解除權使用的基本程序,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發揮任意解除權的真正作用。在實際操作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有些合同主體忽視法律的相關限制條件,隨心所欲地使用該權利,任意解除權成為“任性”解除權,這種濫用權利的做法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應由當事人獨自承擔。就我國當前的法律大環境來說,合同任意解除權的實際應用條件仍需進一步完善,相關細節仍有待于補充。因此,當前合同任意解除權的濫用事件已經嚴重違背了合同任意解除權的最初目的,更難以體現法律的公平公正,這個問題地解決已然迫在眉睫。
(二)約定合同任意解除權的問題
在實踐中,倉儲合同、租賃合同的期限往往是該類合同的重要元素。一般當事人都會約定明確的合同期限,反而約定了明確期限的倉儲合同、租賃合同無法使用任意解除權,而承攬、委托合同即使不在合同里約定也可使用任意解除權。
(三)任意解除權后賠償問題
一旦出現合同糾紛,那么當事人在使用任意解除權解除合同及合作關系后,還應承擔后續的賠償損失,唯有如此,才能維護另一方的合法權益。但是,我國《合同法》中并沒有就任意解除權使用后的賠償問題作出明確細致的規定,包括損失程度如何劃定,損失賠償標準等,這就導致合同任意解除權在實際使用時出現各種問題,使該項權利使用后無法發揮救濟作用。尤其是當受損失一方所得的賠償較少,難以彌補其損失時,實際上任意解除權就相當于變相地損害了合同一方的權益,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公平公正更加難以體現,也違背了立法初衷。
四、我國《合同法》中任意解除權問題完善措施
(一)針對任意解除權行使作出詳細的限制條件
“在我國目前法律環境下,合同任意解除權的使用仍存在相當大的隨意性,當事人的自主性極強,因此這實際上是違背合同任意解除權的初衷的”[3]。因此,當前我國應就任意解除權的使用作出相應的限制,制定詳細、符合我國實際的限制條件,避免各種不公平現象的發生,避免當事人的正當權益受到損害,進而影響法律的公平公正和人們對法律的信心。因此,按照合同的類型,制定相應的任意解除權的使用限制條件。比如任意解除權的使用時間、使用條件等,這些內容的細化、精確化,可有效控制任意解除權的任意使用現象。合同雙方當事人在使用任意解除權之前會詳細參考相關限定條件,在使用之前會更加慎重、小心。除了限定當事人的任意解除權的使用,更重要的應該是從合同簽訂之初就進一步加強合作雙方的信任、信賴,并明確規定一旦一方隨意破壞合作關系,那么另一方有權拒絕解除合同,要求繼續執行合同相關約定。
(二)明確任意解除權的適用范圍
任意解除權的適用范圍主要是因合同類型、行業性質的不同而產生合同雙方適用及合同單方適用。“《民法典》已明確規定的無期限倉儲合同、不定期租賃合同、委托合同,合同雙方均可行使,承攬合同的定作方、貨物運輸合同的托運方等則是只有固定的一方可行使”[4]。但在實踐中,仍存在雖法律無明確規定但仍實際使用了任意解除權的情形:比如消費者在天貓店鋪采購服飾時店家的七天無理由退貨,消費者只要保持服飾的完整無損、不影響店家二次銷售,便可享受店家賦予的“任意解除權”,加上能讓消費者免運費的“運費險”,這種銷售模式使消費者打消顧慮、大膽采購,促進了網絡購物和銷售,對消費者和店家是雙贏;也存在雖無實際應用但適用任意解除權存在必要合理性的情況:如旅游業,旅客在與旅行社簽訂合同之后,旅客出于各種原因要求終止合同的履行。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旅行社仍堅持游客履行合同,那么旅客的合法權益必然受到損害,旅行社也會因此造成資源浪費。筆者認為可以參照“七天無理由退貨”模式賦予旅客隨時使用任意解除權的權利,旅行社因此而遭受的損失,游客可做出相應的補償,可以活躍旅游市場,拉動經濟發展。但實踐中這種無名合同卻實際上限制了旅客任意解除權的使用,從而衍生出大量的糾紛。當然,不論哪種類型的合同,賦予其任意解除權時均應就使用條件做出明確的規定,以防合同成為一種無意義的形式,其法律價值和威懾作用無法充分發揮出來。
(三)要明確合同解除賠償標準
合同任意解除權在被使用后,為了更好地維護法律的公平公正,以及權利行使的合法性,權利使用人應對合同被解除方做出相應的賠償,以更好地維護被解除方的合法權益。因此,我國應就相關的賠償標準做出更加細化、更加科學合理地設置,從而更好地調解因為合同而產生的各種糾紛問題。
總而言之,當前我國合同任意解除權的使用還存在種種問題,任意解除權的使用存在一定程度的隨意性,缺乏相應的賠償標準,任意解除權的適用范圍還需進一步細化等,這種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著法律的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無法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使其遭受不合理的損失。當然,上述種種爭議性較強的問題至今仍未達成共識,還需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并在此基礎上制定更加完善的措施和法律條文,使我國的法律體系更加完整,法律更加公平公正。